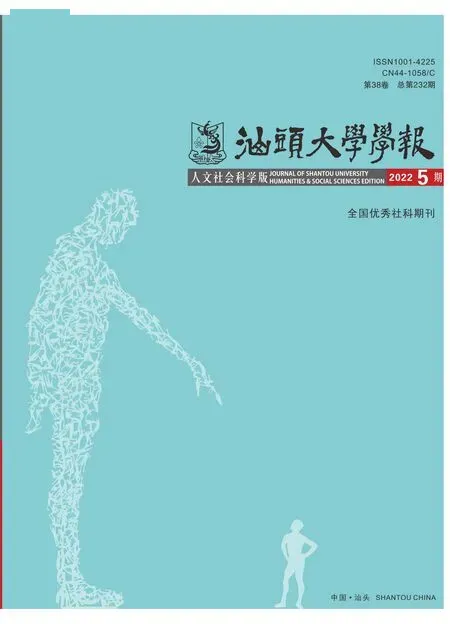被压抑的现代性
——晚清小说《催醒术》解读
马 龙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1909 年10 月,《小说时报》创刊号发表了一篇署名“冷”(真实身份为著名报人陈景韩)的短篇小说《催醒术》,其在学术接受史中通常与现代文学大家鲁迅创作的《狂人日记》进行并举论述。范伯群先生率先注意到这篇晚清小说与《狂人日记》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并撰文加以说明,文章指出陈景韩的构思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及有关杂文不无相通之处,但就深刻的程度与艺术性的高下而言,《催醒术》与《狂人日记》相比当然是有很大差距的。[1]这篇首开先河的文章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带来不小的影响与启示,如禹玲的《从1909〈催醒术〉到1918〈狂人日记〉》就此“顺藤摸瓜”,进一步考察了鲁迅早期著译的文风如何受陈景韩“冷血体”的影响,以及二人在国民性批判方面的思想相通处,兼及两部作品中“狂人”形象的对比分析,从中透视中国近现代转型期文学的内在联系与突进性的嬗变。[2]毋庸讳言,这种比较的研究方法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价值,但鉴于《狂人日记》的巨大影响力,使得《催醒术》在实际展开的比较研究中总是被置于“第二性”的论述位置,并被相当一致地赋予“无论从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技巧而言都逊色于《狂人日记》”的价值判断。虽然这一判断可能是基本事实,但笔者担心的是,比较的研究方法也实际制造了一种无形的“压抑机制”,使得《狂人日记》成为阐释《催醒术》这部小说总也绕不过去的重要参照系,甚至僭越其上成为研究者新的论述主体。如果摆脱了《狂人日记》,《催醒术》还能以何种形态被呈现出来①李文倩、陈辉的《晚清启蒙者的焦虑性生存——〈催醒术〉的叙述学解读》是目前仅见的单独论述《催醒术》的研究文本,但这篇文章选择的角度有限,论者仅从叙事学层面对这部小说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参见李文倩、陈辉:《晚清启蒙者的焦虑性生存——〈催醒术〉的叙述学解读》,《明清小说研究》,2007 年第4 期。?这篇诞生于清末的作品除了“与《狂人日记》相似以及与之相比在思想艺术上略显逊色”外,是否有它基于自身的艺术独特性?带着这样的疑问出发,本文对《催醒术》进行细读,力求全方位、多层次地对这篇作品的创作动因、思想主题、诞生的历史语境等问题加以把握,以期摆脱长期负载于其身的“比较”阴影。
一、创作的动因:陈景韩为何要写下《催醒术》?
作为清末民初上海报坛的知名报人,陈景韩曾先后担任《大陆》《时报》《申报》主笔,在近现代新闻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①关于陈景韩在新闻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可参看余玉:《陈景韩新闻思想及影响探析——以上海〈时报〉为中心的考察》,《新闻大学》,2020 年第3 期。,同为报人的曹聚仁对他评价甚高:“在近代中国报业史上,以往如梁启超、章太炎、宋教仁、于右任等以学者出而办报,声光炳然,但他们都是‘政论家’,直到陈景韩出现,才是一本正经的报人。”[3]161与此同时,陈景韩还于文学界辛勤耕耘,主编《新新小说》和《小说时报》,担任《月月小说》的特约撰稿人,翻译、创作小说共达118 种②根据李志梅的统计,在目前发现的陈景韩118 种小说中,可确定为翻译小说的有77 种,余下的41 种为原创小说。参见李志梅:《报人作家陈景韩及其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成为当时高产的作家之一。作为陈景韩众多的文学成果之一,《催醒术》在今天尤其值得注意,这不仅因为它足够与《狂人日记》这一公认为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典范之作”相提并论,更是因为它显要的发表位置——《小说时报》创刊号首篇。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起因,作家本人并未留下相关的文字说明,但结合彼时现有的一些情况,仍可对其进行有效的推论。
若论《催醒术》的诞生,不得不先谈《小说时报》的创刊。作为一份以刊载小说为主的专业文学刊物,《小说时报》1909 年10 月创刊于上海,由小说时报社编辑发行,有正书局担任发行所,狄保贤主办,陈景韩、包天笑任主编。刊物的名字已然表露出其与《时报》(晚清上海“三大报纸”之一)的密切关联,事实也的确如此。正是因为《时报》开设的“小说”专刊无法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所以出版商狄保贤决议创办一份专门刊载小说的杂志,并拉来他的两员心腹爱将——《时报》馆的两位主笔陈景韩与包天笑一起合作,《小说时报》才得以最终问世。[4]既然陈景韩为《小说时报》的主笔,那么为自己主编的文学刊物撰写小说、提供文学作品似乎顺理成章,但考虑到这一刊物在创刊时并不存在“发刊词”,而将《催醒术》列为创刊号首篇,说明作为主编之一的陈景韩实有将其作为代“发刊词”的重要考量。于是这一作品在《小说时报》的出现,便不能如此简单视之,而要结合陈氏本人的小说观念进行详细分析。
陈景韩虽然翻译、创作小说多部,但他本人却很少发表对小说的看法,如今所能见到的仅《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一文,原载1905 年5 月27日和同年6 月8 日的《时报》。文章上半部主要针对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进行三解:一是认为小说要想发挥开通风气的效用,必须具备有味和有益两种原质,“有味而无益,则小说自小说耳,于开通风气之说无与也;有益而无味,开通风气之心,固可敬矣,而与小说本义未全也”。[5]167二是论者以为要根据社会问题来撰写小说,“知其流弊,而用其矫正之术,是在提倡小说者之善察社会情形而已”。[5]167三是社会情形毕竟是复杂的,众人的观点也难免不一,于是小说在选择社会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大多数人都认同的观点,关注与社会时势最密切的,并且有利于外界竞争的问题:“则惟当以国民最多之数,与乎时势最急之端,以及对于外界竞争最有用之三者,以为之准已耳。”[5]168文章下半部重点论述彼时小说创作宜提倡的三点:当补助我社会智识上之缺乏,当矫正社会性质之偏缺,当提倡“复仇之风”和“尚侠之风”。[5]169-170可以看出,陈景韩在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这一问题上与先前提倡“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等人达成了一致,但他的超越之处在于并未对小说的“文学性”有所偏废,“益味”观的提出表明他仍然关注小说的趣味性、可读性,一言以蔽之,小说在他眼里更像是“有益于社会启蒙的趣味读物”。
综上,陈景韩素来秉持“社会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小说理念,加之狄保贤聘用他担任新刊物《小说时报》的主笔,于是他便写了一篇趣味横生、启蒙意味浓厚而篇幅又较为简短的《催醒术》作为此刊的发刊词。《小说时报》后续刊载的大部分小说既有以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语言运用生动有趣取胜的《噫有情》《百万英镑》和《赛雪儿》,又有影射当时社会、以期对社会产生直接影响的《镜台写影》《新造人术》《巴黎断头台》等,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将“趣味”与“启蒙”完美融合的《催醒术》正是陈景韩为《小说时报》精心创作的发刊词。如果结合下文将要对《催醒术》展开的具体分析,亦能得知这篇小说当为作家本人上述“小说”观念的一次集中性的文学表达。
二、启蒙的寓言:一种解读《催醒术》的有效方式
既往学界在阐释《催醒术》这篇小说时,通常以象征(或象征主义)的解读方式为主,如范伯群先生认为它至少是用象征手法所记下的一天的经历,称它为《狂人手记》亦可,陈景韩用象征的手法,写出当时先进分子觉醒后的孤军奋战与内心苦闷。[1]禹玲通过对《催醒术》和《狂人日记》的比较研究认为前者使用的是单纯的象征与隐喻,而后者是复调的隐喻与系统的象征。[2]从象征的角度进入本篇小说的确是一条切实可行的研究路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作者所要传达的核心思想与内在情感,但需要注意的是,象征手法的运用在不同的小说那里也存在着明显区别,正如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哈南在比较《红笑》和《狂人日记》的象征时所指出的:“《红笑》的象征是神秘的,像诗的隐喻,没有点明,而《狂人日记》的象征尽管十分有力,却是理性控制的,点明了的,一句话,是寓言式的。”[6]306哈南在这里提出的“寓言式”这一说法给予了笔者启发,或许可以换一条进入小说文本世界的途径,即从寓言而非象征的角度重新解读《催醒术》这篇小说。
相较于“象征”,“寓言”理解起来似乎没那么复杂,美国学者杰姆逊在北大举行学术讲演时曾为“寓言”下过一个精彩的定义:“所谓寓言性就是说表面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希腊文的allos(allegory)就意味着‘另外’,因此故事并不是它表面所呈现的那样,其真正的意义是需要解释的。寓言的意思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再写一个故事。”[7]117由此可知,寓言是用一个表面的故事表达一种更为内在的、隐秘的意义,寓意是其本体,而作为外在形式的故事是其寓体,二者之间是一种类比式的关系。我们之所以能够把一部小说称作“寓言”小说,正是着眼于这部小说的表面故事与它所传达的意义之间的关系,而本体与寓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那样总是同一和谐的,二者各自独立,以类比的形式存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构成断裂或龃龉。如果借用转换生成语法的概念,那么小说的表面故事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表示为其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关系。在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框架内,现实主义小说文本与现实经验世界总是存在着直接对应的认知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寓言性质的小说中通常找不见。从这个意义上讲,《催醒术》就是一篇典型的寓言式小说,其所传达的意义和表面故事之间存在张力,小说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存在某种裂痕。
《催醒术》的基本故事是这样的:主人公“我”在某天被人用竹梢一指,仿佛脱胎换骨般获得新生,一切全都变得豁然开朗。被“催醒”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竟然满身污浊,连忙赶回家洗濯。后来有友人来访,“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与我此前的状态一般无二,经过一番劝说,“我”终于也能帮他们清洗身体。这时的我已经疲惫不堪,想要寻求仆人的帮助,却发现仆人的身体更是肮脏过甚,我不得不感叹:“予欲以一人之力,洗濯全国,不其难哉?”[8]朋友和仆人听到这话,却笑我是发了狂。这时的我听到屋外有哭声,连忙跑出去救助,但朋友们全听不到,还一致认为我得了精神病。我走在大街上,看到巷子里全是苍蝇、死鼠、坏蛆,秽臭之气扑鼻而来,而其他人并无任何感觉。走进一家饭馆后,我又发现别人吃着发馊的饭菜、受着蚊虫的叮咬却依然安之若素。小说的结尾,我只能无奈地叹息,“催醒术”虽然使我耳聪身捷、心明眼亮,但也让我劳苦不堪、痛苦万分,不知那施术之人为何只催醒我一人?于是,我决定去找寻那手持竹管的施术人,可是遍寻各处无果,那人已消失无踪。
以上是小说叙述的表层结构,即作为外在形式的故事,主要展现了一个不被外界所理解的狂人(或者精神病人)的“疯”言“疯”行,他不仅说的话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具体的行为也不被外人所接受,深层结构则反映了一个启蒙者被“启蒙”之后转而拯救大众(蒙昧者)的详细过程。污浊的身体和肮脏的巷子、酒馆分明是国民劣根性及腐败黑暗社会的生动隐喻,而为友仆清洗身体、救助贫弱孤者这些在小说中的外人看来完全不合逻辑的行动举止,在寓意层面上皆可看作这位启蒙者实际的启蒙行为,或者说是为了拯救庸众而付出的现实努力。可悲的是,“我”的这些做法却只能换来“群笑予为狂”和“彼殆病神经”[8]。这里所展现出的“我”和“大众”之间的对抗性存在,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大量存在于鲁迅小说中的将“独异个人”与“庸众”并置的这一原型叙事形态。“独异个人”和“庸众”是鲁迅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两种形象,甚至可以由此为他们建立一个“谱系”。[9]7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晚清小说家的陈景韩与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建立起联系。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鲁迅《狂人日记》的过程中,有不少学者也已经注意到其中的寓言性特征,如美籍学者林毓生说过:“他采用了果戈理那篇作品中所没有的寓意技巧,给狂人的话赋予一种双重的含义。他使用了精神分裂症的现代心理学概念,使这个故事从表面上看完全是写实,实际上这篇小说是作者以寓意手法对中国传统所进行的控诉,而且这种控诉并不局限于中国传统的某一特定方面,而是遍及中国的历史整体。”[10]184王富仁也指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将疯子的病理过程的描写作为小说的艺术结构,把精神叛逆者的思想历程的表现作为小说的意义结构,通过将这两种结构相统一,小说象征性地表现了中国现代的启蒙者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的孤立处境和痛苦的命运,表现了他们的思想成长过程和艰难的挣扎”[11]108-111。还有范伯群和曾华鹏在《鲁迅小说新论》一书中谈道“除了偏执狂患者的荒谬的逻辑轨迹之外,还有一种经作者严密遥控的富有哲理的内在逻辑轨迹,……这就是鲁迅《狂人日记》奇妙的双轨逻辑。”[12]14《催醒术》之所以能够与《狂人日记》相提并论,在一定意义上正得益于二者极其相通的寓言性质,或者说其如《狂人日记》一般有意于文本内部安置的两层意义结构或双轨逻辑。
在《催醒术》的最后,“我”的哀叹在小说中的外人看来自然是“胡言乱语”,但在寓意层面无疑表现了一种启蒙者的悲哀:先进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觉醒,但无论是言谈还是举止皆得不到世人的理解与认同,并且整个社会的腐朽力量实在太过强大,凭借一己之力究竟能改变这个社会多少?“我”不得不陷入自我怀疑,深深地沉浸在孤军奋战的苦闷之中。于是,“我”决定去找寻当初那个“催醒”我的人,质问他为何要让“我”陷入如此焦虑的境地,只不过仍以失败告终。整篇小说因这位“手持竹梢者”催醒“我”而起,又由“我”找他而终,这位异人从叙事学层面看充当了整个故事的黏合剂[15],而作为一个寓言层面的、更高意义上的启蒙者(能够“催醒”我的人),他的最终消失或缺席,无疑再一次反证了启蒙的无效性,这正与“我”之前发出的哀叹息息相通。记得鲁迅曾在《娜拉走后怎样》那篇著名的讲演稿中提到:“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13]166《催醒术》中的主人公“我”既已“梦醒”,而且也并非“无路可走”,但所走的启蒙之路荆棘丛生,野兽遍布,因此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最终又能走到哪里?不仅是对于“我”而言,更是对于小说家陈景韩而言,都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与作者本人有着很大程度的重合,所以有必要对小说中“我”的形象进行认真研读。在我看来,这一人物至少包含了批判者、行动者、怀疑者等多重形象内涵。首先是作为批判者的“我”。在被“催醒”之后,“我”首先感到的是周围环境的陌生与不堪,作家在这里综合调用视觉、听觉和嗅觉,为彼时的社会生态作了详尽的寓言式注解:“窗楼”“镜”“栉”盥洗具”“室”“桌椅及室中一切物”乃至人的身体全都积满了尘垢(外人看不到),贫弱者“悲以切”“惨与酷”的呼号不时传入耳中(外人听不到),周围秽气触鼻,毁败之气直入脑门,凄然臭气阵阵袭来(外人闻不到)。这里的“我”俨然是尼采超人哲学的忠实信奉者,对周围的一切进行全新的“价值评估”,而这种对于周遭世界之丑恶、污秽的认定,何尝不是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鲜明体现。其次是作为“行动者”的我,既然已经洞察了社会的部分“真相”,那么势必要有所行动。于是“我”不仅打扫干净了整间屋子、帮助朋友仆人清洗身体,更对贫弱孤者施以援手——给予病妇钱财,阻止老妇人动手打女儿。这里体现了一个有良知的启蒙知识分子的责任承担。最后是作为“怀疑者”的我,面对“我”在清洗时力不从心的感慨,友朋仆人却笑我为“狂人”,“我”听到外界的哭声赶去施救却被周围人视为“神经病”,“我”阻止老妇人打女儿,女孩却“大骇”而妇人则“大怒与我斗”。正是这种种不被理解反被误解的行为反复存在,最终导致了“我”在小说末尾的哀叹。这一哀叹不仅包含着对自我(知识分子个人能力)的怀疑,更是对启蒙本身的怀疑。从被催醒(被别人启蒙)到批判与行动(主动启蒙别人)再到最终的哀叹(怀疑启蒙本身),作家很明显地将自我的思想发展历程寄放在了叙述者“我”的身上,正如《狂人日记》曾被解读为“隐藏着鲁迅自身的灵魂履历”[14]106,《催醒术》也不仅仅是一则关于“启蒙”的绝妙寓言,更是作家陈景韩表达自我的一部“精神履历史”。
三、科学的谐仿:从晚清“催眠术”到《催醒术》
在《催醒术》的正文故事具体展开之前,有一段作者本人的自述值得注意:“世传催眠术,我谈催醒术。催眠术科学所许也,催醒术亦科学所许也。催眠术为心理上一种之作用,催醒术亦为心理上一种之作用。中国人之能眠也久矣,复安用催?所宜催者醒耳,作催醒术。伏者,起立者,肃走者,疾言者,清以明事者,强以有力。满途之人,一时若引剧药,若触电气,若有人各于其体魄中与之精神力量若干,而使之顿然一振者。”[8]这段话用“冷(陈景韩的笔名)”的口吻托出,以明确的启蒙意图呈现“我|冷=作者”所能够想象到的“全民皆醒”的美好图景[15]。实际上,这段话也正为我们将正文故事读解成启蒙的寓言提供了有力证据,然而开首提到的“催眠术”却一直为先前的论者所忽略。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作家在此有意将“催醒术”与“催眠术”相对比,并为前者加持上“科学”的外衣,称其和“催眠术”一样是一种心理上的作用,即一种心理科学。虽能明显看得出是戏语,但由此也牵涉出彼时一个极为重要的现实语境——“催眠术”在晚清的广泛传播以及将之视为“科学”的那股思潮。
“催眠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情况,以来华传教士在报刊上的提及、宣传为始。根据贾立元的研究,自1839 年起,与催眠术相关的信息开始出现于传教士在华创办的英文报纸上,如广东《中国丛报》、上海《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但这种传播的效力势必十分有限,因为读者主要限于能够读懂外文的精英群体,汉语读者对此难有真正的了解。[17]甲午之后,“催眠术”一词及相关知识借助日本这一中转站加速涌入汉语世界,通过论著、小说、报刊、民间表演和讲授活动等各种形式,催眠术于国人而言不再是新鲜又陌生的事物,尤其是在1905 年,上海教育会通学所开办催眠术讲习会,由从日本归国的陶成章公开讲授,讲授的部分内容后以《催眠术讲义》为题发表于《大陆》报1905 年第3 卷第7 期至第8 期,这在当时引起一定关注。①比如在徐念慈创作的科学小说《新法螺先生谭》中,“脑电”说的发明就被追究于这一发生于上海的催眠术讲习事件的刺激。而《大陆》报在介绍催眠术方面,可谓不遗余力。继《催眠术讲义》发表之后,本报又于第10 至16 期连载署名“发端”的论说《催眠术论》,且该报编辑江吞等人根据日文书籍编写的《催眠学精理》一书也于同年8 月出版,进一步扩大了催眠术在晚清社会的传播力度。如此或可推测,作为《大陆》报曾经的主笔,陈景韩在《催醒术》开首提到的关于“催眠术”的那套话语,如称其为科学所允者、一种心理上之作用等,很可能就从阅读此报刊登的有关内容得来。虽然在今天,催眠术时与颅相术、请神术等种种伪科学种类放在一起加以讨论[18]125,但在晚清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之下,考虑到知识界对西学基本采取照盘全收的姿态,加之催眠术又与中国知识分子旧有的儒学和佛学修养暗合[19],因此它仍被当作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来接受,并且颇有流行之势。《催醒术》在开篇特意引入“催眠术”,一方面自是以此衬托小说主题的刻意安排,另一方面也是这一新学风行于晚清时代的间接反映。
除了在作者自述中借“催眠术”这一新兴的西学凸显正文将要展开的“催醒”主题,小说中实际描写的“催醒”情节,亦与现实之中(大众一般理解的)催眠术的实施过程彼此照应。虽然催眠术在近代中国获得流布空间,但非专业知识分子对此难有系统或深入的了解,比如梁启超曾将其与鬼学、魂学联系在一起,并以此为灵魂存在的明证:“但彼‘鬼学’者,文言之曰魂学。至今已渐成为一有系统之科学,即英语所谓‘哈比那逻支’(Hypnologic),日本俗译为‘催眠术’者,近二十年来,日益进步,其势且将披靡天下……据其术,则我之灵魂,能使役他人之灵魂,我之灵魂,能被使役于他人之灵魂,能卧榻上以侦探秘密,能在数百里外受他人之暗示。”[20]46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梁启超尚且如此理解催眠术,遑论其他人对这一西方新学的混杂认知。至于催眠术的具体实施过程,其时虽然不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公开表演,但多被传得神乎其神,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讲述的一则“邵阳黄建刚从欧洲习得催眠术”的故事颇具代表性:“邵阳黄建刚尝游欧洲,得催眠术于德国某博士,能以手指人,呼之,人辄迷惘。尝以其术眩于众。”[21]4576在这里,施术人进行催眠的实际过程如同中国古老的法术再现。与之相类似的是,《催醒术》中主人公“我”的“被催醒”过程,亦如晚清大众所理解的“催眠”过程一般宛如神技:“彼忽仰视,见予下观,次又用竹梢向予直指。予惊,予心豁然,予目豁然,予耳豁然,予口鼻手足无一不豁然。予若易予筋,换予骨,予若另成一予。予目乃明甚,一时顿见予向之所未见者。”[8]凭借那位忽然到来的、衣常人衣、服常人服的外来者(施术人),用手持的“竹梢”随便一指,“我”不仅取得了“耳聪目明”的极致感官能力,更恍若易筋换骨、重获新生,这与上文提到的、晚清大众所想象的神奇“催眠术”(以手指人,人辄迷惘)不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么?总而言之,从先前的作者自述到实际的情节展开,作家皆将晚清现实传入的“催眠术”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物,由此构成对这一西方新近科学的戏仿。
如果说通过小说内容的分析可以将《催醒术》视为一部关于启蒙的寓言式小说,那么联系作者本人的自述及彼时的现实语境,又可将其看作一篇专门针对新学“催眠术”而作的、颇为有趣的科学戏仿小说。这种对于“科学”的有意味借用或谐仿,也曾出现在陆士谔创作的《新中国》之中。在这部小说里,医学大家苏汉民也发明一种“催醒术”,“那催醒术,是专治沉睡不醒病的。有等人心尚完好,不过迷迷糊糊,终日天昏地黑,日出不知东,月沉不知西,那便是沉睡不醒病。只要用催醒术一催,就会醒悟过来,可以无需服药”。[22]50在这里,“催醒术”已不再如陈景韩所言是一种“心理科学”,而是作为一种神奇的“医术”存在,并且专门用于治疗国人所患的“沉睡不醒病”。从这一病症中可以明显看出隐喻性含义,作家通过疾病的书写暗示读者注意“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23]55,而专门治疗此病的“催醒术”,自然也摆脱了“科学”(医学)的基础性外衣,成为晚清启蒙主题的象征性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催醒术”虽然在两部小说里分别被赋予“医学”和“心理科学”的不同意义,但实际上却共享着“启蒙”主题的同一性文学表达。
结语
在晚清小说研究史上,海外汉学家王德威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曾备受学界关注。在他看来,较之沉溺于“感时忧国”这类宏大叙事的“五四”新文学,晚清小说包孕着更为丰富多彩的现代性,“比起‘五四’之后日趋窄化的‘感时忧国’正统,晚清毋宁揭示了更复杂的可能”。[16]2本文借用“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一题旨,意在揭示学界在既往的比较阐释中对《催醒术》构成的无形压抑,并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重新彰显这部小说所具备的现代性审美思想价值内涵。通过本文的读解不难发现,《催醒术》因同时包容启蒙与科学这两种现代性话语而焕发出全新的思想价值内涵,“寓言”与“谐仿”两种艺术手段的运用又构成小说所具备的现代性审美内涵的鲜明表征。然而,小说全篇却又使用了文言语体,由此体现出晚清小说独具的、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混杂”特性,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而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又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与此同时,《催醒术》的存在还明确昭示出中国的“狂人世家”是有一个发展谱系的[1],鲁迅创作的《狂人日记》虽然因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被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但我们亦不应忽略在此之前那位出现于民国报刊的、曾经洞察传统历史文化所有精髓的“狂人”在晚清还有一个“孪生兄弟”。这其实也在提醒我们,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早在19 世纪与20 世纪之交就已开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