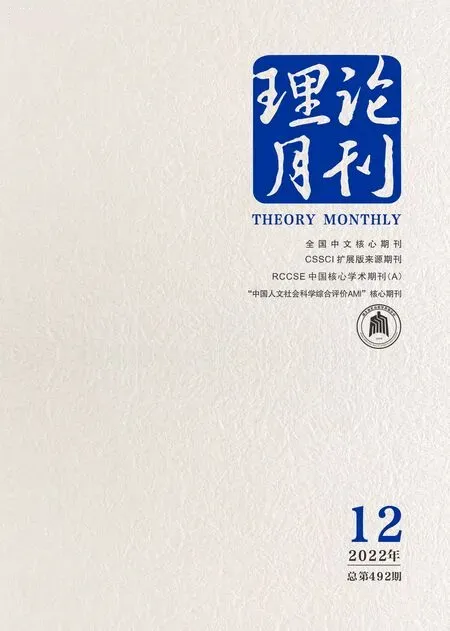“上帝之死”与“元宇宙热”
——一个拉康主义分析
□虞昊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上海 201100)
一、死亡驱力下的“元宇宙热”
2021年3月,首个将“元宇宙”(Metaverse)概念纳入招股书的公司Roblox在纽交所上市,在当下情境中以资本的方式,重新激活了30年前科幻小说《雪崩》(Snow Crash)中的“元宇宙”概念。随后在Meta(原名为“Facebook”)、微软、英伟达、EPIC、腾讯集团、百度集团等公司的推动下,该概念被不断“炒热”。目前,关于元宇宙的讨论次数之多、体量之大、波及之广、热度之高,令人隐隐有见“元宇宙”而不适、谈“元宇宙”而疲倦之感。借助拉康主义开启的分析性视角[1][2],我们可以透过“元宇宙热”及人们对其的倦怠,看到对于元宇宙的追捧与对于元宇宙的倦怠这二者实质上有着共同的根源。由此,我们就能更深层地审视现代人的精神境况,展望未来元宇宙的可能的秩序图景。
依据法国精神分析学者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思想,人与人并非直接面对面地相处,“你”和“我”之间总是存在着“第三者”,即“大他者”(the Other),而日常生活秩序正是源自大他者的“规介”(mediation and regulation)才得以存在。在此,“大他者必须首先被视为一个位点,语言在其中被构建的位点”[3](p274)。就语言的符号性维度而言,大他者即是我们身处其间的以语言为中介的“现实世界”或“符号秩序”(the Symbolic)。但此处存在着双向的“阉割”(castration):一方面,当进入大他者的领域时,主体注定会失去完全的身体性自我并通过语言的中介与之联系,由此“享乐”(jouissance)的“真实”(the Real)就被“阉割”了;另一方面,这又意味着大他者缺失且无法完全地解释享乐,大他者因允许主体的进入而变得不充分了。由此,大他者成了“无根的”(rootless),人皆有越出现实世界及逃离为大他者所规介的符号秩序的冲动,该冲动指向被大他者阉割了的“享乐”,因而就意味着一种否定并退出日常生活秩序的“死亡”。这就是“死亡驱力”(death drive)的含义。
由此观之,“元宇宙热”源于想要越出符号秩序的死亡驱力。“符号秩序中的总体性被称作一种宇宙(a universe)……人的一切要在由符号功能所构成的宇宙中被规定。”[4](p29)元宇宙恰恰是在“me⁃ta-(uni)verse”的意义上构成了对现有宇宙或者说符号秩序的超越,其叙事展现了一种异于现实世界的别样宇宙:更低的响应延迟、更强的游戏沉浸感、更高的用户创造水准、虚拟的经济系统、平等的社交网络、被重构的文明形态……这是元宇宙叙事所描绘的“理想生活”或“最佳秩序”。这一不同于当下日常生活的元宇宙图景,构成了对于现有符号秩序之总体性的超越,意味着越出日常生活的纯粹否定性乃至“死亡”。在这个意义上,元宇宙成为死亡驱力下人的一种“盲目执迷”,并借此获得了话题热度,引发了讨论热潮。
倦怠的产生也源自死亡驱力的“盲目执迷”特性。“通过抓取其对象,驱力在某种意义上学会了这恰恰不是它将被满足的方式。”[5](p167)这即是说,死亡驱力不可能以抓取某对象的方式得到满足,也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其以一种永不停歇、强迫重复的方式朝向对象运动,但并不是为了靠近并获得该对象。故此,当关于元宇宙的讨论形成一股热潮,当网络、算力、人工智能、电子游戏、显示和区块链技术等元宇宙的支撑性技术不断发展,当游戏《我的世界》(Minecraft)、NFT、“希壤”App等被纷纷纳入元宇宙的范畴,当元宇宙在诸公司的推动下被部分性地实现,元宇宙便在实质上临近或进入了现有的符号秩序。此时,元宇宙便不再是死亡驱力所指向的“理想生活”,而成为死亡驱力下人们所要越出的新的符号秩序,再谈论元宇宙便自然会生出倦怠之感。
事实上,当元宇宙作为死亡驱力所指的对象时,其已然发生了改变,且“这是对象就其本质而言的一种改变”[6](p293)——元宇宙被“崇高化”(subli⁃mation)了。拉康给出的关于崇高化的最一般公式即是:“它将一个对象提升……至大写之物(Thing)的高位。”[6](p112)在有关人士与公司的鼓吹乃至推动下,元宇宙正被提升至大他者之高位而成为“崇高对象”。就此而言,无论是将目前正推动元宇宙实现的诸公司称作“布道者”(evangelist)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7](p54),还是将元宇宙的鼓吹者同样称作“布道者”[8](序p25)的《元宇宙》,皆可谓深得拉康主义的精髓。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在现代性与互联网两个层面的“上帝之死”背景下,对迈向元宇宙及其可能的未来图景作出分析性的展望。
二、迈向元宇宙:“上帝之死”后人的“崇高化”
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人的境况》中将现代世界的异化阐释为双重逃离:(1)从地球逃离向宇宙;(2)从世界逃离向自我[9](p6)。该双重逃离源自对于固有人类境况或者说当下现实世界的不满,可被视作死亡驱力的现代性版本。而迈向元宇宙恰恰在双重层面上呼应了上述逃离冲动,即逃离地球以进入新的宇宙,以及逃离世界以进入数字自我①这种逃离举动因其在死亡驱力下总是试图越出现实秩序的符号性边界,在日常生活的文化语境中往往被视为一种“不正常”乃至“疯狂”之举,这也正是为元宇宙“布道”的扎克伯格常被冠以“疯狂”之名的原因。与之类似的还有“疯狂”的马斯克,他虽然将元宇宙概念贬作“流行营销术语”,却同样有着他所执迷的越出当下秩序或逃离地球的方案——火星移民计划。。想要解释迈向元宇宙这一举动的内涵,我们就要回到现代性背景中,重拾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上帝之死”的论断。
大他者是“无根的”,其并无“绝对”(the Absolute)作为根基,但大他者又手握重权,全盘规介了我们的现实世界。因此,人在精神上总是陷入存在性的焦灼感与孱弱的无助感之中,并依赖其童年经验而渴望得到父亲的保护。在此过程中,上帝作为父亲形象之投射显现了[10](p24)。而随着基督教的神学话语逐渐占据了语言得以构建的位点(大他者的霸权性位置),原本仅是诸神之一的上帝一跃而“崇高化”为大他者之符号性的“具身”(embodi⁃ment),从而能够为人提供一种神学上的精神安慰与身份安置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康才常以“上帝”隐喻“大他者”,其思想生涯中的重要术语“父之名”(Nameof-the-Father)也充满了浓厚的基督教神学意味。。
在此背景下,迈向元宇宙实乃人在自身“崇高化”过程中的一种“创世”冲动。虽然在现有讨论中,对元宇宙的确切定义并未达成共识,但有一点为多数论者所同意:从逻辑上看,元宇宙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其秩序将完全区别于传统世界[14]。更为典型的观点是肖恩·普利(Shaan Puri)关于元宇宙的理解:元宇宙是一个“时间”,是我们的数字生活对我们而言变得比物理生活更有价值的“奇点”(singularity)时刻。物理学中的奇点指的是宇宙“大爆炸”的起始点,现有的一切物理定律在其中都会失效;元宇宙的奇点时刻同样意味着元宇宙会在某个点上产生“大爆炸”而形成新世界,其中的人类境况、生活方式、秩序构建、文明样态将迥异于现有世界。换言之,元宇宙与现有世界间存在着奇点式断裂,其将是创世论而非进化论意义上的新世界。而试图创造这一崭新世界的正是人类自身,人类在此过程中试图代行上帝之创世权柄而“崇高化”自身。因此,虽然代表着“一种从零创造的意志,一种重新开始的意志”[6](p212)的死亡驱力指向了元宇宙的“崇高化”,但“崇高化根本性地是创世论”[6](p213),元宇宙的“崇高化”实质上是人自身的“崇高化”,死亡驱力最终指向的是我们自身。反过来说,人的“崇高化”构成了迈向元宇宙的精神推力。
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曾提出:“在追求幸福和不死的过程中,人类事实上是在努力把自己升级为神。这不仅仅是因为幸福和不死是神的特质,也是因为为了战胜年老和痛苦,人类必须能够像神一样控制自己的生物基质。”[15](p38)而元宇宙恰恰是在“控制生物基质”这一思路之外,提供了一种人将自身“崇高化”为神的可能路径——数字化。在元宇宙的“布道者”们所描绘的未来图景中,人将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全面数字化而成为“数字人”(digital person),从此进入一种数字生活。在“幸福”这一层面上,数字身体比物理身体更为重要,肉身即便并未变得可有可无,至少也被极端边缘化了。人们的关注中心是数字身体的感受与体验,于是人可以从沉重的物理束缚中脱身而出,“痛苦”有望从人的身体系统中被移除。在“不死”这一层面上,由于数字身体的重要性已经大大超过了物理身体,人可以将自身数据化而加以“记录”并“上载”至云端,借助数据存储技术,人成为一种纯粹以数据流形态存在的生命,任何数字身体的“衰败”与“损伤”皆可通过相应技术加以“修复”,人于是可以从生死的自然规律中挣脱出来,“死亡”有望从人的生死循环中被移除。“布道者”们声称,迈向元宇宙的人将获得“永生”,生活得更为“幸福”,从而也更具有神性(divinity),更接近“上帝”,元宇宙也因此实现了对人之“崇高化”为神的自我确证。
然而,在元宇宙中,人类真的更加“幸福”吗?人类果真能在迈入元宇宙后将自身“崇高化”为“上帝”吗?元宇宙看似为人类提供了一种上升路径,但这一路径所通向的究竟是“天堂”还是“地狱”呢?上述疑问将分析的视角导向了元宇宙本身。通过对从互联网到元宇宙这一变化的拉康主义分析,我们将看到数字大他者在元宇宙中的返场,以及将人“崇高化”为“上帝”的不可能性。
三、从“不存在上帝,一切都不被允许”到数字大他者的返场
在“布道者”们关于元宇宙的叙事中,“互联网”常常是一个高频词汇,其一般被形容为元宇宙的衬托,元宇宙往往被其视为“互联网的最新(终)形态”。在拉康主义的视域中比较两者,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元宇宙“新”在何处,又“终”于何处。
早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互联网方兴未艾之际,齐泽克就已对“赛博空间”(Cyberspace)①与“元宇宙”概念最早出自科幻小说类似,“赛博空间”这一概念亦首见于科幻小说,由威廉·福特·吉布森(William Ford Gibson)在其1981年所写《燃烧的铬》(Burning Chrome)中提出。有趣的是,“赛博空间”概念的提出比“元宇宙”概念的提出早了11年。,即同计算机和互联网相关的虚拟现实进行了分析。他的一个关键性洞见是赛博空间中“大他者的退却”(the retreat of Other)。他引用了拉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名言的颠倒——“如果不存在上帝,一切都不被允许”,并写道:“如果没有强制选择界定自由选择的领域,那么选择的自由就会消失。”[16](p198)这就是互联网层面的“上帝之死”。
具体而言,在大他者规介了现实的意义上,现实本身就已然是一种虚拟的秩序。赛博空间则不断地追求以“虚”拟“实”,追求越来越高的拟真度。由于这种虚拟空间对于真实度的追求模糊了虚拟与真实、表象与潜在的界限,我们反而体验到了现实生活的虚拟性。那么,这种体验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齐泽克认为:“这个将符号性阉割定义为与‘真实’阉割相对立的虚拟之现实性必须与权力的基本悖论相联系,即符号性权力本质上是虚拟的,是保留中的权力,其充分运用的威胁从未真正发生(当一位父亲大发脾气时,尽管这可能是痛苦的,但这本质上是他无能的标志)。”[16](p193-194)也就是说,当大他者的虚拟性被体验到时,它就会如同一位大发脾气的父亲那样无法保持其权威,会被人感知到其本质上的无能或“无根”。由此,大他者也就从赛博空间中退却了,人们将在赛博空间中直面一个不存在大他者的“无虚拟性现实”(a reality without the virtual)。拉康早已言简意赅地点明:“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5](p235)在大他者退却之后,虚拟现实中的日常秩序便无法通过大他者而得到规介,主体的身份也无法借由大他者而被登记于赛博空间的符号秩序之中。人不再被大他者告知其所欲者为何物,于是也就在本体论层面丧失了“现实感”。因此,在互联网时代,我们面临的是如下人类境况:
……由于与“真实的”身体性他者的接触逐渐消失,一个邻居将不再是邻居,因为他或她将逐渐被一个屏幕幽灵所替代;全面的可得到性将诱发难以忍受的幽闭恐惧症;过多的选择将被体验为选择的不可能;普遍直接参与的团体将更加强烈地排斥那些被阻止参与它们的人。赛博空间打开了一个关于无限变化、新的多样性器官等无穷可能的未来,该愿景掩盖了其严格意义上的反面:一种前所未闻的极端封闭[16](p199)。
《大学英语课程指南》要求大学英语课程培养大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与发展大学生思维能力。在实际教学中,许多大学英语教师在进行文本内容教学时,比较多的是关注文本信息的输入与注重文本的欣赏性,缺乏对大学生思维习惯培养的关注[6]。传统的讲授式课堂早已淘汰,现阶段需要让学生课上与课下结合起来,课堂上“动起来”,将课堂的主导权还给学生。从本设计案例不难看出,多个活动和任务培养了学生的这方面能力,如如何从文章中提炼概念,如何对比四篇文章的异同,如何通过文章评价女性的地位和自我意识觉醒,如何评价同伴和小组成员的表现等。
这是自由选择的不可承受之“重”,也是现代性层面“上帝之死”后人的精神危机在赛博空间中的投射与加深。
相比于赛博空间赋予人的“上帝之死”后难以忍受的沉重桎梏,被宣称为“互联网的最新(终)形态”的元宇宙却有所不同,最为关键的即是其关于虚实关系的新叙事。这种叙事呈现为逐步递进的三个阶段。(1)以虚拟实。在该阶段,元宇宙被理解为内在于现实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虽然对现实进行了部分数字化,但目的仍是映射现实以回到现实。比如,我们在线上交友是为了线下的见面,我们进行虚拟转账是为了达成现实的交易。这一阶段的元宇宙同虚拟现实(赛博空间)的区别,仅仅在于模拟现实程度的高低,因而前者至多是后者的“增强”而非“迭代”。(2)虚实相生。在该阶段,元宇宙从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被提升至平行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世界,“虚”的目的不再是模拟“实”,“虚”本身被体验为一种重要的事物。此时,虚与实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这种界限最终会被打破,虚实之间开始互渗乃至相生。今天许多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元宇宙应用就停留在“虚实相生”的层面上,比如视频平台“哔哩哔哩”中大受欢迎的虚拟偶像、游戏《堡垒之夜》(Fort⁃nite)中观看人数达上千万的虚拟演唱会、以成百上千万美元的价格成交的带有NFT编号的虚拟画作以及虚拟地块……这一阶段的元宇宙已然是现实世界的对等存在,其将在与现实世界的交互中展现更多可能性。(3)以虚纳实。在该阶段,元宇宙将被进一步提升为高于现实世界的存在,现实世界中的一切物理存在都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而向“虚”的层面转化,这反过来将把“实”的空间压缩到最小并将其纳入“虚”之中。当然,这个阶段目前还仅停留在元宇宙“布道者”们的美好蓝图中,其奇点来临的时刻尚未可知。简而言之,这一阶段的元宇宙以“吞纳”现实世界的方式成就自身,虚与实的界限已不再重要。
可以看到,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元宇宙的核心叙事即是“虚”的维度一步步压倒“实”的维度,最终整个现实世界将“溶解”于元宇宙之中。而从更长久的历程来看,原本被互联网从现实中分隔出的虚拟维度,将被元宇宙重新打入现实的秩序中,但不同之处在于,这将是以虚拟为主导的一次“吞并”,现实世界的疆域将被纳入元宇宙的版图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虚拟现实不再是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相反,现实世界成了虚拟世界的组成部分。最终,元宇宙将成为未来人类生存于其中的唯一“真实世界”。正是在这里,我们窥见了“上帝”在元宇宙中的返场。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返场,我们以被屏幕区分开来的虚拟形象与现实形象为例加以说明。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虚拟形象与现实形象之间的分裂:一个现实中智慧、勇敢、正义、节制的人可能在赛博空间中表现得武断、怯懦、卑劣、放荡,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在屏幕之外的现实世界中,一个人的现实形象是被大他者所规介的;但在屏幕之内的赛博空间中,大他者的退却释放了主体内部潜在的、被压抑的内容,从而生成了虚拟形象。在互联网时代,两种形象是之间存在着一种含混性:就虚拟形象不同于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形象而言,它可以被指认为虚假的自我;但是就虚拟形象显示了主体在现实生活中不敢展露的性格而言,它又是比现实形象更加真实的自我[17]。
不过,这一含混在元宇宙中就变得不重要了。由于作为界面的屏幕在元宇宙中消失了,经历了以虚拟实、虚实相生阶段而达到以虚纳实阶段的元宇宙便不再有虚实之分。此时,与其说人的虚拟形象相比于现实形象变得无限重要,毋宁说虚拟形象已经与现实形象合而为一了。而当虚拟形象与现实形象的界限消失时,人在元宇宙中的形象就是唯一的真实形象;当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消失时,元宇宙就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唯一的真实世界。甚至可以说,我们将在元宇宙中重返前互联网时代,其时不再有大他者退却的赛博空间。如果借用电子游戏《我的世界》(Mine⁃craft)与《第二人生》(Second Life)的名称,那么,元宇宙的世界就是至大无外的“我的世界”,元宇宙的人生就是舍此无他的“第一人生”。由此,在赛博空间中退却的大他者在元宇宙中得以返场,人重新为大他者所规介,不必再承受赛博空间中“上帝之死”所带来的精神危机。但值得注意的是,元宇宙的大他者同前互联网时代的大他者之间存在着差别。因为元宇宙的核心叙事是“以虚纳实”,所以其得以构建的重要前提即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达成对现实世界的全面数字化。“所有信息(所有书籍、电影、数据……被计算机化且即时可用)完成数字化的前景保证了大他者近乎完美的实体化:在机器中,‘一切将被写入’,一个关于现实的彻底符号性重现将会发生。”[16](p213)齐泽克将所有信息实现数字化后产生的大他者称作“计算机化的大他者”(the computerized“big Other”)。事实上,全面数字化就意味着“符号”(the Symbolic)秩序演变为“数字—符号”(the Digital-Symbolic)秩序。此时,作为语言得以被构建之位点的大他者便被加入了计算机语言的要素,因而对于在元宇宙中返场的大他者,亦可被冠以“数字大他者”(the digital Other)之名。
分析至此,我们已经能够尝试回答之前提出的疑问:迈向元宇宙这一“创世”举动能否确证人自身的“崇高化”?答案是否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赛博空间中退却的“上帝”将在元宇宙中以数字大他者的面目返场,臣服于数字大他者的人自然无法再将自身“崇高化”为神。在此,一个问题紧接着浮现出来:如果人不是元宇宙的“上帝”,那么在为数字大他者所规介的元宇宙中,人的境况究竟如何?这需要对数字大他者及其规介下的数字人作进一步的分析。
四、数字人:元宇宙的“上帝”还是“白痴”?
从“元宇宙热”出发,经由元宇宙本身,最终我们将目光落到了元宇宙的主体身上。在数字大他者返场的元宇宙中,人将以怎样的主体形态存在?如前所述,按照通行的关于元宇宙的理解(或者说,按照元宇宙之“布道者”们的设想),人应在全面数字化之下以数字人的主体形态进入元宇宙。在这个向数字人转化的过程中,人将从现实转向虚拟、从物质转向精神、从肉身转向灵魂、从有死转向无限……这种人的全面数字化在本体论层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元宇宙中的数字人将是一种拉康式“去中心的”(decentred)主体。
就其实质而言,“‘去中心化’是对,$(主体的空无)之内容(‘自我’,想象与/或符号身份的集合)的去中心化”[16](p181)。互联网时代形形色色的App就是很好的例证。安装在手机、电脑、手环等电子设备中的各种程序,实质上充当了主体的“代理人”:一方面,它被动地代替主体行动,在主体的授权下完成一系列的任务,比如查询天气、收藏文章、储存视频、搜索美食、自动回复消息等;另一方面,它也主动地针对主体展开行动,比如浏览海量信息并筛选、推送与主体相关联或主体感兴趣的内容,或是通过监测心跳、血压、睡眠质量等并对主体的生活习惯提出警告与建议。此处的关键是,这个被主体授权的“代理人”并非相对于授权者的另一个主体,而恰恰是对授权者主体起到补充作用的自我。然而,主体将这个外部的“代理人”仅仅视为一种程序而非与自身平等的他者,因而放心地对其进行授权乃至放权,“代理人”反而得以监测、安排乃至操控主体的生活。“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赛博空间之补充的根本含混:它们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摆脱不必要的负担,但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我们的彻底‘去中心化’——这即是说,代理人也‘调节’(mediatize)了我们。”[16](p182)换言之,去中心化主体的中心不在自身之内,而是被交付给了外部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可以是互联网时代的种种程序,或许更普遍而贴切的称呼是“大他者”——那个调节、规介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大他者。
进而,这一主体的去中心化在元宇宙中可能表现得更为彻底。以虚纳实的元宇宙彻底取消了虚与实的界限,从而也就彻底弥合了肉身与灵魂的分裂。人注定以数字人的形式在元宇宙中存在,而数字人将面临更为“位高权重”的大他者。如果说,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还能够指出身体内部与外部之界限的消失,批判内部器官的外部技术殖民化与外部程序对内部感官的直接操纵[16](p172-173);如果说,在当下,我们仍有必要谈论主体内部力比多与无意识通过数字链接向外的流溢,指控大他者借由大数据技术宣称比主体更了解自身[18][19];那么,在元宇宙中,内与外的区分就随着虚与实的合一而变得没有意义了,数字人的物理身体将被极端边缘化甚至虚无化,人不再有一个身体作为权力不可穿透也无法化约的“黑暗硬核”,人的思想、情感将被全面数字化为由“1”与“0”构成的计算机语言。数字大他者则借助这种语言媒介,可以不必通过身体,毫无阻碍地将其权力直接施加于人的精神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元宇宙”概念的出处《雪崩》中对于“雪崩”病毒的描写,可被视为对元宇宙中数字大他者的传神刻画:
把大五卫的大脑啃得千疮百孔的病毒是一串二进制信息。它化身为一幅位图——也就是一系列黑白像素,白色代表“0”,黑色代表“1”——钻进了他的脑袋[20](p409)。
数字大他者正如“雪崩”病毒一般钻入主体的中心,将数字人处理信息的“大脑”啃得千疮百孔,使主体成为没有“大脑”的“白痴”。由此,针对元宇宙中数字大他者的情况,我们可以转变拉康相关表述的重心:在拉康的描述中,大他者是“相异于我的某物,尽管它位处我的中心”[6](p71),“我”维系于大他者而非自身[21](p130);进入元宇宙后,数字大他者虽是相异于主体的某物,但其牢牢地占据了主体的中心,从而将主体的去中心化推进至极端,令数字人纯然维系于数字大他者。于是,关于赛博空间的这一想象可能在元宇宙中成为现实:“……另一个计算机程序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控制并指挥我的代理人……我可以说是从内部被支配了;我自己的自我不再属于我。”[16](p183)在这种情况下,人非但不会将自身“崇高化”为“上帝”,反而陷入一个更为糟糕的境地,在其中,数字人成为“白痴”。
齐泽克曾多次举过录影机的例子:一名观影爱好者在拥有录影机后,其观看的电影数量往往不增反减。因为他更乐于录下影像以待日后观看,最终满足于拥有录影带而非观看电影,似乎录影机已然以某种方式代替他观看了电影,“录影机在此代表着‘大他者’,代表着符号性登记的媒介”[16](p145)[22](p279)。在元宇宙中,相似的情形将以更极端的方式出现。在全面数字化之后,信息的储存时间将变得更加长久,信息的调用将变得更加便捷,数字人可以更加放心地将种种信息托付给元宇宙的“录影机”——数字大他者。而在数字大他者的规介下,数字人可以不必认知、不必记忆、不必思考、不必行动,因为存在着一个更为全知(omniscient)、更为全能(omnipotent)、更为无所不在(omnipresent)的数字大他者。这样一位“上帝”般的数字大他者会来代他认知、代他记忆、代他思考、代他行动,最终代他幸福并永生不死。这绝非危言耸听,在晚近人工智能导致的“人工愚蠢”中,我们已能够窥见上述变化的端倪[23][24]——那盲目听从智能导航而将车开入深水区、人行隧道以及雪山无人区的车主,正是元宇宙中茫然不知前路何方的数字人在当下的缩影。元宇宙中的数字人是彻底去中心化的主体,是已然停止思考而只知听命于数字大他者的数字“白痴”,最终将成为拉康论域中“忠实地把自己提供给大他者之享乐”[25](p49)的变态主体。
更糟糕的是,这样一位手握重权的数字大他者将重新划分共同体。由于元宇宙立足于全面数字化,能否成为数字人将构成区分新旧共同体的标准——唯有成为数字人的主体才能进入元宇宙,而不愿或无法成为数字人的主体将被元宇宙排除在外。这很像齐泽克对基督教教义“所有人都是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的著名颠倒——“那些不是我兄弟的便不是人”[26](p143-144)。当数字大他者宣称“所有人都能进入元宇宙”时,真正被表达的意思其实是“那些不进入元宇宙的便不是人”。元宇宙将是比赛博空间更为平滑的空间,这不仅是因为以虚纳实使一切物质阻力消失了,更是因为数字大他者所划定的新界限将所有具有否定性的个体都排除了出去,使这些个体成为“余数生命”(remainder-life)[27],从而将一切创伤、症状、反抗、危机、灾难都隔离在了元宇宙之外。最终,元宇宙呈现出一种平滑的“数字之美”[28](p33-34)。
这就是人在元宇宙中的可能境况。如果不愿成为除了“赤裸肉身”之外一无所有的“余数生命”,人就必须接受全面数字化并进入元宇宙,这也就意味着人必须成为去中心化的数字人并对数字大他者顶礼膜拜。悲哀之处在于,主体唯有通过臣服于大他者才能成其为主体,当数字大他者全面规介了元宇宙时,数字人面临的悲惨命运便是:他不得不成为一个“白痴”。
五、结语:“创世”?不,“造神”!
透过拉康主义开启的分析性视角,我们分别考察了“元宇宙热”、元宇宙以及元宇宙中的主体,尝试展现一种元宇宙来临后可能的秩序图景。可以看到,就精神层面而言,2021年兴起的“元宇宙热”肇始于越出符号秩序的死亡驱力,在元宇宙“布道者”们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正被或将被卷入其中。然而,一个元宇宙的未来并不像其“布道者”所描绘的那样充满光明:在现代性意义上的“上帝之死”后,人类试图以迈向元宇宙这一“创世”举动确证自身,实现自身的“崇高化”。然而,在赛博空间中退却的“上帝”(大他者)将在以虚纳实的元宇宙中以数字大他者的面目返场,人由此变为去中心化的数字“白痴”。因此,迈向元宇宙或许并非充满了乐观情绪与英雄主义的“创世”,而很可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造神”。
平心而论,针对元宇宙,我们不必拘泥于《雪崩》的理解,认为元宇宙的前景注定一片黯淡。但我们也不应进行过于乐观的估计,认为元宇宙“是‘心’的绽放,是‘梦’的具象,是‘我思故我在’的全息展现”[8](p15)。在这里,我们可以从齐泽克的提醒中获得教益:“赛博空间将如何影响我们,这并没有直接刻入其技术特性之中;相反,它是以(权力与统治的)社会—符号性关系网络为转移的,而这个网络总是已经过度决定了赛博空间影响我们的方式。”[22](p299)与之同理,元宇宙将如何影响我们,也与由大他者所规介的符号秩序密切相关,这也正是对元宇宙展开拉康主义分析的意义所在——相比于警惕元宇宙中的数字主权者或数字资本家,更值得深入剖析的是决定元宇宙如何影响我们的数字大他者。通过考察数字大他者以及数字人,我们更为清晰地观察到了元宇宙可能将我们引向的未来。
在当下铺天盖地的讨论热潮中,我们有了一种元宇宙正在加快实现的幻觉,但事实上,元宇宙的美好图景目前仅停留于其“布道者”们的乐观描绘中,许多关键性技术仍面临着瓶颈,人类文明也尚未在政治、思想、伦理等诸多层面上做好迈向元宇宙的准备。一言以蔽之,元宇宙仍是一个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开放性概念,对元宇宙的任何断言都可能成为“自杀预言”(suicidal predictions)或“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而人类的未来可能是元宇宙,也可能不是元宇宙,一切尚处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之中。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元宇宙不应成为一项“崇高化”工程,不应成为人类能够通向的唯一且确定的“崇高化”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