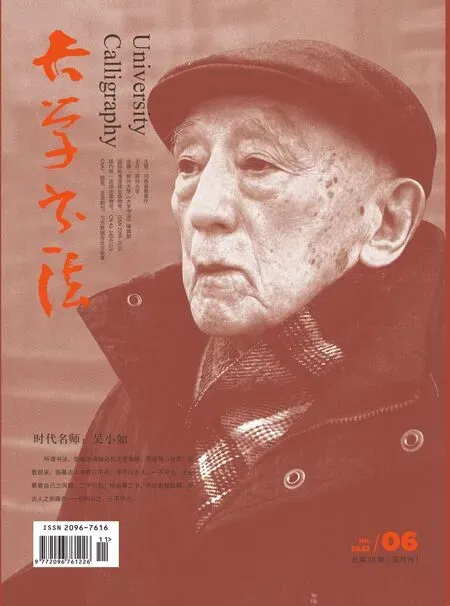从元代论印诗看民间印人文化身份的建立
⊙ 包文运
在元代,由于复古思潮影响,沉寂已久的篆刻艺术得到士人较为广泛的关注,赵孟 作《印史序》导于前,吾丘衍著《学古编》继于后,二人又身体力行描篆作印,一时之间,士人研习古篆籀文,馆阁诸公竞相使用名章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新风尚。士人的需求催生了一大批以刻印为业的民间匠人,他们技道两进、挟技鬻印,在与文人的交游中,得到了士人的认可。而士人也因赏识和赞美这些印人,留下了数量颇为可观的论印诗。元代论印诗的大量出现,不但反映了士人对民间印人文化身份的认可,客观上也推动了元代文人篆刻的发展。
一、文人对民间印人技术的肯定
元代篆刻兴起之后,更多的民间印人进入了文人视野,他们凭借精湛的技艺得到了文人的认可与推介。在元代早期,特别是在印石未普及之前,印章的材质多以金属、玉石、象牙、竹木等为主,这些材质大都质地坚硬,较难镌刻,文人主要以“描篆”的方式参与印章创作,如吾丘衍《赠刊生林玉》诗云:“我爱林生刻画劳,能于笔意见纤毫。牙签小字青铜印,顿使山房索价高。”[1]林玉作为吾丘衍专业代刀人,凭借着精湛的技艺,毫厘不差地刻画出吾丘衍的笔意,抬高了吾丘衍印章的价格。
元代王时中在《赠刻章者》中有“君怀寸铁妙胜笔,凤绾鸾翔龙起蛰”[2]的诗句,高度赞美刻章者“寸铁胜笔”的高超技艺。又如董佐才在《方寸铁为卢仲章赋》中咏道:“方寸铁,百炼刚,吹毛剑锋秋水光,镌勒妙拟吾竹房。倒薤文,连环钮,通侯累累悬肘后。伏龟趺,蟠螭首,颂德纪功垂不朽。铁名已著霜满颅,复得铁业传二雏。勿劖元祐党,勿刻詅痴符。何如往补石经缺,万古六书存楷模。天下英髦知所趋,伊谁之力丹丘卢。”[3]诗中所记的卢仲章,天台人,又名卢奂,别号“丹丘”,善于刊碑刻印,《嘉定州重建儒学记》便为卢奂所刊。诗人董佐才将卢仲章篆刻与吾丘衍篆刻相比拟,高度肯定了卢的刊刻技艺,并劝告卢仲章要秉持“勿劖元祐党,勿刻詅痴符”的人格操守。
如果说卢奂以及王时中诗中不知名姓的刻章者还未能获得文人们普遍认可的话,另一位“方寸铁”朱珪则以其精湛的技艺获得了一大批文人墨客的赞许。朱珪和顾瑛比邻而居,常受顾瑛邀请刊印刻图,与来往于玉山草堂的文人雅士相交游。顾瑛亲自作《题伯盛朱隐君方寸铁》推介朱珪:
神斧磨天割紫云,仙葩殒玉发奇芬。灵书宝诀开刚卯,不数人间小篆文。书刻输君总色丝,前身想是伏灵芝。虎头食肉元无相,铸钮休传左顾螭。我家金粟道人章,瓦款蟠螭识未央。千古典刑今复见,佩之何必兽头囊。镂玉涂金与错银,尽将工巧失天真。君能独擅雕虫技,定品当年合出神。[4]
顾瑛在此诗中盛赞朱珪“独擅雕虫技”,似有“神斧”与“灵书宝诀”相助,所刻印章古意淋漓,天真自然,堪称神品。在此诗之后的跋记中,顾瑛载:“伯盛朱隐君,予西郊草堂之高邻也。性孤洁,不佞于世。工刻画,及通字说,故与交者皆文人韵士。予偶得未央故瓦头于古泥中,伯盛为刻金粟道人私印,因惊其篆文与制作甚似汉印。又以赵松雪白描《桃花马图》,求刻于石,精妙绝世。大合松雪笔法。惜其不得从游松雪之门。使茅绍之专美于今世,因题四绝于卷末以美之。伯盛勿以予言为誉,后必有鉴事者公论也。至正十七年中秋日书于玉山草堂,金粟道人顾阿瑛。”[5]朱珪凭借刻印得汉印法,又擅长在石头上描刻白描画,得到顾瑛的首肯。顾瑛在诗中将朱珪与颇有时誉的茅绍之相提并论,既肯定了朱珪的刊刻技艺,也凸显了朱珪在昆山一带的影响力。
邾经在《方寸铁赠朱伯盛》中对朱珪的技艺这样形容:
朱君手持方寸铁,橅印能工汉篆文。并翦分江龙喷月,昆刀切玉凤窥云。他年金马须承诏,此日雕虫试策勋。老我八分方漫写,诗成亦足张吾军。[6]
邾经是元明之际文学家,字仲谊,号观梦道士,又号西清居士。曾侨居吴山下,往来苏、松间,多次参加玉山雅集活动。在诗中邾经认为朱珪持“方寸铁”摹刻汉篆文,如同用并州剪剪江水一样爽健,又好像用昆吾刀裁玉石一般锐利。他认为朱珪身怀此艺可以“待诏金马门”,实现一定的政治抱负。
陈世昌在赠给朱珪的诗中则不无夸张地认为朱珪的篆刻技艺可以达到庖丁解牛、郢匠挥斤的入神境界,他在诗中盛赞道:“朱生心似铁,篆刻艺弥精。应手多盘折,纤毫不重轻。幺么形独辨,螭匾势初呈。汉印规模得,秦碑出入明。风流金石在,润色简书并。馀刃庖丁解,风斤郢匠成。达观应自我,赏鉴足平生。趣刻无多诉,因君托姓名。”[7]释元鼎《方寸铁歌赠伯盛朱隐君》诗中同样有“铁耕代笔犹神锥,用之切玉如切泥”的诗句,称赞朱珪的刊刻技艺。
当然朱珪这种如入化境的刊刻技艺源于其“心似铁”的定力,也得益于他“幺么形独辨”的训诂学功底,所以朱珪另外一个亦师亦友的朋友陆仁在《方寸铁铭》中说:“娄东朱珪字伯盛,工古篆籀文。其于六书之义,考之尤详,尝以余力刻印章,则为中吴绝艺。”[8]
由上可见,民间印人凭借高超的技艺引起了士人们的赏识与赞许,然仅依靠娴熟的技艺尚不足以让民间印人得到文化身份的认可,他们文化身份的转型是建立在掌握娴熟的技艺与精通“六书之义”的基础之上的。雄厚的文字学知识储备赋予了民间印人们新的身份,得到了文人的接纳与推扬。
二、民间印人文化身份的建立
宋末元初,战火频仍,江南沦丧,大批士人选择归隐山林,绝意仕途,相互以名节砥砺,加之元代统治者废除科举,压制儒士,不少读书人进身无门,转而借艺术创作寻求精神寄托。印章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逐渐引起文人关注。然而,自唐代以来,印文篆法乖舛,古法荡然无存,唐代印章承袭六朝风气,印文多屈曲盘旋,不合古法;宋人印章又承唐制,崇尚纤巧,不宗秦汉,文字更加支离伪谬;至元代早期,印章依然萎靡不振。对此,文彭在《印章集说》中记载:“六文八体尽失,印亦因之,绝无知者。至正间,有吾丘子行、赵文敏子昂正其款制,然时尚朱文、宗玉箸,意在复古,故间有一二得者,第工巧是饬,虽有笔意,而古朴之妙则犹未然。”[9]
其实,至正年间元代印坛并非像文彭所言那样不堪,不少民间印人自觉研习秦碑汉印,通晓六书八体,以精湛的技艺和渊博的训诂知识而为读书人所激赏。民间印人正是凭借“苟焉糊口栖此身,元来亦是知书人”的苦衷与文化诉求而拉近了与文人之间的身份距离,从而得到文人的认可与赞咏。这在陆文圭《赠朱自明序》可以明显看出:
丙寅夏,余来容山,朱晦自明见于明德堂上,鄱之浮梁人也。余扣之曰:“习举子场屋之文乎?”不答。曰:“为刀笔簿书之业乎?”又不答。徐曰:“吾……性颇好古,工图书篆刻之学,游戏三昧而已。儒,幼而学之。吏,亦尝试焉。皆能之而不为者也。”余闻其言而心怪之。[10]
朱晦名不见史传,然从陆文圭记叙中可以看出朱晦对待“儒”与“吏”的态度,不是不能为,而是“能之而不为”。朱晦“游戏”于图书篆刻之学,其目的在于韬光晦迹,如此一来就与专以刊刻图书来糊口度日的民间匠人拉开距离,而与隐士相仿佛。
方回《赠刊印朱才俊》一诗中明确表达了对民间印人朱才俊文化身份的认可:
科斗何年变篆字,至秦程邈翻为隶。今人但习真行草,谁会六书三耦意。篆所最难柱与圈,学打一圈废三年。……自言少小嗜此艺,意欲径上阳冰堂。细观刀笔最佳处,颇识传笺通训故。苟焉糊口栖此身,元来亦是知书人。[11]
在方回看来,时人多研习真行草书,对于篆书的研习与了解不足。学习篆书较为艰难,不但要花较大气力在篆书线条与使转练习上,更需要具备渊博的文字学知识,否则将会结构涣散,字法乖舛。可见,能否具备篆体字的辨释与运用能力,是判断这些民间印人是否具备文人身份的重要前提。张息堂《题衡阳刊匠曾子谦〈字说〉手卷》中也大致表达了如同上文方回诗中的意思:“阳冰谦卦妙入神,当时镌刻知何人。至今宝现逾琬琰,字体清劲无失真。谦谦子谦能辨此,手挥铁毫出文字。功成何止地中山,凿破乾坤六十四。”[12]朱才俊、曾子谦虽为民间印人,却能精通此艺,篆书取法李阳冰,并且通晓经学与训诂,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匠人”了,而是因为进身无门,只能暂栖身于民间印人之列的读书人,因此引起了文人的同情与共鸣。
元代初年,文人习篆风气涌起,吾丘衍主张:“凡习篆,《说文》为根本,能通《说文》,则写不差。”元代不少民间印人精研《说文》,对篆书字形、字义有较强辨识能力,但也难免存在“袭舛踵讹”的现象,并且所制印章大都以新奇相矜,以精巧相尚,究其原因在于“不古”。就印章而言,何为“古”?明人杨士修在《印母》中将印章之“古”概括为“三古”,即“有古貌、古意、古体”[13],扩而言之,古貌是就印章形制外貌而言,古意是就印章刀法与气韵而言,古体则多与字法相关。如何能古?无他法,惟有向汉印汉篆取法方可得“古”。吾丘衍《赠刻图书钱拱之男钱 二绝句》中也给出了答案:“唐人小印网蛛丝,汉篆阴文古且奇。赖有钱生能识此,免将古谱较参差。”“一种青铜自琢磨,尔家铜色似宣和。十年为尔腾声价,不道平生篆已多。”[14]可以说,元代文人不但将能否通晓训诂作为民间印人获得文化身份认可的必要条件,而且也将能否得“古”作为评判“文人印”的重要标准。
在元代论印诗中,我们不难发现文人对民间印人崇“古”做法的认可。如吴澄在《赠篆刻谢仁父序》中认为:“谢复阳仁父,儒家子,工篆刻。予每视其累累之章而喜,岂真为其笔法、刀法之工哉,盖庶几其存古而将与好考古文之君子征焉。”[15]张绅在《印文集考跋》中以具有“三代气象”盛赞朱珪的篆刻 :“朱伯盛好考古篆籀之学,与同郡钱翼之父子及陆友仁、吴孟思、卢功武讲论甚博,尤善仿古名刻及士大夫勒名金石,俨然三代制作气象。”[16]朱珪篆刻之所以有“三代气象的原因在于他取法高古,他在吴睿的指导下,对三代以来金石刻辞无不极意模仿,取《石鼓》《峄碑》之文临习既久,而尽悟其法”[17]。民间印人自觉地崇古尚古的做法,不但契合了时代的复古风气,拉开他们与普通“匠人”的距离,而且也借此获得了文人们的激赏。正如吴澄在《赠郑子才序》载:“建康郑子才,业此技三世矣,士大夫多与之交,非徒取其刀刻之精也,所作之字,分合向背,摆布得宜,上下偏旁,审究无误。于用力也,见其艺之工焉,于用笔也见其识之通焉。艺工而识通,求之治经为文之儒,或未至此。予之进之,岂敢直以工师视之而已哉?”[18]正是具备了这种“艺工”和“识通”的双重背景,使得文人对待这些民间印人的态度产生了转变,他们通过诗歌赞美民间印人的行为,也意味着从内心深处认可了这些民间印人的文化身份。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元代文人对民间印人的接受是建立在从技艺到识见再到审美三个维度逐层递进而实现的。同时具备这三个维度要求的匠人已经不是纯粹的匠人了,而是具有某种文化身份的“匠人”,这样的匠人自然不能归属于“工师”行列,而应归属于文人之列。
三、民间印人人格精神的高蹈
如果说把是否具有精湛的技艺、深厚的文字学功底与崇古尚古的审美取向作为标准,来区别一般民间印人与具有文化身份的印人的话,那么对民间印人的为人处世、行为举止、精神追求等“术”外之“道”的认可与赞许,则代表着元代文人从灵魂深处实现了与民间印人精神上的互通和共鸣。
艾性夫《与图书工罗翁》诗中赞道:
木天荒寒风雨黑,夜气无人验东壁。天球大玉生土花,虞歌鲁颂谁能刻。翁持铁笔不得用,小试印材蒸栗色。我今白首正逃名,运与黄杨俱受厄。藏锋少竢时或至,精艺终为人爱惜。固不必附名党锢碑,亦不必寄姓麻姑石。江湖诗板待翁来,传与鸡林读书客。[19]
诗人艾性夫借歌咏图书工而抒怀,他认为自己的“白首逃名”与图书工罗翁的“铁笔不得用”一样,均为生不逢时、怀才不遇。在面对如同荒寒风雨之夜的现实社会,同样需要洁身自好,不屈事权贵,也不放任消极,而应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寄希望于将来,因为诗人相信罗翁精湛的技艺终会被人赏识。
鲁渊《题马文璧秋山图为卢仲章赋》云:“野馆空山里,林泉象外幽。淡云初霁雨,红叶早惊秋。路转山藏屋,桥危岸倚舟。直疑人境异,便欲问丹丘。”[20]在“直疑人境异,便欲问丹丘”一句中,诗人鲁渊巧妙地将卢仲章别号的“丹丘”一词嵌入诗句,与《秋山图》中的“丹丘”一语双关,因此,此处所要问取的并非简单指《秋山图》中的野馆、空山、幽泉、淡云、红叶、山屋、危桥、斜舟等自然物象,更象征了高逸之士所选择的荒寒寂寥、清雅绝尘的隐居之境和隐士们高蹈的人格精神,毫无疑问,诗人认为卢仲章即是这种隐逸之士。
在元代民间印人获得文人们的精神认同上,以朱珪最具有代表性。如卢熊有诗《寄朱伯盛》曰:“白首耽书更不忘,鹄文虫篆灿生光。高人为赋峨冠石,太史曾题琢玉坊。野屐蹋云闲看竹,春帘凝雾静焚香。别来又泛松陵棹,渺渺轻鸥江水长。”[21]殷奎又在《朱伯盛小像赞》中进一步赞扬朱珪其人:“臞然如昨,秋风野鹤。老矣于今,孤云远岑。轨有道之躅,不娶终身,何行之卓。求古人之心,不刻党碑,何执之深。吁,此其所以傲兀乎变幻。吁,此其所以膏肓乎山林。”[22]
朱珪一生不仕不娶,孑然一身,如野鹤孤云,傲兀世间,寄身泉林,“野屐蹋云闲看竹,春帘凝雾静焚香”。除偶尔出现于玉山草堂与往来的文人雅集外,大部分时间独自一人过着隐逸生活,朱珪的生活状态正符合了元代诸多士人所向往的卓尔不凡、不与世俗同流的人生境界。
倪瓒淡泊名利,绝意仕途,一生以孤高自许,是元代士人中典型的“高人逸士”。他对朱珪的赞扬颇为值得我们玩味,其在《静寄轩诗三首》中咏赞道:“静寄轩中无垢氛,研苔滋墨气如云。匣藏数钮秦朝印,白玉蟠螭小篆文。”“独行应如鲁独居,心同柳下孰云迂。纵教邻女衣沾湿,试问高人安稳无。”“身似梅花树下僧,茶烟清扬鬓鬅鬙。神清又似孤山鹤,瘦骨伶仃绝爱憎。”[23]第一首开篇“静寄轩中无垢氛”一句便表明了倪瓒对朱珪的称许。倪瓒有心理“洁癖”,生活上讲究绝对洁净,精神上向往高度纯净,一生拒绝与他认为“未脱俗”的人相往来,所交之友多清风高洁之士。倪瓒遇到朱珪,似乎找寻到冥冥之中的知音,在倪瓒的心中,朱珪不仅是一位技艺高超、才识过人的民间印人,更是一位有颜叔子、柳下惠般定力与德行的世外高士。倪瓒在朱珪身上找寻到了自我人格的写照,引起了精神上的共鸣。
由此可见,民间印人真正可以触动当时文人内心进而走进文人之列,正是源于自我品行的高洁、人格精神的高蹈。元代论印诗中屡屡出现的“不刊党碑”的典故出自北宋九江石工李仲宁和长安石工安民拒绝刊刻元祐党碑一事,元代文人借此典故表达了对民间印人品行的赞扬和期许,同样,那些具有隐逸情怀的民间印人,也更能获得文人们的同情,从而得到认同和接纳。
结语
明代朱简在《印经》中将印章分为“工人印”和“文人印”,“工人之印以法论,章字毕具,方入能品。文人之印以趣胜,天趣流动,超然上乘”[24]。“工人印”即我们今天所谓的“匠人印”。朱简认为“以法论”与“以趣胜”是厘清“工人印”和“文人印”区别的重要标准,这也为我们解读元代“匠人印”与“文人印”提供了理论依据。朱简在《印经》中阐述二者区别后又着重强调:“若既无法,又无逸趣,奚其文,奚其文,工人无法,又不足言矣。”[25]一方面,朱简认为“法” “趣”不同,品格高下自辨,得法需“章字毕具”才能入能品,得趣则天真烂漫,“一超直入如来地”。另一方面,朱简又强调“法”的重要性,无论是“工人印”还是“文人印”均不可回避“法”的规定性,因为以刀代笔进行印章镌刻的过程天然包含了对刀法熟练程度的规定性,刀不达意,趣何生焉?在明代,印石的广泛普及为文人们参与印章制作提供了便利,印石以晶莹如玉的外观和便于奏刀的质地得到文人追捧,文人们自篆自刻已不存在技术上的难度,自然便从“法”的追求跨越到“趣”的追求上。而在元代,因印章材质较为坚硬,致使大多数文人无法掌握精湛的镌刻技术,彼时,众多职业民间印人满足了文人士大夫对印章的需求,因这些民间印人自身的文化修养不足,也导致这一时期印章制作“法”大于“趣”。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在元代民间印人中,如朱珪、卢仲章等人虽身为匠人,但他们技艺精湛又通晓文字学,特立独行又精神高蹈,因此得到了文人们的认可和推崇,客观上也激发越来越多的士人主动参与到刻制印章的队伍中。文人们亲自书篆文刻印,提升了印章的艺术趣味和文化内涵。元明之际,是一个真正以文人为主导的“文人印”时代。
注释:
[1]杨镰.全元诗:第22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206.
[2]杨镰.全元诗:第65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201.
[3]杨镰.全元诗:第47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277.
[4]顾瑛.玉山璞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8:206—207.
[5]顾瑛.玉山璞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8:207.
[6]钱熙彦.元诗选补遗[M].北京:中华书局,2002:504.
[7]陶元藻.全浙诗话:卷24[M].北京:中华书局,2013:662—663.
[8]韩进,朱春峰.铁网珊瑚校证[M].扬州:广陵书社,2012:474.
[9]文彭.印章集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5:3.
[10]李修生.全元文:卷1776[M].南京:凤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533—534.
[11]杨镰.全元诗: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293.
[12]杨镰.全元诗:第65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25.
[13]杨士修.印母[G]//赵诒琛.艺海一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142.
[14]杨镰.全元诗:第22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208.
[15]李修生.全元文:卷481[M].南京:凤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228.
[16]张绅.印文集考跋[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89.
[17]李峰.苏州通史:人物卷(上)[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300.
[18]李修生.全元文:卷1776[M].南京:凤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212.
[19]钱熙彦.元诗选补遗[M].北京:中华书局,2002:17—18.
[20]朱彝尊.明诗综:卷7[M].北京:中华书局,2007:268.
[21]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第19[M].北京:中华书局,2007:1908.
[22]李修生.全元文:卷1753[M].南京:凤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716.
[23]韩进,朱春峰.铁网珊瑚校证[M].扬州:广陵书社,2012:476.
[24]朱简.印经[G]//陈国勇.神农本草经.广州:广州出版社,2003:44.
[25]朱简.印经[G]//陈国勇.神农本草经.广州:广州出版社,200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