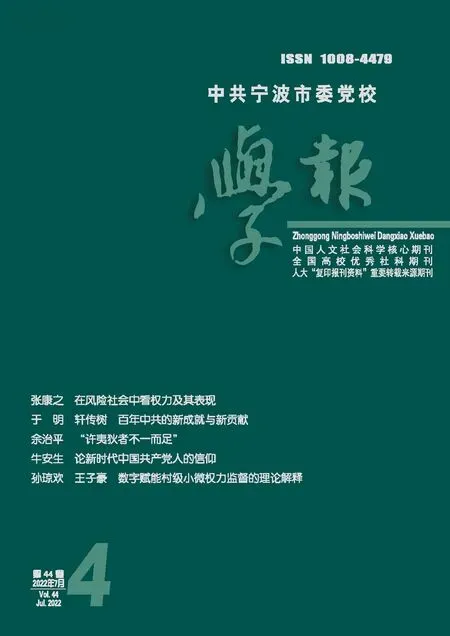“许夷狄者不一而足”——《春秋》“夷夏之变”中“进夷狄”的限度
余治平
“许夷狄者不一而足”——《春秋》“夷夏之变”中“进夷狄”的限度
余治平
(上海交通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0)
公羊家的“夷夏之辨”并不以地缘和人种差异为标准,而以文明教化为本位。《春秋》“进夷狄”,称呼夷狄有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夷狄能行中国之礼,可朝聘、称王、设大夫、纪元、遣使,但还只是起步。夷狄之君楚穆王即便再贤,最高也只能称子。夷狄虽有屈完、子玉得臣之类贤大夫,《春秋》却不称氏。对夷狄贤臣季札,称名而贬。中国夷狄化没有底线,当贬则贬,当绝则绝。夷狄中国化则有限度,夷狄之进步虽可满足礼乐文明的一个条件但并不等于满足所有条件,这并非出于地域、种族的歧视,也非夷夏之人先天禀赋就存在差异性,而是强调夷狄慕王向化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必须有所积淀。“进夷狄”的限度恰恰是“熔铸各种族为一体的一股精神力量”,它对齐桓、晋文联合诸夏中国抗击外侮,对武帝北攘匈奴、南征南越、建构中华身份认同都产生了影响。
春秋公羊学;夷夏之辨;进夷狄;不一而足
《春秋》强调“夷夏之辨”,设“夷夏大防”,而不容混淆边际。历史上的春秋公羊家实际上并不狭隘和孤陋,其所伸张的夷夏之辨始终不以地理疆域、人种肤色的差异为标准,而是以文明教化为本位。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有没有礼乐,行不行王道,存不存仁义,才是公羊家夷夏之辨问题的要害,也是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夷夏之辨多有误解和曲解的核心。董仲舒曰:“《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1](p15)晋沦落为夷狄,楚却变为君子,皆由各自的德行表现所决定。故徐复观说:“《春秋》华夷之辨,已突破了种族的限制,进而为文化的华夷之辨”,应该“以文化来定华夷的分水岭”[2](pp222-223)。入《春秋》以来,四边夷狄凭借其野蛮武力而不断侵扰诸夏中国,毁城池、宫舍与庄稼,掠土地、人口和财物,给诸夏中国带来许多痛苦,引起诸夏中国官民的无尽痛恨甚至还接下了世代冤仇。孔子著《春秋》时,对诸夏中国、尤其是鲁国君王的道德沦丧和礼崩乐坏加以讥讽贬刺,几乎无一遗漏;而对夷狄之区的任何一次进步向化行为也都予以称赏,表面看上去是坐得正,不偏心,显得很公平。然而,经文表彰夷狄、点赞其趋近文明则是有分寸、有限度、有底线的,其有一点进步则肯定他们的这一点,绝不连带别的点,更不可能涉及他们整个的面,几乎从来都没有把夷狄完全中国化,不会对其进行百分之百的肯定,孔子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一、称夷狄之地,“州不若国”
庄公十年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荆,指楚国。荆,本为地名,是上古九州岛之一。《尔雅·释地》曰:“汉南曰荆州。”郭璞注曰:“自汉南至衡山之阳。”[3](p87)荆州地界当北起汉水之滨,南至南岳衡山。《释名·释州国》曰:“荆州,取名于荆山也。必取荆为名者,荆,警也,南蛮数为寇逆,其民有道后服,无道先强,常警备之也。”[4](p78)荆州因荆山而得名,荆山位于今湖北南漳西。这块土地之所以备称为“荆”的首要含义就是预警、警备、警觉。因为其屡屡侵扰诸夏中国,而长期被当作外来强盗,是值得高度警惕与防备的敌人。《诗·小雅·采芑》曰:“蠢尔荆蛮,大邦为仇。”朱熹《诗集传》解释曰:“蠢者,动而无知之貌。大邦,犹言中国也”[5](p482),就是指荆楚之人行为莽撞而缺乏考虑,智力水平和文明程度皆不够,并且因为经常野蛮侵扰诸夏中国,而被当作仇人。
荆蛮是中原诸夏对楚地、楚人的一种蔑称。孔广森《通义》曰:“汉南曰荆州,以州举者,略之若言荆州之蛮云尔。”[6](p44)《春秋》一书在僖公四年“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之前,皆以州名“荆”,用以指代楚国。这种用地名指代国名的书法,显然是《春秋》对未开化夷狄的鄙视。鲁僖公四年,一代霸主齐桓公征服了楚国,楚国第一次出席中原诸侯的会盟,之后《春秋》对荆才改以其国号相称。《谷梁传》亦曰:“荆者,楚也。何为谓之荆?狄之也。何为狄之?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7](p23)夷狄之区因缺少文明而显得野蛮,礼乐不备,人性未化,不易归顺,期待圣人为之立教引导。有没有政府组织、有没有国家机构、有没有君臣一伦是区分文明之邦与野蛮地区的重要标志。《春秋》对南蛮荆楚地区能够以国相称,是一种政治承认,意味着许可其已经进入文明国家行列,开始产生和积累礼乐教化的基本素质。
莘,是蔡国之城邑,位于今河南沈丘东。献舞,是蔡哀侯之名。据《左传》,“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见之,弗宾。息侯闻之,怒,使谓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从之。秋,九月,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8](p32)蔡哀侯与息国之君皆娶陈国妫姓之女。息妫将归,路过蔡国,遭蔡哀侯非礼。息侯请求楚伐蔡,捉拿了献舞。《史记·蔡世家》曰:蔡侯“留九岁,死于楚”。但《楚世家》则曰:已而释之①。蔡侯谥哀公,故《蔡世家》之说较为可靠,从之。
进夷狄之七等级。总结《春秋》经文对夷狄的称呼规律,《公羊传·庄公十年》曰:“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荆,本为一州之名,以州名替代国名,表面上看只是《春秋》经对夷狄部族的一种称谓进阶体系,实际上却是孔子在所传闻之世降夷狄而尊诸夏的一种别有用心的书法。《春秋》严判“夷夏之辨”,立场鲜明,对待中原四边的夷狄部族有不同称谓,而不使夷狄能够主导诸夏中国。划分等级,以免混淆,而形成一套拥有独特话语方式的意义解释系统。
“州不若国”,徐彦《疏》曰:“言荆不如言楚。”[9](pp262-263)荆为一州,楚为一国。称地名,则有别于称国名。地名一般皆因习俗而起,无特别的意指蕴涵,可以是中性的,而称国名则赋予其政治承认和价值认同。
“国不若氏”,徐彦《疏》曰:“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潞氏、甲氏各为狄人之一支,生活于今山西长治一带,与晋人杂居。《春秋》能够对夷狄走出来的人称氏,意味着蛮夷之区已经开始有家族姓氏文化存在了,向文明中夏又迈进了一步。
“氏不若人”,《疏》曰:“言潞氏不如言楚人。”《春秋》对诸夏中国的王侯称人则多有贬义,但对夷狄部族以国称人,则是抬高一等,应该是一种道德褒奖,赞赏其已经获得一定的文明进步。夷狄之区不只是禽兽,已经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存在了。
“人不若名”,《疏》曰:“言楚人不如言介葛卢。”介为东夷之国,后入于齐,其君名葛卢。国名+人名,则显然高于只称氏、只称人,许以文明之国家,尊重其个人。孔子对《春秋》经文的书写,惜字如金。从夷狄走出来的头人首领,能够被《春秋》所称名,说明其身上肯定有闪光点和值得表彰之处。
“名不若字”,《疏》曰:“言介葛卢不如言邾娄仪父。”经文对夷狄首领或小国之君直接称字,则有高于国名+人名的称谓,显得更尊重又亲切。邾娄国,是鲁国近旁一小国。周武王封颛顼苗裔侠(或挟)为附庸,曹姓。最初都城在今山东曲阜近东南邹县。隐公元年,邾娄仪父即入《春秋》。齐桓公称霸,仪父附从朝周,进爵称子。邾娄文公迁至绎山,在今邹县东南。邾娄终《春秋》之世犹存,后改国号为邹,春秋后八世为楚所灭。邾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夷狄,只是附庸国。《春秋》经对其君主称国名+人名也算是一种更高等级的尊重。
“字不若子”,《疏》曰:“言邾娄仪父不如言楚子、吴子。”《春秋》经文称呼夷狄之区的君王首领,比国名+人名更高级的则是以“子”相称,“夷狄大不过子”[10](p229),直接将其纳入公、侯、子《春秋》三等爵位的序列之中,等于正式承认其已经进入诸夏中国礼乐文明国家的行列了,讲尊卑,讲秩序,设爵位,有政制,有礼法,而不再依赖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而生存。这种书法无疑是《春秋》给予夷狄部族的一种最高程度的褒奖。
何休《解诂》曰:“爵最尊,《春秋》假行事以见王法,圣人为文辞孙顺,善善恶恶,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夺爵称国、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备七等,以进退之。若自记事者书人姓名,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已之有罪焉尔,犹此类也。”周代原本就有处罚贵族的五等之科,褫夺爵位而称其国、氏、人、名、字,措辞精确,不得含糊。对夷狄部族之人与事,《春秋》开列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②,秩序井然,界限严明,以适应不同对象加载《春秋》史册的属辞需要。孔广森《通义》曰:“此七等,所以进退四夷,绌陟小国,极于子者,《礼》所谓‘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之义也。”[6](p44)
然而,《春秋》表彰夷狄所进也是有限度的。夷狄之区、夷狄首领、夷狄大夫,即使其力量再强大,事情做得再好,行为举止再有礼义,但最多只称其为“子”。《春秋》用于诸夏中国的那些名例,如天王、君臣、祖祢(父亲的宗庙牌位)、诸侯、世子、大夫,是不可以全部用在夷狄身上的,这是孔子“进夷狄”所能够承受的底线。在孔子那里,夷狄进步到终极状态,发展到最高程度,也不可能实现诸夏化、中国化,所以他们最好也别想什么一变而成为诸夏中国的一员。所以,称赏夷狄,就不要因为他们的某一项进步就完全承认他们已经达到了诸夏中国的文明水平和开化程度,不应该让他们一步到位。
至于《春秋》经对夷狄之称为什么是七等,而不是其他数字呢?徐彦《疏》曰:“所以必备七等之法者,正以北斗七星主赏罚示法。《春秋》者,赏罚之书,故则之。故《说题辞》曰:‘北斗七星有政,《春秋》亦以七等宣化。’《运斗枢》曰:‘《春秋》设七等之文,以贬绝录行,应斗屈伸’是也。”[9](p262)《春秋》书夷狄的“七等之法”拥有深厚的天道根据,以七星照七等,天道、人道合而为一,完全是有汉一代中国人特有的思想气质。
二、行中国之礼,只是起步
行中国之聘礼。庄公二十三年夏季,“荆人来聘”,指荆楚之人前来朝拜鲁君。春秋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交往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然而,夷狄之区能够派遣使节到鲁国访问,参拜被《春秋》理想化了的君王鲁庄公,则是一件值得记录的事件。《公羊传》曰:“荆何以称人?始能聘也。”这是入《春秋》以来,荆楚第一次派遣使节出访鲁国,显然是南蛮势力向文明之邦趋近的重要标志。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曰:“诸侯来朝者得褒,邾娄仪父称字,滕薛称侯,荆得人,介葛卢得名。”[1](p27)《春秋》王鲁,诸夏中国的诸侯王前来朝拜鲁王都能够获得《春秋》的褒奖,更何况远在化外的夷狄之楚呢!何休《解诂》曰:“《春秋》王鲁,因其始来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礼,受正朔者,当进之,故使称人也。”[9](p300)对夷狄部族,《春秋》以地名称呼其国。然而,能够对其称人,则又意味着《春秋》对荆楚南蛮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甚至可看作是一种肯定、一种勉励。能够向诸夏中国派遣使节,说明荆楚之地已经有国家机构形成和对外交往需要;能够向鲁国派遣使节,则表现出荆楚之人向往和仰羡中原王化政治的心情。
后世读者请别小看《春秋》于庄公二十三年所记录下的这次“荆人来聘”!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曰:“荆人,楚人。楚之通鲁自此始。”[11](p225)蛮夷之人也有与外界、尤其是与比他们先进的诸夏中国交通往来的愿望,因而才会有入《春秋》以来蛮夷部族首聘鲁王之举。它既标志着孔子王鲁思想普照化外、威力显现,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效;又可以说明蛮夷王化也已经有了初步改善,甚至还取得了可喜的实质性进展。《春秋》王鲁,荆楚之区能够使臣前来访问,说明其已经开始向慕王化、趋近于文明了,必须予以肯定。
夷狄称王、有纪元。从时间关系上看,鲁庄公二十三年,即是楚成王恽之元年。《史记·楚世家》曰:“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12](p327)楚成王一即位便施行德政,惠加楚地黎民百姓,主动向诸夏中国示好,派人向周天子纳贡献礼,接受周天子的教导和嘱咐,而使得荆楚逐步摆脱“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13](p1699)的野蛮阶段,而朝着诸夏中国礼乐文明的开化状态不断行进。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楚国是有王的,也有纪元,说明楚国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形式和自己的时间制度了。楚人自春秋时期便设置令尹之官,令尹可以“执一国之柄”,“在上位,以率万民”③。这些都是荆楚之地文明的开端。第二,楚成王既然接受了周天子的册封,《春秋》就应该承认其文明地位,而不应该再将其列入蛮夷了。据《史记·楚世家》,早在周成王时期,楚人首领熊绎就被周天子封为子爵,开始建立楚国。周王所封之国,也当是化内之区,可以共享三代文明成果。
对夷狄称人。然而,《春秋》对蛮夷的肯定也是有所保留的。何休《解诂》曰:“称人当系国,而系荆者,许夷狄者不一而足。”《春秋》使用“称人”之辞,则一般都会将其系在国名之下,这里却直呼州名之荆,意在表明其尽管有进步但仍然没有完全达到诸夏中国礼乐教化的普遍程度。不能因为夷狄有一个方面的进步,就承认其已经真正进入了文明国家行列,距离尚远,还需继续努力。《春秋》经文对荆楚从州称到人称的书法转折显然是在“进夷狄”,赞赏蛮夷向好的方向变化。
胡安国《传》曰:“荆自庄公十年始见于经④,十四年入蔡⑤,十六年伐郑⑥,皆以州举者,恶其滑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来聘,遂称人者,嘉其慕义自通,故进之也。朝聘者,中国诸侯之事,虽蛮夷而能修中国诸侯之事,则不念其滑夏不恭而进焉,见圣人之心乐与人为善矣。”朝聘之礼,乃是诸夏中国诸侯之王事。荆楚之人既然能够操持,则说明他们至少在这一件事情上也已经达到文明之国的水平。滑夏是滑夏,朝聘是朝聘,两件事情应该分开来对待和处理。一件事情做得漂亮,并不代表他们所有事情都能够做好而值得点赞和称许。然而,能够从夷狄之人“滑夏不恭”的诸多恶中看到他们的好,并且为他们的进步之点而赞赏,唯有圣人才有这样的胸怀与情怀。“凡变于夷者,叛则惩其不恪,而威之以刑;来则嘉其慕义,而接之以礼。”[14](p120)夷狄与中夏既然有距离,荆楚既然有“滑夏不恭”,也有朝聘之礼,就应该被区别对待,该惩治的就惩治,该褒扬的就褒扬,究竟是刑罚惩处,还是以礼相待,则千万不可混淆,否则也算不上是我们文明人干的事情了。
夷狄可以遣使。由庄公二十三年夏“荆人来聘”,徐彦《疏》则引出文公九年“冬,楚子使椒来聘。”鲁文公九年的冬季,楚缪王派大夫门椒前来鲁国访问、朝拜。楚子,即楚缪王,或楚穆王,楚国之君主,楚成王之子,名商臣,子爵,其父为谥号缪。鲁文公二年至文公十三年在位。椒,楚国大夫,芈姓,斗氏,名椒,字子越,又字伯棼。聘,原本是周天子与诸侯之间,或者诸侯国诸侯国之间派遣公卿大夫进行访问的一种外事活动,现在用于南蛮,则意味着荆楚之地已经成国,已经有与诸夏中国、与鲁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欲求。
《春秋》对荆楚称“使”,也是蛮夷之地的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使者,作为动词,指把官员派遣到外国进行政事活动。而作为名词,使者则指一国常驻他国的外交官员,或派往国外办理包括访问、礼拜在内的行政事务的代表。荆楚之地能够向中夏诸国派出外交使者,说明他们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也已经有了对外交往的现实需要,懂得诸夏之礼,遵循诸夏之礼,使用诸夏之礼,的确是他们趋近文明之邦的一大积极表现。
三、夷狄之君再贤,也只能称子
文公九年“冬,楚子使椒来聘。”经文能够对楚穆王称子,则也算是一种最高程度的褒奖。按照《公羊传·庄公十年》对夷狄部族之人与事所规定的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称谓,子称最高。从无爵到称爵,无论如何都是荆楚之君的进步表现,值得表彰和鼓励。相比于诸夏中国的一些不良君王,坏事恶事做尽,故孔子行使“王权”而不断褫夺其爵位,被《春秋》所“绝”。然而,夷狄之君虽有向化之心愿、慕王之心情,值得赞许,但至于能够实现多少则不能确定,故《春秋》皆不会把话说满,也不会直接将其当作诸夏列国君王一样看待。
胡安国《传》曰:“楚僭称王,《春秋》之始独以号举,夷狄之也;中间来聘,改而书人,渐进之也。至是其君书爵,其臣书名而称使,遂与诸侯比者,是以中国之礼待之也。所谓‘谨华夷之辨,内诸夏而外四夷’,义安在乎?曰:吴、楚,圣贤之后,见周之弱,王灵不及,僭拟名号,此以夏而变于夷者也,圣人重绝之。夫《春秋》立法谨严,而宅心忠恕。严于立法,故僭号称王,则深加贬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义;恕以宅心,故内虽不使与中国同,外亦不使与夷狄等。思善悔过,向慕中国,则进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绝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为《春秋》,非圣人莫能修之者乎!”[14](p229)显然,《春秋》进夷狄是“渐进”,而不是全进,并非一下子就把夷狄描绘得那么完美,而是留有余地,不使满足。其称国、称王、称使、称名,虽皆为“中国之礼”,但显然不可能是“中国之礼”的全部内容,距离还尚远。
胡安国以为,吴、楚之国原本也是圣人之后裔,只是因为他们趁着周天子权威衰退之际而私自封号称王,而遭到《春秋》的批评、指责和剥夺。吴、楚之为王,并没有得到周天子的许可,因而就是一种不合法的政治存在。孔子着《春秋》,一方面严判“夷夏之辨”,界限不容混淆;另一方面,每当夷狄之人做出善举,便予以褒奖,一次不落地都予以记录在册,以示欣喜和表彰,称国、称王、称使、称名……不一而足。可谓既“立法谨严”,又“宅心忠恕”,若非圣人,则肯定达不到这种思想境界和精神情怀。
公羊主张“字不若子”,子虽是《春秋》对夷狄之君的最高称谓,但也适用于诸夏小国之君。庄公十六年,冬,“邾娄子克卒。”克,为邾娄国的君主之名。字仪父,《谷梁传》《左传》作“邾子”。《解诂》曰:“小国未尝卒,而卒者,为慕霸者,有尊天子之心,行进也。不日,始与霸者,未如琐。”[9](p277)《春秋》称邾娄国君为“子”,称名却不称字。所传闻世,小国诸侯卒而不书,既书之则别有用意。邾娄国乃周武王封给颛顼苗裔侠的一个附庸国,曹姓,其最初的都城在今山东邹县境内。及至齐桓公称覇诸侯之时,邾娄君仪父能够归服、顺从,礼拜周天子,尊重君臣之礼,认同尊卑之序,值得鼓励,故《春秋》予以褒奖,进其爵而称其为“子”。邾娄小国,虽在鲁侧,但《春秋》却并未将其当作诸夏中的一员对待,毋宁一直以其为蛮夷未化之部族。可见,公羊家的“夷夏之辨”不在地理距离之远近,而在文明教化之有无。
四、夷狄虽有大夫而不氏
按照《春秋》之常例,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这里则说明《春秋》已经把荆楚看作有王制、有大夫之国了。故《公羊传》解文公九年“楚子使椒来聘”曰:“椒者何?楚大夫也。楚无大夫,此何以书?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则何以不氏?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大夫是一种官僚体系中的存在。能够设立大夫之职位,说明荆楚之地已初步形成自己的一套君臣制度与政治礼仪系统,开始向文明国家迈进了一步。但《春秋》经文依然没有直接称其氏名——斗椒,而省其氏,属辞还不能像诸夏中国之大夫那样名、氏双全。
何休《解诂》曰:“入文公所闻世,见治升平法,内诸夏以外夷狄也。屈完、子玉得臣者,以起霸事,此其正也。聘而与大夫者,本大国。”[15](p294)文公之《春秋》,为所闻之世。按照《春秋》三世说之划分,鲁国十二公中,隐、桓、庄、闵、僖为所传闻之世,属于据乱世;而文、宣、成、襄则为所闻之世,属于升平世。徐彦《疏》曰:“言见治升平者,升,进也,欲见其治稍稍上进而至于平也。”[9](p548)夷狄之治,在升平世只比据在乱世略有进步而已。
所谓“内诸夏外夷狄”,指以诸夏中国为内,而以四边夷狄为外。在孔子所闻之世,以内为亲为友,以外为疏远为敌雠,成为书写《春秋》的一项基本原则。事如成公十五年冬,十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会吴于钟离”,八国大夫的钟离之会,南蛮之吴的与会代表被排在诸夏中国代表的后面,是最后的位置。《公羊传》曰:“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9](pp757-758)以吴为外,秩序上则先中夏而后夷狄。又如僖公四年夏,“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夷狄之大夫因为其能够走出境而与一代霸主齐桓公会盟,才被《春秋》称为大夫。《公羊传》曰:“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尊屈完也。曷为尊屈完?以当桓公也。”一个蛮夷之地的大夫竟然也能够当面与齐桓公争辩,誓死维护楚国的核心利益,因而赢得了《春秋》的尊重。何休《解诂》曰:“增倍,使若得其君,以醇霸德,成王事也。”[9](p389)反过来看,恰恰因为屈完的存在及其参与会盟的生动事迹,齐桓公的霸业才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推扩,其“服楚”——驯服诸夏中国之顽敌才得以真正落实,其“救中国而攘夷狄”之伟大宏图才有了确凿的对象,其“王者之事”才能够施展更为开阔的普遍性。王闿运《笺》曰:“言楚子使屈完如师,则楚有大夫;故去其使,着其名氏,使成为大夫,以当桓公,如外大夫来盟例也”[10](p274),然而,楚大夫毕竟是楚大夫,在《春秋》经中,一时还不能与鲁国之外的诸夏中国大夫并列等同。
子玉得臣,也是楚成王的令尹,级别相当高的大夫。僖公二十八年夏,“楚杀其大夫得臣。”在《春秋》经中,杀大夫足以构成诸夏君王的一大罪恶。如果大夫无罪,君王死书其卒,却不书其葬,以示惩罚。因为大夫乃受命于天子,一国之栋梁,社会之精英,说杀就杀,则是对人才的浩劫,属于犯罪行为。何休《解诂》曰:“楚无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当言‘子玉得臣’,所以详录霸事。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骄蹇臣,数道其君侵中国,故贬,明当与君俱治也。”[9](p480)楚王杀子玉得臣,对楚国是损失,但对诸夏未必不是一件快事。
屈完、子玉得臣这样的楚国大夫,其事迹还能够被加载《春秋》经,除了出于孔子点赞夷狄有“渐进”的原因外,徐彦《疏》还分析说:“然则彼二人皆是传闻之世,未合书之而书之者,欲起齐桓、晋文霸事故也”[9](p549),亦即交代楚大夫,刻画其人事,也是为了烘托齐桓公、晋文公合诸侯、攘夷狄之伟大功效,连南蛮之大夫都一心向慕王道了,说明诸夏中国感化夷狄还是很有收获的,故而才值得《春秋》为之书。孔广森《通义》曰:“楚有大夫前此矣,至此发《传》者,屈完不称使,宜申称使而其君称人,君臣之辞未醇。此始因其能修礼来聘,遂与君臣之辞,同于中国也。商臣弑父而得称子以使者,其罪恶固不待贬绝而见。”[6](p95)《春秋》记录楚国有大夫,大夫能来聘,是对南蛮文明渐进的初步肯定,然而只称其名、不书其氏是因为凭借他们的先天资质暂时还不能一步达到中夏诸国的文明程度。
何休《解诂》曰:“许,与也。足其氏,则当纯以中国礼责之,嫌夷狄质薄,不可卒备。故且以渐。”这里的一个“质”字,很容易让人误会何休是一个种族论者,实际上他也并不是主张夷狄之人先天禀赋浅薄而诸夏中国之人先天聪慧,他只是就文明积淀层面而言。人类的任何文明形式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和演化过程,忽略自身基础的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诸夏中国传承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优秀成果,积累时间长达数千年之久。荆楚之地从野蛮走向文明也有一个必要的历史过程,要想打牢基础,就必须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学,一步一步地前进,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获得突飞猛进。
五、对夷狄贤臣称名而贬
襄公二十九年夏,“吴子使札来聘。”吴王派遣大夫季札来鲁国访问。季札是吴王寿梦的幼子,吴王谒的同母四弟,因采邑于延陵,故又称延陵季子。刘尚慈称其“贤而有德,让国于阖庐。”[16](p500)《春秋》对吴王称子,对其派遣大夫来鲁访问之事称使,都充满了对吴国的褒奖之意;而唯独对季札却直接称名,《公羊传》云:“札者何?吴季子之名。《春秋》贤者不名,此何以名?许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吴国大夫季札贤而有德,连王位都愿意让给阖庐,足以见他是何等的谦逊和伟大。王闿运《笺》曰:“据祭仲、纪季皆不名。”[10](p446)《春秋》记录贤者之事一般都不会直呼其名,以示尊敬,为之避讳,但对季札则称其名,就是要说明蛮夷部族走向文明中国的行列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余地和加以完善的空间。
在所传闻之世,孔子严判“夷夏之辨”,绝不助长潜伏在诸夏中国四边的野蛮力量。《公羊传》曰:“季子者,所贤也。曷为不足乎季子?许人臣者必使臣,许人子者,必使子也。”吴王寿梦之四子分别为谒、余祭、夷昧、季札,一母所生,感情深厚。季札年幼而有才,深得大家喜欢,便都想推选他继承父亲的王位,但季札却不肯接受。于是谒便想出一个四兄弟从大到小相继传递的办法,而迫使季札最终顺利接班。谒、余祭、夷昧前面三位迭相传承之后,轮到季札时,他却出使国外,行踪消失。国不可一日无君,吴王寿梦庶长子僚便称王,在位十一年。夷昧之子阖庐派人弒僚⑦,而把国家王权交给叔叔季札,季札不受,理由是:“尔弑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于是便西去延陵,终身隐退,再也没有踏进吴国都城半步。
季札的拒绝,是以亲情为重,他实在不愿意让叔父、兄弟之血缘关系陷入一种彼此残杀的恶性循环。“君子以其不受为义,以其不杀为仁。”季札有仁有义,能够让出天下人都不愿意让的江山社稷,其实连诸夏中国都很难产生这样的贤德大夫⑧。然而,胡安国却不以季札为贤,相反,而批评曰:“辞国而生乱,札为之也”,季子才应该对让国之后所导致的祸害承担一定责任。三哥夷昧死了之后,“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但他没有做出这样的理智选择,而是“徇匹夫之介节,辞位以逃夷末之子僚”。作为公子,作为大夫,季札在吴国王位交接的关键时刻,不顾一国之安危,也不遵守四兄弟之契约,顾念血缘情感,恪守凡夫小德,而选择回绝、退避。“季子辞位生乱,而《春秋》之所贬。”[14](p381)这才是经文忽略季子之贤德而对其称名的真正原因。胡安国之解,虽有道理,但不符合《公羊传》的诘问和回答,故暂且不从。
《春秋》经“贤季子则吴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为臣,则宜有君者也。”尚未开化的南蛮之吴竟然涌现出季札这样的贤臣,便可知吴之君王也一定很有德行,应该褒奖,称赏其进步。有其君则有其臣,有其臣则必有其君。“许人臣者必使臣,许人子者必使子也。”既然答应做了君王的臣子就必须使自己有臣子的样子,既然做了父亲的儿子就必须使自己有儿子的样子,名实相符嘛!《解诂》曰:“缘臣子尊荣,莫不欲与君父共之。字季子,则远其君,夷狄常例,离君父辞,故不足以隆父子之亲、厚君臣之义。季子让在杀僚后,豫于此贤之者,移讳于阖庐,不可以见让,故复因聘起其事。”⑨臣子获得荣誉,被《春秋》所表彰,其君王也应该跟着分享才对。如果《春秋》经文对季札称子,虽合诸夏中国大夫之例,但却表现得与他的君王距离太远,因为野蛮、落后的君王是培养不出具有如此贤德的卿大夫的。如果过分抬高对季札的属辞,则有可能导致君臣伦理破裂、父子亲情受损,而不利于加深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王闿运《笺》曰:“使臣子者,使其为臣子,不以贤逾君父也,仍用七等待吴,适足以起季子之荣其君父。”[10](p446)所以,经文称季札之名,是在故意压低夷狄大夫的属辞档次,并不符合季札本人的实际德行情操。这也是一种“许夷狄者不一而足”的特殊书法,值得读者铭记。
六、结语
《春秋》经申明“夷夏之辨”,严判文明与野蛮的界限,对诸夏中国的堕落则“夷狄之”,对夷狄的进步则“中国之”,态度鲜明,原则性强。成公三年“郑伐许”⑩、昭公十二年“晋伐鲜虞”之类,皆非文明人所干之事,属于不耻之举,故《春秋》皆以其为夷狄。桓公十五年夏,“邾人、牟人、葛人来朝。”邾娄国、牟国、葛国,三小国君王前来朝拜鲁桓公。事情未必发生在同一天,但《春秋》兼之,把它们放在一起载录而不加细分。《公羊传》曰:“皆何以称人?夷狄之也。”《解诂》曰:“桓公行恶,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为众,众足责,故夷狄之。”[9](p186)显然“中国夷狄化”也没有底线,没有限制,当贬则贬,当绝则绝,《春秋》不留情面,虽然经常会为之避讳,仍不时以一种曲折的方式予以批评和谴责。儒家是要求仁民爱物的,但爱也有差等。董仲舒曰:“王者爱及四夷”[1](p52),而《春秋》却“许夷狄者不一而足”,原因就在于,夷狄之进步虽然可以满足礼乐文明的一个条件但并不等于满足礼乐文明的所有条件,“夷狄中国化”则有底线,有限制,表彰夷狄之进步,要打折扣,不会一次性把好话说完,有分寸,有节制,保留余地,这并不是出于地域、种族的歧视,也不承认人们在先天禀赋上存在难以敉平的巨大差异性,而是始终在强调夷狄慕王向化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对照王道标准,排出成功条件,必须有所积淀,形成基础。其达到诸夏中国的文明教化程度,是“渐进”而不会一蹴而就。孔子之所以如此限制夷狄,追究其历史原因则可能是,他活着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后来四边夷狄与诸夏中国日益频繁的交流往来和不断加强的彼此融合。但至汉初时代,“大一统”帝国的地理疆域早已突破了原先的华夷界限,再主张打压夷狄则显然不合时宜,因为当下朝廷与诸侯封国、四边藩属的关系已经是“只有地方性而不复有种族性的问题”。从《春秋》经到董仲舒所强调的“夷夏之辨”及其“进夷狄”限度要求,应该被理解为“熔铸各种族为一体的一股精神力量”[2](p223),这股精神力量太重要,以致于它对齐桓、晋文的霸业成就,让诸夏中国联手抱团而抗击外侮,以及武帝的北攘匈奴,南征南越,开疆拓土,以及凝聚天下人心,建构中华大家庭的身份认同,形成华夏主体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①参阅[汉]司马迁:《史记》之《管蔡世家》《楚世家》,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277页,第33页。
②七等第之中,段熙仲还有“子(五十里)”“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之分疏。见《春秋公羊学讲疏·名例》,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2页。
③参阅[汉]刘向:《说苑·至公》,见向宗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59页。
④事见《春秋·庄公十年》曰:“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⑤事见《春秋·庄公十四年》曰:“秋,七月,荆入蔡。”
⑥事见《春秋·庄公十六年》曰:“秋,荆伐郑。”
⑦阖庐弒僚,事见昭公二十七年“夏,四月,吴弒其君僚。”《解诂》曰:“不书阖庐弑其君者,为季子讳,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杀,让国阖庐,欲其享之,故为没其罪也。”季札与阖庐之间,是叔父与侄儿的关系。阖庐弒君,虽有罪,但为了吴国的安宁,季札不予追究,而让他享受王权,于亲情加深、于国家稳定都有益处。《春秋》先是为季札避讳,继而为阖庐避讳,故不书季子让国之文,就是为了使读者看起来就好像根本就没发生过季札让国这回事一样。引文见张岂之主编:《十三经注疏》,[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昭公二十七年》,第一0一九页。
⑧在孔子那里,能够让出江山社稷,则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至德”。《论语·泰伯》篇记孔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何晏注“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长子。次弟仲雍,少弟季历。季历贤,又生圣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让于王季。’”皇侃疏《论语》引范宁之说时,也解释道:“太伯病而托采药出,生不事之以礼,一让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历主丧,死不葬之以礼,二让也;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季历主祭,祀不祭之以礼,三让也。”采药不归、父死不还、“自号勾吴”,构成所谓“三让”。泰伯之让天下,并非已经实有了天下而拱手让出,而是以泰伯之德行,拥有天下理所当然,所以孔子才说他是“以天下让”。可参见余治平《“泰伯三让”何以“无得而称”》,上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10 期。季札让国是“泰伯三让”在春秋时代的翻版,也是诸夏中国之道德在南蛮之地的一次鲜活演绎。
⑨参阅张岂之主编:《十三经注疏》,[汉]何休,[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襄公二十九年》,第八八六至八九0页。
⑩董仲舒批评郑国说:“卫侯遫卒,郑师侵之,是伐丧也;郑与诸侯盟于蜀,以盟而归诸侯,于是伐许,是叛盟也。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见[清]聚珍版影印《春秋繁露·竹林》,第一八页。
[1] 董仲舒. 春秋繁露//乾隆三十八年聚珍版影印. 诸子百家丛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2] 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3] 周祖谟. 尔雅校笺·释地[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4] 任继昉. 释名汇校·释州国[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5] 雒江生. 诗经通诂[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8.
[6] 孔广森. 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庄公十年//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二九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7] 顾馨, 徐明. 春秋谷梁传·庄公十年[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8] 左传·庄公十年[M]. 蒋冀骋标点. 长沙: 岳麓书社, 1988.
[9] 何休, 徐彦. 春秋公羊传注疏. 刁小龙整理//张岂之主编. 十三经注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10] 王闿运. 春秋公羊经传笺//续修四库全书(第一三一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1]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庄公二十三年(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2] 司马迁. 史记·楚世家[M]. 长沙:岳麓书社, 1988.
[13] 班固. 汉书·匈奴传赞(下册)[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14] 胡安国. 春秋胡氏传·庄公二十三年[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
[15] 何休, 徐彦. 春秋公羊传注疏·文公九年//李学勤主编. 十三经注疏(标点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6] 刘尚慈. 春秋公羊传译注·襄公二十九年(下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022-04-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董仲舒传世文献考辨与历代注疏研究”(19ZDA027);上海交通大学“董仲舒学者支持计划”项目“春秋‘大一统’的观念兴起与历史影响研究”(HS-SJTU2020A01)
余治平(1965-),男,江苏洪泽人,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B222
A
1008-4479(2022)04-0046-10
责任编辑 陈建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