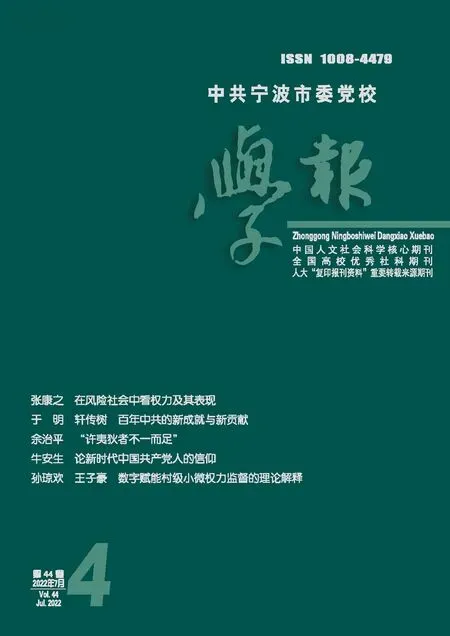“极”高明而“道”中庸:汉语生态哲学刍议
胡晓艺
“极”高明而“道”中庸:汉语生态哲学刍议
胡晓艺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北京 100091)
“无极”“太极”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通过哲学史的学术梳理可以“说”出汉民族的致思历程,而以文字为认识论,对汉语“极”字作哲学分析,则可以“道”出汉民族本源的生态存在。由此出发对汉语生态哲学进行思考:一方面,对汉语文字进行生态哲学维度的挖掘,汉语文字作为一个生态的系统,可以“道”出汉民族天人合一、心物同源的存在,词汇的边界拓展道出汉民族思维的“活络”;另一方面,从汉语文字角度对中国哲学具有生态意蕴的命题、概念进行开掘,汉语“道”生态,需要哲学学者去“道”哲学,对汉语生态维度的“天地不言”予以哲学的“再言”。“极”高明而“道”中庸,于“静默”的“书写”中突破西方语言哲学“词”与“物”的逻辑,代之以“文”与“道”的学术自觉,探索从让哲学“说”汉语,到让汉语“道”哲学的当代“讲”法。
无极;太极;汉语哲学;生态哲学;存在世界
一、作为中国哲学核心概念的“无极”“太极”的一重考察
“无极”最早出现在道家文献中。《老子》二十八章有“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根据张岱年先生的统计,老子之后,“无极”在《庄子》中出现了四次,分别是《逍遥游》“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宗师》“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在宥》“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以及《刻意》的“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无极”在《荀子·修身》中使用过一次,“将以穷无穷,逐无极与?”这几处“无极”的含义,与“无穷”接近[1](p501)。此外,在《淮南子》中也有“极无极”“精神澹然无极”“游无极之野”“终而复始,转于无极”“运乎无极,翔乎无形”“还反无极”等说法,《列子·汤问》说“物之始终,终无极矣”。在这些论述中,“无极”是对天地万物始生之前浑沌不分的状态的描述,“无极”是宇宙形成意义上的万物之源[2](p83)。“太极”最早见于《庄子·大宗师》“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后来《易传·系辞》吸收了“无极”“太极”概念,朱伯崑先生在《易学哲学史》中分析过《易·系辞》“易有太极”章中“太极”一词的内涵。通过比较先秦与后代易学文献,朱伯崑先生认为,“太极”作为一个范畴,在易学史和哲学史上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其最初的涵义指空间的最高极限,如《庄子·大宗师》中所谓“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先秦的文献中,“太极”还不是描述本体或实体的范畴,在《系辞》中“易有太极”章与“大衍之数”章逻辑相同,指六十四卦的根源,是对筮法的描述[3](pp62-64)。“太极”概念说明了易学哲学的两种语言,“易有太极”章虽然是讲筮法问题,但认为从太极到八卦是一个生化或分化的过程,后代的易学家与哲学家从中得到启发,形成一套关于宇宙形成的理论,“太极生两仪”说成为与《老子》“道生一”说并立的一套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宇宙形成的理论。
“太极”的阐释史成为中国哲学思想演进的一种说明,在汉代气论思想的影响下,“太极”逐渐演变为实体的概念,成为说明世界的始基和本体的范畴。汉代宇宙生成模式可简化为无形到有形的形名理论,郑玄以《易纬》中的“太易”为未有形质阶段,以“太极”(包括太初、太始、太素)为有形质阶段,“太易无世,太极有叶,太易从无入有”为汉代宇宙生成论思想的延续。但是他通过借《老子》自然无为解《易》,认为“太易既自寂然无物矣,焉能生此太初哉。则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乾凿度》注),进而指出易道最大特点和根本规律,就是以无为去顺应万物的自然本性,使得万物自通,“此皆言易道无为,故万物得以自通”,因而人们从易道中得到的启示应是“效易无为,故天下之性莫不自得也”“夫惟虚无也,故能感天下之动;惟清静也,故能炤天下之明”(《乾凿度》注),成为中国哲学宇宙论向本体论思想演进的重要环节[4](pp281-284)。
随着道教的出现,“无极”的概念大量出现于“道经”之中,佛经也借用“无极”的字眼,如《大明度无极经》。“无极”概念在不同思想传统的使用,显示出其影响力的深化,更有助于其义理内涵的充分展开。“太极”在魏晋哲学中向本体论范畴转进,玄学本体论将先秦两汉的宇宙本根从天地生成移向人伦事物之内,说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这个过程整体上经过王弼“名教本于自然”,以大衍之数五十不用之“一”为“太极”的说明,经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辩证否定,最后在郭象“名教即自然”处汇合。“无极”到“太极”便不仅是一种宇宙生成过程的描述,也是一种自然无为的浑然到与物无对的中和境界的抽象表达,两种致思方式在宋明道学的易学展开中得到进一步发挥。
儒家对于“无极”概念的接纳,始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并在儒学内部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宋代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自无极而为太极”,以解释宇宙的天道到人道的形成过程,周子之说引发后代释义分歧,史称“无极太极之辩”。朱子标榜“太极”思想所蕴含的“理”,认为“无极而太极”是以“无极”为“太极”的性质,而非宇宙论的形成。朱子以“太极”为“理”的说明,“‘无极而太极’,只是说无形而有理”,以“无极”为“太极”无计度、无造作的自然状态,“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5](p454);朱子言“太极”:“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极也。所谓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者,于此尤可以见其全矣。”[6](p74)又指出:“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周子所谓太极,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7](p2371)在朱子哲学中,“太极”贯通天道人道,从而完成人伦世界的本体论的说明,表明人在天地中本根的存在方式与人道合于天道的价值规范意义,是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本体论表达。而陆象山主张周敦颐所言是“自无极而为太极”,是对宇宙生成的说明,使“吾心”与“宇宙”在心的经验世界中合一。王阳明以“须知太极元无极”“人人有个圆圈在”[8](p85)说明“良知即易”“无极”“太极”都是无善无恶的心体,两者均“与物无对”而“万物一体”。但就人的“觉”而言,“无极”“太极”体现“先天”“后天”之分,从先天到后天,反映阳明“良知”的本体、“致良知”的功夫到“致极良知”的圣人境界的“不二”而“有分”,也体现宋明哲学融汇三教后的哲思结构。
总之,在传统哲学的论述中,“无极”和“太极”都是在万物之先的根源性范畴,或为本原,或为本体。从无极到太极或者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时间性过程,或者无极是对太极的说明,二者同为本体,从无极到万物是本体显现为现象的过程;无极为虚无实体,太极为浑沌之气,或者无极为无具体规定性,太极是理[2](p87)。在宋明哲学家那里,“太极”从本体的意义上说明了天和人是贯通的、一体的,在综合前贤思想基础上,较完整地形成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本体论建构,“太极”的天人贯通性表达了中国人在天地间存在的根本方式与价值根源。及至近代,“无极”“太极”理解的分殊与诠释体现了中国哲学面向西方进行自我反思与创造性发展的重要侧面。熊十力以“心物同源”讲乾坤易蕴,注重太极之气的“有灵有则”,在唯实转圜处开物成务,归本大易以为中国文化生生新种[9](pp528-529);冯友兰先生至晚年仍强调,朱子与陆象山的分歧关键是朱子有“两个世界”,“一在时空,一不在时空;盖朱子的心是具体的,理则是抽象的”,而象山只有“一个世界”,“即只有一在时空之世界”[10](p216)。朱子“太极”的“理”世界说明中国哲学思想发展也达到了“所以有”者的形上世界,而不仅仅在“所以在”者的形下世界,以进行中国固有思想材料的“哲学”分析。金岳霖先生以“无极”“太极”说“道”的无始无终却有“极”,“无极”为“道”的“无始的极”,“太极”为“道”的“无终的极”,借鉴西方哲学思想对传统思想资源进行发展[2](pp83-95)。同时,金岳霖先生以“太极”说自然是真善美如的统一,“太极为至,就其为至而言之,太极至真、至善、至美、至如”,是对中国传统生态哲学智慧的极高概括。可以说,“无极”“太极”概念理解的演变不仅反映了汉民族思维的发展历程,也体现出对本民族思维的反思情状。
二、文字作为认识论:文字“极”所“道”汉民族思维的另一重考察
为何“无极”“太极”能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并反映民族思维的重要特征?从汉语“极”的哲学分析,以文字为认识论,以文字“极”所“道”汉民族思维作另一重考察。
东汉许慎《说文》①中有两次提到“极”,一个同于今日所写之“极”,许慎释为“驴上负也。从木及声”,是指驴上承载东西的木板;一个在古书繁体中写为“極”,许慎释为“栋也。从木亟声”。《说文》中“极”作为所负笈之木箱意思后转给“笈”,繁体木之栋意之“極”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极”的词源。在这里,“极”是指木质房屋的房顶最高处,是名词。
“极”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中是一个重要标准,与其词源意密不可分。《尚书·洪范》箕子对武王陈“建用皇极”的治国大道,后“皇极中道”被儒家认为是王道政治的理想实践。朱子解为“‘皇者,君之称;极者,至极之义,标准之名也。”[11](p134)由于华夏中国处于温带季风气候区,木制房屋的构造要便于雨水下流,因而房屋顶部总是有屋脊高凸,那最高的横梁就是此处的“皇极”,它表达了两层内涵:最高与中间,且最高处在中间,代表着王道上接天意,下爱万民,应取公道、中庸与平衡。“皇极中道”既体现出建筑的自然功用与审美趣味,也是王道价值的体现,由王道引申为人道,就儒家价值理想而言,体现在君子“立人极”的道德实践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追求,体现一种非对立的对待思维。
就“极”的词汇意义的范畴边界而言,它从最初的与木制房屋构建相关的基本含义逐渐应用到表达“极限”概念的生活世界的一般意义,与民众使用“本末”等一样,较早可以离开木的原始含义而使用,但向上溯源,又有民族天人相与的思想留痕。“极”限就是屋之高处,代表人向天的努力,但无论是庄子“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还是“易有太极”的筮法含义向宇宙生成转化的思想脉络,“无极”“太极”是说明易道或天道的实体,也是人可以修身向内、反以相天,却不显扬于外、自高于天的终极所“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无极”“太极”概念正是汉民族这种思想世界的一种哲学抽象。
“太极”关联中国人的“宇宙”观,即时空意识的表述,宗白华先生曾有论述,他考察了“宇”和“宙”的字源学,认为“横架于宇(空间)上的宙(时间)就是太极,就是世界的创造性原理。《易》云:‘时乘六龙以御天’。中国古代农人的农舍就是他的世界。他们以屋宇得到空间观念,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击壤歌》),即从宇中出入作息,而得到时间观念。空间、时间合成他的宇宙而安顿着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从容的,有节奏的。对于他,空间时间是不能分割的。”宗白华先生的论述为我们理解农耕文明的华夏民族的时空观,即他的宇宙观,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也涉及到对“太极”的时空涵义的提示[12](p24)。
细究为何“极”字能够表达中国人政治治理的智慧与哲学思辨的概念,可以进一步追溯到“极”在较早时期与指涉天象密切相关。《论语》中孔子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尔雅·释天》中“北极谓之北辰”,郭璞注“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夏小正》载“正月,斗柄悬在下”,《史记》言北斗齐“七政”,综合考察文献资料可知,北极正是北辰、北斗星,由于北斗永远指向正北,人们想象其为天帝的车乘,在天穹中旋转,如同天帝乘车巡游天界,用它来方正四时,框定历法,而圣人明王正如北极星一样,永远有信,以为垂范。在中国古代,农时历法对民族生存繁衍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掌握可以指导农时的天象知识是古代帝王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与治理能力的体现。正是“极”作为天时星象的词源使用,使得它具有超越一般词汇的意义之境,因而在先秦文本中就被使用,并逐渐以“皇极”“太极”“无极”等核心概念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实践与思想世界。
再就“极”的词汇引申考察,“极”不仅有名词意义,也有动词、副词用法,如“潮平两岸阔,极目楚天舒”,有一个向极致努力的动态意义;如《周易·系辞上》中“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此处“极”与“研”应为探寻深微的努力、研磨。动词再向副词转化,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引申为一般的极限、极致,如极低、极坏也用极。“极”本义的高、中道、王道、天道上达的褒义偏义的名词向中性词副词转化。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理论一般以为是名词向动词、副词,褒义向中性义、贬义的引申,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从词源词族等考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13](pp6-8)。整体而论,从文字使用的角度说,是名词性的“极”向动词性的、副词性的“极”引申;就人类构造文字的思想史而言,人类最基本的一些理性认识,即表现为抽象含义的一些词义,如柔刚、纵横、曲直、强弱、明暗,等等,不可能在文字产生以后才逐渐获得,而是这些理性认识指导人类对整个世界同类现象的观察和命名。但是这两者并非不可调和,且可以由此出发,对汉民族的“象”思维的抽象—具象关系获得新的体会。
仍以木部文字中也是中国哲学思想重要概念的“柔”为例。《说文》释“柔”为“木曲直也”,《尚书·洪范》言“木曰曲直”,被解释为曲直的“柔”可以理解为表示木的一种具体属性的显象的柔枝,也可以理解为树枝的一种抽象属性而脱离木而使用。如果从文字的造字哲学的逻辑而言,人们不可能先有“柔”之一词的出现,才有对曲直的抽象认识。当先有对曲直的抽象理解,再加诸到具体的事物上,木枝最能体现曲直的属性,因而以柔为树枝的具体指称,同时可描述树枝的基本属性。所以《老子》中描述“水”为“天下之至柔”也用木字旁的“柔”,就是“柔”作为抽象意义的具体使用,这种具体使用会不断分化、孳乳而生众多词汇,但作为理性认识中最一般概念的“曲直”属性的词义则处于极稳定的状态,反而成为最“基本”的词义。照此而言,中国人不仅具有“抽象”思维,而且将“抽象”思维的表达以“形象”的方式标出,如“极”与“柔”都从“木”部,而部首又是一类更高抽象的统领。
部首可以作为“范畴”而理解[14],这是我们考察中国文字容易忽视的文字哲学意涵。如以“木”为例,许慎《说文》“木”部的释义为“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从屮,下象其根。凡木之属皆从木。”“木”便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现象的部首,而恰恰如许慎的说解,代表一种东方之冒的性质(其中蕴含的汉易天人宇宙论的思想背景暂且不论),木部部首具有一种一般的抽象性质,以此种抽象性质统领处于此一般抽象性质下的具体文字,这些文字又有自己的抽象性和具体性的分殊,如“柔”又是木性下的一种一般抽象,但是在归属于木部上,木性是作为“文”的“母亲”,孳乳而生众多具体的“字”。部首之间的一般抽象性也有区别,“木”由于具有“五行”的哲学思想背景,因而其一般抽象性比一般部首更高,在级别上低于“一”(许慎部首排列“始一终亥”)同于其他四“行”,而高于其他部首。
以上分析对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或提供了一些启示,中国人并非没有“概念”,而是概念并不需要一个“纯粹”的“形式”予以表达,概念可以通过具体的形象进行“意会”。(“概”从木,为平米之量具,“纯粹”中有丝有粮)这种致思方式可以反思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文字即体即用,既可以作为“言在”以表达存在,也可以“在言”自身即是存在,近代学者运用西方哲学的诸概念来说明中国哲学的这种思维,如杨国荣等学者提出过中国哲学具有“具体的形上思维”[15](p49),也有学者提出过“形而中学”的概念[16](p211),随着学界逐渐对“哲学”是复数概念,由此也必须承认哲学有“家族类似”的类型学差异取得共识时[17](p58),如何表达汉民族的哲学使得汉语哲学的研究方兴未艾。而汉语言文字的“象”思维的“能指”维度为汉民族具体的存在世界提供了另一种说明。其实,“在世”的民族与“在世”的人都有它的“认识”,它与世界在本体意义上已经是一体化的,没有任何一个成熟的民族没有它的概念,只是如何表达它的概念[13]。对汉民族而言,让“汉语”进入哲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反思”民族之“思”如何“进入”民族生存世界;对世界而言,它促进人类对世界的整体理解达到全面认知。
三、“文以合天”:生态进入汉语哲学研究的新思路
透过“极”字与引申的木部文字的简单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汉民族“象”思维中形象与抽象的互相涵摄,它表明语言是“在手”的;一个“字”作为一个范畴,它直接可以连接人意与天机,它又说明语言不仅是“在手”的,而且本身就是“在”,这是汉语言文字为我们突破“纯粹”的“概念”演绎民族思维的重要思路。而我们接下来要追问的是,汉民族的“文”与“在”如何不同于西方的“词”与“物”的逻辑,而得以在“敞开”的“观象”中,直接“道”出不曾被“遮蔽”的思维?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文以合天”,即中国的文字本身作为一个生态的系统,直接“道”出汉民族本源的生态存在。
生态部首道出汉民族存在的根源。与“木”一致,汉语语言中有大量诸如水、火、金、土、草、鸟、兽、虫、鱼等一系列生态系部的词汇,这些生态部首大量构成了汉语文字,在“六书”系统中,多为最基本的象形字构字法。象形字当源于图形文字,只是图画意味减弱而象征意味加强,一般是一个整体,段玉裁归纳为“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章太炎说“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故象形字是“文”,描绘事物轮廓线条的独体象形,数量最多,也是汉字系统中用来构成合体字的基本字根(构字部件)[18](p92),即在汉民族语言的基本构字中,以生态的存在为构字字根。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作为一个个普通字根的部首,在根源处都诉说着汉民族的天人合一的存在,这在东汉许慎的《说文》中有着独特的呈现。就字书编纂而言,许慎的《说文》部首排列始“一”终“亥”,中间间杂木、火、土、金、水五行系统,以天干地支系统作结,所有部首呈现树状分布,540个部首的选取和排列体现汉代宇宙观与自然元气论思想,展开次序反映人类世界的智慧比照天意的展开。由于天意具有阴阳变化、衍生万物、周而复始、包罗万象的功能,因而部首的展开即是孳乳繁多,有序展开而互相关联的过程[19]。作为“经书”的“字书”,《说文》不仅是对上古文字系统的总结,在汉代宇宙论与元气观念的影响下,更是将文字纳入天道系统,以文字的孳乳展开说明天道的生生流行,以“文以合天”的建构完成对“天人相与”的建构。因而文字并非作为言的“符号”,隔阂“人”与“在”,其本身就是汉民族“天人相与”的生态存在的直接表达。
生态词汇道出汉民族思维的特点。象形构字具有抽象性、简化性、分化性、指示性、会合性的特点[20](pp22-23)。两个象形之文“会”而构成新“意”,如双木为林,三火为焱;通过“指”点而成“事”(物),如木下为本、木叶为末。汉语文字学的研究表明,大量的形声文字出现于周代后期,汉语文字通过“声化”的特殊形式,在保留义旁的同时,加上具有意义的声旁,文字孳乳繁多,没有走上拼音化的道路。汉语每一个文字通过部首的追溯,都可以看到源头处的意义,汉语文字是有“根”的;又可以通过部首保留基本含义的同时,加上不同的声旁,声旁亦含“义”,“肖其声而传其义”[21](p13),创造新的文字,而“转注”以为同一部首的字义追溯、“假借”以声为文字的拓展,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以假为真”,文字之间获得互训的可能,汉语文字又是“活络”的。我们从“本”“根”而追溯到“木”,由“活”追溯到“水”,“络”为丝线之活结,汉民族思维即在文字之中彰显。由是观之,汉语生态部首可以作为“范畴”考察民族思维的情状,乔清举在水系文字的考察中给出了水系文字从具体到一般哲学抽象的五层结构[22]。木系文字亦然,对字书与词典作哲学分析,可以将木系词汇分类为:(1)果木专名(如桃李杏);(2)引申为生活世界的具体词汇(如“桂”从树木引申为地域专称);(3)引申为生活世界的一般抽象词汇(如材,构、荣华枯槁);(4)上升为汉民族致思的哲学抽象概念(如极、机、本末、柔、朴);(5)尤为重要的是,木系文字的“活络”边界可以直接道出华夏民族思维的开拓与存在世界的拓展。最重要的体现就是佛教进入中国后,在木系词汇中创造了“梵”等新词、拓展了如“相”“果”“集”等词汇的意义,丰富了“森”“染”等词汇的感情色彩,并在引申而言的“竹”“荷”“花”等草木的“无情有性”的探讨中丰富了汉民族的“感物”深度[23](p390),成为理解宋明道学的重要命题如“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理解近世中国文化新变的殊胜前缘。可以说,生态词汇道出汉民族思维是自然的、实践的、开放的、生长的。
四、“文以载道”:从哲学“说”汉语到汉语“道”哲学
汉语生态维度的挖掘“道出”汉民族的存在根源与致思方式,也“道出”了“道不出”的中国哲学面临的困境与突围的可能。
概而言之,汉语哲学主要有语言哲学的进路(以英美分析哲学“语言”研究为代表)、现象学的进路(以德国现象学哲学诸家对“言”进行现象学之“在”诠释为代表)、文字学的进路(以洪堡特之后对汉语“文字”特性的发现与阐释为代表)和哲学人类学的进路(以舍勒、福柯与德里达等“词物”“图符”研究为代表)。大陆学者韩水法、江怡等从语言哲学的视角给出了方法论探讨,彭永捷将汉语哲学的发展历程概括为“胡话汉说—汉话胡说—汉话汉说”三个阶段[24],刘梁剑关注基于翻译的现代汉语词汇范畴对古典思想的容纳力,李巍偏重从汉语语法结构分析中国道理的言传之路,尚杰、夏可君等从文字哲学、书写哲学的进路,港台学者关子尹对六书的现象学诠释,林远泽对汉字思维的探讨等都给出了开创性的探讨。当然,亦有学者对“汉语哲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张岱年先生指出,词汇本身就是不同时代人类不断创造的表现,哲学话语是通过这些不同词汇的差异发展起来的。在理论的高度上,学者虽然方法不同,但普遍的关怀在于,汉语哲学不仅是让哲学“说”汉语,而是关于哲学本身的问题,也就是哲学的普遍概念是否可以在汉语中得到理解的问题,是哲学的问题意识如何在“母语”中进行哲学表达[25]。因而,汉语如何“道”哲学,将是汉语哲学乃至中国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如果哲学研究包括对“在世”之人与“在世”之民族的存在方式的整体而系统的把握与反思,那么哲学研究者如果疏离了自己存在的根源,这个民族的哲学研究必然展示出一种貌似“世界性”的“区域性”特征,而如果哲学研究者熟练地道出民族的致思情状,并真诚指出借鉴融合的可能,哲学研究才是一种基于“地方史观”的“全球”对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文史哲领域的三大论争——汉字性质论争、中国社会发展停滞论争、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论争——其实异域而同质:它们的一贯态度都是“疑”。汉字性质的论争以“文字发展三段论”(图画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和“语言发展三段论”(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说明中国文字始终没有走向拼音文字,进而说明中国人形象思维的原始性[26];1500年以后中西方历史的“大分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而始终“无果”,说明唐宋以后中国近世社会发展的停滞[27];而哲学上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似乎更为严重,作为纯粹之思的“哲学”如何表达中国人的“爱智”,中国人“爱智”吗,经学何以非“文言”,生命的学问何以对象化,诸多问题都困扰着转型时代的学人。哲学研究者如果深入考察汉字性质的论争,便会发现一条与中国哲学道路相似的发展脉络:在汉语文字领域表现为汉字的拼音革命张本(典型者是20世纪20年代钱玄同《汉字革命》中的观点)—证明汉字表意文字有音声(30年代徐银来的“音义系文字”、40年代唐兰的“含有义符的注音文字”等)—独立探索汉语文字的特征(如裘锡圭的“意符”“音符”“记号”说,到跳出汉字构造,从语言与文字单位关系的思考,如近年来的“语素文字”说等)[28]。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则是从西方哲学范式的引进、以哲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具有哲学性质的思想史料、到中国哲学独特范式的创新开拓。语言文字的“迟滞”、思维的“浅滞”,实际是关联为一的,在现实中表现为历史的“停滞”。它们遥相呼应而丝丝入扣,从宏观上反映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超越“以西释中”模式,从“人云亦云”向“自我主张”的变迁[29]。
因而,当今中国汉语哲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如何不仅仅是让哲学“说”汉语,而是让汉语“道”哲学,必须拥有对本民族存在根源的真正了解,这其中的双重契机就是生态哲学的视域与哲学诠释的方法。生态哲学虽然兴起于工业革命后,伴随着对人类生存样态的反思,它以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而关怀人类,以“新启蒙运动”即生态启蒙的方式重新定义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有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地与我并生”等主张已经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在儒家生态哲学领域已经有了较为详实完整的哲学体系建构[30],道禅哲学的山水自然思想也受到了海内外学者重视。如,从哲学思想史的角度,肇始于先秦儒家“万物皆备于我”的修身诚意正心的儒学主张,吸收道佛思想,在宋明提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哲学命题正是人类心灵的延展,与当今心灵哲学、生物学哲学广泛探讨的“延展心灵”问题可以开展诸多探讨的可能[31](p147)。而从汉语的生态哲学视域也可以说明,每一个汉字都有一个丰富的物我合一的世界,金木水火土、山川雷泽鸟兽虫鱼……汉字的每一个构件皆非“物自体”之物,而是“为我”之物,但“为我”却非“唯我”,物有其客观的存在,中国哲学承认有“物”存在,“在世”的民族中不仅有人,而且有物,甚至有“无情之物”,但物因为人类的灵明之看而“明白起来”,又“明白”人类的心灵,人与物“共在”,心物同源,互相点亮[32]。海德格尔虽然关注自然,主张人类诗意地栖居,但“天空与大地之间”,“只有人去死,动物只是消亡”[33](p67-68)。动植物没有“此在”,“在世”的民族仍然是孤独的“被抛”者。
五、“极”高明何以“道”中庸:汉语生态哲学接着“讲”
生态本就在汉语之中,汉语诉说汉民族生态的存在,以生态的视域认识文字,背后的回归首先就是哲学研究者对自己存在的根源的重新认识,我们在讨论哲学“认识论”前不妨重新“识字”,将汉语的生态哲学意蕴进行阐发。但汉语“道”生态,又需要哲学学者去“道”哲学,汉语由汉民族生态的存在而呈现它的形态,无论是字形、字义、词义、词汇的情感、字典的编纂都不仅仅是文字学或汉语史的工作,而是需要予以哲学的诠释,才能看到与汉民族“自家意思一般”的在世世界如何“不一般”。在学术研究上,才能从“词”与“物”的逻辑到“文”与“道”的致思自觉,此处不妨回到“极”再“道”。
“极”在哲学思想史中的“无极”“太极”等诸范畴已经简要梳理,在文字的考察中,也关联到了它与“天象”之间的重要关系,北极星斗正是“极”最早的指涉,也由此而为房屋之顶、为立人之极、为作为天时掌握者的统治者所应为的皇极中道,进而与中国哲学“无极”“太极”的对待而非对立的和谐一体思维相联系。我们甚至可以再延展而言,以“木”指“星”与中国的天干地支思想的关系,“干”“支”(枝)都是木身的表达(东汉蔡邕《独断》“干,干也”“支,枝也”),中国哲学天人相与之际根本是人与天道运行的休戚相关(“休”亦是人倚木而栖息,“栖”又是木,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之“栖”需要透过印欧语的音声而诗意,而中国汉字本身即可表达诗意),天行有常而人有信、天德流行而人有仁,人极在天地之间,既可人道自立而以天理为则。可以说,天人生态视域下汉语之“言”没有疏离于“在”,又表达出“此在”,认识论与本体论互相涵摄,它不仅“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智慧,更是天人合一的“表达”。这是“文”与“道”的致思自觉,我们不妨由此反过来再思考与此相关的是“词”与“物”的逻辑。
福柯的“词与物”受到法国著名艺术家马格利特的名画《这不是一只烟斗》的启发,艺术家的画面上是一只烟斗,画面下的题字为“这不是一只‘烟斗’”。福柯引申“词”与“物”的疏离而写作长文,认为“语言因素和形象因素的严格区分、相似和判定之间的等值,这两个原理构成了古典绘画艺术的张力[34](p366)。如果沿着这样的脉络,我们可以从中国哲学传统中“言意之辨”给出相似的思考。无论是《周易》“立象尽意” —老子“道不可道”、庄子“言筌”—魏晋玄学言意之辨的脉络,还是儒家“正名”“修辞立其诚”的脉络,佛教“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至禅宗“不立文字”“不离文字”的脉络,都可以与福柯的“词与物”的逻辑进行对话。但还有一种思考方式是“言”外之“思”,即回到物本身,艺术家画了一只烟斗,说“这不是一只‘烟斗’”,启发人们在“看”画时思考“语言”与“实物”的分离(当然也包括艺术与实物的分离,如海德格尔《论艺术作品的的起源》中的农夫之鞋,此处姑且不论),这是基于音系词汇中,确实无法通过“字母”的组合本身看到“在”,而生发一层“词”与“物”之间意义的隔阂,以造成人与物的疏离。福柯亦对中文的书写性质进行了探讨,以中文的垂直性书写为“聚合轴”以减弱语句的序列和主谓结构关系,这种与西方语言的对立模式,帮助西方跳出普遍意义的历史迷梦,但还未达汉语之“意”。就汉语文字而言,我们不仅可以说,“这是一只‘烟斗’”,更可以说“这不仅是一只‘烟斗’”。
就“斗”而言,“斗”字作为象形文字与北斗星相似,画面的烟斗形状也是北斗星的造型,可以说,一个“斗”字可以表达象“斗”的所有物类,而斗字引申为“极”字的意蕴已经论及,我们可以由“斗”之象而说“极”之蕴,也是“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进而说明中国政治治理与哲学致思的独特智慧。再说“烟”,古汉语也写作“煙”,《说文》说,“煙,火气也。从火垔聲。烟,或从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陆玑连珠语“火壮则烟微,性充则情约”解“火气”,又说“烟,或从因。因声。”如果就前一种而言,我们可以从《周易》水火“既济”“未济”的关系来说明,如《说卦》中“水火相逮”方能生“烟”②;而就后一种而言,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思考“因”虽然表音,但声部中也含有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水,“因”原意就是水之“就下”,在治水经验中逐渐上升为因势利导的民族生存智慧,反映着天人合一的民族本源存在[35](pp196-218);对人而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中庸》)体现根据每个人的性情气质而因材施教的教育智慧。对于“烟”,“水”“火”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物类,却需要相资相成,道出民族对待而和谐的智慧,又回到了“无极而太极”。我们可以进一步引申思考通往存在之途的对话。1975年汉学家于连曾来中国学习一年汉语,回忆其学习经历,是对学习的第一句“这是什么东西”(what is this?)翻译的惊愕,“我现在还记得我的惊愕,……一种‘畸变’,真正超乎寻常的从‘东西’变为‘关系’的畸变……这里包含着巨大的思想可能性”[36]。于连从“东西”中体会到关系思维,而并不知“东西”后还有“五行”,还有“易道”,还有“金木水火土”与“雷风山泽”所组成的“天人相与”的生态系统,在文字中即可被“道”出,而“烟”之一字就可道出交互主体(relational approach)、相关互应(correlation),乃至马丁·布伯的“我与你”,展开东西方通往存在之途的对话。
人间烟火、天地氤氲,《周易》哲学的当代书写或可从中受到启示。中国哲学“接着讲”[37](pp187-188)并不仅仅是“接”的探讨也是“讲”的更新,也或可从中受到一二启发。
① 文章引《说文》版本为[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许惟贤整理,凤凰出版社,2015年。
② 有关传本《易·说卦》中“水火不相射”与“水火相逮”的联系,孔颖达解释为“水火虽不相及而相逮及,雷风虽相薄而不相悖逆,山泽虽相悬而能通气,然后能行变化而尽成万物也。”见[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4-95页。1973年马王堆帛书本《衷》篇写作“水火相射”,学术整理参见梁韦弦:《出土易学文献与先秦秦汉易学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4页。
[1] 张岱年. 张岱年全集: 第四卷[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7.
[2] 乔清举. 金岳霖新儒学体系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9.
[3] 朱伯崑. 易学哲学史(上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4] 王晓毅. 宇宙生成论向玄学本体论的转化[A]//邹晓东编. 道玄佛历史、思想与信仰续编[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5] 陈来. 朱子哲学研究[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6] 朱子全书: 第十三册[M]. 朱杰人等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7] 朱子语类: 卷九十四[M]. 王星贤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8] 王阳明全集: 叁(外集)[M]. 陈恕编校, 北京: 中国书店, 2014.
[9]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熊十力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10]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三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11] 周秉钧. 尚书易解[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4.
[12] 宗白华. 境界: 中国美术十八讲[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21.
[13] 詹鄞鑫. 华夏考詹鄞鑫文字训诂论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14] 乔清举. 文字之作为认识论:中国人进入世界的方式[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4): 18-21.
[15] 杨国荣. 科学的形上之维[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16] 黄玉顺主编. 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研究[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6.
[17] 杨海文. 化蛹成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断想[M].济南: 齐鲁书社, 2014.
[18] 万献初. 《说文》学导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
[19] 蔡维玉. 许慎的字义训诂与两汉的神秘文化[D].博士学位论文, 香港城市大学,2011.
[20] 陈梦家. 中国文字学(修订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21] 杨树达.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M].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22] 乔清举. 从汉语水系词汇的哲学分析看汉民族的存在世界[J]. 现代哲学, 2009(1): 116-126.
[23] 方立天. 寻觅性灵从文化到禅宗[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4] 彭永捷. 汉语哲学如何可能[J]. 学术月刊, 2006(3): 49-52.
[25] 江怡. 从汉语哲学的视角看中国哲学研究70年[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 83-91.
[26] 聂鸿音. 从文字发展史看汉字的现状与前途[J]. 语文建设, 1993(5): 12-15.
[27] 张显清. 中国历史“停滞论”的由来和发展[J]. 明史研究, 2003(0): 240-251.
[28] 詹鄞鑫. 20世纪汉字性质研究述评[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3): 41-47.
[29] 乔清举. 中国哲学研究反思:超越“以西释中”[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11): 43-62.
[30] 乔清举. 儒家生态哲学的元理论体系建构及其意义[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8(2): 62-67.
[31] 刘晓力,孟伟. 认识科学前沿中的哲学问题身体、认知与世界[M].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
[32] 乔清举. 王阳明“心外无物”思想的内在义蕴及其展开——以“南镇观花”为中心的讨论[J]. 哲学研究, 2020(9): 49-58.
[33] 余平. 思想的虔诚[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
[34] 肖鹰, 孙晶. 不巧的艺术[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6.
[35] 乔清举. 河流的文化生命[M]. 郑州: 黄河水利出版社,2007.
[36] 杨慧林. “经文辩读”中的思想对话[J]. 社会科学战线, 2019(8): 195-199.
[37] 冯友兰. 冯友兰自述[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021-10-2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生态哲学思想史研究”(14ZDB005)
胡晓艺(1994-),女,江苏徐州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生态哲学。
B21
A
1008-4479(2022)04-0056-10
责任编辑 陈建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