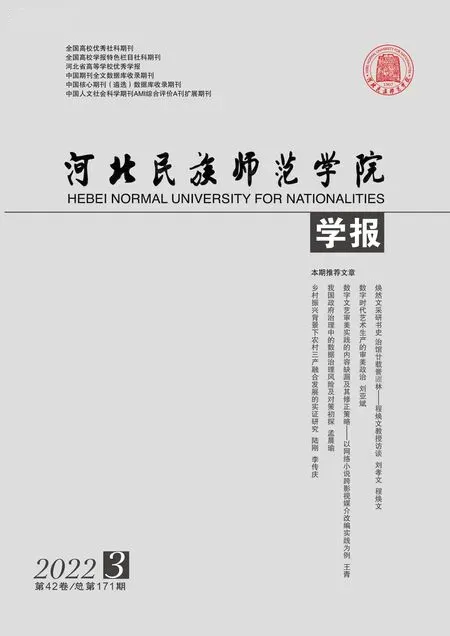一日千里 著作等身的治学秘诀
——王知津教授访谈
张文彦 王梦怡 王知津
(1.广西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2.南开大学 商学院,天津 300071)
张文彦:王老师您好,很荣幸能在世界读书日这一天对您做这次访谈。从您读书治学50多年的经历,请问您的经验和心得是什么?
王知津:我入这个行是1972年春,当时我还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下乡知青,有一个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推荐我到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学习。因为当时是在农村,有一个上大学的机会很不容易,所以我也没有过多地考虑什么专业、将来的发展和前途就直接答应了。于是,我就来到了武汉大学学习图书馆学专业,毕业之后我回到家乡哈尔滨市,在黑龙江省图书馆从事了五年的实际工作。1979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当时这个专业还叫图书馆学,因为当时还没有情报学的研究生,但是我的研究方向是科技情报处理与检索,是偏情报学这个方向的。
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那几年,由于当时是工农兵大学生,没有经过高考,所以我们班同学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干扰,我们在学校学习其实也没有全日制的学,经常安排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比如说学工、学农、学军。我们就是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去,即所谓的开门办学,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所以这段时间就是学一半又活动一半,就这样毕业了,其实基础打得也不是太好。
我毕业之后做实际工作的这五年倒是很受锻炼。当时我在黑龙江省图书馆的科技文献检索室,几个同事都是外语比较强的,因为我外语还凑合,所以我们那几年的主要工作是解答咨询,就是科研人员来查找资料遇到疑问时,由我们来解答。另外,我们也深入到科研单位、工厂还有农村了解实际需要,为他们编了一些专题索引,这些专题索引叫索引,实际上是个文摘,是按照文摘来编排的,每一个条目都有文摘。我记得,我们当时做了两本比较大规模的,一本是《小麦育种》,主要是面向国外的小麦育种的文摘索引,这里边涉及到要把国外的文摘翻译成中文,然后打印成册。还有一本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低温冷害》,因为黑龙江地处咱们国家的高寒地区,冷害对农作物影响很大,所以我们也做了这方面的专题文摘索引。这两项工作实际上对我的锻炼非常大,一个是我对在学校学的一些专业知识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和感悟,因为是自己亲手检索、翻译、重新编排、打印成册,最后送到工厂、农村还有科研单位,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英语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因为我们主要是做面向国外的文献。
1979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生,我的研究方向是科技情报处理与检索。我们那一届同学总共十一个人,这十一个同学都很勤奋努力,大家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地发表论文,比如说,我发表了一篇,你发表了两篇,他发表了三篇,反正大家互相较劲,你发几篇我就发几篇,所以当时我在1980年发的第一篇。随后一直到1982年毕业,在学校期间我发表了五篇论文,也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另外,这期间我们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我和一个同班同学俩人合作翻译了一本书,就是兰卡斯特的《情报检索系统:特性、试验与评价》,这本书后来在1984年的时候正式出版了,我们国内当时叫书目文献出版社,现在叫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这项工作实际上进一步的激发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兴趣,也是因为受到我们那届同学的互相影响,所以我感觉在那三年当中的提高是很大的,毕业之后我就借着东风继续从事研究。
我治学这么多年的经验和心得第一个就是干一行爱一行。我是1966届的“老高三”,本来我应该1966年高考的,当时我们已经全身心的投入高考复习,天天模拟考试准备进考场,但是到了六月上旬的时候,突然间新闻联播就宣布废除高考制度,全国人民都投入到文化大革命当中去,所以我们高考这个机会就已经错失了,然后都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高考都是先填志愿、后考试,我当时报考的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国防科技大学,报的都是航空自动控制、航空发动机、舰艇工程这一类尖端科技的理工科专业。我没听说过还有图书馆学这个专业,跟自己的理想差距比较大。所以当时我在农村的时候,对于让我到武汉大学去学图书馆学专业还是不太理解,但因为当时身处农村,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了,于是就进来了,入了这一行。所以我的经验和心得的第一点就是干一行爱一行,既然你进了这个门,你就要干好这个门里的事儿。
我的第二个体会就是要时刻关注国外的发展动向。因为国内的发展动向我们比较好掌握,都是中文,看有关图书和期刊也容易做到,难的是如何掌握国外的发展动向。我在北大读书期间就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包括我在读研期间发表的五篇论文,都和我查找、阅读、利用国外文献有着直接关系。我是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以后,结合我们国内的实际情况,写了这五篇论文。另外,我的毕业论文选题在当时也是很前沿的,论文题目是《汉语科技文献抽词标引研究》,属于自动标引领域。我是1982年答辩,在那个年代做汉语科技文献自动标引的,我记得国内当时好像只有三个人,三个都是研究生,一个是中国科技情报所的,还有一个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当时就我们三个人做这类题目。中科院的那位研究生是学英语出身的,英语特别棒,她做的自动标引是针对英文的,不是针对汉语的,所以难度还比较小。因为汉语跟英语差别很大,最大的差别就是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的单词和单词之间有空格,计算机读起来很好区分,两个空格之间的字符串就是一个单词,拿出来以后就可以进行自动标引。但是汉语不行,汉语的词和词之间是没有空格的,你不知道哪个字到哪个字是一个词。因为这汉语太复杂了,一个汉字可以是一个词,两个汉字也可以是一个词,三个、五个、六个汉字也可以是一个词,所以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中科院的那位研究生做的那个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中情所的那位研究生跟我一样做的是汉语的,但是他跟我的路径不一样,他做的那个是利用词表,他先编辑一个汉语词表,然后把被标引的文献读进计算机,再跟机读词表一个词一个词地进行匹配,匹配好后就等于把汉语这个词给切开了,切开一段它是一个词。而我是另一条路径:抽词,从原始文献当中抽词,抽出的词通过词频统计,利用一些模型,然后匹配,也就是用自然语言去自动标引。因为这个难度比较大,国内根本没有相关文献,所以就必须得依靠外文文献。为了写这篇毕业论文,我也是查了大量的国外文献。我就举一个例子,其中有一篇是美国的PB报告(作者注释:Publication Board,即美国商务部出版局的科技报告,系美国四大科技报告之一),PB报告它不是书也不公开出版,但是我在别的文献里发现了这篇PB报告的线索,报告的题目是《自动标引的现状和未来》。我得到这个线索以后很高兴,但是我最终的目的是要得到全文。PB报告要成一本书的话也是有三四百页,比较大,我在北大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中国科技情报所都查遍了,也没有找到这篇报告。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图书馆馆藏目录里边忽然发现有这篇报告的缩微版,也就是缩微胶片。于是我就来到北京图书馆的缩微文献阅览室,把缩微胶片给调出来,然后利用缩微阅读器来阅读。当时北京图书馆在北海公园附近,离北大中关村很远,我早上从北大骑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天黑了再从北京图书馆骑回北大,我就这样每天早出晚归把这篇报告给读完了。这篇报告对我写毕业论文很有帮助,虽然它讲的是英文自动标引,跟我们中文不一样,但是它对我的启发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的第二点经验和心得就是一定要随时掌握国外的发展动向。
第三个体会就是不管是写论文还是申报项目,选题一定不要和现有的题目重复,一定要找一个没人做的题目。当然我说的这个没人做不是说一丁点儿也没做,它可能是一个大家都比较忽略的领域。在这里边选题目一般来说都很新,而且还都有价值,所以说选题也很重要,这个思想在我的学术研究工作当中还是给我了很大的收益。我治学的经验和心得最主要的就是这三点吧。
王梦怡:结合您的学术道路,请问您是如何与情报学结缘的?
王知津:当时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学了很多门课程,其中,我对科技文献检索这门课最感兴趣。主要基于两点原因:首先,检索是情报学的一个支柱,从国内外总体上看,情报学的支柱有三个,第一个是情报检索,第二个是文献计量,第三个是情报研究。1972年我们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学校没有开文献计量的课,也没有开情报研究的课,只开了科技文献检索。这门课程有很多奥秘,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像现在的网络、数据库这么发达,怎么样查找到你所想要的资料是很难的,所以这门课很吸引我。另外,检索不能只检索中文,还要检索外文的,需要接触大量的外文检索工具,对于外文检索这一块我也是很感兴趣。
正是因为对我科技文献检索非常感兴趣,老师们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当年我们毕业实践的时候,我就被分配到上海科技情报所去实习,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情报”这两个字。在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实习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还有一位带队老师,我们共同编写了一本叫做《国外常用科技文献检索工具简介》的书,这本书在我们毕业之后由上海科技情报所出版社(即现在的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于1975年正式出版了。在当时武汉大学有科技文献检索方面的油印的教材,中国科技情报所也有这方面的油印的内部讲义,但它们都不是公开出版的,所以我们编写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国内在科技文献检索方面第一本正式公开出版的书。当时我们几个同学编写这本书时分工了,其他同学负责英文的部分,因为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自学过日语,所以我负责日文的部分,日本有两个科技文献工具很重要,要是遗漏的话也是不完整的。一个是日本专利,日本的发明很多,所以这个是不能缺少的。另一个是日本科技文献速报,这个是综合性的,大概一共是十个专辑,由日本科学技术情报中心编辑出版,我当时就是负责的这两章。在毕业实践的过程中我也是收获满满,在毕业实践结束后的总结大会上,系里让我作为代表来总结我们小组的成果,从那开始我就对科技文献检索、情报越来越感兴趣了。
之后,我工作这五年也是在科技文献检索室,还是和检索、情报有关。我考研的时候没有情报学专业,当时我就考了图书馆学专业。虽然专业是图书馆学,但我的方向是科技情报检索与处理,还是情报,因为读研的时候就是情报学方面的,所以毕业以后也还是在这个方向一直做到今天。我就是这样跟情报学结缘的。
张文彦:请问在您的职业发展道路上,是什么一直激励您到现在都在勤于思考、笔耕不辍、佳作不断?
王知津:我是在1992年拿到教授职称的,当时我在黑龙江大学担任系主任,为什么我在拿到教授职称后还要继续努力,因为我要把这个团队带好,你对别人要求严格你自己首先就要做好,所以我就督促自己不能松劲儿。
我到了南开大学取得博导资格以后就开始带博士,我对博士要求也是挺严的。还是这个道理,你对别人要求的严就不能对自己要求的松。我虽然指导博士但是自己首先要以身作则,不能松劲儿,所以我就一直保持着这个状态。
我不当博导退休后就没什么压力了,所以我退休以后的成果就大幅度地减少,现在一些刊物向我约稿,有的我就接受了。我还把学术会议、讲座上的发言报告修改成文章,就这样来做。
张文彦:带学生、教学生、和学生相处是大学老师的日常工作,请问在师生关系这方面您的诀窍和重点是什么?
王知津:第一点就是要尊重学生,我觉得作为老师,既然你指导学生就应从各个方面尊重学生,当然学生有做的欠缺的地方你还是要不客气地给他指出来,但是你要在尊重他的前提下,给他指引方向,跟他好好相处。
第二点就是在指导学生方面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主要给他指方向教给他方法,而不能当保姆。包括他们写小论文、写毕业论文、选题什么的,我统统不包办。举个例子,比如说写毕业论文,我从来不给学生指定题目,而是让他们自己查资料反复思考后想出三到五个题目,然后我和他们共同讨论选哪个题目。题目定下来后,我会让他们自己去列出三级大纲,列好后我和他们再去讨论大纲需要修改的地方。大纲也定下来后,我就让学生自己按照大纲先写完毕业论文的所有部分。等有了完整的论文初稿,我再针对其中有问题的地方给他们进行批注,但我从来不直接给他们修改,只给他们指出来这个地方不对,告诉他们错在什么地方,应该往哪方面修改。只有让学生自己走完这个全过程,他们才能得到锻炼提升自己。所以我感觉我指导的学生出来以后独立性都挺强。
王梦怡:王老师,请问您在做学术研究或者教学管理的过程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特别难忘的事情吗?
王知津: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就以写论文为例,其中有一条经验,就是针对一个研究领域持续地进行研究更容易出成果。比如说,我在读研期间,我翻译了兰卡斯特的《情报检索系统:特性、试验与评价》那本书,它给我的启发很大,然后我又看了许多其它国外的文献,于是我就写了一个系列文章《情报检索系统评价》。这个系列文章在《图书与情报》期刊上连载了六期。连载前面几期时我还没毕业,后面几期我都毕业了,但是都是我在读研的时候写的,所以连续做容易出成果。再有一个例子,毕业之后我给《情报科学》投了许多稿,其实有一篇稿就是《论情报的相关性》,因为当时国内对情报的性质有一场大的讨论,提出了情报的很多性质,其中第一个是情报的知识性,这是大家公认的,第二个是情报的传递性,这个也是没有异议的,但是第三个性质大家就是七嘴八舌了,怎么说的都有。我给它归纳到情报的相关性,只有相关的才是情报,不相关的它只是一条信息而不是情报。于是就相关性我写了几篇文章,其中这篇《论情报的相关性》发表在了《情报科学》上,我写完了以后仍觉得言犹未尽,所以我又写了一篇《再论情报的相关性》,这就是连续写更容易出成果。还比方说,我在当时的《计算机与图书馆》期刊上连续发了四篇规范文档这方面主题的文章,《计算机与图书馆》后来更名《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现在又改名叫《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所以我觉得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连续性,这样容易出成果,这个事我是比较难忘的。
在教学管理方面,因为我在黑龙江大学先后当过系主任助理、副主任和主任,在南开大学也当过系副主任和主任,做了一些教学管理的工作。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一定要从大处着眼,从大局出发,把学科搞上去是你当管理者的最大任务,其它的一些细枝末节不要投入过多精力,你可以交给其他的领导比如说副主任去干。当系主任你不要啥事都管,你就管大事,管学科建设大方向。比如说,南开大学原来只有一个图书馆学的硕士点,没有第二个点。我当南开大学系主任以后首先争取到一个情报学的硕士点,紧接着我又创办了档案学的本科专业,因为我觉得这个学科得全一点,以后才能申报博士点,然后很快我又给争取下来一个档案学的硕士点,有了这两个硕士点以后我就开始向博士点冲击了,先是拿下了图书馆学的博士点,卸任系主任后又拿下了情报学的博士点。我在当系主任的这四年当中,为学校创办了一个档案学的本科专业,拿下了情报学和档案学两个硕士点,又拿下了图书馆学和之后的情报学这两个博士点,使学校的这个学科一下子上了一个台阶。
王梦怡:我们知道您既是一位博士生导师,又有很多的社会兼职,还要同时进行着自己的研究项目,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三种身份关系,又是怎样把他们很好地平衡的呢?
王知津:这几种身份关系表面上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它们是没有矛盾的,是一体的,它们之间都是互相能够促进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所以我觉得做好每一件事对其他的事都有好处、有帮助,自然而然这样就平衡了。
比如说,我当系主任期间,我四年做了五件事,这五件事对于一个学校、一个系、一个学科来说都不是小事。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的科研怎么做?我的项目怎么申请?我的论文怎么写?我的著作怎么写?我是这样处理的:在正常的学期期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搞硕士点、搞博士点、办专业上,这个期间我拿不出大块的时间来写论文、写书。我们知道,写论文也好,写书也好,可不能打断,打断了以后,你再往上接就不好接了,接不上头了。所以我在这个期间干脆就不写文章,而是利用这些零零星星的时间广泛地收集资料,然后聚焦几个研究领域、几个研究问题,拟定几篇论文的题目或者申请项目的课题,就做这些准备工作。等到寒暑假的时候,我可以集中自己的精力和时间,而且我的思路准备好了,资料也准备充分了,就差动笔了,所以我一个假期就可以突击生产出来三到五篇论文,这样的话我一年写六七篇文章是没有问题的。
张文彦:王老师,请问您对青年学子和青年学者的忠告有哪些?
王知津:第一点是要干一行爱一行。你要进了这个门想做的话一定要做到底,不要半途而废,更不能“站在这山望着那山高”,又想改行干别的或者是当公务员又或者是到公司里去,你不要三心二意,一定要忠实于这个职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专业基础要打牢。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这个学科专业的真谛在哪里,我们知道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很快,社会在不断地变革,时代也在不断地发展,同时新的领域、新的术语、新的概念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在这种形势下,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学科专业站稳脚跟,要知道这个学科的根在哪里,如果一个学科连根都不要了,那就随风飘走了,所以知道自己学科的根在哪里很重要。比如说情报学,到底什么是情报学,目前我们对情报学的认识有一定混乱,特别是一些青年教师和青年学者,他们不是从情报学的起源、本质来看待,而是自己作为一个新进来的人随心所欲地去解释,我认为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奉劝青年学者,你在忠实于这个职业、这个领域、这个学科专业的前提下,一定要知道自己学科专业的根在哪里,在任何时候都要紧紧抱住这个根往下扎,不要被各种风风雨雨吹得摇摇晃晃,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要持之以恒,不要怕困难。比如说申报课题,青年学者经常是申请了以后没有中,失败了,受到了一定打击。还有的申请了两次、三次都没中,那打击就更大了。对于青年学者申请项目我有一句俗话:“庄稼不收年年种”。今年没申请上,明年再申请。明年不行后年,后年不行大后年,不断地申请总有一天能成功。如果不申请了,那也无从谈起成功。所以我奉劝青年学者不要害怕挫折和失败,跌倒了就爬起来再往前跑,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要持之以恒,坚持到底。我对青年学子和青年学者的忠告主要就是这三点。
张文彦:谢谢王老师的精彩解答,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