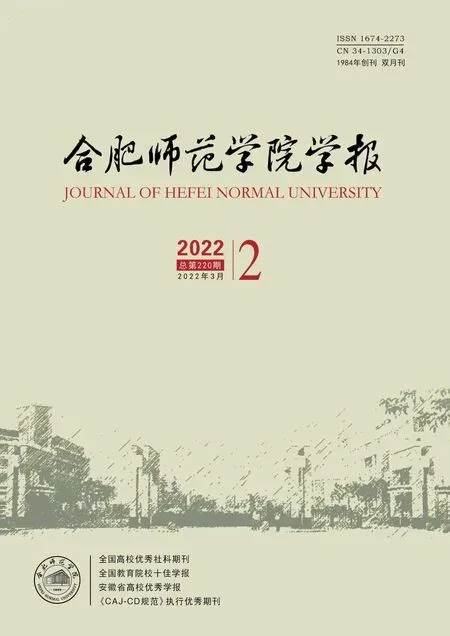媒介赋权视域下乡村文化传播与振兴路径
汪思玲
(安徽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乡村振兴”正式确立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乡村振兴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的任务”[1]。乡村振兴作为一项系统性、全局性工程,既要塑形、也要镇魂。由此可见,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文化的复兴,乡村文化振兴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也是其应达目标,提升乡村文化的传播价值在当下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乡村文化困境:主体的式微与价值的疏离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而乡村文明则是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为这五千年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兴替更迭的空间。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使得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同时,媒体的商业化和城市中心主义改革亦带来了社会价值取向错乱和对农村身份的诋毁[2]。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过去几十年来农村持续的社会分化与农民的去组织化,导致村社共同体趋于解体,乡村社会失去凝聚力[3]。
(一)农民的流失:乡村文化主体的式微
2020年全国农民工共有28560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有16959万人[4],可见,现有农民工仍然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他们离开村庄,辗转于都市之间谋生,多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高昂的房价和现代化的消费方式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难真正融入城市,成为“离土又离乡”的游荡者。除此之外,由于乡村留守儿童问题难以解决,又加上乡村教育基础设施的落后,“陪读”现象在乡村也越来越普遍:即男性青壮年在城市里务工,女性则带着孩子在城市中租房陪读,留在村里的多是一些劳动力弱或行动不便的老人。农村社会的主体——青壮年的长期不“在场”,使得乡村空心化现象愈发严重。农民的大量流失造成了乡村文化主体的空心化,乡村文化价值失去了依托的主体,文化建设也难以有效进行,呈现出退化、凋敝的状态。由此也陷入一种“恶循环”,即城市因为有大量廉价农民工的涌入而得以快速实现资本积累,并吸引着更多乡村青年进入城市,而乡村则愈发陷入困境。同时,在后乡土社会,现代性霸权和城市资本的双重驱动,使得农村变得空心化、离散化和原子化,进而弱化了农民对血缘和地缘的依赖性[5]。乡村从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渐向“无主体熟人社会”演变。
(二)人际的隔膜:乡村文化价值的疏离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6]。“文化自觉”的第一步就是要认识自己的文化,对自身所处的文化有价值认同,乡村文化自然也是这“文化自觉”的题中之义。近年来,随着国内自然村和行政村的减少,对乡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引起了学界的担忧。由于乡村文化主体的长期缺位,乡村文化价值的认同也在这种缺位下被潜移默化地疏离了。新一代的乡村青年很多是在都市里学习、成长的,乡村对他们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独特存在。他们并没有很好地把乡村的一些风俗、文化和农事活动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他们对村庄的公共事务很少关心和参与,也没有对这些传统习俗和文化有过系统的了解,甚至还会把一些地方性的习俗活动视为乡村封建、落后的象征。同时,他们父辈中的很多人也以子女能走出农村在城里安家立业为荣。正如阿斯曼在《文化记忆》里所说:“社会通过一种回忆文化的方式,在想象中构建了自我形象,并在世代相传中延续了认同。”[7]而现代的乡村青年却因为长期与乡村生活的缺场导致了对乡村文化记忆的模糊。他们与其父辈的乡村共同记忆出现了分歧,这种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双重分割不断冲击着文化的延续,阻碍着新一代乡村青年对乡村文化价值的认同。
二、新媒体时代乡村文化的传播机遇
媒介是承载记忆的重要工具,是连接人与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中介,通过“共同阅读”形成“共同记忆”从而生成“共同意识”[8]。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媒介操作的简便化使得很多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乡村人民拥有了表达自我的机会。近年来,媒体上的农村形象也从贫穷、凋敝、需被改造转变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令人向往的现代化乡村。尤其是在以微信、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上,乡村群体超越了传统的血缘与地缘区隔,在网络空间上重新建构了一个属于乡村内部的、稳定的“熟人关系”,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网络空间中书写并传承着乡村记忆和乡村文化。
(一)新媒体重构乡村群体的“熟人关系”
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6%,其中,农村网民规模达2.97亿,占网民整体的29.4%[9]。如果说,传统乡村社会的“熟人关系”在改革开放和城镇化的过程中被打破了,乡村主体成了分散的、原子化、异质化的个体,那么,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和农民网络使用率的增长则重新将这种“熟人关系”在网络空间中建构了,乡村主体实现了网络层面的回归。以微信为例,乡村主体虽然被分散在了不同的地方,但是可以通过创建“微信群”这种实时交流空间来彼此熟络以及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村民的各种微信群主要可以分为三类:有血缘关系的亲友群;有地缘关系的同村群;有姓氏关系的宗族群。他们在这些由熟人组成的微信群中交流日常生活,讨论乡村集体事务,参与乡村的建设和发展。村里的任何事情,他们都可以通过微信群实时得知并参与讨论,微信让他们虽然远在天涯但又近在咫尺。不仅如此,村民还可以通过微信朋友圈的内容创作和互动功能来维持和稳定这种熟人关系,增强彼此间的认同。乡村社会原来非常紧密的人际关系,通过微信得到了强化和放大,微信与社会共同体因此有了更强的耦合度[10]。社交媒体的普及将乡村空间从线下发展到线上,从现实拉进了虚拟,从有边界扩展至无边界。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并未因部分主体的“缺场”而中断,手机重组了时空情境,重构了熟人关系网络,熟人社会的舆论、“面子”、社会资本等逻辑行为准则依然起着支配作用,他们共同构筑了既虚拟又实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移动主体熟人社会”[11]。
另一方面,电商经济在乡村市场的衍生发展,则为乡村主体回归提供了现实机遇。2021年6月22日,抖音发布首个三农数据报告,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抖音农村视频总获赞量129亿,农村视频创作者收入同比增长15倍。创作者中,返乡创业青年占比54%,城市白领返乡创业比例最高,其次是农民工[12]。电商经济在乡村市场的发展,为乡村主体留在乡村进行生产生活提供了更多可能。如拼多多的“多多助农”、淘宝的“爱心助农”、京东的“助农馆”等不仅为农民开辟了多样化的销售渠道,也为乡村增添了就业机遇,吸引青年回乡参与经济建设,让乡村主体实现现实层面的回归。
(二)新媒体推动乡村文化认同
随着乡村振兴的战略号角吹响,电视节目和网络综艺也开始关注乡村的美好和乡村人民的惬意生活,如《乡村爱情故事》《向往的生活》等。人们通过这些影视作品了解乡村、感受乡村生活、领略乡村文化。但无论是真实的纪录片还是虚构的影视作品,他们展示出的乡村美则美矣,却缺少一份真实感,不能全面、客观、准确地表现乡村。以《向往的生活》为例,虽是以乡村生活为主题,但却是一群精心装扮的名人明星带着新奇的心态去体验他们所“向往的”浪漫乡村生活,农民的辛勤劳作与城乡间的区域落差在影视制作和名人的光环下被忽略和隐去了。真实的乡村生活与精心制作的影视作品产生了出入。这是因为长久以来,乡村社会研究中常常有一种客位取向,即站在一个自我中心主义的“高处”,带着“有色眼镜”来俯视乡村社会的种种现象,并将各种问题的症结归咎到乡村主体身上,由此形成的观点其实带有对乡村社会的偏见[13]。
进入社会化媒体时代,用户生产内容(UGC)成为网络世界一种典型的文本形态,乡村逐渐从都市的叙事枷锁中挣脱出来,获得了自我言说的可能的媒介机遇[14]。而短小精悍、拍摄简易、分享便利、娱乐性强、社交功能强大的短视频则成为乡村主体编织叙事的首要选择。低门槛的使用规则、简单便利的拍摄方式加上智能手机和家庭无线网络在乡村地区的普及,使得愈来愈多的乡村主体获得了最直接的“媒介接近权”,他们运用短视频来进行话语表达,逐渐在社交媒体中掌握“话语主动权”。而短视频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所构建的强大的传播矩阵,也在无形中拓展了乡村主体的媒介空间,加速了信息内容的复合型传播。社交媒体大大激活了乡村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们活跃在以抖音、快手、秒拍等为代表的短视频APP上,现在,手机已然成了新农具,拍摄短视频、进行直播成了新农活。一大批农民成功转型为拥有互联网思维、积极运用短视频平台进行农特产品销售的新农人[15]。
在短视频平台上,众多乡村主体以拍摄短视频和进行直播的方式来表达话语、展示自我、传承乡村文化、建构乡村影像。他们有的成为乡村网红,有的成为农民自媒体人,还有的成为地方性的乡村代表。近年火爆的李子柒、丁真等人,不仅仅是网络意义上的乡村网红,更是成为当地具有官方色彩的乡村代言人。李子柒通过“古风+田园式”的美食视频制作,将中国的传统美食文化和恬静的田园生活传递给了海内外受众。丁真的意外走红让理塘——这个四川省西南部的边远县城为全国人民所熟知,理塘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和川西南的秀美风景也因此进入大众视野,在传播当地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拉动文旅消费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等方面都产生了有益影响。
另一方面,短视频平台也在积极为乡村主体的话语表达提供技术支撑、话题引导和流量帮扶。抖音的“新农人计划”、快手的“百城县长·直播助农”等系列活动通过运营指导与培训、流量扶持与变现、平台佣金减免等措施,帮助新农人提升内容创作能力和流量收益水平。抖音三农创作者@牧民达西,用短视频记录草原生活的日常,截至2021年11月22日,共有粉丝367.5万和点赞量5170.5万。无需夸张的语言渲染,也没有繁杂的滤镜包装,达西用最真实的镜头记录着草原的春夏秋冬,“草原丰收会”“游牧文化节”“草原婚礼”等牧区人民的文化习俗被达西用短视频传递给更多的人,少数民族的“赛驼”“驼具制作”等非遗文化也通过达西的短视频进入了大众视野。贵州省铜仁市德江县大寨村书记@古村28渡(驻村书记),将他的驻村日记用视频记录并发布在抖音上,截至2021年11月22日,共有粉丝11.9万、点赞量76.6万。大寨村是有着6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村落,拥有浓厚的土家族文化和丰富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资源。一些代表着大寨村悠久历史文化的事物,如木制的传统民居、千年的金丝楠木、古老的竹编工艺、传统的花灯和民间吹打乐、悦耳的山歌、特色的美食等,都在其视频中被记录下来。庞大的乡村群体创作的乡村短视频开始“霸屏”各个短视频平台,成为短视频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观看这些乡村短视频,人们能直观地领会不同乡村的民俗风韵与秀丽风景,看到农民的淳朴和善良,感受乡村生活的温馨和美好,领略乡村文化的厚重与魅力,引发对乡村和乡愁的羁旅之思与价值体认。
三、新媒体时代乡村文化的振兴路径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乡村文化主体的回归,并重构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在此基础上,乡村文化也焕发出了更强劲的生命力。借助新媒介技术的帆船,探寻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能够让乡村文化传播得更快、更阔、更广。
(一)发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6],由此可见,推进乡村振兴仍然是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乡村振兴的现实语境下,新闻传播也应围绕文化建设,使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创意转化,让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文化是根本、产业是载体,要实现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首先要依托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如各种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走因地制宜的文化产业道路。例如,皖西大别山地区便依据当地红色革命文化资源和茶叶资源,创办开茶节等文化节日,打造红色革命小镇,发展红色旅游,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其次,实现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要重视乡村人才。农民是乡村文化的直接生产者和实践者,要积极引导农民参与文化产业发展,培育乡村人才队伍,发挥他们作为乡村文化主体者的作用。如浙江缙云县官店村的“村晚”,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这个完全由农民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乡村文化盛会,不仅传承着缙云当地的民俗文化,也成为浙江省对外宣传的一个文化名牌,更是农民群众文化主体性、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的代表。现如今,缙云“村晚”已不仅仅是一场节日性的文艺联欢会,它正在成为乡村最具魅力的文化符号,开辟了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经济建设的新模式,开创了乡村文化复兴的新高度。
最后,实现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还要善于利用“互联网+”技术。当前,信息已然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乡村网络设施也渐趋完善,将5G、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应用于乡村丰厚的文化资源,发展数字文化产品,对乡村文化资源进行活态传承,打造出具有乡村特色的文化产业品牌。
(二)弘扬乡村礼治,建设文明乡村
乡村社会是依靠传统与教化来维持的,“礼治秩序”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17]。礼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已经成为一种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根植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到国家制度、社会风俗、典章规范,小到个体生活观念、行为模式、宗教信仰,无不深受礼的影响。传统乡村社会由于缺乏法治的可行路径,对礼治的约束作用就尤为看重,乡村文化也在历代传承中不断发展礼的内涵,例如《吕氏乡约》中的尊幼辈行、造请拜揖、请召送迎、庆吊赠遗等礼俗之交,已成为乡村社会人情往来的依据。礼治仍然在乡村群体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作用,随着乡村现代化的推进,既要加强乡村法治建设,也要重视乡村礼治的约束作用,构建后乡土中国的法礼秩序[18]。
弘扬乡村礼治,要重视并发挥“新乡贤”的引领作用。乡贤作为乡村本土精英,是乡村中现实的意见领袖,他们对道德与礼治的践行可以起到很好的榜样和示范作用。不仅如此,他们也可以利用自身的影响带动村民进行生产发展和文化建设,充当政府和村民之间的沟通桥梁,向上反映农民心声,向下传达、解读政策,缓解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引发的冲突。这种对礼治情感的延续,能够软化乡村的治理方式,避免硬性规章制度的推行所带来的文化与情感的不适,进而改善乡村治理的效果[19]。
另一方面,乡村礼治还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乡村礼治传统由于历史固化性,难以有效应对当今社会的瞬息万变,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也有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些价值准则是对传统乡村礼治内核的扩充与升华。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重建具有时代色彩的乡村道德体系和礼治传统,让礼治、德治和法治互为表里,才能更好地解决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利益冲突、道德败坏和行为失范等现象,从而重构乡规民约,建设乡风文明的现代化乡村,因此,仍需“重新思考乡土中国如何从差序格局走向公正社会、由礼治秩序到法治秩序”[20]的文明乡村。
(三)讲好乡村故事,提升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1]。广大乡村作为中华民族最基础、最广泛的存在,是中华传统文化滋生的土壤,孕育着华夏民族五千多年来的深厚文明。而乡村故事正是这厚重文明的组成部分,讲好乡村故事,有利于发扬壮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提升文化自信,从而更好地抵御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入侵和文化危机。
不同时期,乡村孕育着不同的乡村文化,讲述着不同的乡村故事。历史上,乡村故事是教人向善、使人求真的,既有“卧冰求鲤”的孝道故事,也有“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还有“孟信不卖病牛”的诚信故事等,这些故事彰显了古代劳动人民对“仁、义、礼、智、信”的美好人格追求。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战争的年代,乡村亦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后,赤脚医生、乡村电影放映员、乡村教师,成为对外讲述乡村故事的代表,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讲述乡村故事的优秀文学作品,如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沈从文的《边城》等。改革开放时期,小岗村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是农民发挥积极性、主动性的一次伟大胜利,留下了小岗村精神、沈浩精神等值得后人学习的先进事迹。新时期,乡村故事依然精彩,在党和人民群众的不懈奋斗下,全国832个贫困县于2020年底全部脱贫摘帽,近1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谱写了伟大的脱贫攻坚故事,不仅如此,美丽乡村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农民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传递着新时期的乡村生态故事。
讲述乡村故事,最为重要的是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性。农民是他们脚下土地的主人,是乡村故事的主角,是乡村文化复兴的主体。因此,新媒体时代,讲述好乡村故事要更加重视“我者”视角,跳脱出宏大的精英叙事,让农民成为叙事主体,而乡村则是最天然真实的叙事背景。随着乡村短视频的“异军突起”,一大批有着互联网思维的新农人日益活跃,他们的日常化、个体化、情感化的微观叙事方式,能更好地传达细腻真实的情感,也更易打动受众,与之建立情感共鸣。因此,要重视新农人的内容生产和网络建构,发挥他们作为乡村故事讲述者的主体作用。
另一方面,乡村故事还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宣传,依靠县级融媒体建设,积极打造乡村传播矩阵,对外传播乡村声音。例如陕西宝鸡的艺术传承者便将当地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社火脸谱搬进了陈仓区融媒体中心,用直播的方式现场演绎其制作流程,重点介绍社火脸谱的历史文化,展示其背后深藏的文化内涵。利用县级融媒体中心,用镜头记录乡村历史,传播乡村文化,让更多人看到乡村、了解乡村,从而爱上乡村。
四、结语
城市化迅猛发展,乡村主体开始流出农村,进而流入城市,导致乡村文化主体的式微以及价值的疏离化。进入社会化媒体时代,乡村主体重新回归,这种回归是双重意义的:一是新媒体重构的时空情境,让乡村主体在网络空间中回归;二是电商经济下沉到乡村市场,使乡村主体得以留在乡村参与经济活动,实现现实意义中的回归。同时,媒介也赋权乡村群体更便捷的话语表达方式,让乡村文化得以在更广阔的空间里传播发展,重构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在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今天,要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目标,就必须坚持乡村振兴战略,而乡村文化复兴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部分,因此,传承发展乡村文化、创新乡村文化传播路径在当下仍然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