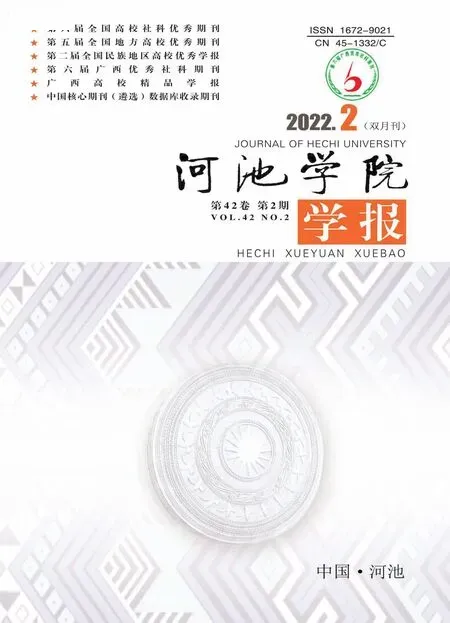回旋于虚实之间
——评东西小说《回响》的叙事策略
许志益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东西长篇小说《回响》在2021年的面世,某种程度上为当下文坛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对此,许多评论家进行了跟踪式的批评,王彬彬曾坦率地形容他的直接阅读感受:“读着《回响》,读罢《回响》,我想到的一个词,是‘摇摆’。我仿佛看到一个钟摆一样的东西在我眼前不急不慢地摇摆着。摇摆意味着不确定。”[1]在这一点上,笔者与王彬彬有着近似的阅读直感,因为在笔者看来,这部小说的独特艺术魅力正在于:它总是反复地回旋于虚构与真实之间,而这也几乎成为《回响》的一大文本美学。
吴俊同样力图捕捉东西长篇小说所隐含的复杂的文本特性,他从对东西纵向创作历程的追踪中,发现了东西对于小说叙事美学所秉持的自觉、执着而独特的追求[2]。此外,丛治辰也指出,对人物心理深度的挖掘,可令《回响》摆脱了通俗文类模式化的书写[3]。可以说,这同样是对《回响》中虚实问题的敏锐关注。笔者认为,塑造这种回旋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文本特征,并非东西无心之举,而是东西作为一名先锋姿态鲜明的作家的自觉探索,其中彰显了东西别具一格的叙事策略与美学追求。
一、叙述、记忆、潜意识:虚实回旋的三个层面
《回响》的一大亮点在于,围绕着“夏冰清之死”和“慕达夫是否出轨”两大谜团,小说在寻觅真相的过程中,建构了众多与之对应的虚构话语,并让虚构与真实之间发生情节和意义上的交织、缠绕。小说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对人性扭曲与异化的批判、对潜意识情感的自我诘问与审视,同时也使文本中的诸多人物、事件、情感得以产生联系,“回响”的意义也于此逐渐生成。
笔者认为,这种虚实之间的混杂交织有三个层面的表现。首先,最直接且突出地体现为人物叙述中的谎言与真相,及人物叙述的彼此替置和颠覆。作为一部融入探案元素的小说,《回响》开篇即围绕着夏冰清遇害的“大坑案”展开,侦破案件的负责人冉咚咚对涉案嫌疑人展开审讯。然而在审讯中,基于各自的利益关系,不同人口中所讲述的事件经过,往往存在着巨大的错位与断裂。这在《回响》中有着普遍的体现,如:关于与夏冰清在蓝湖大酒店初遇的情形,徐山川咬定是浪荡的夏冰清主动与他发生关系,而这一论断终于在后来受到推翻——小刘透露当时夏冰清在包厢内哭了,夏母提供的音频也将真相引向了徐山川的不轨,而徐山川最终在冉咚咚假证据的诱供下,道出了曾经侵犯过夏冰清的事实。同时,出于掩盖自身罪孽与恶行的考虑,人物的讲述往往是真实夹杂着虚构。如在面对冉咚咚的问询时,徐海涛讲述的与曾晓玲的感情经历是实,而与吴文超的“赌球”交易、以及找徐山川借钱买房,都是暗中串通好的虚构说法。
在《回响》中,“谎言”是出于对私欲和利益的一种遮蔽。从成功人士徐山川到其侄儿徐海涛,再到策划人吴文超,又到刘青,最后到民工诗人易春阳,所有当事人都能利用虚构找到为自己脱罪的理由,从而掩盖真相。在这缠绕的犯罪和连环的谎言中,《回响》揭示的是在欲望诱惑下,人性在社会各类人身上所发生的扭曲与异化。这些被人物所虚构出来的事件,最终也随着更多人的讲述和案件的推进而被证伪。这一桩看似滴水不漏的弥天大案,最后也在沈小迎的窃听音频的佐证下水落石出。通过真相对谎言的置换与击破,《回响》构成了一个个叙事的回环,小说正是在回环中推进着情节的进行,读者也能够从阅读中获得一种“解谜”的快感。
虚实交织的第二个层面表现在于人物记忆的虚实交错。一般来说,涉及“记忆”,往往指向人物心理的层面,而《回响》中对人物心理开掘得最深刻、最彻底的,莫过于对主角冉咚咚的描写。冉咚咚在与慕达夫遭遇情感危机后,回忆起了大学时期的初恋郑志多。然而当冉咚咚想去见他时,却在新展公司郑女士、闺蜜朱玉芬的口中得知“郑志多”并不存在,郑志多只是冉咚咚记忆中的一个“虚构”,然而回忆中那场充满细节和真实感的生日求婚,让她感到“他却比任何实体都栩栩如生”[4],这使得事实走向了模糊与不确定性,记忆变得虚实难辨。
与个体记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是心理层面的“病症”。在《回响》中,“病症”大量出现,除了“焦虑症”“多疑症”“心理远视症”“阿尔兹海默症”等之外,还有易春阳患有的“被爱妄想症”。这种“被爱妄想症”能够潜入意识层面,以幻觉替置现实,进而篡改个体记忆。对于易春阳来说,他所回忆起的“谢浅草”是幻觉,实际上是谢如玉和吴浅草两个现实女性的合体。而冉咚咚在观照易春阳的“病症”时,实际上也在审视自我的“病症”。易春阳“被爱妄想症”的病理逻辑与冉咚咚在回忆中对郑志多的虚构情况达成了某种暗合。小说正是借助病症话语来揭示、深挖人在记忆中的粉饰物与真实性。与其说郑志多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不如说他只是冉咚咚记忆中理想男性的一个虚构的符号或化身,只是被以一种难以为主体察觉到的方式植入到了冉咚咚的记忆之中。小说实际上也正是通过那扇虚实交错的记忆之门,探索人的情感真实性。
最后,人物对潜意识心理的自我求证及自我矫饰是虚实交织第三个层面的表现。我们可以认为,《回响》是一部探讨人类内心深处最隐晦、最私密地带的作品,这块领域因为潜意识的伪装机制而变得模糊不清,然而反映的却是真实的本我形态。小说中,冉咚咚试图以一种断案式的方法,去求证慕达夫究竟是否出轨,为此越来越焦虑,近乎偏执。当最终“大坑案”正式告破后,面对邵天伟的求爱,冉咚咚开始重新评估、审视一切,并试着打开自己深处的真实心理层。这样,对他人的求证,逐渐转变为冉咚咚对自我的审讯。她试图向自我内心真实求证,然而这一求证过程却因潜意识的矫饰而变得困难重重。当最后冉咚咚将书房布置成询问室,并要求邵天伟审讯自己,以求证“到底是椅子让人说出真话还是提问者让人说出真话”[4]时,这种审问角色的置换,其实已经成了冉咚咚对自己深处心理的一次严峻试炼,借此,她也终于敢敞开心扉,主动卸载了部分的自我防御。
直到结尾,在与慕达夫的对话中,冉咚咚才最终敢于正视自己的真实心理机制:自己对慕达夫近乎严苛的情感求证,其实是因为自己早已喜欢上了助理邵天伟,但潜意识中出于矫饰和伪装的目的,所以才将罪感和责任转移给了慕达夫——这无疑传达出了一种人类普遍的自我困境。在自我求证和自我矫饰相互抗衡的过程中,一种难辨的虚实感充盈其中。冉咚咚一直向慕达夫求证、向自己的心理求证,然而求证却频频发生错位,这种错位,既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一种推动力,也更是小说构建虚实氛围的一种方式。由此,作者通过人物叙述、记忆、潜意识三个层面的表现,使得《回响》盘旋于虚构与真实之间,这不仅仅是一种氤氲着虚实的氛围情境,更使得小说的人性之思透过虚实的美学形式传达出来。
二、结构探索与文本张力:作为叙事的策略
在一部小说中嵌入虚实交融的情境或元素,其背后往往潜藏着作家的某种谋略与意图。这在一些带有鲜明先锋姿态的创作中皆有体现,如格非的《褐色鸟群》,作家对富有强烈虚构性的心理梦境的描写,不仅使作品染上诡谲和荒诞的氛围,而且更在虚实的恍惚之间,触碰到了形而上的哲学本体论的范畴;又如马原的《虚构》,作者建构了虚实难辨的镜像迷宫,从中彻底地玩弄他的形式游戏,真实与虚构的差异也由此得以取消。
而对于作家东西而言,将虚实的话语融入《回响》中,首先是出于一种叙事结构方面的考量。在东西的既往创作中,也有以虚实话语书写人类情感的作品,其中以《猜到尽头》最为典型。小说中,妻子有一次在夜里去温泉度假村给丈夫送衣服时,却发现丈夫整晚未归,过后她便开始了对丈夫外出行为的种种猜疑,随着越来越近乎偏执的求证,最终的真相却出乎她的意料——而我们会发现,这一故事形态与《回响》是极为相似的,或许我们可以将《回响》视为东西对《猜到尽头》的一次续写。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续写并不是浮浅的复制,而是在此之上融入了探案推理的元素,并构成了命案与家庭的双线叙事。
推理小说这一题材对于东西而言,是较少涉足的领域。为何在《回响》的整体结构设置中,东西会在家庭情感线索之外,融入推理小说的形式?显然,推理小说通俗性强烈,以故事性见长,而这一点无疑与东西的创作理念暗合。东西在关于《篡改的命》的一次对谈中提到——“即便是反故事的先锋小说作家,如莫言、余华、苏童等等,他们都大踏步地后退……而新一代的网络写手,他们更是大张旗鼓地写故事……所以,没必要害怕戏剧性。”[5]作为精英作家的东西,其创作有着向通俗故事趋近的心理倾向,而《回响》则是这一创作理念引导下的一次结构实验。推理元素的融入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可读性,而倘若将“夏冰清之死”一案从作品中移除,只在情节上保留冉咚咚求证慕达夫是否出轨的主线,不仅叙事难以进行,而且小说的可读性也将被大大缩减。
通俗性确实是构成《回响》中融入推理元素的一大原因,但笔者以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推理元素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虚实双性色彩。这种在虚实之间寻求真相的形式,又与家庭情感线索形成了一种呼应。换言之,悬疑探案与家庭情感二者本身都共同指向了一种虚实混杂的情境。东西试图在这种对位的结构中,布置虚实交织的迷宫,他并没有立刻展示出“价值之物”,而是使故事和人物心理不断地盘旋于虚构与真实之间。随着终点的抵达,我们终于得以窥见人在内心深处的真实——这或许正是他颇为先锋性的写作策略。
两条线索的并行结构,对于小说的叙事而言也有很多直接效果。一方面,探案推理的叙事线,让小说整体呈现出“设悬——解悬——再设悬”式的结构主线。另一方面,家庭情感线索的嵌入,以及两条叙事线索的轮流交叉叙事,不仅增添了叙事的生活质感,而且也使得悬疑的推理被延宕,案件似乎成为一个打不开的“死结”,进而使得小说的虚实色彩愈加浓烈。双线并行叙事并不罕见,但能让两条结构线索之间频频产生呼应却是非常独特的——《回响》即是这样的一部作品:一边是悬疑探案,一边是家庭情感,这两条线在叙事中屡屡交汇与穿插。
在笔者看来,这种穿插还不止是人物、事实层面上的简单交织,更是深层意义话语的碰撞。对于这种结构的技法,笔者试举一个较为典型而极端的例子——在福克纳的《野棕榈》中,作者在轮流交叉的章节里讲述了两个独立的故事:一个故事讲述的是一对情侣不顾世俗成规狂热相恋,但最终落得悲惨的命运;另一个故事是两个囚犯救人于水灾中,但圆满完成任务回到监狱后又被荒谬地加判了10年徒刑。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故事,通过福克纳的一种巧妙的对位策略,得以产生了联系和呼应。读者终于发现,两个表面上互不相关的故事,其话语实质是如此出奇的一致,无论对于爱情还是洪水,我们透过这种意象,都能感知到人类非理性生存状态及其困境。《回响》亦如此,表面上看,案件推理与家庭情感两条叙事线索并行推进,但实际上,作者巧妙地在家庭与案件之间安置了连通管道,使得两条线索连结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各种意义在其中产生了联系。譬如,“大坑案”的犯人为了脱罪而选择撒谎,并将责任推诿给他人,冉咚咚的真实心理机制又何尝不是如此?她的潜意识同样为了脱罪(拒绝承认喜欢上邵天伟)而选择撒谎(心理伪装),并将责任推卸给他人(放大慕达夫的错误)。在这一意义上,一直在“大坑案”中审讯他人的冉咚咚,在家庭线中成了自我审讯的对象。
从这种对位结构中还可进一步得出,冉咚咚的“求证”是双重的求证,表面上看,冉咚咚试图向“夏冰清之死”一案求证,实际上,她也尝试向自我内心深处求证。如果说命案的求证因为徐山川、徐海涛、吴文超、刘青、易春阳等人的畏罪和编造谎言而不断使案件的真相受到遮蔽,那么内心的求证便是因为冉咚咚自我潜意识深处的粉饰机制而使得她难以洞穿自我内心的真实。冉咚咚的双重求证因此频频发生错位,虚构的假象也得以不断在读者面前飘摇。在对位的结构和话语的碰撞下,小说意义不断发生着裂变和增殖。东西的虚构游戏,并非流于形式的戏弄,抑或滑向通俗文学式的娱乐,而是在于通过虚构与真实的回旋和碰撞,质询和求证人性深处的真实,向现实求“真”,向人性求“真”。
除了结构策略之外,虚实缠绕也是一种文本策略。作家意图通过虚实话语建构文本张力。而这种文本张力主要表现在真相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小说围绕着两大谜团展开,由冉咚咚的审讯与求证,牵引出关于现实的、心理的虚实话语,真相被暂时遮蔽,进而催生了悬疑、意外之效。读者参与至解谜的游戏中,在阅读的过程中对案件的始末剥茧抽丝,不断地还原案件的真相。尽管小说中的诸多整体性的事件或秩序都可以一锤定音,如:徐山川便是命案幕后的最大黑手,徐海涛、吴文超、刘青、易春阳等人都参与到了这个命案之中,只是为了脱罪选择编造谎言,慕达夫与贝贞之间确实没有冉咚咚所推测的私情,等等。然而,同时也有大量的细节是虚实难辨的。这使得一些碎片性的事件始终飘浮于不确定性的状态,譬如,虽然最终慕达夫没有出轨贝贞,但慕达夫与卜之兰之间是否存在私情却也成了一个谜团。在卜之兰的讲述中,她曾与一名姓穆的教授有过师生恋,冉咚咚层层追问细节,最终发现这名穆教授除了姓名全名和执教大学与慕达夫对不上号之外,其余的证据都让她确信了“穆教授”便是“慕达夫”。这便留下了一个不确定性的谜团:穆教授就是慕达夫吗?慕达夫与卜之兰存在私情?
于是,虚实难分的状况造成了文本的不确定性,并进而导致了读者阐释的多义性。对于这一谜团,有多重阐释的可能,例如我们可以这样解读:此“穆教授”非彼“慕达夫”,慕达夫并未出轨,而冉咚咚之所以会将卜之兰的这些讲述指向丈夫慕达夫,原因就在于她刻意压抑自己对邵天伟的感情,并转而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将责任推诿至慕达夫身上,当机会一旦出现,她就会无限放大,于是她才会在潜意识中将想象中的出轨男性与慕达夫重合。这种解读切中了冉咚咚的深层心理机制。当然,除了这种解读之外,读者也可以认为慕达夫与卜之兰确实存在私情。简而言之,东西对文本细节的模糊化处理,不仅提供给读者多重阐释的可能性,而且更在一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共生的秩序中,建构起了独特的文本张力。
三、互文、内聚焦:虚实话语的深化
就具体的叙事而言,《回响》也动用了诸多形式来进一步深化作品的虚实话语,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互文的运用。《回响》的一大特点在于虚构性文学文本的大量出现。这些虚构性质的种种文学文本,如贝贞创作的《一夜》《敏感族》以及易春阳写的诗歌《抚摸》,都是架设在《回响》这一虚构小说之下的虚构性文本。齐泽克在《事件》中认为:“事件涉及的是我们借以看待并接入世界的架构的变化。有时,这样的架构直接以虚构作品的方式向我们呈现,这种虚构物恰恰使我们能够间接地表达真相。”[6]13《回响》中出现的这些虚构性文本恰恰承载了这样的目的,这种镶嵌式的文本,我们不妨称之为“虚构之虚构”或“虚构的再虚构”。
然而,“虚构之虚构”,并没有将意义指向更加不切真实的虚无,小说反而在这虚构的连环中,以一种更巧妙的方式,精准地命中了真实,并使虚构与真相发生了碰撞,激荡起回响。小说家贝贞创作的小说《一夜》,是一个关于一夜情的虚构小说。因为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发生一夜情时男方在反应上的两个特征非常类似于慕达夫,所以这令冉咚咚直接怀疑贝贞与慕达夫之间存在私情。事实上,虽然《一夜》是以虚构小说的形式呈现,但作者贝贞却是以自传式的笔法进行创作,小说人物及情节的设置都是现实经验的再现。然而,《一夜》中的故事到底发生在谁身上?这在不同之人的讲述之间又频频错位。冉咚咚推断《一夜》写的是慕达夫和贝贞的私情,贝贞的丈夫洪安格却对冉咚咚称《一夜》是根据他们夫妻的故事写的,而在贝贞对慕达夫的讲述中,《一夜》中的情节就是她和慕达夫艳情的再现。可是,当慕达夫试图在脑海中重新拾取这些记忆碎片时,却发现它早已模糊化而变得虚实难辨了,在贝贞的一面之词中,慕达夫感受到“原来记忆是为需要服务的,就像历史任人打扮”[4]。《一夜》所反映的真相也逐渐扑朔迷离,或许只是贝贞期望投奔慕达夫而选择“篡改”了记忆,又或者是慕达夫患上了记忆障碍的疾病。
贝贞最后创作出的小说《敏感族》,也是一个虚构与真实交织的复杂文本,这篇小说与《一夜》一样,都存在着人物命名、情节设置与现实对位的情况。而最后,慕达夫与贝贞两人对《敏感族》结局的不同设计,则隐含了对这段情感纠葛的评判和抉择。慕达夫不满小说人物取名,试图改变小说的虚构性质,认为应当让冬贞回到安木的身边,实际上是借小说之名给予贝贞劝告。于是,人物对情感的审视和诘问,通过一个虚构文本的形式而得到了呈现。此外,命案线中易春阳的诗歌《抚摸》及其互文效果,对于小说情节的叙事推进也有着关键的作用。《抚摸》不仅是虚构性文本,而且更是冉咚咚接近真相的一把钥匙。诗中频频出现的“手”意象,不仅折射出易春阳渴望被爱,却卑微扭曲的内心,而且也成为“夏冰清之死”一案的重要突破口。
在这个意义上,《回响》通过这种虚构文本的镶嵌,不仅使得故事中的案件、情感谜团变得复杂交错,而且也构建了多重的文本层次,让不同文本之间产生了内在关联,进而使小说的深层意义在互文中得以彰显,虚构也得以与真实产生共振。更为重要的是,虚构文本还构建了一个丰富的镜像世界,使人物在虚构的镜像中精准地映照出内心的真实,最终在虚与实的回响中逐步逼近人性的深处地带。
在叙事视角上,《回响》也体现出一种巧妙的形式。小说采取了“第三人称视角”与“多重内聚焦视角”相结合的叙事视角。在整体结构上采用第三人称视角,以主人公冉咚咚作为主要聚焦的角色,既能够使小说的叙述更加灵活,也让冉咚咚成为小说着重塑造和刻画的对象,使其形象立体而饱满。然而,每当徐山川、徐海涛、吴文超、刘青、易春阳等命案嫌疑人被冉咚咚审讯时,小说又迅速地切换至内聚焦视角,让案件信息、人物关系经由嫌犯口中说出。但是,处于讯问席位置上的人为了自保,所讲述的信息无疑掺杂着大量的谎言。此时这些内聚焦叙述者由于渴望脱罪而产生的说谎动机,无疑使其功能身份转变为“不可靠叙述者”。《回响》中的不可靠叙述者,除了畏罪而撒谎的徐山川、吴文超等人外,还有一种特别的典型——易春阳,他患有“被爱妄想症”,而不被划入正常人的行列,这种精神方面的认知障碍,使得他所讲述的信息彻底成为表意的迷宫。“谢浅草”作为他所幻想出来的虚构人物,实则是谢如玉和吴浅草两人的结合体,他所一直重复的“手”也是一种抽象化的表意符号。在易春阳的陈述中,我们闯入的是精神失常者的高度私密化的心理世界,在这里,所有的真相都以一种变形、抽象化的形式而存在,等待我们去推断和破译——这自然为小说抹上强烈的虚实色彩。
再看嫌犯的陈述,这种陈述其实具有着双重的对象,表面上看是向侦破案件的负责人冉咚咚的陈述,但同时也是向读者的陈述——读者此刻也成为破案人。读者可通过嫌犯的讲述来了解这宗错综缠绕的案件,这其中无疑大大发挥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尽管嫌犯巧诈的话语是一个虚实难解的巨大谜团,但所有共犯所讲述的弥天大谎并非滴水不漏,它最终会在前后证词的错位中被逐渐揭破。这样一种多重的内聚焦视角,不仅构造了虚实难辨的事实情境,而且更让案件的解谜成为可能。在犯人所构建的谎言迷宫中,参与破案的读者于其中拾取真实的碎片,并逐渐拼凑出真相的始末。这种形式,在大大增添了小说的可读性的同时,也深化了小说关于虚构与真实的话语表达。
统而言之,通过人物叙述、记忆与潜意识三个层面的深入呈现与大胆解剖,《回响》展示了虚实盘旋的叙事所可能包涵的效能与力度。这种叙事策略对于东西而言,是出于结构探索与文本张力的双重考量。而互文的运用和多重内聚焦的叙事视角,除了深化叙事话语之外,更赋予了文本别样的美学况味。作为读者,阅读《回响》是一种颇有意味的游戏。我们在虚实交错的迷宫之间解谜,这种解谜,不仅是对犹如死结的悬案的勘破,而且更是对自我心理深处最隐秘的真实的勘破。在东西的这种独特叙事下,读者所探寻的真相要么被屡屡刻意延宕与悬置,要么被反复地解构与重构,使得小说总是回旋于虚构与真实之间。当小说到了近乎“无解”的境地时,真相又再次反弹,最终的“实”被和盘托出,柳暗花明。而且,每一个虚构谎言的矫饰和蒙蔽,都使得最终破译出的真相更有价值和份量。《回响》所呈现的便是这种精湛巧妙的叙事技巧与策略,它既为当下小说通俗性与先锋性的结合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的向度,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小说叙事如何处理虚构与真实关系的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