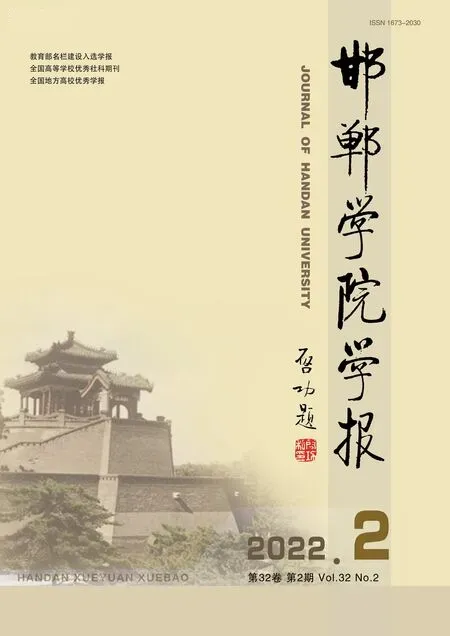论荀子道德哲学的四层意涵和内在理路
秦 晓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127)
荀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以博大精深著称,其道德哲学呈现出丰富的意涵和完整的内在理路,并以儒家成德、成人的境界为最高追求。学界对荀子道德哲学的研究逐渐深入,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读和分析①关于荀子道德哲学的研究可参看,王楷:《论荀子道德主体性的生成和活动》,《社会科学》2019 年第1 期。东方朔,徐凯:《情性与道德转化——荀子论“化性起伪”如何可能》,《社会科学》2018 年第4 期。谢晓东,徐笑悦:《自律还是他律——荀子道德哲学的基本属性》,《中州学刊》2018 年第3 期。涂可国:《儒道互补中的荀子诚信伦理——荀子道德哲学研究之四》,《邯郸学院学报》2017 年第3 期。刘晓靖:《荀子道德理想简析》,《道德与文明》2015 年第4 期。卫建国:《探寻“积”的伦理学意蕴——荀子论道德之“积”》,《伦理学研究》2012年第5 期。王楷:《积善成德:荀子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进路及其当代启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6 期。吴祖刚:《心与礼义:荀子道德哲学的构建》,《船山学刊》2012 年第2 期。。本文立足于《荀子》文本和学界研究成果探讨荀子道德哲学中的天人观、人性论、工夫论和境界论,强调荀子道德哲学这四层意涵的连贯之义与内在理路。荀子的道德哲学不仅承续和发展了孔子以来的儒家重德思想,而且通过向善、积善而成善的论述昭示了个人何以成德的自觉之路。荀子的道德哲学力图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综合考察道德的实践意义,彰显了荀子思想的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
一、天人之分:荀子道德哲学的天人观
荀子的天人观是探究其道德哲学的基础,荀子对天人关系有较为正确客观的认识,在破除殷商以来的神秘天命观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确立了道德行为的主体性归属。《荀子·天论》详细论述其天人之分的思想,荀子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道有其自身规律和运行法则,不为个人品行的好坏而转移,由此表明个人行为结果的好坏应该由自我负责,而非是上天恩威所造成的。“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1]364—365人们可以利用自身的知识和智慧去治理社会,从而达到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但是人却不能“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1]365人不能与天争职,不能取代自然之天的功能和作用,而应该“明于天人之分”[1]364,明察自然与人类的职分,才能做到“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1]366的“知天”境界。这里的“知天”是人在全面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处境和局限时的理性反思,在“知其所为”和“知其所不为”①荀子说:“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的权衡判断中凸显主体意识的作用。
既然人的行为结果不是天命神恩造成的,那么人类社会的治乱和人道德修养的优劣就须由人自身负责,“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1]368君子遵循礼义的规范审慎对待人事,通过自身的努力从而达到内外兼修的成人境界,所以荀子强调“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1]369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在于个人道德修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若夫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1]369品德的高低完全在于主体自觉践行道德的程度。在荀子看来如果人们能够“明于礼义”则能够“制天命而用之”[1]375,通过自身道德修养的不断完善进而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从而为人类社会服务,这样的一种思路可以称之为荀子式的“道德哲学”。强调人的“为己”能力,通过自我的完善促进道德水平的提升,这种道德感的提升不是天命先在的赋予,而是人“日进”努力的结果。由此看来,荀子脱离了天命迷信的思想,充分肯定人在道德上的理性认识和实践能力。
道德行为并非来自于天命,而是人自觉实践的体现,从天人观来看,荀子提升了人的道德主体地位,部分否定了天的神秘力量和人的迷信思想。本于人的理性能力,荀子对于当时的迷信行为进行了批判。对于祭祀求雨、日食月食等现象荀子认为是“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1]374,祭祀求雨等行为并非有求就必有所得,而是统治者为了文饰政治的举动,以安抚民心,所以“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1]374。对于社会治乱是否是由上天造成的这一问题,荀子坚定地认为社会“治乱非天也”。荀子指出大禹使得天下安定而夏桀致使国家动荡,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为因素,不能将人类社会治理的好坏归结为上天的安排,这为荀子道德哲学增添了理性的进步色彩。此外,在《荀子·非相》中荀子列举大量事例批判了当时盛行的“相术”,提出“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1]85的正确看法,荀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以其有辨也”[1]92,能够进行独立思考,判断事物对错的能力,高度肯定人理性思考的积极作用,这就把人的理性能力和天命神学划清了界限。由此,荀子认为对于人道德行为的评价也并非是要皈依天意的安排,个人行为的好坏应该由自己负责,这是道德上君子和小人的重要区别。
可以看出,荀子论述道德哲学的前提是其对于天人关系有着较为正确的认识。从天人之分的角度荀子认为人不能“错人而思天”[1]375,应该重视人自身的因素和社会环境的熏陶。荀子认为应该将道德的依据内化于人的道德自觉,通过人自身不断的道德实践提升自我的道德境界,排除天命迷信的干扰,从而为成人、成德奠定理性的基础。“荀子的着眼点始终是人类社会而不是自然天道,其论证‘天人之分’是为人类在社会中行为寻求自身的依据和准则”。从天人关系出发荀子对人性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通过“化性起伪”等命题荀子进一步论证其道德哲学的人性论特色。
二、化性起伪:荀子道德哲学的人性论
基于对天人关系的理解荀子在人性论方面进一步强调“人性”的二重性和动态性。一方面从自然之天来看人性来源于自然的赋予,本无善恶可言,只是一种淳朴的自然状态;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性随之变化,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性会展现不同的趋势。荀子道德哲学的特色在于将人性中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相结合,将人性的发展看作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动态演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充分重视人的主体因素,注重社会整体对人性的熏陶和造就。通过“化性起伪”等命题表达荀子动态发展的人性观,从天人观到人性论的贯通是荀子道德哲学的特色。
道德的形成在于“化性起伪”的作用,自然之性是人的原初状态,并无道德可言。荀子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1]432—433自然之性必须通过人类社会的涵养和改造,道德意识的形成和道德行为的实践是人遵循礼义和社会教化的结果,单纯的谈论“性”和“伪”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道德思想的社会起源问题。本性和人为的有机结合,通过人的社会属性去改造自然状态,将人的非社会因素转化为社会因素,从而达到“性伪合而天下治”[1]433的目的。唐端正说:“荀子分天与人、性与伪,以天与性为本始材朴,以人与伪为文理隆盛。善是天与人、性与伪合的结果”,荀子清醒地认识到人的自然之性不能自为地形成完美无缺的状态,道德的产生必须经由人类社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通过圣人制礼作乐的文化作用去改造人的自然之性,以达到教化人心的功效。
荀子看重礼义之道的教化作用其目的之一在于将自然之性中的“为恶”倾向消除在萌芽状态,通过社会礼治习俗等规范将道德品质润化入心,从而改变自然之性因欲望引发的“无序状态”,进而达到道德自觉的理性高度。荀子所言的性恶应从荀子思想的全貌去考察,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单独的字句。荀子之所以明言“性恶”是由于其警惕地认识到人性中存在“为恶”的倾向,由此必须高度重视对人性的培养和转化,涵养人性中的向善禀赋,通过礼义教化改变人性的“为恶”倾向,使其向善发展。荀子承认人类存在欲望的本能,他说:“人生而有欲”[1]409,这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和欲望是人性中的自然因素,但荀子也清醒地认识到如若一味地放纵自然本能会造成人毫无礼义廉耻乃至社会混乱无序的糟糕后果。在欲望本能和外物的关系上,荀子主张要“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1]409,荀子这样一种合理调节人之欲望的认识是想通过“化性起伪”的方式达到人性善好和社会文明的良好状态。荀子主张对人性中自然因素进行积极引导和对“伪”的高度重视也是对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思想的引申和发展。从孔子所言“性”与“习”的差异发展成荀子主张“性”与“伪”的区分,可以看出,荀子注重在社会实践和礼义规范中提升人的道德品质。荀子倾向于肯定通过主体的道德实践去自觉抵制人性中自然本能的无度以及“为恶”的倾向,呵护和培育人性中的向善禀赋,力图通过不断地“积善”成为儒家理想的君子乃至圣人。
荀子强调性伪之分着眼于人性中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二重维度,而且荀子认为社会因素在培养人性中的“向善禀赋”方面最为重要,这种“向善禀赋”是人类道德品质的真正起源。人性中“为恶”的倾向如果不加以节制和引导就会流入更加恶劣的危险境况中。荀子看到人性的原初状态是天所赋予,但这种人性的原初状态有向善禀赋和为恶倾向的不同层面,如果没有“伪”则人性必然会流入恶中,所以荀子认为“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1]515。人性从人一出生就会离开淳朴的状态,会由于欲望本能等因素将人引向“恶”的深渊。离开社会中的礼义教化会造成“顺情性则不辞让”[1]516的无礼局面,也就是说如果一味的顺纵“情性”,好利欲得的动物本能就会乘虚而入,破坏道德礼义,威胁人的崇高性,由此荀子着重强调“化性起伪”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说:“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1]517—518,通过圣人努力改变人性中原初存在的“为恶”倾向,利用礼义教化熏陶和润养人性中的向善“禀赋”,为人的道德品质养成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内外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人高尚的道德素质。荀子从经验观察的角度看待人性中的不同面向,关注了人性中存在的危险因素,荀子否定孟子提倡的“性本善”学说,主要目的是为其道德哲学中的“成德”路径提供理性经验上的依据。荀子看到人性在原初状态下的“为恶”倾向从而阐明礼义规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将人性中的道德演变放置在社会交往的整体环境中去理解,凸显社会环境对人的重要影响。当然,以上分析也从一个侧面看出荀子认为道德是人类社会的独特发明,是人理性自觉维护“生活世界”安定和谐的重要保证。
方达指出:“荀子之‘性’在被剥离道德与政治的双重内在意义根据的前提下,一方面作为‘人’达成上述目的的实践资质而凸显自身的内涵,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为现实的实践活动保留了空间,并由此彰显自身的全部意义。”[2]58荀子通过讨论人性中原初的为恶倾向和向善禀赋这二重维度,认为人性在自然因素中没有道德属性可言,应把道德属性纳入人性的社会因素中进行改造。荀子对人性的理解,往往被后世简单地批评为“性本恶”,是有欠公允的。荀子之所以形成人性中有为恶倾向和向善禀赋的看法,并且注重社会礼义的教化,这和荀子“天人之分”的天人观有密切关系,“天生”和“人成”构成荀子道德哲学的两个基本关注点。可以说,自然之天为人性提供原初材料,并表现为人的欲求本能,“为恶”倾向就是人欲失调的内在原因。同时,人作为天下最贵者,又有内在的“向善禀赋”,通过人自身学习礼义从而不断涵养道德情操,这就是“人成”的重要意义。理解荀子的天人观是探究其人性论的基础,而这二者都成为其道德哲学合理性论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天生人成”和“化性起伪”为荀子“积善成德”的道德工夫论提供了依据,人性中的善好可以不断的积累和提升。荀子重视人自身的特质和潜能,通过人自身的努力积累善行和善性,从而达到儒家的道德理想境界,展现出荀子道德哲学的实践特色。
三、积善成德:荀子道德哲学的工夫论
以上通过论述荀子道德哲学的天人观和人性论能够察觉其道德哲学从天人关系到人自身内外关系的贯通。从天人之分的天人关系中荀子总结出天道和人道的不同职分,主张人应该对自己的道德行为负责而不是迷信天命。由天人观进而到人性论,荀子认为人性中也有二重性,通过区分人性中的为恶倾向和向善禀赋,荀子察觉到人性在原初意义上虽“朴”,但其中也善与恶的两层分疏。荀子正是看到了人性中“恶”的一面,理性洞察到人性复杂的面向,所以其主张在“化性起伪”的礼义教化中改变人性中趋恶的倾向,以唤醒人性中的“向善禀赋”,通过“积善”而不断善好。荀子认识到“性”与“伪”二者需要相互配合,人应该在教化中学习礼义,不断提升道德水平,重视人在社会生活中培养道德的实践意义。荀子认为道德的养成须有实践的基础,“积善成德”成为荀子道德哲学的工夫论特色和践行方式。
《荀子·劝学》开篇说:“学不可以已。”[1]1荀子鼓励人们要加强学习,达到德才兼备的境界。荀子尤其重视学习的积累过程,他说: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1]8-9
通过形象的比喻荀子强调学习实践的重要性,道德的养成不是停留在头脑中玄想的空洞观念,而是要通过不断的践行方式来扩充自我的道德感。荀子认为君子的学习不是口耳之学,而是力行之学,“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1]14,君子的一言一行都可以成为别人的道德表率,因此要特别注重个人道德言行的内外如一。荀子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以美其身”[1]15,完善自我的身心,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积善成德”正能体现荀子追求的成德路径。荀子对积善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主张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学也者,固学一之也。”[1]21对于成德目标的达成须有坚持如一的品质,要将道德实践贯穿于人的一生之中。只有通过不断的“积”,才能将礼义道德内化于人的知行活动中,变成人自觉的道德能力。
“积善成德”表现为不断进行道德实践的过程,由此荀子十分强调“行”的重要作用。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往往存在“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1]456的问题,所以荀子强调在人心能够“虚壹而静”[1]467的认识基础上,人还必须“知道察,知道行”,如此才能成为真正的“体道者”[1]469,能够明察和付诸实践才能真正的体悟大道,成为有智慧的人。人的道德品质通过实践活动得以巩固和加强,荀子由此认为“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1]38,其对人自身道德养成的看法涵摄知与行而且突出行动的必要性和目的性。荀子说:“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1]168,可见人能够自觉进行道德实践才是“成人”的理想状态,荀子由此指出圣人“无他道焉,已乎行之矣”[1]168,圣人就是能够完全自觉践行道德之人。
“积善成德”也体现出道德实践的自觉和崇高。荀子认为自我的道德提升并非来自于外力的强迫,而是一种道德自觉。成德的目标就是成人,成人是自身完善的追求,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15,儒家自孔子以来强调的为己之学在荀子心中依然是人道德感培养的自觉认识。荀子说:“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1]23君子注重德行的纯粹和整全,而这种道德的高尚境界必须经由人自觉的实践才能达成。荀子反对外在的强制,始终认为“积善成德”是人“贯之”的道德实践活动,拥有这种“一以贯之”的道德感,则能够卓然挺立于天地之间。在不断“积善”的道德实践中,人的主体精神全然彰显,达到“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1]23的崇高道德境界,这与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3]128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指向“成德”的理想境界。荀子将这种高尚的道德境界称为“徳操”,拥有“德操”就能成为儒家的理想人物,荀子由此特别重视积累善行,涵养善性的工夫论意义。
此外,“积善成德”还在于人对礼义的学习和实践。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在讨论《荀子》中的国家与社会时考察了礼的作用,他指出:“荀子认为礼是儒家学说的‘王道’,它们在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处方上,将道德规范、美学思想和社会行为方式结合在一起。”[4]11礼是社会伦理规范的整合,也是人们学习效法的对象,荀子从天人关系、人性论和社会现实等角度论证了礼治的不可或缺。荀子认为礼义作为个人和社会的规范不仅体现在外在的约束和制度上,更重要的是对于个人身心修养的提升作用。“积善成德”的工夫进展同样也是修身的过程,而修身的主要要求就在于学“礼”。《荀子·修身》说:“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1]26,礼对于身心调节和个人认知的完善均起到促进作用,所以荀子说“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1]31。学习的主要内容在于掌握礼义规范,个人通过“积善”对礼义进行内化和吸收,通过认知和实践活动促进人们遵守礼义,这其实就是“伪”的重要方法。荀子认为:“礼者,所以正身也”[1]39,礼是端正身心的重要凭借,由此则君子能够“以公义胜私欲也”[1]42。可见,“积善成德”的工夫实践是个人用道义战胜私欲的斗争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人通过持续不断的道德实践充盈人性之中的道德感,从而使人性沐浴德性之光。
概言之,通过“积善成德”的工夫进路,荀子认为一个人的善性可以积累,不断涵养人性的“向善禀赋”,达到一定程度就能成为儒家的君子和圣人,这是荀子道德实践的理想关怀。东方朔指出荀子的意图在于“人唯有经由此积伪功夫才能将自己能够成为圣人的潜能发挥出来并转化为实现形态”[5]142,这样的“积善”活动不单是道德行为次数上的增加,更是一个人从动物本能转化为社会道德存在的德性提升。荀子着眼于社会全体的道德进步,将“学而时习之”[6]2的理念遍及社会成员,荀子认为只要坚持学礼,积累善德,都可以成为道德高尚的人。荀子“积善成德”的道德工夫论扩展了儒家道德哲学的适用范围,并通过切实可行的践行方式对人的身心起到净化和提升的作用。对于个人积善而成德的道德期许透露出荀子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精神。
四、圣心备焉:荀子道德哲学的境界论
荀子道德哲学的宗旨在于达成儒家的道德理想境界,通过天人观、人性论和工夫论等不同角度可以看出荀子道德哲学的内在理路和成德路径。这一成德路径的目的在于“成人”,憧憬儒家圣人的境界,荀子称为“圣心备焉”。普通人通过道德实践能够成为圣人,通过提升人的道德修养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荀子为人人可以成圣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做了细致的论述。
首先,荀子认为普通人和圣人都有相同的“质”和“具”。荀子在回答“涂之人可以为禹”的问题时说:“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1]523,普通人和大禹具有相同的材质和才能,这就为涂之人可以成为禹奠定了人性的基础。圣人与普通人不同之处在于圣人能够完全自觉地实行仁义法度,而普通人虽有材质但却没能完全自觉的发挥出来,没有一直自觉坚持“积善成德”。由此,涂之人在道德养成上必须善于学习和实践,将自身所具有的“质”与“具”充分实现出来,扩充完善自我的才具,以促进道德的自觉达成。
其次,普通人可以通过自觉的道德实践积累达到圣人的境界。具备“圣心”的关键在于持续的积善,荀子主张:“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悬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1]524通过持续不断的道德实践,“圣心”就会自然呈现。荀子认为圣人之所以成圣是通过长期实践达到的一种自在自为的状态,所以荀子指出:“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1]524“积”是成圣的前提条件,普通人通过长期积累善行也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成就圣心。《荀子·儒效》中也指明:“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1]171,通过“慎习俗,大积靡”[1]171的自我道德实践,不断积累善行和善性,从而达到至善状态的人就叫作圣人。荀子指出“圣心”和“凡心”共同具备实现道德境界的材质,区分在于是否能够完全实现出来。换言之,荀子对于“圣心备焉”的论述隐含着个人的道德禀赋从潜能到现实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从“凡心”到“圣心”的超越。
最后,“圣心备焉”也是人自觉进行道德实践所达成的状态,而非外铄和强迫的结果。“圣心”之完备全在于人心“知”道的能力,这充分展现了“心”在荀子道德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荀子宣称的“大清明”之心是人能够体认道德至善的内在依据,是人通往“道”的“心”之途径。荀子再三强调“心”在道德认知和实践中的功用,正是有见于“心”的主动能力和贯通能力,由此所呈现出来的“圣心”就是一种至善无蔽的道德境界。通过修养工夫的不断推进,人心的能力也逐渐加强和完善,道德自觉的程度会逐渐增加。不过荀子也清楚地看到,积善能够达到儒家圣人的境界,然而在现实中并非每个人都是圣人。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荀子提出“可以而不可使也”[1]524的观点,他认为能够达成“圣心”是人自觉实践的结果而非外在的强迫所致,人之所以积累善行不是因为外在的功利标准而是人内心对道德境界的自觉向往和追求。道德上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在于人们是否拥有“可以”为禹的道德自觉,由此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1]524,荀子强调人的道德自觉是“可以为禹”的先决条件。荀子的论述展现出达成道德境界的可行性途径,但并未断言每个人必然能够成为圣人。实现道德境界的关键因素在于进行人是否能够自觉地持续不断的“积善”,荀子认为普通人如若能够“积善而全尽”则“圣心备焉”也是能够达成的。
总而言之,荀子向往儒家理想的道德境界并给普通人以方法和指导,通过礼义教化的功效促使人们自觉学礼、知礼,在积善的道德提升过程中完善自我人性中的道德禀赋,从而达到“圣心备焉”的境界。人性中的自然因素是天生而来的,人虽不能造就和决定自然本能,但在道德实践中能够通过自觉的善行转化人性中“为恶”的倾向。在“化性起伪”的工夫修养中,人通过道德实践修养身心,砥砺品行,澡雪精神进而提升道德感,长期不懈的学做圣人,进而达到圣人的理想状态。荀子对“圣心”的强调正是看重个人道德自觉的体现,也是儒家一贯的目标。荀子有感于战国中后期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和人性沦丧的危机,在功利横行的动乱时代坚守儒家成人、成圣的道德追求。荀子主张人应该将道德的养成视为自觉的行为而非外在的强迫,这是宣扬人性善好光辉的强烈呼声。荀子对人道德感不断生成和积累的认识,力图通过向善、积善而成善的方式昭示普通人的成德之路,可谓用心良苦。“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1]171,荀子将道德境界看作人能够通过自觉积累达到的目标,这是一种理性而务实的思想。“圣心备焉”成为荀子道德哲学境界论的突出特征,也已潜藏着后代成性说的思想萌芽。
余 论
综上所述,荀子的道德哲学具有较为严密和完整的内在理路。首先,从天人观的角度荀子论述了外在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不同,主张天人之分,认为人应该为自己的道德行为负责,确立了道德行为的主体性归属。其次,从人性论方面荀子区分了人性中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属于人的本能是天生而成的,而社会因素则可以通过礼义教化进行改造提升,荀子区分了人性中原初的为恶倾向和向善禀赋,由此提出“化性起伪”的命题,强调道德的自觉性和实践性。再次,从工夫论入手荀子主张人能够“积善成德”,通过自觉的道德实践,积累善行,达到成德、成人的理想目的。最后,从境界论来说荀子道德哲学的目的在于达成儒家理想的道德境界,“圣心备焉”彰显了道德的至善状态。总之,荀子的道德哲学是儒家成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述普通人如何成德上荀子力求通过理性经验的路径分析成德的可行性,注重知行结合,强调道德活动的实践意义。荀子指出人的道德感“不学不成”[1]578,扬善去恶,弘扬道德价值,坚守道德自觉是人“最为天下贵”[1]194的宗旨所在。
通过对“性伪合”的论述,荀子指出人性向善的可行方案。荀子主张将人的自然本能提升和转化,通过学习礼义涤除人性中破坏个人道德和社会发展的自然因素,为人成就自身道德提供理性经验的方法。荀子凸显道德自觉的必要性和严肃性,在终身学习中成就人的至善状态。荀子认为在成德的过程中个人要时时反省和改进,并结合儒家圣人的标准省察自身,这一工夫修养的经验进路不同于先验道德的先在性,而是通过实践经验达到儒家的道德境界。荀子道德哲学中对人性的这种认识,不同于复性说的先验设定而是一种颇似成性说的经验之路。荀子所主张的道德进路,是在“性伪合”的前提下对人性向善禀赋的培育和巩固,也大不同于思孟学派所主张的先验道德思路。刘纪璐说:“荀子跟孟子一样是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只是孟子比较理想主义,从性善出发,带出以道德情感来重建社会秩序的希望,而荀子则是切实的实用主义,从性恶出发,强调以礼义师化来建构社会的秩序以及个人的道德行为。”[7]256孟荀两位思想家的道德目标都是达成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二人采取了不同的论证进路,但都主张培养自我德性,都强调个人道德自觉的必要性,可谓殊途而同归。
当然,荀子道德哲学的追求不仅仅关乎个人“成人”,而是关注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荀子主张通过礼义教化的方式不断巩固社会道德风尚进而实现儒家治道的理想。荀子从儒家的立场出发认为,道德是连接个人与社会,内与外的媒介和基础,道德是政治哲学的根基。荀子的这一主张既是周代重德思想的承续,也凸显出儒家德治理念的优先性。这种德治的传统是儒家思想的底色,荀子不仅深化了礼的内涵,而且主张将伦理道德应用于国家治理中,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目的。荀子对于道德哲学的认识既坚持个人道德自觉的必要性,又突出道德对家国秩序建构的重要性,是一种融合儒家道义和修齐治平目标的道德主张。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就此指出:“荀子为‘采纳’一种道义论的道德主张而提供了一种结果主义论辩”[8]256可谓确有所见。荀子尊崇礼义,注重个人道德的提升和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他强调:“礼者,人道之极也”[1]421,真正遵循礼治的君王才能实行“王者之政”。荀子在“迫于乱世,䲡于严刑”[1]653的残酷现实面前高扬儒家道德理想的大旗,将对个人道德自觉的认识融入“积善成德”的经验进路中,积极探寻人的道德价值,鼓舞普通人也可以成德、成圣。这种关注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文明构建的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是荀子思想中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