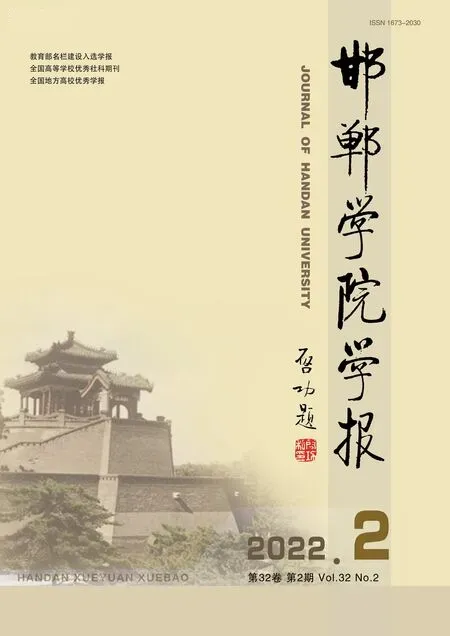中国传统复仇观与礼法之争
贺如文
(淄博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淄博 255314)
一、复仇作为刑法起源之一,其观念的变化与文明进程、民族文化心理相统一
复仇既根植于人性的本能,又在文明的演进中受到习俗传统、道德法律乃至时代思潮的影响。作为一种本能,复仇欲难以彻底根除、克服,正如康德所言:“由于遭遇到不公而产生的恨,亦即复仇欲,就是不可遏制地产生自人的本性的一种情欲”“它是最强烈、最根深蒂固的情欲之一”[1]265作为一种观念,复仇随同历史文明进程的发展不能不发生变化。据有关学者考证,复仇源自人类的种族保存性,在氏族社会时代,它被视为一种种族保存的基本美德及绝对义务,是人类社会的一般现象,复仇不受节制,反受到鼓励。最原始的复仇都是血亲复仇,其形态往往表现为同态复仇。随着人类脱离原始社会,建立起国家,复仇受到了国家刑律的限制,私人复仇逐步地让渡为国家刑罚,其后复仇被法律所明确禁止。可见,复仇与法的起源息息相关,有些学者认为,复仇的本质并不是主观情感,而是一种实现社会外部均衡的竞争与斗争[2]141-144,故复仇为刑法起源之一。在对法的研究中,复仇一直是个非常核心的重要观念。黑格尔和康德共同主张,惩罚应当是纯粹的报复[3]1226,保罗·利科认为惩罚“尤其是当其保留了赎罪这一古老理念的某种特征时,保持了被削弱了的、过滤了的、文明化了的复仇形式”[4]150。复仇观念的演进与法的观念的进步脱不了关系,而法的进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识,在法的意识的统辖下,总体说来,各个国家民族的复仇观在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演化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阶段。在人类文明的原始阶段,复仇已经有所演化。柯斯文在《原始文化史纲》中将原始人的复仇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全族复仇,直到一方完全被歼灭才罢手,人们不仅对复仇不加丝毫的限制,反而对不复仇进行惩罚;二是仅限于同类复仇,所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复仇行为不再散漫无度;三是以赎罪金代替杀戮复仇,血腥复仇的现象大规模消减。这显示出了理性逐渐战胜原始激情主导人类文明进程的强大力量。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在考察复仇与法的关系时认为,人类复仇经历了四个阶段:复仇义务期,复仇限制期,复仇赔偿时期,复仇禁止期(刑罚时期)。严格来说,金钱赔偿作为复仇的替代制裁,是一个由限制复仇到禁止复仇的过渡时期。进入刑罚时期,私力复仇乃为法律所全面禁止。可见,人类文明的进展与对复仇的限制与禁止呈现出同序发展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期间,复仇始终是作为一种威慑力量而存在的,即使人类文明全面进入了复仇禁止期,复仇作为一种自卫,与法治相互补充,也从未从社会现实中绝迹。
复仇观形成与确立的过程是缓慢的,它同时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与濡化过程,反映出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演化轨迹及特色。在文明社会中,复仇主要受到法律的约束禁止,但也部分地受到文化习俗的影响。西方文明之发展强调法,故其复仇观多从法的演化与推进来演绎及考量,正义、惩罚、赎罪、权利等观念都在对复仇与法的关系的思考中一再得以讨论和辨析;其受宗教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忏悔与宽恕的观念在宗教教义的影响下成为西方复仇观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在西方社会,法律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当复仇这一私力救济作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从人类文明史中消失后,诉讼便成为遏止和解决社会冲突的主要手段。“这一现象表征着一个极有意义的社会进步:人类不再依靠冲突主体自身的报复性手段来矫正冲突的后果,尤其不再用私人暴力杀戮式的冲突来平息先前的冲突。”[5]3尤其在西方社会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神权统治后,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推动了人类理性文明的飞跃发展,它发扬光大了古希腊的理性、批判精神,确立了人类自主理性的崇高地位,人类对法的思考和实践进入一个高度繁荣和发达时期。启蒙哲人们以理性之思奠定了自由、责任、人道主义等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公权力代行私力复仇职能的刑罚朝着更加人道更加和平的方向迈进。进入20 世纪,法律和观念意识中的复仇色彩越来越淡化,国际法的诞生、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胜利、南非反种族隔离与种族和解的成功等等都显示出人类理性在调解、制止冲突,消除仇恨,推动人类社会实现永久和平进程中所发挥的惊人作用,以至于保罗·利科在谈及法的正义观念时断言:“我们时代伟大的胜利存在于将复仇与正义分离的过程之中。”[4]前言6
二、礼法之争中的中国伦理化复仇观反映了尊礼卑刑的民族文化心理
与西方对法的强调不同,中国文明发展长期处在礼教伦理的规范之下。礼本于人情,复仇观也多出于对伦理秩序的维护及对人情的体察以成型。复仇观在演变过程中较少受到法的左右,反接受了儒家礼教文化的强制规范。瞿同祖认为:“儒家以‘礼’规范复仇的行为,实有别于原始社会的报仇,可说是‘伦理化’的复仇观。”[6]26台湾学者李隆献在《复仇观的省察与诠释》一书中进一步将这种中国古代文化特有的伦理复仇观核定为五伦复仇观。所谓“五伦”乃为父子、君臣、夫妇、昆弟、友朋这五种人伦关系,对这五种人伦秩序,孟子宣扬应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汉代董仲舒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作为规范人的行为的总原则,后进一步发展为三纲六纪说。五伦观念作为儒家礼教中最为基础性的观念,是整个道德秩序的起点,有学者称它“在后续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发展过程当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成为所谓‘纲常名教’的中心,深刻地影响着华夏文明的价值选择、精神气质和基本走向,也规范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之社会群体及个人行为模式和立身处世的根本准则。”[7]所谓五伦复仇观,是按照纲常名教确定的尊卑贵贱之分,上下等级之别,亲疏远近之异,对复仇行为的义务范围和实施方式予以规范,形成了一套亲疏有别的复仇原则和避仇方法。《礼记·曲礼上》云:“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大戴礼记·曾子制言》曰:“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贯穿于这套复仇规范中的是“忠”“孝”“仁”“义”等概念范畴,这些概念范畴“决不仅仅是思想交流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又是思想的主宰。”[8]究其实质,这套复仇观确立、规范、巩固的乃是一种与政治连体的统治秩序。进入文明社会,复仇的私力救济功能必然要让位于国家公力惩罚职能,因而,尽管伦理复仇观占据民众意识的主导观念,但是法的干涉注定无法避免。中国传统社会中“礼”与“法”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紧张或对立,“在我国的司法史上,‘法礼之辩’历朝历代一直争论不清。所谓法礼之辩,即国家法律与忠孝礼节之间的矛盾,譬如一向让皇帝丞相挠头不已的‘孝烈’。此类于法不容、于情可宥的案件,实质在于血亲报仇的礼教观念与国家刑法严正性之间的冲突。”[9]礼法之争在复仇观的确立与演化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复仇观也鲜明地反映出礼法之争的实质和主导,复仇观念看似徘徊于礼法之争的罅隙,而实质上最终服从礼的规范,这是导致中国民间社会崇尚复仇的根本原因。李隆献认为:“人类的复仇行为即使有生物性的来源,然而在复仇观社会化的过程中,庞大的儒家传统以其一贯的方式,亦即将原始社会的种种习俗规范化、礼仪化、经典化,因此原本血亲复仇的模式——或者以氏族成员为对象;或以造成对方相同的痛苦为目的,或专以施害者为对象——这些模式便逐渐为儒家经典诠释所收编,先是藉由经学的地位将之学术化,在经由深习儒家思想的循吏法外施恩的实践,因此在民间社会形成一股坚实的复仇思想与风尚。”[10]53儒家的五伦复仇观尤其是“父仇不共戴天”的观念在士人与百姓中可谓根深蒂固,民间传统中也一直存在着崇尚孝义复仇的风气,这个特点可以说与儒家文化提倡忠孝之道,尊崇伦理秩序,推行以礼越刑的政教之道有根本的联系。儒家文化强调实施礼教,以礼辖制法是其根本特征,“尊德礼而卑刑罚,是儒家一致的信仰。”[6]313梁漱溟认为,“中国制度似乎始终是礼而不是法。其重点放在每个人自己身上,成了一个人的道德问题。”[11]188瞿同祖提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治特征是“以礼入法”,确然抓住了礼法之争的本质。礼法之争这一表象反映的是谁为根本的主体之争,事实上,斗争的结果最终无不屈从于礼的统摄之下,达成法对礼的妥协,国家律法“于是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儒家的目的也就以变通的方式达到,而踌躇满志了。”“所以礼所容许的,认为对的,也就是法所容许的,认为合法的。礼所不容许的,禁为的,也就是法所禁为的,所制裁的。”[6]349考察礼法之争的史实,唐朝时陈子昂奏议徐元庆案、韩愈所论的梁悦案都是极典型地反映了礼法之争的实例。
徐元庆案发生于武则天主政之时,同州下圭(今陕西渭南)徐元庆之父被县尉赵师温所杀,元庆手刃仇人后投案归罪。时任谏臣的陈子昂提出“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12]195,他采取折中之策,建议诛之而后旌表其孝,被武后采纳。陈子昂的判决强调的是以国法为重,实质为法陵越礼之上。70 余年后,柳宗元作《驳复仇议》对陈子昂的判案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反驳。他反对这种既诛又旌的做法,以为“旌与诛,不得并也”[12]195,“《驳复仇议》认为‘礼之大本’为‘防乱’,‘礼’与‘法’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法’之判决应合于‘礼’”[10]249。唐宪宗元和六年发生梁悦案,梁父被杀,梁悦手刃仇人,投案自首。韩愈认为,“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于《周官》,又见于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2]15韩愈为儒家经典不“非而罪之”,法律不强自规定作出了辩解。“之后儒者皆颂扬柳、韩,贬低陈”[2]15。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法或可一时陵越于礼之上,但在多数时期,则总是屈居于礼之下。儒家的孝义观对于复仇观影响至大,李隆献总结:“中国传统的复仇观,乃是以儒家‘孝义伦理’为基础而发展出来的行为,……历代的‘复仇’事件多半能获得社会舆论的怜悯、认同,甚至官方/执政者的同情,乃至嘉勉、褒扬。”[10]260从这两桩案件的处理原则及对后世的影响看,法与礼始终处于不对等的地位,“礼”是道的体现,是根本性的原则,而“法”则仅仅被视为治国之术,术不能违道。
三、以“孝义复仇”为重的中国传统复仇观体现了家国同构的统治秩序原则
中国律法的传统不同于西方法典中的“立约”传统,中国律法不具有神圣性及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其内含的道德基础受习俗决定。而西方律法自汉莫拉比法典起法律的制定中就存有人与神的“立约”传统,树立了法的权威性和确定性,中国的律法因统治者意志的变更及习俗的变化则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观之复仇,复仇观念的增强和减弱,有时也会系之于礼法之争表现的强弱。统治者若强调法,则复仇观念为之削弱,统治者若偏于礼,则复仇行为就愈演愈炽,这亦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秩序上法的弱势不固,统治者的个人权力始终左右着法律的实施,体现了人治的不稳定性。在国家治理上,因为尊礼卑刑的权力统治特点而呈现一种制度上的松动散漫状态,这种松散的治理结构给予了复仇行为以极大的生存空间。
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复仇观念较强盛,除了维护伦理秩序的礼始终凌驾于维护社会秩序的法之上这一原因外,与社会结构的政治建制也有极大的关系。封建专制的大一统下,以县为基层单位的政府约束极为松散,县级以下不设立治理与办事机构,其日常秩序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家族势力地方乡绅势力辖制的乡民自治来实现对民众的统治。“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基层统治的平稳之所以能够实现,还是有赖于家国同构的国家建构体制。家国一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建构特点,其实质是忠孝的联姻,以“孝治天下”来确立统治秩序,孝达成的既是对家长的忠实,也是对家族、国君的忠实,“孝”成为统治秩序最根本的奠基基础。在中国,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政治秩序建构模式使统治阶级大张旗鼓地宣扬孝道,推崇孝道,不可能否定也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打击孝道的体现——血亲复仇。独特的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制度设计,形成了国法与家法的共生共荣关系。家法作为一种私法,从来未受到国家公法的打击,反受到承认与保护。家法公然成为国法的下位法,以宗族、祠堂为其精神、物质表征。家法既是对国法的解释和落实,也是对国法的补充与协助,且家法的实施更偏重于国法中的伦理内容。汉唐以来,法是德的副本,而家法更是德的表现。儒家强调个人道德,尚没有把行为原则与法联系在一起,只要能有利于五伦之德的,便是合理。另一个是私法与公法的问题。法家思想体现在公法中,当然强调国法的权威,但是,自古就有家法,私法,复仇也就有了法的意义上的存在。大规模的家族仇杀与械斗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而家族/家庭内的矛盾争斗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向来是公法不情愿干涉的,借助家法它们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且得到公法的默认。追根究底,黑格尔说,中国“那终古无变的宪法的精神”就是“家庭的精神”,“这种关系表现得更加切实而且更加符合它的观念的,便是家庭的关系。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缘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13]121-122故而,在家庭精神的立法原则下,孝义复仇行为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排斥和否定的,除非它在某段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妨碍了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孝义复仇行为多受到保护,直到民国时期这一传统仍在延续,发生在1935 年的施剑翘为父复仇案就是一则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