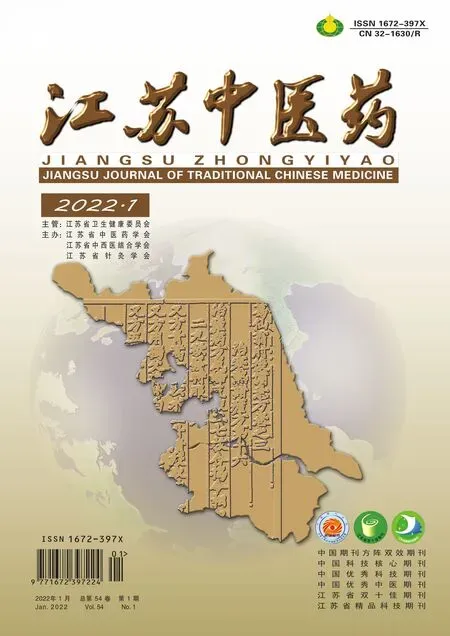陈宝贵基于癌毒理论辨治肝癌之经验
林小林 桑 怡 刘 丹
(1.杭州市中医院,浙江杭州 310007;2.天津市武清区中医医院,天津 301700)
指导:陈宝贵
“肝癌”病名在古代中医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可将其归属于“胁痛”“臌胀”“黄疸”“癥积”“肥气”等范畴。早在《难经》中就载有与其相似的症状:“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久不愈,令人发咳逆,疟,连岁不已。”《仁斋直指附遗方论》中“癌者,上高下深,岩穴之状……毒根深藏”是对“癌”最早的记载。首届全国名中医陈宝贵教授为张锡纯中西医汇通学派的第三代传人,其在“正损为本,癌毒为标”的理论指导下辨治肝癌,注重扶正祛邪、抗癌解毒,临床疗效颇佳。笔者有幸侍诊,现将陈师基于癌毒理论辨治肝癌之经验介绍如下。
1 正损为本,癌毒为标
陈师认为肝癌病因以正气亏损为本、癌毒搏结为标,而癌毒致病又有内伤外感之辨。外感者,六淫之邪如周边环境中某些物理或化学潜在致癌因子、病毒等侵袭,损伤正气,气血循行瘀滞,而成积块。内伤者,在先天禀赋不足基础上,复因七情内伤,致使肝气不得疏泄;饮食劳伤,水谷失运,生湿成痰化热;痰湿阻滞血行,最终导致气滞血瘀痰凝,阴阳失衡而成癌瘤。病机主要为先天禀赋不足,素体正气虚损,复因热郁、血瘀、痰凝、气滞、湿阻而成癌毒,从而导致脏腑、气血、经络、阴阳失调,日久郁而成有形之结块,症见胁下痞块、疼痛拒按,其中黄疸为主要症状。
1.1 伏毒蓄积,胶着难解陈师认为癌毒作为恶性肿瘤的特异性致病因子,伏藏于正虚之处,贯穿肝癌发生发展始终,与热、瘀、痰等病邪胶结为患,导致肝脾两伤,癌瘤形成。因此,伏毒蓄积为肝癌发病之关键[1-2]。肝癌初期发病隐匿,症状纷繁复杂、潜伏难察,确诊之时多处疾病中晚期,药力难消,或经西医手术、放化疗后“余毒”伏藏于里。“伏毒”入络入血,根深蒂固,胶着难解,暗耗脏腑精气血津液,一旦他邪引动,便一触即发,势不可挡。癌瘤痼疾总属消耗性疾患,夺取水谷精微气血以自养,损伤脏腑,耗损正气,患者多见消瘦、纳差乏力、精神萎靡,邪胜正竭而阴阳离决。
结合现代医学,陈师认为肿瘤组织内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肿瘤细胞的异常增殖和分裂、逃脱免疫监控、逃逸凋亡,致使肿瘤恶性无序生长;肿瘤组织局部缺氧坏死、炎性细胞浸润,可视为“癌毒”的“伏毒蕴结”表现;肿瘤患者恶液质、免疫力低下、易感染,是“伏毒伤正”之表现。
1.2 流毒走注,于至虚之处传舍《灵枢》中载有:“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络脉……留而不去,传舍于经”,“传舍”是《内经》对疾病传变的认识[3]。陈师认为癌毒走注侵袭是“流毒”特点,亦是肿瘤转移的先决条件。癌毒留结,近可氤氲浸淫,远则随气血运行而流窜走注,于至虚容邪之处停积,阻滞气机,酿痰成瘀,与相关脏腑亲和搏结而成新肿块。
现代研究发现,肿瘤细胞是在机体免疫异常的基础上,合成和分泌生长因子、基质金属蛋白酶等介导细胞外基质重塑,促进新生血管形成,为肿瘤的生长和转移提供物质基础,同时降解钙粘蛋白,分泌大量波形蛋白、纤连蛋白等,使肿瘤细胞获得运动性,近可向邻近脏器种植扩散转移,远可通过脉管、淋巴道等远端定植[4]。陈师认为免疫抑制、微环境的异常可理解为局部“正气虚损、阴阳失衡”,其依附的载体血管、淋巴管、肿瘤间质等可视为气血三焦等通道,而肿瘤侵袭和转移的特点可理解为流毒走注。
此外,陈师认为流毒走注与瘀血密切相关,正如唐容川《血证论》言:“瘀血在经络脏腑之间,则结为癥瘕。瘕者,或聚或散,气为血滞,则聚而成形。”瘀血主要是由血行不畅凝滞于脉中,或血液不循常道,或离经之血溢于脉外所致[5]。通过取象比类,陈师认为肿瘤患者机体高凝状态,肿瘤阻塞脉道,形成癌栓,即为“血行不畅而凝滞于脉中”;血液在结构高度无序、血流紊乱、缺氧、酸性微环境的肿瘤血管内循行,即为“血液不循常道”;肿瘤血管内管壁细胞间隙增宽,基底膜降解缺失,内皮细胞重叠生长,突入管腔,导致血液外渗,或由于血管通透性增高,血液渗漏至组织间隙导致出血,即为“离经之血溢于脉外”。
1.3 阴阳失衡,正邪交争肿瘤的形成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陈师认为,阴阳失衡、正邪交争贯穿癌毒演变始终:肝癌发生早期,肿瘤细胞内基因失控突变,能量代谢紊乱,破坏正常细胞的生长平衡,浸润局部组织,是“癌毒渐盛,正气渐衰”;肝癌发展进程中,肿瘤细胞降解周围基质,促进肿瘤新生血管生成,为肿瘤组织获取营养,突破基底膜进入血管、淋巴管完成远端移植,是“癌毒极盛,正气极衰”;肝癌发展晚期,肿瘤细胞增殖失序,营养失供而坏死,是“正气衰竭,癌毒极盛,而成阴阳离绝之势”。
2 扶正祛邪,抗癌解毒
现代医学治疗肝癌,多聚焦于瘤体本身,其作用靶点相对单一,犹如孤军作战,往往不能正中要害,反而容易被肿瘤细胞各个击破,无法阻止肿瘤的转移和远端定植。肝为藏血之脏,喜条达而恶抑郁,肝藏血,血养肝,肝体充足,肝用则调和;肝主疏泄,血归肝,则肝体充盛。因此,陈师在肝癌治疗中补肝体和益肝用并重。其次,陈师治疗时注重固本清源,把握肝癌的“伏毒”“流毒”病机,做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先安未受邪之脏。此外,陈师临床思辨肝癌“癌毒”盛衰时,除了通过人体外在器官和形态神色以“司外揣内”,推断内在脏腑的变化,把握疾病的本质和发生发展趋势之外,还结合现代诊疗手段例如腹部CT、肝脏磁共振成像、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组织分化类型、肝功能、肿瘤细胞增殖标志物Ki-67表达、凝血功能、血常规检查等来判别癌毒的毒力大小、寒热属性、预后。在肝癌治疗进程中,陈师始终秉持“扶正祛邪”与“抗癌解毒”的治疗理念。
2.1 杜绝生毒之源,未病先防脏腑经络功能的平衡与协调,是固护正气和祛除邪毒的基础。肝癌多由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肝纤维化、肝硬化进展而来,上述病因致使肝细胞在损伤后的再生修复过程中生物学特征逐渐变化,基因突变、增殖与凋亡失衡、慢性炎症及纤维化过程中的活跃血管增殖,为肝癌的发生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陈师认为这种平衡的打破可视为肝脏气血津液阴阳的失衡。针对原发疾病发展过程中气滞瘀阻,生湿酿痰,郁久化热成毒,治疗原则以“清源”为主,未病先防,治以理气化痰、活血化瘀、清热解毒。此外,肝体是肝用的物质基础,肝用为肝体功能活动的表现。肝体阴血制约肝用阳气过度升腾,避免肝用亢盛,使之冲和条达;肝疏泄阴血,通畅经络,则肝体柔和。肝主疏泄,促进津液气血正常输布代谢,则无聚湿成水生痰化阴之患。因此在治疗时尤重“固本”,施以疏肝柔肝,擅用逍遥散、柴胡疏肝散、当归芍药散等方以安未受邪之地。
2.2 清除已生之毒,既病祛邪针对肝癌发病过程中气滞痰湿瘀热毒邪之所盛,陈师辨何邪之所盛而针对性地选用相应治法:
(1)清热解毒:风、痰、湿、瘀、火、毒内蕴,阻滞经络,日久皆可化热,炼灼成毒,治以“热者寒之”。清热解毒药多苦寒,常用于治疗热毒内盛、癥积痈肿。现代研究发现清热解毒药具有抗炎、抗内毒素、抗氧自由基、抗病毒、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等作用[6],陈师常用山豆根、山慈菇、马齿苋、甘草、白蔹、半枝莲、半边莲、白花蛇舌草、苦参、蒲公英、黄连等药物。(2)化痰软坚:痰凝郁结是癌毒走窜、蕴结难消的基础,古有云“怪病多痰”。化痰软坚药多辛、咸,常用于痰气凝滞、瘰疬癥瘕。现代研究发现化痰软坚药具有激活内皮网状系统、抑瘤、抑制血管生成等作用[7],陈师常用半夏、天南星、牡蛎、海藻、僵蚕、薏苡仁、八月札等药物。(3)活血化瘀:瘀血阻滞,郁结壅塞,稽留不去,息而成积,“菀陈则除之者,出恶血也”。活血化瘀药多辛温,可温经通络散寒、行血消癥。现代药理研究发现活血化瘀药可抑制肿瘤增殖、诱发凋亡、调节免疫、抑制血管生成,对放化疗有减毒增效、逆转耐药的作用[8],陈师常用川芎、郁金、鬼箭羽、刘寄奴、乳香、没药、当归、桃仁、丹参等药物。(4)以毒攻毒:癌毒为患,其致病猛烈且顽固,非攻不克。虫类药具有搜风通络、攻逐走窜之效,可引药力直达病所,松透病根。现代研究表明,许多虫类药有以毒攻毒之效,可抑制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抑制炎性微环境,发挥抗肿瘤效应[9],陈师常用蜈蚣、全蝎、蜣螂虫、土鳖虫、蜂房、蟾酥等药物,多配伍养血滋阴之生地黄、石斛,健脾益气之当归、白术防攻邪太过而伤正。
2.3 瘥后调摄,防其复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自古多强调正气的重要性,如“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治积者,宜先养正,正气足则积自除。仲景言“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陈师认为肝体为肝阴肝血有形之体,非阴柔酸敛之品不能补之,处方多喜用酸枣仁、五味子、炒白芍、山萸肉、鸡血藤、山楂、生地黄;癌瘤瘥后,更要扶正固本,脾土得肝木而达,故而肝癌治疗更要注重肝脾同调,时时固护胃气,调节脏腑气血阴阳平衡,正如《金匮要略》云:“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陈师临床常用六君子汤、参苓白术散、三仙汤、补中益气汤、化积丸、化肝煎、平胃散等健脾,擅用薏苡仁、柴胡、炒白术、茯苓、鸡内金、麦芽、陈皮、麦冬、白扁豆、甘草、大枣、生姜等培土以荣木。久病及肾,肝肾“乙癸同源”,精血互化,针对肝肾亏虚证,陈师多予黄精、熟地黄、生山药、泽兰、牛膝、桑椹、枸杞子、柏子仁等滋肝益肾。治疗期间对患者宣教亦至关重要:饮食调护方面嘱患者戒烟禁酒,忌食辛辣刺激之品以防“食复”,加强优质蛋白摄入;起居调摄方面嘱患者起居有常,适量运动以防“劳复”。
2.4 调畅情志,心身同治肝喜条达恶抑郁,主疏泄,调畅气机情志尤为重要。肝癌患者知晓病情后,多会出现情志抑郁,疏泄不及,气机郁结,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情绪紊乱,如焦虑抑郁、敏感、内向、神经质、易激惹、易怒、悲观、失望、情绪低落、拒绝社交等。长期的负面情绪刺激加重患者的病情,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导致疾病进展加快。陈师临证尤其重视情志因素对肝癌病情发展的影响,认为剧烈的情绪波动是启动癌症加重的按钮,治疗时应重视调畅情志,情志得舒可通畅全身气血循环,调和阴阳。临证时陈师常根据病机辅以补气理气疏肝之品,如柴胡、郁金、香附、八月札、香橼、佛手、代代花、玫瑰花、栀子等,同时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关注其心理变化,移情易性,通过“告”“语”“导”“开”等技巧与方法稳定患者心态,即初诊时多耐心告知患者具体病情,在肝癌进展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导安慰,在肝癌病情相对稳定时让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病情,正确认识自身疾病,缓解患者负面情绪,营造舒适、自信的心理稳态。
3 验案举隅
张某,女,85岁。2020年8月27日初诊。
主诉:腹胀乏力、目黄肤黄尿黄1月余。患者1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腹胀、乏力,伴目黄、肤黄、尿黄,腹围增大,间断恶心欲吐,当地医院查肝脏MRI提示:肝癌伴肝内多发转移,腹膜及网膜多发转移,腹水形成,肝硬化,脾肿大,门脉高压,侧枝循环。甲胎蛋白(AFP):178.47 ng/mL(正常范围:0~8.78 ng/mL),糖类抗原125(CA125):438.9 U/mL(正常范围:0~35 U/mL)。患者拒绝手术治疗,对疾病恐惧焦虑,于当地医院行常规化疗。患者化疗后身体虚弱,为求中医治疗遂来杭州市中医院。刻下:腹部胀大如鼓,皮色苍黄,脉络显露,右胁下疼痛,胃脘痞闷隐痛,善太息,偶有心慌气急,纳差,口苦,寐欠佳,大便干结、球状,偶有牙龈出血,舌质紫暗、苔黄干,脉芤。西医诊断:肝恶性肿瘤伴多发转移,肝硬化失代偿期;中医诊断:肝积,鼓胀(肝脾肾虚,血瘀阻滞)。治以健脾柔肝滋肾,活血利水。方选调营饮合六味地黄汤加减。处方:
当归10 g,川芎6 g,赤芍12 g,白芍15 g,莪术10 g,延胡索10 g,大腹皮10 g,桑白皮10 g,茯苓皮15 g,陈皮10 g,猪苓10 g,柏子仁15 g,党参15 g,生地黄15 g,甘松6 g,炒山药30 g,牡丹皮12 g,泽泻15 g,生甘草6 g,三七粉3 g(冲服)。14剂。每日1剂,水煎,分早晚温服。配合芒硝外敷腹部及双下肢。
2020年9月10日二诊:患者服药后小便量增加,双下肢水肿较前减轻,仍有胸闷气急,服药期间因感受风热,出现咳嗽咳痰,痰白而黏,微恶风寒,四肢乏力,食欲欠佳,鼻塞流涕,舌质紫暗、苔黄少津,脉芤。诊断为风热感冒,肺卫失司。治以疏风清热,宣肺固卫。方用桑菊饮合止嗽散加减,处方:桑叶10 g,菊花6 g,桔梗10 g,前胡10 g,芦根15 g,百部10 g,厚朴10 g,杏仁15 g,枇杷叶15 g,白前10 g,荆芥10 g,防风10 g,浙贝母15 g,陈皮10 g,鸡内金10 g。5剂。每日1剂,水煎,分早晚温服。
2020年9月15日三诊:患者诉诸症较前明显缓解,四肢仍有乏力,双下肢水肿明显,口淡无味,夜间盗汗明显,舌质暗紫、苔白腻,脉芤。初诊方去白芍、延胡索、生地黄、甘松、三七粉,加用生黄芪30 g、浮小麦20 g、川牛膝15 g、山萸肉15 g、白花蛇舌草15 g、鸡内金15 g,14剂。
2020年9月30日四诊:复查腹部超声提示腹水较前减少,肝内占位性病变稳定。患者双下肢水肿较前缓解,夜间下肢抽搐、腰酸腿乏,夜间仍有盗汗,间断干咳,五心烦热,舌质紫暗、苔薄黄,脉微细数。三诊方去柏子仁,加五味子6 g、女贞子30 g,14剂。
患者仍在随访,病情尚平稳。2021年4月30日肝脏MRI提示:肝癌伴肝内多发转移(与2020年7月14日影像学结果比较,病变无明显改变),腹膜及网膜多发转移,肝硬化,脾肿大,门脉高压,侧枝循环。AFP:245.79 ng/mL,CA125:349.6 U/mL。
按语:本案患者为肿瘤晚期患者,首诊时癌毒蓄积已深,走注流窜,邪盛正虚,且患者在院外常规化疗之后,正气已虚,肝脾肾三脏受伐,气血精微乏源,苦于抗癌药之攻伐,情志抑郁,故寻求中医治疗。陈师认为该患者正气虚甚,不能耐受攻伐,故将健运脾胃、固护正气贯穿于治疗始终,不以祛邪为主要目的,只有脾胃得养,五脏之气方可充养。在六味地黄汤滋补肝肾基础上,针对初诊时患者为腹水所苦,选用调营饮活血化瘀、行气利水,同时选用五皮饮利水消肿、理气健脾,以解患者燃眉之急。二诊时,患者外感风热,故先予疏风解热之剂合宣肺益气之品安内攘外,防止外感之邪引动伏毒而成燎原之势。三诊时,标急之患平息后,陈师复又着眼于病之根本,瘀血、痰饮、湿阻相互搏结之癌毒,治以扶正祛邪、攻补兼施。方中当归、川芎、赤芍、莪术活血行气以祛邪,化瘀以解走注之势;白花蛇舌草清热解毒;生黄芪、浮小麦敛汗补气;猪苓合五皮饮利水消肿;柏子仁、党参安神益气;继予六味地黄汤扶正固本。四诊时,患者肝肾阴虚化热,寐尚可,去柏子仁,加五味子合白芍酸甘养阴,女贞子滋水涵木。患者每次复诊时,陈师皆开导安慰,帮助患者正确认识病情,积极应对疾病进展,缓解患者负面情绪,稳定患者心态,疏解焦虑抑郁情绪。随访至今患者病情未见明显进展,药物治疗辅助心身治疗取得佳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