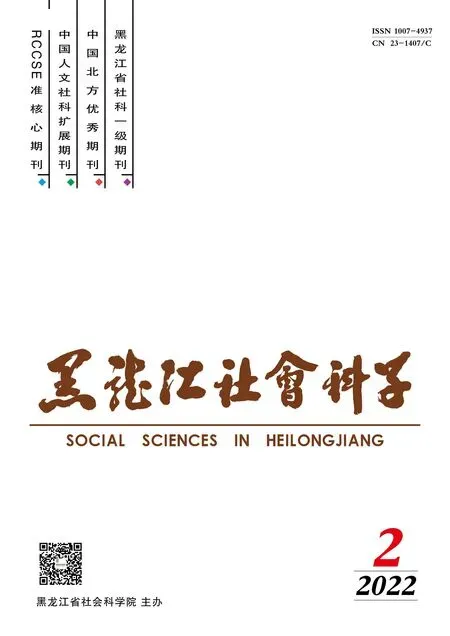论尼·巴依科夫的黑龙江流域生态写作
金 钢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哈尔滨 150028)
尼·巴依科夫全名尼古拉·阿波隆诺维奇·巴依科夫(1872—1958),又译拜阔夫、巴依阔夫、巴依柯夫、巴伊科夫、贝柯夫等。他是“20世纪初哈尔滨俄侨中最著名的作家和自然科学家”[1],其声名和作品远播日本、欧洲,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俄侨作家。巴依科夫在黑龙江流域生活了近半个世纪,亲切地称这里为自己的“第二故乡”。黑龙江流域的自然生态是他科研和创作的唯一主题,他在这里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13部文学作品。它们以黑龙江流域的自然与人类两者间的关系为探讨对象,建构了巴依科夫独立的生态伦理观,表现出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所谓黑龙江流域,即黑龙江水系所流经的区域。黑龙江是东北亚区域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也是中国第三条大河,其上、中游为今天中俄两国的界河,下游与乌苏里江汇合后进入俄罗斯境内。黑龙江水量丰沛,滋养了生活在流域里的人类和各种自然生物。黑龙江流域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相生相依的文化。本文将巴依科夫写作的地域界定为黑龙江流域,一方面因为无论是如今的“中国东北”还是曾经的“满洲”,都不能准确描述巴依科夫活动的范围,而“黑龙江流域”这一偏重地理学而不是行政区划的概念更为恰切;另一方面,巴依科夫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寻与黑龙江流域的文化内涵也是非常契合的。对大自然的关注和面对自然的人性思考,是巴依科夫创作的重要特点。黑龙江流域的自然景物与风土人情,在巴依科夫笔下得到了充分展现。
对自然生态的关注,是文学一个历史悠久的主题,“但作为具有自觉生态意识的文类,生态文学是西方新兴工业技术革命催生的新型文学产儿”[2]。巴依科夫的创作是伴随着殖民开发与铁路修建进行的,相比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逊1962年发表的影响巨大的《寂静的春天》,巴依科夫的《大王》《兽情夜》《原始森林的真理》《牝虎》等作品可以视为生态文学早期的重要文本。
一、远赴黑龙江流域的基辅人巴依科夫
巴依科夫出生在基辅附近,父亲在基辅军事法庭任法官,后来晋升为彼得堡最高军事法庭法官。巴依科夫少年时代就读于基辅军校,1892年在彼得堡第一古典中学通过考试,取得中学毕业证书后注册为圣彼得堡大学自然史学系学生,但因父亲病逝而退学,转入梯弗里斯步兵士官生学校,1894年毕业后在高加索第十六米格列尔近卫军步兵团当军官。该团团长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大公是位民俗学家,爱好野生动物,后来任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当时有一支狩猎队专门为他搜集各类动物标本,尼·巴依科夫参加了这支狩猎队,在高加索博物馆馆长Г.И.拉德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必要的生物学知识和制作标本的技术。
巴依科夫早在1887年就结识了著名的俄国自然考察家尼·米·普尔热瓦里斯基,听他讲述1867—1868年在乌苏里地区进行自然考察的情形。普尔热瓦里斯基还对年轻的巴依科夫说:“如果对自然和狩猎感兴趣,那么我建议你去远东。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样的自然,哪怕在我们的高加索和突厥斯坦也是找不到的。”[3]普尔热瓦里斯基的话打动了巴依科夫,他后来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几乎都与黑龙江流域的大自然联系在一起。
巴依科夫热烈向往黑龙江流域的神秘土地,1898年中东铁路的开建对他来说是一个好机会,他第一时间提交了申请,请求调至中东铁路护路队。经过了一番波折之后,巴依科夫于1901年2月携家属抵达哈尔滨。他被任命为中东铁路护路军(后改编为外阿穆尔军区)第三旅军械官,定居于边境站(现在的绥芬河)。他每年都在中东铁路东线,从二尖山子(现名玉泉)到边境站,两次巡视各站驻军的军械。在《1902年初到满洲》中,巴依科夫记录了他初来哈尔滨市的情景,面对了无人烟的旷野,他写道:“我看过一些资料,知道哈尔滨以东是丘陵地带,那里资源丰富,山清水秀,所以,我毫不惊慌,只是盼着列车能早点到达哈尔滨。”[4]
当时的哈尔滨车站的站房是一座长长的木刻楞房子,里面用木板隔出各种办公用的房间和候车室。1902年的哈尔滨最热闹的地方是老哈尔滨火车站附近,即便当时的后阿穆尔边防军司令部、气象站、电报局、医院这些主要部门也都还在临时搭建的土坯房里,新的办公地才准备打地基。俄侨记忆中的早期的哈尔滨,荒芜却宁静,落后而又自然。当然,在俄侨的回忆中,也无不流露出他们初到黑龙江右岸时对这一森林茂密,生长着老虎、人参地域的向往。黑龙江流域的原始森林、草原、高山等罕见而又壮美的自然风貌令他们感到震惊,未被砍伐的参天大树藤蔓缠绕,那里生活着从来未被惊吓过的野兽和鸟类。原始村落中的神话、传说及迷信更为这片土地笼罩上神秘的色彩。
巴依科夫对黑龙江流域的原始森林有着浓厚的兴趣,先后考察了镜泊湖、石头甸子、大锅盔、大秃顶子、凤凰山等地。他还在自己家里建立一个小型野生动物饲养场,同时为俄国科学院搜集大量动物标本,因此得到“通讯研究员”称号。巴依科夫还是一个出色的猎人,他带领连队的士兵先后捕获两只东北虎。其中一只是他1911年任第四连代理连长时在苇沙河(现名苇河)附近猎获的,制成标本,后来送给哈尔科夫博物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巴伊科夫于1914年奉调回国,被派往前线,在波兰、立陶宛、东普鲁士一带作战,后晋升为上校。内战时期,他参加白军,1920年携家眷取道君士坦丁堡流亡埃及,后来在北非和南亚各地流浪。1922年10月,巴依科夫回到他怀有深厚感情的黑龙江右岸。不过这时他已经不是当年中东铁路护路军的指挥官,而是个流亡者,只好在亚布力俄人林场当监工员维持生活。1924年,巴依科夫出任东省铁路管理局地亩处林务监督官,移居哈尔滨。1924—1932年,他受东省文物研究会委派,多次对当时吉林东部山区进行科学考察,其间撰写了多篇调研报告和论文。巴依科夫因研究工作成就卓著而被选为东省文物研究会终身会员。
东省铁路管理局地亩处撤销以后,巴依科夫于1928—1934年在哈尔滨铁路中学任生物教师。1930年代初,他转而从事文艺创作,写作小说和散文,署名“骑猎者”“流浪者”“眼镜”等在各种刊物上发表。1934—1943年,他在哈尔滨、天津等地出版12部作品,平均每年超过1部。长篇小说《大王》(1936)问世后获得巨大的成功,很快再版(1938)。另外还有两部长篇小说:《牝虎》(1941)和《黑大尉》(1943),其余几部皆为短篇小说和散文集。他的一些著作陆续译成其他语言,《满洲狩猎》英文版于1936年在伦敦问世,《我在满洲的狩猎活动》(即《满洲丛林里》)和《满洲的野兽和人参》的法文本先后于1938年和1939年在巴黎出版。至20 世纪40 年代以前,巴依科夫的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捷、波兰等多种语言,其中《大王》最广为人知。
二、万物有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哈尔滨为中心的黑龙江流域,无论是文化氛围还是自然环境,都与俄罗斯的远东有着诸多相似之处,而由于气温较西伯利亚森林要高,这里的山林物种更加丰富,更为色彩斑斓。普里什文曾写道:“我在哪儿都没有见过像满洲里这个地方如此辽阔的原野:这儿有森林茂密的群山,绿草如茵的山谷,那草高得足以把骑马的人隐没在里面,还有像篝火那样的大红花,像鸟儿似的飞舞的蝴蝶,以及两岸繁花似锦的清流。像这样任你自由自在地逗留在未开发的大自然中的机会,以后未必再找得到了!”[5]巴依科夫的著述绝大部分描写黑龙江右岸的大自然,从形式上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黑龙江右岸的自然考察报告和对这里动植物的研究;另一类是以这里的猎人和野生动物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和散文。作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猎人和勤奋的自然考察家,同时兼有诗人的气质和文学才华,因此这些科学论著和文艺作品之间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的自然考察报告和生物研究著作都是根据他亲自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准确而生动地描述了黑龙江流域山林中各种野生动植物的形态和习性,向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自然知识。尤其是他对目前已濒于灭绝的野生东北虎的研究,至今还保留着很高的学术价值。
巴依科夫以科学家清醒的预见性,不止一次大声疾呼,提醒人们注意保护自然环境和保持生态平衡,非常明确地提出今天尤为迫切的环保问题。巴依科夫的小说和散文与其学术著作密切相关,也以他个人在黑龙江流域山林中的亲身体验为基础,再现了黑龙江流域山林当年那种“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原始自然生态,揭示了大自然的无限诗意。他身为外国人,“侨居我国,却无限热爱这里的山山水水、茫茫林海和飞禽走兽,绘制出五彩缤纷的大自然的美丽画卷,满怀深情地描写了山林中各族居民的生活和劳动,鲜明生动地刻画了各种走山人——猎人、淘金者、采参人、捞珠者的形象”[6]。
巴依科夫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首推《大王》。《大王》共有33章,书中有作者亲笔绘制的各种动物的插图。这部小说全面体现了巴依科夫对自然界的考察成果和文学艺术成就,是他的代表作。在作品中,“大王”是那个年代活跃在黑龙江流域的一只老虎,在它宽阔而又平坦的前额上清清楚楚地显示出一个“王”字,而它后脑勺蓬松的鬣毛则显示出一个“大”字,它是群山和无边无际林海的统治者。《大王》追随虎大王的活动轨迹,将小兴安岭、长白山、张广才岭等崇山峻岭的景色充分展现给读者。阿穆尔虎、满洲虎、野猪、黑熊、鸱枭、松鸭、山鹰、蜜蜂、萤火虫、稠李树、雪松、榛子树等动植物,作者写起来如数家珍,可以说《大王》是黑龙江流域大自然的“百兽图、百鸟图、百木图”[7]。
在《大王》中,不仅人类是有思想、会说话的,动物、植物,甚至整个原始森林都是生机勃勃的有思想的活体。暗夜雪松林边飞过的鸱枭发出凄凉的叫声:“谁——啊?”多嘴的喜鹊看到虎大王在猎食黑熊,就唠叨起来没完:“真是苍天有眼!去年你吞吃了我的小鸟,现在你自己要给咱们的大王当点心啦!”[8]55每种动物都是有灵性的,都是平等的。年轻的虎大王在观察黑貂捕猎松鼠时发现,那小小的黑貂是同自己一样“不知疲倦、完美无缺的猛兽”[8]40,而且它能够在最高的树木枝头飞驰,这是虎大王做不到的。小说的开头部分写虎大王的母亲生养子女的过程,与人类没有什么差别,充满了母亲的机警与柔情。
《大王》中还重点塑造了老猎人佟力的形象,他既是一位优秀的猎人,又是森林里的医生和巫师,拥有强大的意志力。在与虎大王狭路相逢的时候,他还能保持镇定地向前走,迫使虎大王给他让了路。这在虎大王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产生了一种对人的敬意。但这种敬意也只限于对佟力一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老猎人佟力与虎大王一样,都是原始森林法则的遵守者和执行者。虎大王对用陷阱害死它伴侣的猎人李三以及偷盗者孙发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行使原始森林的法则。而在小说的结尾,佟力遵从原始森林的法则,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献祭给虎大王,以平息老虎们的愤怒,然而虎大王已经在外来捕猎者的枪下受了重伤,最终死在山巅的巨石上。
黑龙江流域这片广袤的原始森林“有着自己的历史,自己独特的生活,自己的习俗,自己的法则和自己的同远古传说相联系的故事”[8]36。这片森林是一个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动植物和这里的山民共同生活在这个系统中,他们具有统一的生活准则,这使得动植物和人类能够彼此理解,和谐地生存下去。这里展现出来的是原生大自然的雄伟而绝妙的美。但是,随着中东铁路的贯通和外来移民的迁入,这片原始森林的面积逐渐缩小,野生动物便退到密林深处,躲避铁路线和新建的村落,希望在人迹未至的森林角落寻求安宁。然而,它们的退让更加助长了人类的贪婪,这片土地上几千年来的和谐平静终究还是被打破了。
三、殖民开发:人与自然相互伤害
一百多年前,白山黑水之间的广袤山林丝毫没有受到人为的破坏,而保持着纯粹原始的自然生态。中东铁路整个东段,从玉泉直到绥芬河,都是穿越原始森林而敷设的。巴依科夫当年一来到这里就深深地爱上了壮美的山林。与此同时,他也亲眼目睹了铁路营运以后沙俄以及其他外国资本对黑龙江流域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当年由外商把持的我国东北三大外贸出口物资中有两种直接取自森林,即黑龙江流域特有的红松木材和野生动物毛皮。对大自然的严重破坏,当时被认为是“进步”,可对巴伊科夫这样一位有远见的科学家和作家来说,这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他热爱大自然,痛切地感受到中东铁路的修建对黑龙江流域原始森林的严重威胁,并且预见到不可避免的悲剧前景。
对原始自然生态的保护与殖民开发这一矛盾的思考是巴依科夫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在《牝虎》中,巴依科夫严厉斥责了一些殖民者为了采松子而伐倒巨大松树的可耻行为,作者借猎人巴保新之口说道:“你瞧瞧这美景!这不是造物者的伟大吗?……为什么劳作于工厂的人们都不信神?他们从来未见过天国的美丽,他们知道的仅有污秽瘪小的工房与烟气弥漫的工厂。密林的住民,虽然不过是些箪食瓢饮的简陋百姓,但是他们离‘自然’和‘神’很近,因此他们的精神是纯洁的,头脑决不污浊。”[9]这里将殖民者和殖民开发的工人与原始森林里的居民对立起来,表达了对自然神性的赞颂和对工业技术文明的批判。
在《大王》中,巴依科夫以虎大王的视角看待原始森林发生的变化:殖民开发者在深山老林里修起了铁路,砍伐掉了虎大王家乡的树木,烧毁了大片的森林。这些都引起了猛兽不可抑制的敌意,千百年来,猛虎都是这片原始森林的王者,而随着殖民开发者的到来,这里的食物链和生态平衡都被打破了。大片郁郁苍苍的森林被冒着浓烟的厂房占据,原来茂密的森林里只有各种生物的交响乐,而由于铁路的修建,取而代之的是火车的隆隆声、尖利的汽笛声、刺耳的锯木声、蒸汽锅炉的轰鸣声,以往虎大王那震撼山林的吼声被这些工业机械的响声压下去了。巴依科夫直言不讳地指出人是“世上一切生物的最可怕的大敌”,“像暴君一般无情”[8]87-88。而虎大王完美的、强健的肉体终究还是敌不过新式猎枪,巴依科夫以大王之死表达了对殖民开发行为的焦虑与质疑,体现出强烈的自然主义意识。
相对于大自然的神奇与壮美,巴依科夫认为殖民开发者是愚蠢而又丑陋的,他用“柔弱的躯体”“小盒子般的住房”等词语描写人,表现出作者的主观倾向性。在读到森林被烧毁、参天大树在无情的斧子下倒下、绿色丛林被住房和铁路所替代时,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仿佛呻吟和痛哭的不是原始森林,而是作者本人。不过,巴依科夫不仅是为原始森林的命运悲叹,他更是在为人类未来的命运忧虑。事实也正像作者所预言的那样,野兽们为了觅食,为了生存,开始了与人类生存地盘和生存权利的争夺。开始的时候,一些野兽因无处觅食,只是猎捕村子里的家畜和狗。逐渐地这些家畜也不能填饱它们的肚子了,它们开始进攻人类,先是成年野猪,紧接着便是老虎的跟踪而至,这使得当地居民极为恐慌。巴依科夫在描写野兽与人类的争夺中,用不少的篇章和笔墨描写动物对人类的敌意与愤恨,从而进一步表达了他对殖民开发者破坏原始森林的尖锐批判,并且推断出害兽必将害己、人类终究会自食其果这样一个朴素的哲理。
在《大王》中,人类想出诸多狠辣的办法对付野兽。他们将宰杀的马肉里塞上毒药,放在老虎经常经过的地方,结果不仅毒死了红狼,还有别的走兽和飞禽,而中了毒的野兽又被一些不明所以的人吃了,引发进一步扩散。野兽们因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更加频繁地进攻人类。这种互相伤害让人想起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卡逊认为,“地球生命的历史是一部各种生命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地球植物和动物的形态与习性都是由环境造就的。就地球的全部时间而论,生物对周围环境的反作用却相对很小。随着时间的推进,尤其是到20世纪,人类获得了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10]。这种力量过于强大了,可能会对自然环境产生不可逆转的破坏。只是人类对此还没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比如核爆炸向空气中释放出的锶,或随雨水进入土壤,或以放射性尘埃形式落在地表,进而被草、玉米或小麦吸收,最终进驻人类的骨骼中直至其死亡。同理,农田、森林以及花园里喷洒的农药会在土壤中长存,接着进入生物体内,在中毒和死亡的链条中不断地传递下去。它也可以随着地下水神秘地转移,通过空气与阳光的作用再次出现,并生成新的物质,毁坏植被,使动物生病,让曾经可以饮用纯净地下水的人们遭受离奇的伤害。
《大王》中所描写的人毒害动物、终归又自食恶果,所反映出的问题让人深思。地球上各种生物的演化是非常漫长的,经过了几百万年。在漫长的时间里,地球生物发展进化,物种逐渐增加,慢慢与周围环境达到了一种协调平衡的状态。自然环境极大地影响着生物的形态,指引生物的演进方向,包含了各种有利的和不利的因素。一些岩石会有危险的辐射;甚至为万物提供能量的阳光中,也有可以造成伤害的短波辐射。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是几年,而是上千年时间,生物慢慢得到进化,与自然环境达成平衡。所以,时间是一个最基本的要素,但是现代社会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时间。人类过于迅猛的发展脚步,到头来的结果可能只是欲速而不达。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黑龙江流域,工业化的发展还只是起步阶段,没有达到严重破坏生态平衡的程度,当时关注生态环境的人并不多。然而,如今当我们重读巴依科夫作品的时候,不能不敬佩他超前的自然生态意识。另外,作者在反思人类文明的进程的同时,也对殖民开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意味深远:“大王明白了,某种新的不可抑制的力量在往前推进,摧毁路上的一切。”[8]120这股新力量固然可贵,但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那这股力量很可能会在摧毁原始生态的同时,摧毁这力量的掌握者——现代人自己。黑龙江流域的森林资源十分丰富,而自中东铁路修建以来,铁路所需的枕木、用做机车燃料的木料、修造船只和架设桥梁所用的木材,以至铁路员工盖房和烧火用的柴薪等,都取自铁路经过的黑龙江流域的森林。中东铁路公司对森林的滥砍滥伐,给黑龙江流域的森林资源与生态平衡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种破坏所造成的创伤恐怕在几百年之内都难以恢复。
四、天人合一与生命救赎
在人类文明的开端,大自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当人类文明越来越发达,人的身体和心灵却离大自然越来越远。人们大多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很少去感受大自然的壮丽景观。人的力量已经太强大了,强大到藐视自然。人类滥用科技对自然界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为回应,大自然也不再以广阔的胸怀包容我们。但是,人类毕竟是从自然襁褓中走出的孩子,与母亲的联系难以割舍,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个现代人的心里,都有一份回归自然、重返天真的情结。
巴依科夫的创作既表现出俄罗斯文学的生命救赎意识,又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之后,生态危机便逐渐演化为全球性的问题。俄罗斯地广人稀,气候寒冷,经济开发相对困难,这些可能都是很多俄罗斯作家一直没有放弃对大自然万物有灵信仰的原因。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在俄罗斯民族灵魂中还保持着强有力的、与俄罗斯大地的神秘性和俄罗斯原野的广袤性相联系的自然的元素。在俄罗斯人的‘天性’中,自发的原始力量,较之西方人,尤其是受拉丁文化影响成长起来的人们,更为有力。天然的异教因素也进入到俄罗斯式基督教之中。”[11]在俄罗斯文学中,大自然一直是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对于俄罗斯文学来说,大自然是“物质”的,为人类生存提供保障;但更是“精神”的:大自然—宇宙、大自然—历史、大自然—家乡、大自然—母亲的主题在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特别活跃,俄罗斯文学家们在自己的作品里向我们传达着由大自然所启迪的美和哲理。
自然对于俄罗斯文学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巴乌斯托夫斯基这样说:“一个不热爱、熟悉,不了解大自然的作家,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不够格的作家。”[12]俄罗斯文学有着强大的人道主义传统,精神道德探索、社会伦理思考是俄罗斯经典文学的恒常主题。在这一方面,大自然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自然是检验人性的标准。从一个人如何对待大自然,可以判断他如何对待他人,可以推知他的精神世界是美是丑。这足以佐证俄罗斯文学与大自然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在巴依科夫看来,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是人类获取幸福的家园。为此,他在作品中不断地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构问题,并对破坏自然生态的行为进行了直接而又尖锐的批判。
巴依科夫在黑龙江流域生活了几十年,黑龙江流域的水土养育了他,中国传统文化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在他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他的小说中既有对黑龙江流域动植物的广泛描写,还有对当地居民生活、民间传说、民间信仰的展现。比如森林里的居民害怕得罪山神,从来不用“老虎”这个词,而是称“大王”,或者“大—老—子”。通过对一些俄罗斯殖民者交谈的描写,巴依科夫也表达了对当地文化的崇敬:“怪不得中国人要拜它为神!就像我们尊奉圣徒尼古拉那样,他们尊奉虎大王!看来这就是规矩!”[8]123
巴依科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仅仅表现于这些表层的看得见的现象,他的小说中蕴含着对中国文化更深一步的理解,融汇了他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佛教的灵魂转世说的认识。《大王》中的老虎不仅是猛兽,还是人性化的,更被披上了“天人合一”的灵光:“据民间传说,一位伟人的灵魂,经轮回投胎,转世为大王;大王一死,灵魂又转世为一朵凡人肉眼看不到的黄色莲花。灵魂在这朵莲花之中达到彻底的净化,并同宇宙之灵融为一体。”[8]32可以看出,小说中的老虎成了人、动物、自然和宇宙的统一体。巴依科夫通过灵魂转世与“天人合一”的观点将人和自然紧密地联系起来,人、动物、自然在互相转化中互相依赖,缺一不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东北也曾有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创作,不过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他们更多反映的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社会主题,难以脱离开民族矛盾和社会斗争去孤立地描写大自然。如今,从长白山到大小兴安岭,纯粹的原始森林已所剩无几,很多珍贵的野生动物种群已濒临灭绝。如果想要回忆往昔的神奇大森林,可能只有到巴依科夫的作品中去寻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巴依科夫为我们填补了文学史的一块空白。尤其在追求科学发展、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今天,巴依科夫作品的意义就显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