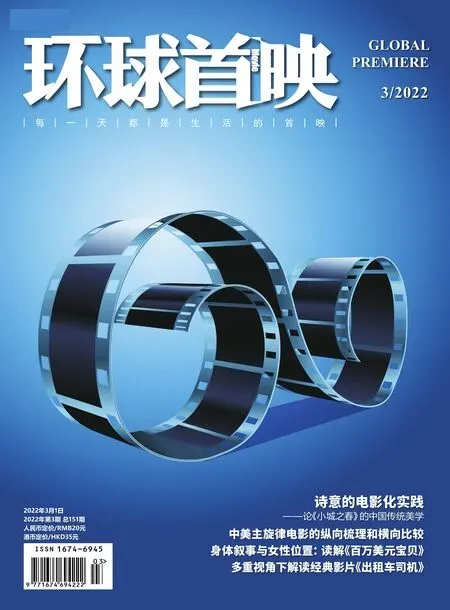他者的建构
——从女性主义视角看电影《最后的决斗》
张艳丽 山东艺术学院
雷德利·斯科特作为一个“高产”的英国导演,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尝试了科幻、悬疑、战争、历史等多种题材,致力于达成商业与艺术之间的平衡。在他的电影中,如《异形》《末路狂花》等都有着明显的女性主义思想的流露,所塑造的女性角色往往兼具智慧、勇敢、善良等品质,这在《最后的决斗》中也有同样体现。本片根据艾瑞克·雅克参考中世纪法国最后一次司法决斗所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围绕骑士尚·德·卡鲁日的妻子玛格丽特指控乡绅贾克·勒·格里斯强奸自己的案件所引发的决斗展开情节内容,分别从三位主人公的视角出发讲述他们口中各自的真相。雷德利·斯科特以其精湛的影像,形象地呈现了中世纪法国宗教、政治、法律等面貌,鲜明地凸显出了父权社会下的女性的“他者”形象。本文将从多视角叙事及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思想两部分来论述《最后的决斗》这部影片中的女性意识的表达。
一、多视角下的女性叙事表达
(一)叙事无诡计
影片分三个章节进行叙事,即尚·德·卡鲁日口中的真相、贾克·勒·格里斯口中的真相以及玛格丽特夫人口中的真相。导演以三位当事人的视角分别讲述各自口中的真相以还原完整事件本身的情节安排无疑是种较为突出的叙事方式,这让人难免想到著名的《罗生门》的叙事,但它又与之不同。电影《罗生门》虽然也是通过盗贼、武士的妻子及武士的亡魂三位当事人来分别讲述事件真相,但每个人都为了减轻自身罪恶、维护自身形象,而将事件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进行虚构,因此三者口中的事实大相径庭,真相也变得扑朔迷离。而《最后的决斗》中,无论是尚·德·卡鲁日还是贾克·勒·格里斯抑或是玛格丽特,三者虽然都是从自身视角出发讲述发生过的事,但却并不存在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刻意虚构故事内容,或为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多作辩护。影片中的三个故事交代的是同一事件,发生过的事情三者都未否认,且大致内容基本吻合,导演仅仅对各自视角下的故事进行了细节补充。这种当事人未掺杂任何个人“诡计”的陈述事件的手法,似罗生门而非罗生门,且三个视角下的故事使得整部影片的故事更加客观完整,尤其是女性视角的叙事部分,突出了故事所围绕的强奸案件的女性受害者的个人 体验。
(二)女性即真相
由于主体差异性的存在,不同主体对待同一事件的记忆总有偏差,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因此,在电影《最后的决斗》中,虽然每位主角都在讲述自己亲身经历过程,并尤为确信的事实,且三者彼此所述事实之间也出入甚小,但正是这些细微的差异,折射出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以尚·德·卡鲁日与贾克·勒·格里斯共同参加的战役为例,在前者的记忆中,自己率先冲出杀敌,并且救下了贾克·勒·格里斯;但是在后者的记忆中,由于卡鲁日的鲁莽,造成了战争的被动局面,他还要救落马的卡鲁日。这便是主体记忆重点的偏差,虽然客观事件基本一致,但两人都有选择性地忽略了自己被人救下的情节,且强调了自己对彼方的恩赐。视角主体不同,不仅使记忆内容有偏差,在感知与描述事件方面也会有所差别。在尚·德·卡鲁日让妻子玛格丽特亲吻贾克·勒·格里斯以向其表示友好时,在贾克·勒·格里斯的记忆中,两个人都非常享受这一吻。且他认为,聚会时两人的交谈、跳舞时玛格丽特望向自己的目光是对自己的示好,尤其是在他闯入玛格丽特家中,追赶她的过程中掉落的鞋子也是她为挑逗自己而为之,那一声声“NO”更是对自己欲迎还拒的表现。这些记忆内容虽然真实发生过,但是在玛格丽特看来,亲吻不过是在丈夫要求下的勉强一吻,其后的交谈是礼貌回应,跳舞的眼神乃是自己在讨好丈夫时的偶然一撇,鞋子是自己慌乱之下掉落的,“NO”更是表示拒绝之意。因此,《最后的决斗》中虽然讲述了大体一致的故事内容,但三位当事人在以自己的视角看待事实时存在的差别,就使得每一视角的叙事都尤为关键。
电影的故事所围绕的强奸案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因此,分视角叙事的情节布局,使得这一事件不再仅仅是历史书上的寥寥数语,也不再是按照故事逻辑所进行的影像版的故事简述,而是为观众鲜活地呈现了故事主人公们的真实感知历程,尤其是以强奸案件中的受害者玛格丽特的视角进行的叙事,增加了对女性体验的关注。电影《最后的决斗》的编剧团队由本·阿弗莱克、马特·达蒙、妮可·哈罗芬瑟三人组成,三人将原本可以拍摄为史诗类型的电影改编为了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品,通过电影的表达为史料记载中所缺失的玛格丽特的发声提供了机会。在银幕上闪过“玛格丽特口中的真相后”所停留的“the truth”字眼,更是为此部影片明确了立场,表达了对玛格丽特视角下所论述事实乃真相的认同,增强了观众对玛格丽特遭遇的共鸣。
二、电影的女性主义思想表现
(一)女性主义思想内容
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3次浪潮。从第一阶段的女性要求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发展为第二阶段的妇女解放运动,促进女性意识觉醒的同时,追求男女在各领域的平等;在如今仍继续着的第三阶段女性主义浪潮下,女性更为注重自身需求和生存空间,主张超越男女性别差异。女性主义的三次浪潮,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全人类范围内的男女平等,即“要让女性恢复原来的地位,也要让她们重新伸张被压抑的人性”[1]。但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是由于女性受压迫、被歧视的问题由来已久。传统父权文化统治下,女性一直被塑造为男性的附属品,处于“他者”的困境中。在波伏娃看来,女性不是根据其本身,而是根据男性来定义并形成自我的,即“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2]。在这样的处境下,女性在社会群体中逐渐被“稳固”在被动、消极的一方。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对造成男、女两性地位差异的根源进行了探讨,她认为自古以来,女性“他者”的被动地位,是由外在的社会文化因素所造成,而非内在的生理差异。这一理论与她的存在主义思想有关,波伏娃受萨特“存在先于本质”理论的影响,认为人与物的根本区别在于,物在生产出来前就被规定好了形状、用途等本质,但人是先存在于世,其本质的生成要在生命结束时才算最终完成。女性作为与男性一样的“人”存活于世,长期生活在由男性主导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她们对自身和外界的认知、言语的表达乃至思考的方式皆来自男性文化,即男性文化塑造了女性“气质”。同时,波伏娃认为女性只有从“他者”转变为“此者”,才可能真正改变自身的被动地位,赢得独立的人格和自由选择的权利。但这一转变的达成除了受时代因素的制约,还受到女性自身选择的影响。
(二)电影中的女性主义思想体现
电影《最后的决斗》中的女性在传统父权意识形态下,作为男性的服从者存在,无法掌控自己命运,以“他者”形象示人。尚·德·卡鲁日在与玛格丽特举行婚礼的现场发现嫁妆中少了一块地之后,大发雷霆。随后他对玛格丽特父亲表示自己赐予了他们尊贵的姓氏,希望玛格丽特有能力执行妻子的义务,怀上继承人,玛格丽特的父亲随即表示:“小女身强体健,已准备好实践婚姻义务,继承人与孩子随即就会诞生,而且多产”。这一对话的出现,无疑是对玛格丽特婚姻本质的揭露,父亲将她嫁给尚·德·卡鲁日是看上了对方的家族名望,卡鲁日娶她是看上了她所能带来的丰厚嫁妆,以及希望她能为自己繁衍子嗣。无论是父亲还是丈夫,都只将玛格丽特视为达成自己目的的工具。婚后的玛格丽特在丈夫不在时,将收租、记账、耕种等事物打理得井井有条,但依然遭到婆婆“结不出果实”的讽刺,怀孕生子被当作衡量一个妻子好坏的标准,而不是玛格丽特作为个体的表现。在玛格丽特穿着新衣迎接归来的丈夫时,本是为讨好丈夫,却因为领口太低而遭受丈夫的言语攻击,这也表明了婚姻中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永远作为配角依附于男性生活。男性不仅在婚姻中占据主导,在两性关系、法律等方面亦是。贾克·勒·格里斯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与玛格丽特是“两情相悦”,而并非强奸,并在强奸她后威胁她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的丈夫听到这件事,可能会杀了你”。在两个人为数不多的交集中,贾克·勒·格里斯的“自认为是”凸显了他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导”性思维,以其丈夫来威胁她,也是认定了女性皆惧怕丈夫。在玛格丽特鼓起勇气告知尚·德·卡鲁日自己被强奸的事实后,他的愤怒与看到那匹普通黑马想要与具有战马血统的母马交配时所产生的狂躁心理是一致的,都是由于自己的财产受到侵犯而产生的情绪反应。尚·德·卡鲁日由起初对妻子的怀疑到最终答应可在法律上支持她,并非是出于丈夫对妻子的疼惜与尊重,而是为了夺回自己的尊严与脸面。虽然最后的决斗胜利了,众人纷纷为尚·德·卡鲁日欢呼,却无人关心玛格丽特作为真正受害者的心理状态。玛格丽特的境遇作为这一时代女性生存状态的缩影,其存在一直被搁置于社会之次要层面,如同影片结尾处的那一声叹息,在人群的欢呼中失声。
不同的女性在面对传统父权文化环境对自身的“塑造”时,所做的选择也不同。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认为“他者”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受男性压迫,失去自由和自我的女性,另一种是满足于被压迫的现状,放弃追求自我的女性”[3]。在《最后的决斗》中,玛格丽特的表现倾向于第一种类型,她受到父权制文化的影响,全身心地投入到“他者”的角色中,努力成为一个好妻子,服从丈夫安排,操劳家庭事务,努力孕育子嗣。在劝新婚好友买新衣时,她道:“让你的新婚丈夫惊喜一下”,这就说明了在她的观念中,穿衣打扮的目的是为了讨好丈夫,并非是出于自身喜好。而其好友、婆婆等女性,虽然与玛格丽特同样作为男性的附属物存在,但她们已经将父权思想不断内化并强化为自觉意识,从而满足于此种状态,这即是波伏娃所讲的第二种类型,也进入了萨特口中的“自欺”。萨特认为,“人的存在不仅仅是否定由之在世界上表现出来的存在,也是能针对自我采取否定态度的存在”[4],即人通过否定自己以符合外界赋予的身份特征,陷入“自欺”的女性便是如此。她们长期沉溺于男性营造的稳固环境中,通过否定自身来满足父权社会对自己的“期待”,逃避人在自由选择中创造自己本质的这一责任。这时的女性便成了男性的同盟,对于同性之中的“异类”,即不符合父权文化要求的女性,报以极大地敌意。回到电影本身,在得知玛格丽特被强奸后,好友以及婆婆非但没有表现出同情与关心,反而对其表示怀疑与斥责。玛格丽特的好友主动向法庭提交了她曾对贾克·勒·格里斯评价过“他的外表倒是难以忽视”,以此作为她撒谎的证据,但却完全忽略了她后来所说的“他很粗野,也很无礼”。玛格丽特的婆婆认为玛格丽特的发声只会为她们家族带来耻辱,她坦言自己也曾遭遇过强暴,但自己未曾向丈夫哭诉,而是自己站了起来。在她的世界观中,不能为丈夫添麻烦,凡是可能对家族名誉有损的事都应该保持缄默,这才是正确的事情。这也就说明了玛格丽特的婆婆和其好友一样,在父权文化的影响下,她们皆把玛格丽特当作了“异类”而站在了其对立面。这也说明,玛格丽特的“我不能保持沉默,我必须发声”的态度,是其对父权文化制度下女性被压迫状态的抗争,她勇敢地做出了与身边女性所不同的选择。她的智慧与勇敢,带有雷德利·斯科特电影中女性角色的典型特征。雷德利·斯科特的电影《异形》中的女性,不同于以往科幻电影中女性的柔弱形象,由男性的辅助性配角“转正”,承担与男性同等的工作,且具备聪慧、善良、勇敢、有能力等众多优秀品质;在《末路狂花》中,路易斯开枪杀死强奸塞尔玛的男人后,两人踏上了逃亡之路,塞尔玛在这个过程中由一个懦弱的家庭主妇,转变为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独立女性,摆脱了父权文化的束缚,决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女性成长主题在《最后的决斗》中也得到了体现。玛格丽特被强奸后,转变了以往的柔弱形象,勇敢地向丈夫、世人说出真相。尤其是在她得知丈夫隐瞒决斗的后果后,对丈夫的失望使她开始真正清醒,不仅不再对丈夫言听计从,而且直接撕下了丈夫虚伪的面纱,斥责他是个为了自己的面子不惜拿她与孩子的生命冒险的伪君子。此时的玛格丽特从“他者”的处境中挣脱出来,有了清晰的自我意识。
三、结语
在《最后的决斗》中,雷德利·斯科特导演依然保持了对女性群体的关注。虽然这部电影是历史题材,但不论是其女性叙事视角的加持还是影片中所凸显的父权文化下女性被建构的“他者”形象,都为女性主义电影增添了力量。就电影的女性表达而言,相比于雷德利·斯科特之前所创作的《末路狂花》,这部《最后的决斗》缺乏了对女性心理体验的挖掘,且为迎合女性受众以及奥斯卡奖项的偏好而有意凸显的女性叙事即真相的视角,成了此部作品为外界所诟病之处,这也为女性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