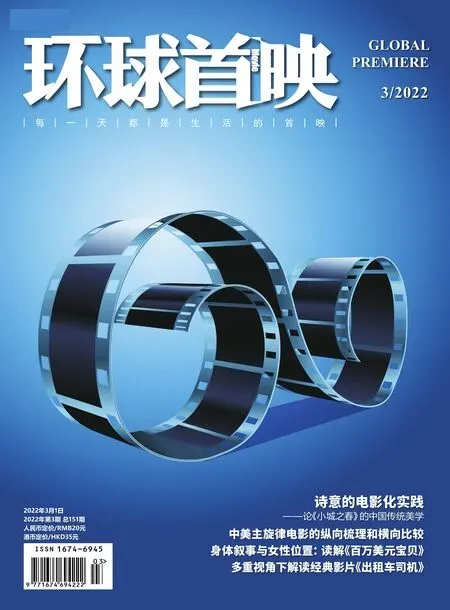多重视角下解读经典影片《出租车司机》
陈韵馨 中国传媒大学
一部电影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什么,影片的意义更多的是通过与批判理论的相互作用来决定的。作为展现美国70年代社会风貌的代表作,影片经过时代的洗礼,当代的我们通过运用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审视,从而尽可能展现一部影片最为丰富的内涵与意义。
一、影片的类型特色
影片《出租车司机》并不是一部典型的类型片,我们无法轻易地将其归入任何一种类型片中。外国学者曾这样评论这部电影:“它把西部片中常见的孤胆英雄,暴力手段和标准的复仇情节移植到纽约的街区。因此不少影评家将影片称为‘马路西部片’”[1]。影片中也存在着不少犯罪元素,但我们也不能轻易将其归纳为犯罪片。若从类型杂糅的视角来看,各个元素相对来说较为细微,影片更为关注对主人公心路历程以及对于社会现状的刻画。因此,试图用更为宽广的类型片视野来看待影片的类型,影片是极具美国四五十年代黑色电影风格的。
(一)主人公的人物设置
黑色电影的主人公往往是道德上具有双重人格、对周围世界充满敌意、失望孤独、最后在死亡中找到归宿的叛逆人物。《出租车司机》的主人公特拉维斯整个的心理与行动相当符合黑色电影的主人公设置。从越战退伍后始终被战争阴影笼罩,夜不能寐,也找不到生活的方向。当应聘成为出租车司机那一刻起,他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了纽约街头,“晚上什么人都有,妓女、下三烂、小偷、女王、仙女、毒虫、毒贩、变态、怪物”。不同于白天的光鲜亮丽,夜晚的纽约暴露出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而这些恰恰也是特拉维斯所不能忍受的。在搭载到总统候选人时特拉维斯这么说,“因为这个城市像开放式下水道,到处是垃圾跟人渣,我觉得我快受不了了,当选总统的人应该好好加以整顿”“我想总统应该好好处理这个问题,把所有垃圾冲进马桶里”。通过特拉维斯的自述,我们感受到了特拉维斯对这个世界的不满与敌意。其实在一开始,特拉维斯是渴望去融入这个社会的,即使夜晚的种种令他感到失望,他依然在日记中是这样写道:“日子一天天地过,像是没有终点,我一直都需要找个地方去,我不相信人该过着自闭的生活,我相信人就该融入社会。”然而当他主动踏出自己的小世界,与他认为的“天使”贝茜建立关系时,现实的阶级分层让他感受到了这个社会的病态已经无药可救。这时他的孤独寂寞更加无处排解。“在我的一生中,寂寞对我如影随形,无论是在酒吧、车上、人行道、商店,紧追不舍,我无处可逃,我是个寂寞的人。”“一成不变地度过每一天,每天都一样,挣脱不了的锁链。”他渴望去追求改变,极端的心态促使他走向使用暴力的手段,他在暴力中找寻自我存在的意义。他对着镜子自言自语,试图寻找那个能够与他对话的人。“这个人再也无法忍受,他要站起来对抗人渣、变态、走狗废物,这个人要站起来”。在刺杀总统的计划失败后,特拉维斯在血洗妓院中感受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完成了他心中的救赎也救赎了自己,实现了自己的“光荣死亡”。
(二)影片中的意象设置
黑色电影“对于水有一种近乎弗洛伊德式的依恋”[2],影片中也充满着水的意象。在影片的开场,我们就看到了特拉维斯眼中雨刮器下的纽约街头,灯红酒绿又带着一种迷幻的不真实感,奠定了水这个意象在影片中的重要作用。特拉维斯曾经说过“有时候下一场雨,能让这些人渣从街头消失”。似乎只有雨这样自然纯净的东西才能洗去纽约街头顽固的罪恶。在搭载嫖客与妓女时,出租车曾经过一个冲天的水柱,这是将特拉维斯想法具象化呈现,然而我们看到现实是特拉维斯必须关上窗户,避开这本可洗刷罪恶的水。水在影片中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水能够冲刷罪恶;另一方面,雨水冲刷过后会产生失焦的状态,也代表着当时动荡混乱的社会。
二、影片的叙事架构
观众最直观理解电影的方式是通过影片的叙事。《出租车司机》作为一部经典的新好莱坞电影,充满了新好莱坞电影的特色,以一种介于好莱坞经典叙事与艺术电影的创新审视之间的斯科塞斯式叙事手法。
(一)影片的线性结构叙事
影片《出租车司机》从出租车司机特拉维斯视角出发,讲述了他目睹了纽约的空虚堕落,试图寻找自己的自我价值最后戏剧性地成了社会英雄的故事。影片以线性结构叙事,在叙事过程中弱化了情节之间的因果关系,以事件堆积引起人物心理变化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电影制片厂时代的经典好莱坞电影将角色作为统一故事的主要原因,并构建线性情节来重申这一点。线性情节确定了故事的语法,将其按顺序组织在四个节点上——“未受干扰的阶段、干扰、斗争和干扰的消除”[3]。《出租车司机》在大结构上沿用了经典好莱坞的叙事语法,影片中雏妓的几次出现都是线性结构发展的节点。影片前30分钟建立了一个主人公未受干扰的阶段,那个时期退伍后饱受失眠困扰的特拉维斯拥有了一段还算稳定的新生活,开着夜间出租车赚外快,去色情电影院看电影消磨时光,也与自己的女神有了进一步的进展。在这一阶段,着重描绘了特拉维斯的生活状态,通过他的言行举止塑造了他孤独怪异的人物形象,并通过他的对话与独白展现了他内心的困惑孤独。30分钟之后雏妓第一次出现,预示着影片进入下一个阶段——干扰出现。影片通过简短的十分钟完成了特拉维斯的心理转变,这一阶段中只通过一次约会清晰地展现了贝茜所代表的上层阶级主流社会与特拉维斯所在的中低层阶级的格格不入,贝茜拥有两份高雅的唱片,而特拉维斯只能拥有一辆出租车,极具讽刺意味。这直接导致特拉维斯了解到阶级之间的鸿沟,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无法消除,而之后的多次电话更是直接将特拉维斯推进深渊。来到办公室的对峙是特拉维斯的一次情感爆发,直白地通过台词表达了特拉维斯当时的心理,“现在我知道她和其他人有多像,冷漠又疏离,好多人都是那样,特别是女人,她们都一样”。与准备枪杀出轨老婆的男乘客的对话坚定了特拉维斯转变去抗争的念头,影片也正式进入斗争阶段,特拉维斯开始主动地去寻找自我价值。导演由外而内地展现了特拉维斯是如何斗争的,从对自己的外部改造,买枪锻炼身体,整修装备;到通过观看电视内容时的内在心理变化以及产生拯救初级的念头,把特拉维斯逐步塑造了一个单枪匹马拯救世界的孤胆英雄形象。在最终干扰消除的阶段是相当戏剧性的,在干扰和斗争阶段,导演都极力烘托特拉维斯将通过刺杀总统候选人帕兰汀来证明自我价值,如果将这作为干扰消除,显然特拉维斯是必然失败的。但如果将特拉维斯的自我价值证明,自我心态改造作为最终干扰的消除,特拉维斯则是成功的。这不仅仅体现在其经历血战后戏剧性地成了社会的英雄,更体现在他最后对于贝茜看清释怀的态度,当特拉维斯选择礼貌地与贝茜“再见”的那刻,观众也了解到了特拉维斯的变化,无论特拉维斯最后选择和他人一样冷漠还是回归自己的小世界,他都获得了解脱。
(二)影片的好莱坞经典叙事
大卫波德维尔指出好莱坞经典叙事安排两条情节线进一步使线性发展复杂化,一条感情线,一条行动线[4]。《出租车司机》大体符合这一好莱坞经典叙事,也安排了两条情节线,由影片中的两个重要女性角色串联起来。影片中的感情线非常简单,发生于特拉维斯与贝茜之间。特拉维斯对在竞选办公室工作的白领丽人贝茜心生爱慕,主动追求,拉近两人距离,在一次约会过程中发现了两人思想上无法逾越的鸿沟,看清了贝茜的冷漠疏离,两人关系就此破裂。两人的情感建立在特拉维斯的一个美好的幻象之上,幻象的破灭也意味着情感的结束。与其将特拉维斯的转变看作对于情感的一种复仇,此处更倾向于是对于社会的一次抗争。在影片前三分之一,感情线这条情节线基本就已经结束。与好莱坞经典叙事不同两条情节线相互交织不同,《出租车司机》中更多的是两条情节线顺接。在行动线方面,在影片的前半小时,特拉维斯是麻木毫无目的地生活着的,贝茜是他跳脱这种孤寂生活的一个希望。在希望破灭之后,特拉维斯才主动开始了自我价值找寻的行动。影片的行动线是相对复杂的,整体来看特拉维斯是寻找一种自我认同的行动线,而这自我认同并不能够通过一个简单的行动线完成。贝茜在完成了感情线的功能之后,还代表着一种当时的政治表达,而这种“伪善”的社会现状正是特拉维斯要去抗争的。这也是特拉维斯的显性行动线,他的一系列外在转变都是为了他刺杀总统抗争社会而服务的。这样的行动线的设置本身就代表着结局会以失败告终。因此导演在此行动线外附加了另一条隐性的行动线,由雏妓艾瑞丝引出。特拉维斯曾意外撞见试图逃跑的雏妓艾瑞丝,这一小意外在特拉维斯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在试图融入主流社会失败后,特拉维斯就产生了试图通过拯救比自己更低阶级的雏妓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的想法,这构成了特拉维斯的另一条行动线,也是其在刺杀失败后血洗妓院,最终戏剧性成为英雄达成自我价值的行动线。
三、影片中的作者风格
马丁·斯科塞斯从最初的“电影小子”到如今的“电影社会学家”,从最初的黑色电影类型片到如今的多类型多元创作,不管是在新好莱坞时期还是当代好莱坞时期,都保留着其电影独特的个人特色。斯科塞斯的个人特色不仅仅来自自己曾经的岁月,也来自他对于社会冷静凌厉的审视态度。下文将从斯科塞斯影片创作空间和核心主题两大方面进行分析。
(一)创作空间——街头
回顾马丁·斯科塞斯的早期创作,《谁在敲我的门》《穷街陋巷》《出租车司机》,不难发现一个非常鲜明的共同点——故事的主要空间是街头,更为准确地说是纽约街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斯科塞斯对于纽约街头的喜爱,甚至可以说是痴迷。与大多数影片中展现的光鲜亮丽的大都市纽约不同,斯科塞斯展现的恰恰是纽约那光鲜背后的丑陋罪恶。《出租车司机》中退伍老兵特拉维斯为了逃避自己的失眠症,也为了赚些外快在夜间开出租车,也是这份职业使得特拉维斯看到了夜晚纽约“脏乱差”的一面——街上随处可见的酒鬼、皮条客小子、妓女、嬉皮士都表明了这个时代的纽约是何等的空虚颓废。斯科塞斯选择展现纽约的这一面与他从小生活街区的常态息息相关,他跟随父母来到纽约后一直住在意大利裔美国人聚集地,被称为“小意大利”的皇后区,在这个街区,与主流社会的不融合使它充斥着冲突、暴力与堕落。
(二)核心主题——身份认同
斯科塞斯曾这样描述自己生活的皇后区:“在这个地方,居民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法律。我们不会理会什么政府、什么政界显要、什么警察,我们觉得这样子是天经地义的。”[5]正是曾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独立于整个美国社会之外的,甚至可以说是与美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街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斯科塞斯的电影中一直存在一种“自我身份认同”的探寻。依然是在早期带有自传色彩的三部影片《谁在敲我的门》《穷街陋巷》《出租车司机》中,我们可以看到导演通过让主角在街区中闲逛给观众带来一种角色与整个社会的强大抽离感。其中《出租车司机》中运用光晕与失焦更加地加深了主角与社会的间离。这样的生活状态究其社会与历史的原因有二。一方面在人数上美国社会的移民基本由英裔美国人组成,意大利裔占了少部分;另一方面在宗教信仰方面整个美洲大陆从较早的一批英移民进入后,基督教中的清教信仰就迅速扩散到整个北美,意大利移民们笃信的是天主教,因此意裔美国人与早已在本地生根的英裔美国人不仅有着语言上的障碍,在宗教信仰上也存在着差异,这导致了意裔美国人与整个社会的大部分群体存在着微妙的隔阂。意裔美国人们在罗马天主教会信仰下,有着非常顽固的家庭中心思想,保有着传统的家族意识,这种思想阻碍了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融合,阻止了外界向意裔美国人的渗透,加深了其与其他阶级群体的隔阂。由此,意大利人强烈的个人奋斗与自我实现、为家族争光的意愿在得不到正确疏导的情况下,意裔美国人容易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这样的主题也在斯科塞斯的电影中反复出现。《出租车司机》中虽然没有前两部影片这么明显的自传色彩与移民心理特色,但是其核心主题依然是自我认同。退伍归来的特拉维斯经历融入主流社会失败,饱受孤寂生活困扰的他试图做出改变,寻找自我价值,最终在暴力制裁中获得救赎,意外成为英雄被社会接纳,获取了自我价值。
四、结语
通过从类型电影视角切入,我们看到了介于类型电影与艺术电影之间,一个优秀的黑色电影范本;通过对影片叙事的研究,我们看到了新好莱坞电影的具体构建形式;通过从作者论视角的研究,我们看到了斯科塞斯电影的特点,他是如何书写故事拍摄电影的。从多个视角对影片进行分析,可以窥探出影片具有丰富的内涵,窥探出“电影社会学家”马丁·斯科塞斯对于那个时代的审视与思考,窥探出时代发展过后其中的时代烙印,形成《出租车司机》经久不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