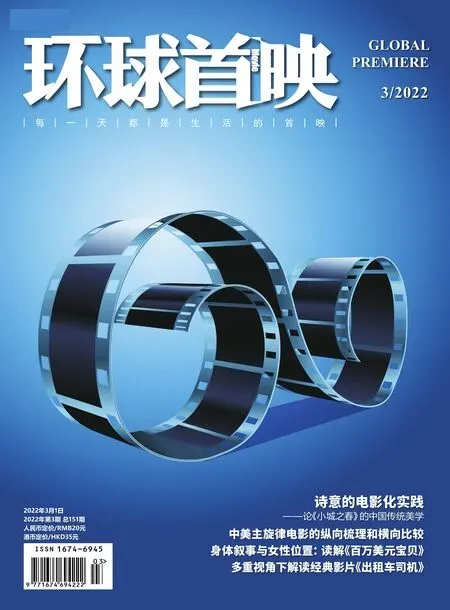身体叙事与女性位置:读解《百万美元宝贝》
赵媛媛 中国传媒大学
《百万美元宝贝》是体育片中一个特殊的文本,影片没有选择“适合女性”的体育项目,而是选择了一个通常是男性主导的力量表演型项目——拳击,展示了女主角麦琪在教练弗兰基的帮助下在拳场上实现梦想的过程,影片突破类型常规,并未终结于赛场的胜利,而是展示了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光辉。不过在这个感人故事背后,我们能够看到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体育片如何书写女性身体、放置女性的位置及被死亡与尊严的“崇高”命题替换和隐藏的话语。
一、拳击运动与女性身体
(一)作为审美对象的身体
伊格尔顿曾说:“美学是作为有关身体的语言而诞生的。”[1]拳击是一项典型的力量表演性体育运动,其特点就在于力量的对抗和身体的展示,身体本身就是审美的对象,于是我们看到麦琪的训练过程也是其穿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展现其健美身材的过程。比赛中短裤和运动内衣让身体大部分裸露,展示了对于人的超越性和理想性的身体追求,本片女主角也为此在三个月内坚持健身和拳击训练[2]。
(二)作为主体意志表征的身体
在体育中,身体不只是物质性的审美对象,灵与肉不是简单的二分,可以说身体本身就是精神与意志的媒介,更是自我主体性的彰显。麦琪的自由精神与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她对身体的自主选择上,经斯科雷普的提点和弗兰基的训练,麦琪进步神速,这是最表层的对身体控制的能力。在首次次重量级比赛中,麦琪被打断鼻梁骨血流不止,弗兰基建议弃权,麦琪却坚持让弗兰基止血继续上场,显然一开始她是惊慌的,而且斯科雷普已经告诉我们“身体知道拳手自己都不知道的事”,会有自我保护的机制,而麦琪正是克服了强烈的恐惧与身体的警报,彰显了强大的自主意志。最后,麦琪瘫痪在床,甚至不能自主呼吸,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和自由选择的能力,从对身体支配能力超越常人的运动员跌落至失去身体控制的“非人”,被人抱上抱下、擦身喂食,作为人的主体性已经丧失,于是她对身体做出了最后的仅能做出的选择,也就是了结生命。由此,影片对身体的表现由最初的审美对象逐渐上升到“普遍人性”的层面。
(三)隐藏性别的身体叙事
上面我们讨论了身体作为体育运动的审美对象、身体作为人的主体性的表征,然而第一种审美特征是传统意义上“男性化的”,第二种对主体性的表现则是非性别化的、普适于人的,其实这也是为何观众初看影片时会体味出的一般体育类型片的“刺激”的、“励志”的,以及超越励志的“人性”的感动,然而细读下去,本片性别的议题就逐渐浮现出来。
拳击是一项典型的“男性”运动,女子拳击也曾是奥运会现有项目中“最后一个实现男女平等的项目”[3],麦琪在片中的女性身份更多是通过他人的话语,而非自身的身体特征被指认的。弗兰基拒绝麦琪的理由在于指认她是女孩,然而此时的麦琪长袖衣裤包裹的身体本身是不具有性别身份特征的。而后,谢瑞尔羞辱丹吉尔的方式也在于对麦琪女性身份的指认,他对丹吉尔说他唯一能打败的人就是这个女孩,而丹吉尔则说我不打女人,随后谢瑞尔甚至调侃侮辱麦琪的身体特征,丰满的身体是好莱坞话语中典型的女性性别表征,而不具有这种传统观念中的性别特质在这里成了对麦琪从事一项男性运动的嘲讽,也就是麦琪的性别身份遭到了质疑。麦琪用同样的身体话语回讽了谢瑞尔的弱小引来众人的大笑,于是在这里无论谢瑞尔、丹吉尔还是麦琪,以丰满胸部等标识的女性是“弱者”的代名词,即使隐藏了这一身体的性别特征,也不是一个能够从事男性运动的人。
于是,女性能够从事这项运动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成了:隐去女性身份,成为男人。可以由弗兰基的话语中看到这一点:弗兰基答应麦琪训练她时,提完要求后答应“会尝试忘记你是个女孩的事实”“受伤了别找我哭”,麦琪首次向弗兰基寻求认可时,说除了呼吸问题自己做得还不错吧,作为一个女孩,弗兰基的回答是:“我不训练女孩。”“蓝熊”作为麦琪最后的劲敌是赛场上重点渲染的对手,在最后对决的出场时,她摘下帽子的凶狠面庞使观众很难辨认出这是一个女性,男性的面部特质与强劲的拳击能力是画等号的,然而即使如此她的输也是必然的,不仅因为麦琪是主角,她妓女出身的身份,这个性别特征极端明显的身份,就已然被判下必输的结局。而同时,妓女的出身与心狠手黑也被画了等号,身体/性的肮脏与道德的越轨对等,与此相对,麦琪的身体纯洁与她的心灵善良/道德优良也是成正比的。于是在麦琪对决“蓝熊”时,弗兰基开始给出的对策是击打她的胸部,最后的对策则是击打屁股的坐骨神经,这种明显对女性脆弱部位的攻击正印证了在拳击运动中,女性的身体即弱点的隐藏话语。于是这个故事中能够赢得比赛的赛场上的麦琪,是需要在身体上去性别的。
影片后四十分钟麦琪离开赛场住进医院后,麦琪的女性表征也是被搁置的,凸显的是其身体的逐渐残缺和不受控。于是影片在去性别化的话语中完成了一种非常规的女性身体叙事,这种叙事带有一定的大男子主义的俯视,却也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传统“带有欲望的凝视”的女性身体表达的消解,虽然这种消解建立在去性别/去女性特征的表达上。
二、人物关系与女性位置
(一)矛盾的宝贝——麦琪与弗兰基
影片伊始,不寻常的意味就隐约蔓延。一场看似正常的、暴力与阴暗的男性拳击比赛正在上演,然而出乎意料的,一位女性向观众席走来,在一个明显的主观的俯视镜头中,构成了麦琪对弗兰基的凝视,一个女性对男性的凝视,这是一种对传统女性被观看位置的颠覆,可以说,麦琪主动的选择了弗兰基。
弗兰基最初拒绝麦琪的理由是“我从不训练女孩”,然而这显然不能劝退麦琪,于是弗兰基在之后加入了对麦琪年纪的质疑,这可以说是冒犯性的打击,所以随后弗兰基带有愧疚地将梨形球赠予麦琪。麦琪“打动”弗兰基的攻势除了日常的训练展示出的坚毅品格、斯科雷普的助攻外,还有她对性别弱势的利用和隐藏。弗兰基是善良的,他不忍看丹吉尔对空气打拳,不忍让斯科雷普退麦琪的钱怕打击到她,对弗兰基而言,麦琪和丹吉尔都是“弱者”(一个是女孩,一个是被侮辱为“只能打败女孩”的人),是需要被予以同情及不忍伤害的。一方面,麦琪直白的自我揭露(对自己处境的揭露、对年龄的揭露)使弗兰基处在一个愧疚的位置而不忍拒绝,另一方面,麦琪拒绝同情和去性别化的姿态又赢得弗兰基的认可。
对麦琪而言,弗兰基是早逝的父的替代,她带弗兰基去自己与父亲去过的餐馆,说弗兰基让她想到了父亲;对于弗兰基,麦琪同样填补了他女儿的缺席。麦琪与弗兰基的不言自明的首个关系是——父与子(孩子)。其实片中父与子的关系除了弗兰基与麦琪,还有斯科雷普与丹吉尔。丹吉尔与斯科雷普实际上是麦琪与弗兰基的映射,斯科雷普是原著小说中不存在的人物,而电影改编时将弗兰基的部分特点转移到了斯科雷普身上。这两对关系中,子虽弱小但都富于热情拥有强大的内心,父虽权威但却是残缺的(一个年迈、一个“半瞎”)。弗兰基在麦琪生日那天主动教导了她,上半身隐于黑暗的出场方式与斯科雷普首次发现麦琪时如出一辙,借由相似的镜语,弗兰基接过了斯科雷普暂代的“父”的角色。而后弗兰基提出了要求:不要问问题,一切听自己的。于是之后,麦琪就成为那个被弗兰基在窗内窥视的角色,但麦琪并不听话,并且在二人关系中占据主动,是她主动选择的弗兰基,也是她最先问到弗兰基的家庭。于是麦琪在父的规训下留有一定的自由,且这种规训是以训练/教导/保护为表现的,并没有强烈的压迫性,也因而难以察觉。
当麦琪又一次没听弗兰基的话在鼻梁断裂后继续比赛并取得胜利后,她成了弗兰基口中的“莫库什勒”。麦琪由此成为弗兰基心中的“宝贝”,也成了所有观众的“宝贝”。麦琪对弗兰基是完全忠诚的,当斯科雷普试图让她有更好发展找来别的经理人时,她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在她那里,弗兰基作为父,是可以提出挑战但不能背叛的,麦琪的忠诚也通过将自我与弗兰基的关系向狗狗与父亲关系的类比和指涉中显现。狗对于人是忠诚的伙伴,狗狗听话,而人也宠爱它们,这种互爱的关系是否意味着人与狗的关系平等呢?答案是否定的。在这层角度上,作为“宝贝”、作为忠诚的伙伴,弗兰基对麦琪的爱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同情与体察,“莫库什勒”是一个明显的、带有父对子俯视角度的话语。
不过对“宝贝”的话语麦琪是矛盾的,一方面她听命于父忠诚于父,另一方面她在一定限度内反抗着父的权威,而且意识到了自己活在父之名中,于是麦琪通过自嘲完成了对这一话语的指认和部分的解构:麦琪躺在病床请求弗兰基结束自己之前,问他莫库什勒的涵义,说道“人们高呼我的,不是我的名字,是你给我起的那个该死的名字”。
“莫库什勒”在影片内的解释是“我的宝贝,我的血肉”,除了孩子这层含义,放在基督教文化中,还潜在的诠释了另一种关系——男与女。上帝创造了亚当,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了夏娃,所以亚当对夏娃说:“我的骨中骨,我的肉中肉”。于是男性由神造、女性只是男性的肋骨,这样男性胜于女性的话语就潜藏在基督教文化脉络中,“骨血”也就成了男性主体地位的表达。如前所述麦琪的女性身份主要通过他人的指认而非直观的身体表现,这当然是一种对传统女性身体被观看位置的解构,但这种解构是以消除女性性别特征为代价的。另一方面,发现麦琪与弗兰基男与女关系的时刻也是麦琪的女性身份被指认的时刻,例如麦琪首次被爸爸以外的男人喊“love”就高兴的问弗兰基自己赢了比赛那个人会不会向自己求婚,或是麦琪母亲看麦琪脸上的伤问她是不是弗兰基打的,还让她找人嫁了,麦琪在传统女性的场域是失败的,因为她的成功需要放下女性身份进入拳击这一男性的场域。
经过上述对父的话语的一系列的建构与解构,麦琪经由自我努力(咬舌)而不得完成的最终的身体选择,由弗兰基之手得以完成。当弗兰基关于莫库什勒意义的告白,成为观众感动的泪点时,观众对麦琪最终归于父亲/男性怀抱的行为在感动中完成认同。
(二)游离的女性——麦琪与其他女性角色
麦琪与母亲的鲜明对比,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独立女性对传统男性中心的“厌女症”的批判[4],我们可以回到影片中检验这一论述。从观众心理上,片中对于母亲这一角色的批判建立在与麦琪相对立的三个方面,一是身体的,二是道德的,三是价值上。首先最直观的批判体现在身体上,母亲肥胖的身体、麦琪口中“我们家的问题通常与体重有关”的直白明示,与麦琪作为一个拳击手对身体的训练和控制形成强烈对比,一个无法控制自己身体的人自然是一个不具有主体性的完整的人。第二层也是最强烈的一层批判来自道德的驳斥,麦琪攒钱给母亲买房却被母亲嫌弃,麦琪受伤躺在医院母亲却带一家在迪斯尼游玩甚至为了财产让麦琪咬笔签字,这种违背正常道德观的行为是观众对母亲形象的极大厌恶与对麦琪的极大认可的最重要的来源。最后才是对母亲的传统男性中心价值观的批判,这种批判在母亲懒惰自私的个性与麦琪勤奋善良的对比中得以实现,由于母亲是令人厌恶的形象,因此母亲所认为的嫁人的归宿也就自然的被否定了,与此同时,观众更加认可的,是麦琪通过自身努力实现梦想的选择。由此可以看出,通过麦琪与母亲的对比,带来的最强烈的批判在道德层面上,对于传统男性中心的性别话语的批判则更多依赖观众对母亲角色的厌恶和对麦琪角色形象的 认可。
与同为女拳手的对手“蓝熊”相比,正如前述,麦琪的成功是在对“蓝熊”女性特征的攻击/贬低/藏匿的意义上完成的,“蓝熊”的妓女出身、相较之下更为丰满的胸部,通过对其“心狠手黑”的形象建构,完成对传统女性身体特征的贬低,这些特征与其说是女性自在的先天的,不如说是被文化建构出的、投射有男性欲望目光的女性特征。然而同时,赛场上出现的身材曼妙的拳击女郎却依旧承担了或者说分担了本应对麦琪和其他女性投射的欲望的目光。这种传统男性中心话语的解构是不彻底的,甚至只是流于表面的,很可能是为顺应一种女性观影的市场趋势和女性崛起的文化潮流做出的商业选择。
三、结语
作为体育片,麦琪这一女性形象确实有所更新,但本片毕竟是由男性导演拍摄,最终呈现为男性视点下的“宝贝”。而在新世纪初美国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这样一部影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也是不难理解的,一方面,通过对麦琪励志故事的感动与自我投射,观众认同了人生的意义在于选择和过程而不在结果,另一方面,当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困境也借由弗兰基与麦琪超越血缘的爱得到了象征性的化解,导演伊斯特伍德也曾表示这是一部关于“爱、希望和梦想的故事”[5],于是在“爱与梦想”和“宝贝”之名的召唤下,所有话语凝结成一个动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