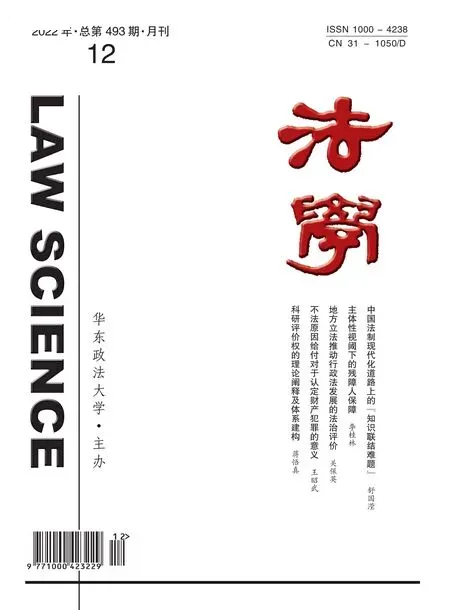论我国消费损害赔偿特别代表人诉讼机制的构建
●范晓亮
在现代化社会大分工的基础上,社会关系愈加复杂,尤其是在福利国家出现后,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往往难以分离,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1〕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4页。有学者认为,随着大规模消费、金融争议与产品质量侵权等新纠纷类型的出现,诉讼法理念和制度安排随之调整,产生了“现代型诉讼”。〔2〕参见肖建国:《现代型民事诉讼的结构和功能》,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1期,第112页;肖建华:《现代型诉讼之程序保障——以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载《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5期,第44-45页。“民事诉讼超越了个人化或者当事人化,而具有社会性取向”在消费争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3〕参见[德]米夏埃尔•施蒂尔纳主编:《德国民事诉讼法学文萃》,赵秀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若漠视消费者损害赔偿诉讼涉及的公共利益保护功能,将使得诉讼的损害赔偿功能无法有效实现。对此,有学者提出了修复相关司法解释中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共通性〔4〕参见吴如巧等:《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共通性——以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的分析》,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67-168页。、融合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双阶段团体诉讼〔5〕参见黄忠顺:《论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融合——兼论中国特色团体诉讼制度的构建》,载《法学家》2015年第1期,第19页。、以公益诉讼判决作为私益诉讼的示范〔6〕参见肖建国、黄忠顺:《环境公益诉讼基本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4期,第11页。等主张。在此研究基础上,本文主张构建以损害赔偿和公益保护为功能目标的特别代表人诉讼,而能够充分代表消费者权益的诉讼主体选任和能够充分组织当事人群体并保障其诉讼权利的原告组织形式成为制度构建的核心。以此为目标,有必要以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基于代理型任意诉讼担当理论作为代表人,以默示加入制作为主要的原告组织形式,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中对两者衔接的逻辑和正当性进行论证,并作出规则设计。
一、消费损害赔偿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必要性、功能与构建思路
(一)消费争议的特殊性与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必要性
消费者权源于民事权利,但在消费者市场地位与能力的结构性弱势之下,又在不断突破民事权利的边界而进入公共利益领域,呈现整体性、人权性、规制性和不对等性等特征。〔7〕参见钱玉文:《消费者权的经济法表达——兼论对〈民法典〉编纂的启示》,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1期,第143页。消费争议具有总体数量较大、单位数额相对较小、影响范围广、争议同质化等特征。一方面,消费者提起单独诉讼因受限于诉讼成本而缺乏足够的诉讼动力,但因数量较大且具有扩散性,若不妥当解决将有损消费者整体信心和市场秩序。另一方面,消费者权利救济在社会基础、社会化程度等方面区别于传统上以债的相对性为基础的私人民事权利救济,而更具有扩张性和权利义务的非对等性,涉及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经济法范畴。〔8〕参见李友根:《社会整体利益代表机制研究——兼论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20、123页。消费者在民法上的个人权利问题易被急剧放大为群体事件,甚至转化为经济法上的消费者整体权益问题,这就要求争议解决方案需超越单独消费者的局限,在实现损害赔偿的同时,以遏制侵害消费者整体权益和市场秩序的行为为目标进行规则设计。
消费争议的解决方式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是主要由公共监管部门通过执行实体法律规章进行的公共执法(public enforcement),在管理市场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公众所受损害进行弥补。〔9〕参见徐昕:《法律的私人执行》,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第18页。二是主要由法定或权利人授权代表的主体通过民事诉讼进行的私人执法(private enforcement),包括实现个人损害赔偿和对公共利益的维护。〔10〕世界范围内典型的群体性民事诉讼包括美国法上的集团诉讼制度(class action)、欧盟法上的集合救济制度(collective redress)、德国法上的示范诉讼制度(musterverfahren)、日本法上的选定当事人和团体诉讼制度等。参见陈巍:《欧洲群体诉讼机制介评》,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3期,第109页。在主要受大陆法系传统影响的国家,传统上大多以公共执法模式为主。但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体量的扩大、商业模式的更新和全球化的深入,消费争议呈现规模化、复杂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单一的公共执法模式受到挑战。2005年“德国电信案”推动了对传统示范诉讼机制的改革,新《投资者示范诉讼法》随之实施。〔11〕参见吴泽勇:《〈投资者示范诉讼法〉:一个群体性法律保护的完美方案?》,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第146-149页。十年后,欧盟连续发生大规模消费争议,包括2015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召回850万辆汽车的“尾气排放门案”、2017年涉及40万名旅客的“瑞安航空公司航班取消案”和2018年“史莱姆斯诉脸书(爱尔兰分公司)案”等。〔12〕See In re Volkswagen “Clean Diesel” Marketing, Sales Practices, and Products Liability Litigation, MDL No. 2672 (N. D.Cal.); Birmingham Firemen’s & Policemen’s Supplemental Pension Sys. v. Ryanair Holdings, 18-CV-10330 (JPO) (S. D. N. Y. Jun. 1,2020); Maximilian Schrems v. Facebook Ireland Limited, Judgment of the Court (Third Chamber) of 25 January 2018, Case C-498/16, ECLI identifier: ECLI:EU:C:2018:37.上述案件凸显了在欧盟出现的因政府治理失灵导致公共监管不足的现象。
基于对群体性侵权行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担忧、“厌讼”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强政府管制模式等因素,我国长期以来倾向于通过公共执法维护市场秩序、解决消费争议,保护公共利益成为执法的主要目的,但难以兼顾损害赔偿功能的实现。随着我国国内外消费市场规模和复杂程度的提升,近年来消费群体争议呈现增多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单一的公共执法模式明显不足,而有限的司法资源和传统民事诉讼模式也不适应消费争议的特殊性,尤其是难以实现群体损害赔偿功能,加强私人执法成为现实要求。〔13〕参见黄忠顺:《食品安全私人执法研究——以惩罚性赔偿型消费公益诉讼为中心》,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84-87页。作为我国私人执法的主要形式,“保护不特定消费者的利益”之公益诉讼以不作为之诉为主,而在损害赔偿之诉方面,普通代表人诉讼适用的效果不彰,特别代表人诉讼近年来成为关注焦点。
在我国,消费者因不当经营行为遭受实际损害的,难以直接在公益诉讼中受偿,需另行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扩散性的消费者权利受到损害时常体现为单位数额小和人数众多的损害赔偿争议,现有的代表人诉讼和单独诉讼无法有效应对,但扩散性损害的数量累积起来也造成了对公共利益的影响。为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完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实质性实体请求权归属于消费者,具有公益组织性质的消费者协会依法取得形式性实体请求权,〔14〕参见黄忠顺:《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研究》,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第261页。在诉讼案件的选取上不可避免地含有履行其保护公益职责的目的,并通过限制消费者诉权的默示加入制一揽子解决争议,产生了示范效应,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心理安定,也产生了公益保护的效果。因此,特别代表人诉讼一方面可以补充公益诉讼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示范效应、消费者明示退出等激活普通代表人诉讼。
此外,在判决经营者赔偿消费者损害的同时,对经营者施加惩罚性赔偿,以达到威慑违法经营者、稳定市场秩序的目的,这被认为超越了损害赔偿诉讼的界限而具备了公益保护的功能。但目前惩罚性赔偿公益诉讼仍属于一项探索性制度,司法实践呈现多元化样态,在请求权基础等理论研究方面也存在争议。〔15〕参见杨会新:《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问题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4期,第116页;李智卓、刘卫先:《惩罚性赔偿不应适用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理辨析》,载《中州学刊》2022年第3期,第49-53页。但在特别代表人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则更具可行性,使消费者私法性的赔偿请求权在私益诉讼中得以实现。消费者享有实质上的惩罚性赔偿实体请求权,消费者协会享有形式上的惩罚性赔偿实体请求权,只要存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和《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消费者协会就应有权代表消费者提起请求惩罚性赔偿的特别代表人诉讼。
(二)代表人诉讼结构的核心:诉讼主体选任与原告组织形式
确定代表人的诉讼主体选任与凝聚被代表人诉讼请求的原告组织形式是代表人诉讼机制构建的关键,应结合所需解决纠纷的特点和类型进行规则设计。群体性纠纷来源于特定类型的实体法律关系,具有相对性、暂时性或阶段性,并因实体法律关系确定与否而变得更加复杂。例如,数个当事人为某种实体目的而确定了合同关系,若因某种违约事由发生争议就可能演变为群体性纠纷。在合同纠纷中,由于这种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在纠纷发生前就已确定,因而当事人在数量上和内在的规定性上都是确定的,这就是所谓人数事先确定的群体性纠纷。另一种群体性纠纷产生于主体事先不确定的法律关系中,如环境侵权纠纷、消费侵权纠纷,在纠纷发生之前后,所涉当事人人数均不确定。
按具体纠纷类型划分,群体性消费者诉讼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于对不特定消费者的公益保护,法院对违法行为作出禁止令或程度相当的宣告性救济。在此类诉讼中可能包括金钱救济,但这不是唯一的或占主导地位的。这类诉讼是整体救济,而非针对单独权利人的特别救济,在我国表现为由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基于不作为请求权、撤销请求权等公益性实体请求权提起的消费公益诉讼。
第二类是因单一事件造成群体性侵权损害,如涉及商品房集中销售、旅游消费者遭遇交通事故、特定消费品的质量和价格问题等,此类往往被视为必要的群体诉讼,将相关案件强制合并,既有利于避免在同一事实上重复诉讼而浪费司法资源,也有利于全面、公平地保护权利人。在此类型下,权利人易于确定和通知,且受损害数额较大,有较强的参与意愿,因此以明示加入制为主要形式,由实体权利人作为代表人提起普通代表人诉讼具有可行性。
第三类是扩散性的小额消费争议,权利人范围难以确定,但具有共同的法律或事实问题,影响个别权利人的个性问题处于次要地位。此类争议具有权利人数量多且不确定、损害分散等特点,并因单位金额微小而难以激励权利人提起单独诉讼,也难以通过明示加入制凝聚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且授权难题也使不具有实体法律关系的社会组织取得诉讼代表权的正当性存疑。但损害得以累积则数额庞大,若违法经营者逃脱惩罚,将进一步造成市场秩序的破坏和社会公众心理隐患。〔16〕参见汤维建:《群体性纠纷诉讼解决机制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 129-131页。解决此类消费争议的主要目的在于威慑违法经营者、撇去违法收益,而填补当事人的微小损害实际上成为次要目的,因而混合了公益保护与私益保护的效果。〔17〕参见黄忠顺:《消费者集体性损害赔偿诉讼的二阶构造》,载《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5期,第67、71、74页。此类诉讼程序最为复杂,当事人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诉讼请求的差异使损害赔偿各有异同,由具有保障消费者权益法定职能的社会组织基于默示加入制提起特别代表人诉讼成为可行的选择,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三)代表人诉讼的社会基础、功能差异与路径选择
受各国不同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体系的影响,代表人诉讼的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有所不同,需剖析其背后的多重因素并及时跟进其理论发展。
我国的代表人诉讼曾以美国法上的集团诉讼作为主要参考,但基于维护社会安定、追求诉讼经济等考虑,其制度设计脱离了自身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实践中案件量极少,效果不彰。〔18〕参见雷桂森:《试论我国证券侵权救济的群体诉讼模式选择》,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1期,第83页。在美国,司法权具有更多主动性,且在市场导向的背景之下,其政治与法律文化素来支持以诉讼作为保护公共利益的积极手段。美国法上的民事诉讼功能较为宽泛,除刑事案件以外的民事、经济、行政、宪法案件的解决大多依循民事诉讼程序,〔19〕参见何其生:《国际规则中的“民商事项”——范围之争与解释方法》,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9卷第2辑,第4页。而判例法传统也为通过诉讼实施与完善公共政策提供了有效路径。美国法上的集团诉讼实质上是由实体权利人提起的代表人诉讼,以实现损害救济、遏制违法行为、规范市场秩序和保护公益为目标,并通过默示加入制、惩罚性赔偿、证据开示、胜诉酬金等特别规则而得以强化。忽略现象背后的逻辑,仅对我国的共同诉讼等现有规则进行调整,以追求美国法上集团诉讼的功能,将会陷入法律移植的“明希豪森三重困境”,〔20〕参见舒国滢:《走出“明希豪森困境”——〈法律论证理论〉译序》,载[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译序”第1页。最终在损害赔偿和保护公益方面均难以发挥作用。
任何融贯的法律体系都有一套成熟的政治理论与道德信念作为支撑,并以此作为自我批判、完善与重述的基础。〔21〕参见雷磊:《法教义学与法治:法教义学的治理意义》,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第72页。在政府导向的经济形态之下,中国和欧盟均强调发挥政府职能,在以社会福利体系弥补小额侵权损害的前提下,传统上依赖基于实体法律的公共执法机制维护公民权益、制约违法行为、调整市场秩序,而对以民事诉讼为渠道实现补偿或威慑功能的私人执法方式则持较为保守的态度。〔22〕欧盟曾有学者认为,应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置于公共执法框架之内,由政府主导消费者救济,并着重推广业已运行良好的、由政府资助但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申诉专员(independent ombudsman)等制度。See Manning G. Warren, The Prospects for Convergence of Collective Redress Remed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47 International Lawyer 101, 118 (2014); Christopher Hodges, Multi-Party Actions:A European Approach, 11 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Law 323, 332 (2001).在大陆法系传统的法教义学框架中,民事诉讼以争议解决和权利保障作为中心功能,立足于两造程序权利的平等,以请求权为基础实现对当事人的私法救济并保障当事人对诉讼权利的处分权。虽然判决具有外部性效应,但这并不属于诉讼的直接目的,仅政府有权执行公共政策。〔23〕See Paul G. Karlsgodt, World Class Actions: A Guide to Group and Representative Actions Around the Glob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15.因此,一直以来在欧盟较难通过诉讼实施公共政策,其对兼具救济、惩罚和威慑功能的惩罚性赔偿等制度持谨慎甚至排斥的态度。〔24〕See Paras. 11 and 53 of the Commission White Paper on Modernisation of the Rules Implementing Articles 85 and 86 of the EC Treaty, Commission Programme No. 99/027, OJ C 132, 12.5.1999, p. 1-33.同时,出于对诉权滥用造成经营者歧视的担忧,目前欧盟对私人执法顾虑重重,〔25〕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方面,包括德国在内的成员国也基于诉权滥用的担忧而持谨慎态度。参见陶建国:《德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德国研究》2013年第2期,第73页。私人执法难以替代公共执法的主导地位,而仅作为一种补充。〔26〕2012年2月,欧洲议会在其决议中表明了该立场。See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2 February 2012 on “Towards a Coherent European Approach to Collective Redress” (2011/2089(INI)), OJ C 239E, 20.8.2013, p. 34.欧洲议会曾提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Wal-Mart Stores Inc. v. Dukes et al.案”〔27〕See Wal-Mart Stores Inc. v. Dukes et al., 564 U. S. 338 (2011).中就集团诉讼制度引发滥诉现象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并再次强调集团诉讼制度采用分权监管的思路,与欧盟予以集中监管的传统并不契合。〔28〕See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2 February 2012 on “Towards a Coherent European Approach to Collective Redress”(2011/2089(INI)), OJ C 239E, 20.8.2013, p. 34.
但是,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其一般都具有较强的国家主义和集团主义观念,这种观念渗透到程序法领域,令其民事诉讼机制相对于英美法系而言,具有更强的国家干预色彩以及强调社会利益的特点。〔29〕参见张卫平:《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与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两种诉讼体制的比较分析(上)》,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4期,第58页。在群体性消费争议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之后,欧盟开始尝试以民事诉讼作为公共监管的补充手段。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以特别代表人诉讼实现“集合救济”(collective redress)为中心的立法探索从1984年开始延续至今,〔30〕欧洲共同体于1984年发布的备忘录即开始了对代表人诉讼的探索。See Memorandum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transmitted on 4 January 1985, COM (84) 629 Final, 12 December 1984, Bulleti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upplement 2/85.并以2020年11月25日发布的《保护欧盟消费者集合权益的代表人诉讼指令》(以下简称《欧盟代表人诉讼指令》)作为主要成果。〔31〕See Directive (EU) 2020/1828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November 2020 on Representative Ac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llectiv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2009/22/EC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OJ L 409,4.12.2020, p. 1-27.欧盟立法集中考虑大陆法系传统可接受的普遍性规则,以有效衔接公共执法与私人执法、加强实现损害赔偿功能。欧盟与我国具有类似的大陆法系与公共监管传统,在立法过程中曾与我国一样试图借鉴美国法上的集团诉讼进行宽泛的集合救济,但效果不彰,最终以法定社会组织基于任意诉讼担当理论作为特别代表人提起消费损害赔偿之诉,其在探索中收获的经验值得借鉴。
二、任意诉讼担当:诉讼主体选任的理论依据和正当性
(一)代理型任意诉讼担当:特别代表人诉讼主体的选任依据
由消费者保护组织提起特别代表人诉讼有助于消费者接近司法、平衡两造诉讼能力和提高诉讼效率。但消费者保护组织并非实体消费法律关系当事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以实体法律关系为核心,司法机关也通常不会承认非实体法律关系主体的诉讼当事人资格。但是,法定的任意诉讼担当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当事人制度。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前提下,由实体法律关系主体以外的第三人经实体权利人授权而代表其提起诉讼,主张实体权利人享有的权利,法院判决的效力约束实体权利人,〔32〕参见王甲乙:《当事人适格之扩张与界限》,载《法学丛刊》1995年第1期,第128页。可以以此突破实体法律关系对诉讼当事人资格的限制,更好地发挥权利保护和纠纷解决的功能。
有学者认为,任意诉讼担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代表型任意诉讼担当,是指由实体法律关系的权利人作为代表人,为自己及其他权利人提起诉讼。这对当事人适格理论冲击较小,已经被规定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代表人诉讼和《证券法》普通代表人诉讼之中,但因消费争议的特殊性而实施效果有限。(2)代理型任意诉讼担当,是指具有独立实体权利义务的主体,接受实体权利人的授权,以当事人身份参加诉讼。这对现行法的影响较大,因此我国法对此较为谨慎,也是本文论证的重点。(3)拟制型任意诉讼担当,是指由诉讼法拟制诉讼程序中的主体,实体法律关系主体授予其诉讼实施权,拟制的主体不具有任何实体权利义务,仅作为诉讼程序中的当事人而存在,例如德国和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对无权利能力社团诉讼地位的规定。〔33〕参见纪格非:《功能论视角下任意诉讼担当的类型研究》,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2期,第164页。
基于任意诉讼担当理论的损害赔偿特别代表人诉讼在我国《证券法》中得以明确,投资者保护机构受50名投资者委托,可以作为代表人提起诉讼。目前具有“投资者保护机构”资格的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持有每家上市公司的一手股票,因此也具有投资者的身份,通过建立实体权利关系的方法使投服中心提起特别代表人诉讼具有更充分的正当性。但消费者保护组织不可能以消费者身份享有诉争实体权利,若基于代理型任意诉讼担当理论提起消费损害赔偿特别代表人诉讼,则属于当事人适格范围的扩大,需要进一步论证。
传统上代表人诉讼的目标是保护被代表人在私法上的实体权利,因此要求代表人与被代表人之间有实体法律关系,以保证诉讼程序集合诉讼请求和限制被代表人诉权的正当性。但随着对法律及其与社会关系认识的变化,上述正当性要求也发生了变化。物权法、债法等传统部门法建构于法学对规范的逻辑整理,主要功能是分类整理,但不能将其理解为一个内部无矛盾的、自洽的和独立的统一体。随着社会生活日趋复杂,针对群体利益保护的立法规制更多是为了应对眼前的现实问题,按照社会事实领域而建构(如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并非单纯基于实体法律关系的逻辑设计。〔34〕参见纪海龙:《法教义学:力量与弱点》,载《交大法学》2015年第2期,第96页。代表人诉讼所保护的目标已经超越了私人实体权利,进一步扩展至社会公共利益。为平衡诉讼两造能力,并避免不受控制的诉讼影响社会稳定,同时也期望通过协调公共监管机制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35〕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代表人诉讼的功能扩展至提高诉讼效率和促进纠纷解决,对实体法律关系的要求降低。因而,由立法明确具有不作为请求权、撤销请求权等公益性实体请求权的特定消费者保护组织基于任意诉讼担当理论以当事人的身份提起救济消费者的诉讼,实现了实体法律关系的适当联系,成为一些国家通行的做法。〔36〕参见刘学在:《日本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介评》,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6期,第146页。例如德国法规定,消费者可以将损害赔偿请求权授予消费者保护组织以提起特别代表人诉讼,判决仅对明示授权的消费者有拘束力,未予授权的消费者仍有权提起单独诉讼或共同诉讼,这也成为《欧盟代表人诉讼指令》的文本基础。
(二)欧盟对代理型任意诉讼担当代表人诉讼的探索
2009年,欧盟全面修订了1998年《关于提起禁止令诉讼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98/27/EC指令》,〔37〕See Directive 98/27/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9 May 1998 on Injunc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s’ Interests, OJ L 166, 11.6.1998, p. 51-55.并公布了《关于提起禁止令诉讼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2009/22/EC指令》,〔38〕See Directive 2009/2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3 April 2009 on Injunc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s’ Interests (Codified Version) (Text with EEA Relevance), OJ L 110, 1.5.2009, p. 30-36.规定由成员国立法授权特定社会组织提起不作为之诉,由法院发布禁止令以规制侵害不特定消费者权益的不公平合同条款或非法商业行为。但在同一时期,损害赔偿之诉发展缓慢,塞浦路斯、爱尔兰、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等国家没有进行相关立法。而在进行了立法的国家也规定有限,如德国仅主要针对证券投资者诉讼作出规定,比利时仅主要针对消费者诉讼作出规定。2011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建立欧盟集合救济体系的持续性措施》以进行公共谘商,〔39〕See European Commission, Public Consultation: Towards a Coherent European Approach to Collective Redress,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SEC (2011) 173 Final, Brussels, 4 February 2011.并首次对“集合救济”作出统一定义,即“达到消除、阻止侵害众多消费者或中小企业权益的非法商业行为的目的或实现损害赔偿的法律机制”。同年7月,欧洲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发布倡议,表明议会将继续开展工作并在2012年依据工作成果发布决议。
2013年6月,根据欧洲议会的工作成果和决议,〔40〕See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2 February 2012 on “Towards a Coherent European Approach to Collective Redress”(2011/2089(INI)), OJ C 239E, 20.8.2013, p. 32-39.欧盟委员会认识到实施一个有拘束力的区域统一规则的难度较大,转而以《在成员国建立针对侵犯欧盟法项下权利之行为的禁止令和赔偿的集合救济机制所依循一般原则之建议》(以下简称《欧盟集合救济建议》)〔41〕See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f 11 June 2013 on Common Principles for Injunctive and Compensatory Collective Redress Mechanisms in the Member States Concerning Violations of Rights Granted Under Union Law, OJ L 201, 26.7.2013, p. 60-65.的形式,以一系列具有普遍适用价值的非拘束性规则为基础构建了法律框架,主要思路是将“代表人”规定为资格范围较为宽泛的社会组织,推进由其提起的损害赔偿特别代表人诉讼。“建议”这种文件形式在欧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没有创设强制性义务。在“Salvatore Grimaldi v. Fonds des maladies professionnelles案”〔42〕See Salvatore Grimaldi v. Fonds des maladies professionnelles, Judgment of the Court (Second Chamber) of 13 December 1989,Case C-322/88, ECLI identifier: ECLI:EU:C:1989:646.中,欧盟法院表明,建议与指令的区别只是没有为成员国创设义务,但实际上反映了欧盟计划针对该领域进行立法的意图,因此成员国在解释法律时仍须将欧盟发布的建议考虑在内。
2018年1月,根据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盟集合救济建议〉实施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43〕See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f 11 June 2013 on Common Principles for Injunctive and Compensatory Collective Redress Mechanisms in the Member States Concerning Violations of Rights Granted Under Union Law (2013/396/EU),COM/2018/040 Final, 25.1.2018.《欧盟集合救济建议》的积极影响主要集中于发布了代表人诉讼的框架性规定和示范法,即由社会组织提起特别代表人诉讼以实现损害赔偿,并在防止滥诉的基础上保障公众诉诸法院的权利。比利时、立陶宛和斯洛文尼亚的最新立法已纳入《欧盟集合救济建议》的主要内容,法国和英国国内法的修订也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借鉴。考虑到2018年《评估报告》所揭示的成员国立法状况,且基于2015-2018年间“大众公司尾气排放门案”“瑞安航空公司航班取消案”“史莱姆斯诉脸书(爱尔兰分公司)案”三起重大群体诉讼带来的紧迫性,欧盟委员会于2018年4月启动了以“消费者保护新规划”为题的一揽子立法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进一步推进《欧盟集合救济建议》的内容融入成员国立法。(2)准备发布一个旨在促进通过代表人诉讼程序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指令,并以《发布以代表人诉讼保护消费者集合利益的指令及撤销2009/22/EC指令的提议》之文件的形式开始进入立法程序。〔44〕See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Representative Ac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llectiv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nd Repealing Directive 2009/22/EC, COM/2018/0184 Final - 2018/089 (COD).(3)考虑设立有权提起跨境诉讼的欧盟消费者申诉专员。(4)准备发布一个旨在完善和实施欧盟消费者保护实体法律规则的指令,以促进公共执法并与代表人诉讼相配合,即《发布更好地实施和促进欧盟消费者保护规则现代化的指令的提议》。〔45〕See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 93/13/EEC of 5 April 1993, Directive 98/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Directive 2005/29/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nd Directive 2011/83/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s Regards Better Enforcement and Modernisation of EU Consumer Protection Rules, COM/2018/0185 Final - 2018/090 (COD).
为促进良好、规范和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实现《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81条所要求的保障公民接近正义的权利和降低民事诉讼难度的司法机制,在欧盟委员会、议会、理事会的持续推动之下,以2020年11月25日生效的《欧盟代表人诉讼指令》作为最终成果。实施该指令的目标集中于通过法定社会组织提起特别代表人诉讼实现损害赔偿,将之前包括了消费、环境、医药、金融等争议的宽泛适用领域集中于消费争议,并明确排除了反垄断案件的适用。《欧盟代表人诉讼指令》同时对促进诉讼效率的规则进行了改良,包括代表人资格、原告组织形式、证据规则与诉讼时效等。
具有与我国类似的大陆法系和公共监管传统的欧盟就特别代表人诉讼提供了良好的参考样本,但要论证借鉴的可行性,还需进一步对该规则在我国实施的正当性进行分析。
(三)社会组织担当代理型特别代表人诉讼主体的正当性
首先,规则的正当性应与现有法律框架相协调。以我国201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正为标志,社会组织开始基于法定的任意诉讼担当而获得代表人诉讼的主体资格,并将有权就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代表人范围限定为省级以上的消费者协会。随着消费公益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的立法完善、〔46〕已有学者提出环境损害救济方式应采用以禁止令为主、以损害赔偿为辅的模式。参见杜群、梁春燕:《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单一模式及比较视域下的反思》,载《法学论坛》2016年第1期,第54页。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示范效应以及对单一救济模式局限性的反思,损害赔偿特别代表人诉讼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规定了由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提起以公益诉讼为形式的不作为之诉,而兜底条款使用了“等”字,为消费者协会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收缴不当所得之诉等给付类型诉讼的权限留下了进一步解释的空间。〔4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20号)第13条规定:“原告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证券法》明确了投资者保护机构在取得投资者授权后可基于任意诉讼担当理论提起损害赔偿代表人诉讼,这在“康美药业案”中得以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并将产生制度溢出效应。〔48〕参见汤维建:《中国特色的证券代表人诉讼》,载《人民司法》2020年第28期,第43页;辛宇:《投资者保护公益组织与股东诉讼在中国的实践——基于中证投服证券支持诉讼的多案例研究》,载《管理世界》2020年第1期,第69、81、84页。
其次,规则的正当性应有利于诉讼功能的实现。从新公共管理主义的角度来看,公共执法的不足可以通过吸纳企业管理理论予以弥补,即改变传统上单一的政府供给模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以提供更多元的公共产品和服务。〔49〕参见高志宏:《公共利益观的当代法治意蕴及其实现路径》,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2期,第22页。既然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那么也应当认可社会组织经当事人授权作为诉讼代表人以行使诉权的方式参与社会管理。〔50〕参见张卫平:《民事公益诉讼原则的制度化及实施研究》,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4期,第14页。由消费者协会基于代理型任意诉讼担当理论而提起特别代表人诉讼,可突破实体法律关系对诉讼当事人资格的限制,以当事人的身份更好地发挥诉讼的权利保护功能,并进一步简化诉讼程序、实现提高诉讼效率等程序性功能。
最后,规则的正当性应基于代表人具有诉讼法所要求的实体法律关系。无条件的诉讼担当将使当事人适格标准变得过于宽泛,为传统的当事人理论带来冲击,也与律师代理制度产生紧张关系。代表人对诉讼应具有“法的利益”并获得实体权利人的授权,以使代表人与诉讼标的保持一种实体法上的适当限度联系。代理型任意诉讼担当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人,其正当性来源于权利人授予代表人诉讼实施权,并且代表人对实体权利关系管理的参与程度达到甚至超过权利人。〔51〕参见纪格非:《功能论视角下任意诉讼担当的类型研究》,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2期,第168页。而且,省级以上的消费者协会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7条为法律依据提起公益诉讼,而该条规定消费者协会可以“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也可以被解释为其提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法律依据。一方面,消费者权益应包括不特定人的、开放性的公共性质权益,消费者协会享有不作为请求权、撤销请求权等公益性实体请求权,可基于法定诉讼担当提起预防、威慑和矫正违法行为的公益诉讼。另一方面,消费者权益也应包括集合性、封闭性的私人性质权益,省级以上的消费者协会应被认为满足了适当限度的实体法律联系要求,可基于任意诉讼担当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既对消费者予以私益损害救济,也对违法经营者产生一定程度的威慑效果。
三、默示加入制:特别代表人诉讼效率与诉权保障的衡平
(一)代表人诉讼执行公共政策的功能与对默示加入制的需求
抽象的公共利益作为法律保护客体,受其不确定性影响而难以对其内涵和外延作出准确界定,阻碍了对程序规则的进一步建构。〔52〕参见杨会新:《去公共利益化与案件类型化——公共利益救济的另一条路径》,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4期,第15页。但以个人利益的形式对公共利益进行解构,将其具体转化为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在诉讼程序上提出要求的权利后,就可以通过损害赔偿诉讼进行集合救济。〔53〕参见夏勇:《依法治国——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侵害多数消费者权益造成的损害,以及环境污染造成的水体、土壤损害和水产养殖户、农作物种植人的损害等,都可以通过追究违法行为人的侵权责任获得救济。对于因社会经济模式变革而发生的规模化、复杂化争议,予以妥善解决有利于遏制违法行为、维护消费者权益和市场秩序、保障公众接近正义权利的实现。以上“非商品价值”和集体抱负虽然难以通过货币化形式化约,但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外部性可以促进上述目标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损害赔偿和公益保护的边界开始模糊。
在以诉讼请求为中心的民事诉讼制度中,由原告依处分权提起诉讼实现请求权。这样一种传统范式建立在两造诉讼地位与能力相对平等的基础上,并以诉讼的利益和成本基本平衡为前提,但在应用于消费争议时则面临困境。有学者认为,对于轻微侵害,要么得作为社会所接受的事实加以忍受,要么虽然超过了忍受限度但还不值得使用司法资源时,受害人可以通过一定的自力救济措施进行排除。除非有实际的或潜在的不当行为之重复,或造成对受害人财产的永久性不利影响,否则法院会对是否介入案件持犹豫态度。〔54〕参见[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但是,当扩散性轻微侵害的效应叠加时,若多数受害人都对此予以容忍,则消极影响相当大,会造成更多的经营者仿效以寻求违法利益,最终导致人们对正义的失望。〔55〕参见[日]小岛武司:《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陈刚、郭美松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在现代社会经济的规模和复杂性愈加扩大的背景下,实体法中出现了创新的消费者保护、环境损害赔偿、电子数据与隐私权保护等规则,有学者认为在上述法律领域中尚未形成非常明确的和稳定的教义,而更需要注重基于经验的政策性和对策性研究。〔56〕参见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第61页。在同一时期,程序法上的创新体现在代表人诉讼之中,〔57〕被作为大多数国家参考范本的美国法上的集团诉讼也是在1966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修订后才开始在实践中迅速发展的。参见王开定:《美国集体诉讼制度》,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7页。这在通过默示加入制由代表人代表权利人在法院进行间接权利登记、诉讼、调解等程序,迅速拟就大规模诉讼集团,一揽子解决争议以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平等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代表人诉讼通过调整并集中诉讼请求使程序更加有效、可行,权利人可以声明退出程序,否则就将被自动纳入诉讼集团,可从胜诉判决中取得损害赔偿金,同时也将受判决拘束。
欧盟法上的特别代表人诉讼主要采取明示加入制,而我国对默示加入制的现实需求可以通过中欧法制的比较获得认同。首先,欧盟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和安全保障体系,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与补偿的社会保险水平较高。而我国确保消费者人身或经济安全的社会保险赔偿体系不尽完备,需要以追究侵权等责任的法律机制加以补充,〔58〕参见章武生:《我国证券集团诉讼的模式选择与制度重构》,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2期,第289-290页。因而对特别代表人诉讼默示加入制的需求更加迫切。而且,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以解决争议为主要功能,同时兼顾保护私权,最终服务于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总体目标。〔59〕参见傅郁林:《民事诉讼法修改的价值取向论评》,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80页。其次,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虽然受德国法和日本法的影响而带有明显的大陆法系印记,但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和前苏联诉讼模式的影响,并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对美国法进行了相当比例的借鉴。〔60〕参见陈刚:《法系意识在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41页。与欧盟相关规则相比,我国的代表人诉讼更多地受到法制混合特质的影响。再次,与欧盟成员国以“回应型”为主要形态的国家权力相比,我国的公权力角色更加能动,故我国法对公共利益范围的界定更宽泛。〔61〕参见廖永安、王聪:《法院如何执行公共政策:一种实用主义与程序理性有机结合的裁判进路——以“电梯内劝阻吸烟案”为切入点》,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2期,第6页。最后,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经过长期积淀,其法教义学理论高度成熟和稳定,虽自认可适用于解决绝大多数的利益冲突,但迟缓了对价值判断的进一步更新与容纳。〔62〕参见[德] 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146页。因此,欧盟难以在民事诉讼领域推动默示加入制等激进的立法改革。而公共政策频繁进入司法是当下中国司法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63〕参见宋亚辉:《公共政策如何进入裁判过程——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例》,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6期,第115-116页。因此,为使特别代表人诉讼在我国切实取得效果,应不局限于借鉴欧盟法上的代表人诉讼经验,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容纳默示加入制。
(二)价值衡平与功能取向:默示加入制的理论基础
民事诉讼通常将公正和效率作为基本价值追求,前者包括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的公正,后者秉承“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要求迅速推进诉讼程序以实现“案结事了”。随着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在20世纪后半叶进入司法领域,诉讼的经济性也进入与效率相关联的诉讼价值追求之中。无论是公正、效率还是经济,诉讼规则的构建就是在各价值追求之间进行衡平,其间存在牵制、博弈或此消彼长的关系。〔64〕参见张卫平:《论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追求》,载《法治现代化研究》2021年第3期,第7页。诉讼规则的设计、运行和解释等过程实际上就是衡平多重价值追求之间关系的过程。〔65〕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学方法论》,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2期,第9页。在不同的社会基础和发展阶段中,民事诉讼价值的衡平有着不同的方式,并导致规则所发挥的功能也有所不同。具体到特别代表人诉讼,则包括了保障当事人权利、简化诉讼程序和提高诉讼效率等功能取向。〔66〕参见刘学在:《论任意的诉讼担当》,载江伟教授执教五十周年庆典活动筹备组编:《民事诉讼法学前沿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263页。
因同一违法行为损害多数消费者的利益,使得消费争议具有争点共通性与利益集合性,结合不同的诉讼功能取向将形成不同的规则构建思路。一方面,若将代表人诉讼的功能理解为争议解决,则应侧重于通过默示加入制最大限度地将诉讼请求合并,通过集合大规模、扩散性的相同利益诉求,一次性地解决争议,并形成高额赔偿判决甚至施加惩罚性赔偿。这将对违法施加威慑,对潜在消费者也形成保护,使损害赔偿特别代表人诉讼也兼具了公益保护的效果。〔67〕参见肖建华:《现代型诉讼之程序保障——以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载《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5期,第46页。另一方面,若将代表人诉讼的功能理解为权利保障,则要求在制度设计上明确立法依据和消费者授权条件,通过具有充分代表性的主体主张集合性权利,并通过明示加入制解决当事人适格理论对于无利害关系或无诉的利益的主体提起代表人诉讼的障碍。
比较而言,美国法上的集团诉讼以规制大规模侵权行为和市场违规行为为主要目标,以争议解决为核心功能,兼具损害赔偿和威慑违法行为的功能,经由默示加入制、惩罚性赔偿、胜诉酬金、证据开示等一系列规则基础上的高额赔偿而实现。而随着欧洲人权法院对《欧洲人权公约》中公平审判权的解释,引申出“诉诸法院之权利”,〔68〕参见李庆明:《国家豁免与诉诸法院之权利——以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为中心》,载《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6期,第151页。这也影响了欧盟法上的代表人诉讼,使其将公正审判与权利保障作为目标,在完善的公共监管机制的基础上,以法定社会组织基于任意诉讼担当理论作为诉讼代表人,并明确了明示加入制、禁止惩罚性赔偿等一系列规定,目的是在防止滥诉的前提下,进一步清除公民诉诸法院维护权利的障碍,提供高标准的司法救济。不同的社会基础、功能和目的使得美国法和欧盟法上的群体诉讼机制具有显著差异。
(三)诉讼处分权的限制与默示加入制的正当性依据
民事诉讼中的意思自治,或称处分权,包括了权利人决定是否行使请求权的自由,即如果权利人决定行使特定请求权,其也应对案件享有充分的控制权。权利人有权放弃或者授权他人行使权利,但需要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而非推定的承诺或假定的授权。诉讼处分权被视为具有独立的价值而受到特别保护,其重要程度甚至高于损害救济,这被作为反对默示加入制的主要原因。默示加入制在欧盟立法进程中曾经历从被拒绝到接纳的过程,尤其是德国法学界在解释代表人诉讼时曾试图超越问题本身的特殊性和新颖性,而将其嵌套在传统争议解决的思维模式中,希望保持逻辑的一致性,避免破坏传统诉讼法的精确与稳定。德国有学者曾认为默示加入制损害了当事人的听审权和处分权,〔69〕See Astrid Stadler, Mass Tort Litigation, in: Rolf Stürner & Masanori Kawano (eds.), Comparative Studies on Business Tort Litigation, Mohr Siebeck, 2011, p. 172-173.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也因此放弃了引入消费者个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规则的尝试。有学者认为,对于没有得知诉讼信息或没有明示退出诉讼的权利人,禁止其另外提起诉讼实际上损害了《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强调的公平和公开听审的权利。〔70〕See S. I. Strong, Cross-border Collective Redress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the Face of the Brussels Regulation, 45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12 (2013).但是,欧盟法对默示加入制的排斥近年来有所松动。
在立法探索上,在欧盟方兴未艾的案件管理主义理念使其民事诉讼规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高效、便捷越来越受到重视,更强调司法效率与质量的动态平衡。代表人诉讼在瑞典、荷兰等国的兴起即是通过加强法官职权和审理集中化提高司法效率的重要表现。在荷兰《2005年集团和解法案》实施后,当事人从荷兰法院受理的群体争议案件中获得的总赔偿数额位于欧盟成员国之首。〔71〕参见纪格非:《案件管理与一体化背景下的欧洲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发展动向》,载《东方法学》2019年第4期,第114、122页。由法律授权行政部门或社会组织作为代表人提起具有公益性质的不作为之诉已被大多数成员国接受,如果未经权利人明示授权的代表人诉讼得以在不作为之诉中适用,那么在损害赔偿之诉中不可适用默示加入制的论断也就开始松动。在原告组织形式上,2013年《欧盟集合救济建议》依据成员国的实际仅规定了明示加入制,但根据2018年《评估报告》的统计,奥地利、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立陶宛、马耳他、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和瑞典仅采取明示加入制,比利时、保加利亚、丹麦和英国则根据案件类型区别适用明示加入制和默示加入制,而荷兰和葡萄牙仅采取默示加入制。2020年《欧盟代表人诉讼指令》考虑到成员国立法的差异短期难以消除,在重点推动成员国纳入明示加入制的前提下,由各国自主决定采取何种形式,同时也规定住所地位于法院地国之外的消费者须适用明示加入制,但对住所地在法院地国的消费者采用何种程序则没有限制。
默示加入制在代表人诉讼中的适用也在欧陆法学理论上得以论证,即为了实现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民事诉讼法并不排斥对诉讼处分权予以一定限制。首先,依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之理论,基于私人主张权利的行动虽出于主观自利动机,但也会产生客观公益效果。〔72〕参见[德] 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1-34页。其次,海茵•盖茨认为,近代自由主义法学理论并未否认损害赔偿民事诉讼与公共利益具有的密切关联性。〔73〕参见[德]海茵•盖茨:《为公共利益诉讼的比较法鸟瞰》,载[意]莫诺•卡佩莱蒂编:《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刘俊祥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即在救济个案当事人权益的同时,起到威慑违法行为人及其同类不再实施违法行为的效果。〔74〕参见赵红梅:《经济法的私人实施与社会实施》,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第179页。尤其是在反垄断诉讼中,惩罚性赔偿和禁止令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提供私人救济,还包括对市场秩序的维护。最后,伯恩特•吕特斯认为,法教义学除了强调形式逻辑外,也具备价值判断和确定的规制目标,〔75〕参见[德]伯恩特•吕特斯:《法官法影响下的法教义学和法政策学》,季洪明译,载李昊、明辉主编:《北航法律评论》2015年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42页。这意味着其也具有体系内的反思和批判功能,即从新的社会现实与需求中发现应被法律认可的普遍价值,例如获得立法认可前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并促使此等价值在立法或司法层面中得到认可。
因此,诉讼处分权并非具有绝对性,随着正义观念的拓展、公共利益观念的构建和国家职能观念的更新,限制诉讼处分权的伦理基础开始形成。〔76〕参见李国海:《反垄断法公共利益理念研究——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中的相关条款》,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第19页。民事诉讼中包含了当事人主义和法院职权主义的内容,但默示加入制代表人诉讼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在实现大规模损害赔偿救济、撇去非法所得和禁止违法行为等功能之外,还具有威慑违法行为、规范市场秩序、增强消费者信心等公益效果,因此相对来说包含了较多法院职权主义的内容。〔77〕参见邵明、常洁:《民事诉讼模式重述——以公益和私益为论述角度》,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102-105页。默示加入制对当事人诉讼处分权进行限制的正当性来源于程序保障,即被代表人的利益与立场已经通过代表人诉讼得以实现,并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被代表。〔78〕参见黄国昌:《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270页。
(四)复合通知:默示加入制程序正当性的技术保障
在以听审权为核心的程序正当性考察中,一般要求尽量将诉讼信息通知所有当事人。诉讼通知也属于公民知情权的范畴,部分当事人虽然实际上难以或不愿参加诉讼,但保障其知晓并参加诉讼的权利也被视为达到了其参加诉讼的目的。〔79〕参见[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当事人之间一般在损害事实发生前不具有实际联系,只因为共同的法律或者事实问题而联系在一起,救济内容也参差不齐。确保向当事人通知起诉、和解、承认对方当事人诉讼请求和撤诉等信息,并由其决定是否退出诉讼,使得诉讼结果能够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这也是使当事人受默示加入制约束的正当性前提和法理基础。
消费争议的当事人通常在地理位置和职业领域等方面具有分散性,客观上难以明确每一位当事人的姓名和地址以进行直接通知,在一般情况下多采取公告方式,在不产生不合理费用的情况下才考虑特别通知。在现代化电子信息技术得以充分应用的前提下,公告通知开始展现更多元的有效形式。美国法院普遍采取传统纸质邮件、媒体和电子信息技术相结合的综合通知方法。〔80〕See Juris v. Inamed Corp., 685 F. 3d 1294, 1319 (11th Cir. 2012); In re Oil Spill by the Oil Rig “Deepwater Horizon”, 910 F.Supp. 2d 891, 939-940 (E. D. La. 2012).《欧盟集合救济建议》规定在不影响诉讼的正常进行、言论自由权、知情权、被告的名誉和商业秘密等前提下,法院和代表人应在尽量广泛的范围内通知诉讼信息,并要求成员国设立全国性的诉讼登记机制,信息须客观和详细,通过电子信息平台向公众免费公开,并应当在欧盟委员会的协助下保证各成员国间的一致性和网络互联。〔81〕参见《欧盟集合救济建议》第 10、12、35、36、37段。
目前电子诉讼信息平台在我国仅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特定载体与方式,并不具有特定的法律效力,也缺乏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平台。〔82〕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课题组:《“互联网+”背景下电子送达制度的重构——立足互联网法院电子送达的最新实践》,载《法律适用》2019年第23期,第22页。在实践中,我国的证券登记结算系统为投服中心确认权利人范围提供了保障。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改革委员会”也有类似的计划,即为协助在其他法域的潜在当事人群体考虑是否加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展开的代表人诉讼程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建设专门网站以公布有关诉讼程序的信息。我国《民事诉讼法》于2012年引入电子送达后,各地人民法院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尝试。在《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出台后,最高人民法院继续深入推动电子送达、庭审记录、电子案卷等领域的改革。〔8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上海法院网”开设了“法院公告”栏目,发布上海市各级法院的诉讼文书公告送达信息;“中国法院网”设置了“法院公告”栏目,登载各级法院已在《人民法院报》刊登的送达公告。此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推动包括传统纸质邮件、媒体和专用网络公告平台、公众号、通信号码、搜索引擎、电子邮件、被告网站主页等在内的多元通知方式。随着技术的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也可以进一步推动通知方式的完善,如通过机器学习技术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记录、通过IP区域等建立数据库以确定权利人范围,并进行定向通知。〔84〕See Alexander Aiken, Class Action Notice in the Digital Age, 165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003-1007 (2017).配套技术的进步与通知程序相结合,形成功能性转换以生成有效的电子通知方式,有助于推动代表人诉讼的完善,但对于其所引发的侵犯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数据保护等问题,还需要另行研究。
因此,建议明确公告通知在代表人诉讼中的法律效力,并在人民法院信息化的现有基础上,建设专门和统一的电子诉讼信息平台。可采用电子诉讼信息平台与电商数据库对接的方式,通过数据分析锁定消费者的联系方式。可采取复合通知方法,若能从现有资料确定当事人的通知方式,如销售记录、消费者名册等,则应首先进行特别通知;对于姓名和地址不明的当事人,应在电子诉讼信息平台和在目标地区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公告通知。此外,基于程序正当性的要求,是否发出通知不应完全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建议我国法明确规定“非有充分正当理由,应当发出公告”。〔85〕《民事诉讼法》第5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79条规定,人民法院在代表人诉讼中“可以发出公告”。不发布公告的,法院应作出裁定并说明理由,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和上诉。
(五)默示加入制可能引起的滥诉问题
美国在市场管理方面注重通过监管与诉讼的双重治理,但在三权分立体制下,司法权过度争取诉讼的权力范围,从消极方面来说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滥诉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不仅出现于集团诉讼之中,在美国的一般民事诉讼中也存在。〔86〕See Frank H. Stephen & James H. Love, Regulation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Boudewijn Bouckaert & Gerrit De Geest (eds.),Encyclopedia of Law and Economics, Edward Elgar, 2000, p. 988-990.在具有普通法系传统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默示加入制发挥了较为有力的争议解决和消费者权益保障功能,但很少发生滥诉的问题。〔87〕See Rachael Mulheron, The Class Action in Common Law Legal System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art Publishing, 2004, p. 74.在大陆法系传统的立法框架和社会环境中,代表人诉讼并未发挥类似于在美国的强势作用,虽然有多个欧盟成员国采纳了默示加入制,但并未因此发生滥诉。〔88〕See Csongor I. Nagy, Comparative Collective Redress from a Law and Economics Perspective: Without Risk There Is No Reward, 19 Columbia Journal of European Law 486, 489 (2013).可见,默示加入制不会当然地引发滥诉,我国现阶段更应当考虑的是如何加以适当激励以发挥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功能,防止其遭遇《民事诉讼法》中的代表人诉讼条款事实上易于被搁置的困境。
四、结语
随着我国实体法的逐步完善,在有效实现损害赔偿的过程中,进一步保障消费者权益、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成为消费损害赔偿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功能目标。在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机制设计上,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依据任意诉讼担当理论,消费者的诉权在由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提起的特别代表人诉讼中得以实现和保障,同时针对消费争议的特殊性以默示加入制提高司法效率,并以基于电子诉讼信息平台的复合通知方式保障权利人对诉讼的知情权,其有权决定是否参加诉讼,可满足默示加入制的程序正当性要求,集合诉讼请求以一揽子解决争议。其次,特别代表人诉讼机制不仅可以有效地实现扩散性的消费者权利保护,还可以激活现有的普通代表人诉讼。通过发挥特别代表人诉讼判决的示范效应,消费者可以选择明示退出特别代表人诉讼,提起个别诉讼或普通代表人诉讼,并可参照特别代表人诉讼判决制定诉讼策略、援引判决内容和达成调解协议,以降低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个别性实现的成本。再次,应完善消费公益基金机制,研究“非限定还原”理论,〔89〕See Antonio Gidi, Class Actions in Brazil – A Model for Civil Law Countries, 51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340(2003).考虑设置将判决的赔偿金在补偿消费者损害和支付诉讼费用之后,剩余的部分转入消费公益基金的机制,专款专用,支持包括代表人诉讼在内的公益保护措施。最后,建议规定经法定数目的消费者申请后,消费者协会决定不予提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应书面说明不起诉的理由,并且将特别代表人诉讼作为消费者协会履职考核的计分项,以激活诉讼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