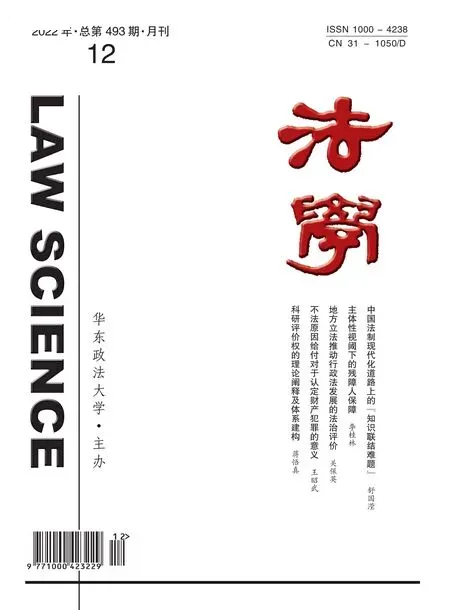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上的“知识联结难题”
—— 一种基于知识联结能力批判的观察
●舒国滢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因此,中国法制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整体现代化〔2〕从后发国家的视角看,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法制向现代法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内容包括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其核心和基础在于现代“工业文明”或“工业化”。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27页。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它并不是指现代法治本身的现代化,而是指“中国以建构和实现法治为目标的法律制度现代化”,即实现法治作为目标内嵌在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之中。本文的重点是,基于知识联结能力的批判视角来探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法制现代化道路上遭遇的“知识联结难题”,以及破解该难题所需要的智识条件。对于这样一个涉及众多复杂因素/变量之主题,若不放宽历史视界,而采取任何简单观念的历史观察方式,或者采取短时段的事件历史之评判,都远不够达到认识的目标,不能使人真正把握问题的重点,而且可能导致对中国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法制现代化过程的误读。
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肇始:因应时局的方式
从存在论角度看,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经历过像欧洲近现代社会那样一个“现代化”的时间过程,〔3〕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经历了“现代化”过程,现代性社会最早起源于西方(欧洲)。参见金观涛:《历史的巨镜》,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现代化”是中国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被迫开出的一个历史议题。〔4〕确切地说,“现代化”是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之“西化”论中逐渐引出的一个概念、观点和话题。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87页。这应当是我们研究中国法制现代化问题所持的基本观察态度和理论姿态。
从文化形态上看,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某种“鲁棒性”(robustness)〔5〕在计算机科学中,所谓“鲁棒性”,也指控制系统在一定(结构、大小)的参数摄动下,维持其他某些性能的特性。根据对性能的不同定义,可分为“稳定鲁棒性”和“性能鲁棒性”。参见张宪民、陈忠主编:《机械工程概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9页;赵长安、贺风华编著:《多变量鲁棒控制系统》,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特征,其制度、文化和国民生活习性始终保持一种稳定性结构,具有几乎不受外来文明干扰或更改的能力。〔6〕金观涛和刘青峰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结构的不变性与王朝的周期性更替是共生现象,形成一种“儒家意识形态”“大一统帝国政治”“地主经济”三元一体的社会结构的稳态(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这是其区别于其他轴心文明的宏观特征。参见金观涛、刘青峰:《中国思想史十讲》,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95-96页。自秦统一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仅有“建立—兴盛—衰亡”的“王朝循环”周期,但王权易主并不影响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一脉相承。〔7〕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88、530页。这可能是因为中国自有周以来即奉行一套“华夏文明”所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及“帝国社会”的自我解释体系。〔8〕“帝国社会”的自我解释一语,参见[美]埃里克•沃格林:《秩序与历史(卷四):天下时代》,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374页;桑兵:《华洋变形的不同世界》,载《学术研究》2011年第3期,第89-91页。中国人持有“傲视四方”的“天朝上国”心态和“夷夏之防”“以夏变夷”理念,〔9〕在古代中国士人看来,“天下”有“万国”,万国的中心是“中国”,即“中央帝国”(或“中央之国”)。中央帝国的君王——“天子”是“天下之王”“万王之王”。参见范忠信:《国家理念与中国传统政法模式的精神》,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1期,第145页。康有为于1895年5月在“上清帝第四书”中曰:“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故于外无争雄竞长之心,但于下有防乱弭患之意。”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载《康有为政论集》(上册),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1页。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国家”——“天下国家”观念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所处的地理优势。中国长期控制东亚大陆并远离其他古典文明的中心,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造成体制威胁的外来挑战。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30页。其古代的“空间意识”以王畿为中心,根据部族亲疏关系、文化水平、地理远近等因素来构成以京师为中心并由此展开不同等级的辐射状之“天下秩序”,形成大小不同的地域与文化圈。
这些不同的文化圈适用不同的法律,比如甸、侯、绥、要诸服适用“国内之法”,荒服“不制以法”,即不以“国内之法”强逼之,而“听从其俗,羁縻其人”。唐人韩愈谓之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0〕[唐]韩愈:《韩昌黎全集》卷11,世界书局1935年12月印行,第191页。这种天下法秩序观与近代(欧洲)国际法原理是不一样的。〔11〕参见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267、269、290-291页。当然,以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和文化为基础形成的法文化圈(“中华法系”)亦与经受过欧洲近代大学法律教育的浸润、思想文化运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近代自然科学精神勃兴、启蒙运动等)的涤荡,以及受工业革命、社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影响的两大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法律价值、制度理念、法律原则、概念,以及法律思维和法律技术等方面存在着文化性质、继受(传播)方式和范围上的差异。
如果没有近代以来世界在诸方面大格局的改变(15—17世纪地理大发现,海洋航路的开辟,资本主义兴盛,海上贸易发展,欧洲殖民主义蔓延等),如果没有某些特殊历史事件的介入,中华法系和西方的两大法系之间本可以像以前的若干世纪那样,依靠历史上形成的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文化阻隔带”并按照惯性保持和发挥其各自地理上的文明效能(或文化影响力),换言之,中西之间由于这种文化阻隔本不会发生法律文化上的实质性接触,也不一定能够产生法律文明上的冲突,以及因为这种冲突而使中国传统法制文化和法律技术(律学)遭遇从未有过的严重挑战,继而不得不在法制发展道路上作出痛苦的方向性调整,不得不尝试通过“移植”来接受中国人在历史上未曾见闻的完全属于“异类”的法律文明。
由于19世纪中后期整个世界时局的骤变,中华帝国作为有数的几个疆域辽阔的传统帝国被“猝不及防”地拖进了由西方(欧洲)世界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中心”)和这些传统帝国(“边缘”)之间双向的秩序关系,因而也具有了此前不曾具有(与欧洲列强殖民地之现代化不同)的世界史的意义:现代世界体系在改变着这些处在“前现代”时间结构中的传统帝国,这些“前现代”的传统帝国在被现代社会改变的过程中,其未被完全改变的传统文化也反向影响着整个世界的格局和世界体系的重构(“现代化的双向对流影响”)。值得玩味的是,一定程度上受传统帝国文化影响的现代世界体系又以新的“混合文明形态”〔12〕新的“混合文明形态”所要描述的是一种包含有(时间结构意义上的)“传统”/“现代”与(空间结构意义上的)“中心”/“边缘”文明因素的一种新的世界文明类型,其可能杂糅不同类型的社会理想(主义)、信念和价值观追求,难以归结为某一特定的地域文明类型(如欧洲文明、东亚文明)或体现某一单纯的社会理想的文明类型(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影响着这些后发的传统帝国社会的现代化(包括法制现代化)进程。上述“多重历史—文明之交叠层垒”现象是我们考察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背景,其中交织着诸多复杂的历史因素和影响历史的社会变量。
就中国的情形而言,应当承认,最初被拖进现代化历史中的国人是不可能完全看得清楚这个历史局面的。那时,清王朝处在内忧(农民起义)外患(外敌侵略、殖民)的危局之中,古老的中国在地理视野、历史感受、文化价值观,以及政制、法律和学术等方面均面临“不可思议的”“陌生的”泰西(西方)之异质文化/文明的冲突与挑战,故而从建立在中国古代“空间意识”〔13〕卡尔•施米特说,不同的空间对应不同的生活方式:“大都市里的居民对世界的看法与农民不会雷同;捕鲸人的生活空间与歌剧演员也截然不同;在飞行员的眼里,世界和生活不仅呈现出另一种样子,而且具有另外一种维度、深度和视野。当事关不同的民族和人类历史的不同时代时,空间意识的差异就更深且巨了。”[德]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考察》,林国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5页。基础上的“天下观”的“中心”(王畿/甸服)逐渐沦为世界的“边缘”(荒服),变成了被近代新国际秩序构成的“世界体系”遗弃的“孤岛”和西方列强(借用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的用语:“海上的兴风作浪者”或者“海狼”〔14〕同上注,第25页。)打着“文明国家”的旗号(携带着“基督教—欧洲国际法”)纷至沓来以(中国人视角的)“狼道”(即“人与人之间像狼一样”[homo homini lupus])方式强占地盘、哄抢宝藏、争食猎物的“失去栅栏的土地”(自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在下面这一点上达成了默契,即把地球上欧洲以外的土地当作殖民地,当作征服和盘剥的对象,所以自此以后的时代也可以称为“欧洲人的土地占有的时代”,19世纪后期中国的土地变成了欧洲人之“能量、行动和建功立业的力场”〔15〕同上注,第 47、67 页。)。从海上侵入的西方列强通过强行征服而制造的“空间混乱”(raum-chaos),以及由此在中国人之中形成的错乱的“空间意识”使整个清帝国处在与西方世界的敌对性惶惑、恐惧不安的生活状态之中,〔16〕借用卡尔•施米特对古代帝国的评价,我们也可以说,过去的中华帝国如同其他古老帝国一样,把自己“视为整个世界,自视为宇宙和家园。这个世界之外的大地部分,如果不构成威胁,则要么觉得无关痛痒,要么视为罕见的珍奇;如果构成威胁,则视之为邪恶的混乱体……”而事实上,“16—20世纪的欧洲国际法,将欧洲基督教国家视为整个世界秩序的创造者和承担者。‘欧洲标准’被认为是当时的常态标准,理所当然地适用于世界其他板块。所谓‘文明’即被等同于‘欧洲文明’。在此意义上,欧洲依然被看作世界的中心。”“直到1890年,主流观点仍然认为国际法就是专指欧洲国际法……因此,所谓‘人类’主要被理解为欧洲的人类,……‘进步’即是指欧洲文明的直线发展。”在此背景下,1840年鸦片战争(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清帝国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其“(固有的)世界之外的大地部分”(特别是欧洲,甚至也包括自己的近邻——日本)正在涌动的力量对自己构成的“威胁”,并因为这个巨大的“邪恶的混乱体”正在使用“狼道”(lupus)、而非“人道”(homo,即人与人之间像人一样)的方式。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大地的法》,刘毅、张陈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5-56、66、208-209页。对自己的内在秩序造成威胁,从而陷入全面的混乱。有关人类历史的动力和力量而产生的“空间革命”。参见[德]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世界的考察》,林国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5-36页。其所面对的选择性难题是:中国作为“基督教—欧洲国际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客体,要么接受欧洲文明(被迫纳入由欧洲列强主导的“世界国家秩序”),要么只能降格为一个殖民地民族(或者作为文明化民族的殖民地性质的被保护国)。〔17〕[德]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考察》,林国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44、46页;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与此同时,帝国社会内部也出现了变革的呼声,大一统之“超稳定结构”开始出现松动,其中孕育着由农业文明/传统(固有)文化向工商文明/现代化(舶来的)文化转型的深层的阵痛性危机和融入陌生、未知之世界体系的普遍焦虑,帝国的精英们由被迫“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兴办洋务洋学,变法实行新政,救亡图存,再后泛行“新文化运动”,乃至试图采取灭祖断根式“全盘西化”(用西方法律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法律)或彻底改变“祖宗之法”的应策。〔18〕参见李贵连:《晚清立法与日本法律专家的聘请——以梅谦次郎创办的法政速成科为中心》,载日本法政大学大学史资料委员会编:《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裴敬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页编者序。传统中国的法制连同其固有的经济结构、皇权体系、意识形态和以村落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形态,在内外综合压力之下逐步解体。〔19〕参见徐忠明:《西方市民社会与现代法制建设及启示》,载《政法学刊》1995年第3期,第24页。从此,世界“法律地图”发生了结构性改变, “中华法系”作为一个法律文化圈的地理概念已经名存实亡。
由此观之,中国走上法制现代化之路,并非出自完成现代文明转型的自觉,而完全是仓促因应时局的一种应急策略选择,此种现代化属于“外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即一种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受外力冲击、外部刺激而引发的兼有“突发性”和“应变性”的现代化。其特征是面对可能“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以“救亡图存”为近因,以实现“富国强兵”为目标。〔20〕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4-125、131、532页;徐忠明:《西方市民社会与现代法制建设及启示》,载《政法学刊》1995年第3期,第24页;杨耕:《传统与现代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载《哲学动态》1995年第10期,第27-28页。或者说,在当时的危局(“国势蹙迫”)下,帝国上下把“现代化”仅仅作为一种实现“富国强兵”“(与)列国竞长”“为政于地球”(康有为语)的实用主义工具性路径,作为“以列国并立之势”(与西方“并驾齐驱”)进入现代的单向度之目标追求,其中透显出仓促应对外部世界之窘迫、无奈和焦躁。〔21〕仲伟民认为,面对1840年以来从未遇见过的强敌(粤语时称“番鬼”[The Fankwae]),清政府最初的应对策略不过是祖先留下的两个办法,一是“华夷之辨”,二是“孙子兵法”。二者既有关联,也有区别。前者的逻辑指导我们要“驱逐鞑虏”,后者的逻辑指导我们“驱逐鞑虏”的具体做法。这种战略的荒谬与战术的愚蠢,导致我们在战争中不仅一败涂地,而且屡受屈辱,颜面尽失。参见仲伟民:《孤立于世界的悲剧与灾难——由“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看19世纪真实的中国》,载《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第102页。
这种窘迫、无奈和焦躁无疑传导给了以后百年的中国历史,也给中国法制现代化历程打上了一种浓厚的激进主义历史底色,〔22〕罗荣渠先生指出,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均具有重大意义的20世纪有三大特征: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发生巨变、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世纪;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社会震荡最剧烈、最不稳定的一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各国革命,自由主义衰落,法西斯主义一度兴起,苏美冷战,原子弹威胁,等等);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意识形态斗争最剧烈、思潮变化巨大、技术知识(机器人、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猛增、信息传播最快的一个世纪。而在这个世纪的前半叶,中国面临“双重危机”(民族危机和国家重建危机),历史发展欲速则不达,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激进主义趋向。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23-425、502-511页。呈现为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在中国社会内部,存在着“变”与“不变”、激进和保守两种势力〔23〕同样,1940年以降,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过程中也凸显出一个重要的特征:一方面是使中国法律外倾西方化的“变”,另一方面又是使被引进和移植的法律内倾中国化的“不变”。参见张晋藩:《“变”与“不变”:20世纪上半期中国法律近代化转型的趋向问题》,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第5页。(激进派和保守派有关“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相互角力,此消彼长。这种社会内部诸种力量的互耗,反而使中国在现代化(包括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时行时停,有时甚至行一退二,步履艰难,一波三折,总体上处在崎岖的道路之上,这一历史呈现为一种“被延误的现代化”(the delayed modernization)。〔2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50、253页。
二、中国法制现代化被延误的知识因素:知识联结能力的历史限制
(一)被延误的法制现代化
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那些在地理和人口规模上体量较大的国家/帝国)一旦选择“现代化”(包括法制现代化)作为自己重新“进入世界”和“打开世界”的方式,它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不再是一个可以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舒舒服服”的“自我制度实验”、自我发展经济和“文化再造”过程,而必须是“以世界作为整体政治—社会单位”(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所代表的“世界”,有学者提出“世界共和国”[Weltrepublik]概念〔25〕Otfried Höffe, Vision Weltrepublik. Eine philosophische Antwort auf die Globalisierung, in: Winfried Brugger, Ulfried Neumann, Stephan Kirste (Hsg.), Rechtsphilosophie im 21. Jahrhundert, Suhrkamp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8, SS. 380-396.)来部分地参与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进程。应当看到,这里存在着希图走现代化之路的国家与外部世界(尤其是那些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互视”或“双向的对流认知(解读)”:外部世界审视和认知(解读)试图实行现代化的国家,后者亦审视和认知(解读)外部世界(既以外面的世界为观察对象,也以世界的眼光[他者的眼睛]反观自我),由此而形成“对世界的知识”,以及借由“对世界的知识”而产生的“对自我的知识”(反射性自我认知/反观知识)。显然,试图走现代化之路的国家的“双向知识”(“对世界的知识”和“对自我的知识”,尤其是如何对待需要借鉴的知识和如何对待本国的传统〔26〕如钱穆先生谈民族自我认知的意义:“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钱穆:《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载《看历史》2013年第7期,第114页。)对于它们实现现代化目标而言是异常重要的。
如前所述,从客观方面看,中国自1840年以来出现“被延误的现代化”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晚清民间起义,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自强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皇权帝国解体,国民革命,军阀割据,土地革命,日本侵华,战乱频仍,政局长期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儒教文明崩坏,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人口增长,疾病(瘟疫)蔓延,传统小农经济封闭,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村普遍贫困化,城乡差距拉大,工业基础薄弱,工商业依附政治权力,工业资本积累严重匮乏等。〔27〕参见雷颐:《被延误的现代化——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载《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3期,第4-11页;初新才:《1911-1949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延误的原因》,载《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第23-27页;石冬明:《传统社会结构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28-31页。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的破坏,国家主权与统一的破损,社会秩序的混乱,大量资源的破坏与浪费,民族精神的损伤,从而减损了中国现代化的驱动力。〔28〕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55-356页。按照罗荣渠先生的描述,这个百年的历史过程伴随着统治的衰败,“半边缘化”(半殖民地化)和中国原有历史的中断,病急投医,模仿和抄袭各种外来的现代化方案,为引进现代文明的创新而丢掉既往文明的更新,在抄袭外国和回归传统之间摇摆不定,杂乱无章,从而延宕了中国的现代化。〔29〕同上注,第254-255、350-351、358页。
比较而言,中国法制现代化作为中国整体现代化的一个部分,其发生的时间相对较晚,被延误的原因亦更为复杂。总体来说,在一个有古老法律文明传统的国度,法律不可能主动担当改变“社会文明类型”的角色(只有列强在其殖民地才有可能因为统治和殖民的需要而下令废除殖民地原有的法律,强制推行自己的“文明”法律,来改变殖民地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而是有选择地、渐进地因应社会本身的变化。所以,不是古老的法律会突然毫无理由地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而往往是突然(至少部分地)变化了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要求原有的法律必须改变,即社会推动法律变革(“变法”)。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近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变化的外部因素和“中国问题”(特定国情)内生的特殊原因打破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变法”在所难免,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30〕参见张晋藩:《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1期,第4-6页。
尽管如此,关于如何“变法”,这里有三个基础性立论需要确立:第一,中国法制有一个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现代化问题;第二,中国法制现代化存在着一个实现现代法治的“理想图景”或“理想目标”;第三,清末以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特殊的历史事件,上述“理想图景”或“理想目标”在某些历史阶段并未实现,故而存在所谓的“法制现代化被延误”现象。
第一个立论表明:中国要实行现代化,不可能直接依靠传统中国未经过任何转型或更新的旧法制来达到目标,借助传统的旧法制不可能使中国社会“自然进化”为现代法治社会。〔31〕参见信春鹰:《从艰难与挫折中走向辉煌——20世纪中国法治发展回顾与未来前瞻》,载《清华法治论衡》2000年第1期,第514-515页。换言之,从传统中国的法制中不可能径直开出现代化议题,当然也不可能将它作为推动和保障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工具。但在这个立论上有可能存在另一个完全相反的意见,在该立论的实际的和潜在的反驳者看来,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与其法制现代化没有直接干系,或者说作为工具意义上的传统法制与现代化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对立,〔32〕罗荣渠先生指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历史连续性的破坏与延续的深刻矛盾运动。这意味着中国走现代化之路,也不能完全抛弃传统(当然包括中国传统的法制),不能打断历史的连续性。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57-358、361页。但笔者认为,这里的核心问题在于:当旨在“规划”未来可欲的“可能生活世界”之现代化改革方案与作为“既有的制度事实”的传统之间的矛盾如果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可能就有一个“取一舍一”的选择。两者之间反而有可能存在相互联结的方式和方法。照此理解,法制本身无所谓现代化,“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伪命题。这无异于说,“旧瓶”完全可以装“新酒”,不论是“新酒”还是“旧酒”,都不能缺少作为盛酒容器的酒瓶,而酒瓶本身无所谓新旧。
不过,对于第一个立论的反驳性意见会遭到第二个立论的理论审查。第二个立论引出“实现现代法治”的话题,实际上就等于否定了“‘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伪命题”的判断。如果说,中国法制现代化是“以建构和实现法治为目标的法律制度现代化”,那么,由于传统中国旨在维护“王道大一统”的旧法制与“现代法治”在价值目标和法律精神上的扞格不入,它对于以现代法治为原则的现代制度文明实际上缺乏解释力和论证力;而任何一个旨在实行现代化的国家均必须以法治化,即以实现现代法治价值和法治精神、建构法治制度为其鹄的,〔33〕与传统的法制相比,法治价值和法治精神所体现的是一种全新的法律世界观,这种不同于古代社会的法律世界观与发生在近现代科学的、哲学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中重要的转变(比如,从人类整体主体性转变为人类个体主体性,故而尊重个人的尊严、生命、自由、财产,以及强调人人平等)高度契合,尤其适合于为在实践中建构现代法律价值和法律制度奠定基础。参见[澳]G.德•Q.沃克:《法治的危机——危险与机遇》,李小武、吴伟光译,载《清华法治论衡》2000年第1期,第456-457页。这就在传统中国法制与社会现代化之间划出了一道需要逾越的鸿沟,传统中国法制不可能不经过任何(思想—知识上的)更新或转型而直接与现代化发生联结,并且径直作为社会现代化的“合法性”基础和联结的“桥梁”。
至于是否有一个实现现代法治的“理想图景”或“理想目标”,这个问题的讨论并不是辩护性的,也不是纯理论性的,而是实践性的。说它不是辩护性的,是因为这个主题即使内含有对诸如“‘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伪命题”之类判断的反驳,但其本身的立论要义在于寻找实现法治的“图景”或“目标”,其主旨并不在于对其他议题的反驳或辩论,以维护自己的立论。它不是纯理论性的,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要从理论上“说明”实现现代法治的“理想图景”或“理想目标”的一般(普遍)标准,或者在理论上把作为借鉴/移植对象(即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个或某一些现代法治文明类型不加反思地确定为本国实现现代法治的“理想图景”或“理想目标”。这些都不是讨论该问题的正确方式。只有将实现现代法治的“理想图景”或“理想目标”作为一个实践性议题才是正确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这样一个准备“计划”投身于现代法治建设的“内在参与者”必须从实践层面寻找到一种切合其自身“国情”的法治“图景”或“目标”,而且从其“内在的观点”来看是“符合实践理想的”。
故此,当传统中国的旧法制作为一个制度体系失去了直接作为晚近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合法性”基础并作为联结桥梁后,如何走现代法治之路,寻找既切合中国实际又“符合实践理想的”(可欲的)法制现代化方案就变成了中国平顺地完成由古代“农耕文明”社会向现代“商工文明”社会的转型,〔34〕参见张恒山:《论文明转型——文明与文明类型》,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0年第32期,第19-21页。并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历史任务。
(二)阻碍法制现代化的“知识联结难题”
重启现代化并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任务涉及处在各个不同历史时刻的当事者或当局者以什么样的知识来对其所处的“当下历史的局势”作出何种判断,这个判断可以被简称为“当下历史判断”。在这里,“当下历史判断”本身并不重要,以什么样的知识进行此种判断才是“在实践上重要的”。道理很简单:基于错误的知识或不适当的知识只能导致错误的或不适当的“当下历史判断”,而根据这种判断就不可能寻找到既切合实际(国情)又“符合实践理想的”的法制现代化方案。只有基于正确的或适当的知识才有可能找到可欲的法制现代化之路。显然,若深入研究此问题,就必须回到上文提及的“双向知识”的讨论。
检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我们似乎隐约地看到:处在各个历史时刻的当事者或当局者所作的“当下历史判断”总是或多或少表现出某种“片面性”和“短视性”,他们看起来都来不及与外部世界进行足够充分的“双向的对流认知(解读)”(“文化互视”),有时欠缺必要的“对世界的知识”,尤其是缺乏有深度的“对自我的反观知识”。也就是说,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道路上总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知识联结难题”:这个难题表现为在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主题上的诸种知识之间难以形成对接,即存在着联结的困难。
从理论上看,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议题,至少有以下六类知识(如果加上时间/历史和空间/地域等认识对象,尚可作更为细致的知识类型分解)值得在理论上加以重视:(1)域外世界(这里主要是指中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作为构成单位的“世界”)以“内部参与者”角色所形成的有关其各自历史上和当下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之自我认知的知识;(2)域外世界中一些后发国家或地区以“外部观察者”或者有时以“内部参与者”角色(这主要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对于其曾经作为“模范”对象移植而来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之认知的知识;(3)域外世界作为“外部观察者”对于中国历史上和当下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知识;(4)中国作为“外部观察者”对于域外世界历史上和当下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知识;(5)中国作为“内部参与者”对于中国自己历史上和当下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知识;(6)中国既作为“外部观察者”,也作为“内部参与者”对“作为整体政治—社会单位”(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世界”的法律制度(国际法律规则)的知识。
第一类知识之所以对中国法制现代化是重要的,在于中国人应当像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和伍廷芳等人在主持变法修律时那样,透过域外世界的自我法律知识找到“折冲樽俎,模范列强”的方式。也就是说,域外世界的自我法律知识是中国人设计自我法制现代化方案参考的基础,即要了解“法治典范国家”及其“法治模式”,必须先了解“法治典范国家”的自我法律知识。
第二类知识包含那些移植“法治典范国家”及其“法治模式”的后发国家或地区对于其所移植的他国历史上和当下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认识。〔35〕第二类知识是清华大学法学院张明楷教授在2021年10月13-15日召开的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上对于笔者所做的学术报告进行评论时提出的。对于张明楷教授就本文论点所作出的实质贡献,笔者特致以诚挚的谢意。后发国家或地区对于所移植的法律经历过实践尝试,由此而经历过较长时间的文化过滤和文化调适,其中不乏化解本土法律制度、法律文化与所移植而来的异质法律制度、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矛盾的成功案例,也可能具有实践尝试不成功的个案及经验教训。这些成功和不成功的案例对于中国法制现代化方案的选择和设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类知识乍看起来与中国法制现代化无关,但它实际上在两方面会产生相关的影响:第一,域外世界对中国法律的正确知识或错误知识会使域外世界的当事者或当局者对中国进行的法制现代化方案具有不同的认知态度、判断和策略,这反过来又作用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展的方式;第二,域外世界对中国法律的知识也会被中国人用来作为认识自己历史上和当下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无反思性知识(比如,对待亚细亚[包括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西欧学术界有一种正统的观念,即“东方专制主义”;对此,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 于1957年著《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提出一套“治水社会”的理论,对此,中国理论界中至今仍有相当部分的信奉者〔36〕参见[美]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奚瑞森、邹如山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第36-55页。),或者相反,中国借助域外世界对中国法律的知识而产生某些极端敏感的反思性知识,这些知识既可能是对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之极端“否定论”和“悲观论”,也可能是完全盲目自大的“独尊论”和“优越论”。毫无疑问,第三类知识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完全可能发生实践上的溢出性效应。
第四类知识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学习、模仿(模范)现代法治模式的必要知识前提。没有对域外世界的自我法律知识(特别是对那些拟作为“模范”对象的“法治典范国家”法治化[包括经验和教训]历程的自我总结和评价知识)全面深入的了解,中国在走法制现代化之路时其实难以找到正确、合适的“路标”,因为此时中国有可能不清楚存在哪些“法治典范国家”及其“法治模式”,应当以什么样的“法治典范国家”的“法治模式”作为“模范”对象。诚如前述,在此情形下,中国靠完全封闭的“自我制度实验”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第五类知识对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一个有着悠久的文明传统、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多样及各地发展不平衡的泱泱大国实行任何“变法”都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在此方面,无论怎样强调我们自己对于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了解都不为过,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实行“新政”“新法”都不可能抛开自己的“本土资源”,而强制推行一种与本土制度文化无关、完全异质的“自我殖民地化”式的所谓“先进制度”。〔37〕梁漱溟先生很早就注意到:近代中国向西洋学习着挫败,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走向富强,反而加深了国人水深火热的生活。其原因在于:西洋文明的模式在中国不可复制,西洋文明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参见颜炳罡:《人类文明的中国模式何以可能——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实质及其当代意义》,载《文史哲》2021年第4期,第149页。只有通过“对于自己传统法律的知识”,深入了解本国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之“土壤”性质,才会找到与需要“移植”的“先进”法律进行嫁接的可能性。故此,在模范“法治典范国家”的法治时,应当知道如何将这种“模范”行动与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制文明传统进行合理审慎的对接,避免走“变法”的弯路,否则就会由于法律嫁接不当造成法制现代化方案“实验,失败,再实验,再失败……”之过程的恶性循环,或者因为新旧法律之间的剧烈冲突导致法律发展之历史连续性的破坏和社会持续性的动荡不安,有可能为之付出沉重而惨痛的社会—历史代价。〔38〕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60-361页。
第六类知识问题在近代中国初走法制现代化道路之时即已存在,但在当代,该问题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形成的世界体系(尤其是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 所确立的世界体系,简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强调和平商议、协调解决国际争端,因而成为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奠基石)自觉不自觉地把近代和当代的各个国家强行纳入统一的“世界国家秩序”中,〔39〕近代世界体系发展的总趋势是:在各国关系中,文明的进展可以被认为是“从武力到外交、从外交到法律”的运动。See Louis Henkin, How Nations Behave: Law and Foreign Policy, 2d e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9, p. 1-400.将主权国家逐渐变成了“整个世界的一部分”。有人甚至把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表看作“法的世界化”(“法律世界化”或“法律全球化”)进程开始的标志,认为这个宣言显现出“非排他的全球”“承认所有文化的全球”性质。〔40〕参见[法]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法的世界化——机遇与风险》,卢建平译,载《法学家》2000年第4期,第114、116页。无论如何,现代世界体系以其不可阻挡的力量将它的国际法治秩序及其(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西方价值的)“文化选择”强加于国际社会的各个成员国家,这也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历史性条件”。作为置身于现代“世界结构”之中的中国已经从历史上“世界游戏”的“局外人”转变为“世界游戏”的“参与者”,〔41〕黑格尔指出:“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123页。另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律哲学当下基本使命的前提性分析——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世界结构》,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第100-103页。当然也有义务了解和熟悉各个领域的国际法律规则,应当将国内法治(“国家级法治”)建设与国际法治(“国际级法治”)建设衔接起来,不应主动放弃参与乃至主导国际社会法治秩序与“和谐国际”重新共同建构的资格,不应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的历史进程中再次失去发言权。〔42〕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认为:“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的历史进程中起重大的作用。”[美]伊•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罗荣渠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文版序言”,第2页。这像是沃勒斯坦专为中国读者说的一句客套话,但对于我们中国人的未来事业仍然不失为一种正面的期许。鉴于国际法治(“国际级法治”)有可能构成“解释、理解、合法化各国政府的政策”的一个重要指标,〔43〕See Ian Hurd,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Law and the Limit of Politics, in: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8, No. 1,2014, pp. 39-51.那么,中国对于(尤其是其中涉及联合国成员国“法治自愿承诺”〔44〕2012年9月2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国家级和国际级法治宣言》(《联合国法治宣言》)之后,又倡导各会员国可以单独或联合作出“法治承诺”,其内容包括国家行动和国家援助、条约的批准和加入及实施、国际法院管辖权的接受和判决的执行、有关防止和惩处国际威胁的措施、治理与反腐败、立法改革与发展、司法制度保障与改革、冲突和冲突后社会和平与法治建设、人权保护、性别与儿童权利,等等。参见曾令良:《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建设》,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第144-145页。的)国际法律规则的知识反过来会影响国内法治建设,影响中国内部的法制现代化进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45〕参见贾烈英:《联合国与国际法治建设》,载《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2期,第55、67-76页;曾令良:《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建设》,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第140-146页;范进学:《“法治中国”:世界意义与理论逻辑》,载《法学》2018年第3期,第3-13页。
在中国,无论走何种法制现代化道路,怎样寻求实现现代法治的“理想图景”或“理想目标”,都离不开对上述六类知识的深度了解,以及对它们进行的有效联结。现代法治的“理想图景”或“理想目标”绝不是像某种摆放在博物馆或艺术馆中的展品,随时供人们浏览、观赏。毋宁说,它们的形象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中自我展现出来的,它们的面纱在国家的法治实践/建设的时间过程之中才有可能被一丝一缕地撩开,这需要处在各个历史时刻对时局作历史判断的当事者或当局者在变动不居、波云诡谲的历史形势中对时局有清醒、客观、正确适当的判断,并准确地抓住对于其所从事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所欲实现现代法治目标极为重要而又可能稍纵即逝的“历史时刻”。
(三)破解“知识联结难题”的历史限制
对于正在进行法制现代化的国家而言,在实践上区分是否为“符合理想的”(可欲的)“法治图景”或“法治目标”,取决于处在各个历史时刻对时局作历史判断的当事者或当局者对上述诸种知识进行综合的、正确的或适当的运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具体的当事者或当局者之知识联结能力的巨大考验。当事者或当局者的知识联结能力决定着他们所欲从事的法制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决定着这种事业所能达到的文明深度和历史高度。
的确,处在各历史时刻的一切当事者或当局者都不是先知先觉的,也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他们多多少少受到其各自历史时代认识的局限。换言之,既有的复杂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之“不动的在地性”(unmoved locality)以及悠久的文明/文化传统和历史之“交叠的层垒性”,都先在地限定了当事者或当局者的意志、认识和判断的能力以及他们对诸种知识的联结能力,使他们难以摆脱历史时间结构中的“罗陀斯岛”而“自由地”跳动自我的身躯。〔46〕黑格尔认为,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序言第12页。
以如此的态度来观察中国晚近百年的法制现代化之路,或许可以让我们多了一份理解历史的同情心和洞悉历史变化的辽远感,进而从容地观照在每一个历史时刻从事法制现代化事业的当事者或当局者之所知、所思和所行,细致地捕捉历史上的行动者(实践者)之每一行动的重要瞬间,在波涛汹涌、惊心动魄的大时代中找到社会整体的“大我”与行动者(实践者)个体的“小我”之间互动的、有时或许有些曲折沉重的历史过程及其因由。
如上所述,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李鸿章所称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历史认识、判断及采取的因应策略,客观上是缺乏必要的知识准备的,更谈不上对于上述六类有关法制现代化知识的有效联结和综合运用。我们回头看中国晚近百年处在各个时期对时局作历史判断的当事者或当局者(即那些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有识之士”),观察他们的“应急”态度和时政主张(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康有为的“通三统,张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之说及“全变”“尽变”的诉求,从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全盘西化”到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和“五权宪法”,等等),〔47〕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或许也可以得到部分佐证:当事者或当局者的内心深处都存在一个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最大问题”,即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48〕梁漱溟先生认为:“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梁漱溟:《中国民族之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载《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110页。但不可否认,他们大多采取了“居中国”而“观天下”(以“一统垂裳”的世界观来解读当时的“中国”和“世界”〔49〕参见[日]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77页。)的“文化过滤”姿态(平心而论,这是那个时候任何一位思想深刻的中国思想者必然采取的一种知识态度,他们绝不会甘于做任何意义上的西方文化—思想—知识的“复读机”或“搬运工”),那么要求这些伟大的“智者”个个成为会通“中国”和“世界”(包括其中的法律)的知识“冰人”并提出一套系统的、融通古今中外且在实践上完全可行的崭新“法制理想图景”,其实是勉为其难的。
当然,如果我们把历史时距拉得更长一些来观察中国法制现代化历程,那么就可以看到,作为再认识(知识)对象的“中国”和“世界”问题并非是自1840年才开始的,其源头尚可追溯至“西法东渐”的早期历史。为说明此点,这里列举一件史料:在1662-1690年,荷兰政府曾寻求与康熙帝谈判。当时,为使清政府给予其特使外交豁免权,荷兰代表援引了《万国法》,而清朝官员对此一无所知,对于荷兰人提出的所谓国家主权平等的说法也是闻所未闻。〔50〕参见贾兵兵:《国际公法:和平时期的解释与适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直到鸦片战争前,时任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的林则徐才开始“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鸦片战争后委托好友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等。〔51〕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页。又过了二十多年,清朝才于1862年8月24日设京师同文馆,负责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之后,清政府相继在各地创办“洋务学堂”30余所。1872年后,又先后派四批幼童赴美留学。然而,直到清末变法之初(1901年前后),中国真正懂得西洋法学的人不超过3人(伍廷芳、严复、黄遵宪),故而延聘外国专家起草新法、大规模引进西方法律及法学成为当务之急,学习西法实属无奈之举。所以,蔡元培先生当时就讲:“至于今日,公法大明,苟其保自主之权,申善邻之义,国无大小,号曰对等。交涉上文明之程度,即为其国安危之所系。而我国职外交者,或通语言而昧政策,或究政策而绌语言……此译学所以亟也。”〔52〕蔡元培:《译学》(1901年11月11日),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4页。
伴随着清末改制修律及随后出现的各种社会风潮,延续数个世纪、作为古老中国法律智慧和实践知识载体的传统“律学”就像在风烛残年里过活的羸弱老人,从此倒毙在这种声势浩大的“西化”风潮之下,各式提倡“新学”的法律学堂(特别是大学的法律系)成了各种不同来路(无疑,日本在这个过程中担当着“中转站”的角色〔53〕据不完全统计,仅1909年,在我国从事法政教育的日本教习111人,其中就包括1908年10月,沈家本奏请、光绪“允之”,已在京师法律学堂担任法学教习的冈田朝太郎帮助清廷起草《刑法》和《法院编制法》,松冈义正帮助起草《民法》和《诉讼法》,志田钾太郎帮助起草《商法》,小河滋次郎帮助起草《监狱法》。在这一段时间,翻译出版的法律著作/教材也基本上是日本人的作品。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69-371页。)的西方法学法科的“试验场”,仰仗西方法学家改造中国的法律学和中国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被不同时期的中国政府聘用为法律顾问及担任中国大学法律教习的“来华外国人”以他们的非中文母语讨论中国法律制度,留有不少珍贵的所谓“局外旁观”之论,〔54〕参见王健编:《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该书收录了“晚近来华外国人”,著名者如赫德、丁韪良、庞德、冈田朝太郎、宝道等所著有关“中国法总论”“宪政建议”“法典编纂”“治外法权”“司法改革与法律教育”等方面文论共67篇。可以作为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第三类“特种”知识[其中有些作者直接以中国实行“法律现代化”为题,〔55〕如庞德著《如何使法律现代化》(1948年),霍才豪著《论中国司法改良》(1912年),等等。他们对当时中国人法学知识(尤其是对于本文所提及的“第四类知识”)的评论,认为“中国维新法学……尚在萌芽,……乃自法律维新以来,非由中国旧制自有发生,纯系采取东西洋各国巧合而成,以是知中国之法学……现尽在幼稚时代”,这些言语总体上看还是比较中肯的。参见王健编:《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160-171、591-593页。区别于那些未曾来华的西方学者如孟德斯鸠、马克斯•韦伯等有关中国传统政制的论述])。
概括地说,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孙中山语),中国的法学知识进入“西方法学的中国/汉语表达”时期,国人期待通过西方法学的汉语翻译,完成“汉语的文化符码(cultural code)”的改造和转换(“文化过滤”),革新或改造中国旧的法学,重新奠基中国人直接观察自己的“法律生活世界”的观念、态度、概念框架、知识范式和方法论,让中国人自我完成“中国法律的西方概念重构”过程,增强中国现代法学的解释能力和解决实践问题的技术能力,使自我知识完整化、成熟化和体系化,并据此实现一种新的“现代”的法律制度(法治)、法律文化/文明转型。
但“西方法学的中国/汉语表达”也同时阻断了中国对于自己传统法律的知识(即“第五类知识”,尤其是古代的“律学”知识)直接作为寻求中国法制现代化之“符合理想的”(可欲的)“法治图景”或“法治目标”的可能性,并使“律学”知识丧失了作为实践法学知识对于当时有效的法律制度的一般解释能力(the explanatory capacity),使之难以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活的”法学知识的作用,甚至难以继续维持其自身的生命力,因而造成中国传统法学的第一次学问传统的“历史/文化断裂”。这实际上是说,近代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古代“律学”任何的机会和时间,通过自我知识的更新/转型与移译而来的西方法学(“翻译法学”〔56〕1938年12月,蔡枢衡在《云南日报》撰文指出:“中国近代法学已有数十年历史, 就其内容与实质言,纵谓中国尚无法学文化,似亦非过当之论。盖中国法学文化大半为翻译文化、移植文化。”转引自杨瑞:《北京大学法科的缘起与流变》,载《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111页。)知识进行有效的联结,以“中西法律文明互补”〔57〕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思想界也有一批思想者提出中国现代化之“中西互补”论,也有学者把胡适等人的“西化”论称为“文化的自然折衷论”或者(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涵化”(accculturation)理论。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82-388页。的方式联合建构出“符合理想的”(可欲的)“法治图景”来共同推进中国法制现代化前行的进程。
接下来的法律发展史众所周知: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人民政权采取革命的方式不仅摧毁了旧政权的“法统”,而且连同“六法全书”体系之下形成的法科教育体制、培养的法律人才,以及在这个“法统”之下生成的法律精神、法律思想亦一并消解。与此同时,由“翻译法学”作为基质的所谓“新法学”知识传统在新的革命政权建立之后戛然中止其前行的步伐,“现代”的法律文化/文明转型也很快就走向了另一条道路:新中国“一边倒”政策〔58〕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文中明确提出了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的方针。该方针的提出,是由当时国际、国内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参见关锦炜:《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政策研究综述》,载《北京党史》2009年第5期,第30-34页。使其整个制度建构、经济发展和学术思想的资源不得不借鉴和倚重苏联模式。这样,新的人民政权在法学知识的联结上也出现了“全盘苏化”和全面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的“一边倒”趋势。随着1952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大学院系调整、“司法改革运动”及“肃清反人民的旧法观点”、清除旧法人员等活动,我国聘请了一批苏联法学家,翻译了一批苏联的法学论著和教科书,派遣了一批留学生赴苏学习、吸收、借鉴苏联法学,而中国近代以来经年积累起来的法学知识传统随着旧法统一起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国法学知识再次经历了一次学问传统的“历史/文化断裂”,笔者称之为“第二次断裂”,它直接阻断了以欧陆英美法学为底色的“翻译法学”本身的进一步发展,从此,革命的“斗争法学”(后来我国法学界称之为“维辛斯基法学”〔59〕“维辛斯基法学”是以时任苏联总检察长、苏联科学院院士安•扬•维辛斯基的名字命名的。维辛斯基也被称为“苏联法学界名副其实的‘教主’”,其有关阶级斗争的法学观点,长期以来构成我国“法学理论的基本精神”。参见王志华:《苏联法学家的命运(二)——维辛斯基非同寻常的一生》,载《清华法治论衡》2009年第2期,第482、485页。)的知识传统得到确立,并逐渐被奉为正宗,成为判断法学知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60〕参见杨心宇、陈怡华:《我国移植苏联法的反思》,载《社会科学》2002年第8期,第45页;张文显:《论法学的范畴意识、范畴体系与基石范畴》,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3期,第6页。
但此后的历史表明,在法学知识来源上采取全盘仿效“苏联模式”,尤其是长期固守“斗争法学”,不可能完成新中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任。
三、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的重启:破解“知识联结难题”所需要的智识条件
对于中国当下及未来法治发展而言,法制现代化道路的重启无疑是一个在时间(历史)和空间(世界)两个维度上均具有重要影响的大事件。
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的重启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一个理论反思与思想解放的过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引发中国理论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61〕参见邓加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载《博览群书》2013年第6期,第11-15页;黄力之:《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声——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回眸》,载《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6期,第111-126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将工作重点和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并着重提出了健全民主和加强法制的任务:“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62〕《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稳步推进经济、政治法律体制的各项改革,陆续提出新的治国方略和原则,从而进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快车道”:1982年《宪法》序言规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并于1999年将该项原则写进《宪法》第5条;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200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宪法》第33条第3款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2008年3月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201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6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进一步确定:“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6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乃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基于对“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6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的认识判断,而努力寻求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符合实践发展要求的法治道路,也是力图走出过往百年法律制度之曲折的历史循环,以自信、开放、昂扬的姿态主动迎接“法律入世”,〔66〕笔者赞同这样一种看法: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从被动适应世界现代化挑战到逐步主动迎接挑战的过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放性回应国际国内由历史遗留下来的及当下正在生成的诸多复杂法律问题的挑战,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法律文明伟大复兴的梦想。可以想见,这一宏伟的事业对于当下时代之正在发生变化的“法律全球化”(“法的世界化”)趋向也必将产生某种深远的影响力,必将为之带来具有相当势能的振波效应。
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的重启本身并不能用“制度实践”的行动方针直接解决上文所提及的诸种知识之间的联结难题,因为其中的一些知识类型(第一、二、三类)的变化并不取决于中国作为“双向知识”之一方主体的单方面知识态度、知识兴趣和知识取向。由此观之,在当代世界,中国除了有“经济入世”“法律入世”等问题外,还有一个“知识入世”问题(即中国知识与世界知识对接,借此让世界重新“发现中国、了解中国、认知中国”,使中国学术进入当代主流世界的知识-话语体系之中,并使之能够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展现“中国思想”“中国价值”“中国评价”“中国表达”“中国主张”)。当然,“知识入世”也应当包括我们中国的法律知识/法学知识与外部世界法律知识/法学知识之间的对接(联结),由此使中国的法律知识/法学知识进入当代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法律知识/法学知识—话语体系之中。
从“双向知识”的角度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宏伟的事业也不可能完全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的知识条件下进行。历史的实践证明:由于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由于文明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人为地阻隔中国与外部世界在法律/法学知识领域的“双向的对流认知(解读)”,像近代中国的某些历史时刻那样搞单向的“知识壁垒”,借助“斗争”和“对抗”形成“政治怨恨”,通过“错误的集体记忆”(“集体无意识”)造成“双向知识偏见”甚或“双向的文化歧视”,这种做法及其后果不可取。
的确,我们当今处在科技高度发达和资讯极度丰富复杂的信息时代,由于技术—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便利的交通而出现了时间—空间距离的“收缩”(即“时空收敛”[time-space convergence])现象,〔67〕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0页及以下。伴随全世界人口高密度往来迁徙于地球的诸大陆之间,以及航天技术将人类送入外太空,当今的人类内在地形成了一种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全然不同的地理感受,即人们愈来愈把我们生活的广袤的地理世界看作一个“地球村”,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大爆炸”之奇幻景象。尽管有如此技术的进展,尽管有世界与人类感知的变化表面上看似朝着有利于人类便捷交往(交流/沟通)方向发展的趋势,但从实质角度观察,这些技术进展和发展趋势却可能进一步加剧人类心灵深处的“被弃”的受伤感觉、不能忍受贫乏的“庸常(日常)”生活所造成的“腻烦”心理、拒绝沟通的“认知(认同)壁垒”、基于各种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信念而产生的“价值观鸿沟”,以及排斥异己(内心抵牾统一的、机械的、整齐划一的“标准化运动”〔68〕参见[美] 罗伯特•列文:《时间地图》,范东生、许俊农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的意志倾向,反而不一定能够完全消除中国和世界之间双向“言路不通”的问题。在此情形下,免不了会出现一部分国人像历史上的那些“守旧派”一样秉承传统华夏(中央)帝国的“天下观”,对一些在他们看来属于“蕞尔小国”的法治类型持有某种程度的轻蔑态度,或者反过来,一些“闭眼看世界”的外国人对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道路抱持知识上的和价值观上的偏见。显而易见,这必然会导致并加深国家、民族之间的“文明冲突”,当然不符合当代世界的“全球化”大势,也与我国正在从事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目标背道而驰。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文明交流互鉴”,〔69〕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开幕式上再次强调:“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参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版,第259-260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9-470页。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70〕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4年10月23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毫无疑问,这些高屋建瓴、思想深刻的主张为中国和世界法律知识/法学知识之间的双向联结和“交流互鉴”提供了指导思想。
若要完成中国和世界法律知识/法学知识之间的双向联结和“交流互鉴”,前提是需要对于当下中国的法律知识/法学知识的情境(context)、格局和传统有一个审慎的观察与判断,这一点同样是重要的,因为下面这个道理也很容易明白:知己知彼,不求为战,但寻互通,取长补短,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知己知彼”首先在于“知己”,不知己之短长者也不知他人之短长,且容易形成自我认知和对外认知态度的封闭。只有深入了解当下我们中国自己的法律知识/法学知识的现实情境、格局和传统,才可能找到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法律知识/法学知识之间的“话语逆差”,努力学会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方式与方法“讲好中国的故事”(特别是中国法律的故事),改变我国法学界在国际社会法律学术话语上的“西强我弱”“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被动局面,营造良好的“交流互鉴”环境条件,实现中国和世界双向法律知识/法学知识之间“不求为战,但寻互通,取长补短,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目标,逐步进入国际社会法律/法学知识界的主流。
更为重要的可能还在于“知己知彼”,深入了解当下我国法律知识/法学知识的情境和格局,了解在我国法律实践中现实起作用的法学知识传统,这对于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顺利推进我国法治建设的事业是紧迫而必要的。只有从我国法学知识的现状出发,努力通过其自身一点一滴的知识改进,稳步地将我国法学打造成为一套真正适合于我国法律实践的科学知识体系,才能够使之更好、更有效地服务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大局。如果像在“斗争法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那样,仅仅将法学当作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工具,只允许其在“政治挂帅”“政策高于法律”的话语空间寻求学科的正当性根据,以现实政治的方式和手段使其完全放弃或丧失自主的学术(科学)性格,而沦为贫血的、空洞的、暴力的词语堆积体,那么指望这样一种仅由苍白的政治话语框架构成的所谓“学问”来完成现实政治的重托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实政治摧垮法学知识和理论的身骨而又指望其以羸弱之躯担负无法承受之重,这样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在继续讨论上述话题时,笔者打算顺便讲述一则德国法学史上的有名“故事”,作为我们如何讲好“中国法律的故事”参照的例子。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法律也面临着分裂,法域分立。面对这种局面,德国的国民要求民族统一、自由及“法律事业统一化”(Vereinheitlichung des Rechtswesens)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德国到底走何种统一化道路,尤其是要不要制定全德统一的民法典,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时任海德堡大学罗马法教授安东•弗里德里希•尤斯图斯•蒂堡撰文《论通用民法对于德国的必要性》,〔71〕A. F. J. Thibaut, Ueber die Nothwendigkeit eines allgemeinen bürgerlichen Rechts für Deutschland, Mohr und Zimmer,Heidelberg 1814.以“满腔的热情”表达了“德国私法统一化”、制定“帝国统一的民法典”之必要性。他认为,对于德国市民的强化和提升而言,一部“睿智、经过深思熟虑、简单明了且富有见地的法典”(ein weises, tief durchdachtes, einfaches und geistvolles Gesetzbuch)是必不可少的。〔72〕同上注,第34页。蒂堡的观点遭到了柏林大学法学教授萨维尼的反驳,他立即写出《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 一文,反对德国制定统一民法典。其主要理由是认为德国当时制定法典的“时机不成熟”。
与蒂堡企图通过制定统一的法典来实现德国统一的想法不同,萨维尼则把“有机进展的法学”(eine organisch fortschreitende Rechtswissenschaft)〔73〕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作为实现整个国族达到共通的适当手段。在萨维尼看来,蒂堡倡言通过制定一部新法典来实现德国的统一乃在于把所有的法律均看作是来自制定法,即国家最高权力的明确规定,进而只把制定法的内容作为法学的对象。〔74〕同上注,第5页。实际上,法律像“语言、习俗和政制一样”是“有机地”成长起来的。也就是说,法律并不是通过国家意志(或立法者意志),〔75〕同上注,第11页。而是通过“内在的、默默起作用的力量”(innere, stillwirkende Kräfte)产生的,这种力量来自民族自身(“民族信念”[Volksglaube /Volksüberzeugung]、“民族的共同意识”[das gemeinsame Bewußtsein des Volkes]),〔76〕在这里,萨维尼为所有的法赋予了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基础”:通过民族的整个过去而非立法权力的意志给予法的素材,所以,“民族信念”或“民族的共同意识”才是“法的真正所在”(Der eigentliche Sitz des Rechts,法的真正本座)(Siehe Karl Bergbohm,Jurisprudenz und Rechtsphilosophie: kritische Abhandlungen, Bd. 1, Einleitung. Abh. 1, Das Naturrecht der Gegenwart, Verlag von Duncker& Humblot, Leipzig 1892, S. 487.)。应当指出,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萨维尼尚未明确使用“民族精神”(Volksgeist)一词,而更多地用“民族信念”(Volksglaube/Volksüberzeugung)这一概念。直到1840年,萨维尼才在《当代罗马法体系》第1卷第2章第7节有关“法的一般产生”(Allgemeine Entstehung des Rechts)的论述中,借用普赫塔著作《习惯法》(Das Gewohnheitsrecht, 2 Bde., 1828-1837)中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一语作为实在法产生的力量来源,由此,“民族精神”代替“民族信念”用语,成为萨维尼及其历史法学派理论中的核心概念(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System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Rechts, Erster Band, S. 14.另见Gerd Kleinheyer,Jan Schröder, Deutsche Juristen aus fünf Jahrhunderten: eine biograph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S. 354;Erik Wolf,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in: ders., Grosse Rechtsdenker der Deutschen Geistesgeschichte, 4. Aufl., S. 493.)。故此,学界认为,普赫塔最早将赫尔德所使用的“民族精神”这一术语引入历史法学派的纲领之中(Siehe Christoph-Eric Mecke, Begriff und System des Rechts bei Georg Friedrich Puchta, V&R unipress, Göttingen 2009, SS.145-153.)。故此,法律与民族的本质和性格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机的联系(organischer Zusammenhang),它的发展如同民族的任何其他取向一样遵循相同的内在必然规律:“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最终随着民族特性的丧失而消亡。”〔77〕[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在此意义上,所有的法律首先作为整个民族生命的一部分而存在,其所产生的是习惯法,而不是制定法,即习惯法优先于制定法。〔78〕萨维尼在1840年出版的《当代罗马法体系》第1卷第13节中对于立法、立法者、制定法(Gesetz)、实在法、民众法(Volksrecht,部族法)及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做了更为明确的说明。他指出,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并通过绝对力量实施的实在法称为制定法,其制定属于国家的最高权力,其内容是已经存在的民众法(部族法),或者说,制定法是民众法的机体(Organ des Volksrechts),在此,立法者处于民族的中心点(Mittelpunkt),将民族的精神、价值观念以及需求集于一身。正因如此,他强调必须将立法者视为民族精神的真正代表。总之,立法对于法的形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实在法的补充性辅助,二是作为其渐进发展的支撑(Siehe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System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Rechts, Erster Band, SS. 39-40.)。故此,法学也只能“历史地”把法律看作有机生成的产物,即法学必须是一门历史科学。只有当法学能够有效地把握全部法律素材时,蒂堡所要求的法典编纂才是有意义的,而当下的德国制定法典还不是时候。故此,法典编纂不是必要的事情,而是一个“时机问题”(eine Frage der Opportunität),德国当下的时代使命不是制定法典,而是建立和完善德意志法学。〔79〕Vgl. Adolf Friedrich Rudorff,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Erinnerung an sein Wesen und Wirken, S. 31.
萨维尼的言论激起了德国学术界范围很大的意见反弹和争论的升级。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中批评萨维尼:“否认一个文明民族和它的法学界具有编纂法典的能力,这是对这一民族和它的法学界莫大的侮辱。”〔80〕[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1页。即使萨维尼的拥护者(历史法学派中的日耳曼派学者)也批评萨维尼一方面主张“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却不把学术的重心放在最能体现“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日耳曼—德意志古法的研究上,而用毕生的精力去阐释德国14世纪以后“继受的”不属于德意志民族精神的“罗马法”。他们认为萨维尼的基本立场中内嵌着根本无解的“深层矛盾”。
现在看来,实际上,萨维尼当时所遭遇的就是诸种法学知识之间“联结的难题”。为了破解这个难题,萨维尼本人提出了法律的“双重生命原理”(doppeltes Lebenprincip):〔81〕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Vom Beruf unserer Zei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 Dritte Auflage, Verlag von J. C.B. Mohr, Heidelberg 1840, S. 12.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说明法律与一般的民族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政治要素”(das politische Element),但法律还有另一种独特的科学生命,即“技术要素”(das technische Element),它们以法律科学作为载体,掌握在法学家(作为整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代表”)这个特殊的阶层手中。法学家在从事法律科学研究时应当从罗马法学家卓越的法技术中获取法律论证的技艺,从富含“科学”素材的罗马法中汲取其生命营养,而传统的日耳曼—德意志古法(作为民众的习惯法)所能提供给学术研究的素材极为有限。萨维尼以此等的见识和雄心,从1840年到1849年撰写并出版了8卷本以19世纪“德意志学术精神”(勤于考证,用语精准,推理严密,数学思维与抽象化体系建构)系统阐释罗马法的鸿篇巨制《当代罗马法体系》,激励其身后的几代法学家不断地利用他们的母语(德语)写作论述并解释以拉丁语表达的罗马法教义的大部头作品,建构和完善他们所称的“学说汇纂体系”,完成了拉丁语罗马法教义的“当代化”和“德国化”,彻底改变了德国法学在整个欧洲的落后面貌,实现了德国法学家在整个19世纪所抱持的“通过罗马法,但超越罗马法”〔82〕Rudolf von Jhering, Der Geist des rö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seiner Entwicklung, I., 2. Aufl., Druck und Verlag von Breitkopf & Härtel, Leipzig 1866, § 1, S.14.的集体宏愿。萨维尼以自己的学说阻却《德国民法典》在19世纪早期问世,为德国法学赢得了积蓄力量、“有机推进”的时间,实际上最终使德国法学家们真正成长起来,他们建构的“学说汇纂体系”不仅成为1896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的知识基础(有人甚至把1888年完成的《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形容为“写入法律条文的温德沙伊德《学说汇纂法教科书》”),而且也构成后来欧洲、南美、东亚一些国家(也包括我们当代中国)的民法学教科书知识的“母体”。〔83〕Michael Stolleis (Hrsg.), Juristen: ein biographisches Lexikon; von der Antike bis zum 20. Jahrhundert, Zweite Ausgabe, C. 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2001, S. 20; [葡]叶士朋:《欧洲法学史导论》,吕平义、苏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笔者讲述上面这个故事是想说明,法学上的“知识联结难题”并非完全无解,历史上有非常成功破解这一难题的个案,但要取得这种成功确实也需要具备一些可能的智识条件,如开明的政治制度,宽松自由的学术思想氛围,民族意识的整体觉醒和“历史性反省”,思想解放运动的冲击,法学家群体内部形成一种法学及在方法论上具有更新与建构体系的理论自觉与集体冲动,著名法学家的思想引领,不同代际的学者心无旁骛、潜心供奉“天职”般在法学上持续努力用功作业,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贡献,在世界观、方法论、概念论和文献学上对法学的支持等。没有这些条件,法学就不可能持续地释放出理论的活力,绽放出理论的绚烂之花,并散发出芬芳四溢的精神韵味。
如果我们不是根据特别严格的历史—社会统计学数据来看问题,那么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说:一切拥有自己古老的法律历史和文明传统的国家,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或历史时刻由于各自不同的内外原因又不得不学习、移植或继受他国的法律及其知识,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法学上的“知识联结难题”,均有可能遭遇“萨维尼处境”(或者“历史法学派处境”)。在此意义上,尽管当代中国的社会与19世纪德国的社会在历史发展阶段、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制度、民族性、立法、司法与法学的使命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历史时差,但单从法律/法学知识的发展现状看,也并非不存在类似的“萨维尼处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84〕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18页。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实际要处理的法学知识难题是很多的,比如如何从法律科学的角度阐释和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过程中,如何做到既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又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照抄?或者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依凭的法学知识资源是什么?例如,我们如何重新诠释中国传统律学中的“文化精华”,在法律实践中,“全盘苏化”后所习得的法学知识哪些需要坚持,哪些需要摒弃,中国当代法学是否超越了“西方法学的中国/汉语表达”(“翻译法学”)阶段?这每一项工作都是摆在全体法律工作者和法学工作者面前的重任,其中涉及诸多的知识联结难题,亟待首先在法律科学上予以解决。
话虽这么说,上述难题也不是本文有能力一一详细处理并提供妥当答案的,笔者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继续讨论上文有关“知己”的话题,没有进一步展开分析和论述当下中国的法律知识/法学知识的情境、格局和传统问题。笔者相信读者对所开列出来的这些话题清单本身肯定抱有非常强烈的兴趣,但限于主题和文章的篇幅,只得对这些话题暂搁不论。利用即将结束本文的最后一点机会,笔者还想表达一句话(但并非是不重要的):若法学自身尚不知“法学为何种学问”,〔85〕有关法学之学问性质的最新讨论,参见苏永钦:《法学为体,社科为用——大陆法系国家需要的社科法学》,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第83-95页。若法学连“关于”法的理论(theory “about” law)和“法的理论”(theory “of” law)都还分辨不清,指望它去完成超出其自身知识能力的更高使命(比如,在理论上为中国法制现代化指出前进的方向和道路)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当今法学者提高自身的知识联结能力对于其使命担当的提升可能是更为重要的。
——评《中国现代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