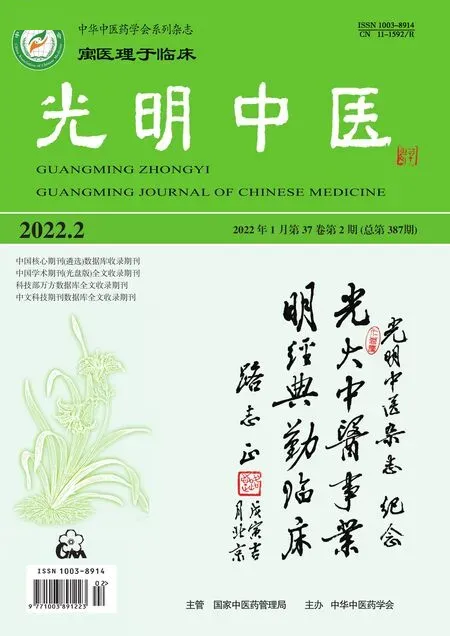中医外治法治疗妊娠恶阻现状
覃晓洵 杜雪莲 黄剑美
妊娠早期,尤以妊娠10周内多见,近半数患者可出现恶心、呕吐症状,0.3%~1%可发展为严重持续的恶心、呕吐,甚至食入即吐,进而导致电解质紊乱、代谢性酸中毒、肝肾功能受损等,严重者甚至出现Wernicke脑病[1],部分妊娠妇女因呕吐剧烈无法耐受或继发相关疾病不得已而终止妊娠。目前对于妊娠剧吐病因尚未完全阐明,相关研究发现可能与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水平升高、雌孕激素水平增加、胃肠功能紊乱、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精神心理因素变化等因素相关[2]。西医治疗该病以静脉补液支持治疗为主,对患者进行维生素,尤其是B族维生素的补充以及纠酸治疗,虽能取得一定疗效,但治标不治本,补液减少或停止补液,患者呕吐再发或加重,增加治疗费用的同时,加重患者精神负担。
中医方面的治疗,可追溯至上千年前,“妊娠恶阻”病名首见于《诸病源候论·妇人妊娠病诸候上》,其病机为冲气上逆、胃失和降,中医治疗多采用健脾益气、和胃降逆、平补肝肾等治法[3],以三因制宜为原则,辨证论治,标本兼治。但妊娠呕吐剧烈时,部分患者嗅觉较为敏感,因中药散发的气味浓烈而抗拒口服中药,因此患者更易接受的中医外治法的运用,可弥补口服中药的不足。近年来中医外治法在妊娠恶阻病中的运用形式越发多样性,例如:针刺、拔火罐、艾灸、推拿、穴位贴敷、穴位注射、中药直肠滴入、耳穴压豆等,提高临床疗效的同时,也为临床医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现将近年相关研究综述如下。
1 针刺治疗
选穴得当,针刺刺激穴位得气后发挥降逆止呕且不损母胎的功效,临床运用针刺治疗妊娠恶阻根据手法、疗法的不同,可见如下分类。
1.1 普通针刺彭建东[4]运用针刺治疗妊娠恶阻患者58例,以中脘、内关、足三里为主穴,根据证型不同加以针刺不同配穴,得气后留针20 min,每5 min行针1次,以平补平泻手法为主,观察治疗前后患者恶心呕吐程度及尿酮体检查结果,总有效率为96.55%。李海燕[5]使用针刺疗法对34例妊娠恶阻患者进行治疗,选取内关、足三里、公孙;耳穴选取交感区、胃区,针刺1次/d,留针30 min,留针期间中等强度刺激。经7次治疗后,所有患者痊愈。
1.2 腕踝针腕踝针是从腕部、踝部取相应点进行皮下针刺的疗法。颜国辉[6]将69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对照组34例仅使用西药补液止吐、纠酸治疗,治疗组35例在对照组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加以腕踝针治疗,取腕踝针双下(1、2区),该区域涵盖肝胃区域,可调和肝胃[7,8]。留针2 d,间隔1 d,2次为一个疗程,1个疗程后治疗组治愈率94.3%,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1.3 飞针马文君等[9]将妊娠剧吐患者72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各36例,对照组采用西医对症支持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联合岭南飞针手法治疗,选取内关、足三里、神门、百会穴,针刺时快速旋转毫针,把旋转的针顺着经脉走向“飞”入穴位里,以达无痛效果。针法采用捻转补法,留针30 min,1次/d,连续治疗7 d后治疗组的痊愈率为77.14%,对照组的痊愈率为47.06%,2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飞针手法因无痛或疼痛感较轻,患者较易接受。
1.4 揿针揿针属皮内针,可埋藏于皮内持续刺激穴位,较普通针刺留针时间长,疼痛轻,患者亦可自行按压针具强刺激穴位以更有效地发挥作用。黄诗蔚[10]利用揿针配合穴位按压治疗38例妊娠剧吐患者,对照组38例患者仅给予补液支持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双侧内关揿针治疗,按季节决定留针时间,夏季留置2 d后换针,春、秋、冬季留置7 d,共治疗7 d。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和治愈率分别为 89.5%和 52.6%,对照组分别为81.6%和 28.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虞蓓蓓[11]应用揿针结合安胃饮治疗脾胃虚弱型妊娠恶阻患者41例,对照组41例仅给予安胃饮口服。揿针取穴:足三里、内关、神门、印堂,留针至少72 h,间隔1 d再次治疗,共治疗7 d。结果显示治疗组妊娠恶阻症状评分降低幅度大于对照组(P<0.05)。侯乐[12]运用揿针治疗脾胃虚弱型妊娠恶阻患者34例,揿针取穴:内关、足三里以及耳穴中脾、胃、神门、交感,每次留针24 h。对照组给予中药香砂六君子汤口服。2组均治疗7 d。结果显示揿针组总体治愈率高于中药组。
1.5 梅花针叩刺梅花针叩刺皮肤,不伤肌肉,操作简单,却可达疏通经络、调整脏腑气血之效。魏竞男[13]运用梅花针自患者头额部轻叩至双侧颞部及耳廓,每天2次,每次15~20 min。3 d为一个疗程。并结合中药内服、补液治疗肝胃不和型妊娠呕吐患者30例,对照组30例纯西医补液治疗。治疗后针刺组总有效率93.33%,对照组为66.6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穴位贴敷
将中药组方碾磨成粉后制膏或以生姜、蒜泥等单味药贴敷于穴位,无肝脏首过效应及胃肠道疾病对药物吸收的影响,持久作用于人体,药物通过经皮吸收、刺激穴位,而达到治疗目的。因制作简单,且患者接受度高,广泛应用于临床。在妊娠恶阻的治疗中,有单穴贴敷治疗,亦有多穴位贴敷治疗,均取得一定疗效。
2.1 单穴位贴敷单穴贴敷治疗妊娠恶阻常取神阙穴,因脐部皮肤薄弱,血管丰富,药物贴敷此处吸收较好,可调理脾胃。该穴定位简单,且脐部凹陷,药物易于存放,患者依从性好。陈湘宜等[14]运用和胃安胎膏(党参、丁香各15 g,黄连12 g,竹茹9 g,陈皮6 g制膏)外敷神阙穴配合补液治疗肝胃不和型妊娠呕吐患者30例,贴敷每天1次,每次保留4 h。5 d为一个疗程,治疗1~2个疗程后,与单纯补液的对照组比较,治疗组呕吐消失时间、尿酮体转阴时间、用药时间以及住院天数均短于对照组(P<0.05)。龚琳[15]将80例妊娠剧吐患者随机均等分为2组,对照组予单纯补液治疗,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吴茱萸贴敷神阙穴治疗,每次敷贴6 h,2次/d,7 d为一个疗程。1个疗程结束后治疗组总有效率95.00%,对照组为80.00%,治疗组妊娠剧吐复发率(10.00%)低于对照组(37.50%),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彭华杰[16]运用止吐安胎脐贴(药用续断15 g,鸡内金15 g,桑寄生15 g,墨旱莲15 g,姜半夏15 g,木香10 g,陈皮10 g,砂仁10 g,菟丝子10 g,甘草3 g磨粉调糊制饼)配合补液治疗妊娠剧吐患者46例,贴敷每日1次,保留4 h,连续用药7 d后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仅补液治疗)(P<0.05)。
2.2 多穴位贴敷林振宇[17]运用中药(组方:砂仁10 g,陈皮10 g,生姜12 g,白术10 g,茯苓10 g,党参10 g)穴位敷贴中脘、内关、足三里穴配合补液治疗妊娠剧吐患者40例,三穴合用,调理脾胃,治疗2周后,较对照组(仅补液治疗)住院天数缩短,孕妇呕吐情况改善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钟帆[18]将60例肝胃不和型妊娠恶阻孕妇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0例,对照组予补液支持治疗,观察组在此之上配合穴位贴敷(组方:木香 6 g,砂仁 6 g,苏叶10 g,黄连3 g,藿香 10 g),贴敷中脘、双内关、双太冲穴,每日1次,1次6 h,5 d为一个周期。治疗2周期后观察组总有效率(86.67%)优于对照组(80.00%),P<0.05;观察组复发率(3.33%)低于对照组(13.33%),P<0.05。
2.3 子午流注择时贴敷依据子午流注理论,选择每日十二时辰中该经脉脏腑功能最为旺盛之时进行取穴贴敷,可提高该穴治疗效果[19]。庞海清等[20]等选取235例妊娠剧吐患者,分为观察组117例和对照组118例。对照组给予砂仁生姜散穴位敷贴,不择时;观察组基于子午流注法于每天辰时(07:00—09:00)行砂仁生姜散穴位敷贴。治疗后,观察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姚慧[21]基于子午流注理论,于每日辰时(7:00—9:00)或巳时(9:00—11:00)对治疗组60例脾胃虚弱型妊娠恶阻患者进行穴位贴敷,每日1次,2 h/次;对照组60例与治疗组均进行常规补液支持治疗。2周后治疗组的总有效率、酮体转阴率均高于对照组,平均住院天数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耳豆压穴
耳与经络、脏腑关系密切,耳廓上分布着与脏腑相应的反应区,以王不留行籽、决明子等进行耳穴压贴,并嘱患者适时按压刺激穴位,可疏通经络、调理脏腑。包晓杰[22]在静脉营养治疗基础上加以王不留行籽耳穴压豆治疗妊娠恶阻患者60例,耳穴选取神门、贲门、交感、内分泌、脾、胃、肝、肾等穴,5 d更换1次耳穴。对照组仅静脉营养治疗。治疗后试验组尿酮体转阴时间、饮食恢复正常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P<0.01)。朱郑芳等[23]等以耳穴贴压肝穴、脾穴、胃穴联合补液治疗妊娠恶阻患者70例,5 d为一个疗程,治疗2个疗程后耳穴贴压联合补液组治愈率、总有效率高于单纯补液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4 艾灸
刘炜[24]在常规补液基础上加以艾灸治疗重度妊娠呕吐患者55例,对照组55例仅补液治疗。艾灸取穴足三里、中脘以及内关,脾胃不和者加灸关元,肝胃不和者加灸太冲。每日灸1次,每次15 min,10 d为一个疗程。治疗后联合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住院天数明显少于对照组,酮体转阴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邹慧英[25]将98例妊娠恶阻患者随机均等分为2组,对照组给予补液、口服中药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运用无烟艾灸仪配合治疗。艾灸仪治疗穴位为上脘、中脘、间使、足三里。治疗后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0.05)。
5 灌肠
药物经直肠黏膜直接吸收发挥作用,避免了肝脏首过效应以及胃液对药物吸收的影响,尤其适用于对气味极为敏感、食入即吐、妊娠期便秘的患者。冯华等[26]运用生脉饮合增液汤加减灌肠联合补液治疗气阴两虚证妊娠恶阻患者40例,对照组38例仅补液治疗。治疗后,治疗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复发率以及平均治疗时间均低于对照组(P<0.05)。刘凤霞[27]自拟中药橘皮竹茹汤或香砂六君子汤直肠滴注外治结合补液治疗妊娠恶阻患者60例,对照组60例仅补液治疗,用药5 d后,治疗组肝胃不和型和脾胃虚弱型治疗后总有效率90.91%、92.59%均分别高于对照组相应证型的80.00%、72.00%(P<0.05)。花梅华[28]运用米汤保留灌肠治疗妊娠剧吐患者23例亦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
6 推拿
推拿通过手法按揉刺激穴位以发挥作用,操作简单、安全。陈国旺等[29]对30例妊娠恶阻患者给予按揉背俞穴和颈部推拿配合静脉补液(推拿组),与单纯静脉补液(对照组)治疗比较,推拿组呕吐症状的改善情况、住院天数和尿酮转阴情况均优于对照组。张改花[30]运用中医捏脊配合内关、足三里、公孙穴位按摩治疗妊娠呕吐患者,可有效缓解患者呕吐症状,缩短酮体转阴及住院时间。张文静[31]对妊娠恶阻的患者进行合谷、内关、足三里穴位按摩,患者呕吐症状及焦虑状况明显减轻。
7 穴位注射
孙莉[32]将100例妊娠剧吐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5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补液支持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予维生素B1注射内关穴联合维生素B6注射足三里穴治疗。治疗3 d后治疗组临床疗效及平均住院天数、24 h呕吐次数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张翠英等[33]对妊娠恶阻患者给予黄芪注射液穴位注射内关、足三里,有效缓解患者临床症状,改善尿酮体水平。
8 其他外治法
除上述几类临床使用率较高的外治法之外,尚有学者尝试采用拔火罐、热奄包等方法治疗妊娠恶阻病,亦取得不错疗效。疏利珍[34]在静脉补液基础上运用中脘穴拔火罐结合内关、足三里(肝胃不和加太冲穴)穴位按摩治疗妊娠恶阻患者44例,对照组42例仅补液治疗,治疗5 d后试验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杨小鹤等[35]在补液支持治疗基础上加用吴茱萸炒粗盐包热熨胃脘部治疗妊娠呕吐患者25例,对照组25例采用补液支持治疗,4周为一个疗程,连续治疗2个疗程后,总有效率盐包组高于对照组(P<0.05),盐包组呕吐证候积分及尿酮体积分水平较治疗前及同期对照组更优(P<0.05)。胡蓉等[36]运用中医理论进行辨证,在角、徵、宫、商、羽五音中选出适合患者病症的音乐,开音乐处方,配合耳穴贴压治疗妊娠恶阻患者50例,对照组50例采用补液治疗。治疗4周后,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胃泌素、胃动素、血清血管活性肠肽水平优于对照组(P<0.05),止吐所需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
9 结语
妊娠剧吐属中医学妊娠恶阻范畴。《诸病源候论·妇人妊娠病诸候上》:“恶阻病者,心中愦闷,头眩,四肢烦疼,懈惰不欲执作,恶闻食气”。妊娠恶阻者常因呕吐剧烈而致精神萎靡,郁郁寡欢,甚者伴有胃痛、咽疼等不适,无法耐受者则选择终止妊娠。因此对于妊娠恶阻者需加以重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少堕胎发生率。西医治疗本病尚为局限,补液、纠酸等对症处理虽可一时缓解症状,但治标不治本,症状易反复。中医治疗该病,可选用中药内服以及外治法,因恶阻患者对气味敏感,吐剧者甚至食入即吐,因此常拒绝接受中药内服,或因食入即吐而影响中药的发挥。中医外治法沿用至今,针对妊娠恶阻病的治疗,诸多技术已较为成熟,随着中医适宜技术的发展,中医外治法在妊娠恶阻病中的运用形式越发多样性,且操作简便,经济、安全,患者接受度高,疗效确切。但对于中医外治中新技术的开展,尚需多加实验以证实疗效;对于各项技术可将远期疗效以及对胚胎影响情况进行观察,并深入研究各项技术的作用机制,以提高临床疗效,使中医外治法在妊娠恶阻病的治疗中得以大力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