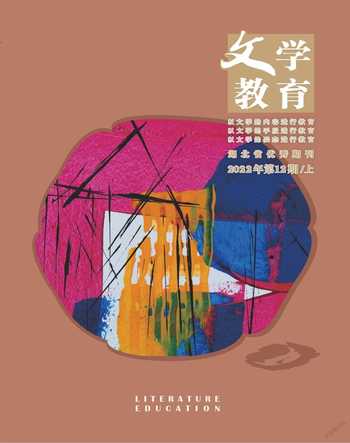从恩施傩戏探究巫巴文化
胡钰晟
内容摘要:“傩戏”又被称为鬼戏,是汉族最古老的一种祭祀鬼神、祈愿消灾的娱神舞蹈。围绕“恩施傩戏”,将恩施地区巫巴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三峡地区巫文化现象产生的基础,对“恩施地区巫巴文化的产生”、“巫巴文化遗留的影响”以及“恩施‘傩戏所代表的巫巴文化内核”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关键词:恩施傩戏 巫巴文化 人文内核
透过“傩戏”,我们得以窥见先民们对于自然崇拜的演化历程,站在科学的角度审视傩戏所代表的巫文化,后者无疑是非理性的,但出于历史的原因和生存的需要,又为远古人类社会所必需,它多以巫文化为内核,俗与艺为表象,这种互为表里的文化在我们的历史中源远流长,时至今日依然能在诸多民俗活动中瞥见它的影子。
一.恩施地区巫巴文化的产生
(一)释“巫”
关于“巫”一字最早的明确解释,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巫部》:“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袖两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凡巫之属,皆从巫。”[1]巫与祝、工本是同意。不难分辨出,在先民们的理解中,“巫”带有相当浓厚的神秘主义和原始宗教崇拜的色彩,它是采用祭祀、舞蹈等方式用以降神,达到天人沟通的目的。而在《辞海》中对于“巫”的理解则更为全面和客观:“各种行使巫术的人的泛称。皆被视为具有超自然力,并能借以行巫术,鬼魂和精灵观念出现后,更被视为能与鬼神交往,并驱使为之服役。”[2]综上看来,所谓“巫”,多产生于人类的摇篮时期,纵观全球诸多文明的演化历程,无一不经历“巫术”崇拜时期的,“它是人们在蒙昧时代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种认识形式和实用手段。”几乎所有处于蒙昧阶段的文明,都会将风雨雷电、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归咎于一个超乎客观存在的“主”或“天”,并无一例外地认为这些现象是可以通過人的行为而改变的,通过祈福、仪式、许愿等方式就能够激发这种能力。
(二)恩施地区巫巴文化产生的地理原因
巫巴文化的形成是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而在这些要素中,地理环境无疑是最重要的之一。面对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地理位置,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的产生受制于人,而人的生活方式又受制于当地的地理环境。恩施地处湖北西南,武陵山北部,清江中上游,属于典型的三峡地区。其文化特征以巴文化为主,春秋时期,恩施属于古巴国地,后至战国,属楚巫郡地,自汉末后始建沙渠县。
恩施地区崎岖多山,险绝的自然环境使这一地区的居民长期无法与外界文化进行交流,自汉末后建县,依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留着原始的生活方式和作息习惯。环绕恩施地区的险峻山峰就像是一道天然的屏障,隔断了该地区人民与外界交流的渠道,极大避免了中原文化对该地区的融合与兼并,这也就为巴巫文化的长久流传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使得恩施地区的居民长久以来屈服在强大的自然力量之下,在面对诸多自然现象时感到茫然无措,继而十分合理地将其巫鬼化,并试图通过祭祀、典礼、献祭等方式改变这些自然现象。孙光宪《北梦琐言》有这样一则故事:“合州有壁山神,乡人祭必以太牢。不尔致祸,州里惧之,每岁烹宰,不知纪极。”[3]对自然界无法理解事物的恐惧和疑虑,又为巫术进行驱鬼祈福提供了完整的内在基础。
(三)恩施地区巫巴文化产生的社会条件
从行政区沿革上看来,恩施地区建县的历史并不短暂,但以中原文化影响的进程来看,却十分缓慢,这是普遍存在与经济与生产力落后地区的一种现象。据《华阳国志》所载:“南广郡土地无稻田蚕桑,多蛇蛭虎狼”;牂牁则“畲山为田,无蚕桑,畜寡产”[4]皇甫冉《杂言迎神祠二首》诗序说:“吴楚之俗与巴渝同风,日见歌舞祀者。”[5]恩施地区在划归中原文化范围后,依然在长时间里保留着文明蒙昧时期的古老特性,即重淫祀、信鬼神。伴随着经济实力的落后,恩施地区在文化教育上也有着一定的滞后性。不仅仅在恩施,以恩施为代表的整个西南地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文化教育都相当落后。例如益州地区在东汉章帝时益州刺史王阜才“始兴文学,渐迁其俗”[6]包括恩施地区在内的整个西南文化体系,自上而下的,长期处于非正统的观点下,上至统治阶级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巫文化有认同和归属感,这一点通过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一个小故事,我们得以窥见其一角:“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
在文化封闭的西南边陲和封闭地区,人们无法通过法律和文明对恶势力施以遏制,没有正常的生活环境,人们只能转而寻求鬼神的庇佑。中原文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思想解放,从殷商时期开始,巫术便逐渐服务于王权政治,而恩施地区的巫文化,由于长期处于远离正统的位置,依然保留者自身的原始状态,作为一种民间的民俗活动长期存在并发展。
二.巫巴文化遗留的影响
(一)释“傩”
《说文解字》中将“傩”解释为“行有节也。从人,难声。”段注:“行有节度。按此字之本义也。其驱疫字本作难,自假傩为驱疫字,而傩之本义废矣。”[7]“傩”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极古老的“迎神驱鬼”仪式,与巫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巫巴文化与“傩”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傩”起源于原始的巫术,在傩祭中,通常是巫师头戴面具、手执兵器同时载歌载舞配合各种肢体动作,来完成向鬼神祈愿的仪式,“傩”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如今依然广泛分布于我国的西南众多省份,如四川、云南、湖北等地,具有鲜明的宗教崇拜和艺术色彩。
(二)“傩戏”的演化历程
傩文化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上古时期:在这个阶段,傩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并未从对“巫”或“觋”的个人崇拜中脱离出来,其形式主要以傩祭为主,《古今事类全书》中记:“昔颛顼氏有三子,亡而为疫鬼。于是以岁十二月,命祀官时傩,以索室中而驱疫鬼焉。”[8]不难看出,早在上古时期,在中华大地上生活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以“傩”作为祭祀的手段进行祈福。
(2)商周时期:傩祭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初步具有举办形态和举办时期的一项政府活动举行。《礼记·月令》中记载:“季春之月,命国傩九门磔攘,以毕春气……仲秋之月,天子乃傩,以达秋气……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征鸟厉疾。”[9]季春之月、仲秋之月、季冬之月三个时间都是商周时期重要的时刻,周人认为在这三个时期里,天地之间浊气上升,清气下降,阴阳调和失去了平衡,因此要通过傩祭来完成上达天听的效果,目的是通过祭祀与疫病与鬼怪相抗衡。
(3)秦汉时期:随着儒家思想正统的确立和大一统王朝的兴盛,这一时期的傩祭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举办流程,彻底成为统治阶级借以维系自身统治正确的工具。《后汉书·礼仪志》的“大傩篇”记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10]
两汉时期民间的傩仪也大致与文献记录的流程相似,这也为后续的民间傩仪向傩戏的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以巫为身份代表的祭祀性仪式已经崩塌,大量传统巫傩习俗只留存于民间,并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结合新的表演形式形成了后世人们所熟知的“傩戏”。
(4)宋元时期: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们将“傩祭”彻底向“傩戏”完成转变的时期称为宋元时期,但其基本在宋代就已经完成,并且由于蒙元统治者信仰与传统中华文化信仰的区别,在元朝时期“傩戏”一度被压抑和打击。《东京梦华录·卷十》:“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自禁中驱祟出南熏门外转龙弯,谓之‘埋崇而罢。”[11]
由此可见方相、十二兽等均已消失,鬼神多为人形,替换成了钟馗、土地、灶神等我们所熟知的道教人物。这都源自于宋徽宗对于道教近乎狂热的崇拜,道教思想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因此在宋朝这一时期巫傩与道教完成了合流,原本自汉唐以来的传统傩祭形象逐渐被道教中的鬼怪人物形象所代替,同时由于中原移民的不断南迁和世俗化生活的快速发展,脱胎于原始崇拜的“傩祭”逐渐与民间的诸多戏曲形成了融合,最终形成了以戏曲和舞蹈为表演形式的祈愿戏曲“傩戏”。
在傩文化的历史演进中,傩文化的表现形式大致经历了由傩祭——傩舞——傩戏的演变过程,而傩文化中的主题也伴随着它的表演形式进行着不断的变更,由最初的驱傩,逐渐演变为娱神,再到如今随着世俗生活的快速发展,与众多戏剧表演形式完成了融合,形成娱人的一种民俗表演方式。
(三)恩施傩戏与原始艺术
在人类历史的萌芽时期,文艺的产生与劳动有着密切关系,在远古时期的人类文明中,纯粹以艺术为目的的文艺创作活动十分少见,而傩戏作为巫文化的具体表现,自然也是远古先民们为了生存而展开的。
恩施地区的“傩戏”主要分为两类,分别是恩施傩戏和鹤峰傩戏。前者代表为傩愿戏而后者则是傩坛戏,恩施市流传的傩戏由傩愿戏和坛傩两个部分组成,傩愿戏现存于红土乡的漆树坪村和大河沟村,它由湖南经湖北鹤峰县传入,大约有320年的历史;坛傩现存于三岔乡,它起源于明代洪武年间恩施谭、杨等姓人家祭祖的“弘农堂”,至今还保留有交牲、开坛、请水等25坛完整的法事。二者虽然属于傩戏的不同分支,但其独特的文化内核仍然是一脉相承的:二者的形式与内容不尽相同,但主要包括请神、祈福、还愿等几个主要项目,傩戏的主要目的依然是表达人对天地自然的尊崇之心,这正是人类早期精神活动的形态之一,在这些前提下,傩戏背后所蕴含的巫术与恩施地区的先民们的原始审美具有深层的联系,傩戏与人们的远古审美都具有拟人和模仿的双重特性,人们自然而然地将难以理解的自然现象和日月山川赋予人性,二者在情感的激發上,都是通过祭祀、舞蹈等行为以求鬼神庇佑。
恩施傩戏中处处透露着巫术心理对于乐舞的影响。音乐和舞蹈是人类最原始的表达自身想法与感受的行为,它早于文字的诞生,在绝大多数的人类文明早期壁画中,都由对歌舞形式的展现,例如狩猎、祭祀、婚丧嫁娶等行为,人们都通过舞蹈和音乐进行表现,在现今恩施傩戏的表演方式中,依然能够寻觅到这些从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痕迹。恩施傩戏多以祭坛为中心,舞蹈者扮演的角色真是在远古先民们祭祀活动中的巫师角色,舞蹈者常身着法衣,手持法器并诵念咒语,以傩坛为中心,将世俗的事物与神圣的存在进行划分,随着舞蹈的动作的加剧,舞蹈者会体验到一种强劲的活力,他们往往将这种活力视为与鬼神沟通的结果,而在舞蹈中所诵念的咒语不仅仅是为了贴合音乐的节奏感,更是为了达到娱神的目的。其中所包含的仪式,或许在最初只是先民们为了庆祝丰收或狩猎成功的一种集体行为,但随着人类审美情趣的进步,这种仪式逐渐与巫术心理所融合,创造楚独立的艺术门类。恩施傩戏也正是按照着这种演变的历程,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审美活动行为。
三.恩施“傩戏”所代表的巫巴文化内核
(一)注重“耕战祭祀”
恩施地区人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长期受到“巫鬼文化”的影响,虽然在如今的社会已经鲜有留存,但在恩施“傩戏”的表演戏目中仍然保留着大量有关“田神”和“战神”的戏份,如恩施三岔乡现存的25种坛傩戏目中,就有《送神》《招兵》《迎百神》《放牲祭猪》《土地》等,以战争和农耕为主题的祭祀戏目。
在我国,对于农田和土地的祭祀古已有之,《周礼·大司徒》云:“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郑玄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对于农田和战争的祭祀贯穿着整个傩戏演进的过程,因为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人类文明的原始时期,巫不仅代表个人或集体的权威,同时也是对文化知识以及氏族和部落在管理和生产方面的贡献。而战争与农耕正是一个部族或文明能否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在恩施地区寻见不少村落仍然在沿用上古流传至今的测时方法,用以确定农耕播种的时间和季节。
(二)歌舞娱神
巫巴文化的重要的通神手段就是通过歌舞形式,用来表达人与鬼神的交流,这也是恩施地区“傩戏”能够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早期恩施傩戏还是以祭祀为主,这样做的目的有两点:
第一,通过歌舞用以表达人们信仰的虔诚。现存的恩施傩戏戏目在祭神方面,依然保留鲜明的特色,例如在戏剧的演绎过程中时常会出现跪拜、仰天高歌的方式,这种方式是为了在形式上达到以同天听的目的,拉近鬼神与祈愿者的距离。
第二,通过歌舞祭奠亡灵安慰生者。在如今恩施大部分地区,在举办丧事活动的时候,会在死者面前高歌狂舞,目的是祈祷死者能够顺利地将灵魂升入理想的境界。
恩施傩戏中所流传下来的歌舞形式,反映的都是远古巫巴心理中,先民们一种狂热的娱神乐鬼的情绪和早期的、对于生命意识的认识。
站在科学的角度审视巫文化,其无疑是非理性的,但出于历史的原因和生存的需要,它又为远古人类社会所必需。恩施地区地的环境促使其巫文化的早熟并自成特色,它多以巫为内涵,俗与艺为表象,这种互为表里的文化,在恩施代代相袭,不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至今。湖北恩施地区“傩戏”便是湖北地区“巫”文化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以湖北恩施地区“傩戏”为研究对象,旨在分析其“巫文化”特征,通过这一分析,为湖北地区巫民俗文化留存的非遗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0
[2]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1349
[3]孙光宪.北梦琐言[M].北京.中华书局.1960,逸文卷三:176
[4]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四:260
[5]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卷二四九:2798
[6]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四:237
[7](东汉)许慎原著,汤可敬撰.说文解字今释[M].长沙.岳簏书社.2001:648
[8]常宏.中日面具藝术的审美比较——以鬼神面具为例[D].山西大学.2006届硕士学位论文
[9](清)阮元校刻.礼记正义卷十六,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1374
[10](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3127
[11](宋)孟元志撰.邓元诚注.东京梦华录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253
本论文为湖北文理学院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项目编号:S202210519023)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