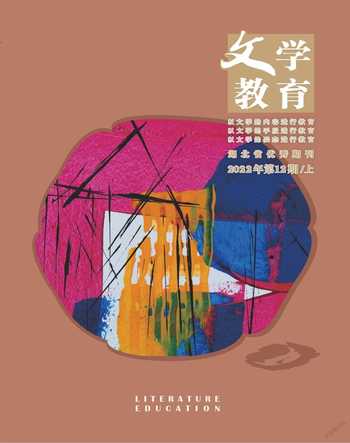巴金小说中的知识女性形象探究
蓝柳英
内容摘要:巴金小说中塑造了不少的知识女性形象,有信仰革命的知识女性、反抗封建家庭的知识女性、归顺传统的知识女性以及挣扎彷徨的知识女性等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生存状态、个性追求以及面临的困境,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巴金的个人风格,表达了巴金对中国女性实现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期望。
关键词:巴金 小说 知识女性 女性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任何社会,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妇女解放既是人类解放的重要方面,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准。由于长期受到“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传统伦理观念影响,中国女性一直深受束缚和压迫,文学作品中对知识女性的书写更是少之又少。“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受到新思潮影响,女性解放运动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众多作家都有意识地对知识女性角色进行了塑造。巴金也通过笔下的知识女性形象书写,表达了他对女性命运的热切关注。以往对巴金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较多集中在被封建礼教摧残的悲剧女性形象上,本文则聚焦于巴金小说中的知识女性形象书写,将巴金小说中的知识女性分为信仰革命的知识女性、反抗封建家庭的知识女性、归顺传统知识女性以及挣扎彷徨型的知识女性等四种形象加以论述。通过分析这些知识女性形象的塑造来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生存状态、追求个性解放的过程以及面临的困境,揭示巴金笔下知识女性形象独特的美学价值。
一.暗夜中的闪电——信仰革命的知识女性
巴金曾回忆自己读妃念格尔的自传时激动的心情:“实在这本书像火一样点燃了我献身的热情,鼓舞了我底崇高底感情。我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无穷的惭愧。我觉得在这样的女人底面前,我实在是太渺小了。”[2]巴金曾不止一次提到过俄罗斯女革命者的传记对他产生的影响,那些革命女性的英雄事迹和崇高信念让巴金感受到女性身上不容忽视的力量,巴金不仅为此编译了传记《俄罗斯十女杰》,当他走上文学道路时,也不忘将她们的革命精神和事迹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
《爱情三部曲》(包括《雾》《雨》《电》)是巴金描写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道路的代表之作,里面的李佩珠是一个被巴金称为“近乎健全”的革命知识女性。李佩珠在《雾》中并没有直接露面,仅是作为陈真口中“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中的一员出现。而到了《雨》中,俄国革命女性妃格念尔的自传《回忆录》深深地打动了她,妃格念尔坚强不屈的伟大人格点燃了她的内心,崇高的革命精神叩响了她的信仰之门,“縱然她不能够了解这个女性的思想,但是那种热烈的献身精神、生死相共的友情和火一般燃烧的字句是谁都能够了解的,谁都能够被它们感动的,她当然不会是一个例外。”[3]这本书彻底扰乱了她的灵魂,她不想成为一个别人口中“脆弱的女性”,而是想成为一个像妃格念尔一样坚强崇高的人,她不想“在爱情里求陶醉”,而是要“在事业上找安慰,找力量”。当周如水说革命只是男人的事情时,她更是大胆反驳:“难道女人就只该在家里伺候丈夫吗!”接受了革命启蒙的她此时决心走出自己狭小的个人天地,走向社会,走向革命。
到了《电》中,李佩珠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稳重的革命女性。她热情大胆,积极地参与和组织革命活动。她处变不惊,在集会遭到包围时沉着地安抚群众,这时“她的声音飞起来,高出于别种声音之上,压倒了一切。”她头脑冷静,不主张轻易地流血和牺牲,她说:“我们没有理由轻易牺牲。血固然很可宝贵,可是有时候也会蒙住人的眼睛。”她温柔细腻,安慰迷茫痛苦的德华:“没有人生下来就有勇气,谁都是在那个大洪炉里锻炼出来的。”她行动果敢,在危机时刻沉着指挥大家撤退,在面对父亲失踪的消息时,她迅速从悲痛中调整状态,继续投入到革命工作中。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这是一位智慧、勇敢、坚强的女革命者,既有为理想事业奉献的决心,也有清醒严密的意识和头脑,是当时的知识女性走向社会、走向革命的典范。
巴金早期作品中的知识女性,除了《爱情三部曲》中的李佩珠,还有《灭亡》中的李静淑、《新生》中的张文珠等等。她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接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受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并且最后走出家庭的小天地踏上了社会革命的道路。她们身上带着强烈的俄国女革命家的印记,这些有着革命信仰的知识女性不仅体现了巴金对女性的关注和赞美,也是青年巴金革命情怀和社会理想的一种投射。
二.出走的娜拉——反抗封建家庭的知识女性
暴露和批判封建家庭的罪恶是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初,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初,封建大家庭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巴金用其深情的笔墨描摹了一个个在灰暗腐朽的封建大家庭里可爱鲜活的女性形象,其中就包括那些充满叛逆性格的新知识女性,记录她们的觉醒、挣扎、抗争和出走。
琴是贯穿《激流三部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最早从封建囚笼中伸出头来探望外面世界的女性。她父亲早逝,母亲因此疼爱有加,甚至不顾当时的社会眼光把她送进学校接受文化教育。而“五四”新思潮的洗礼以及觉民、觉慧两兄弟带来的先进思想,激发了她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人格独立的自我意识,并且一步步从觉醒走向强化。作为女子,她深知在千百年来封建礼教的压制下,女性的处境比男性更艰难,她从易卜生的《娜拉》(又称《玩偶之家》)中明白:“我想最要紧的,我是一个人,同你一样的人……或者至少我要努力做一个人。……我不能相信大多数人所说的。……一切的事情都应该由我自己去想,由我自己努力去解决。”她渴望男女同校,得知新学堂要招女学生时更是大胆的说:“我第一个去报名!”面对婚姻,她勇敢地发出女性最深处的声音:“……我要做一个人,一个跟男人一样的人。……我不走那条路,我要走新的路。”而后坚决地和相爱的二表哥觉民一起,反抗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
除了自我的觉醒和反抗,琴也不断地鼓励和帮助其他的女孩走出闺闱,踏足外面的世界。她给周报写文章,宣传女子剪发,领着高家姐妹打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禁忌一起去逛公园、看戏剧,还帮助淑英抗婚出走,支持和帮助淑华进学堂。琴“像长姐一样爱护她们、指导她们”,也像园丁一样,把女性独立解放的思想浇灌到高家小姐们的闺房中。但她的女性解放之路并没有局限于家中,而是随着自身思想的不断成熟开始扩展到社会。后来的她与觉民等先进青年们一起办进步报刊,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发挥自己的才干,坚决地和封建势力作斗争。正如书中琴的同学许倩如所说的:“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坚决地奋斗,给后来的姊妹们开辟一条新路,给她们创造幸福。”
巴金曾说:“我常常说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就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睁开眼睛,仿佛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4]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当时激励了众多中国青年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作为直面“五四”新思潮洗礼的这一类新型知识女性,琴身上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对封建旧制度的大胆反叛、对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的追求。在她的带领下,家中的淑英、淑华也在一步步走向觉醒和反抗,她们的胜利不仅是女性抗争封建礼教的胜利,也是伴随“五四”新思想到来的新时代的胜利,寄托了巴金对“五四”精神的颂扬和期待。
三.禁锢的鸟儿——归顺传统的知识女性
在“五四”新思潮冲击着20世纪的中国社会时,那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成为最先接触到先进思想的那一批人。她们之中有的响应时代的召唤,张扬个性解放和独立自主的精神,纷纷走出家庭,迈向社会,成为反抗封建旧制度的一份子。在这新旧交汇的历史时期中,也有一些知识女性最终屈从于现实和命运,放弃曾经的理想和抱负,回归到中国传统女性的一方天地,而《憩园》中的万昭华,就是这样一个无法挣脱传统“心灵桎梏”的现代知识女性。[5]
万昭华并没有出生在充满罪恶的封建大家庭中,而是生长于一个和睦的知识分子家庭里。哥哥是有着良好名声的大学老师,她自己也接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甚至于“她没有过门的时候,人人都说她是个新派人物”。但即使是这样,她最终依旧选择归顺传统,接受了没有经过恋爱的包办婚姻,从一位新式知识女性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依附丈夫的旧公馆里的富太太。她自觉地用中国传统女性贤良淑德的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她温顺、随和、善良,脸上总是挂着笑,对待下人也很宽厚,她急切地想要做好一个主妇、妻子、母亲。她为没能教育好小虎而懊恼,为没有管理好公馆而自责,可赵家的仇视、继子的轻蔑、丈夫的不理解,都让她陷入无助之中。一方面,她自觉无法满足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对家庭女性的期待,同时,她又抑制不住去怀念自己曾有过救人济世的理想和抱负,想要活得痛快而又意义。她也曾感叹道:“我有时候想,就是出去做一个护士也好得多,我还可以帮助那些不幸的病人……”但是她没有勇气去行动,只能通过看电影、看小说来消遣和慰藉自己的孤独和苦闷,就像那笼中供人赏玩的鸟,关着关着,自己也不想飞走了。直至最后她有了身孕,只能无奈地说:“要飞也飞不起来。现在更不敢想飞了。”
封建文化对女性的压迫不仅仅是体现在对身体的摧残上,也表现在对女性精神的禁锢。巴金赋予了万昭华很多美好的品质,让人忍不住同情和怜爱,但同时也揭示了她自身的性格悲劇和顽固封建残余的影响。像万昭华这一类知识女性,虽然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但因为自身无法摆脱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最终依旧陷入成为“玩偶”的命运。由此可知,只有当女性主动挣脱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才能真正走出这令人窒息的封建高墙,实现精神和实体的双重解放。
四.“回归”的娜拉——挣扎彷徨的知识女性
1918年《新青年》在其新出版的“易卜生专号”栏目上介绍了易卜生的戏剧《娜拉》(又名《玩偶之家》),主人公娜拉摆脱夫权束缚,离家出走的反抗精神成为当时“五四”妇女解放的一面旗帜。一些深受影响的中国知识女性因此效仿娜拉,出走旧家庭,走上追求个性解放的道路。但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黑暗的社会现实让这些出走的“娜拉”们陷入新的困境之中,她们的女性解放之路步履维艰,正如鲁迅先生后来预示的结果一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6]
《寒夜》里的曾树生在当时已经算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女性了。她从大学教育系毕业,与丈夫自由恋爱而结合,有过远大的教育理想,想办一个“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她甚至在银行里有着自己的工作,与丈夫一起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可在那冰冷黑暗的“寒夜”之中,社会、经济、家庭、个人等种种因素让她踏上了“出走”的路。解放前夕,时局的动荡让当时的重庆人民陷入极度的不安之中,出走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后方似乎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与此同时,就像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出的那样:“经济,是最要紧的了。”对曾树生来说,放弃调职就得离开银行,对经济的依赖让她没有勇气和决心去面对这样的生活。况且,家中还有一个深受封建落后思想毒害的婆母,因她不是儿子明媒正娶而讥骂她,因她不像旧时的媳妇一样侍奉丈夫和婆母而憎恨她。而丈夫的懦弱和胆小,儿子的疏离和淡漠,也让这个家庭像那颜色惨淡、忽明忽暗的电灯一样“……永远亮不起来,永远死不下去,就是这样拖。”同时,曾树生自身对享乐生活的追求也让她不自觉地想要挣脱现状,她呼喊着“……我只想活的痛快一些,过得舒服一些。”她并不是一个“健全”的知识女性,她只是一个“受屈辱、但又孤立无援的软弱的知识妇女。为了求生存,她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街头。”[7]精神的欲求和现实的冰冷让她走出了那个“没有温暖”的家庭,但也让她陷入了精神和行动上的困境,让她在出走后又回到重庆去找寻那个破碎的家,面临的却只有人去楼空的结局和冰冷的寒夜,留下“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哀叹。
《寒夜》的最后并没有说明曾树生的结局,巴金后来在《谈〈寒夜〉》中说道:“……她可能会飞回兰州,打扮得花枝招展,以银行经理夫人的身份,大宴宾客。”也许曾树生可能会选择从一个破碎的家庭里又回归到另一个新的家庭中,继续做一个依附于男人的“玩偶”,未出逃的“娜拉”。她也曾觉醒过、抗争过,可是就像“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8]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健全的制度保障和经济的独立,失去家庭庇护的“娜拉”们在社会上难以生存。
巴金先生曾说,他写《寒夜》是为了:“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9]像曾树生这类知识女性,她们为自己的个性解放和独立自主做出了抗争,但难以调和的家庭矛盾让她陷入痛苦之中,罪恶的战争和黑暗的社会现实更让她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这启示我们,在当时那个社会,女性解放不能单靠女性个人的力量,只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中国妇女的前途和命运才能得到保证,才能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
巴金青年时期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并怀着极大的社会改造的热情来参与文学创作。其早期作品中的知识女性形象带着浓厚的国外女革命家的印记,缺少符合中国本土的时代特点,有些过于片面化和理想化。但随着巴金思想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在后期的《憩园》、《寒夜》中,将知识女性置身在新旧交替的中国社会,着重表现知识女性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中的两难境地,使得人物更加丰满和鲜活。她们或许并不完美,但都洋溢着时代的气息,这些内涵丰富的知识女性角色,既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长廊,也表达了巴金对女性命运的热切关注和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610.
[2]巴金·俄罗斯十女杰·巴金全集(第二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340.
[3]巴金·爱情三部曲··巴金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32.
[4]陈丹晨·巴金全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22.
[5]蔡丽敏·女性的心灵桎梏:重读巴金的《憩园》与《寒夜》[J]·宁德师专学报,1997.(3):53-57.
[6]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6.
[7]陈丹晨·巴金创作中的女性形象[J]·文艺研究,1983(6):62-75.
[8]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6.
[9]巴金·巴金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265·
(作者單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