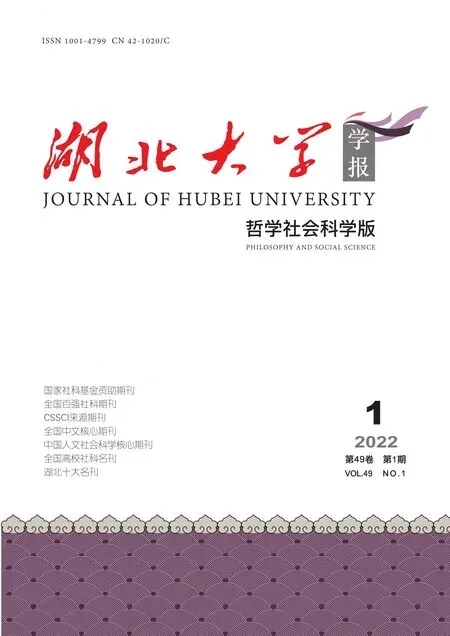为理智主义辩
——从人工智能的视角出发
戴益斌
(上海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444)
理智主义与反理智主义之间的争论最早可以追溯至赖尔(Gilbert Ryle)。赖尔严格地区分了命题性知识(knowing that)与能力之知(knowing how)(1)参见郁振华:《论能力之知:为赖尔一辩》,《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命题性知识即命题表达的知识,在宽泛的意义上,它可以被理解为关于“事实是如此这般”的知识。命题性知识既可以是陈述性的,也可以是假言式的,还可以是范导性的。在赖尔的意义上,只要是能够用命题表达的,都可以称之为命题性知识。能力之知则是实践性的,总是体现在某种活动之中,比如知道如何骑车、下棋、游戏等等。因此,能力之知总是体现为知道做某事的知识。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赖尔指出了两种理论立场,即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和反理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之间的对立。前者认为能力之知可以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后者则反对这一做法。通过一系列讨论,赖尔认为理智主义是站不住脚的。他的核心理由是,理智主义的观点会导致无穷倒退(2)Cf. Gilbert Ryle,“Knowing How and Knowing That:The Presidential Address”,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Vol.46,No.1,1946.。21世纪初,斯坦利和威廉姆森(J. Stanley and T. Williamson)的论文《知道如何做》批评了赖尔的论证,重新讨论了命题性知识与能力之知之间的关系,并主张将能力之知还原为命题性知识(3)Cf. J. Stanley,T. Williamson,“Knowing How”,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98,No.8,2001.。这引发了新一轮对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之间争论的讨论。
在理智主义与反理智主义的这场争论中,本文主张为理智主义辩护,原因在于:首先,从直觉上说,反理智主义有可能会妨碍能力之知的迭代过程,而理智主义则有利于能力之知的积累;其次,在事实层面上,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可以证明理智主义的合理性。本文试图在回应反理智主义的基础上,从人工智能的发展中获得某些洞见,证明理智主义的合理性。
一、反理智主义的挑战:关于无穷倒退的论证
在理论层面上,反理智主义者对理智主义立场的批评有很多,但最严肃的批评来自于赖尔的无穷倒退论证。在讨论这个论证之前,有必要厘清赖尔的一些预备性工作。根据赖尔的观点,能力之知与命题性知识之间的区别在语言层面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对于能力之知而言,可以有一系列的形容词来描述,比如,积极的语词有聪明的、细心的等,否定的语词有愚蠢的、粗心的等,赖尔将这些语词统称为智力(intelligence)的概念家族;与之相对,命题性知识所涉及的活动是构成理论思维的活动,赖尔称其为理智(intellect)活动,其中的典型代表是数学和各门已经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在赖尔看来,智力与理智之间的区分对应着能力之知与命题性知识之间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理智主义者也承认智力与理智之间的区分,同时也认为能力之知与命题性知识有所不同。只是理智主义并不认为二者之间有种类上的区分,他们倾向于认为能力之知是命题性知识的一种,可以还原为命题性知识。正是在这一点上,赖尔给出了他反驳理智主义者的决定性意见,也即他的无穷倒退论证。
关于无穷倒退论证,赖尔说:“对于命题的考虑本身就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的实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显示智力,而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愚蠢的。但是,如果要有智力地实施一项活动,必然先实施一项理论活动,而且要有智力地实施,那么,任何人要打破这种循环都是逻辑上不可能的事情。”(4)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徐大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8页。译文有改动,参见Gillert Ryle,The Concept of Mind,London:Hutchinson,1949,p.30。赖尔的这个论证比较简短,但它的核心思路还是清楚的。可以将他的论证过程重构如下:
前提1:任何对命题的思考活动都会体现出智力特征;
前提2:对理智活动智力特征的刻画依赖于有智力地实施一种新的理论活动;
结论1:实施新的理论活动会体现智力特征;(由前提1得)
结论2:对新的理论活动的智力特征的刻画依赖于有智力地实施另一种新的理论活动;(由前提2得)
……以至无穷。
前提3:无穷倒退不可能;(普遍共识)
结论:理智主义方案有问题,能力之知无法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5)一个常见的重构模式来自于斯坦利和威廉姆森,他们认为,赖尔的循环论证大致可以表述如下:“如果能力之知是命题性知识的一个种类,那么要实施一个行动,就必须思考一个命题,但对命题的思考本身就是一个行动,这需要另一个思考命题的行动。如果能力之知是命题性知识的一个种类的主张,要求能力之知的每一次展现都需要伴有另一个思考命题的行动,而这种思考本身就是能力之知的展现,那么能力之知将无从显现。”(J. Stanley,T. Williamson,“Knowing How”)郁振华认为,这种重构模式忽视了赖尔对能力之知的刻画中所蕴含的智力因素(郁振华:《论能力之知:为赖尔一辩》)。笔者同意这一观点。事实上,斯坦利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知道如何做》(J. Stanley,Know Ho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一书中对循环论证进行了重新表述。
赖尔构造的这个论证很巧妙。以上对赖尔论证过程的阐述表明,赖尔是通过利用“无穷倒退不可能”这样一个普遍共识来反驳理智主义立场的,但是得到“无穷倒退”这一结论,是否就可以用来反驳理智主义呢?事实上,这里仍然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先,在赖尔的论证过程中,除前提3这个普遍共识之外,赖尔至少还利用了另外两个前提,其中前提2被赖尔视为理智主义的解决方案。因此,正常来说,赖尔通过无穷倒退否定的是前提1和前提2的合取,而并非前提2自身。其次,赖尔认为前提2是理智主义的方案,但他并没有说明理智主义为什么会采用这种解释方案;除此种解释方案之外,理智主义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案能够解释思考理智活动中的智力特征?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赖尔对理智主义的反驳力度很有可能会比他想象中的要弱很多。
关于第一个问题,赖尔用无穷倒退论证否定的是两个前提的合取。一般来说,只有当赖尔论证前提1为真的情况下,他才可以认为前提2是有问题的。但根据赖尔对能力之知的刻画,前提1似乎是真的。因为在赖尔那里,能力之知并不是“出于纯粹的习惯、盲目的冲动或心不在焉地做出的行动”(6)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第41页。,而是有技巧地做出的行动,因而会体现出智力特征。然而,赖尔的这个命题实际上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解读:1.在现实世界中,任何对命题的思考活动都会体现出智力特征;2.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任何对命题的思考活动都会体现出智力特征。第一种解读方式很常见,是反理智主义者最为常见的解读方式,也是学者最容易接受的理解方式;第二种解读方式是一种带有模态谓词的解读方式,它要求在所有可能世界中,对命题的思考活动都体现出智力特征。这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论。
赖尔的描述表明,智力特征属于一种价值上的判断,比如聪慧或愚蠢、细心或粗心等,这些都属于价值维度的语词。换句话说,智力特征并不具备任何本体论意义,它其实是来自于人类从价值维度对某一活动所作的评价,真正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是此活动本身。以人工智能产品AlphaGo围棋机器人为例,AlphaGo之所以被认为具有智力特征,是因为评价者立足于人类现有的价值维度,惊叹于它赢得了与人类顶尖棋手的对战。如果是在一种可想象的可能世界中,比如由各种不同的人工智能围棋机器人组成的世界中,AlphaGo即使赢得了所有的围棋对弈,也不会引起这个世界中其他智能机器人的惊叹。因为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存在价值判断,也不会有人认为AlphaGo会体现出任何智力特征。也就是说,在赖尔那里,虽然智力与能力之知具有对应关系,但这种对应关系并不具有必然性。只有当一种类似于人类世界的价值判断存在时,对命题的思考活动才会体现出一种智力特征。因此,如果坚持第一种解读方式,那么前提1似乎是真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确会从价值维度判断事物;但如果坚持第二种解读方式,那么前提1是有问题的,因为想象某个不涉及到价值维度的可能世界是可能的。因此,在存在这两种不同解读方式的意义上,前提1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
更进一步的考虑似乎可以表明,在前提1的这两种解读方式中,第二种解读方式可能更为根本。首先,第一种解读方式是基于现实的考虑,第二种解读方式中的“可能世界”则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因为现实世界只是可能世界中的一种。而且,现实世界在不断地发展变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尚未实现的可能世界有可能进一步变成现实世界。其次,即便在现实世界中,分离出不存在价值维度的“世界”仍然是可能的,需要利用的只是瓦雷拉(F.J.Varela)所提出的“微世界”概念。在瓦雷拉的视角中,微世界指的是,行动者处于其中的并且由它(可以)感知到的东西所决定的环境(7)Cf. F. J.Varela,Ethical Know-How:Action,Wisdom and Cogni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9-10.。如果我们将不同解读中的“世界”理解为微世界,那么在宽松的意义上,智能机器人在不依赖于人的环境中运作,也可以形成某种微世界,比如智能机器人群体基于它们的周遭环境所形成的微世界。这表明,虽然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大可能会导致人类的消失,即不会导致价值维度在现实世界中的消失,但它的确表明,在微世界中,价值维度并非是一个必然选项。综上考虑,第一种解读方式可能略显狭隘,第二种解读方式更合理些,而这种解读方式同时表明前提1并不成立。
关于前提2,赖尔认为,理智主义为了解释对命题的思考活动体现出来的智力特征,需要借助另一种思考命题的活动,但这很可能不是理智主义者的主张。理智主义者主张能力之知可以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这种立场并没有强调,对能力之知智力特征的刻画依赖于另一种思考命题的活动。斯坦利就认为,赖尔的这种要求对理智主义者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人类经常明智地行动,但并不需要首先公开承认任何格言或规则,比如现象学家利用现象学方法思考某些经验对象时,并不需要有任何在先的对命题的思考活动(8)Cf. J.Stanley,Know How,p.14.。反理智主义者可能会选择的一种回复是,用在先的理智活动理解某一活动的智力特征,是赖尔对理智主义的一种定义。但问题在于,赖尔对理智主义的定义很可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理智主义者只是强调,能力之知能够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它们之间不存在种类上的区分。除此之外,理智主义者并不需要用另一种理智活动解释某一活动的智力特征。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认为能力之知能够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与认为需要用另一种理智活动解释某一活动的智力特征是两回事,二者之间并不等价。承认前一点与否定后一点,在逻辑上并不冲突。如果坚持用后一点定义理智主义,那么赖尔的无穷倒退论证,即便在现实世界中,也只能用来反驳需要用另一种理智活动解释某一活动的智力特征这一观点。但是,这一论据并不能证明能力之知不能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
其次,前面已然澄清,智力特征来自于人类从价值维度对某一活动所作的评价,但在一种可能世界里,如果不存在类似于人类这样的存在物,那么活动本身可能就不会体现出智力特征,因而也就不需要用关于其他命题的理智活动进一步解释此种活动。事实上,在现实世界中,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也在逐渐提高,相互协作的群体机器人其实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们之间既相互独立,又构成一个整体,但不需要任何价值性的评价。
以上论证表明,赖尔反驳理智主义的核心论证所依赖的两个前提或多或少都是有问题的。他的第一个前提并不具有必然性,在一种可能世界中,能力之知不会体现出智力特征;他的第二个前提是他自己构造的一个假设,对于理智主义者而言,这个假设并不合适。因此,无穷倒退论证并不成立,赖尔试图通过无穷倒退的论证来反驳理智主义是无效的。
二、人工智能具备能知之知:理智主义的证成
相对于反理智主义而言,理智主义似乎更具有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来源于我们的一项观察,即人工智能相关成果至少已经证明,那些通常被认为无法还原的能力之知,实际上可以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以AlphaGo围棋机器人为例,我们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2016年,AlphaGo围棋机器人打败了人类围棋高手李世石。这是人工智能领域内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人类对机器的认识。因为很多人倾向于认为,围棋是计算机最难攻克的领域之一。他们的理由大致有两点:1.围棋需要计算的内容超出了现有任何计算机的能力;2.围棋中涉及到的“局”、“势”被认为是计算机无法刻画的。如果因为AlphaGo在自我学习过程中参考了人类棋盘,因而不能被认为在围棋智力上超出了人类水平,那么AlphaGo Zero的出现则打破了这一认识。AlphaGo Zero自始自终并未借助任何人类经验,它在空白状态下通过自我学习,在40天之内就打败了AlphaGo的升级版。这表明,人工智能在某一领域内,通过自我学习,可以完全实现对人类相关领域的超越。事实上,这一结论在被不断地证实。比如,清华大学薇薇作诗机器人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人脸识别技术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场景,波士顿动力公司推出的Atlas机器人可以实现奔跑与跳跃,等等。完全可以设想的是,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类有能力将人工智能在这些不同领域中所获得的成果综合在一起,实现更大的突破。比如说,在围棋领域中,AlphaGo Zero下棋时不再需要借助人类辅助落子,而是真正以类人的形态出现,自主读棋盘、拿棋子、落棋子等。这意味着,在人工智能领域内,智能机器人可以像人类一样实现知道如何下棋、如何奔跑、如何骑车等一系列活动。在赖尔的意义上,似乎不得不承认智能机器人具备能力之知。
根据目前学界的共识,人工智能之所以在最近几年有显著的提升,主要来源于算法的精进。而在这些算法中,应用最广的算法有五大类:规则和决策树、神经网络、遗传算法、概率推理、类比推理。规则和决策树背后的核心理念是所有和智力相关的工作都可以被归结为对符号的操控;神经网络则试图通过改变神经元之间的联结方式获得自己想要的输出;遗传算法的核心是适应度函数,通过此函数给程序打分,反映它与目标的契合度;概率推理是以贝叶斯定理为基础进行概率计算或者为证据寻找最可信的解释方法;类比推理的基础是对于作为学习基础的相似判断的信任,包括最近邻算法以及支持向量机(9)参见佩德罗·多明戈斯:《终极算法: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世界》,黄芳萍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65-70页。。
通过分析,可以推知这些算法都是通过命题的方式显现的。规则和决策树依赖于对符号的操控,而符号可以用命题表达;神经网络的关键在于它学习的主题以及其中蕴含的奖惩机制,这些同样可以用命题来表达;遗传算法中的适应度函数是一个有待填充的命题;概率推理的核心即贝叶斯定理本身就是一个命题;而类比推理所依据的相似判断也是一个命题。事实上,如果考虑这一事实,即AlphaGo采用的是神经网络算法,并且它之所以成功的原理与机制已经用命题形式发表在《自然》杂志之上,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加确信,人工智能的实质是由一系列命题构成的。
基于以上讨论,大致可以得出两个结论:1.人工智能产品可以展现出它具备某种能力之知,知道如何做某事;2.人工智能产品本身是由一系列命题性知识构成的。综合这两个结论,可以进一步推知,原则上,某些能力之知可以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因为人工智能产品之所以具备能力之知是因为它拥有命题性知识,除此之外,它并没有其他知识来源。而这恰恰是理智主义立场的核心主张。这表明,在理智主义与反理智主义的争论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成果可以证明,理智主义立场似乎更合理些。因为至少某些曾经被认为不能还原的能力之知被证明是可以还原的。
然而,德雷福斯(H. Dreyfus)的观点对这两个结论提出了挑战,在他看来:“所有形式的智能行为中都包含着不可程序化的人类能力。”(10)参见休伯特·德雷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宁春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293页。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理智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德雷福斯的观点表明,总是存在某种能力之知不能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根据德雷福斯的分析,他同时代的人工智能乐观主义者,比如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艾论·纽维尔(Allen Newell)、约翰·麦肯锡(John McCarthy)等人,他们的人工智能工作中存在四个基本假设,即生物学上的假设、心理学上的假设、认识论上的假设和本体论上的假设。生物学上的假设指的是,在某一运算水平上,大脑以离散的运算方式加工信息,采用某种生物学的办法,等价于开关闭合与断开的办法;心理学上的假设指的是,大脑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装置,它按照形式规则加工信息单位;认识论上的假设阐述的是,一切知识都可以被形式化;本体论上的假设指的是,存在一组在逻辑上完全互相独立的事实(11)参见休伯特·德雷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第166页。。在这四个假设中,后三个假设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认为,“人一定是一种可按规则对取原子事实形式的数据做计算的装置”(12)休伯特·德雷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第239页。。德雷福斯认为,这四个假设都是站不住脚的。其中,生物学上的假设与当时已发现的证据不相符;而后三个假设则存在一些概念上的问题,与哲学上已获得的认识相冲突。
德雷福斯所利用的哲学上的认识有很多。这些认识至少有以下几种思想来源:1.胡塞尔对意识问题的思考;2.格式塔心理学对整体结构的认识;3.海德格尔对意义的理解;4.梅洛·庞蒂对身体的现象学分析;5.维特根斯坦对规则的分析。这些思想资源都指向一点,即人类行为并非是可形式化的。这似乎可以证明,人工智能专家试图通过将人类行为形式化以模仿人类智能的做法可能是行不通的。然而,在评论这个结论之前,有必要弄清一个问题,即德雷福斯所说的“形式化”是什么意思。
通常认为,形式化指的是,通过将研究对象转变成符号来考察的方法。但是,在德雷福斯的讨论中,他所说的“形式化”指的是一种特定的人工智能进路,即符号主义进路。符号主义进路的代表人物有很多,比如德雷福斯提到的西蒙和纽维尔,他们认为,“物理符号系统具有实现通用智能行为的必要和充分手段”(13)Allen Newell,Herbert A.Simon,“Computer Science as Empirical Inquiry:Symbols and Search”,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Vol.19,No.3,1976.。也就是说,符号主义者往往认为,符号系统可以实现对智能行为的刻画。虽然符号主义的代表人物之间可能存在某些细微的差别,但还是可以将符号主义的基本思想概括如下:在人为定义知识的前提下,通过符号的逻辑演算解决人工智能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人为定义的规则是其中的核心要素。从德雷福斯对形式化的理解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批评实际上是对人工智能研究过程中符号主义进路的批评。因此,面对德雷福斯的批评,至少有两个问题可供思考:1.德雷福斯对符号主义的批评是否恰当;2.德雷福斯对符号主义的批评是否可以扩展到人工智能的其他研究进路之上。
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些符号主义者,比如麦肯锡认为,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批评过时了,因为在德雷福斯的论述中,没有看到他关于最新文献的论断,比如符号主义者对非单调逻辑的使用(14)John McCarthy,“Book Review:Hubert Dreyfus,What Computers Still Can’t Do”,Artificial Intelligence,Vol.80,No.1,1996.。从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来看,麦肯锡的回应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符号主义使用的是演绎推理,它是一种根据已有知识基于逻辑规则推导出新知识的推理过程,但非单调逻辑与之不同。非单调逻辑强调新知识的加入对原有系统的改变。不过,麦肯锡的反驳似乎不足以回应德雷福斯的批评。因为无论是符号主义中的演绎推理,还是非单调推理,都是一种基于规则的思路,都试图通过规则把握智能行为。但德雷福斯告诉我们,通过对人类行为的反思,哲学家们发现,人类的智能行为不是遵循规则的,而是依赖于背景知识、依赖于上下文的。为此,德雷福斯给出了人类智能行为的三个特征:1.人类的智能行为是情境式,依赖于知识背景和上下文;2.身体在智能行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智能行为并非规则性的行为。基于这些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即便符号主义在研究人工智能的过程中添加了非单调推理,只要这种研究思路不放弃规则的主导地位,那么它仍然无法避免德雷福斯的指责。事实上,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批评真正出问题的地方在于,他无法将这种批评扩展到人工智能的所有研究进路之上,特别是目前流行的以深度学习技术为代表的联结主义进路和行为主义进路。
首先,当今最流行的人工智能技术即深度学习包括两个部分:知识与经验。知识是人类预先给予智能机器的,比如数学公式等。在人工智能领域,它们也被称为“先验知识”。经验是智能机器在运行过程中得到的反馈,这与人类的经验类似。就像人类在生活中发现不能用手碰触燃烧的火焰是一种经验一样,人工智能的经验也是后天的。将知识与经验融为一体是深度学习技术的一个典型特征。这一特征表明,人工智能可以避免德雷福斯的第一个批评。因为人工智能中的知识成分等同于德雷福斯所强调的知识背景,而经验则相当于他所说的上下文。
其次,强调身体在智能行为中的作用,也不足以反驳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并不排除利用其他材料和技术实现人工智能产品的“身体”构造,比如生物材料技术、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导航与定位技术等等。虽然这些技术本身很复杂,但是都可以用命题的形式表达出来,它们以文字形式呈现在教科书、论文、专著之中即是例证。比如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其基本原理是利用多传感器资源,将传感器获取的信息进行整合,形成关于外部环境或被测对象某一特征的描述。这并没有超出命题所能表达的范围。因此,试图通过“具身性”概念否认人工智能具备模仿人类智能的可能性(15)类似的批评参见何静:《具身性与默会表征:人工智能能走多远?》,《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很可能是不恰当的。人工智能可以利用其他材料与技术实现人工智能产品的“身体”构造,从而以具有“身体”的形态实现人工智能与外在世界之间的“耦合”。人工智能技术中的行为主义进路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
最后,智能行为并非规则性行为,这一结论是恰当的,我们的确可以在智能行为中找到很多证据,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会失败。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表明,人工智能在联结主义思路的影响下,并没有强调规则在智能行为中的作用,而是主张人工智能在数据中学习,即通过给定的数据统计出某些近似的规律,以解决人工智能期望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并不强调规则的使用,而是强调概率的使用。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成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德雷福斯对规则的批评也不适用人工智能领域所使用的最新技术。
基于以上讨论,可以发现,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像德雷福斯所说的那样,蕴含了四个基本假设。因为研究者们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并没有假设大脑是以离散的方式处理信息的,也没有假设人类的智能行为一定可以按照符号的形式将其形式化,而是主张将每一种智能行为看作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蕴含了很多成分,它既与先验知识有关,也与经验反馈相联。而且,德雷福斯对人类智能行为特征的描述并不会妨碍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模仿,人工智能中的联结主义进路与行为主义进路可以适配人类智能行为的这些特征。这些结论表明,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考察并不成立。
事实上,德雷福斯对人类智能行为特征的概括可以看作是能力之知的某种共性。因为能力之知恰好体现在人类的智能行为之中。如果这个判断成立,以上论述可以确定,在实践领域内,人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之知是人工智能无法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理智主义的观点是合理的,能力之知可以还原为命题性知识。
三、理解能力之知:整体论视域下的理智主义解释
能力之知是可还原的,但应如何理解能力之知呢?在理智主义的框架下,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或许能为我们澄清能力之知给出某些启示。人工智能的相关成果表明,学会一件事情,或者说具备某种能力之知,并不是简单地可以用一句话如“某人会做某事”来概括的。它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多。这些内容构成了一个整体,而实现某种能力之知即是在这种整体的意义上完成的。无论是从人工智能的一般工作原理还是从某个特定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发,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人工智能的一般工作原理来看,目前人工智能的灵魂即“机器学习”实际上包括四个部分:学习目标、学习结构、训练数据和学习算法。这四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任何一个部分的缺乏都会导致人工智能无法完成它所设定的任务,无法展现出它所具有的特定的能力之知。
从特定的人工智能产品比如AlphaGo出发,AlphaGo的算法里结合了树搜索技术以及大量的经验训练,并且内置了快速落子网络和策略网络,它们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系统,去掉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无法完成对人类围棋冠军的挑战。人工智能领域内的这些事实表明,在理解能力之知的问题上,整体论的视角是一种合适的选择(16)需要简单澄清的是,“整体论”一词应用在不同领域之中会有不同的含义。比如在语言哲学中,整体论意指,一门语言中所有语词的意义相互依赖;而在认识论中,整体论意指,一个陈述的认知意义反应在它与其他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全体之上。本文在宽松的意义上使用“整体论”一词,其要点在于将各式各样内部相互关联的系统看成是一个整体。。
而且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看,整体论的视角更符合人类对知识整体的认知。哲学家们对知识的探索似乎越来越清楚地表明,知识之间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对一个概念的把握,依赖于是否已经把握与它相关的其他概念;为了理解一个命题,需要理解与之相关的其他命题。在某种意义上,离散性的知识体系很可能并不存在。在涉及到能力之知的相关问题时,可能也是如此情形。获得一种能力之知,意味着对该能力之知涉及到的所有内容都有所认识。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认识过程并不是即时性地瞬间完成的,而是渐进式的。行动者一步一步完成对某类知识的把握,逐渐加深对该类知识的理解。随着对能力之知相关内容认识的增加,行动者对能力之知的理解和操作也更会加清晰与熟练。
基于整体论的理论视角,可以推知,原则上能力之知最终可以还原为一系列命题性知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还原与理智主义的代表人物斯坦利和威廉姆森所采用的还原模式不一样。斯坦利和威廉姆森通过分析“汉娜知道如何骑车”这样的事例试图阐明,某人S具有某种能力之知KH可以还原为,在某一特定语境C中,存在某种方法W,并且S知道W是KH的方法,且在实践的呈现模式下,拥有此命题(17)Cf. J. Stanley,T. Williamson,“Knowing How”.。很明显,这样的还原模式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即将一种能力之知还原为一个命题。但这种还原模式很可能是行不通的。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实现一种能力之知,并不是一种命题性知识可以完成的。整体论的视角表明,一种能力之知涉及到相当多数量的命题性知识。在AlphaGo的案例中,数量众多的代码综合在一起才体现出AlphaGo具备下围棋的能力。这也就是说,当我们试图还原某种能力之知时,应该将其还原为一系列命题的组合,而不是某个单个命题。
能力之知往往体现在做某件事情的行动之中,这种行动可以进一步分解,而分解后的行动大多都可以用适当的命题来表达。比如说,在“汉娜知道如何骑车”这个事例中,汉娜知道如何骑车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汉娜知道在开始骑车前,应保持身体平衡,坐在车座上;汉娜知道,准备骑车时,双手应握住车把;汉娜知道,双手握住车把后,用双脚踩蹬;等等。当然,在这种分解过程中,仍然可能会有某些命题隐含了某种能力之知。比如汉娜知道双手握住车把后用脚踩蹬,实际上就隐含了汉娜知道如何用脚踩蹬这种知识,而这恰恰是一种能力之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还原,即继续将这种用脚踩蹬的能力之知,进一步分解为更为基础的知识,比如知道把脚平稳地放到脚蹬上,知道用脚发力,等等。当然,这种程序可以继续下去,但不会无限进行下去。因为在对能力之知进行分解的过程中,它所蕴含的能力之知,如果看成一个集合的话,是真包含于它自身的。这意味着分解的次数越多,其中所蕴含的能力之知越基础。而对于这个最为基础的能力之知,一定会有某种命题系统与之相互等价。否则的话,不但AlphaGo不可能,任何一种能体现出有某种能力之知的智能机器都是不可能的。
需要澄清的是,将能力之知还原为某个命题系统,命题系统中所包含的命题不仅有陈述性的,还有很多是范导性的和假言式的。而且,范导性的命题和假言式的命题在这种命题系统中很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假言式的命题。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命题系统中,陈述性的命题往往表达的是对事物的认识,比如雪是白的;范导式的命题呈现出一种规则或指令,指引着行动者在某种情况下做出某种相应的回应,比如靠右行走;而假言式的命题则通过前件与后件之间的关系,表达了一种普遍性,比如如果a是植物,那么a会光合作用。对于能力之知而言,普遍性大概是一个必要属性,因为主体拥有某种能力之知,意味着他可以在不同场合中使用这种能力之知。这也是假言命题在命题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原因。
如果以上对能力之知的考察是合理的,那么这将证明,能力之知原则上可以还原为命题性知识。能力之知与命题性知识之间并没有种类上的区分。只不过,将能力之知还原为命题性知识,不是将一种能力之知还原为某一命题所表达的命题性知识,而是将能力之知还原为由一系列不同类型的众多命题构成的命题系统。这一结论表明,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理论上,相比反理智主义而言,理智主义更为合理。进一步的思考表明,从整体论的视角为理智主义辩护,会有很多优势。
首先,整体论的思路不但可以证明能力之知可以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而且可以证明能力之知和命题性知识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差别。一方面,能力之知可以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因而二者之间,并没有种类上的差别;另一方面,能力之知与单个命题表达的知识之间的确存在差别,这种差别体现为一种样式上的差别。因为能力之知往往是由命题系统构成的,而学界通常所说的命题性知识,往往都是由单个命题表达的知识。前者是系统性的,而后者是个体性的。当然,这种样式上的差别,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也会体现出一些差异。比如在存在价值判断的现实世界中,一个命题系统,尤其是当它包含有很多范导性命题和假言命题的时候,往往会体现出一些智力特征,但单个命题几乎不会表现出这种智力特征。此外,应用单个命题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比如将单个命题表达的信念指派给行动者时,往往可能会出现一些盖梯尔反例的情形,但应用一个命题系统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形。事实上,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理智主义者可以解释能力之知的智力特征,而不需要依赖在先的对某一命题的理智活动。
其次,从整体论出发,可以解释以往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之间的争论可能存在的问题。理智主义者通常认为,能力之知并非知识的一种特类,它和命题性知识并无区分;反理智主义者则倾向于在能力之知与命题性知识之间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但是他们的讨论往往是原子式的。斯坦利和威廉姆森的解释方案很明显,他们用一种命题性知识解释一种能力之知;赖尔对理智主义的反驳也蕴含了这种思维方式,因为他似乎想当然地认为,“要有智力地实施一项活动,必然先实施一项理论活动”(18)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第28页。译文有改动,参见Gillert Ryle,The Concept of Mind,p.30.。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为这种思维方式给出任何辩护。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只能用一种命题性知识解释一种能力之知,为什么有智力地实施一项活动,只会涉及到一项理论活动。与之不同的是,整体论的思考方式不仅在理论上有很多说明,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在经验领域也得到了一些证明,知识的学习过程是一种明证。当然,最重要的是,以整体论的思考方式思考能力之知与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在事实层面上相契合。
最后,从整体论上证明能力之知可以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这一结论对于知识的积累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反理智主义者认为,能力之知不能还原为命题性知识。如果这是合理的,那么这将意味着能力之知只能通过个体行为呈现出来,行动者也只能通过自己的领悟力学习能力之知。在这种情况下,能力之知的传播和积累会面临巨大的障碍。但事实上,这样一种观点在很大程度是成问题的,因为已有证据表明,从AlphaGo到AlphaGo Zero,人工智能棋艺的精进相当迅速。理智主义者认为能力之知可以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通过命题形式学习能力之知,这为能力之知的积累提供了保障。
当然,以上从整体论角度思考能力之知的各种优势并没有要求我们必然在现实社会中将各种能力之知还原为命题性知识。因为事实上,将能力之知还原为命题性知识系统,这一过程并不容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超出了有限个体的认识。比如说,AlphaGo的研发并非是集一人之力完成的。这很可能是众多学者在直觉上倾向于认为能力之知与命题性知识属于不同类型的知识的原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原则上,我们不能将能力之知还原为命题性知识。这也就是说,在理论上,能力之知可以还原为命题性知识,但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应该将能力之知还原为命题性知识可能还要考虑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经济问题、还原效率问题等等。而在语言层面上,由于使用“能力之知”这样的语词比使用它可能被还原的一个命题系统要简单得多、方便得多,因此,基于实用精神,在语言层面保留“能力之知”这一语词是可以接受的。
综上所述,理智主义与反理智主义之间的这场争论,无论是在事实层面上,还是在理论层面上,理智主义都更具有优势。在事实层面上,人工智能的相关成果可以证明,能力之知可以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二者之间并没有种类上的差别。在理论层面上,反理智主义者通过无穷倒退论证反驳理智主义的核心主张并不成立。因为它所利用的两个前提都不是必然有效的。在一种可能世界中,能力之知并不会体现出智力特征;并且,理智主义不需要求助于在先的对命题的思考活动就可以说明能力之知可能体现出的智力特征。从整体论的视角出发,能力之知被证明可以还原为一系列命题性知识的组合。能力之知与命题性知识之间的差别是命题系统和单个命题之间性质上的差别。我们之所以在语言层面上使用“能力之知”这个语词,也只是因为相比较而言,它在使用上更加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