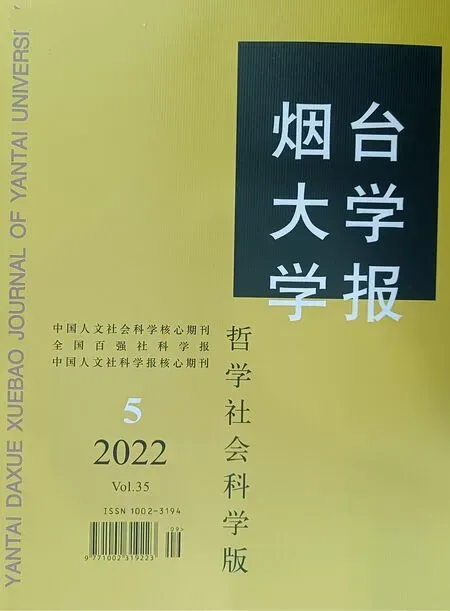莫言与沈从文的动物书写比较论
魏家文
(贵州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在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中,动物的身影无处不在,它们在建构“高密东北乡”和“湘西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莫言对动物的书写不仅是出于一种对动物本身的好奇,而且与作家对生命和人性的反思联系在一起。对沈从文而言,湘西的美除了自然山水之外,还包含那些充满灵性与生命活力的动物,它们与自然山水一起共同建构起“希腊小庙”这一人性王国,成为作家人性理想与诗意栖居的重要参照对象。尽管莫言和沈从文笔下的动物书写问题已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二者各自独立的研究上,还未见从比较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出现。实际上,对莫言与沈从文笔下的动物书写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探寻二者在叙事技巧和生命伦理追求上的内在契合之处,而且有助于加深对二者创作能得到世界认可的深层原因认识。
一、动物之于莫言、沈从文小说的文本建构
在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无论是家养动物还是野生动物,它们的身上不仅显示出生命的自然属性,同时也显示出生命的社会属性和理想属性,成为彰显作家人生理想和文学理想的重要参照物。从总体上看,动物书写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环境氛围的营造、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一,动物作为故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彰显了人物性格,揭示了人物的命运。通过对莫言创作历程的梳理可以发现,莫言的动物书写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莫言不仅继承古典审美传统,而且还接受西方动物书写的影响,激活自己的人生经验,将动物撒播在小说的方方面面、里里外外,使其成为自己小说修辞的常规载体,成为莫言对世界、对生命、对人展开思考和认识的‘装置’。”(1)郭洪雷:《论莫言小说的动物修辞》,《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从总体上看,动物书写在莫言的小说中经历了从小到大、从无心到有心的转变过程,随之而来的是动物性逐渐变淡、文学性日渐浓厚。早期的《放鸭》(1982)《三匹马》(1983)中的“鸭”和“马”只是一种平常的动物形象,作家还没有赋予它们隐喻意义。当莫言读到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笔下的秋田犬之后,在创作《白狗秋千架》时,莫言开始有意识让动物作为主角之一参与故事情节的进展,成为小说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小说中的白狗不仅见证了“我”和暖的初恋,同时也是秋千架上意外事故的见证者,当十多年后“我”重回故乡时,它又充当了“我”和暖见面的引路人。在小说的开篇,正是白狗的出现激活了我的故乡记忆。在白狗的引导下,“我”得以和初恋暖相见,如果没有白狗的出现,“我”也许就不会注意到高粱地里劳作的暖,“我”和暖也不会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场景中见面,暖与“我”的对话中也不会充斥如此多的不和谐声音。当“我”怀着失落与忏悔的心情离开暖家时,又是白狗将“我”引向高粱地,当暖在那里向“我”提出帮她实现生一个会说话的孩子的愿望后,“我”竟然无言以对,故事在这里戛然而止。由此可见,在整个小说中,白狗不仅是故事情节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将故事情节推向高潮的引导者。
此外,像《红高粱家族》中的红狗、黑狗、绿狗在战乱中被主人遗弃,成了自谋生路的野狗。为了生存,它们被迫和昔日的主人展开了斗智斗勇的生死大战,它们和人类一样成为故事的主角。《怀抱鲜花的女人》中的黑狗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它时刻陪伴在女人的身边,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黑狗在关键时刻出现,又在适当的时候消失。《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死后分别轮回为驴、牛、猪、狗、猴。小说用动物的视角借助生死轮回的形式再现了中国农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风云,如果没有这些动物的参与,小说的叙事不仅无法顺利展开,而且“西门闹”的形象也不会给读者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此外,动物不仅是故事情节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揭示者。比如,《红高粱家族》中“黄鼠狼”的每一次出现都与恋儿的命运紧密相关:黄鼠狼的第一次出现是在恋儿外出挖野菜时,它的出现让恋儿兴奋嚎叫、口吐白沫,黄鼠狼的出现唤醒了恋儿内心深处隐藏的情欲,“我爷爷”也因为恋儿的诱惑而移情别恋,恋儿和“我爷爷”“我奶奶”之间的关系和命运也随之发生变化。黄鼠狼的第二次出现是在恋儿遭到日本鬼子轮奸时,黄鼠狼的幻影如死神一般在恋儿眼中不断闪现。在此过程中,黄鼠狼的幻影多次与日本鬼子的形象重合,它的每一次出现都加速了恋儿的死亡进程,直到恋儿死亡后才消失。此外,像《生死疲劳》中的“驴折腾”“牛犟劲”“猪撒欢”,既是对不同动物性格命运的描述,也是对不同时期“西门闹”性格命运的揭示。不难看出,《生死疲劳》的艺术魅力在很大程度上与莫言用动物视角替代人类视角的叙事技巧有关。
与莫言类似,沈从文笔下的动物在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和揭示人物命运上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粗略统计,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有近40 篇出现了各类动物形象,其种类多达 20 多种。以《边城》为例,小说中出现的动物将近30种,其中黄狗出场的次数最多。小说开篇就告诉读者,由四川到湖南的官路到了湘西边境时有一个名为“茶峒”的小山城,一座白色的小塔建在离小溪不远处,塔下只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里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和一只黄狗。小说开篇就将黄狗推到读者面前,暗示黄狗不仅是这个家庭成员的一分子,同时也是整个爱情故事的见证人。翠翠和二佬初次在河边见面的时候黄狗就在场,当二佬邀请翠翠到他家等爷爷归来时,翠翠误会了二佬的意思,骂他“悖时砍脑壳的”,这时黄狗以为翠翠被人欺辱对着二佬汪汪叫起来,翠翠说:“狗,狗,你叫人也看人叫!”翠翠原本是想告诉黄狗那个人不值得叫,但二佬误以为翠翠是让黄狗不要对好人叫。正是在这种误解中,二佬埋下了对翠翠爱慕的种子,同时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可以说,黄狗在翠翠与二佬的相识、相恋的过程中实际上充当了“媒人”的作用,在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和揭示人物的命运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像《三三》中的白狗、《王嫂》中的黑狗、《牛》中的小牛、《会明》中的母鸡、《劫余残稿》中的笋壳色母鸡,这些动物书写在小说中都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其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动物成为彰显人物性格品质和情趣的重要参照对象。在莫言眼中,动物和人一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价值取向,甚至比人类更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红高粱家族》中的猎户耿十八刀被日本鬼子连砍十八刀而命在旦夕,是路过的狐狸帮他舔伤口让他死里逃生,但后来耿十八刀为了一己私利杀死了救命恩人狐狸,动物的善良和人的自私在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生死疲劳》中的西门牛宁死不耕种集体的地,在遭受到西门金龙的毒打后死也要死在自己主人的地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人的西门金龙为了自己的前途,公然宣布与自己的养父蓝脸划清界限,其人性的自私与残暴令人唾弃。 《白狗秋千架》中的白狗在十年后重新认出“我”后,并没有表现出久别重逢的惊喜,而是表现出一种漠然的表情,究其原因是对“我”抛弃暖的行为不满。当“我”去暖家看望暖时,白狗对“我”的到来只是象征性地叫了几声,并没有对“我”表现出明显的恶意,充分显示出它温良宽厚的品质。尽管白狗对“我”的回乡并不欢迎,当暖对白狗说出她的愿望后,白狗还是将“我”引向高粱地。与“我”面对暖和故乡人时流露出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不同,白狗在暖遭遇到身体和爱情的双重打击后,依然不离不弃陪伴在暖身边,两相比较,人和狗品德的高下立分。在小说结尾,当暖提出让“我”帮她实现生一个会说话的孩子的愿望后,“我”却不知道何去何从,这就不得不让读者对“我”还乡的真正目的产生怀疑:到底是为了忏悔还是为了炫耀?
相比之下,沈从文常常从人与动物平等的视角、以动物朴实本真的生命之美来映衬美好的人性人情,借此塑造淳朴善良的底层人物形象。沈从文小说中的动物不仅能帮助主人做事,而且能理解主人的心情,这样的动物除了《边城》中的黄狗外,还有《牛》中的牛。小说中的牛大伯是旧中国遭受无情掠夺的底层农民的代表,作家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把人和牛之间的情感交流作为故事的主线。小说从牛被牛大伯误伤开始,到小牛伤愈,直到最后小牛被官府征用到一个不可知的地方结束。在整个小说中,牛不仅能帮助牛大伯做事,而且能领会牛大伯的意图,甚至还会做梦。正是在人与牛的情感交流中,牛大伯这位心地善良、忍辱负重的底层农民形象跃然纸上。可以说,如果缺少牛的参与,不仅整个故事情节无法建构起来,牛大伯的形象也会因为缺乏相应的参照对象而变得苍白无力。与《牛》相似,《会明》通过军人会明养鸡过程中与动物的情感交流,凸显了会明这个被战争异化的军人天性中善良淳朴的一面。伙夫会明受蔡锷将军的影响,渴望在战争中立功成为一名英雄。但自从在部队休整期间得到一只老乡送的母鸡后,会明的兴趣逐渐从当英雄转移到照顾母鸡。在此过程中,会明人性中善良的天性被重新激发出来:“自从产业上有了一只母鸡以后,这个人,他有些事情,已近于一个做母亲人才需要的细心了。它同别人讨论这只鸡时,也像是一个母亲与人谈论儿女一样的。”(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92页。当母鸡孵化出小鸡后,会明就像一位母亲一样照顾这些小鸡,不仅日常生活离不开这些小鸡,甚至梦中出现的也是这些小鸡叽叽喳喳的叫声。
其三,通过对动物的描绘来渲染环境、烘托人物心情。在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王国里,不仅有极富地域色彩的山川河流和植物,还生活着各样的动物,它们与自然风景一道在渲染环境、烘托人物心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为了复仇带领乡亲们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最后几乎全军覆没,余占鳌面对躺在河堤上牺牲了的乡亲们,内心的悲痛无法言表,只能独自面对墨水河喃喃自语,此时小说这样写到:“八月初九的大半个新月亮已经挂上了天,冰冷的月光照着爷爷和父亲的背,照着沉重如伟大笨拙的汉文化的墨水河。被血水撩拨得精神亢奋的白鳝鱼在合力飞腾打旋,一道道银色的弧光在河面上跃来跃去。”(3)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88页。小说用飞腾打旋的白鳝鱼来烘托余占鳌内心不甘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情,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此外,莫言在那些回忆自己早前乡村劳动生涯的小说中,常常用动物的叫声来烘托劳动快乐的一面。比如,在《我们的七叔》中描写社员集体麦收时这样写到:“天不亮时,就有许多鸟儿在空中歌唱。人们披着星星,戴着月亮,提着镰刀下坡,借着星月之光割麦子。”(4)莫言:《我们的七叔》,《花城》1999年第1期 。在《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中描写村民们拉着石磙子在操场上转圈修操场时,莫言用“人欢马叫闹春耕”来形容这一欢腾的劳动场景。
对沈从文而言,“湘西世界”的美不仅表现在自然风景上,同时也表现在动物上,动物和自然风景一起在渲染环境、烘托人物的心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代表作《边城》中,吸引读者的除了那满山的翠竹、清澈透明的河水外,还有生活于其间充满灵性和生命活力的各种动物:竹林间交替鸣叫的竹雀杜鹃、草丛里各处飞着的绿色蚱蜢、溪面上飞来飞去的红蜻蜓、闪着蓝光在夜空中自由飞行的萤火虫、深潭中仿佛游在空气中的游鱼等。正是在这样让人心旷神怡的自然环境中,边城人养成了自然、质朴的天性。不仅如此,动物在烘托人物的心情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小说《贵生》的开头部分,作为单身汉的贵生在秋天收获的季节里心情大好,桥头杂货铺老板对贵生很满意,只要贵生愿意,随时都可以和老板如花似玉的女儿结婚。小说用“移情于物”的手法来烘托贵生的好心情:“贵生在溪沟边磨他那把镰刀,锋口磨得亮堂堂的。手试一试刀锋后,又向水里随意砍了几下。秋天来溪水清个透亮,活活的流,许多小虾子脚攀着一根草,在浅水里游荡,有时又躬着个身子一弹,远远的弹去,好像很快乐。”(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365页。水中鱼虾的快乐,实际上是贵生“移情于物”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沈从文在描写人物不愉快的心情时,同样采用了“移情于物”的手法。比如,在《边城》中,当接二连三的不幸降临到翠翠头上时,小说用“溪面飞来飞去的红蜻蜓”来烘托翠翠纷乱不安的心绪。
除了用“移情于物”的手法来烘托人物的心情外,沈从文还善于采用“缘情写物”的写法来烘托人物的心情。“缘情写物”主要基于这样一种心理现象:人类在某种心理或感情的诱发下,家养的动物尽管不在眼前,但会以一种表象的形式呈现在人的脑海中,作家通过人物对某些动物的联想和爱憎的描写,可以在不动声色中揭示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丈夫》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丈夫》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年轻的丈夫因为贫穷自愿把还没有生育的妻子送到船上去做妓女,丈夫想妻子的时候就在农闲时去看望妻子。有一次,当丈夫在看望妻子时想与妻子单独相处时,妻子刚好要接待客人,在金钱和权力的淫威面前,丈夫被迫退到船的后舱“低低的喘气”,此时丈夫内心的痛苦虽可意会,但不易言传。小说既没有用“金刚怒目”来表现其“愤怒”,也没有用嚎啕大哭来表现其“痛苦”,而是笔墨一转这样写道:“这丈夫到这时节一定要想起家里的鸡同小猪,仿佛那些小小东西才是自己的朋友,仿佛那些才是亲人,如今和妻子接近,与家庭却离得很远,淡淡寂寞袭上了身,他愿意转去了。”(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第49页。与近在咫尺的妻子相比,丈夫此刻感到家中的鸡和小猪才是自己的“亲人”,并且愿意马上就回到乡下去。尽管只有寥寥数语,但丈夫痛苦惆怅的心情却在不动声色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
二、人与动物的相互映照与相互润泽
从总体上看,莫言常常采用人与动物相互映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生命与人性的看法。在莫言眼里,人的历史和动物的历史常常混在一起:“光荣的人的历史里掺杂了那么多狗的传说和狗的记忆,狗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交织在一起。”(7)莫言:《红高粱家族》,第153页。正是基于对人与动物同源性的认识,莫言在写人的时候常常以动物作为映照人类生命力退化、反思人性的一面镜子。
其一,通过对动物驯化后的生命与驯化前的生命的对比,表达了作家对野性生命的赞美与呼唤。众所周知,“种的退化”是莫言早期小说的重要主题,莫言不仅通过“我爷爷”“我奶奶”的生命形式与“我辈”生命形式的对比,揭示出现代人所面临的“种的退化”问题,而且通过对动物驯化后的奴性生命和驯化前的野性生命的对比,表达了作家对原始生命力的赞美与呼唤。比如,《白狗秋千架》中的白狗虽然成了人类的好朋友,但在人类的圈养下逐渐丧失了原来纯正的血统,“很难再见一匹纯种”(8)莫言:《白狗秋千架》,《中国作家》1985年第4期。;《生死疲劳》中那些来自沂蒙山的充满反抗精神的野猪在人类的驯化下逐渐丧失了原始的生命活力,除了觉悟的刁小三逃脱了瘟疫的魔爪外,其余的野猪都在瘟疫中丧失了性命。相反,动物一旦摆脱了人类的控制重获自由,不仅野性的生命力会被重新激发出来,而且其智力水平也得到明显提升。
《红高粱家族》中的家狗因为战争被主人抛弃,为了生存,这些狗被迫和从前的主人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当这些被人类驯化的狗食用了人的尸体后,野性的生命很快被重新激发出来:“人血和人肉,使所有的狗都改变了面貌,它们毛发灿灿,条状的腱子肉把皮肤绷得紧紧的,它们肌肉里血红蛋白含量大大提高,性情变得凶猛、嗜杀、好斗。”(9)莫言:《红高粱家族》,第196页。家狗重新恢复野性后,其体力与智力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它们开始在与人类的战斗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比如,当这些野狗在与人类的战斗中意识到手榴弹的巨大威力后,为了避免人类手榴弹的突然袭击,狗的首领把队伍拉出几十里远,然后对队伍进行严格整顿。“我”家足智多谋的红狗在取得狗队的领导权之后,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它所组织的几次进攻堪称兵法的完美运用,其计谋之高连聪明的人类也为之赞叹。比如,为了扰乱“我爷爷”的心智,红狗在混战中将“我爹”的卵子咬掉一个,让领队的爷爷心智大乱,足见狗与人一样懂得擒贼先擒王的韬略。《丰乳肥臀》中的宠物狗因为城市禁狗令的颁布成为流浪狗后,被迫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更严重的是它们要时刻提防城市打狗队的偷袭。虽然这些狗失去了从前养尊处优的生活,但它们的生命潜能却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被极大激发出来,共同的生存遭遇使这些流浪狗紧密团结起来。为了报复打狗队的残暴行为,这些流浪狗设计吃掉了打狗队长正在上幼儿园的小儿子,其智慧与报复心与人类相比毫不逊色。
与动物相比,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类不可能回到原始生活中,但莫言还是借助一个富有传奇色彩人物的经历对此进行了思考。《丰乳肥臀》中的鸟儿韩从日本鬼子的劳工集中营逃脱后,藏匿于荒山之中生活了十五年,成了北海道荒山密林中名副其实的“野人”。为了在动物统治的世界生存下去,鸟儿韩被迫回到原始人的生命状态。他像野兽一样在山林中划出自己的势力范围,警告生活在他附近的一群灰狼不要越界。当狼群准备吃掉他时,他身着擦擦作响的黄色鳞片、毛发像一股汹涌的黑烟,双眼放着绿光,嚎叫着向狼逼近,狼嚎叫,他也嚎叫,而且他的嚎叫声比狼叫更悠长更凄厉;狼呲牙,他也呲牙;狼在月光下跳起神秘的舞蹈,他也装出欢天喜地的样子跳跃着,最后,“他从狼的眼睛里,发现了友好和缓和”。(10)莫言:《檀香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398页。从此以后,鸟儿韩与狼群成了和平相处的邻居,最终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活了下来。
其二,通过人与动物的相互映照,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以及人性与兽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事实。在莫言看来,人与兽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莫言这样说:“人类进化至如今,离开兽的世界只有一张白纸那么薄;人性,其实也像一张白纸那样单薄脆弱,稍稍一捅就破了。”(11)莫言:《白狗秋千架》,第335页。基于这种认识,莫言小说中不乏对人的兽性行为的大胆揭示:《红高粱》中的活剥人皮、《丰乳肥臀》中的煮食人肉、《檀香刑》中的凌迟活人、《十三步》中的食死人肉、《丰乳肥臀》中的奸尸、《马驹横穿沼泽》中的人狗交配、《红蝗》中的人驴交配等。不仅如此,莫言还指出,人一旦坏起来就会超过所有的动物,因为“动物都是用本能在做事情,而人除了本能以外,还会想出许多方法来摧残自己的同类”。(12)莫言:《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26页。与莫言持相似看法的不乏其人,比如米兰·昆德拉就将人定义为“一个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将他的邻人推向死亡深渊的生灵”。(13)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7页。需要指出的是,莫言对人性并非持一种完全悲观的态度,而是持一种辩证的态度,莫言认为人的兽性是不正常社会的产物,是特殊的环境使然。比如,莫言在论述战争对人性的影响时这样说:“我想在当年的中国战场上、东南亚的战场上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日军,实际上是一些被异化的、在战争的大环境下变成了野兽的这样一批人,如果这批人回到了正常的生活环境,那么他们很可能要忏悔他们过去的罪行。”(14)莫言:《碎语文学》,第199 页。
与莫言以人与动物的相互映照来反思人的生命现状、揭示人性复杂性的叙事方式不同,沈从文主要通过人与动物相互润泽的方式,凸显动物的治愈能力,以动物做譬喻凸显湘西男性生命的野性美与湘西女性生命的自然美。
其一,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动物不仅作为自然的生命形式存在,而且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中,显示出对恢复人的生命活力的强大治愈能力。《会明》中的伙夫会明渴望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但长时间的休战让他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会明为此很失落。后来,附近的农民送给他一只母鸡后,会明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母鸡身上,当母鸡开始产蛋后,每天收获的鸡卵让昔日颓废的会明变得忙碌而对生活充满信心。当母鸡孵化出小鸡后,会明每天像一位尽职的母亲一样照顾小鸡,他的梦中不再出现血腥的战场,而是梦到小鸡在自己身边吱吱地叫,仿佛在叫他“外公”。类似的人物还有《一个女人》中的三翠,三翠是一个无人疼爱的童养媳,虽然生活忙碌而艰辛,但因为每天忙于照顾饲养的动物而感到生活的充实和美好。她每晚在房后牛栏里小牛吃奶、大牛嚼草声音的帮助下甜蜜入睡。三翠尽管每天很早就要起来放鸡放鸭,当她看见鸡鸭飞出笼子时,三翠却感到很欢喜。当三翠看到鸭子在水里欢欢喜喜呷呷叫时,她就忍不住用石头打鸭子,边打边骂,其实三翠在这样情形下,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欢喜快乐了。
其二,沈从文常用动物作譬喻来彰显湘西男性生命的野性美与湘西女性生命的自然美。在众多的湘西题材小说中,沈从文常常以狮子、老虎、牛、狗等具有强悍生命力的动物来譬喻湘西男性。比如,在《边城》中,沈从文用“老虎”“公牛”来赞美天保和傩送两兄弟的结实强壮;在《柏子》中,沈从文把具有充沛体力的水手柏子比作一头小公牛;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沈从文把豹子赞为“一个人中的虎”;在《龙朱》中,沈从文把龙朱这样一个让女子疯狂的美男子比作狮子。与用猛兽作譬喻来彰显湘西男性生命的野性美不同,沈从文常常用柔弱优美的小动物来彰显湘西女性生命的自然美。比如,沈从文在赞誉翠翠的生命形式时用温柔的黄鹿作为参照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1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64页。类似的女性形象还有《阿黑小史》中的阿黑(小花鹿),《凤子》中的少女(小獐鹿)。与此同时,沈从文还让女性成为小动物的朋友,与动物一起享受生活的乐趣。比如,《一个女人》中的三翠任由小猫吃自己的汤泡饭而不生气;《三三》中的三三时常追逐到处乱跑的鸡,和鸡一同游戏;《边城》中的黄狗忠实陪伴在翠翠身边,与翠翠共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长河》中夭夭的小白狗可以帮助主人完成想做而不便做的事情。
三、“低姿态”背后的生命伦理
动物进入莫言和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首先关乎的是小说的叙事视角问题。叙事视角的变化是现代小说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标志之一,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开始,“低姿态” 叙事就开始成为小说艺术的伟大传统。它主要表现为作家不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以一种低于常人的视角和理解力来看待自身所处的外部世界,它所传达出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亲近世界的方式,同时传达出作家对自身卑微的生存境遇的清醒认识。这种“低姿态”的叙事方式是对长期以来流行的人类中心的质疑和挑战,它从新的视角审视、修补和充实了人性内容。
莫言和沈从文小说中的动物书写,表面上关乎的是小说的叙事视角问题,实际上关乎的是生命伦理这一深层问题。生命伦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道德伦理的价值观,其要义在于“把生命视为天地间的最高律令”(16)魏家文:《两种不同的生命图景——论莫言与沈从文小说的爱情叙事》,《百家评论》2020年第4期。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暗含着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所有的生命形式,它是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的颠覆。在尼采眼里,人类是一种不完满的动物,究其原因在于当人从动物的世界里脱离出来后,原始的动物性痕迹并没有完全消失,甚至比动物更像动物:“你们已经走完了从蠕虫到人类的道路,但你们身上有许多东西仍然是蠕虫,从前你们是猿猴,而即使现在,人也仍然比任何一只猿猴更像猿猴。”(17)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0页。从这个意义上看,作家笔下的动物书写总是关乎人类自身,莫言和沈从文的动物书写也不例外。从总体上看,生命是二者共同关注的对象,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莫言主要是为了表达自己对片面现代化的反思,沈从文主要是为了表达自己对自然人性的赞美和对城市人异化人性的批评。
莫言是一个对生命充满深刻体验的作家,他常常从自己的生命直觉出发来选择自己的文学道路。在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中,莫言以自己的生命直觉发现了“种的退化”的现实问题,指出“人类正在用自身的努力,消除着人类的某些优良的素质。”(18)莫言:《红高粱家族》,第327页。在《红高粱》中,莫言通过对“我爷爷”“我奶奶”自由自在的生命形式和强悍的生命活力的张扬,反衬出“我辈”生命力退化的严酷现实。与此同时,莫言还以动物为参照物,通过对驯化后的奴性生命与驯化前的野性生命的对比,表达了对现代化负面性的反思。在莫言看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在富裕的物质条件下逐渐丧失了自身的生命活力,这是人类和动物共同的悲剧。在莫言看来,动物在被人类驯化后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变成了人类的奴隶,这对动物没有任何好处。正如鲁迅所言:“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19)鲁迅:《略论中国人的脸》,《鲁迅全集》第 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433页。同样,人如果丧失了原始的生命力,对自身的发展同样没有任何好处,无法在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中存活。在莫言看来,人类的进步不仅体现在外在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上,同时也体现在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上。因此,莫言反对的是那种以压抑放弃人的本性的那种单向度的现代化,肯定的是那种让人的内在真实人性与外在体质同时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莫言对野性生命呼唤不是为了否定当下的道德理性和伦理规范,而是希望人类社会的进步不要以丧失人性的本真为代价。在莫言看来,理想的生命形式应该是理性生命和感性生命的协调发展,而不是理性生命的单向度发展。这种对理想生命形式的思考,充分显示出莫言动物书写的深刻性所在。
与莫言相比,沈从文的动物书写主要是出于对自然人性的赞美和对城市人异化人性的批评。在沈从文所构建的湘西世界里,充溢着和谐自由的人性赞歌。其中,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润泽与和谐共存是其重要表现。由于沈从文崇尚的是一种在道家思想主导下的自然人性, 因此沈从文认为只有在这种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存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人性才是理想的人 性,这正是沈从文在他的湘西题材小说中不遗余力地赞美乡下人身上自然人性的深层原因。与此同时,沈从文还用动物的“天性”与“灵性”来反衬、批判都市人性的异化。比如,小说《呆官日记》从一只当了官的狗的视角出发,为读者描绘了一群庸碌无为、思想腐朽的公务员形象,讽刺了那些道貌岸然的城市人。《三三》通过对城市来的男人怕狗的描写,不仅嘲讽了城市男人的胆小,而且寄寓了作家对城市文明的批评。此外,为了表达自己对城市人的厌恶,沈从文在这篇小说中还刻意突出城里人与狗的对立。比如,当三三听到男子充满调戏意味的话后,三三想的是来一只狗将这个人吓倒落到水里再被水冲走;当三三在梦中发现自己因为拒绝把鸡蛋卖给城里人而城里人不走时,她渴望有一只狗出来替自己解围,正想着,忽然从家里就扑出来一条大狗,顷刻就把这两个恶人吓倒落到水里去了。
总之,莫言和沈从文笔下的动物书写,无论是对野性生命的呼唤还是对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美好图景的展示,都体现了作家对生命伦理的张扬。相比之下,莫言不仅批评了片面现代化对人的生命活力和人性的戕害,而且通过揭示人性与兽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事实,证明人性的善恶更多是环境的产物,这就意味着莫言开始超越沈从文在人性问题上所持的“都市恶”与“乡村美”的片面价值立场,开始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人性的善恶问题,这也正是莫言的深刻性所在。二者在动物书写时所采用的“低姿态”叙事方式,表明二者在生命伦理上有着相似的思考与追求,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出二者在思想观念上的遥相呼应。这不仅是对现代小说伟大艺术传统的自觉传承,同时也是二者的小说能得到世界认可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