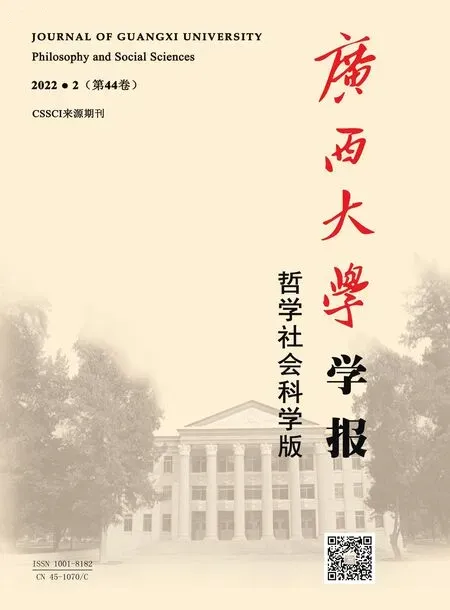论修身工夫与技艺工夫之异同
陈立胜
一、引论
功夫/工夫论研究是近年来儒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在现代日常汉语中,功夫/工夫一词使用大致限定在“工夫茶”、武打“功夫”以及表时间义的“一袋烟工夫”。传统意义上的修身功夫/工夫早已成为“僵尸”词,而涉及此意义的功夫/工夫,则多以“修养”“修行”代之。儒学作为“生命的学问”在本质上是一套自我转化的“为己之学”,理学的“功夫/工夫论”更是身心修炼法门的一大宝藏。但在现代哲学学科知识体系的“筛选”下,功夫/工夫所内含的一套身心转化的实践智慧(“体道”)及其背后的天人合一信念(“道体”),被全盘“格式化”,组装进现代哲学中“知识论”“应用心理学”“形而上学”范畴之下。随着中国哲学主体性意识的觉醒,重新“激活”功夫/工夫话语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学界已明确提出将功夫/工夫引入哲学的主张。
最早尝试对功夫/工夫进行界定的学者当推徐复观。他在其《中国人性论先秦篇》的结论中指出,先秦人性论是由哲人“自己的工夫”所把握到的。而“工夫”虽可概括在广义的“方法”一词之内,但工夫与方法实则有着重要的区别:对自身以外的客观对象加以操作、加工以便达到某种目的,这是“方法”;与此相对,“以自身为对象,尤其是以自身内在的精神为对象,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在人性论则是为了达到潜伏着的生命根源、道德根源的呈现——而加内在的精神以处理、操运的,这才可谓之工夫。人性论的工夫,可以说是人首先对自己生理作用加以批评、澄汰、摆脱;因而向生命的内层迫近,以发现、把握、扩充自己的生命根源、道德根源的,不用手去作的工作”。①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409 页。徐复观将“方法”与“工夫”区别开来,乃是基于工夫是以“自身”为对象,即工夫具有自身反涉义。但很多一般性的技艺工夫如舞蹈、体操、拳术等亦是直接以“自身”为对象,或虑及此,徐复观又特别强调工夫是以“自身内在的精神”为对象。
倪培民近年来致力于功夫哲学的建构,并明确提出将功夫引入哲学的主张。他为功夫下了一个“三维合一”定义:“从‘功力’的角度看,功夫是本体的性质,是通常需要长时间实践修炼,有恰当的方法指导而获得或者开发、彰显的才艺能力。从‘工夫’的角度看,功夫是有恰当的方法指导,为了获得才艺、能力而进行的实践修炼。从‘功法’的角度看,功夫是为了获得才艺、能力而进行长时间实践修炼的方法。”①倪培民:《将“功夫”引入哲学》,《南京大学学报》2011 年第6 期。功夫概念是由才艺能力、实践修炼与方法三要素构成的“三维合一的概念”。这实际上是将围绕功夫/工夫一词的词簇进行综合所得的一个定义。功力即是理学家所说的工夫的“效验”,“功法”(修炼的方法)与“实践修炼”的“工夫”其内涵是重叠的乃至是同一的。理学家所讨论的工夫次第、工夫“入手处”“得力处”与“第一义工夫”“头脑工夫”“根本工夫”“究竟工夫”等均含“功法”与“工夫”两义于一身。的确,“工夫”一词是一“厚概念”,牵涉“本体”(人性论与宇宙秩序)、实际修炼过程及其最终所臻境界。不过,理学家讨论工夫/功夫时,都自觉地避免将功夫/工夫自身与其效验(“功力”)混同。②谢良佐拜见程颐(一说程颢),程子问曰:“近日事如何?”谢良佐对曰:“天下何思何虑。”程子曰:“是则是有此理,贤却发得太早在。”(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426 页。)显然,在程子看来,“道理”是与实际的“体道”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悬空讲道理则只是“效验”,属于揣摩,对塔说相轮。王阳明曾问在坐诸友“比来工夫何似”,一友举虚明意思,阳明曰:“此是说光景。”一友叙今昔异同,阳明曰:“此是说效验。”二友惘然,请是。阳明曰:“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说效验,却是助长外驰病痛,不是工夫。”(王阳明:《传习录上》,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第27 页。)可见理学家讨论工夫/功夫均是着眼于当下实地用功之入手处与过程,而忌谈效验与功力。
杨儒宾则给出了工夫/功夫四要素说:“工夫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它通常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才可以精熟,最后达到预期的境地。有意识、时间、精熟、目的可以视为工夫的四要素。……在今日的日常言语中,‘工夫’一词仍有此涵义。放在理学脉络中看,工夫也是指一种自觉的道德实践,学者需要花费时间不断地从事道德的工作,仁精义熟,最后预期可以达到人格的大而化之之境。”③杨儒宾:《未摄天根岂识人:理学工夫论》,https://www.docin.com/p-2073238037.html与倪培民的三要素说相比,杨儒宾四要素说中“时间”“精熟”两要素相当于前者所说的“工夫”,“目的”相当于“功力”,而“有意识”则强调功夫/工夫的“自觉性”“主动性”,这一要素的确是功夫/工夫内涵不可或缺的,不然,功夫/工夫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教化”观念难以区别。
要之,学界对工夫/功夫的界定均能考虑到功夫/工夫的修身义与一般性的技艺义,但修身功夫/工夫与一般技艺功夫/工夫均曰功夫/工夫,两者之间有何异同?学界对此未见系统论述。鉴于此,本文首先简要勾勒功夫/工夫一词语义演变过程,进而阐述传统儒学的道艺观,在此基础上,从目标定向义、时间历程义与自身反涉义三个方面揭示修身工夫与一般技艺工夫之异同,以期推进对功夫/工夫一词的理解。
二、“功夫”与“工夫”
“功夫”与“工夫”一词含义演化,学界已有较详尽的考察。④林永胜:《功夫试探——以初期佛教译经为线索》,《台大佛学研究》2011 年第21 期;《反工夫的工夫论——以禅宗与阳明学为中心》,《台大佛学研究》2012 年第24 期。“夫”,丈夫也,古代从事徭役工作的都是成年平民男子,故“夫”也指服劳役之人;“功”,原为功绩、功业义,引申出事功、劳作义;“工”,原义为曲尺,除引申为“巧饰”义外,尚有工匠义,如谓“工欲善其事”。
早在建和三年(149 年)的《广汉长王君治石路碑》(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九十八)中就出现了“功夫九百余日,成就通达”一语,故黄生《义府》(卷下)云:“‘功夫’即今俗所谓‘工夫’,不知汉人已有此语。”此处的功夫显然系指役夫、役徒所付出的劳作时间。黄生系明末清初学者,其“‘功夫’即今俗所谓‘工夫’”一语表明,在明末习俗表示时间义通常用“工夫”而非“功夫”一词。“工”“夫”二字连用大约在西晋才开始,在隋代以前的文献中,“工夫”的用例不及“功夫”的十分之一。到了唐代,“工夫”的用例与功夫等量齐观。宋代以降,“工夫”已经成为较主要的用语,但“功夫”一词仍不时被使用。要之,“功夫”“工夫”其最初的含义即是被征调做某项工程的劳动力、人力。而工役是有期限的,故引申出“时间”义(如云“闲工夫”/“闲功夫”),由于功夫/工夫的词义兼有人力与时间的意涵,由此亦衍生出“做事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由花费时间与精力做某事而成就某种能力、本领,达到某种造诣,亦成为功夫/工夫的衍生义。作为被征调的功夫/工夫,其劳作与付出的时间、精力都是“被动”态的,而作为修身、修行意义的功夫/工夫,其劳作与付出的时间、精力则是“主动”态的。换言之,前者功夫的主体是可计量的复数,是“对象化的复数格位”,后者一定是“个人性的单数主格”。①林永胜:《功夫试探——以初期佛教译经为线索》。
修身义上的功夫/工夫最早出自佛教文献。潘平格指出:“工夫二字,起于后世佛老之徒,盖是伦常日用之外另有一事,故说是工夫。”②潘平格:《潘子求仁录辑要》,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256 页。的确,在西晋翻译的佛经中,“功夫”一词就产生了个人做事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义,布施一类的活动蕴含着信徒所付出的心血与精力,故亦被称为“功夫”,功夫即“功德”。后来布施与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一道作为“完整的六度条目”而被通称为功夫。“功夫”遂具备了“欲达到某一修行目标所设想出的方法或手段”义。由于“禅定”与“智慧”二门被认为是成佛的关键,故在唐代开始的佛教典籍中,“功夫”通常就是用来指坐禅这种修养方式。坐禅的过程非常复杂,它包含着一系列身心活动的自觉调整:先是趺坐,然后续以“数息、随息、止、观、还、净”六妙法门。在佛教那里,功夫/工夫变成了“个体将其身心进行高度的集中,以投入某种具有可重复性、窍门性、进阶性的仪式化操作技法”。③林永胜:《功夫试探——以初期佛教译经为线索》。
由此佛教的功夫/工夫意涵,回头看儒家文献,最能呈现这种相应修身功夫/工夫的文本莫过于《大学》。《大学》“三纲八目”终始条理、次第井然,由内而外、由己而人,内外一如、人己一体,其修己(内圣)向度不仅可与佛教的功夫/工夫相媲美,其安人(外王)向度更被儒者视为与佛教区别所在。《大学》由《礼记》普通一篇一跃而成为《四书》之一,并被誉为“孔氏之遗书”,“初学入德之门”,良有以也。
功夫/工夫一词进入儒学文献始于邵雍、张载与二程兄弟。在起始,“功夫”与“工夫”两词就未加区别而混同使用。即便在同一段落中,两词也交替出现:“尧夫易数甚精。自来推长历者,至久必差,惟尧夫不然,指一二近事,当面可验。”明道云:“待要传与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学,须是二十年功夫。”④《河南程氏外书第十二》(明弘治陈宣刻本),今中华书局本《二程集》统一为“工夫”。这种混用的情形后来屡见于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文献中:
问:何谓工夫?先生不答,久之,乃曰:“圣门功夫,自有一条坦然路径。诸公每日理会何事?所谓功夫者,不过居敬穷理以修身也。……”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⑤朱杰人等:《朱子语类》卷二十八,《朱子全书》(第1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第1029 页。
与“工夫”相连的习语如作工夫、做工夫、用工夫、下工夫、费工夫、见工夫,也同样见于与“功夫”相连的习语如作功夫、做功夫、用功夫、下功夫、费功夫、见功夫。即便今人专指武术的“功夫”在清末小说如《彭公案》《小五义》中,也有“练过了一身武工夫”“文有文才,武有武工夫”的说法。
综上,“功夫”与“工夫”在宋明理学文献中通常是不加区别而混同、交替使用的。只有在现代汉语中“功夫”比“工夫”一词多了一层“武术技能”的含义。为了行文方便,以下统一使用“工夫”。
三、儒学传统的“道艺观”
一切技艺活动都需要付出精力、花费时间,反复习练,方能达到相应的造诣、获得某种不同凡响的能力,故凡技艺活动均有其工夫,将修身工夫与一般技艺活动之工夫(简称“技艺工夫”)相比,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工夫之为工夫的一般性特征,也有助于我们把握修身工夫有别一般技艺工夫之独特性。
实际上,在孔子所设想的君子修养之道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游艺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但自秦汉以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几近荒废,朱子感慨道:“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晓。御,是而今无车。书,古人皆理会得,如偏旁、义理皆晓,这也是一事。数,是算数,而今人皆不理会。六者皆实用,无一可缺。而今人是从头到尾,皆无用。”故在朱子看来,“艺”虽是“小物”,“似若无紧切底事”,“零碎底物事”,惟“志道”“据德”“依仁”方是工夫“主脑”,是“本”,但“游艺”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环:“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①朱杰人等:《朱子语类》卷三十四,《朱子全书》(第15 册),第1217—1218 页。此一说法亦为阳明所继承:“琴瑟简编,学者不可无;盖有业以居之,心就不放。”②王阳明:《传习录下》,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第114 页。
阳明心学中,唐顺之与顾应祥踵事增华,将“艺”之精微义发挥得淋漓尽致。
唐顺之继承了朱子游艺与存心的关系说:“若使尽捐书册,尽弃技能,兀然槁形灰心,此亦非大难事。而精神无凝聚处,亦自不免暗路漏泄。若就从观书、学技中将此心苦炼一番,使观书而燥火不生,学技而妄念不起,此亦对病下针之法,未可便废也。燥火不因观书而有,特因观书而发耳。妄念不因学技而有,特因学技而发耳。”③唐顺之:《答姪孙一麟》,《荆川先生文集》卷六,马美信、黄毅点校:《唐顺之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263 页。技艺之学可以磨练心性、凝聚精神,阳明注重“事上磨练”,技艺之学作为“一事”,不失是一种去“燥火”、息“妄念”的磨练方式。不啻如此,唐顺之还进一步提出“德艺一致”说:
至于道德、性命、技艺之辨,古人虽以六德、六艺分言,然德非虚器,其切实应用处即谓之艺,艺非粗迹,其精义致用处即谓之德。故古人终日从事于六艺之间,非特以实用之不可缺而姑从事云耳,盖即此而鼓舞凝聚其精神,坚忍操炼其筋骨,沉潜缜密其心思,以类万物而通神明。故曰洒扫应对精义入神,只是一理。艺之精处即是心精,艺之粗处即是心粗,非二致也。④唐顺之:《答俞教谕》,《荆川先生文集》卷五,马美信、黄毅点校:《唐顺之集》,第195 页。
窃以六艺之学,皆先王所以寓精神心术之妙,非特以资实用而已。《传》曰“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顾得其数而昧于其义,则九九之技小道泥于致远,是曲艺之所以艺成而下也。即其数而穷其义,则参伍错综之用,可以成变化而行鬼神,是儒者之所以游于艺也。游于艺,则艺也者即所谓德成而上也。⑤唐顺之:《与顾箬溪》,《荆川先生文集》卷七,马美信、黄毅点校:《唐顺之集》,第305 页。
“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必须落实于具体的生存活动之中,此落实处(“切实应用处”)即是“艺”。而艺之“精义致用”即谓之“德”,“精义致用”语出《周易·系辞》:“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能够深入“艺”之精微处,知其所以然,则自可致用。艺之粗迹只是“小道”,是“曲艺”;艺之精处则义理存焉,是“游艺”。
唐顺之好友顾应祥则进一步提出“君子之学自性命道德之外,皆艺也”之主张:
或曰:“下棋损闲心,且勿学。”余曰:“君子之学自性命道德之外,何者非艺也?彼焦心苦思,求功于文字者,亦何益于身心乎?余以适吾意耳,庸何伤哉!”
初贱子之好算也,士夫闻之必问之曰:“能占验乎?”答曰:“不能。”又曰:“知国家兴废乎?”曰:“不能。”其人莞尔曰:“然则何为?”不得已,应之曰:“将以造历。”其人愕然曰:“是固有用之学也。”“君子之学自性命道德之外,皆艺也。彼摛章绘句,取媚于人以求富贵者,较之以数为乐,求自得于心者,故有间矣。”①顾应祥:《围棋势选序》、《复唐荆川内翰书》、《崇雅堂全集》卷九、《崇雅堂全集》卷十三,万历三十八年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感谢宁波大学陈昊博士惠赠影印本。
顾应祥是明代的大数学家,知识渊博,百家九流,无所不窥。他将技艺视为“适意”“求自得于心”之学,而与“道德性命”之学一起构成了“君子之学”的主题。与朱子“本末”论述不同,“君子之学自性命道德之外,皆艺也”的主张实际上是要证成技艺之学的相对独立性:它既有自身知识、技能的内在理路,又能有益于身心而给人以精神上的愉悦。②关于顾应祥与唐顺之的知识兴趣,参见刘荣茂:《阳明学派的知识面向——以顾应祥、唐顺之为中心》,《哲学与文化》2020 年第6 期。
修身工夫与一般技艺工夫其相通处还在于,二者作为“工夫”都是“实学”,都是一反复操作的学习过程。邹守益说:“世俗说一‘学’字,未有徒腾口说而不措诸行者。如学诗则必哦句咏字,学文则必操觚染翰。至于曲艺,学木工则必操斧持矩,学缝匠则必执剪裁衣。至于学圣人之道,乃坐谈口耳,以孝弟忠信敷为辞说,以饵科第,而事父从兄判若不相关,可为善学乎?”③邹守益:《复初书院讲章》,董平编校整理:《邹守益集》卷十五,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年版,第723 页。实际上《庄子》论道精彩动人的章节也多是技艺一类的寓言故事,如“庖丁解牛”(《养生主》)、“轮扁斫轮”(《天道》)、“佝偻者承”、“津人操舟”、“丈人游水”、“梓庆削木为鐻”、“纪渻子养斗鸡”(《达生》)、“大马之捶钩者”(《知北游》)、“匠石运斤成风”(《徐无鬼》)等,这些技艺故事均展示“道进乎技”之一面,生动地刻画出技艺人“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心性世界。换言之,“道”与“技”相通相贯,李贽说:“以道与技为二,非也。造圣则圣,入神则神,技即道耳。”④李贽:《樊敏碑后》,《焚书》卷五,张建业主编:《李贽文集》(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版,第203 页。王叔岷认为“道进乎技”之“进”字与“尽”字通用:“道是自然,技乃人为。尽乎人为,则合乎自然矣。”⑤王叔岷:《庄子校诠》(上),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版,第105 页。
那么,修身工夫与技艺工夫之异同何在?
四、修身工夫与技艺工夫之异同
第一,目标定向义。修身工夫与技艺工夫均旨在相应能力的培育,故均是一目标定向下的自觉的实践过程。
修身工夫牵涉身心活动的整体取向,它将认知、情感、意志聚焦于成为“君子”“圣贤”这一目标,其能力培养着重在德性。修身工夫作为一种目标定向的实践活动在整体上是一种意向性活动,就其将人生自觉地加以整体定向而言,它是一种立志行动。王阳明说:“学本于立志,志立而学问之功过半矣。”⑥王阳明:《与克彰太叔》,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第983 页。又说:“合着本体的,是工夫;做得工夫的,方识本体。”⑦王阳明:《传习录拾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第1167 页。立志于成圣,即是合着本体,即是工夫。就其注重培养德性而论,它是一种旨在成就理想人格的实践活动。
技艺工夫亦有明确的目标及其相应的认知、情感、意志聚焦,但这种技艺的学习是人的某种具体能力的培养,这种具体的能力固然能够表现出人性所能达到的某种运动能力、创造能力、技巧能力的高度,但缺乏这种能力对“人之为人”的人性体验至多构成一种“遗憾”,但不会是一种“后悔”。一个人不会打马球,对于其丰富多彩的人生体验而言或是一种“遗憾”,但人却不会因此而“后悔”当初为何不学习打马球。因为在人身上有无限的展示自己运动能力的方式,至于哪种能力成为自己的“特长”“爱好”,既取决于自己的禀赋,也取决于后天的成长环境。一颗麦粒埋入土中,发芽、抽干、长叶、吐穗,最终成熟,它的本质就完全实现了。人是必有一死的存在者,其一生纵然多么丰富多彩,在其终结之际却不能说他充分实现了自己身上的各种潜能。人生倘若像电脑一样拥有重新启动模式,相信很多人的人生会有所不同。
修身工夫所培养的不是某种特殊的技艺能力,而是人之为人的在世能力。这种人之为人的能力构成了人的尊严所在。缺乏这种能力,人作为人是不完整的。在此意义上,不妨将修身工夫所培养的能力称为“构成性能力”(constitutive abilities),即构成人之为人的能力,它跟一般的技艺能力有着根本的区别。王阳明对此有专门阐述:“今之习技艺者有师,习举业者求声利者有师,彼诚知技艺之可以得衣食,举业之可以得声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诚知己之性分,有急于衣食官爵者,孰肯从而求师哉!夫技艺之不习,不过乏衣食;举业之不习,不过无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为人矣。人顾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①王阳明:《答储柴墟二》,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一,第814 页。修身工夫旨在培养人之尽己之“性分”的能力,缺乏这一能力,人则“不得为人”。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修身工夫的目标始终定位于“自我转化”上面。所谓修身工夫不过是一种实现根本转变的手段,其本质即在于从深陷于存在的困扰(“长戚戚”)中摆脱出来,并与终极实在(道体)结合在一起,从而证成一全新的人格(成圣)。一般技艺工夫成就的往往是“匠人”“艺人”,而修身工夫历来注重“君子不器”,故更强调一“全人”人格之培育。实际上,作为一种终极的自我转化之道的修身工夫在不同宗教传统中侧重点或有不同,但其结构则是一致的。②斯特伦:《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金泽、何其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2—13 页。
必须指出,我们将修身工夫所培养的能力称为“构成性能力”,这绝不意味着一般性的技艺活动就不具有修身的意义,也不意味着修身工夫可以完全脱离一般的技艺活动而展开。传统的技艺文化历来重视“德艺一致”“德艺双馨”,“艺”之培养与“德”之提升不可分离。而在传统修身工夫论中,事上磨练一向是被理学家着重强调的。既然心性世界必须在人实际的生存活动中得到磨练与成长,而技艺活动本来就跟人的生存活动分不开,或者说技艺工夫不过是一种专题化、仪式化的生存活动而已,那么修身活动与技艺活动确实是无法截然分开的。
第二,时间历程义。“登高自卑,行远自迩”,修身工夫与技艺工夫均有一个由浅及深、由近及远的展开过程。这个“时间历程”既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时间,也不是心理意义上的时间,而是由工夫修炼程度所刻画的“节点”与“进程”,因而呈现出次第性、阶段性特征。
以心灵修炼而言,《大学》讲“止、定、静、安、虑、得”,佛教《瑜伽师地论》讲“九住心”(“内住”“等住”“安住”“近住”“调顺住”“寂静住”“最极安静”“专注一趣”“等持”),《庄子·大宗师》讲“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基督宗教讲灵性修炼的三十阶梯[第1—3 阶梯以信为基础,是切断与世界的联系的阶梯;第4—26 阶梯以望为力量,是建立美德的阶梯(其中4—7 是心态的转化,8—23 是美德的培育,24—26 是灵性的更新);第27—30阶梯以爱为依归,是与上帝联合的阶梯],③克里马卡斯(John Climacus):《神圣攀登的天梯》(The Ladder of Divine Ascent),许列民译,香港:道风书社,2012 年版,第xxiii 页。都无非指示出修身工夫有其自然展开的次第。
工夫次第的展开也表现为由“生”到“熟”到“忘”的过程。庄子是善于描述技艺工夫由“生”到“熟”的能手,在他的笔下,善游者“忘水”,善解牛者“忘牛”。张行成解“精义入神以致用”一语时指出:“惟至诚为能生精,惟至精为能生神。此生出之本,有至理在其间,然不过乎专一而已。精义入神,不知所以然而然,故能致用也。津人操舟,偻者承蜩,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皆入神致用之义。在孟子,则曰:‘为仁在熟之而已。’精则熟,熟则妙。天下之事欲进乎神者,要在于熟,无他巧也。”④张行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邵雍著:《皇极经世书》,郭彧、于天宝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版,第1397—1398 页。朱子也一度将儒门上学下达工夫拟之为庖丁解牛技艺:“圣人便只说‘下学上达’,即这个便是道理,别更那有道理?只是这个熟处,自见精微。”又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只是就近处做得熟,便是尧、舜。圣人与庸凡之分,只是个熟与不熟,庖丁解牛,莫不中节。古之善书者亦造神妙。”①朱杰人等:《朱子语类》卷十八,《朱子全书》(第14 册),第625 页。苏轼《小篆般若心经赞》以学写字、学说话为例生动描述了这一“熟能生巧”的过程:
草隶用世今千载,少而习之手所安。如舌于言无拣择,终日应对惟所问。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墙壁,纵复学之能粗通,操笔欲下仰寻索。譬如鹦鹉学人语,所习则能否则默。心存形声与点画,何暇复求字外意。世人初不离世间,而欲学出世间法。举足动念皆尘垢,而以俄顷作禅律。禅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处安得禅。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间无篆亦无隶。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正使匆匆不少暇,倏忽千百初无难。稽首般若多心经,请观何处非般若。②苏轼:《苏轼文集》卷二十一,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618 页。埃克哈特在阐述将上帝引入自己内心深处的修炼活动时也有类似的比喻:“这就像学书法的人,一开始他必须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到每一个单独的字母,铭记在心,慢慢熟练了,就不必左思右想,就可以奋笔疾书。”埃克哈特:《埃克哈特大师文集》,荣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12 页。
语言是透明的,人之说话直接就将注意力集中于话语所指涉的实事上面,而不是话语的发音与声调上。同样,人之写字其心思直接就在字之所指涉的实事上面,而不是字迹、字形、字体与笔画上面(“无篆亦无隶”),亦不是写字的手与笔上面(“心忘其手手忘笔”),甚至也不是写字这一主体活动上面(“笔自落纸非我使”)。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四体不言而喻”,都是真积力久、默识心通之表现,都是功夫纯熟后所展示出的“从容和节之妙”。罗汝芳说:“世间各色伎俩,熟极皆可语圣,况以道而为学乎!”又说:“天下之事,只在于习,习惯自然。”③方祖猷:《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年版,第274、347 页。
汉学家毕来德(J.F.Billeter)曾指出庄子哲学的核心是由“人”而“天”的机制转换:“人的机制”是一种意向性机制,一种自觉谋划、计度、造作的活动机制,“天的机制”则是一种自发、自然、浑全的活动机制。而由人而天机制的转换无非是由故意的、有意识的活动方式向浑全的、深层的、自然的运作方式转变:“原来有意识地控制并调节活动的意识,忽然被一种浑整许多的‘事物之运作’取代,而这一运作则解除了意识一大部分的负累,使人不再使劲费力,这时我们所有的官能与潜力,无论是已知的还是未知的,都一同组合起来,往我们期待的方向行动了,而其共同协作现在已具备了必然的特征。”④毕来德:《庄子四讲》,宋刚译,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45—46 页。对毕来德由人而天的机制转换与新主体观的评论与研究参见陈赟:《庄子哲学的精神》第七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235—254 页。而“忘”则标志着“天的机制”转换的发生,“游”与“神”则标志着“天的机制”运作特征。毕来德所描述庄子技艺工夫中的这种由人而天的机制转换同样也见于儒家修身工夫之中。实际上儒学成圣的工夫追求在根本上即是一由“人”而“天”的工夫历程,即是由“天德良能”成为全部生命运作机制的过程。张载《正蒙·三十第十一》即说夫子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与天同德,不思不勉,从容中道”。在儒学尤其是宋明儒学的主体性哲学中,如无修身工夫,则常人之应物不免“动于气”,“自私而用智”,“憧憧往来”,疲于应付而有累;惟“一循天理”,则“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动亦定”,“静亦定”。孔子所要求的四毋工夫(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所要求的“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程颢所要求的“定性”、张载所说的“天德良能”、朱子所说的“豁然贯通”、阳明所称的“无善无恶”、王艮所说的“良知致”,等等,在根本上都是要由“人的机制”转换为“天的机制”。周敦颐一句“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通书·志学第十》)已道破其“天机”。⑤周敦颐:《周敦颐集》卷二,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版,第22 页。
阳明弟子薛侃曾将为学工夫分为三节:“初则舍非求是,中则有是无非,后则是非俱忘。”⑥薛侃:《研几录》,陈椰编校:《薛侃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版,第35 页。显然工夫的终极境界都是“忘”,为善去恶的不断努力最终让“良知”如如呈现其自身,一切人为的规则意识、一切人为的善之造作与计度均被“化”掉、“忘”掉,天的力量(良知良能)沛然莫之能御、不容已地展开其自身。阳明另一弟子王畿则将悟道工夫分为三种:“入悟有三:有从言而入者,有从静坐而入者,有从人情事变练习而入者。得于言者,谓之解悟,触发印证,未离言诠,譬之门外之宝,非己家珍;得于静坐者,谓之证悟,收摄保聚,犹有待于境,譬之浊水初澄,浊根尚在,才遇风波,易于淆动;得于练习者,谓之彻悟,摩砻煅炼,左右逢源,譬之湛体冷然,本来晶莹,愈震荡愈凝寂,不可得而澄淆也。……学至于忘,悟其几矣乎!”①吴震:《王畿集》卷十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年版,第494 页。对王畿悟说的阐述参见张卫红:《由凡至圣:王阳明体悟本心的工夫阶次:以王龙溪〈悟说〉〈滁阳会语〉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哲学史》2013 年第8 期。阳明自谓其良知说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此即王畿所说的“从人情事变练习而入者”;“学至于忘”之“忘”是由“人”而“天”的标志;“左右逢源”之“源”则是深不可测的溥博渊泉,即生生不息、不犯做手的天德良能自身。
修身工夫与技艺工夫均有一个由浅及深、由生及熟及忘、由人而天的展开过程。两者的区别在于修身工夫强调这个过程是变化气质的过程,是人性中“仁”的力量不断地涌现(“体仁”)与对一切遮蔽“仁”的习气、私欲不断地突破与克服(“制欲”)。这一时间历程在根本上也是人格不断突破、不断提升的过程,孔子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即是一典范。这些人生历程的“节点”宛若“路标”,不仅反映了夫子一生修身工夫的轨迹,更为沿着这些路标前行的后继者提供了一个个自我反省的“契机”。通过这个契机,原本自是人生自然生命的年龄点以十五、十年为界,不断唤起“临界”者蓦然回首,对其个人以往经历的生命整体进行反思、省察,“行年”意识、“临界”意识与修身的“行己”意识交迭在一起构成了修行者的年龄意识。而就“由人而天”的转换机制看,修身工夫所臻天德良能之“天境”在无为、无心、自然、不言、何思何虑、无声无臭面向上与技艺工夫是一致的;不过此只是“作用”面向上的一致。除此之外,修身工夫还具有生生不息“由仁义行”的一面和《礼记·孔子闲居篇》所说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这一全覆、遍载、普照万物的一面。而技艺工夫则侧重于让身体“动手”能力、身体的掌控、操作能力以及创造能力从“人为”“造作”中摆脱出来而不断趋向自然、自如。
第三,自身反涉义。修身工夫与技艺工夫均注重某种能力的培养,故最终都是自身反涉的,即落实于一己的身心上面。
一般的技艺工夫要借助于某种工具、器械而习得某种技能。在工夫习练中,习者对其所使用的工具或器械有一从“生疏”到“熟练”的过程,最终工具或器械会成为他肢体的一部分,或准确讲成为他肢体的某种“延伸”。在这个工夫习练的过程中,对工具或器械的使用在本质上是自身反涉的:如相应的心态的调适、身体姿态的变化、呼吸的控制等。而不借助任何工具的技艺活动如体操、气功、武术、舞蹈一类纯粹“身体技艺”其一举一动直接是自身反涉的。
修身工夫其对象当然是“身己”,即自己、自身。此“自身”作为“修”的对象,跟一般被修理的对象如器物截然不同。它不是一个“现成的存在者”,而是一个有待成长、有待成就的活生生的“存在”(海德格尔所谓的“此在”)。这个“此在”究竟如何展开其“在世之在”,端赖其自身的筹划。人这一根本性的存在地位决定了修身工夫本质上即是一自身反涉的活动。人自身即是一“作者”,其一己的人生即是其“创作”的对象。一件雕塑的作者在“创作”其作品时,“作品”自身并不能“感受”到、“自觉”到被“创作”,而作为修身的对象,“自身”则能感受到、自觉到被“修”、被“塑造”,因为“创作者”与“被创造者”本是同一“此在”。一个无端发怒的人一旦意识到、自觉到其发怒的“无端”性,怒火即会得到抑制,这正是修身工夫自反性的表现!人情事变,不外得失荣辱,不外喜怒哀乐,而修身工夫亦不外在此得失荣辱、喜怒哀乐的自反、自省中展开。当然体操、气功、拳术、舞蹈一类纯粹“身体技艺”活动,其身体姿态的塑造、运气的调控当下即是自知、自反的,活动的主体与客体亦是同一“此在”。
那么,修身工夫与一般技艺工夫在自身反涉义上有何区别?第一,一般技艺工夫的自身反涉性只在该技艺工夫展开时段表现出来。如一个击剑运动员在击剑活动中保持着相应的“精气神”的自反性调整,但在击剑活动结束后,他作为一个常人,其“精气神”又重新回到平常状态,当然他的一举一动也可能会让人感受到某种击剑运动员的精神气质。换言之,一般性技艺工夫有其应用的场所与时机,非其地、非其时则技无所施。如庄子笔下的匠石运斤,只有在信任他的“郢人”面前方能施展其技,一旦离开郢人,则“无以为质”,其技亦无所展开了。而修身工夫将整体生命作为“修”的对象,故其自身反涉性并不限于某个时段。修身工夫自身反涉性是在修身主体在世的生存活动中,在与他者(天、地、人、物)具体的交往过程中,随时、随处、随机展开的。第二,一般技艺工夫自身反涉的内容聚焦于运动或创作心态的调整,而修身工夫自身反涉的内容则是道德心性,当然两者也不能截然区隔。如程颢就讲过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①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三,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60 页。第三,修身工夫的自身反涉性实有两个向度,一是在待人接物过程中行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反身而诚这一自反性,即将世俗指向他者的求全责备的外向性目光逆转为指向自身的自我审查目光,二是在整体的人生过程中始终对自己的言行举止与心理活动保持一种自反性的观照(“慎独”工夫)。修身工夫这两种自反性究极而言都是要返归“本心”“良知”,举凡“私欲之萌”“客气之动”以及“怠心、忽心、懆心、妒心、忿心、贪心、傲心、吝心”之生均反之于本心、良知,则私欲、客气与诸习心自然退消。②王阳明:《示弟立志说》,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60 页。
五、结论
儒家传统中,自孔子倡导志道与游艺,至阳明心学则明确提出“德艺一致”“道技不二”“君子之学自性命道德之外,皆艺也”之主张,学“道”与学“艺”密不可分。
修身工夫与技艺工夫皆曰“工夫”,固有其相通的一面,概之有三:
第一,修身工夫与技艺工夫均旨在相应的能力的培育,故均是一目标定向下的自觉的实践过程。第二,修身工夫与技艺工夫均有一个由浅及深、由生及熟及忘的时间历程,这一历程在本质上是由“人的机制”转变为“天的机制”。第三,修身工夫与技艺工夫均注重某种能力的培养,故最终都是自身反涉的,即落实于一己的身心上面。
但儒学自孔子始即强调“君子不器”,修身工夫与注重“成器”的技艺工夫自然有其重要的区别。
第一,修身工夫强调人之一生即是一“成为”人的过程,即是一变化气质的过程,故其培养能力均是人之为人的“构成性能力”,而技艺工夫则侧重培养人的“动手”能力、创造能力以及身体掌控与操作能力。就此而言,修身工夫旨在完成根本性的自我转化,成就一“全人”之人格,技艺工夫则旨在成就一“匠人”“艺人”之人格。第二,修身工夫所完成的“由人而天”的“机制转化”乃是人格不断突破与提升的过程,最终与天道所启示的无私之爱合一,而技艺工夫则侧重一切技艺活动从“人为”“造作”中摆脱出来而不断趋向自然、自如而不自知。第三,修身工夫自身反涉性是全时段地体现在修身主体在世的生存活动之中的,其自身反涉的内容是一切行动、意念所系的道德心性。而一般技艺工夫的自身反涉性只在该技艺工夫展开时段表现出来,其自身反涉的内容也聚焦于与运动或创作联系在一起的心态之调整。
需要补充的是,无论是修身工夫抑或是技艺工夫都牵涉到可否授受及如何授受的问题,就工夫之为己、切己而言,一切工夫都是第一人称的切身活动,这种切身性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故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但工夫也是在一个相应的共同体中得到“传承”的,故有其“窍门”与“口诀”,无论修身工夫抑或是技艺工夫,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