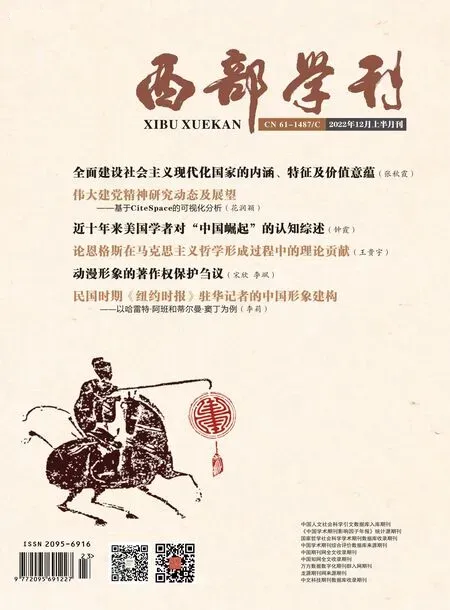晚清清水江儒商的义利观
——以一起山场产权纠纷案为例
曹 宽
清代中晚期,贵州省东南部清水江地区因从事木材贸易而获得财富的家族往往令子弟入学从儒,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文化实力,借此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一个兼具商人身份与儒学文化背景的儒商群体便由此诞生。这些儒商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往往以儒家伦理道德约束自己,遵从“谋利以义”的价值观,在面对利益与道义的冲突时,他们将道义作为优先考虑的选择。
清水江地区自明清时期便因繁盛的木材贸易而闻名,据乾隆时期的贵州巡抚爱必达记载:“自清江以下至茅坪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无隙,土无漏阴,栋梁杗桷之材,靡不具备。坎坎之声,铿訇空谷,商贾络绎于道,编巨筏放之大江,转运于江淮间者产于此也。”[1]随着与中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儒家思想逐渐传入该地区,并被当地人民接受、吸纳,对他们的处世之道和商业伦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义在利先”的价值观便是这种影响的一个突出表现。光绪年间,清水江畔的文斗寨发生了一起产权纠纷案,案件当事人在处理这起纠纷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他们重义轻利的儒商风范。
一、山场产权纠纷的始末与焦点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文斗寨的姜东山、姜登程等人被卷入一起山场产权纠纷,因而致信族中德高望重的姜德相求助。在信中,姜东山等人声称其拥有一片名为汪度库的山场的所有权,并有契据为证,“夫此方山场……橘子有瓣,核桃有间,各契朗然。况我等于道光九年砍一届,有分单、买契可据。同治十年砍一届,有胡家栽手契可据。后又开挖种栽,其人现在。栽股之契非诬,躬逢目睹,有何异论?”[2]纠纷的对象——姜登程也拿出了一张购买该山场股权的契据。两下争执,于是先由中人出面,“查契勘山,许其各管各业,两下俱遵”,然而对方旋即反悔,随后宗族亲属前来劝解,可是姜东山等人认为家老有袒护对方的嫌疑,于是绕过鸣神裁判的步骤,直接将此事上报官府。
在另一封姜东山等人写给族中子弟的信中,可以得知姜德相回绝了姜东山等人的请求,为了向后辈表明心迹,姜东山等人用更加激烈的言辞表达了他们如此行事的动机:“我等老年,既称忠厚,汝等年轻,亦学忠厚,势必弃祖业与谋主,才为忠厚乎……银木总无多,清白之祖业,即可让与谋主,斯不为造孽乎?”这场纠纷发展到最后,姜东山等人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再是山场的价值,他们的目的变成了证明这份祖业的“清白”,并借此为后生晚辈做出表率。
综览事件全貌,这起纠纷的焦点集中于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判定纠纷双方是非的关键是什么?答案是契据,民间契约文书在清水江一带具有习惯法意义上的效力,在经济纠纷中,谁能拿出契据,谁就占理,谁就拥有道义上的优越性。姜东山等人认为己方的正义无可置疑,因为“我等之业,原于始祖,云字派买来,至今宣字,经管八代,契据身逢,毫无异议”,而对方则是“陡将文浩得买启华之契,指鹿为马”。
第二,既然姜东山等人的契据更可信,为何中人、寨老都劝姜东山等息事宁人,将股权分与对方?姜东山等人认为这是因为其中有“奸宄教唆”,至于所谓的“奸宄”,自然就是那“阴贼险狠”的对手。这样的可能性自然是存在的,但这些中人、寨老或许也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在他们看来,寨中、族中的安定无事才是最重要的,没必要为了这点矛盾把事情闹大。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种对集体来说损失更小、获利更大的策略,而姜东山等人自然不这么看,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实际的侵害。
第三,姜德相为何拒绝姜东山等人的求助?与试图做和事佬的中人、寨老不同,姜德相质疑姜东山等人的焦点在于“不鸣神而鸣官,得无虚且畏之拟”,这既是质疑姜东山等不肯鸣神,是否心里有鬼,也是质疑姜东山等人提起诉讼的程序是否正义。在清水江地区,一般的民间纠纷在上报官府之前还有鸣神裁判这一道步骤,就像现今的法庭诉讼有预审、初审直到终审几个环节,姜德相认为鸣神是解决争端的程序中不应绕过的一环。姜东山等人则认为鸣神的适用范围是“二比之契,股同界异,界同股异;或上下一色之木,而我独截砍下段,以为己有;或谓那家之契,是私造混争”这几种情况,而他们对自己持有的证据有十足的把握,不想再陪对方演这出贼喊捉贼的闹剧,或许他们也担心在鸣神的过程中,对方又使出阴谋诡计让形势变得愈发不利,为避免夜长梦多,才打算借助官府和法律的力量尽快对对方加以制裁。
可以发现,无论是作为当事人的姜东山等人,还是旁观事件的姜德相,他们评价是非的尺度都是道义而非利益,这种“先义后利”的价值观与他们身具的儒学文化背景是息息相关的。
二、纠纷当事人的儒学背景
在写给族中子弟的信中第一句,姜东山等人便写道:“圣人云:使四方不辱命,斯可谓士。”此典出自《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3]姜东山等人引用此句,是为了责备后辈在面见姜德相求助时未能完成使命,申明己方的立场。由此不难看出,姜东山等人不但对《论语》之类儒家经典颇为娴熟,而且将儒家理想的“士”的形象作为对家族子弟的期许。在此信末尾,姜东山等人再次谆谆叮嘱:“勿辱祖宗以辱子孙,斯可谓之士矣。至于考试,各要精研,伫候捷音,曷胜翘望。”可以看出,在姜东山等人的培养下,姜氏年轻一代也纷纷入学受教,以参加考试获取功名为最重要目标。
然而姜氏家族却并非书香门第,而是当地的地主富商。以为首的姜东山为例,在文斗寨发现的契约文书中,有十余份老契、老约均外批“东山家存”字样,这些老契虽系故纸,却是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需要交付与该片土地新的所有者作为凭据的,姜东山家存有这么多老契,说明他在后来的交易中取得了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那么他的身家自然非同一般。作为姜氏家族的后辈,这些出身商人家庭的年轻人以后必然会继承家业——参与这次纠纷的调解过程就是对他们的历练,而家族对他们抱有通过科举路径走向仕途的期待,儒学文化背景与商人身份在他们的身上是并行不悖的。
姜东山等人求助的对象姜德相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姜德相出身于偏远的文斗寨,却考中了光绪年间最后一届文举人,他能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既赖其天资聪颖,又得益于其家世渊源。姜德相家族的发迹始于其五世祖姜仕朝。姜仕朝出身贫苦,但善于经营,他趁嘉庆年间清水江下游发生“争江”事件,江路阻塞的机会,以低价大量买进林农囤积的木材,在江路疏通后以高价卖给前来采购的商人,由此一夜暴富,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姜仕朝在发家之后有感于教育的重要性,不惜重金从府城聘请名师来家执教,其子姜载渭更兴办学校,将家中子弟送去读书,由此在家族中确立了崇儒重道的文化观念[4]。姜仕朝的后人被称为文斗寨“三大房”,其中多有因子弟入学补廪或捐监拔贡而成为当地名流者,姜德相作为后辈中的佼佼者,更是考取功名,进一步巩固了家族的地位。
无论从姜东山还是姜德相家族的历史中,都可以看到一条由经济实力转化为文化实力的发展脉络。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百姓被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士”地位最高,而“商”地位最低,“士”是商人群体虽有财富也难以从阶层上超越的对象。虽然自明代以来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商人地位有所提升,但士商之辨仍然存在。明代李维桢为新安盐商蒋次公所作的墓表中便有这样的表述:“国有四民,士为上,农次之,最后者工商,而天下讳言贾……士大夫至讳与贾人交矣。”[5]可见当时社会的一般价值观便是如此。因此不难理解,商人即便挣得大量钱财,却始终割舍不下考科举求功名,由商入“士”进而“入仕”的情结,不能实现于己身,便通过兴办教育等方式令子孙后代入学从儒。从商的家业自然不能舍弃,又兼以从儒学文的背景,于是几代之后,这些地主富家的后人便拥有了亦儒亦商的双重身份背景。在距离中原朝廷颇为遥远的文斗寨,姜氏家族的发展史证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影响到了这一地区,“四民”之说本就是儒者掌握社会文化的话语权而来的产物,而姜东山等人身为地主商人,却将“士”作为对子侄的期望,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
可以看到,在这次争夺山场产权的纠纷中,无论当事人还是相关人士都具备相当程度的儒学文化背景,至于将来可能仲裁此案的地方官员,无疑也是儒学出身。既然各方文化背景接近,那么儒学文化,或者说建立在儒家伦理上的价值理念,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对纠纷的处理与解决,而在本案中影响最大的,无疑就是当事人与调解人关于“义”与“利”的权衡。
三、儒家文化与儒商义利观
姜东山等人的义利观受儒家文化影响极深,而在传统儒家学说中,对义利关系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这两种看法都肯定“义”是为人所应具有的美德,区别在于对“利”的取舍。一种看法认为:“利”纯粹是身外之物,非但不应主动求取,甚至有妨害君子取义成仁的嫌疑。《论语·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皇侃《论语义疏》引范宁云:“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也。”似乎仁义与货利是不可兼得的,便如君子与小人一般泾渭分明。这种思想影响极大,尤其是高扬天理性命之学的宋儒,将“利”字视如洪水猛兽,程颐有言:“不独财利之心。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须寻自家稳便处,皆利心也。”[6]这便将一切为自身着想的行为与思想都完全否定了。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人可以谋利,只要无损于仁义之德行便可,这种思想同样可以在孔子的言论中找到源流。《论语·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郑玄注:“富贵不可求而得者也,当修德以得之。若于道可求者,虽执鞭之贱职,我亦为之。”这也就是把道义作为富贵的先决条件,认为在合乎道义的情况下谋取利益是可行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贸易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活动,特别是到明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上述的第二种观点显然更利于商人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因而更受商人群体欢迎,王阳明提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7],便是顺应这一社会潮流的表现。王阳明承认逐利是人之所欲,是“心”也即是“理”的一部分,因而并无不妥。到了清代大倡实学之际,实用功利主义哲学家颜元将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8],旗帜鲜明地将明道与谋利视为并行不悖、可以统一的两种行为,这便将人们的思想从官方宣扬的程朱理学“禁欲”“灭欲”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有学者指出,明清实学经济伦理的“义利之辩”在批判继承传统德政主义和功利主义义利观的基础上,形成了明清实学经济伦理中“义利并重”“多层次均衡”的新功利主义价值观[9]。这一方面为儒商的身份认同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塑造了儒商用以自许的文化心理,即他们的行为准则有两条:一是明道,二是谋利,而明道之任更重于谋利,若二者不可得兼,舍利而取义才是更值得赞许的选择。
回顾前面讨论的山场产权纠纷,可以发现其中主要涉及两组矛盾,其一是房族利益与整个家族利益的矛盾,前来调解的中人、寨老等,他们在此事件中的所作所为颇类似于傅衣凌先生所说的“披着乡族互助的外衣,限制资本的增殖,以乡族的协议来调和封建各阶层间的强弱对立”[10]。姜东山等人对此的态度是“如谓我等必尽弃为种德,何不劝彼照契管业,莫听唆霸害,更为种德乎?”他们宁肯冒着损失利益的风险,也不肯接受这种姑息养奸的调解方案。其二是事实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矛盾,其实在传统社会,报官的花销损耗远远大于杀牲鸣神,但姜东山等人宁愿顶着来自于同寨村民与地方权绅的压力,也不惧艰难地选择报官,甚至做好了“设官不顺,有誓在先,谁人退悔,决不容情”的打算,他们做出这一价值判断的依据何在?其实核心就在于:“我等老年,既称忠厚,汝等年轻,亦学忠厚,势必弃祖业与谋主,才为忠厚乎?银木总无多,清白之祖业,即可让与谋主,斯不为造孽乎?”忠厚、清白,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品德成了影响姜东山等人行为的关键,因为他们“学忠厚”,所以不能违背道义,面对不义之事绝不姑息、绝不退缩,在衡量利弊的时候,他们心中的天平上最重的砝码不是商人所看重的银木等财物,而是在儒学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亲仁好义的品德。无论是逞一时之气还是真的做了垂范后人的深远考量,姜东山等人都是依据儒家提倡的仁义为先的价值观做出了决定,而这也正在无形中体现了他们的儒商精神。
所谓儒商精神,最核心的便是要“谋利以义”,利可求,但必须取之有道。有这一操守,逐利也无愧于心。姜东山等人所谓的“清白”,便是指财产来自正道,而他们对纠纷对手的指责,也集中于其使用阴谋诡计来谋夺财物的做法不合乎道义。马克斯·韦伯以为中国商人由于“缺乏一个内在的价值核心”而偷奸耍滑、反复无常,然而在明清商人伦理中,勤俭与诚信是占有中心位置的品德,姜东山等人的事例恰恰说明在儒家文化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儒商”这一群体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文化底蕴,他们的义利观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
四、结语
清水江地区虽然在历史上长期属于“化外”,但在当地因木材贸易而兴盛起来后,儒家文化迅速随着贸易活动渗透进这一地区,被当地商人群体接纳,由此形成清水江地区的儒商群体。他们既有商人的重利之心,又用儒家伦理道德约束自己、教导子弟,由此将儒商身份与儒商精神代代相传,姜东山等人正是清水江儒商的典型代表。从本文讨论的山场产权纠纷事件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价值判断大多基于儒家提倡的仁义等伦理道德,尤其是在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经过千百年的争论和阐发,先哲终于总结出一条“谋利以义”的原则,而姜东山等清水江儒商就以自身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一原则,他们堪称“贾而好儒”的儒商典范,他们的义利观至今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学习价值。
——以置产簿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