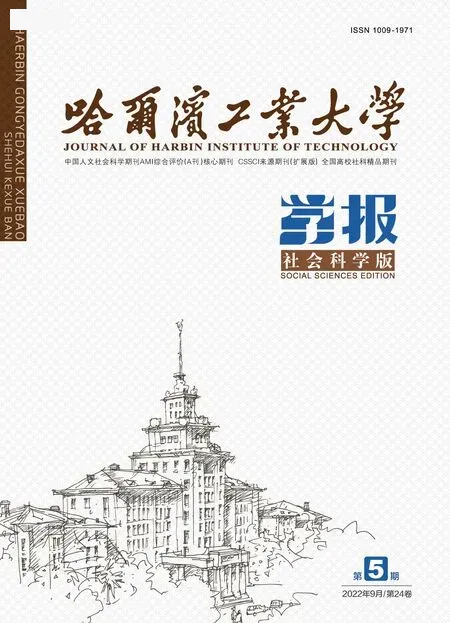李渔经典作品的当代搬演和舞台传播
——以创作社剧团《少年金钗男孟母》对《男孟母教合三迁》的谐拟转化为例
魏琛琳,李佳伟
(1.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西安 710049;2.香港中文大学 翻译中心,香港 999077)
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戏剧家李渔(1611—1680)的作品在当时和后世都极受读者欢迎,范骧(1608—1675)曾用“当事诸公购得之,如见异书,所至无不虚左前席”[1]317描述其作品受欢迎之盛况;又以“予自吴阊过丹阳道中,旅食凤凰台下,凡遇芳莚雅集,多唱吾友李笠翁传奇,如《怜香伴》《风筝误》诸曲,而梨园弟子,凡声容隽逸、举止便雅者,辄能歌《意中缘》,为董、陈二公复开生面”[1]317,记录当时各个民间剧团竞相排练、上演其剧作的景象。时至今日,搬演和改编李渔作品的情况仍不绝如缕,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台湾创作社剧团对《男孟母教合三迁》的改编。编剧周慧玲将其改编为舞台剧《少年金钗男孟母》,上演于现代台湾剧场,反响热烈,获评“十大错过可惜表演”。此剧以对经典作品极富创造力的重新演绎展现出不可磨灭之深情,从同性情谊、文化包容、表演形式等方面赋予原作新的内涵,不仅展现出改编者的经典阐释力和艺术创造力,而且验证了经典文本的艺术品位和社会价值。
本文从“互文性”出发,将《男孟母教合三迁》和《少年金钗男孟母》并置进行分析,探索现代改编作品对李渔原作的承继和延续,思考编剧从解构和重构角度对李渔原作进行的改写和颠覆,进而发掘改编发生时中国台湾地区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以及中国台湾民众对同性情谊的态度演变。
一、互文与演绎:文本的承续与创新
在对索绪尔和巴赫金的语言理论进行吸纳和融合之后,法国符号主义学家、女权批评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在《巴赫金:词、对话、小说》中提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概念,认为“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换”[2]146。此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在其《S/Z》《从作品到文本》等著作中提到“互文本”一词,正式将互文理论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后来,Kristeva又进一步指出互文性是“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2]113,认为任何文本都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是对其他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当“互文性”逐渐成为确定的理论概念并走出先锋派小圈子后,以米勒(J.Hillis Miller,1928—2021)、布 鲁姆(Harold Bloom,1930—)为代表的耶鲁学派开始将文本置于更加广泛的语境中,思考文本的存在方式[3]及存在的心理机制[4];与此同时,法国理论批评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1930—)、费特尔(Michel Riffaterre,1924—2006)等人将“互文性”视为一种建设性的文学研究方法,认为“互文性”是文本内部表现出的与其他文本引用、戏拟、影射、转述、重写、否定等关系的总和[5],文本的写作和阅读有赖于这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6]。在互文性视域下对《少年金钗男孟母》进行观照,会发现其不乏对李渔原作的吸收继承和精彩演绎,并在再现李渔经典作品思想性、艺术性的同时,为其增添了别样的起伏与张力。
《男孟母教合三迁》围绕一则南风故事展开:相貌俊美的志诚书生许季芳生性厌恶女人,一心追求男色,但迫于传宗接代的压力不得不娶妻生子,其妻于生子后不久身亡。几年后,许季芳偶遇“眉如新月、眼似秋波、口若樱桃、腰同细柳”[7]111的绝色美男尤瑞郎,便变卖家产高价将瑞郎聘回家中,并将其父接到家中同住,待如亲父。为报答季芳深情、维持自己的美貌,瑞郎毅然决定自我去势并扮成女子,欲与季芳做长久夫妻。但觊觎瑞郎美色的奸人污蔑季芳“私动腐刑”,导致季芳在公堂受尽屈辱、愤然离世。尤瑞郎“哭得眼中流血,心内成灰”[7]126,并遵从季芳遗命为其守节抚孤。他对遗孤许承先管教严厉异常,“日间教他从师会友,夜间要他刺股悬梁”[7]129,甚至效法孟母三迁。后承先顺利出仕,瑞娘(即瑞郎)获封诰命。
中国台湾创作社剧团的编剧周慧玲据《男孟母教合三迁》改编出现代话剧《少年金钗男孟母》①此剧于2009年在台北首演,观众反响热烈,被联合报评为“十大错过可惜表演”。台北创作剧团曾自评“本剧蕴涵着四大特色:不同表演形式的交糅、不同文类的聚集、不同文化的交错、广大社会的文化包容”。参见台北创作社剧团《性别混声·台湾本色——“创作社”的〈少年金钗男孟母〉》,载《福建艺术》2009年第5期,第46-48页。,由上、下两场组成。上半场“少年金钗前世缘”大抵承袭李渔原作,讲述季芳和瑞郎的相遇相识相知相许,强调彼此的真挚情感和无悔付出;下半场“男孟母迁今生情”详细呈现改名瑞娘的瑞郎和他酷爱以男装行世的表姐王肖江携子迁台,共同抚育许承先长大成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承先不知不觉爱上同性友人、父母昔日仇人陈大龙之侄陈念祖,引发剧中人物对性别身份的探讨。随着情节发展,瑞娘和承先都由起初对“现代同性情谊”的恐惧不安逐渐变得认可接纳,展现出改编者对当下社会大众对同性情谊态度的反思。剧作最后,瑞娘获颁模范母亲奖,各位主人公讨论参加颁奖典礼时的着装,并以服装为“符号”隐喻自己对性别及相关问题的看法,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人文关怀。
相较原作,《少年金钗男孟母》在背景设定、次要人物处理、性别颠倒、角色反串、主人公情感认同等方面进行了改编和重构。首先是剧作的时间背景发生了变化。上半场的故事情节发生在1912—1915年南风盛行的闽中地区,下半场的背景被设定在1955—1964年的台湾地区,与此同时,主人公的经历和处境成为不同时期民众情感状态和生存环境的真实投射,用意颇深。其次是王肖江的性别和身份变化。原作中王肖江出场较晚且着墨无多,是季芳死后瑞娘决定迁居时考虑到“一来路上不便行走,二来到了地方,难做生意”[7]127,才想起有个母舅叫王肖江。但在《少年金钗男孟母》中,王肖江在第二幕中便出场了,身份由瑞郎的母舅变为表姐,性别从男性变为女性。她与传统女性形象截然不同,酷爱着男装、整日东奔西跑、睿智且颇有主见、保护瑞郎逛“没有女人凑热闹”的莆田赛会、陪瑞郎迁居、助其养家教子……是一个颇具男性气质的存在。这种“跨性别重塑”的设定使原作多了一重“性别颠倒”:不仅瑞郎自我去势成为许承先的“母亲”,而且王肖江作为承先的“阿姨”承担起“父亲”的职责。这样一来,原作中本来毫无婚姻和血缘关系的瑞娘、肖江和承先便组成一个性别关系复杂的三口之家。再次是剧中的角色反串。编剧安排女演员徐堰玲反串男性角色尤瑞郎,这一设计构成改编作品对原作“性别”和“身份”的重要解构(后文详述)。最后是对待同性情谊的态度发生变化。在原作中,中举后的许承先得知瑞娘身份后“终身只当不知,不敢提起所闻一字”[7]130。这种“讳莫如深”足以说明末清初虽南风盛行,但主流文化对此种社会风尚仍旧态度暧昧。而改编后的《少年金钗男孟母》却尝试为产生同性情谊的双方找寻出路:虽然两代人的家庭关系一度因“儿子”许承先的性取向变得紧张,但当瑞娘把自己穿过的白西装改好送给儿子的同性恋人陈念祖,意味着她作为母亲终于接受儿子的选择;作为儿子的许承先也藉由这件白色西装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感受到家庭关系中难以言喻的温馨体谅、不需被言说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编剧为主人公跨越性别认同的障碍、现代新型家庭伦理观念的建立与和谐家庭关系的存续发展探索了新的可能。
二、解构:符号化的“性别”与“身份”
德里达认为“解构”是一种阅读和写作方式、一种批评策略。这种策略要求阅读和写作行为突破原有标准和规则,对文本提出新见,并推动形成新文本。在此过程中,能指得以自由游戏,新的意义不断涌现。《少年金钗男孟母》对原作的改编便是如此,改编者赋予表姐王肖江男性化的性格特征、安排女演员反串男性角色……使“性别身份”符号化,解构了性别身份固定论以及基于此产生的传统社会分工;与此同时,文本的意义无限开放,凸显着作为深层意指的“内在真情”。
(一)对性别固定论的消解
在原作中,当瑞郎自我去势,季芳见事已至此便“索性教他做妇人打扮起来”[7]122,并“把瑞郎的‘郎’字改做‘娘’字”[7]122,使瑞郎不仅在生理性别上,而且在社会性别上也发生颠覆性变化。这是李渔创新求奇、不拘格套的表现,但越强调瑞郎的名字变化、女性装扮,越说明李渔未能跳出男、女性别对立的刻板印象,更未能反思潜藏在这种二元对立背后的社会机制和权力话语。《少年金钗男孟母》在改编时着意弱化这种二元对立,通过更改角色设定和增加性别反串实现“性别越界”的效果,对主人公原有的性别身份进行模糊甚至消解。
在延续尤瑞郎扮演女性角色这一设定的同时,《少年金钗男孟母》将王肖江的身份由“母舅”改为“表姐”,并安排她承担男性角色在家中的责任和任务,多添一重“性别颠到”。表姐肖江的首次出场是在瑞郎希望前往赛会时,尤侍寰请求她陪伴、保护瑞郎:“肖江,你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瑞郎不幸,生在这恶赖地方,就怕他一出门就,唉,你帮我看紧他吧。”[8]28她被改编成一位行动自由、勇敢洒脱、不拘世俗的女性,首次亮相便身着西式男装,打破了传统男权社会为女性设置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颠覆了大众以往对女性的固有看法。赛会上,瑞郎和肖江互相“指控”对方“不男不女”的话语机锋更是打破“定式”,展现出性别的模糊性和可流动性,暗示性别本无固定意义。
从1960年代起出现的性别新概念认为:将某些行为归属于男性或女性只是一种社会习惯,性别是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建构,个人生而为男为女,并没有天生的性别认同,他们是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性别认同的,在经过社会的建构之后才成长为男人和女人。易言之,虽然生理性别是天生的,但社会性别是被社会建构的[9]。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更是指出性别的结构与权力结构共存,权力在两分的、表面上看上去是本质主义的性别区别中是因不是果。性别是话语的产物,是异性恋霸权的产物[10]2-3。从这个意义上讲,改编剧作中肖江和瑞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颠倒,恰是对以往的社会性别固定论进行了双重消解。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安排了女演员徐堰玲反串尤瑞郎这一男性角色。无论是决定自我去势以解除自己的男性身份,还是扮成女旦以端茶研磨等行为巩固自己作为“妻子”的特征,瑞郎的所有行为都由女性演员表演完成。这种反串扮演的角色调度凸显了性别和亲密身体关系的符号化,原有的所指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不具备意义的能指本身。这就不仅从根本上模糊了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而且消除了以往存在于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矛盾对立。易言之,如果观众认可男女演员演绎男男情欲的做法是成立的,那么这一符号化的过程显然已经被清晰地感知,暗示着性别互换甚至消解的可能。
(二)对性别身份及传统社会分工的颠覆
Butler认为,身份没有固定的本质,只是“风格化的重复表演”。她曾在《表演性行为与性别建构》中讨论性别如何通过身体和话语行为表演建构[11],后又在《性别麻烦》中指出“性别只是一种表演,在性别表达的背后没有性别身份;身份是由被认为是它的结果的那些‘表达’,通过表演所建构的”[10]34。也就是说,性别并没有本体论的身份,它只是通过表演建构了它所意味的那个身份。“社会性别也没有所谓的真假,其内在真实是一种虚构,是在身体的表面上建制、铭刻的一种话语幻想。”[10]178易言之,性别只是一套关于身份的话语效果。
《少年金钗男孟母》中的许多处理都对这套话语进行了解构。如:
(念白)“瑞郎颔首微笑,簪花一朵云鬓旁,俨然戏台上的女旦。”
许:眼下这位哪里是瑞郎?根本就是瑞娘。
瑞:(旦 状)从 今 开 始,我 就 是 瑞娘了。[8]48
编剧有意突出瑞郎扮旦状,“俨然戏台上的女旦”更是直接揭示出性别的表演性质和表演意义,可见性别符号间的界限可以通过“表演”被模糊和跨越,这种“可变性”暗示着观者性别表达的无限可能。聚焦下半场第六幕,参加“模范母亲”颁奖时,主人公一反常态,瑞郎不再做女性装扮,而是身着当年的白色长袍;肖江改穿女性洋装,“踏着曼波舞步、眼角带着狐媚上场”[8]103……此时“服装”作为承载意义的符码(signifier)暗示着性别,当主人公开始根据自己当下意愿选择具有不同性别特征的服装,意味着他们可以自由地对自己的性别和性取向做出选择……当尤瑞娘作为“许妈妈”送给儿子的同性恋人陈念祖自己当年的白色西装,服饰符码就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暗示他对自己昔日性别身份的坦诚和对念祖、承先关系的接纳,也标志着文本对身份和性别的解构达到高潮。
瑞娘在获颁“模范母亲奖”后与“表姐”王肖江的对话亦可证实这一点:
瑞:肖江,为了承先和我,你当了一辈子单身女郎,始终没机会自己成家。我心里一直很过意不去。你才是真正的模范母亲。
肖:开什么玩笑,一句过意不去就算啦?(……)哎哊!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来,有多少人把你当成我老婆,又把我当成你丈夫,以为我们是一家人?我解释都解释不清楚,干脆将错就错。
瑞:这我就不懂了,那些人什么时候见过两个女人当家的一家人啊?
肖:两个男人。[8]106
性别的跨越性和流动性跃然纸上。
此外,编剧安排女性角色王肖江着男装、走南闯北外出经商,后来又在五十年代末期的台湾—香港跑起单帮……这样一来,不仅基于外貌、着装、身份等僵化的性别身份认同得到解构,基于性别差异而进行的传统社会分工也得到了彻底颠覆。在符号化的性别身份背后,无悔的爱情、无言的亲情等作为修辞系统的深层意旨不断得到突出和彰显。
(三)解构之后:突显作为深层意旨的“内在真情”
在接受《破报》访问时,周慧玲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运用角色安排,让不同人跨越以往没有跨越的地方,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分不清谁是男的,谁是女的,因为这并不重要。”[12]她在另一次采访中也提道:“角色设定上,肖江与瑞郎是姐弟,角色呈现上,他们有时像兄弟,有时像夫妻,角色表演上,他们却是由两位女性演员担任。因此,观众在舞台上看到的,将不只是单一性别,而是同时看到四个层面的关系:姐弟、兄弟、夫妻、姊妹。这样的角色调度实际混杂了又男又女的特色,因此很难被清楚定义,那正是我的目的。人伦如果是关系,我们对关系的理解,太受制于既有定义,而且还常常取决于血缘或法定的意义,却忽略最至关重要的——彼此长期相处所投注的情感厚度。《金钗》表面上看来,有基本人伦,但这不是我真正关注的。我想要呈现的是,不受定义制约的真实情感。”[13]正因为这样,她才刻意创造出一个“母子是父子,姐弟伪夫妻”的另类家庭。可以说,无论是季芳对瑞郎的情深义重、瑞娘对季芳的无悔付出,还是肖江对瑞娘的多年陪伴、瑞娘对承先的悉心照料、承先和念祖的勇敢坚持、郑校长对同性情谊的理解包容……都将故事重点从原作中的彼此牺牲转移到因爱而构建家庭的可能。当许承先最终说出“不管你和爸当初怎样,我都不会介意。我只知道你是我妈”[8]99时,观众已然明白,在人与人之间、在组建家庭时,最重要的并非彼此的性别或身份,更不是外部评价、社会风尚,而是义无反顾、不求回报、无限包容的爱。
陈大龙的角色设定也是这一编剧理念的明证。不同于李渔原作中对妒忌、诬陷季芳的学中众人一笔带过,《少年金钗男孟母》中刻画了对季芳饱含深情的陈大龙:他曾与许季芳相处,看到季芳和瑞郎“恩爱有加”后心生嫉妒,他是由爱生怨,才诬告了季芳。但当他看到季芳在庭上挨打,又忍不住大喊“住手!住手!”[8]54更在季芳濒死时绝望哀嚎:“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啊,季芳!”[8]56后来更是在季芳死后不久便自杀殉情。编剧重新设定了许季芳和告密者之间的关系,凸显了告密者陈大龙对情的难以割舍和对爱人的强烈占有。诸如此类的设定,使无可替代的真情闪耀在《少年金钗男孟母》的字里行间。
总之,改编剧作《少年金钗男孟母》通过两位女性演员的反串与易服模糊了主人公性别,反映出社会性别的外在“表演”特质,揭示出其“可流动性”。该剧不仅对社会性别固定论进行了解构,而且使传统社会分工得到了颠覆。这样一来,“身份”和“性别”被符号化,符号的深层内涵、沁人肺腑的内在真情得以凸显。
三、重构:被消解的“矛盾”与“反讽”
新编剧作反思了父权制社会结构,消解了原作中的矛盾与反讽,对原作进行了大胆重构。
(一)对男性权力结构和父权制社会观念的反思
原作中产生同性情谊的双方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相差甚远:季芳家有田产、屋业,瑞郎却家境贫寒。伴随经济、地位差距而来的,是两人在人格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表现为二人角色的主从性①“考察明清小说中同性恋者的角色分配,可以发现,他们一般都按双方的社会、经济地位,如尊对卑、富对贫、主对仆、师对徒、长对幼等等,分为主动方和被动方,泾渭分明,绝不混淆。”参见施晔《明清同性恋小说的男风特质及文化蕴涵》,载于《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126-132页。吴存存的《明清社会性爱风气》、Raquel A.G.Reyes和W.G.Clarence-Smith的Sexual Diversity in Asia,C.600-1950,以及Chang,J.W.的Prostitution and Footbinding:Images of Chinese Womanhood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San Francisco等研究也对这一问题有过论述。和尤瑞郎性别认同的“戏拟性”[14]。
施晔曾指出:“中国古代男风就其实质而言是将男色想象、戏拟成女色而加以亵玩或爱恋的风气,促成这种习气的深层原因是中国几千年的男性霸权体制,不仅使女性一直处于次要、服从的第二性地位②Moi Toril曾指出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的差异,强调生理性别是从本质论角度而言,而社会性别是从建构论的角度而言的。当社会整体处于父权制价值观的控制下,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实际上展现出一种上下秩序意义。参见TORIL M《性别/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陈洁诗译,中国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年版;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1949—)也曾明确指出意识形态本身不能更不是一种“社会意识”而是一种“社会存在”,它通常被某种“虚假意识”所支持。参见ZIZEK S《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光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而且渗透到男性内部,强权男性将年少貌美、性格温顺的男童戏拟成女性,对他们的性别做故意、暂时的误认同,以实现对他们的性压迫、性侵犯。”[15]129周华山也曾指出:“如果将男性扮作女性视为同性关系的一种必要性,实际上也是异性恋中心论者的观点,只是一种男尊女卑意识形态的复制。”[16]因此《男孟母教合三迁》中的尤瑞郎青春髫龄、姝丽慧颖,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后来更是被赋予女性的名字和装扮,强化其女性气质。这样一来,同性情谊中“主动方追逐被动方”的行为就成了对以往男性“占有女色”做法的戏拟和延伸,这种行为使男性主动方猎奇猎艳的心理得到满足,与此同时感受“占有更多”的愉悦,从而实现渔猎天下美色的终极理想。“然而,这种将男作女的戏拟是暂时的,因为美人易老,男色比女色更难保鲜。花样少年一旦出现了男性特征,他们就被踢出戏拟受宠的行列。”[15]129可见好男风者对被动方的雌化带有明显的“时效性”。在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同性情谊被动方一方面接受主动方对自己身心的雌化想象,另一方面也会因为美色易逝、容颜易老而感到焦虑和恐慌。因此,尤瑞郎不惜冒死自宫。
“更可怕的是,这种由同性恋双方共同促成的戏拟现象甚至还引入了对女性贞节的期许。男风小说的作者站在主动方的立场上要求被动方专情忠贞,一‘女’不侍二夫。”[15]129由于被动方地位同样(甚至比女性更为)低贱,社会便把对女性贞节的严酷要求原封不动地加到他们的身上。《男孟母教合三迁》就是基于主动方心理书写的对理想龙阳的期待,希望被动方能按三从四德的标准行事。表现在尤瑞郎身上就是为爱无怨无悔、为情忍辱负重等,他在身体和心理上都绝无出轨的可能。易言之,封建男权社会所倡导的贞洁观,实质就是在要求女性(或被戏拟成女性的男性)无条件遵守和服从男性权力结构下男尊女卑等霸权主义道德话语。仅仅是为了淡化这种强烈的男性霸权色彩,“拥有话语权的文人们为男风小说精心制造了‘始于色而终于情’的书写模式,从而使低层次的渔色行为上升为高层次的情感诉求,并为这些小说罩上才子佳人式的华丽外衣”[15]129。
这种父权制社会的价值观念在改编后的《少年金钗男孟母》中得到重构。虽然许、尤二人的设定沿用了原作,但编剧新增了一些内容:瑞娘看到肖江从香港进的货品抢手、生意大好时感叹:“当年让我跟着你跑单帮就好了,何必跟老爹去卖什么米?到头来还得把儿子卖了,才有钱换副棺材。”[8]21可见他渴望以一种独立、自由、正常的方式生活,表现出明显的主体性和自觉性;也是为了突破父权制权力话语,周慧玲在改编剧作中详细刻画了当年姿色出众的南风被动者瑞郎在成为母亲后对下一代陷入同性情谊的恐慌;更为明显的是,编剧不再仅仅让作为“女性”的尤瑞郎单方面为男性作出巨大牺牲,而是也着意安排了作为“男性”角色的王肖江为“女性”进行义无反顾的真诚奉献:他终身未婚未育帮助瑞娘抚育季芳的孩子,传统夫为妻纲、传宗接代等社会观念都不再适用。此外,新作中第二代同性恋人“承先”与“念祖”地位平等,不存在上下级之分、贵贱之别。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对男性权力结构和原有父权制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消解与重构。
(二)对反讽的消解和对异性恋霸权的重构
在《男孟母教合三迁》中,当尤瑞郎发现许季芳“睹物伤情”,听到“这件东西是我的死对头,更是将来与你的离散之根”后毅然自我去势。李渔高超的反讽技巧于此可见一斑:瑞郎为维持二人关系而斩断“孽根”的情义之举恰恰成为季芳含冤而死、自己辗转迁徙的“离散之根”;而他自认“为报恩绝后,父母也怪不得我”[7]121的忠义至诚恰恰被太守认定为对儒家孝道的违逆:“岂不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么?我且先打你个不孝!”[7]124这些他自以为情深义重的壮举恰恰落实了原本不必降临的灾难。在《少年金钗男孟母》中,作者对此处情节仅一笔带过,更多着墨于下半场“男孟母迁今生情”上,削弱了原作中的反讽意味。
再回顾一下季芳“睹物伤情”后瑞郎的行为:他一面安慰季芳“若是泛泛相处的人,后来娶了妻子,自然有个分散之日”,表忠称自己“如今随你终身,一世不见女子,有甚么色心起得”[7]120;一面说服自己“如今世上有妻妾、没儿子的人尽多,譬如我娶了家小、不能生育也只看得,我如今为报恩绝后,父母也怪不得我”[7]124。这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他为表忠心而宣称的“一世不见女子”反而说明他自己也认可季芳所言女性可以作为唤起其性欲的客体的观点(他接受“排遣之道”也正是为了防止异性恋的产生);第二,他在劝服自己时首先考虑的并非肉体欢愉,而是生育问题:切断阴茎的行为意味着他从此丧失异性恋的资格和生育及传宗接代的能力(他只是以报恩为借口合理化自己让尤家绝后的举动)。因此,在这些极具反讽意味的行为背后,潜藏着的是瑞郎心底对异性恋的恐惧,这与季芳因担心他随年龄增长会逐渐倾向于选择心仪男性的焦虑其实别无二致。易言之,异性恋对两人关系的威胁才是瑞郎自我去势的真正缘由。从这个角度而言,虽然李渔原作中未曾直接提及异性恋霸权(hetero⁃sexual hegemony),但它却一直潜藏在文本背后,影响着文本的情节走向。但在新编剧作中,编剧安排瑞娘和肖江同时反串、设定陈大龙对许季芳一往情深、承先与念祖相处光明磊落,还借郑校长之口表达“有些事情,只是人们不习惯或不了解,但不一定就不对”[8]64等彰显对同性情谊开放、包容的态度。最后两代人也藉由“白色西装”实现了对彼此的坦诚与祝福。这些都帮助实现了对原作中异性恋霸权的消解与重构。
此外,由于晚明社会思潮与儒家文化发生碰撞,李渔在《男孟母教合三迁》中,一方面感佩许、尤二人的深情、盛赞季芳对瑞郎之父的孝敬与赡养,称之为“三纲的变体,五伦的闰位”[7]107;另一方面却又以说书人口吻对南风大加贬抑,称这桩事“无当于人伦”[7]130,呼吁读者不要误入歧途。这种风流和道学的龃龉、对南风“既是赞许也是嘲弄”[17]的矛盾态度是《男孟母教合三迁》挥之不去的底色。面对这种矛盾,《少年金钗男孟母》的编剧表现出极大的智慧:她安排了多个人物如爱慕季芳的陈大龙、性别反串的王肖江、不识南风的郑某等分别承揽起原作叙述者对南风的分歧。由于角色的身份、立场、动机不同,他们对南风秉持不同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当女儿身的肖江保护瑞郎出入原本只有男性可以进出的公共场所、当原本的好南风者赵重生和李继业成了担任执法任务的警察(暗示南风者就是执法者,警察也会是同性恋)、当在原本的男同性情谊中加入女同志的情欲……周慧玲最终以“性别混声”制造出“众声喧哗”的效果。就这样,《少年金钗男孟母》消解了李渔原作中的矛盾,重构出全新的家庭观念,得到强调的唯有“不受制约的真情实感”。
(三)离散视域下的身份焦虑
另一处值得注意的重构是“男孟母三迁”。《少年金钗男孟母》虽沿用了原作中的“三迁”行为,但更改瑞娘迁居路线为:从莆田到泉州、从泉州到漳州、从漳州到台湾。虽然都为教子而迁,也都强调女性的贞洁与贤良、展现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但改编路线后的“迁居”便与原作产生了本质区别:新增入了离散色彩。易言之,瑞娘与孟母迁居的根本原因和内驱动力并不相同——孟母三迁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性质与普通迁徙(mi⁃gration)基本无异;瑞娘是出于对季芳遗言的遵循,不仅出于自爱,而且受迫于对南风的恐惧,“肖江,我当初也只是有几分颜色,就害得别人家破人亡,弄得自己东逃西窜。我自己经过那番孽障,怎么能不保护承先?”[8]69可见其迁居带有被动性和受迫性,具有逃亡(fleeing)、被驱逐(queer expulsion)和自我监禁(self imprisonment)的性质。因此改编剧中的“瑞娘三迁”更像是一种以受害者身份(victimhood)进行的流浪迁徙(diaspora),这就使瑞娘在作为行为主体、性别主体的同时成为离散主体,使《少年金钗男孟母》在消解原作矛盾和反讽色彩的同时具有了离散特征。
最终,拒斥同性恋的承先慢慢消解了自己的恐同症,瑞娘也逐渐接受了承先和念祖的关系——编剧试图通过这些设定反映台湾社会的逐渐进步和日趋包容。可惜的是,当赵重生和李继业成为便衣警察,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急迫地向郑校长追讨当年那封赵重生向许承先表露爱意的情书。此时,那封内容自始至终都不曾明晰的“同性情书”已然构成新的反讽:在宣称开放自由的表象之下,台湾社会仍然没有摆脱对异己的区分,并且一直以更为幽微的方式规训着个体的性。
小 结
2009年台湾创作社剧团据其改编出年度大戏《少年金钗男孟母》,引发热烈回响。与力倡“脱窠臼”却受限于儒家传统和时代语境的李渔不同,编剧周慧玲在改编时不遗余力地倡导同性情谊的正常与正当,在将“性别”和“身份”符号化的同时,强调“情”是“爱”的基础,“爱”是组建家庭的核心要素和主导价值。这样一来,对原作情欲二分理念的反抗成为新剧的无声言说:身份、性别不再重要,而对“爱”的大力提倡和追求歌颂永不停歇。也正是因为这样,《少年金钗男孟母》着重描绘了主人公讨论“穿什么去领奖”的场景,当瑞郎和肖江选择了符合自己当下性别认同的服装,性别被消解、霸权被颠覆,自由选择性别的场域已然向每一个人敞开,正如海德格尔的“礼物”,具有无限可能。此外,《少年金钗男孟母》在角色设计、情节颠覆、错置作品时空背景等方面作出的努力,也成功消解着李渔原作中的矛盾与反讽,使重构后的剧作闪耀着不断探索与力求创新的绚烂光芒。
立足经典、并以现代思维加以改编和重构的《少年金钗男孟母》,不仅运用文本的叙述策略对抗主流性别论述、表现出特定时空下的性别观念,而且通过解构、颠覆、谐嘲、戏拟等方法呈现出编者基于社会背景和时代语境对李渔原作进行的突破与重塑、对大众心理做出的检省与反思,凸显着改编者的独特思考与人文关怀。无论是与李渔原作的互文、承继,还是对其进行的演绎、颠覆、重构,都显示出权威文本的可拆解性,彰显着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无限魅力和不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