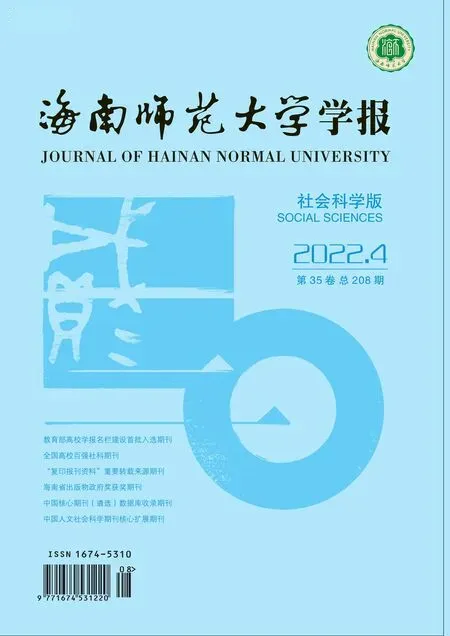“小留学生”现象与华人新移民群体的多重焦虑
——论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中的小留学生形象
池雷鸣
(暨南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32)
21世纪以来,加拿大华人新移民文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有很大的创作实绩,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作家,如张翎、陈河、李彦、曾晓文、孙博等。随着《劳燕》《阵痛》《流年物语》《金山》《甲骨时光》《沙捞越战事》《尺素天涯》《红浮萍》《海底》《移民岁月》《白日飘行》《夜还年轻》《回流》等一大批长篇小说面世,加拿大华人新移民文学已然成了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一个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重要存在。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其的关注与认知,还不足够,尤其是缺乏整体性探究。①参见池雷鸣:《“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的界定、研究现状及局限》,《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4年第3期。事实上,无论是作为区域的“北美”,还是文化的“西方”“加拿大”都不能与“美国”混为一谈,更不必说被替代,成为“美国”的附属。具体以民族政策、民族文化为例,加拿大,是世界上多元文化政策的典范,追求平等多样的民族文化,而与美国的文化“大熔炉”政策有实质的区别,因而被誉为“文化马赛克”的国度。在多元文化政策的法律保障下,加拿大华人新移民在多元文化的追求中不仅有着高度自觉的族群意识,而且对族群内部的差异以及差异的统一也有着清醒的认知,并将此投射于文学创作之中。
本文将通过聚焦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中的小留学生形象,在细读的基础上,透视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群体如何看待“小留学生”及其现象,并试图揭示蕴藏在文学表征中的深层次整体性动因。从鸦片战争时代的“被全球化”到新时代的“主动全球化”,中国走向世界的姿态和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相应地留学事业也要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有新的意义与使命。在此语境中,加拿大新移民作家针对“小留学生”现象所文学表征的代际、历史、伦理焦虑,对窥探留学的“发挥作用”将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一、代际焦虑与惊诧的文学体验
“小留学生”现象,如今已成为移民浪潮中的一个聚焦点。对“小留学生”现象较早的关注者,是加拿大新移民华文作家孙博。①参见徐学清:《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中的海外华人——评加拿大华裔作家孙博的长篇小说》,《创作评谭》2005年第6期。他较早在专栏文章和新闻访谈类著作《小留学生闯世界》中介绍“小留学生”群体在海外的生活世界,后又以小留学生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小留学生泪洒异国》。之后,在加拿大华人新移民文学中,针对或涉及小留学生现象的写作,开始蔓延开来,比如陈河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女孩与三文鱼》,柯兆龙的“温哥华”系列三部曲,曾晓文的《移民岁月》等。
这类写作,若从《小留学生泪洒异国》算起,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尽管情节、事件各有不同,但从始至终是一种焦虑情绪的重复。正是由于新移民浸透在创作中的焦虑,令文本中小留学生们的海外生活充满悲剧色彩,并在结局设置中得以渲染。孙博在《小留学生泪洒异国》中重点叙述七个小留学生,其中五个落入自杀、入狱或者失落的凄凉境地;陈河《我是一只小小鸟》中的三个小留学生,都惨死于歹徒之手;《女孩与三文鱼》中的周沸冰因杀死房东的小女儿而被捕入狱;曾晓文《移民岁月》里的健立因作假牟利而被警方通缉……除了《小留学生泪洒异国》中因刻苦努力而圆梦哈佛的郑志文和冯家丽,给大家带来一些暖色之外,小留学生群体在新移民所构建的文学世界中,是以蓝色的冷色调经营着他们的离散生活:性放纵、绑架、欺诈、杀人、自杀、拜金、二奶、黑社会等。这种生活,与他们在国内原有的生活经历悬殊甚大,更是与他们所肩负的父母望子成才的心愿背道而驰。希望开端的暖色调和悲剧结局的冷色调的反差及其细节渲染,带来了惊诧的文学体验。
问题是,这种惊诧并不是全部的现实体验。在现实世界,小留学生浪潮依然强劲,成功的喜悦依然是家长的世界(实施希望)和孩子们的世界(肩负希望)共同期待并能够实现的主流,也是两个世界的统一。也就是说,郑志文和冯家丽这样的小留学生人物,才是现实世界所需要的。显然,与小留学生群体相关的写作,并没有构建属于现实世界最希望实现的可能性,反而与之发生了背叛与断裂,持之以恒地汇聚成一条蓝色调的“传统”,并源源不断地生成惊诧感。这种因小留学生失望的现状引起的惊诧感,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学生产。它源于作家们的叙事策略:对现实世界的偏颇反映或者说对小留学生世界阴暗面的聚焦,并呈现出无意的一致性,因而具有了集体意味。从所涉的文本形态②比如《小留学生闯世界》的“代序”与《小留学生泪洒异国》故事情节的吻合,《我是一只小小鸟》《女孩和三文鱼》中对报刊、网络媒体的故事性引入及情节化嵌入。来看,现实世界中小留学生“血”和“泪”的媒介传播,产生了创作的焦虑,促使被感染的新移民作家用文学的想象去构建事件背后的可能性。被构建的可能性,高度契合了创作的焦虑感,作家们甚至不惜用细节强化和放大蓝色调的情绪,从而实现了叙事策略与叙事意图的统一,并在统一中营造希望和失望比对后的惊诧感。
这种惊诧感,首先是面向期待读者的,这明显地体现在“作者的话”中。陈河曾在《我是一只小小鸟》的创作谈中披露过写作的意图:“对于国内将要出国留学的孩子和家长们也许会有点提醒的作用。”③陈河:《我是一只小小鸟·创作谈:成长的代价》,《中篇小说月报》2010年第3期。孙博在《小留学生泪洒异国》里,通过人物“南方”(作者曾用的笔名)的话来表达关切:“让读者真实了解小留学生的生存状况,供已出国或准备出国的学生参考,让家长们通过这部作品去思考,自己的孩子是否具备出国的能力?付出的沉重代价是否值得?到底多大的年龄适合出国镀金?”④孙博:《小学生泪洒异国》,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94页。
新移民作家通过惊诧感明显地希望家长们和孩子们审慎对待“留学”,反思“留学”所承载的图景,并在蓝色调的“传统”里呈示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与反差,以确立他们在焦虑中的反省立场,力图将从社会事件感染而来的焦虑情绪,传递给依然对西方充满憧憬的父母们。正是在“西方憧憬”的维度上,新移民作家又再次在期待读者身上发现了自己往昔的影子,令外在的传播性焦虑转化为内在性的自我焦虑。于是,“提醒”与“反思”的言说,也是他们对离散经历的反省,并融汇成源于“西方憧憬”破碎体验的警示:杜绝西方的魅惑,正视祛魅的西方。或许,为西方祛魅,正是蓝色调传统得以形成的原因之一。
在涉及小留学生的写作中,一种代际姿态鲜明地存在其中,并同样展现在文本形态之中。《我是一只小小鸟》在故事的结尾处,有一段“附记”,将“作者”引入了情节之中;《小学生泪洒异国》中的“南方先生”,也可以视作另一个情节化的“作者”。不必在乎这是否是文本的嬉戏,有一点可以明确,情节化的作者与现实世界的作者至少在话语姿态上具有同构性。他们不是用同龄人的姿态在言说,而是保持上一代人的话语姿态(这在南方先生的言说内容及话语身份上有明确表现)进行有选择性的,有目的性的叙事。
在《异域文化夹缝中的小留学生们》①澳洲华文作家胡仄佳曾就小留学生现象发表过自己的看法:“这一代人远比他们的父母辈喜欢物质享受会花钱花得毫不手软,也更缺乏吃苦精神和应对实际生活中的种种能力,或者说责任感淡薄,其成熟度和不想长大的意愿矛盾对立得厉害。”参见胡仄佳:《异域文化夹缝中的小留学生们》,《青年作家》2007年第6期。这篇文章里,澳洲华文作家胡仄佳将小留学生现象置放在“从淘金路至留学路”的历史轨迹之中来看待,特别是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以“洋插队”自况的一代留学生作为它的历史参照。曾晓文在谈移民文学现象的变迁时也说过,“……新一代的小留学生:他们虽可以写,但他们没有经济压力和生存挣扎,一出国就买宝马了,没有餐馆打工这些七七八八的经历……”②刘芳:《曾晓文:书写移民和他们的历史》,《东方瞭望周刊》2010年第4期。可见,这种鲜明的代际意识,在对全球性存在的小留学生现象的关注与聚焦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加拿大新移民作家而言,也同样有代表性,并呈示在他们构建的小说世界之中。
孙博在《小留学生泪洒异国》中特意塑造了“司徒老师”,作为老留学生的代表,并将代际意识演化为她对小留学生的教导性言说:“20年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班上没一个同学敢开半点小差,老师眼一瞪,我们就抖三抖。……别人背后骂你们是‘留学垃圾’,我也不承认,但你们自己也要争口气呀……”③孙博:《小学生泪洒异国》,第72页。至此,在这种尽可能的委婉表述中,我们再次感受并确认到那种浓浓的焦虑情绪。“留学垃圾”,这个结论性的称谓,已经不再拘囿于家庭,而是蔓延至更为广阔的空间范畴:社会。在这个层面上,情感落差所带来的惊诧文学体验,已演化为一代人不如一代人失望的社会情绪。这与“留学”本身的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有关。
二、历史焦虑与“留学垃圾”的重新审视
现代中国人留学的历史,应从“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说起。1847年,19岁的容闳启航赴美,入读美国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莫森学校(Monson Academy),随后就读于耶鲁大学。在容闳的策划和推动下,1872年夏末,清政府官派第一批幼童三十人赴美留学,至1875年,共派遣120名。虽然因为顽固派的反对,“小留学生”们并没有完成原定的15年留学计划,但仍然达成了容闳的当年愿景:“以为国家贮蓄人材”④容闳:《西学东渐记》,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小留学生们大都成长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知名人士或者技术骨干,如邝炳光、邝荣光、梁金荣、程大业、詹天佑、薛有福、蔡廷干等。可以说,从中国近代“留学”的源头起,留学生就被寄予厚望,并因而披上了“精英”的外衣。改革开放初期,始于近代的留学传统得以传承。派遣留学生不仅被视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被评价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⑤留学生丛书编委会编:《中国留学史选粹·前言》,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2年,第2页。可见,在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屈辱传统和救亡图存的国族心愿中,“留学”从来不仅仅是个体、家庭的事情,同时也承载了振兴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并且转化为理所应当的精英意识,渗透在国民的文化心理结构中。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再来观照小留学生郑志文和冯家丽所散发的暖色,便可审辨出这种精英意识的光辉。或许,可以从另一个维度去重新审视“作者的话”里的提醒与反思:在为西方祛魅的同时,也正在强化“留学”的传统光辉。以此为参照,“留学垃圾”意味着对历史传统的背弃,是浸在骨子里的历史屈辱的延续。由它而来的焦虑,便可扩展为一种对文化传统和面向西方的焦虑。
在现实的社会语境中,新移民作家已经经历了从被西方魅惑到逐渐在面对面中为西方祛魅的体验、思想的转变,当下的他们正在奋力为被西方承认而斗争,并努力构建支撑这种承认的新居之根。面向未来的灿烂愿景,不是凌空的现实规划,而是根植于肥厚历史土壤之中的经验性蓝图。尽管华人历史的追溯可分为两类:一是先侨开拓的新居史,一是更为厚重的故土史,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向西方的屈辱史,可谓是世界华人的源点。
历史,不仅是当代之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是面向未来之镜(以史为鉴)。韦尔策就曾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他说:“对自己的过去和对自己所属的大我群体的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乃是个人和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人们当前——着眼于未来——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①[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对“留学垃圾”的认知,新移民作家们正是在“大我的群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社会层面来展开的,并将其根植进肥厚的历史土壤之中,将其纳入未来的展望之中,而在未来之中,新移民与小留学生之间的代际差异,将在浓郁的焦虑中得以弥合,因为这代际焦虑,并非源于个体间的差异,而是“共同体”的整体意识,尤其是在加拿大多元社会语境下得以确认的少数族群身份中。
三、伦理焦虑与“孝”的现代反思
新移民的离散写作,一再重复小留学生褪变为“留学垃圾”的沦落过程,反复用冷色调着墨那凄凉的结局,在隔岸希望之火的参照下,持续地生产惊诧的文学体验。这所谓的“蓝色调传统”,并不是一味地让人们陷入不可挣脱的泥淖之中,而是在人物的塑造与环境的形塑中,始终留有峰回路转的余地,以翘首那风雨后的暖意。
《小留学生泪洒异国》中的曹俊杰,由于不堪忍受异乡的孤独和英语水平太差所造成的巨大压力,选取以死亡作为最后的解脱。在他寄给国内家人的遗书里,除了前面两个缘由之外,还有一段感人至深的“孝言”:“爸爸,妈妈,还有爷爷,我辜负了您们的一片衷心期望,我成不了才,也没有脸见您们。妈妈,您有心脏病,每天要按时吃药。爸爸,您的工作压力很大,但就不要喝太多,对身体不好。爷爷,不要抽那么多烟,最好戒了,祝您长寿”②孙博:《小留学生泪洒异国》,第90页。。曹俊杰的自戕是一种维护人格完整的极端行为,并没有危害他人。《女孩与三文鱼》里的周沸冰,与之相对,就是一个为了满足一己私欲(报复欲)而残忍杀害无辜小女孩的“冷血”。面对着周沸冰的“残酷”与“危害”,小说实际上并没有将叙事的重点聚焦于此,而是更多地着墨于他的另一面孔,那暖色的一面,其中之一即是他的“孝言”:“我还想说,他(指周沸冰的父亲)现在也慢慢变老了,长年在海上漂流也太辛苦,最好还是回陆上吧。”“我知道你们为了我,用去了所有的钱,现在已经开始借钱,但我以后会挣很多钱给你的。我现在就已经开始挣点小钱了。妈妈,我真想能留在这里,以后让你也移民过来。”③陈河:《女孩与三文鱼》,《女孩与三文鱼》,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107-108页。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论语·泰伯》)。正是由于对人性本善的坚守,新移民的离散写作,虽然再现了小留学生的沦落过程,但也用小留学生们真挚的孝心,否定了“留学垃圾”的称谓,表现出如司徒老师那样的不承认姿态。这与新移民作家将小留学生群体视为华人族群的下一代的社会意图是契合的。他们不仅不承认,而且还用文学发出“拯救”与“关爱”的社会吁求。这鲜明地体现在《小留学生泪洒异国》中。小说中,南方先生并不是一个情节性人物,而是一个功能性角色。他的叙事意义在于,在感性的文学表述中传递出理性的力量,直接通过他的言说来表达作者的叙事意图。在前文的引述中,我们得出“提醒”与“反思”的写作动机。此处,我们将再引述南方先生的一段话:“……加拿大社区素有‘邻里相望’的传统,英文叫Neighborhood Watch,把它移植过来,让我们一起呼吁在坐的华人社团负责人,发起关爱小留学生的活动,好不好?”④孙博:《小学生泪洒异国》,第94页。从中可以看出,“关爱”与“拯救”的叙事目的。
南方先生的存在,令《小留学生泪洒异国》具备了元小说(metaficiton)的一些特征。帕特里夏·沃(Patricia Waugh)认为,区分元小说与非元小说的基本依据在于小说中是否有意识暴露了作者的自我意识。⑤[英]Patricia Waugh:《后设小说:自我意识小说的理论与实践》,钱竞、刘雁滨译,中国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年,第6页。同样出版了《小留学生闯世界》访谈录的南方先生,不仅表明了作者孙博自我意识的有意暴露,实质上也混淆了作者与人物的界限,令作者直接进入故事情节之中。与孙博相似,陈河则以“附记”和“以此文纪念……”的文本印记,来凸显他在文本中的自我意识。需要指出的是,与“为虚构而虚构”的元小说相比,孙博、陈河等人的写作,并不是通过有意识地暴露叙事的痕迹,或者有意味的文本游戏,来夸大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距离;恰好相反,他们是为了凸显自身对文学创作的关注,力图建构虚构的真实,通过自己对文本世界的“露迹”与“参与”,来有限度地实现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统一,进而将有关小留学生现象的“提醒”与“反思”、“关爱”与“拯救”,从文本世界过渡到现实世界之中,以达到令读者规避小留学生问题的虚构性,并正视它的真实性叙事效果。
小留学生在离散中缺少父母的陪伴,实际上,这也是各个代际间留学生共有的生存状态。纵观中国留学生史研究,就代际问题,实质上是很有争论的,①参见宋健:《中国十代留学生》,《重庆与世界》2003年第10期;王奇生:《中国留学史上的“六代”留学生》,《神州学人》1994年第10期;佚名:《第五次浪潮——中国留学生百年回顾与展望》,《21世纪》1993年第6期。但无论是,五代、六代还是十代的划分,仍然有两个代际的留学生是被疏忽的:一个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台湾留学生群体,另一个是我们现在关注的小留学生群体。除却历史研究的意义,仅在父母的维度或者家庭伦理的视野内来看,当下的小留学生群体与以往任一代际的留学生群体都有所不同。以往的留学生固然也会肩负着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愿,但更多的是承载救亡图存,振兴民族国家的重任;即便从中国台湾留学生群体开始,这种历史重担的意味有所缓解,开始关注个体,逐渐实现由“留学”到“散居”的转变,直至“为留而学”成为“留学”的主流,但从始至终,父母都很少是他们“留学”和“散居”人生规划的有机构成。
除了社会语境,全球化变迁之外,从家庭伦理的角度来看,小留学生们背负的几乎全是父母的寄托,里面的确有望子成龙的心愿,但有一部分却承载着父母自己的西方憧憬,如《小留学生泪洒异国》里的卓艳芳,得知儿子因绑架杀人而深陷牢狱时,痛不欲生地说,“马涛可是我的命根子!是我唯一的希望,我还指望他带我去加拿大呢”②孙博:《小学生泪洒异国》,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还有《移民岁月》里瑞贝卡的母亲,希望通过留学进而留在西方,让女儿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贵族梦。除此之外,从现有的有关小留学生现象的写作来看,父母的寄托中还有两种内容:一是中国人的顽疾——面子与攀比,如《小留学生泪洒异国》里白芸的父母,为了跟出国风,不惜全家举债;另一个是当下中国社会的顽疾——贪腐,父母让孩子出国,就等于让来路不明的钱洗干净,同时也为自己的未来留一条康庄大道。如《小学生泪洒异国》中夏小松、曹俊杰的父母、《移民岁月》中健立的父母、《我是一只小小鸟》中的马红堡等。
在父母的寄托中,除了爱的本性之外,私欲也是其主要的构成。这意味着下一代的“留学”已经不是纯粹的个体行为,固然少了某些历史的包袱,但已然成为某些父母满足私欲的工具。这种爱的工具性与小留学生“遗书”里的“善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再次生成惊诧的文学体验。由于小留学生本身的未成年性,其所引起的种种问题,父母自然难脱其咎。在这个问题上,有人专门以“‘小留学生’浪迹天涯的根本原因在于父母”为标题著文③马健:《“小留学生”浪迹天涯根本原因在于父母》,《出国与就业》2004年第7期。,对小留学生的父母进行指责。与这种掷地有声的指责相较,新移民的离散写作采取的是一种无声的批判。除了再现“提醒”与“反思”“关爱”与“拯救”的社会吁求之外,这类写作不仅真实地呈示了小留学生们的孝心,还客观地展现了小留学生沦落之后,父母们的悔恨与愧疚,如马涛的母亲,竟因此而发疯;曹俊杰的父亲在审判中主动坦白、配合警方破获更大的贪腐案等。可以说,正是孙博、陈河等人对客观与真实的美学追求,令他们的写作展示出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批判效应。这种效应,不在陈述,而是在由陈述所引起的有心读者的自觉警惕与反思,进而生产出穷究与思变的焦虑感。这种感受首当其中的是家庭伦理中的“孝”。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④《孝经·三才章第七》,《礼记·孝经》,胡平生、陈美兰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9页。汤一介先生认为,“孝”作为一种重要的家庭伦理的哲理依据就是孔子的“仁学”⑤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⑥《中庸·第二十章》,《论语·大学·中庸》,陈晓芬、徐宗儒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4页。汤一介先生曾解释,第一个“亲”为“爱”之意;第二个“亲”,是指“亲人”。⑦汤一介:《“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在《郭店楚简·语丛二》中,有以下一条:“爱生于性,亲生于爱。”⑧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9页意思是说,“爱”是人的本性,而亲情是由“爱”而生的。至此,可以说明“孝”与“爱”(“亲”)的关系,也说明了爱自己的亲人,即“孝”,是源于人的天性。
很多时候,人们对“孝”的了解往往失之偏颇,总是强调“孝”的一个维度,即子女对父母的爱心,而忽视它的另一维度,即父母对子女的爱心。特别是在“父为子纲”的封建思想中,“孝”发生了很大的扭曲。鲁迅曾对此进行了辛辣的揭露与严酷的批判:“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的‘纲’。倘如旧说,抹掉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真情,播下乖刺的种子。……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①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
从对小留学生现象的写作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父母将“爱”视为“买卖”“报恩”“交换”“利害”等所谓的“纲”思想,这当然是对“孝”的曲解,也是现代语境下家庭伦理中封建性的延续与呈示。也就意味着,孙博、陈河等人有关小留学生现象的“提醒”与“反思”、“关爱”与“拯救”的社会吁求,不仅仅停留在对社会表层的关注,更是深入到文化心理结构层面进行揭示。这种文学情节性的批判,实际上是一种无声的批判。它批判的不是小留学生们的留学动机,而是掺杂其中的,甚至喧宾夺主般隐匿的父母的动机。离散中青春的陨落,固然有西方阴暗面的诱因,但其源点大部分应归因于父母对“孝”的工具性理解与实践,或者说是对“亲”的根源性背离。
四、多重焦虑与面向未来的华人新移民
虽然“留学”的传统得以传承,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它同样发生了变异。最为明显的是,“留学”已经从“学而不留”的时代过渡至“为留而学”时代。同样通过人物的言说——“小留学生何去何从?可以大胆地说,90%以上的人会想法设法留下来,落地生根,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是我们的一份子”②孙博:《小学生泪洒异国》,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93页。,孙博在其文学世界中将时代变迁清晰地勾勒出来。
在如今的新时代,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举措与中国积极主动的“全球化”追求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及其效应,尤其是中国的强劲发展和持续繁荣,让更多的留学生选择“回流”,乃至国际移民也开始“跨国离散”,进入“双重离散”③参见郭世宝、丁月牙:《从国际移民到跨国离散:基于北京的加拿大华人研究的“双重离散”理论建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的新阶段。作为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构成,新时代中国推动“全球化”的重要环节,在“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留学政策方针的指引下,留学事业依然持续发展,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大关,持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的地位。④张烁:《中国去年留学人数首破60万》,《人民日报海外版》第2版2018年3月31日。虽然留学生的“回流”也同样大幅提升,但改革开放40年已然有200万以上的留学生选择留在他乡,⑤改革开放40年,留学519万人,学成回国313万人。参见张烁:《中国去年留学人数首破60万》,《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3月31日第2版。成为华侨华人群体的一分子。正如“来去自由”的政策方针所表述的那样,无论是“学而不留”,还是“为学而留”,都是留学生们的自由权利,甚至是全球化所赋予他们的空间流动权利的体现,因而在这个层面上,留学生与来源国(中国)之间的真正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回国,而在于他们能否为母国真正地“发挥作用”。
显然新移民作家们所焦虑的不是“回国”那部分,而是“为学而留”的“小留学生”们。克尔凯郭尔曾认为,焦虑不可能因确定的东西而产生,它所涉及的则是“由可能性而产生的、作为可能性的自由的现实”⑥Søren Aabye Kierkegaard.,The Concept of Anxiet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58.。由小留学生问题而产生的焦虑同样是由可能性而产生的,这也就意味着,新移民在与小留学生相关的写作中一再保持的焦虑情绪是根植于历史、面向明天的未来性焦虑——关涉小留学生们如何在新居之所上“发挥作用”。
在“代际焦虑”中,新移民将家庭血亲关系推及社会、族群层面,把小留学生视为加拿大华人族群的“下一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正如司徒老师不承认“留学垃圾”的存在那样,新移民们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更期望“长江后浪推前浪”,而非一代不如一代的哀叹。于是,新移民将焦虑舒缓的可能性寄托于历史之中。
如果说,在“代际焦虑”中,新移民确立了与小留学生之间的族群代际关系,那么在历史的回溯中,新移民将“自我”与作为“他者”的小留学生统合为一体,共同面向未来,思索“留学”如何“发挥作用”。这种使命感的确认,是历史性的内在要求,更是一种历史的传承与反思。历史性地看,新移民正是“为留而学”的一代,也就意味着不可避免地将与母国发生空间的疏离,至少在这一点上与历史传统是相背离的。同时,在所难免的空间性愧疚,一方面促使新移民将小留学生视为“为留而学”的下一代,另一方面也被小留学生的悲惨经历所提示,进而让新移民不得不正视自身与故土之间的现实疏离与历史关联。与历史中的前辈及其所开拓的家国精神相比,从留学到留居的新移民希冀在历史的愧疚中能够有所作为,“发挥作用”,进而弥补现实疏离并担负历史传承,而对“小留学生”现象的关注,特别是对小留学生形象的建构,正是新移民自身所面对历史焦虑的一种文学投射,同时也在文学叙事之中得以舒缓。
虽然如孙博《回流》、尧尧《你来,我走》所表述的那样,新移民中确切有“双重离散”的存在,但就“小留学生”现象而言,“为留而学”依旧是小留学生中较大的留学动机。忆往昔,“为留而学”何尝不是新移民们的动机呢?但终究此时的新移民早已度过了留学时期,真切地在加拿大开始实在的生活。随着新居体验的累进,他们已经由昔日“魅惑的西方”逐渐过渡到“西方的祛魅”,进而发现一个真实的西方,由此也使他们开始调整面向西方的姿态,真正地游刃于东西方之间,并很有可能地生成一个“边缘的视点”,而正是得益于这样的视点,新移民得以对“小留学生”现象进行重新观照与审视,而不是停留在“留学垃圾”的简单描述与控诉中。
在对“小留学生”现象的批判与反思中,新移民作家始终处于一种伦理焦虑之中,却又难能可贵地保持一种焦灼的清醒。新移民作家在对“小留学生”现象的剖析中发现,小留学生们留学的动机很多时候掺杂着父母走向西方的愿景:
大部分家长认为,中国目前在科技领域、环境保护、文明程度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经济收入差距也太大,生活水准更无法相比。在国内即使把孩子培养成大学教授,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孩子一生的经济状况,而且,这些差距相当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①孙博、余月瑛:《小留学生闯世界》,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第214页。
这些家长们的“愿景”与当初新移民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西方时是何曾的相似。《曾在天涯》中的胡大鹏得知高力伟拿到去加拿大的签证时,前者用直抖的双手捧着签证,告诉后者:“这等于多活了一百年。”“这里一百年以后还不见得那么发达,那你马上就得到了,这不是多活了一百年么?”②阎真:《曾在天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
但是,历史的车轮毕竟已经走到了日新月异的新世纪,这种似曾相识,让已经在新居之地面对面体验二十余年的新移民们倍感焦灼,因为他们深知昔日故土之上的“西方”在如今真实的西方面前,只是被虚构的幻象,而更可悲的是,这幻象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依旧保持在时间的源点,存留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在这种觉醒后的悲凉中,在代际焦虑、历史焦虑的混杂中,新移民作家一方面通过描写小留学生沉沦后的“孝言”,对之表达父辈们的关爱之情、拯救之心,而另一方面又不断揭示家长们的“盲目”与“私欲”,对悲惨的小留学生处境进行深层的挖掘与剖析。
新移民作家因关注和聚焦“小留学生”现象而引起的多重焦虑,固然有着社会性的诱因,但更多的是内在心理上的镜像效应:新移民作家们在小留学生及其背后的家长们的身上看到了昔日的“盲目”,甚至“私欲”。这个镜像效应,固然存在于文本之中,更在于文本之外。萨义德曾说过:“在阅读一遍文字时,读者必须开放性地理解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写进文字的东西,另一个是被它的作者排除在外的东西。每件文化作品都是某一刹那的反映。我们必须把它和它引发的各种变化并列起来。”③[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91页。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移民作家通过文学表征的“新移民——小留学生——家长”之间的镜像效应,不仅在具体的文本中有着文学的意义与价值,而且还应该把这些意义与价值置放于更为广阔的文本之外。
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言,焦虑是因可能性而产生的。在笔者看来,新移民因“新移民——小留学生——家长”三者之间的镜像效应而生成的多重焦虑,也同样是因可能性而起的,特别是当他们在历史之中、在故土之维、在新居之地,重新思索离散的生存体验,瞻望未来的可能性时。新移民与小留学生之间虽没有真切的血缘,但由于在加拿大、在新居之地的少数族群身份,让二者之间生成了在故土上被忽视的族群关联,特别是隐性的种族歧视与多元文化政策产生不可调和、甚至难以察觉的矛盾冲突时。正是在这样的新居语境中,新移民基于邻里相望的“拯救”与“关爱”,更多的是一种族群情感的呼唤与维系,而在其中孕育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全球播散的努力与行动。
新移民与家长之间,虽然有着难以避免的空间差异,但因故土情感与成长记忆,二者之间依然有着难以割舍的历史关联,而走向西方时的魅惑心理正是其一。只不过,此时的新移民已经在新居体验中觉醒,已然为西方祛魅,并在真实的西方中具备了反思的能力与力量,而二十年后的家长们却依旧维系着走向西方的迷梦无法自拔。这种历史的落差,让新移民在“小留学生”现象(特别是对“孝”现代异化的深层关切)中认识到文化自信在东西方语境之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特别是当因“小留学生”激发而成的镜像效应关涉记忆中的西方憧憬与魅惑时。之所以产生魅惑的心理,盲从于幻象之中难以自拔,正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人文化自信的丧失让“媚西”进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而“小留学生”悲剧的产生,“媚西”难脱其咎。由于镜像的存在,新移民也不得不正视并反思自身的“媚西”记忆,而且由于“代际”与“离散”的时空转换,特别是在未来的瞻望之中,他们在“新移民—小留学生—家长”的三维关联中,不仅重新确认了新居与故土之间的空间关联,还真正认识到文化自信在离散语境,特别是面向未来的过程中得以重建与发展的必要性,而文化自信的建构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球播散提供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