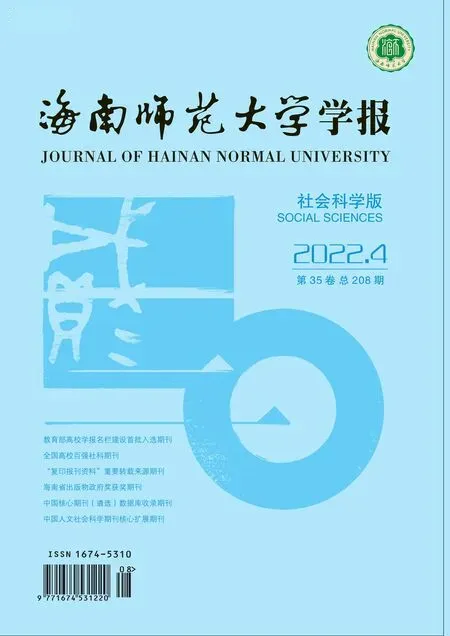印尼华人的文化认同与本土融入
——基于华文文学视角
马峰
(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东南亚与中国同属东方文化圈,中华文化在地缘传播中对东南亚影响深远,而华人移民则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在文化接触的进程中,移民自带的族裔文化与移居地的本土文化必然产生相互碰撞。不同立场的社会群体往往有着不同的身份观,与文化冲突导致的身份裂变相比,社会整合则讲究文化身份的整顿粘合。对于印尼官方而言,为了控制国家内部的文化冲突,他们一度采取强制性的文化整合。1965年“九·三〇事件”以后,在苏哈托统治时期,更是颁布了针对少数民族的全盘同化政策。有些偏执的本土论者将“少数民族同化”概括为“外裔加入和被吸收到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的躯体之中,以致具有自己特点的集团再也不复存在了。”①周南京、陈文献等编译:《印尼华人同化问题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1996年,第133页。然而,华人的文化身份带有故国标识,这是先天性的族群精神遗传,是无法替代乃至全然剔除的。少数民族同化政策有助于形塑对主流文化的集体认同感,然而整齐划一的整合举措也必然造成弱势族群的文化纠结与身份迷失。其实,在文化迁移与文化变异的交叉作用下,文化的多元混杂往往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文化多元与文化整合的角力中,印尼华人如何剔除文化认同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如何应对主流文化的同质整合?如何在自我调适中融入本土?在全球化时代又该如何抉择多元文化进路?检视印尼华文文学的整体状况,可以梳理出印尼华人从文化原乡认同到尝试融入本土的变化路径。在1966—1998年的华文封锁期,华文文学发展几乎停滞,黄东平《侨歌》三部曲、阿五《人约黄昏后》等是少数代表性作品,其文化原乡认同也比较浓郁;1998年华文解封后,虽然华文作家有断层现象,但是仍出版了不少华文文学作品,如林义彪《大唐客长罗芳伯传奇》、晓彤《哑弦》等皆是管窥华人文化认同更迭的重要参照文本。
一、文化原乡的精神纠结
乡愁书写是华文文学中绕不开的母题,乡愁即是对原乡的眷念之情,“文化乡愁”与“文化原乡”的不同提法并无本质区别,如果“乡愁”暗示了主观情感的拉近,那么“原乡”则摆设了一种客观审视的距离。对于分散各地的移民群体而言,总有一些无形的文化因子让他们紧密结合,而原乡作为文化发源地无疑是最具韧劲的纽带。当然,心怀暂居异地的侨民,心持定居当地的华人,还有心系本土的华裔,其不同心态所承载的原乡份量也轻重有别。在现实中,“乡”在不同的华人群体中所指有别。当下的印尼华人以华裔为主体,他们的“乡”至少有两层寓意,一是祖籍国的精神文化原乡,二是入籍国的实体生息家乡。如果踏上寻根问祖的返乡之路,那么在中国还有“陌生”而“遥远”的祖居地故乡。可以说,任何一个移民个体或群体都会因身居异地而回望原乡,现实世界的原乡由于时间磨砺会渐行渐远,而精神世界的原乡由于文化沉淀反而越来越近,最后原乡变成遥远的地理符号,却又化育为深埋心底的文化因子。
(一)华文教育的文化承载
20世纪初,东南亚华文教育的兴起与原乡情结紧密关联。华侨经商致富后担心后代“数典忘祖”便想兴办教育,“当时创办华文教育首先是为了维护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而不是首先使华人子女获取在当地谋生的手段”①梁英明:《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海外华侨不仅非常重视华校教育,还将传承祖国文化视为优良传统之一。他们特意从中国聘请教师,教导后代学习中国传统的生活、风尚、习惯等,避免被本土文化所同化。单就文化传承的使命感来考量,黄东平的《侨歌》可谓是一部向荷属东印度时代的华文教育致敬之作。在新式教育兴办之前,曾担任华人“甲必丹”的林显臣就从中国请秀才教私塾,让大儿子林添禄接受正统的中国教育。土生土长的侨生群体经过数代繁衍,在语言及生活上早已本土化,但他们依旧保留传统的文化习俗。“他们世代把它保持下来而不废弛,该是它支持着他们的精神世界,使他们还成为中国人的缘故吧!”②[印尼]黄东平:《七洲洋外》,北京:中国友谊出公司,1986年,第351页。通过个体性的私塾教育,在一些子弟身上实现了纯粹的文化回流,这也成为侨生“再华化”的范例。当新式的“中华学校”创办,这种中华文化的宣导态势便迅即普遍而炽烈起来。
在华校教师兼作家的阿五身上,华文教育情结格外凸显。《火》充满了对客家教育传统的钦佩,父母不顾家庭的经济困难,仍坚持把孩子送回国“续续符”,它浓缩的正是客家人对原乡文化的深层依恋。在《又是榴梿飘香季节》里,开首便借华人的思乡咏叹寄予明显的文化意图——虽然华裔侨胞在南洋落地生根,但是依然心心念念着故乡寻根。两个华侨家庭,一家送子女到荷兰“祖家”深造,另一家送孩子回“祖国”学习。在中西教育方式的不同抉择中,夹杂着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而西化家庭的冷漠则映衬出传统家庭的和睦安乐,这恰是原乡教育所承载的文化魅力所在。为何回国升学如此受重视?从作者的叙述话语便可窥知,“远在当年沪战爆发前夕,上海市郊区有一幢建造巍峨,专为招待华侨学生回去深造的黉宫;它是华侨子弟曾经北望神州久已引领企慕的憧憬”③[印尼]阿五:《竞赛》,《人约黄昏后》,中国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13-14页。。在“神州”“祖邦”的称呼中,华侨子弟已然将原乡神圣化,即使他们学成之后重回印尼或辗转美国,但是认同空间依旧充塞着原乡文化。④关于印尼华文教育与华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关联,参见马峰:《印尼华文教育历史发展与华族身份认同调适》,《民族教育研究》2019年第6期。
(二)华侨领袖的文化示范
林义彪的《大唐客长罗芳伯传奇》开拓了印华文学的长篇历史小说题材。书名有四层内涵,一是“大唐”,指唐人之意,这是早期海外华人对自我族群的惯称;二是“客长”,道出了人物的身份地位,这是客家人对同族有威望的首领或前辈的尊称;三是“罗芳伯”,他原名罗芳柏,伯与柏一字之差,而“伯”则体现了当地的用语习俗,这更能凸显印尼华人先贤的本土融入;四是“传奇”,将历史渊源与英雄色彩相交叉,其用意在于架构一部基于华侨历史的英雄传奇。1772年,罗芳伯带领乡里逾百人奔赴西婆罗洲淘金,随后创立盛极一时的“兰芳大总制”(1777—1884),并采用共和式的领袖推荐体制进行管理。他不止在印尼华侨华人中影响深远,在世界华人领域也极具代表性。作者慨言:“谨以此书,作为向在世界各地客家人的献礼,并对客家先驱大唐客长罗芳伯表达无限的追思。”①[印尼]林义彪:《大唐客长罗芳伯传奇》,雅加达:印尼客家博物馆出版,2013年,第5页。罗芳伯(1738—1795),生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石扇堡。小说的古典气息浓郁,儒学典籍、名篇佳句、历史典故都信手拈来,而最值得称道的是罗芳伯的传世作品《金山赋》《遣怀》《祭诸神驱鳄鱼文》。作者深度挖掘印尼华侨历史,贴切再现古典情景,在罗芳伯的丰功伟绩之外,其杰出侨领的典型形象也具有极强的中华文化示范力。
(三)文化原乡的在地回望
不少作家在书写老一辈华侨形象时,经常使用“唐山”“祖国”来指称原乡,这也连带出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感。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称呼并非空间实指,主要应是一种文化隐喻。就文化原乡的异地回望而言,书写形式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借用古典文化符码,正如白放情、许也许等常在创作中注入古典诗词的韵味,有者则采用章回体小说的传统形式。二是书写中国故事,不免与本土产生疏离。钟若迟的《虎》透过采龙眼、办私塾、借洋枪等事件,隐示了馒头庄的地域特征,据此可以推定这是一处民国时期的南方小山村。小说中的谢先生是中国传统乡绅的代表,他是德高望重的私塾先生,也是乡村事务的民间协调者。三是中华文化的在地移植,体现了文化的变异与适应。在松华的《那年春节》中,由于地方当局禁止华人过春节,主人公反而在历史回溯中寻找到一种心理潜层的文化抵抗。“童年时,就听父亲讲过,彼岸叫对面港。深入其内地有个中华湾,湾中有条河叫淮因河。日军南侵占领麻埠的三年里小镇上的华人都纷纷往这里避难,故叫中华湾。”②[印尼]松华、雯飞:《晨间一瞬雨》,雅加达:印华作协,2006年,第101页。“中华湾”与“唐人街”一样,这种原乡式命名成为文化移植的重要模式,在集体无意识中走向族群及其文化的自觉。另一篇《险过爆石山》,作者写到“土生华人”群体,即华人男子与印尼原住民妇女通婚的后裔,在他们身上铭刻着根深蒂固的原乡文化印记。在西爪哇的乡间小镇,这些混血华裔早已本土化,却还保持着春节、冬至、端午节等各种传统节日习俗。他们不识华文,也不会讲祖籍语,而住屋却悬挂着红底黑字的对联。两篇小说提供了截然相反的文化视角,在官方同化与自然同化的两种进程中,原乡文化的在地回望也走向不同路径,前者的文化召唤内隐却强烈,后者的文化传续外显却平和。
原乡本是精神的依托地,当原乡的文化传统在现代转型中遭逢变质,那么对文化原乡的想望又将何去何从?文化回望可以采取批判性与反思性地介入姿态,并不一定都要步入理想田园,原乡的花果飘零也可以在异地实现灵根自植。金梅子的《古壶》就通过中国宗亲对祖传古壶的觊觎,表现传统文化在原乡的价值崩塌,反而是移居印尼的长男开枝散叶,身为华裔第二代的阿龙也在回乡之旅中继承了先祖遗志。“世代相传的宝物”只能被埋藏,其实也一并埋葬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而“最安全”的决定显出文化悲情的无奈。③[印尼]金梅子:《客家面》,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37页。“阿龙”被有意刻画为“龙的传人”,而海外华人传统的散播也具有反讽意味,在中华原乡与海外离散的双向撕扯中造成巨大冲击。古壶被深埋在家乡的菜地里,并没有被带到印尼。纵使这片土地上的家族后辈会慢慢遗忘,暂时沉睡地下的传统物象却并未远离。虽然文化原乡的回望显得异常沉重,但是文化传统的种子显然已在海外华裔的精神园圃落地生根。
二、立足本土的文化融入
印尼华人早已扎根本土,虽然在文化上依然存有隔膜,但是已经显露出积极的文化融入姿态。实际上,华人的“文化融入”与国家层面的“文化融合”还有着不小的距离。文化融合是经由异质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而自然生成的,文化融入主要指弱势文化向主流文化的主动接触,在对主流文化的主动接受过程中仍保留自我文化,并且形成开放式的文化共存。在印尼的文化环境中,华人文化显然处于文化融入阶段,尚未达到真正的文化融合。那么,在中华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华人的文化融入究竟情势如何?吴祖桥在对苏北省的观察中指出,目前印尼华人文化虽然和祖先留下的稍有差异,但原则上并没有违背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精神;而根据郑一省在三宝垄的个案调查,汉文化的变迁不仅表现在土生华人族群人数的大量增加,即使仍保留着较多汉文化特征的华人,其日常生活习俗也在逐渐印尼化。①郑一省:《汉文化在印尼的传播与变迁:以印尼三宝垄市为例》;吴祖桥:《印尼苏北省的华人文化现状》。参见周建新主编:《第六届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138、295页。这两种观点看似相反,却都指向中华文化的本土变迁,这种变化与适应正是文化融入的双向结果,而精神的中华性与日常的本土性可以共融不悖。当然,融入过程并不见得畅通无阻。华人立足本土的文化融入已是既成事实,但文化接触的自然性、长期性、开放性依旧不可或缺。
(一)日常用语的在地化用
日常用语是文化融入的显性标志,黄东平的《侨歌》极富南洋韵味,算是语言在地化用的典型。华侨用语有杂糅的特质,“除了当地语、洋语等等而外,汉语方言就有厦门话、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等等;而汉语与当地语混杂使用,则更普遍”②[印尼]黄东平:《短稿二集》,新加坡:岛屿文化社,1993年,第299页。。作者尽量避免方言用语的杂糅难解,有时为便于理解则采用括号加注的形式。华侨踏遍了南洋群岛,“华侨的劳迹还留存在当地的言语里:楼顶(即楼上loteng)、豆腐(tauhu)、豆芽(tauge)、风炉(anglo)、木屐(bakiak)、肉丸(bakso)……用的都是闽南话的译音字。”③[印尼]黄东平:《七洲洋外》,雅加达:印度尼西亚金门互助基金会文化部出版,2003年,第6页。向忆秋指出,《侨歌》中的闽南侨商形象体现了“作为闽南移民所携带的闽南族群文化基因”④向忆秋:《黄东平〈侨歌〉三部曲中的闽南侨商形象》,《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就此而论,“闽南话”无疑是闽南族群在地融入的显性文化基因。
华侨与当地人的长期相处,语言的交融也丰富多彩,有印尼语、荷兰语的音译词,也有华侨自己创造的新词。《侨歌》有大量根据当地语言音译的词语,地名的直译最为常见,小说所聚焦的“海边城市”便称为“坷达·班岱”(kota pantai)。印尼语音译词范围广阔,有称谓类:先生叫“端端tuan”,华人官员称“甲必丹kapten/kapitan”,乡村译作“甘榜kampung”等;有日常生活用语:当地妇女的上衣译作“加峇耶kebaya”,蜡染布的花裙称“巴泽batik”,筒裙译作“纱笼salon”;还有商业用语:店铺译作“土库toko”,小杂货铺叫“亚弄warung”,菜市场叫“巴刹pasar”等。
华侨长期生活于南洋,面对陌生事物,总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说法,于是一系列生动贴切的新鲜词汇就应运而出。华侨在家乡与异域的感触对比中产生身份标记的用词,祖国家乡叫做“唐山”,新来的华侨叫“新客”,出过洋的叫“旧客”,当地出生的华人叫“侨生”,契约劳工被称为“猪仔”。同时,一些“番词”固然体现了华侨不畏艰险去开拓蛮荒的精神,但也不无对异地的歧视贬低,这反而体现了文化融入的艰难,如“过番”“番客”“番邦”“番话”“生番”“番婆”等。另外,还有“红毛鬼”“荷兰鬼”“红毛楼”等对殖民者含贬义色彩的词汇。这些形象贴切的词汇,暗含着华侨的智慧,通俗中不乏风趣。
(二)代际认同的文化更迭
随着华侨到华裔的代际更迭,文化原乡渐行渐远,年轻一辈更贴近现实居所的本土家乡。晓彤的《金伯》表现出不同代际的认同差异,金伯是老一辈的华侨典型,向往回唐山落叶归根。“我热爱我居住的地方,也习惯了我现有的环境,当然我明白我祖上的来源,可是我出世在这南岛,这儿是我的家。所以无论如何,我就不能像金伯那样对遥远故土的情深,万般的感触与乡愁。”⑤[印尼]晓彤:《哑弦》,雅加达:印尼与东协月刊社,1996年,第67页。由此可见,“我”作为新生代的华裔,已经趋向于落地生根的认同观。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政治认同及文化认同的融入趋势更为突出。于而凡的《五月》所塑造的华裔大学生“小叔”正是融入本土文化的典例,连女友也是原住民。对于族群文化差异,他的言辞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华裔新生代的文化认同观。“我认为我们并没什么价值和文化的大差异,我们在学校受到的教育一样,在家里讲的也是印尼话,吃印尼菜,对华语华文我一概不通,还讲什么中华文化,除了肤色不一样,基本上和大部分印尼人并无什么不同。我可不像你还固守华人本位,护守什么支那文化。我已认同印尼这土地。”⑥印华作协、获益编辑部编:《浴火重生》,中国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0年,第39页。然而,在1998年的五月暴乱中,华人族群成为被迫害的对象,这让新生代对本土角色产生极大的认同困惑。或者说,政府行之有效的同化政策在此刻走向悖反,已经融入本土的华人族群再次成为被原住民所排斥的“异己”。对于融入的两难,结尾的诗歌抒发了民族融合理想的破灭,漂泊之感则流露对世界大同的美好期冀。
(三)本土家乡的文化呈现
当下的印华作家基本都是土生土长的华裔,对他们而言“家乡”早已纯然源自本土,因此“家乡书写”即是本土书写的重要范式之一。对于本土家乡的文化呈现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个体的家乡情结,往往以乡愁眷恋为引发。松华的《点点乡愁话黄饭》便借童年美食去品味乡愁,而故乡早已是生养自己的印尼家乡。离开家乡到雅加达,自己就成了他乡异客。黄饭又叫黄姜饭(Nasi Kuning),由稻米、椰汁、香茅、黄姜水混合煮成,用香蕉叶包裹香味更加浓郁。黄饭是印尼传统美食,在饮食文化的内里也承载着本土文化。二是泛化的乡土情致,在乡土风物的欣慕中融入本土文化色彩。云风的《惊情》写到穆斯林婚礼的田园场景,“乡村里若有举行婚宴,都是在自家门前的空地,支起铁柱,用帆布搭成能容纳百人的场地,用椰叶缀成花絮的舞台,左邻右舍的亲友都会自动前来帮忙”①[印尼]云风:《风从洛水来》,雅加达:印华作协,2015年,第81页。。在原住民的乡村婚宴上,不论是民族传统服装峇泽的穿着,还是婚嫁习俗及喜家装点,满目皆是本土文化风情。
白放情对家乡及乡土都有较多描绘,他的《远山情牵五代心》再现了华人家族的离散史。小说中,黄飞然是热血归侨的代表,在红色使命的感召下回国服务。他的祖辈在印尼经营过钻石矿业,还有橡胶园,后代却分散各地。“这个第二故乡,有他的家呵!今天,他越过太平洋上空,回到他的高曾祖父来时还是一片原始荒岛的岛上来。他激动,他感慨万千!山岗下,就是他长大的家啊!”②[印尼]白放情:《远山情牵五代心》,《梦于沙朗岸》,中国香港:梦萍出版社,1999年,第313-314页。当原乡想象与现实落差,他无法释怀对印尼家乡的诸般怀念。“第二故乡”的称谓值得玩味,在他的言语中“第一故乡”依然是中国原乡,作为出生地的家只能退居其次。三十年后,他重返故土毫无陌生感,其实在他的心目中“第一”“第二”并不那么真切,离乡的牵挂反而消弭了两个故乡间的现实距离。在作者笔下,连归侨返乡都对印尼没有隔膜,那么长期生息于此的华裔,其本土融入自不待言。
三、从文化互动到多元认同
在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里,多元文化所表现的相融要大于相斥。反之,在文化相对保守、闭塞或排外的社会里,那么文化隔阂就被人为拉开扩大,而文化冲突与文化自保则会愈显突出。有论者指出,“多民族国家社会个体双重身份分析框架被撕裂,身份焦虑成为社会个体在真实世界中的现实境遇”③于春洋、于亚旭:《全球化叙事中的社会个体身份认同——以多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讨论》,《东方论坛》2020年第5期。。姑且不谈政治身份,仅就文化身份而言,印尼华人的身份焦虑尤重。印尼由多民族组成,华人文化当属其多元文化的一份子。然而,政府曾经实施的民族同化政策却严重制约了华人文化的发展,当弱势文化被权力机制所规训,多元文化就必然无所凭依。换位思考而论,华人同样也需要摆正文化心态,避免民族主义情绪的文化僭越。在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他者”文化问题上,饶芃子主张多元文化的认同,应该拆除民族主义的误解,促进平等的沟通和理解。④饶芃子主编:《中国文学在东南亚·前言》,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页。反之,不同文化间持续的对立与对抗,只会在异化他途上越走越远。寓言体小说《神鸟》就提供了一个文化极端的反面例证,于而凡通过“神鸟颂歌”(王母青鸟)与“神犬赞歌”(二郎神犬)的二元对立,表征了文化图腾式信仰与文化霸权式征服所带来的文化冲突。⑤朱文斌、曾心主编:《新世纪东南亚华文微型小说精选》,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9页。当社会的文明进步以某种文化的霸权宣教为依托,文化包容的缺乏必然导致虚假文明的坍塌。作者借二元对立所潜伏的必然性冲突,反思以自我中心的原教旨主义,实际上暗示了多元文化的相处之道。因此,在多元文化的具体操作上,应当抱持不同文化并存的立场,摒弃非此即彼的单边模式,在文化冲撞中进行磨合对话,在文化适应中进行互动交融。
(一)华人的文化吸收与文化并存
关于多元文化及其认同问题,张云鹏认为,“一种文化在与异质或异族文化的碰撞、交融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文化认同这一现象,也就是对异质文化中有效成分的吸收”⑥张云鹏:《文化权: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向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11页。。一般来看,印尼华人的文化认同具有双重性,中华文化与本土文化处于并存状态。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并未改变,但已经适时吸收了本土文化。可以说,华人的本土化伴随整个移民历程,而本土文化的影响与接受亦然。高鹰的《风雨芝加本浓河》写到独立战争时期,小说中的华大嫂不仅深明大义,而且有积极融入本土的自觉意识。“我们居住在印尼,就得首先学好印尼文,此外,还要学好中文……”①[印尼]高鹰:《高鹰文集》,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第132页。她让孩子把印尼文摆在首位,并且要兼顾中文,体现了华侨在吸收本土文化的同时也努力保留族群文化。另外,凡若的《凤凰的叹息》表现了印尼华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调适及开放思维。主人公任霜飘负责大型演唱会的舞台设计,因为华人被称为“龙的传人”,所以他避免使用带有政治威严的龙的形象,而特意选取凤凰作为背景。“凤凰可以象征为华夏文化”②[印尼]凡若:《我爱浪漫》,雅加达:印华作协,2006年,第255页。,这与中华文化艺术的弘扬恰好契合。同时,他们又邀请原住民艺术家狄朵绘制图案,于是凤凰成了天堂鸟、孔雀、鹦鹉的奇特混合,这是多元文化交混并存的有意尝试。
(二)友族的文化利用与文化反哺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存在,华人文化对本土文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少友族在学习华文、接触华人的过程中也会有意无意地吸收利用中华文化。白羽对此多有表现,其一,是对中华文化的工具性利用,以《班芝兰的惊喜》为代表。小说写到一位道地的爪哇人为了工作与生活坚持学习华语,虽然租售华文书籍只是作为谋生工具,但是几十年来在班芝兰却也默默散播了华夏文化种子。班芝兰被称为雅加达的唐人街,几处华文租书摊成了历经文化浩劫的华人心灵慰藉,而原住民的文化经营纵使无意也是一种文化惊喜。其二,《最后一个孝子》表现友族对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反哺,也反讽华人家庭的亲情淡薄与文化遗失。当在澳洲工作的小儿子连为父亲奔丧都不回,反而是老屋邻居玛斯义多的祭拜告别真诚感人。③[印尼]白羽:《最后一班夜车》,雅加达:印华作协,2006年,第86页。如果说老伯从唐山带来了优良的中华文化,那么原住民玛斯义多在学习利用中无疑扮演了传统继承者。他要做老伯的“孝子”,恳求家属要瞻仰遗容,这种有意尽孝的文化反哺也象征了中华文化嫁接于本土文化的再生可能。
从文化濡染到文化趋同算是文化利用的至高境界,云风的《“杀贼”高手》是该类别的典型之作,小说从失窃案引出友族对中华文化的欣慕。“其实令余欣龙珍惜如命的‘龙头金裤带’不单是那举世罕见的钻石珠宝,另外也蕴含着他对‘龙’这吉祥物的一种情有独钟和热衷于龙的文化的情愫,一名华人朋友曾告诉他,他出生的那一年正好是龙年,按华人十二肖属,他是属龙的,1965年以前,他也受过华文教育,直到华校关闭。他热爱华夏艺术文化,一手书法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那个‘龙’字,千变万化,栩栩如生,使人不信是出自友族兄弟之手的挥毫杰作。”④[印尼]云风:《风从洛水来》,雅加达:印华作协,2015年,第73页。在这里,“余欣龙”的名字别有深意,不妨直译为“我欣慕龙的文化”,这种自我赋名恰恰蕴含了友族对华人文化的趋同。“龙”具有文化表征性,戴上“龙头金裤带”便觉得荣耀,更感觉自己像是“龙的传人”。从接受华文教育到热爱华夏文化,再到融入华人族群,友族在自我转换中形成对华人族群的深层文化认同。
(三)从冲突到融合的多元文化认同
随着代际更迭,即使在华人家庭内部,单一文化模式也不再可行。张逸的《吃饭》营造了文化冲突的逼真现场,从碗筷到叉子、汤匙的使用,中华传统成了落后标签,西化(本土化)悄然侵蚀了华人风俗。在中式家庭的传统观念里,饮食与饭桌都有文化与伦理的寓意。当饭桌被截然区隔,传统的仪式感被破除,老爸老妈用筷子吃东边的一份,而儿孙们用叉匙吃西边的那一份。在三代人之间,“东边”承载着老一辈的东方化(中国化)余绪,而“西边”的年轻辈已成为西化的拥趸。其实,只要摒弃单一文化理念,采取开放式的多元文化心态,家庭内部完全不必如此隔膜。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海外华人常会遭受身份定位的认同困扰,张逸的《尴尬》对此有深刻表现。在各国文化汇集的建筑物里面,印尼华人突然变得无处安身。因为不懂中文,他在中国馆不受欢迎,被误认为是崇洋媚外;在印尼馆,本土生长的华人竟不被“代表国家的团体”接纳。在外面的广场,他被“印中团”热情召唤,这个“印尼出生的中国人”团体成了特异的存在物。“建筑物”象征了全球化的国际社会,每个“厅房”都代表着某个国家。如果说“里”与“外”言喻了政治边界,那么文化显然是跨界的或无疆界的,而“广场”无疑可以承载起跨国界(中国与印尼)、跨族群(移民与土著)、跨语言(北京腔的普通话与标准的印尼语)的多元文化包容。“踩蓬”(chambong)音乐中的太极拳表演,《男儿当自强》音乐伴奏的“唐突”(dangdut)舞蹈,这两个节目(《太极踩蓬》《唐突当自强》)是典型的印尼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汇新生。①[印尼]张逸:《烟花》,雅加达:印华作协,2010年,第71页。印尼华人在尴尬处境中找到出路,在跨国文化的融合中找到归属感,文化杂糅产生了新的文化认同,而多元认同也建构起一种离散族群的文化自信。
四、结语
印尼的华人族群虽然积极主动地尝试文化融入,也敞开胸怀悦纳异质文化,但固有的原乡文化情结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仍不免有些隔膜。文化隔膜的存在是相互的,是一种施受拉扯的关系,其内在的身份焦虑有着多种表现形态。华人作为施动者,既有自我文化的优势心态,也有异质文化的猎奇心态。当华人作为受动者,有时会受到主流文化的同化压迫,有时将面对原住民的敌意排斥。在施动与受动的文化罅隙,还有大量不为所动的文化旁观者,超然抑或绝望都难逃落寞孤寂。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内在的文化传承与外在的文化挫折并存,华人的文化焦虑也就不可避免。华人扎根于印尼本土必然面临文化上的冲突,需要在多元混杂的文化环境中进行认同调适。显然,绝不能盲目沉醉于原乡文化,或者殇悼于传统失落而裹足自限,也不能过分依从官方的文化政策,或者依赖友族的文化反哺,华人的本土融入与文化吸收切实可行但有待加强,主要解决之道还是应该从族群内部的文化包容中提升自我的开放视界。强制性的民族同化已经成为历史,主流的本土文化也趋于开放,华人文化渐渐从遮蔽中走出。因此,华人族群在文化认同上可以把中华文化作为主导,但要正视本土文化的主流地位,这种自然的文化接触与文化融合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