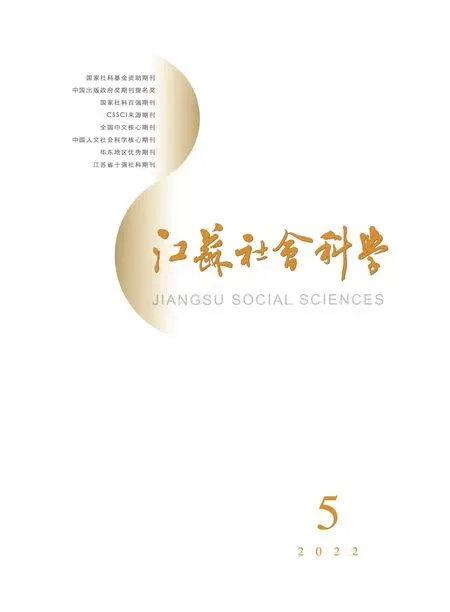论“文选学”在宋代的衰微和变迁
严孟春
内容提要 迄至唐代,《昭明文选》一直都受到文人的欢迎,唐代不仅有李善注本和五臣注本问世,而且还成为科举士子们的案头读物。但到了宋代,《文选》的阅读与研究却由热转冷,此后也未能再回热起来,这种情况持续至清末。探究其中原因,可以感受到由唐至宋在文化环境和文学审美方面的变迁。要言之,宋人对《文选》的冷落既是科举考试改革、理学思想兴起等文化环境变化的结果,同时也和《文苑英华》的编集、北宋欧苏诗文革新运动的推进以及文人创作心态的变化等文学事件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一、引言
南朝萧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集《文选》,历一千五百年时间之洗礼,至今仍耀亮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的璀璨天空,为学界、时人所关注,成专门之学,是谓“文选学”。“文选学”在唐代兴盛,为显学,进入北宋七八十年后则转而趋冷,被苏学等其他文章学、批评学所取代,是《文选》研究史上的一大变迁。变迁发生的原因乃在于唐、宋两代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文学条件,对此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学界更好地挖掘《文选》对于文章学、文体学发展以及对于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意义。当代学界对唐代出现的《文选》热现象颇为关注,多有论文探究其成因。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对宋代“文选学”的研究却关注较少,有影响的论文也不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1]章学诚:《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从学术发展的方面说,这是需要补齐的一环。本论文拟以宋代“文选学”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文选》研究在宋代衰落的诸多原因,借以把握宋代文学的发展变化,以就教于方家。
二、《文选》在唐代受到热捧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包括诗、赋等37类各种文体且侧重于骈文的文学总集。由于在它之前的杜预《善文》、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刘义庆《集林》诸书均已亡佚,所以《文选》在保存我国早期文学创作文献方面有着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价值,是我国古代有重大影响的文学选本。人们对于《文选》的关注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在其问世后仅五十年,便有学者萧该著《文选音》以研究《文选》,惜其书已亡佚。继之,隋、唐之间的曹宪亦专力《文选》研究,作《文选音义》,并始见“文选学”之专名。据《旧唐书·曹宪传》载,曹宪不仅自己撰著《文选音义》,且以其所学授弟子,培养出了像许淹、李善、公孙罗、魏模这样的著名学者,其中尤以李善为翘楚。
唐高宗时期的李善,扬州江都人,学贯古今,博闻强记,然不善治文,时人因此称他为“书簏”。他善讲《文选》,远近之人咸奔投其门下受业,号“文选学”。高宗显庆三年(658年),李善进呈《文选注》六十卷,为时人所称道。《文选》之所以能在后世风行,成为显学,“李善注”可谓最为有力焉。李善的注释引证赅博、体例谨严,征引诸书近1700种,在语源和典故的注释方面特别详尽,但是他比较忽视文义的疏通,这是其注释的不足之处。这个问题在后来的“五臣注”中得到了解决。所谓“五臣注”,指的是玄宗开元年间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对《文选》一书的合注。《四库全书总目》这样评价“五臣注”:“然其疏通文义,亦间有可采。唐人著述,传世已稀,固不必竟废之也。”[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86页。可以说,这是比较公允的见解。换言之,“五臣注”弥补了“李善注”重典故解释而轻文义串讲的缺憾,有其存在的价值。因此,南宋以来,人们往往将两种注合璧刊行,称为《六臣注文选》。
除了学者的专门研究,实际上,一般文士对《文选》也钟爱有加。《文选》在社会上的普及率、地位及价值,皆远超当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代表的儒家五经。杜甫在儿子宗武过生日时写诗嘱咐他要“精熟《文选》理,休觅彩衣轻”[2]杜甫:《宗武生日》,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十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78页。,又在《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诗中描绘“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3]杜甫:《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十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48页。的美妙情景。唐代文士之重视《文选》,由此可见一斑。之所以产生如此盛况,一要归因于唐人雅好文学,二要归因于唐代的诗赋取士。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4]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唐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是建立在对南朝文学、北朝文学继承基础上的融合、革新与创造。在诗的方面,宫体诗在初唐时期仍大行其道,上官仪、李峤、崔融、沈佺期、宋之问诸人继续写着绮艳轻靡的诗歌,唐太宗对宫体诗也有所偏好;源自南朝沈约“四声八病”的格律诗此时得到规范并被发扬光大。在文的方面,唐人延续了南朝骈体文的作文风格,讲究辞藻、声律、对偶、用典,从初盛唐直至晚唐。
《文选》正是一部体现了南朝文学观念的文学总集。首先,萧统认为文艺发展的规律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5]萧统著、李善注:《文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第3页。,即认为文艺创作越到后来越会具有文艺的特质和美感,特别是追求形式上的极致发展。这实际上是对南朝文风的理论肯定。其次,萧统严格区分文学与非文学两类创作,并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6]萧统著、李善注:《文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第3页。为选文标准编纂《文选》。最后,尽管萧统要求文学创作须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7]萧纲:《答湘东王书》,道宣编:《广弘明集》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页。,持一种中道、平衡的创作理念,但从《文选》选文以及他的一些表述可以看出,他是比较喜欢和认同“飞文染翰”的南朝文学的。
南朝文学、唐代文学、《文选》三者之间的一些契合,是唐人热爱《文选》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超功利的文学阅读。而唐代《文选》之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实用性的利益驱动:《文选》所裒辑的都是中国历代诗赋文章的精粹,对科举考试很有用处。唐代以诗赋取士,文士们都竭尽全力学习、掌握诗赋文章的写作技艺,以期在科举考场上一较高下,争一个大好的锦绣前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1]孟郊著,华忱之、喻学才校注:《孟郊诗集校注》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诗赋文章既重要如此,有谁不在《文选》的学习上尽心尽力呢?
三、“文选学”在宋代的转向
宋承唐制。大唐国力的繁盛为宋人艳羡和称道,他们在若干典章制度上都学步唐人,继承因袭。如在唐代风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到了宋代不仅得到了继承,而且更加发扬光大。宋代科举考试的规模扩大了,科举考试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增强了。随之,人们阅读《文选》的热情也得到了延续,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鉴于唐五代社会发生的大规模战争与混乱,宋代统治者对唐代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采取重文轻武国策、提高儒学地位、加强封建专制集权的制度建设等。这些改革从整体环境和氛围上改变了《文选》研究与传播的态势。虽然说在北宋最初的几十年里,宋人沿袭了唐代对《文选》的阅读和研究路数,但和唐代相比,“文选学”在宋代却出现了两个较明显的变化:其一,有关《文选》的学术性研究趋于碎片化,多散见于诸种笔记、诗话中,像李善注、五臣注这样整全的、系统的、认真的研究成果再也没有出现过,取而代之的是《文选双字类要》《文选类林》等专事辞语典故之摘录排比的著作大行其道;其二,由于有李善注和五臣注的加持,《文选》在唐代可谓有学有用,学用结合,而宋人初时对于《文选》虽热情不减,却似乎更倾向于它的应用,更注重《文选》的工具性。这两个变化表明,人们从研究视角所认知的《文选》,亦即所谓“文选学”,到了宋代开始慢慢趋向衰落了。
宋代“文选学”趋于衰落的现象前人已有言之。南宋王应麟等学者在《困学纪闻》卷十七“评文”有言:“李善精于《文选》,为注解,因以讲授,谓之‘文选学’。少陵有诗云:‘续儿诵《文选》’。又训其子熟精《文选》理,盖选学自成一家。江南进士试《天鸡弄和风诗》,以《尔雅》天鸡有二,问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选》烂,秀才半。熙丰之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矣’。”[2]王应麟、翁元圻、乐保群等:《困学纪闻》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这段话透露了几个信息:①所谓“文选学”侧重对《文选》的研究。李善注解《文选》是“文选学”出名之始,熟精《文选》之“理”是“文选学”作为“自成一家”的专门之学所应有的旨趣。②人们热情追捧《文选》,既是由于科举考试的刺激,也是出于写诗作文的需要。“秀才半”的秀才不是指科举考试的科目或等级,而是指善于读书作诗文者。③宋神宗熙宁、元丰以后,士子们不通《文选》之理而穿凿谈经,虽则《文选》还流布人间,所谓“文选学”却“废矣”。《困学纪闻》中还有几则涉及《文选》的评语可以表明,带有研读、研究性质的所谓“文选学”在唐代很兴盛,到了宋代却转向衰落了。但他只是指出了转衰的现象和转衰的时间点(“熙、丰之后”),却没有揭示原因。
四、《文选》受宋代科举考试改革影响
唐宋两代的进士科都有策论考试,“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选举志上》卷四十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63页。。所谓试策,就是写一篇切于时用的论述文,主要针对时事有感而发,如唐人论藩镇、宋人论开边等。试策的目的是要发现明事理、通实务的实用型人才,为国家政治、政府管理服务。这本是设置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试策也差不多是科举考试中最稳定的考试科目。但在唐宋两代文士的心目中,试策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大体说来,唐代文士看重诗赋,宋代文士喜爱策论;诗赋展现文学才情,策论展现政治眼光和胸襟。一个极端的情况是王安石对科举考试内容的改革:他干脆取消了进士科的诗赋考试。
宋代文士之所以偏好科举策论,乃是出于王朝内外政治形势的紧张促迫。内政上机构臃肿、财政困难、党争激烈、官民对立,外交上则因守内虚外、轻武积弱的政治而频受外族的侵凌和挤压。严峻的现实环境迫使文士们放弃悠游浪漫的诗情,转向经世致用之学。王禹偁以“小畜”名其集,示其“兼济天下”之志;范仲淹、欧阳修强调文章必须反映现实、揭露时弊,具有批判性;苏轼也要求文章须“有补于国”……文士们的家国情怀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文选》显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文选》所录为诗赋骈文之作,诗赋部分既已为宋代文士所轻,而骈文部分乃抒情美文和应用性杂文,其中题为论的作品十三篇,题为史论的作品九篇,数量较少,参考价值不大。类似于科举策论的则一篇也没有。“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今之所集,亦所不取。”[1]萧统著、李善注:《文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萧统明确拒收类似于科举策论的作品,这让《文选》在热衷科举策论的宋代文士那里失去了市场。
宋代科举考试在考试形式、程序上所做的改革,也导致了“文选学”在宋代的衰落。唐代科举考试不封卷,成绩之甲乙多在事先拟定,行卷、温卷、请托风盛行,朝廷也要求考生纳省卷,以作为评定成绩的参考。宋代统治者为了考试的公平起见,采取糊名封卷以及其他一些形式和程序上的改革措施。这一改革本意在革除唐代科举之弊,却意外地促成文风的变化。
简言之,唐代文士面临的学科知识学习的直接考试压力比较小,所以他们往往把精力放在创作才情的发挥和文学修养的培养上,而不屑于知识饾饤;与此相关联的,玄宗时五臣注《文选》,不求训诂精确、释事翔实,亦不多征引文献,而以疏通文义为主,简注详疏,通俗浅近,具有普及意义。宋代文士则不然。每一次考什么他们不知道,每一次考试都生死攸关,而对付考试的有效办法,除了夹带小抄之外,便是考前对知识材料的死记硬背。知识材料掌握得越丰富,则撞上考题的概率越大,考试成功的机会也就越高。落实到《文选》研究上,人们便专事辞语、典故等分类知识的摘录与排比了。掌握《文选》里的辞语和典故,能给人学问渊博的感觉(不一定能转化为创作能力),对应付考试还是有帮助的。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2]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0页。此则记载一是描述了北宋前期在《文选》阅读方面专重辞藻典故的风气,二是说明南宋以来,苏轼的文章取代《文选》,成为文士们新的争相追捧的对象。这两种情况之所以出现,都和宋代科举考试的改革有着莫大的关系。
五、苏轼文章取代《文选》
苏轼的文章之所以取代《文选》,除了科举考试的原因外,还有文学革新运动的影响。文学革新运动发端于中唐。唐人爱《文选》,其文章创作亦走着《文选》选文的路线,以骈体文创作为主。初唐的四杰、盛唐的燕许大手笔、晚唐的小李杜皆骈体文名家。骈体文辞藻华丽、韵律铿锵、形式优美,是其优点,但它“文过其意”,不“便于时用”[3]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30页。,也是不争的事实。早在隋唐之际,人们已发现这个问题,到了中唐,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中唐时期,安史之乱动摇国本,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随之而来的藩镇割据局面又导致朝廷权威下降,社会四分五裂。严峻的政治现实催生了韩愈、柳宗元主导的古文运动。韩柳古文以单行散句的文字取代骈体文,于论说事理颇为便当;加之韩柳以古文倡儒学、斥佛老、续道统,“辅时及物”[1]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24页。,“回狂澜于既倒”[2]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排捣鼓荡,激浊扬清,一时间成就斐然,声势浩大,可惜很快退潮。晚唐五代宋初,南朝文风回归,文坛恢复了旧观。
欧阳修承接韩愈倡儒学、兴古文之志,利用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知贡举的机会,打击“太学体”,倡写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的古文。与此同时,欧阳修又把文学革新运动扩展到诗歌领域,反对当时诗歌创作中或率易或险怪或艰涩的不良风气,提倡平易自然的风格。和韩愈一样,欧阳修既提出了文学革新的理论主张,又身体力行,取得很好的创作实绩,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佳作。和韩愈不同的是,欧阳修善于发现人才,奖掖后学,发现了一批青年才俊以继续推进文学革新事业。尤其是苏轼的横空出世,更是令他又惊又喜。“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3]欧阳修:《与梅圣俞书》,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九,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59页。“我老将休,付子斯文。”[4]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56页。其爱才惜才之心,千百载之下,仍令人动容。
毋庸置疑,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之所以能获得最终的全面胜利,苏轼之功可谓最大。苏轼以天纵之才投身文学事业,诗词文赋各体皆工,创作出有如行云流水般的作品;又不负欧阳修的重托,完成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新运动。苏轼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对于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远远超出了樊宗师与韩愈的弟子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苏轼的有力参与和领导,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很有可能会重复中唐古文运动的命运。
苏轼彻底改变了宋代的文风。“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时谚透露了此一讯息。北宋后期特别是南宋以来,苏文受到了热捧。虽然有元祐之禁,但热度不减,身价反高。“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5]朱弁:《曲洧旧闻》卷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六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39页。苏轼之影响可见一斑。
经过唐宋两代文学革新运动洗礼的苏轼,其创作面貌已与《文选》选文截然不同。在作品题材选择上,苏轼写作散体文、文赋及自然雅洁的诗词,而不是《文选》所中意的那些诗赋骈文;在写作风格上,他推崇自然平淡的文风,重视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丰富充实的内容,反对争奇斗巧、空洞无物的创作。苏轼在各体文学创作上皆有极高的天分和造诣,又能融会贯通,创造宏大气象,将宋代文学创作推向了新高度。苏轼一生大起大落,几经沉浮,创立出一种入世而又超世的人生智慧,达到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6]苏轼:《自题金山画像》,苏轼著、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四十八,中华书局1982版,第2641页。逆境之中他没有消极,没有沉沦,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令人感佩的是,他到老都不忘初心,视文学创作为毕生事业,黄、惠、儋三地是他人生最沦落处,也是他文学创作最大放异彩处,被他看作是“平生功业”之所在。
苏轼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南宋以来的许多文人士子,而他的文学创作更是风靡了文学界,成为现成的新的规范。他之后的作家们不必舍近求远地去学习数百年前的已然和时代文学思想文学趣味不合拍的《文选》了。《文选》所收文章多数是形式大于内容的赋与骈文。比如骈文,作家写作的着力点放在骈四俪六、排偶声律、典故藻采等形式方面,而对于所要表达的内容却不甚用心,从而导致很多骈体文作品内容贫乏、文风纤弱、形式绮靡。借用刘勰对《文赋》的批评,这样的创作“巧而碎乱”,“然汎论纤悉,而实体未该”[1]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卷十《序志第五十》、卷九《总术第四十四》,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10、529页。。它们不仅不能文从字顺,而且不能“有补于国”[2]苏轼:《栾城集墓志铭》,苏轼著、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附录一,中华书局1982版,第2806页。,适时适意地反映民生疾苦和国家危难,表现作家士人们忧国忧民的情怀。《文选》最终为苏文所取代,乃是大势所趋,并不奇怪。
六、“文选学”衰落的其他因素
一是《文苑英华》的编集。《文苑英华》紧接在《文选》之后,编纂历代文学作品,上起萧梁,下迄唐五代,且编纂体例和《文选》大致相同,向来被看作是《文选》的续集。由于《文苑英华》在编纂时有政治上的考量[3]刘壎《隐居通议》卷十三:“宋初编《文苑英华》之类,尤不足采。或谓当时削平诸僭,其降臣聚朝,多怀旧者;虑其或有异志,故皆位之馆阁,厚其爵禄,使编纂群书……迟其岁月,困其心志,于是诸国之臣俱老死文字间。世以为深得老英雄法,推为长策。”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六六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22页。,并不像《文选》那样完全出于推动文学进步的目的,故其编纂质量并不尽如人意,未能取得如《文选》一般的成就和关注度。《文苑英华》的编纂者往往随手掇拾、草率从事,致使集中的脱漏、错讹、重复、割裂、颠倒之处所在皆是;加之卷帙浩繁、编次杂乱,翻检阅读颇为不便。宋代曾数度诏命校订《文苑英华》,至南宋宁宗朝,经由学者周必大、彭叔夏之手,方毕其事。
尽管在编纂质量上有欠缺,但对于宋人来说,《文苑英华》却比《文选》多了一个优势,那就是方便他们学习唐代文学。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唐文(骈文和散文),形成了我国古典文学创作的新的典范和高峰。大小李杜、王孟元白、韩柳……是文学创作天空中不朽的璀璨的巨星,《滕王阁序》《阿房宫赋》《蜀道难》《长恨歌》及“永州八记”等,是脍炙人口传之久远的名篇佳作。宋人明乎此,在宋初便竞相学唐,成为风尚。且不论白体、晚唐体、西昆体、江西诗派、四灵诗派、江湖诗派等公开标榜学习唐诗,即如欧阳修所发动的诗文革新运动,究其实,也是向唐代文学学习的结果。只是,宋人在学唐的时候走出了自己的新路。学习唐代文学须有读本。在这方面《文选》完全帮不上忙,而《文苑英华》则成为现成的阅读材料。《文苑英华》虽号称选录历代之文,实际上所收主要是唐代作品,篇数竟占到全书的十分之九。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文苑英华》是一部唐代作品总集,似乎也不算太过。在当时,还没有比《文苑英华》更合适更方便的唐代文学读本。宋代皇帝数度诏修它,正好说明了社会对《文苑英华》的急迫需要,也反映了它与《文选》在社会需求度上的此长彼消。
二是理学的兴起。理学是宋代思想学术的重心,影响及于社会生活各方面,并和佛教、道教思想相融合,促成整个社会心态的内向化。理学兴起对于文学的影响表现在:第一,宋人爱在创作中发议论,文赋如此,诗歌亦如此。陆九渊说:“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议论远过之。”[4]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尝闻王顺伯云:‘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议论远过之。’此议论甚阔,可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6页。严羽也说:“(宋人)以议论为诗。”[5]严羽:《沧浪诗话》,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第九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720页。严羽并指出,宋诗之所以好“议论”,乃是因为“穷理”所致,落入了“理路”。第二,宋代的诗文创作有崇理尚意的特点。理学家以诗论理自不必说,就是一般的诗人,也喜欢在诗歌中表现理趣与哲意。跟唐诗相对照,这一点很突出。比如同样是写庐山的绝句,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展示了庐山壮丽的景观,而苏轼的《题西林壁》则意在阐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思。在文章创作上,宋人往往能够从寻常题材中提炼出重大主题,“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6]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卷八十四,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010页。。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引发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情;欧阳修建丰乐亭,提炼出了“宣上恩德,以与民同乐”的主题;王安石游山时见石碑上字迹漫漶,便生出“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的联想……第三,宋人作诗讲“法度”,讲“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作文讲结构章法、脉络肌理,这与唐人作诗作文的风气不同。比如韩愈教人作文,只说要广泛阅读、悉心揣摩、长期坚持,或称“惟陈言之务去”[1]韩愈:《答李翊书》,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页。,或称“师其意不师其辞”[2]韩愈:《答刘正夫书》,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07页。,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写作方法和技巧。宋人的这种风气和理学家的“穷理”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所谓的法度章法之类,就是诗人、作家们“穷”出的写作之“理”。
理学影响下的宋人创作与《文选》形成对比,比如宋人的崇理尚意之风气就明显不同于萧统的选文理念。萧统声称他编纂的《文选》不收录“老庄之作、管孟之流”,其理由是老庄、管孟的创作“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3]萧统著、李善注:《文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萧统的意思是,文学就是文学,应该追求文字之工、辞章之美,即需要追求辞藻、对偶、用典、声律等形式要素,而不应只着意于作品的思想意义。南朝是一个儒学衰微、文风骀荡的时代。梁简文帝萧纲倡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且须谨慎,作文且须放荡。”[4]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梁文纪》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三九九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77页。梁元帝萧绎亦称赏“绮縠纷披,宫徴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揺荡”的创作[5]萧绎:《金楼子·立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四八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853页。。萧统的文学理念虽然和萧纲、萧绎有差异,却也认为文学的发展是一个由质朴不断走向华美的过程,踵事增华,变本加厉,所以《文选》编收的都是“名溢缥囊”“飞文染翰”的作品。南朝儒学衰微,宋代理学兴起;南朝文学弃质尚丽,宋代文学崇理尚意;南朝文学“飞文染翰”,宋代文学议论横行。如此看来,《文选》之不受宋人待见,实良有以也。
三是创作心态的变化。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宋代的社会文化环境较之唐代有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导致作家们整体创作心态的变化。大体说来,唐人写诗作文比较豪迈奔放、发扬蹈厉,其情感的表达是热烈外向、不可遏止的,而宋人则转向了平和、保守、内敛。这一变化正好和《文选》在唐宋两代间的由热趋冷现象相一致。古语说,汉有汉风,唐有唐韵。汉唐文学有着其他时代文学所无可比拟的阔大气象与风调情韵。早在初唐时期,就有四杰横空出世,一扫南朝文学的绮靡文风;又有陈子昂倡言“兴寄”和“风骨”,“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炼,有金石声”[6]陈子昂著、徐鹏校:《陈子昂集·修竹篇并序》,中华书局出版社1960年版,第15页。,吹响了盛唐之音即将到来的号角。由于疆土辽阔,国力强盛,盛唐诗人们在其诗歌中竭力张扬功名心、进取心,表现自信和豪情。他们的诗作充满着情感的张力以及勃勃的生命力。“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即使到了国势转衰的中唐,仍然有韩愈、白居易等诗人在高歌着时代的最强音。
但是到了宋朝,激情与自信渐渐消减,很多诗人开始退出社会,躲进书卷中写诗。他们学习白居易、贾岛、李商隐、韩愈、杜甫,“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7]黄庭坚:《答洪驹父书》,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九,嘉兴沈氏藏宋刊本,四部丛刊第990册,第92页。。他们在书中摭拾典故,他们用心炼字炼意,他们探求作诗的法度……紫徽公《夏均父集序》云:“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而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8]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上海涵芬楼藏赐砚堂钞本,四部丛刊第一三一一册,第147页。直到陆游方才醒悟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是一种内向化的创作方法。他们的诗作中没有充盈于唐诗中的那种神采飞扬。
苏洵曾这样描述欧阳修的写作风格:“执事之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1]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纡徐委备”“容与闲易”是对欧阳修写作风格之贴切的描述,观《醉翁亭记》等作品便能体会到这一点,其不同于有如“长江大河”的韩愈文章明矣。其实,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动者和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写作风格是宋代文坛的主导性风格。也就是说,宋代作家整体上都取一种冷静平和、舒缓理性的创作态度,是一种内敛、保守的创作心态。赵宋王朝偃武修文,优待文士,作家们于是就有了一个安逸、舒适的创作环境,也由此塑就了淡泊恬静的审美趣味。苏轼有诗云:“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2]苏轼:《送参寥师》,苏轼著、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十七,中华书局1982版,第906页。苏轼亦称赏“枯澹”的诗风:“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3]苏轼:《评韩柳诗》,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10页。
正是在这样的创作心态和审美趣味之下,陶渊明被宋人“发现”。陶渊明是东晋诗人,却不受南朝人待见,也不受唐朝人待见。刘勰《文心雕龙》未提及陶渊明;钟嵘《诗品》仅将陶渊明列为中品;萧统虽然编过《陶渊明集》,对他多有肯定,但《文选》中却没有收陶渊明的散文;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杜甫称赏“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仅将陶作为一位隐逸诗人。对此,钟嵘《诗品》的解释是:“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词兴婉惬。……世叹其质直。”[4]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0页。这一解释可谓切中肯綮,也就是说,陶渊明的诗风不合乎以《文选》为代表的南朝及之后唐朝人的口味。然而,唐宋异趣,唐人热捧的《文选》被宋人冷落了,而一向被冷落的陶渊明却受到宋人的欢迎。以苏轼为例,他写有大量的效陶和陶诗,同时整体上否定《文选》:“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引》斯可见矣。”[5]苏轼:《题文选》,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93页。又说:“梁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6]苏轼:《答刘沔都曹书》,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四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29页。《文选》与陶渊明在宋代的冷热消长,反映了宋人创作心态和审美趣味的变化,也表明了“文选学”在宋朝衰落与宋人创作心态变化之间的相关性。
七、结语
萧统《文选》自其问世以来,经历了一个由热到冷的接受过程,唐时热,宋以后趋冷,直至清代。当然,所谓的冷和热乃是相对而言,人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抛弃《文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选学妖孽”还是和“桐城谬种”并列,被时人视作革命的对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唐人热捧《文选》的盛况此后未能复现。无论是受热捧还是受冷落,皆是不同的时代使然,而和《文选》的文本本身无关。萧统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此后的风云变幻、潮起潮落无疑皆操控于时代之手。“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7]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时序第四十五》,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42页。,文学读本的兴衰也是如此。透过“文选学”在宋朝衰落这一现象,我们感受到了宋代文化环境和文学审美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