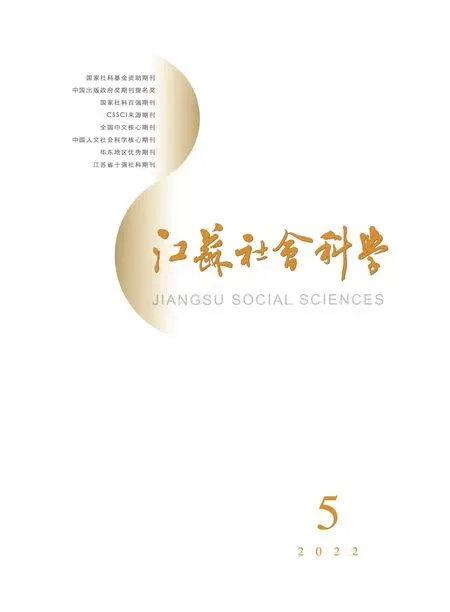以夷制夷理论与两汉王朝的践行
晋文
内容提要 从宏观理论来看,战国以来的与时俱进理论可视为以夷制夷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渊源。所谓胡服骑射也完全符合“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意味着胡人的骑射战术在军事上确有长处。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尤其匈奴的反复侵扰,使得以夷制夷的理论形态应运而生。从西汉晁错的最早论述来看,其内容主要有“因俗而治”和“师夷长技以制夷”。除“因俗而治”外,两汉以夷制夷的践行,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西汉前期对骑兵大军团的组建和西汉中后期对大量少数民族军队的使用。相对来说,东汉以夷制夷的践行更加普遍和高明。两汉以夷制夷的践行对民族与边疆地区的治理发挥了重大作用,不仅维护了大一统帝国的稳定,而且促进了许多少数民族或部族的汉化,但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局限。
所谓以夷制夷,就是要对大部分“夷狄”或“蛮夷”实行间接统治,让他们能自己管理自己,并利用其内部矛盾去制服与中原王朝为敌的“夷狄”或“蛮夷”。这种思路旨在用少数民族或部族来治理少数民族或部族,或者用少数民族和部族的方法来战胜少数民族和部族。前者多具有归顺秦汉等中原王朝统治的自治性质,亦即“因俗而治”[1]卜宪群、袁宝龙:《“因俗而治”展现秦汉治边智慧》,《历史评论》2022年第1期。,也带有让不同少数民族和不同部族相互制约的意味;后者则承认非汉民族比汉族确有某些长处,实际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较早表述。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2]相关成果主要有李干芬:《略论历代封建王朝的“以夷制夷”政策》,《广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黄今言:《两汉边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上官绪智:《“以夷制夷”策略在两汉时期的发展及其缘由》,《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上官绪智:《两汉政权“以夷制夷”策略运用的主要方式和特点》,《南都学坛》2006年第6期;熊贵平:《以夷制夷方略及其在汉代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探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朱尖:《西汉末至新莽时期边疆政策的嬗变与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本文拟就以夷制夷理论与两汉王朝的践行问题再做一些探讨。
一、以夷制夷的理论渊源
从总体上说,华夏文化的原典都是鄙夷“蛮夷戎狄”的。如《尚书·舜典》:“蛮夷猾夏,寇贼奸宄。”[1]孔颖达等:《尚书正义》卷3《虞书·舜典》,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0页。《诗经·宫》:“戎狄是膺,荆舒是惩。”[2]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22《鲁颂·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7页。所谓“《书》戒‘蛮夷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为患也”[3]《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赞》,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30页。。但随着华夷之间的战争与交往越来越多,至战国时期关于以夷制夷的设想及其践行便逐渐开始产生。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据《史记·赵世家》记载,为了增强赵国的军事力量,赵武灵王下令全国向胡人学习,都穿短小紧身的胡服,并训练骑马和射箭,使赵国在短时期内成为令人瞩目的强国。值得注意的是,赵武灵王曾特别阐发了胡服骑射的必要性。例如:
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
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虙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4]《史记》卷43《赵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08—1809、1810页。
从中可以看出,赵武灵王论证胡服骑射的主要依据就是与时俱进理论。尽管他的古今观并没有一句提到以夷制夷,但“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和“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的表述,却为以夷制夷等各种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因此,从宏观理论来看,战国以来的与时俱进理论可视为以夷制夷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渊源[5]晋文:《汉代的古今观及其理论的构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此外,赵武灵王主张胡服骑射,还意味着胡人的骑射战术在军事上确有长处,而绝非公子成等人所说,都比不上华夏文明。这也完全符合《诗经》中的“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古训[6]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1《小雅·鹤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3页。。从这个方面来说,胡服骑射即成为华夏民族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的渊薮,并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成功范例为后世所继承。
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尤其匈奴的反复侵扰,使得以夷制夷的理论形态应运而生。从相关记载来看,类似以夷制夷的表述最早出自西汉晁错。他在给文帝的上书中说:“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晁错同时提出了以夷制夷的具体建议:
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即归义)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7]《汉书》卷49《晁错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81、2282—2283页。
从而第一次明确阐释了以夷制夷的理论,成为两汉王朝治理民族与边疆地区的利器。具体来说,以夷制夷理论又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是倡导“因俗而治”。从内容来看,这与秦汉王朝的远近有别政策有很多重叠交叉之处[1]晋文:《也谈秦代的工商业政策》,《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所不同者,因俗而治更强调以夷制夷的具体做法,而远近有别则重在宏观理论上的认识。以属国为例,史载匈奴浑邪王归降,武帝“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2]《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34页。。这里的“因其故俗”,就是保留匈奴原有的社会组织,让投诚汉王朝的匈奴人自己来管理自己。尽管朝廷在属国中也设置了一些官吏参与管理,如《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所说,“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复增属国,置都尉、丞、候、千人。属官,九译令”[3]《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5页。,但属国里的匈奴人基本都实行自治,并被给予很多优待,这是毋庸置疑的。名臣汲黯就曾对这种做法强烈批评说:
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4]《史记》卷120《汲郑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09页。
属国如此,更不用说还有许多没有设置属国的少数民族或部族了[5]黎明钊、唐俊峰:《秦至西汉属国的职官制度与安置模式》,《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如史载“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6]《史记》卷30《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40页。关于西汉初郡的性质问题,参见黄纯艳、潘先林:《古代民族关系史的“西南类型”——基于〈西南古代民族关系史稿〉的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6期。云云。又如:“滇王离西夷,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7]《汉书》卷95《西南夷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42页。
二是强调取长补短。这一主张可概括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也等于公开承认“蛮夷戎狄”在某些方面确有长处。由于时代的局限,秦朝君臣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在秦军当中也有数量不少的“蛮夷戎狄”兵[8]史党社:《“属邦”发微》,《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但西汉建立后,由于汉军的白登之围,汉朝君臣对这一问题有了充分认识。司马迁描述白登之围和匈奴骑兵的强大时说: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9]《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4页。
韩安国所说,“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10]《史记》卷108《韩长孺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61页。,也表明匈奴的骑兵优势是一个客观事实。因此,如何抵消匈奴的军事优势便成为汉朝君臣重点考虑的问题。其中晁错的思路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汉朝在综合国力上远远超过匈奴,军队的数量和潜力也远远大于匈奴,但骑射是匈奴最大的军事优势。而短时期内即可抵消其骑射优势的方法,就是让归义的匈奴人和其他游牧民(部)族同匈奴骑兵作战。因为这些“归义蛮夷”也同样有骑射的“长技”,而且以夷制夷还可以达到“不烦华夏之兵,使其同类自相攻击”[11]《汉书》卷49《晁错传》注引师古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81页。的效果,所以他才从战略高度最早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主张。这不仅在理论上阐明了以夷制夷的必要性,而且使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设想成为西汉王朝的共识,对取长补短、勇于和乐于学习非汉民族的“长技”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为西汉以后历代王朝所继承,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12]李干芬:《略论历代封建王朝的“以夷制夷”政策》,《广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当然,以夷制夷的设想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以夷制夷投入巨大,在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往往会中断或消解。以夷制夷的设想实际是建立在强盛的大一统王朝的基础上的,无论是“因俗而治”,还是“以蛮夷攻蛮夷”,抑或其他,都离不开强大国力的支撑和充裕财政的保证[1]晋文:《秦汉经济制度与大一统国家治理》,《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而一旦出现大的内乱或王朝更替的情形,其国力衰落、财政匮乏,这种以夷制夷的运行就会被严重破坏。尽管作为战术,以夷制夷仍然发挥着作用,但作为国家战略却可以说被完全瓦解。许多“蛮夷”不是脱离了秦汉王朝,就是纷纷自立,甚至对两汉王朝采取敌对政策。以秦亡汉兴为例,秦始皇南平百越,北击匈奴,使秦朝的疆域极大拓展,而西汉建立后,其疆域却大为缩小,瓯越、闽越、南越和西南夷都成为独立或半独立地区。这就使得秦朝以夷制夷的成果大多化为泡影。其次,也是两汉王朝始料未及的,以夷制夷带来了一些严重隐患。以夷制夷的本意是师夷长技让少数民族或部族自相攻击,从而达到制服与汉王朝敌对的少数民族和部族的目的。但在实施的过程中,被用来以夷制夷的少数民族或部族也逐渐学会了这种策略,反过来以夷制夏。他们大多借着汉王朝的扶持,在打击与汉王朝为敌的少数民(部)族的同时,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把自己当成了与汉王朝讨价还价的筹码,甚至成为使汉王朝感到忧虑的地方割据势力。以东汉为例,从光武帝开始,对南北匈奴便采取分化政策,让南匈奴和汉军一起抵御北匈奴,并让乌桓也一起打击北匈奴和鲜卑,同时监督南匈奴。如《后汉书·乌桓传》载,光武封乌桓“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复置护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2]《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82页。。但在北匈奴被制服后,乌桓、鲜卑却逐渐成为北方边境的大患,南匈奴亦多次反叛。这不能不说是以夷制夷的一个严重后果。
二、两汉以夷制夷的践行
除了“因俗而治”的诸多记载外,西汉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以夷制夷的事例,莫过于西汉前期对骑兵大军团的组建和武帝及武帝以后对大量少数民族军队的使用。
如前所述,西汉自高祖平城战败后,其朝野上下便意识到骑兵大军团的重要性。为了战胜匈奴强大的骑兵,汉朝必须学习匈奴的骑射长技,以汉朝的骑兵大军团来对抗匈奴的骑兵大军团。而组建骑兵大军团,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首先要做的就是养马,因而马政也成为西汉王朝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一个关键。从张家山汉简来看,汉初马政涉及养马、用马和马的买卖等方面,比如《津关令》规定:
禁民毋得私买马以出扜〈扞〉关、郧关、函谷【关】、武关及诸河塞津关。其买骑、轻车马、吏乘、置传马者,县各以所买名匹数告买所内史、郡守,内史、郡守各以马所补名为久久马,为致告津关,津关谨以藉(籍)、久案阅,出。诸乘私马入而复以出,若出而当复入者,出,它如律令。御史以闻,请许,及诸乘私马出,马当复入而死亡,自言在县官,县官诊及狱讯审死亡皆津关,制曰:可。(506—508)[3]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85—86页。
尽管其中养马的律令多为对官营马场的规定,而用马的规定又多有限制诸侯王国的意图[4]龚留柱:《论张家山汉简〈津关令〉之“禁马出关”——兼与陈伟先生商榷》,《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臧知非:《张家山汉简所见汉初马政及相关问题》,《史林》2004年第6期。,但汉初就开始重视马政却毋庸置疑。证诸传世文献,我们也可以想起晁错的名言——“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5]《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3页。。从文中“今”字来看,“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的措施是已经实行的马政,晁错也未说此政的创立与文帝有关,可见其渊源应当更早。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汉初君臣对马政的重视[1]陈直:《汉代的马政》,《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随着马匹的逐渐增多,汉朝对骑兵大军团的组建也初见成效。史载文帝三年(前177年),“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婴将骑八万五千往击匈奴”[2]《史记》卷95《樊郦滕灌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73页,第2668、2669—2670页,第2668页。。至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3]《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1页。,汉军骑兵已多达十余万人。经过前后六七十年的发展,到了武帝前期,汉朝对骑兵大军团的组建成效斐然,主要有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两大骑兵军团。史载汉匈数次大战后,“汉马死者十余万匹”[4]《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71页。,由此便可见一斑。汉朝骑兵大军团的组建,对汉武帝“威服”匈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简要记录了卫青和霍去病两大军团的战功:
最大将军青,凡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一与单于战,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万一千八百户。封三子为侯,侯千三百户。并之,万五千七百户。其校尉裨将以从大将军侯者九人。其裨将及校尉已为将者十四人。
最骠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捕首虏十一万余级。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万五千一百户。其校吏有功为侯者凡六人,而后为将军二人。[5]《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41、2945页。
这不仅实现了西汉王朝要战胜匈奴的夙愿[6]晋文:《两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诉求》,《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8期。,也完全体现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效果。
关于“蛮夷”兵或“戎狄”兵的使用,在秦及汉初就曾有一些记载。比如楚汉之争,在楚军和汉军中都有所谓“楼烦”骑的存在。《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载:灌婴“击破柘公王武,军于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卒斩龙且,生得右司马、连尹各一人,楼烦将十人”;“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虏骑将八人”[7]《史记》卷95《樊郦滕灌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73页,第2668、2669—2670页,第2668页。。又《史记·项羽本纪》载:“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集解》引应劭注曰:“楼烦胡也。”[8]《史记》卷8《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329页。更重要的是,无论楚军骑兵,还是汉军骑兵,他们在组建时都曾吸纳了不少秦军的骑兵。所谓“楼烦”骑者,便应当有一部分来自秦军。这从楚汉骑兵的组建都可以得到印证。如“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9]《史记》卷95《樊郦滕灌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73页,第2668、2669—2670页,第2668页。。但必须注意的是,尽管在秦及汉初的战争中有一些少数民族官兵的参与,但那时的秦汉王朝没有从战略高度来看待以夷制夷问题。真正强调以夷制夷,把大量“蛮夷戎狄”兵用于对周边少数民(部)族的战争,还是从汉武帝时开始。
据《史记·南越列传》:“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10]《史记》卷113《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75页。在征讨南越国的汉军中便有“归义越侯”率领的水军和“夜郎兵”,这对于尽快攻灭南越国发挥了很大作用。又据《卫将军骠骑列传》,在霍去病统率的远征漠北的汉军中亦有大量的“荤粥之士”即匈奴兵。如武帝嘉奖令说:
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1]《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36页。
此后,这方面的记载便大量见诸史乘。比如:
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以兵临滇。[2]《汉书》卷95《西南夷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42页,第3843页。
贰师遣属国胡骑二千与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敌。[3]《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79页,第3785页。
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汉使多言其国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4]《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6页。
(武帝)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5]《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74页。
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犇命万余人击牂柯,大破之。[6]《汉书》卷95《西南夷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42页,第3843页。
(元凤四年)夏四月,诏曰:“度辽将军明友前以羌骑校尉将羌王侯君长以下击益州反虏,后复率击武都反氐,今破乌桓,斩虏获生,有功。其封明友为平陵侯。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县北阙,封义阳侯。”[7]《汉书》卷7《昭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0页。
本始二年,汉大发关东轻锐士,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皆从军。……校尉常惠使护发兵乌孙西域,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余骑从西方入,与五将军兵凡二十余万众。匈奴闻汉兵大出,老弱犇走,驱畜产远遁逃。[8]《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79页,第3785页。
至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黎,积谷,因发诸国兵攻破车师,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使人与吉相闻。吉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遂将诣京师。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9][10]《汉书》卷70《傅常郑甘陈段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05—3006页,第3010—3011页。
类似事例还有一些,都无可争辩地证明,西汉王朝的以夷制夷战略曾取得了巨大成功,尽管也有一些失败的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元帝时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兵对北匈奴郅支单于的诛灭。据《汉书·甘延寿传》和《陈汤传》载,陈汤与甘延寿商议击灭北匈奴,在是否上奏朝廷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甘延寿还有些犹豫,而陈汤则当机立断——
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之校,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10]
最终便击灭了北匈奴,并将郅支单于悬首“槀街蛮夷邸间”。其中不调中原一兵一卒,不费朝廷任何费用,即将与汉王朝长期为敌的北匈奴击灭,也更加凸显了以夷制夷的巨大威力。所以宗正刘向便据此为甘、陈二人论功说:
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廑(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鼓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余人。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
元帝的嘉奖诏书也曾特别指出了这一点,即“内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臧,因敌之粮以赡军用,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蛮,名显四海”[1]《汉书》卷70《陈汤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17—3018、3019—3020页。。这充分说明,对以夷制夷的作用和意义,西汉中后期的绝大多数君臣都有了深刻认识。
及至东汉,以夷制夷的做法更多,在形而上的观念层面也更加成熟和自觉[2]上官绪智:《“以夷制夷”策略在两汉时期的发展及其缘由》,《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以南北匈奴的分裂为例,五官中郎将耿国便向光武帝建议:“臣以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南匈奴)东扞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万世安宁之策也。”耿国的建议得到光武帝采纳。“由是乌桓、鲜卑保塞自守,北虏远遁,中国少事。”[3]《后汉书》卷19《耿国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16页。再以西域为例,班超为征服龟兹、焉耆,于建初三年(78年)向章帝建议:“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4]《后汉书》卷47《班超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76页。此建议也得到朝廷的认可,使西域不久平定。又如和帝继位,南匈奴意欲击灭北匈奴,大将耿秉也同样向窦太后提出:“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5]《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53页。最终在短短几年之内,汉军便联合南匈奴等将北匈奴击败,使其余部被迫西迁,从而彻底解决了长达200多年的匈奴侵扰问题。
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东汉建立后以夷制夷的践行会更加普遍,这固然是汲取了以往的成功经验,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东汉王朝已经从战略高度对以夷制夷有了充分认识。仍以匈奴为例,早在南北匈奴分裂时,将军臧宫和马武便依据以夷制夷向光武帝预言,东汉王朝对匈奴的“威服”已近在眼前——
(建武)二十七年,宫乃与杨虚侯马武上书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缘边被其毒痛,中国忧其抵突。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6]《后汉书》卷18《臧宫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95页。
尽管从全局考虑,光武帝最终拒绝了臧宫、马武的建议[7]晋文:《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发展与完善》,《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但以夷制夷和其他方面的准备,使东汉王朝对匈奴逐渐形成必胜的优势,亦即天时、地利、人和,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数十年后,北匈奴被汉军和南匈奴等联合击败,并被迫西迁,便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再如“章和二年,鲜卑击破北匈奴,而南单于乘此请兵北伐,因欲还归旧庭。时窦太后临朝,议欲从之”,尚书宋益也依据以夷制夷坚决反对让南匈奴迁回草原。其主要理由是:
自汉兴以来,征伐数矣,其所克获,曾不补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难,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来降,羁縻畜养,边人得生,劳役休息,于兹四十余年矣。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归功圣朝,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今北虏西遁,请求和亲,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扞,巍巍之业,无以过此。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诚不可许。[1]《后汉书》卷41《宋均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15—1416页,第1416页。
显而易见,宋益的考虑更加深远,主张让南北匈奴、鲜卑等互相制约,而汉朝即可以坐收更大的渔翁之利[2]上官绪智:《“以夷制夷”策略在两汉时期的发展及其缘由》,《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这的确是以夷制夷的高明做法,也更加体现了东汉王朝的长远利益,所以最终被窦太后采纳——“会南单于竟不北徙”[3]《后汉书》卷41《宋均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15—1416页,第1416页。。
三、以夷制夷的作用及局限
两汉以夷制夷的践行对民族与边疆地区的治理发挥了重大作用。其历史意义在于,两汉王朝已把以夷制夷作为民族与边疆地区治理的主要方法,以夷制夷不仅卓有成效,维护了大一统帝国的稳定,而且成为国家制度,促进了许多少数民族或部族的汉化,为汉民族的壮大补充了新鲜血液,也为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密切联系和友好交往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4]晋文:《汉民族的形成及其民族意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前揭汉武帝的“威服”匈奴和开疆拓土,汉宣帝时南匈奴的称臣,汉元帝时的“虽远必诛”,东汉和帝时北匈奴的被迫西迁,以及南匈奴在境内的长期定居,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另外,以夷制夷的大力践行也使汉朝的政治精英更加认识到少数民族的长处。为了取长补短,他们主张向各个少数民族学习,并利用他们的长技,从而更加丰富和发展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5]尹波涛:《略论西晋时期的“用夷”论与实践》,《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从西汉前期组建骑兵大军团开始,到西汉中后期“蛮夷戎狄”兵被大量使用,再到东汉时期以“蛮夷戎狄”兵为主,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由于“汉人”已不再是东汉军队中的主要构成,因而如何更好地招募少数民族官兵,也成为朝廷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后汉书·应劭传》载,为了平定“边乱”,在究竟应招募哪些胡兵的廷议中便出现了乌桓、鲜卑和羌胡的争辩。“于是诏百官大会朝堂,皆从劭议。”朝廷最后采纳了应劭的“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6]《后汉书》卷48《应劭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09—1610页。的建议。东汉以夷制夷的践行还推动了东汉兵制的变革。与西汉主要采用征兵制不同,东汉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募兵现象。而招募“蛮夷戎狄”兵的普遍,即为以夷制夷而大量使用“蛮夷”兵,或“羌胡”兵等[7]黄今言:《两汉边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就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如任延调任武威太守,“郡北当匈奴,南接种羌,民畏寇抄,多废田业。延到,选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赏罚,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据要害,其有警急,逆击追讨”[8]《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任延》,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63页。。遑论东汉时期史不绝书的“蛮夷”“秦胡”“羌胡”和“胡兵”“胡骑”的募兵记载了。
两汉王朝的以夷制夷也存在一些局限,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对以夷制夷出现了误解,认为以夷制夷就是让少数民族自相攻击,不需要中央王朝的引导和参与,有的时候便失去了有利于国家巩固和发展的机遇。比如“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蚡。蚡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覆,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1]《汉书》卷64上《严助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6页,第2777页。。幸亏在严助的提醒下,武帝才没有被田蚡所误导。此后“闽越复兴兵击南越”,武帝派兵讨伐,淮南王刘安又提出异议:“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其认为“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2]《汉书》卷64上《严助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6页,第2777页。。再如和帝时期,诸羌聚众四万余人,威逼为汉所用的小月氏胡,对护羌校尉邓训的大力保护,许多人亦认为不妥。“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护。”[3]《后汉书》卷16《邓训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09页。这在以夷制夷的践行中便往往会出现争议,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阻力。
二是歧视少数民族,在生活中和军队里都出现了很多压迫和虐待少数民族的现象。板楯蛮夷的反叛,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早在秦惠文王设置巴郡后,阆中巴人便已成为秦廷重用的弓箭手。楚汉之争时,板楯蛮夷被大量编入汉军。“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一直到东汉后期,板楯蛮夷皆战功卓著。
板楯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其人勇猛,善于兵战。昔永初中,羌入汉川,郡县破坏,得板楯救之,羌死败殆尽,故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楯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虽受丹阳精兵之锐,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乱,太守李颙亦以板楯讨而平之。[4]《后汉书》卷86《南蛮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42—2843页,第2843页。
但“忠功如此”,在东汉王朝愈趋腐败的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下,板楯蛮夷最终也公开反叛。所谓“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刭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5]《后汉书》卷86《南蛮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42—2843页,第2843页。。这对以夷制夷的践行亦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是军纪败坏,往往抵消了以夷制夷的功效。这主要表现在朝廷对非汉民族的军人难以严格管理,有些少数民族的军队战斗力不强,却大肆破坏军纪,烧杀抢掠百姓,造成极坏的影响。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统治腐败的东汉后期。以鲜卑骑兵为例,前揭应劭便揭露说:
往者匈奴反叛,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又武威太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斩获丑虏,既不足言,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裁以军令,则忿戾作乱;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劫居人,抄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马。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6]《后汉书》卷48《应劭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09—1610页。
这反而加大了对以夷制夷的投入,实际上得不偿失。
四是以夷制夷的滥用,也使得朝廷对地方军队和边疆地区的控制逐渐松弛,为军阀割据大开了方便之门。这在东汉后期亦表现得特别突出。《后汉书·刘虞传》载前中山国相张举和前太山太守张纯的反叛就是一个显例。又董卓之乱,他的部下也主要是非汉民族的步骑。正如名士郑太所言:“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明公(董卓)拥之,以为爪牙,譬驱虎兕以赴犬羊。”[7]《后汉书》卷70《郑太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58页。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以夷制夷的滥用,才使得东汉后期的军阀割据问题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痼疾[8]薛小林:《西州与东汉政权的衰亡》,《史学集刊》2017年第2期。,并对三国以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