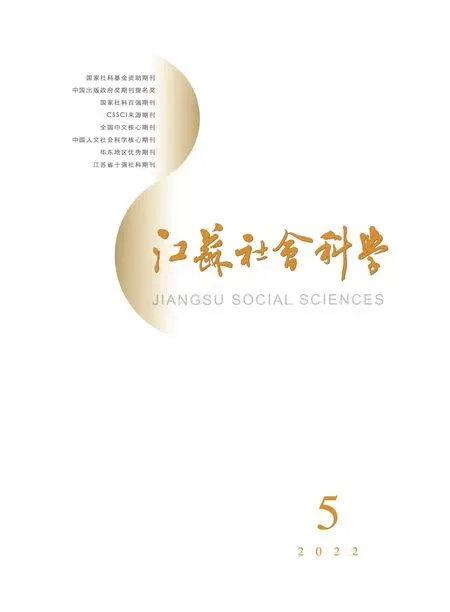论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
龚天平
内容提要 当代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中的社会偏好理论对人性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自利人假设的新假设。这种新假设认为,人的行为是在给定约束和信念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偏好最大化的过程,而人们追求最大化的偏好既包括自利偏好也包括社会偏好。社会偏好就是人性中的涉他偏好,是人性利他性的反映。它使人关心他人,维护社会规范,合乎伦理;也使人具有正义感,惩罚侵害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人。与自利人假设相比,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也拥有最大化的形式,但最大化的内容不同;也关注偏好概念,但偏好的指涉不同;也关注人的行为,但行为的性质不同;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还特别强调信念。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对人性内涵的理解是合理的,对偏好内涵的理解是适当的,也恰当地突显了社会偏好范畴的伦理维度。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梯若尔说,当今经济学越来越明显地偏离其20世纪确立的研究边界,而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拓展,并与社会科学逐渐走向再统一,即在付出了“越来越游离于其他学科之外”的代价后,向“曾与人文社会科学融合在一起的经济学”[1]让·梯若尔:《共同利益经济学》,张昕竹、马源等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19页。回归。正是在这种回归的过程中,经济学领域产生了日益引起人们兴趣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而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中,一些著名学者又提出了一种所谓的社会偏好理论,社会偏好理论对人性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自利人假设的新假设,我们姑且把它称为“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那么,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具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整套严密的逻辑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即自利人假设有何相同和相异之处?这种人性假设又有着怎样的合理性?本文试图从伦理学角度做出系统回答。
一、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的基本内涵
美国著名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说,社会科学一般都需要立足于一种元假设的基础上,所谓“元假设就是一种不言自明、潜藏在所有经济解释的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假设”[1]马克·格兰诺维特:《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王水雄、罗家德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5—6页,第6页。。它是指“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组成的基本前提预设”,是人们“理解一组社会现象的概念原点”[2]马克·格兰诺维特:《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王水雄、罗家德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5—6页,第6页。。这种元假设其实主要指人性假设。经济学的元假设或人性假设在新古典经济学及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那里就是自利人或理性人假设,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描述的经济人。当然,斯密本人既不倡导(或排斥)利己主义也不倡导(或排斥)利他主义,而是通过有条件地肯定自利(将自利纳入合宜性轨道)和利他(反对纯粹利他主义和禁欲主义),实现对对立两者的超越,把自利与利他统一起来。“经济人”在约翰·穆勒那里得到明确概括和界定,并真正被抽象为一种假设。到了帕累托那里,“经济人”被作为一种最优准则确立下来。大卫·李嘉图、费朗西斯·埃奇沃斯、列昂·瓦尔拉斯等则将其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其基本观点是:经济人是自利的、理性的,会最大化地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在良好法律制度约束下,经济人追求自利最大化会有效增进公共利益。自利人假设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中受到了强烈的批评,美国桑塔费学派的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迪斯提出了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来代替它。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主要包括如下两点内容。
第一,人的行为是在给定约束和信念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偏好最大化的过程。对于社会偏好理论人性假设的这一内容,塞缪尔·鲍尔斯等在《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中用一整章的篇幅做了详细的论述。他们认为,通过“约束、偏好和信念方面的信息”就足以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做出他们所做出的行动”[3]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赵准、徐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第40—41页,第35页。。这一观点被赫伯特·金迪斯于2009年和2011年命名为BPC假设,即信念(beliefs)、偏好(preferences)、约束(constraints)假设,意指“人的行为是在给定约束和信念的前提下,最大化自身偏好的过程”[4]叶航、陈叶烽、贾拥民:《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这三个范畴有其特定内涵:所谓信念,是指个体对其行为与行为结果之间关系的理解;所谓约束,是指个体行为在给定情境下所受到的限制,或个体行为所遭遇的各种条件;所谓偏好,是指“个体对行动造成的各种可能后果进行评价时所依据的正面或负面情感”[5]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张弘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迪斯是在批判自利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信念、偏好、约束假设的。针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创立者之一费朗西斯·埃奇沃斯所提出的“经济学的首要原理是每一个行为主体都受到且仅受到自利所驱使”[6]F.Y.Edgeworth,Mathematical Psychics:An Essay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as to the Moral Sciences,London:Kegan Paul,1881,p.16.这一命题,塞缪尔·鲍尔斯及其合作者以“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为例,认为把自利作为人性的一般性假设错得很离谱[7]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赵准、徐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第40—41页,第35页。。于是,塞缪尔·鲍尔斯认为,人是各不相同的,自利人假设是不符合事实的。当然,假设每个人都是利他的也不合实际。自利人假设存在很多遗漏之处:一是遗漏了与自利性同样普遍的同情、无私和利他性,在判断人性是自利还是利他时,关键是看人的行为动机,即要看人的“行为是否由对他人的关心所驱动,而不是它是否给自己带来了幸福”[8]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赵准、徐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第40—41页,第35页。;二是遗漏了影响人性的价值观、社会经历,自利人假设把人考虑成自然的,其行为被假设为在每一种社会形式中都是普遍存在、一成不变的。其实,“人们不仅各不相同,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不同也各有差异”[1]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赵准、徐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第46页,第46页,第51—52页,第56页。。这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塞缪尔·鲍尔斯和由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组成的一个团队设计了一组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生活状态截然不同的小规模社会中进行的实验,以便考察人们的谋生方式与他们的偏好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这些实验,他们发现,不同人群中的典型行为之间具有明显差异,自利人的行为作为典型行为在任何人群中都不存在,各种人群之间的行为差异是每个人群中人们的谋生方式差异的反映,而谋生方式差异又造成了人们的偏好差异和信念差异。
偏好受基因的影响,是人类天性的反映。但是,偏好既是由基因遗传决定的,也是由文化继承造成的。从其他人那里习得的偏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信念既有每个人从自身生活经验中总结而得的,也有从其他人那里习得的,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由于行为选择部分地建立在每个人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即信念的基础上,因此信念深刻地影响着人的行为。人类基因一般而言并没有非常大的差别,因此遗传决定的偏好也差别不大。但是,作为文化之组成部分的习得偏好和信念则差别很大,由它们所引发的行为也有很大的差别。“行为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各个国家或人群之间的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甚至当我们是成年人时,我们从其他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因为我们所处地方的不同而差别极大。”[2]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赵准、徐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第46页,第46页,第51—52页,第56页。习得偏好和信念差异又源于谋生方式即经济生产的差异。所以,“经济生产出人”[3]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赵准、徐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第46页,第46页,第51—52页,第56页。。
所谓“经济生产出人”,在塞缪尔·鲍尔斯那里意味着,经济并非仅仅创造商品和服务,还生产出人。创造商品和服务是生产,人的生产是再生产。再生产既包括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殖生育,也包括个人成长和发展中所必需的所有过程,如家庭中父母的养育教育和成人后与配偶的家庭生活、学校里老师的培养、其他机构中对其他人劳动投入的享受等。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社会实现再生产。而不同社会的再生产是不同的,再生产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人。人的不同主要体现为偏好差异,偏好差异又主要是由经济制度塑造的。因为一个社会的生产和商品分配方式是该社会中的个人必须达到某些条件从而成为特定的人并维持生存的基础。比如教师就必须善于学习、有仁爱之心,企业家就必须自我激励、富有冒险和创新精神。经济制度“对构成社会的人们规定了互动的典型模式……这些模式反过来又影响到人们成熟起来以及在其一生之中发展变化的过程,形成他们的个性、习惯、品味、身份和价值观——简言之,他们的偏好”[4]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赵准、徐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第46页,第46页,第51—52页,第56页。。
与“自利人”不同,人是合作的物种。对于所有形式的人类合作之根据的寻求,我们最好的途径是通过考察自利以外的动机来实现。自利性只不过是一种人性,而且并非最普遍的人性。更普遍的人性则是互惠互利、关心他人、对原则得到维护的渴望之类的利他性。与动物相比,人类合作是由偏好引导的。人类之所以合作,是因为人类可以设计出据此而生活的伦理准则,具有道德情感和实施社会规范的智力和语言能力,而这些都是人性的组成部分。遵守伦理准则,按社会规范行事,成为人类偏好的组成部分,这种偏好并不仅仅是外部约束,而且是可习得、可内化为人性的。但是,自利人组成的人群却无法作为一个整体而融洽地运作,因为他们之间只有相互竞争。因此,“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本性共同作用,使得智人成为我们这样的独具合作性的物种。我们具有合作性这个事实,意味着好人并不总是落在最后。说明为什么好人并不总是落在最后的推导过程,也让我们明白了新古典经济学家有时过分强调了竞争作为进步的源泉的作用。合作也是必要的”[5]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赵准、徐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第46页,第46页,第51—52页,第56页。。
第二,人们追求最大化的偏好既包括自利偏好也包括社会偏好。也就是说,人们的合作行为并不仅仅出于自利,也出于社会偏好。2004年,塞缪尔·鲍尔斯在其《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中对此观点做了最初的阐述:一是“很多行为可以用社会偏好进行完美的解释:在选择行动时,个人通常不仅考虑行动对自己的影响,也会考虑其对他人产生的后果。而且他们通常不仅关心他人行动的后果,还关心行动意图”;二是“个人是遵循规则的适应性当事人”;三是“行为……是情境依存的”,“偏好是与情景相关的和内生的”[1]塞缪尔·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江艇、洪福海、周业安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72页。。2011年,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迪斯在《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中对此观点又进行了系统、完整的论述[2]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张弘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在社会偏好理论人性假设看来,人性中既有自利偏好,也有涉他偏好,涉他偏好就是社会偏好,即人类的亲社会动机。社会偏好使人关心他人,维护社会规范,合乎伦理,也使人具有正义感,惩罚侵害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人,这种惩罚使惩罚者产生满足感、成就感、荣誉感,相反,如果没有做出正义举动则会产生羞耻感、内疚感。由社会偏好激发的道德情感是由人类祖先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形塑的,人类祖先中由具有社会偏好的个体组成的群体相比于其他群体在生存和演化上更有优势,而这又使社会偏好得以扩散并延续下来。
二、自利人假设与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的同与异
自利人假设自提出之日起,虽然得到许多人的认同、继承,但也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也正是在肯定与批评中西方经济学日益完善,经济分析方法逐渐成熟。作为一种新的人性假设,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也是在批评自利人假设的过程中出现的,两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区别。
第一,自利人假设与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都拥有最大化的形式,但最大化的内容不同。最大化概念是与功利主义伦理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边沁等人创立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是以行为或规则的后果是否带来最大效益来判断该行为或规则之正当性”的规范伦理理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或者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快乐)”[3]邓安庆、蒋益:《伦理学上的诸种“主义”释义》,《云梦学刊》2021年第1期。是其最著名的口号。换言之,功利主义伦理学认为,行为后果能有助于行为所及的所有人的功利总量最大化才是合乎道德的,这种功利在功利主义那里,是指快乐、幸福、利益等。边沁说,功利是指“任何客体的这么一种性质:由此,它倾向于给利益有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幸福”[4]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8页,第58页。,而功利原理是指“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5]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8页,第58页。。边沁功利主义的继承和修订者、伦理学家、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把功利主义伦理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结合,使前者成为后者的伦理前提,继承以英国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趋乐避苦”人性论,视幸福为善,把最大幸福原则当作道德的基本信条,从而对自利人假设的最早说法即经济人假设作了明确界定。他说,经济人假设“只把人看作是渴望占有财富,并能对达到目的的各种手段的有效性进行比较”[6]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程恩富、顾海良主编:《海派经济学》第6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从而谋求财富最大化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出,约翰·穆勒不仅从心理和伦理双重角度充分阐发并肯定了经济人假设的财富最大化动机,而且把这一假设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延伸,提出了“效用”最大化原则。至此,功利概念的内涵不仅具有幸福、快乐的意思,而且有了效用的意思,自利人假设最大化的内容也就变成了效用。所以,准确地说,约翰·穆勒的功利主义应该是“效用主义”[1]徐大建:“译者序”,约翰·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的最大化是偏好最大化。从l9世纪70年代开始,作为古典经济学对立面的边际效用学派登上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舞台并引发了“边际革命”浪潮,使得西方经济学从此发展到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人假设也进入自利人假设的新阶段。新古典经济学家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经济人”被抽掉伦理的、社会的因素后,使经济学成为科学的基石是什么?此时,“偏好”范畴进入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建构经济学科学体系的视野,在他们看来,通过偏好范畴,可以明确区分“自利”与“自私”,抛弃主观的感性因素并转向理性选择。这一主张主要是罗宾斯提出的,也被后来经济学家比如以数理分析形式讨论自利人假设的萨缪尔森等人大大发挥。自利人假设最大化的内容也就从效用转化为偏好。而偏好最大化的形式也被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所吸取。偏好最大化也与功利主义伦理学密切相关。在伦理学中,彼得·辛格提出了一种偏好功利主义,他说:“我应当采取的行动,必须是能够满足更多偏好的行动,该行动要基于偏好的强度进行调整。”[2]P.Singer,The Expanding Circle:Ethics,Evolution,and Moral Progres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101.在这种理论看来,传统功利主义追求幸福、快乐、效用最大化,但幸福、快乐、效用都是难以通约、无法精确计算的主观感受,因此应该用偏好来代替。偏好在此是指愿望的满足、奋斗的成功,偏好功利主义主张,凡是能使人的偏好最大化的行为即是道德上正确的行为。显然,在最大化形式上,偏好功利主义与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已经是一致的了。
第二,自利人假设与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都有偏好概念,但偏好的指涉不同。自利人假设也讲偏好,但这个偏好是指理性偏好。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主要有三条,其中一条是,主体在结果之间有理性偏好。这意味着,单个的主体被看作完全理性的,即他们拥有驱使他们做出选择的偏好,而这种偏好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排序是完整的,即“对于任何两个替代选择x和y而言,要么能动主体喜欢x超过y,要么能动主体喜欢y超过x,要么能动主体是中立的”;二是“替代选择的排序是可传递的”,即“如果能动主体喜欢x超过y,而且喜欢y超过z,那么,能动主体喜欢x超过z”[3]罗伯特·毕夏普:《社会科学哲学:导论》,王亚男译,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8—219页,第261页,第274页。。此处的“替代选择”就是偏好。主体的这种偏好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自利的,即不指涉他人,而仅指涉自己。“主体对于其他主体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只要对主体自己的经济福利没有影响,主体既不会喜欢也不会讨厌其他人的结果或者行为。”[4]罗伯特·毕夏普:《社会科学哲学:导论》,王亚男译,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8—219页,第261页,第274页。也就是说,理性偏好是指自利的个人偏好,理性的即自利的,自利的即理性的,而且它还意味着,行为主体具有完全信息,没有认知缺陷。
与自利人假设的偏好概念不同,社会偏好理论人性假设的偏好是指社会偏好。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回避了理性概念。赫伯特·金迪斯认为,理性概念的意义过于纷繁复杂、歧义丛生。他说:“倘若理性意味着自私,则唯有天良丧尽者才会是理性之人。”[5]叶航、陈叶烽、贾拥民:《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罗伯特·毕夏普也批评道,理性概念是不完整的,很容易变得不可证伪,常常不能理解实际行为,代表着不适用于人类的理想化的理性形式,特别是它“继承了与工具主义的行动概念相关联的伪装意识形态的所有问题”[6]罗伯特·毕夏普:《社会科学哲学:导论》,王亚男译,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8—219页,第261页,第274页。。在经济生活中,“人们实际上并不按照经济人这一概念来行动。很多人的确想要被公平地对待并抵抗不公平的结果,即使这样做会使他们遭受经济损失……诸如宽容、同情和善良等价值,总是在人们的选择和行动中发挥作用”[1]罗伯特·毕夏普:《社会科学哲学:导论》,王亚男译,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6页。。因此,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就用社会偏好概念代替了理性偏好。理性偏好又称自利偏好,意指只涉及行为主体自身状况的偏好,而社会偏好则是指涉及他人状况的偏好,既包括自利偏好也包括非自利的、利他的偏好,或者说理性偏好和感性(情感)偏好。
第三,自利人假设与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都关注人的行为,但行为的性质不同。人的行为是指人在思想的支配下表现出来的活动。行为是外在的,一般与心灵、意志相对,后者是内在的。但两者都是人性的重要内容,所以我们可以说心灵、意志是内在人性,行为是外在人性。自利人假设关注人的行为。但是,自利人假设把人的行为都假定为经济主体谋求效用最大化的表现,使行为被同质化、无差异化了。正因如此,如塞缪尔·鲍尔斯所言,坚持自利人假设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用“一组生产函数来表示所有厂商的行为”,用“一组无差异曲线来表示所有消费者的行为”[2]叶航、陈叶烽、贾拥民:《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第11页,第11页。就成为可能。
而在坚持社会偏好理论人性假设的新兴经济学家们看来,由基因和环境因素决定的生物性状都可以用经济学或博弈论来分析。所谓“生物性状”,是一个遗传学范畴,意指生物体所表现的形态结构、生理特征和行为方式。在此种行为分析范式下,新兴经济学就既可以分析人的理性行为,也可以分析新古典经济学自利人假设无法建模、难以分析的非理性行为,包括非自利的或利他的亲社会行为。新兴经济学家认为,人们的行为并非同质的、无差异的,而是异质的、多样化的。所以,他们立足现实世界,通过关注人的多样化行为来理解人性及其价值诉求。正如弗朗兹和尼森所说,新兴经济学并不通过“一个极强的理论假设来描述所有的行为”[3]叶航、陈叶烽、贾拥民:《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第11页,第11页。,从而与新古典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殊为不同。这样,就理论假设与行为的推导关系而言,如塞缪尔·鲍尔斯所概括的,前者是从行为推出新的人性假设,而后者是从理论假设推出行为[4]叶航、陈叶烽、贾拥民:《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第11页,第11页。。
第四,相对于自利人假设而言,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强调信念。所谓信念,从哲学上看,是个体对某理论、观点、原则、世界观的真理性和实践行为的正确性的内在确信,它是该个体在长期的人生实践中,根据自己的生活内容、积累的知识,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所确定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从心理学上看,信念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的统一,但它并不强调认知的正确性,而是强调情感的倾向性和意志的坚定性。信念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比如理论信念、政治信念、文化信念、审美信念、道德信念等。应该说,自利人假设也有关于信念的理解,即在市场上活动的自利人都是以效用最大化为价值诉求的。但这种信念是对理性的信念。理性就意味着相互冷淡,不包含情感。而在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看来,信念是人们对事物先验的主观判断,既由社会也由特定文化或情境所决定,具有极强的情感倾向性,还可以在个人之间分享。加里·S.贝克尔评论道,在一定偏好支配下的个人最大化自己的效用这一假设中,“偏好在任何时点上都仅仅由个人当时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本身所决定……独立于过去和将来的消费,也不受别人行为的影响”。然而,在所有的社会中,个人偏好“都会取决于少年时代的经历和其他经历、社会相互作用以及文化因素”[5]加里·S.贝克尔:《偏好的经济分析》,李杰、王晓刚译,格致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也就是说,人们追求偏好最大化的行为是必定受到信念的影响的。因为对于个人来说,其所置身的环境即社会、传统和文化都是给定的,这些材料与其自身的经历共同熔铸成他的信念,这些信念又会被个人带入其追求偏好最大化的过程即行为之中。也正是基于此,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非常重视信念,以至于把信念当作人们追求偏好最大化的约束条件之一。
三、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的合理性
人性假设是人性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哲学特别是伦理学的逻辑起点。应该说,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在人性理论发展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假设,对经济学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这一人性假设的合理性何在呢?
第一,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对人性内涵的理解是合理的。人性是与物性相对而言的。所谓物性,是指世界上与人类相对的万物以及自然环境的面貌、本性和运行规律,物虽然没有思想、情感,但有生命,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及运行法则,动物还有生存本能。与人类一样,物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与人构成生命共同体。所谓人性,是人的本性、人的特性、人类天性、人类属性等概念的简称。查尔斯·霍顿·库利曾从三种意义上阐释过人性的内涵:其一,人性是“人类的由种质产生的严格的遗传特性”,即“人类出生时即具备的各种无形的冲动和潜能”[1]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王湲译,华夏出版社2020年版,第21页,第21页,第21页,第21—22页,第22页。,这是人性的生物学内涵;其二,人性是“人类在亲密联系的简单形式或称‘首属群体’中,特别是在家庭和邻居中发展起来的社会性本质”[2]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王湲译,华夏出版社2020年版,第21页,第21页,第21页,第21—22页,第22页。,具体是指“某些基本的社会性情感和态度”“人际关系中的自我意识”“喜欢别人的赞同、怨恨、非难、竞争心理”“在一个群体中形成的社会是非感”[3]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王湲译,华夏出版社2020年版,第21页,第21页,第21页,第21—22页,第22页。等,这是人性的社会心理学内涵;其三,人性是讨论人性善与恶时使用的,这种人性与环境和风俗紧密相关,因为“随着外部影响的变化而在道德或其他意义上都是变化的”[4]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王湲译,华夏出版社2020年版,第21页,第21页,第21页,第21—22页,第22页。,在一种环境中人性为恶,如自私、无能、好斗、保守,而在另一种环境中则人性为善,如慷慨、有为、温和、进步,因此这种意义上的人性是指可变化、可教育的,即“可以让它按我们的意愿发挥作用”[5]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包凡一、王湲译,华夏出版社2020年版,第21页,第21页,第21页,第21—22页,第22页。的人性,这是人性的伦理学内涵。这就意味着,人性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伦理学三种意义上的内涵,是指人类作为一种与其他生命存在相区别的存在物而具备的类本性。这种类本性的具体内容就是肖恩·塞耶斯所界定的,人性即“人类的诸种需求、诸种能力和诸种力量”[6]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冯颜利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也就是人的需要、行为动机、认知方式、感受方式、行为能力、人际互动方式等。
在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看来,人性即人类天性。但是,人性又并非纯粹自然的,而是通过自然与社会相互作用塑造的。这显然是一种社会人性论观点。社会人性论意指在不否认人性自然性的基础上强调人性的社会性,把社会性视为人性本质的人性论。这种人性论在人性思想发展史上源远流长,古希腊哲学家们就已经天才地猜测到了人性的社会性,近代欧洲哲学家如培根、洛克、18世纪法国唯物论者、费尔巴哈等,都提出并系统地论证了人性社会性思想,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人性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而在马克思主义人性论那里,人类作为自然性的存在物,有维持自然生命延续的需要,这种需要就是自然人性。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即是说,自然人性一般表现为天赋、才能,特别是欲望。但是,人并不单纯是自然性的存在物,还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作为社会性的存在物,人就对他人和社会共同体具有依赖性,从而具有维持他人和社会共同体存在的需要。因为社会和共同体是单个的人得以存在的寓所,单个的人就生存在社会和共同体之中,如果他人和社会共同体不存在,单个的人也无法存在,而这种需要就是社会人性。马克思说:“人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合乎人性的需要,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要,他作为最具有个体性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这就意味着,社会人性脱胎于自然人性,但又不与自然人性等同,而是超越自然人性的,是人通过社会交往而生成、练就的人性。因此,人其实是把自然人性和社会人性内在地集于一身的人,人性是自然人性与社会人性的统一。这种统一,正如肖恩·塞耶斯的精辟阐述:“人是自然的社会存在。我们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相互贯通……企图把它们彼此分开和彼此对立起来……是不可能的。”[2]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冯颜利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199页。1933年,总结持续9年的霍桑实验的《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一书出版,梅奥正式提出了社会人性论。社会人性论认为,经济人理论认为人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工作的观点是错误的,其实经济因素只是第二位的,社会交往、他人认可、归属某一社会群体等社会心理因素才是决定人工作积极性的第一位的因素。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正是社会人性论的延续,它并没有否定人性自然性,而是在认识到人性自然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人的社会和心理需求,认识到了人性既有自然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人的行为即人性的外在化表现既由理性也由情感引导,强调了基因和文化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与自利人假设相比,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更为合理。
第二,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对偏好内涵的理解是适当的。人类是具有偏好的动物,偏好来源于人性。克里斯托弗·博姆说:“人类的偏好源于人类的天性,同时也进一步形塑着人类天性。”[3]克里斯托弗·博姆:《道德的起源:美德、利他、羞耻的演化》,贾拥民、傅瑞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所谓“偏好”,简单地说,就是指个人对自己追求的对象的喜欢、偏爱,是个人固有的、稳定的行为取向。在生活中,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人们的很多行为都受到偏好的支配和影响。人与人的偏好是异质的、多样化的,但都是人类天性的流露。人类天性体现为需要、欲望、能力等。
在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看来,来源于人性的偏好既有基于基因遗传的,也有基于文化继承的,个体的偏好是自利偏好与利他偏好的统一体。对于这种观点,我们可以与自利人假设相对照来予以检视。前文已述,自利人假设坚持人只有自利偏好。本来,在约翰·穆勒那里,经济人假设是有严格限定的,即它只是一个适用于在市场上行动的人的假设。他认为,那种不考虑这一限定而把这一假设向其他领域推延,视经济人为事实上的人,认为人只有自利偏好,并从此出发去解释一切社会问题包括政治、文化、伦理等问题的观点是荒谬的。即便在经济生活中,他也认为这一假设不能无条件、无界限地适用。所以,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分析经济问题时,既把经济人视为自利人,也把人视为关心社会福利即具有利他偏好的人。然而,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到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视经济人为实际生活中的人,把自利偏好当作唯一的偏好,甚至还通过排除人们所处社会的历史、文化、道德环境,把这一假设向政治、文化、伦理等领域推广,把人们的利他行动都解释成出于自利。这显然令人无法认同。因为即便是在市场上行动的人也并不是生活于真空中,而是受社会文化、伦理、制度等条件的制约,因此他们同时也具有利他性特征。当然,自利人假设也并非一无是处,它确实较为确切地呈示了市场行动者的经济动机和行为。“这类学说,如果仅仅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可以展示出,在私利的动机下,人们的行为会产生何种结果,对于认识市场的特征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4]赵修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辩护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8页。
而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视域中,人首先是一种个体性的存在物。作为个体性的存在物,人与人是不同的,这是由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自然个体所决定了的,正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所以都有维持个体存在、延续、发展的需要,此即个人利益,是个人自利偏好的体现。但是,任何人又并非纯粹的、抽象的个人,而是只能在社会整体中才能存在的人,即是说,人又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物。费尔巴哈说:“只有许多人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人’,只有许多人合在一起才成了人所应当是的和能够是的。”[1]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0—191页。马克思也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物,每个人都有维持社会整体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此即社会整体利益,而这种整体利益就是个人利他偏好的体现。这就意味着,人其实是把自利偏好和利他偏好内在地集于一身的人,人性及人的偏好总是呈现为自利性与利他性的双重性特点。人性及人的偏好的这种双重性特点,无论人们是否自觉,自觉到何种程度,都是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只不过因不同历史条件而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性质。也就是说,人们的现实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决定了人性及人的偏好具有双重性,而现实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的基础就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即一定的生产方式。
与自利人假设不同的是,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认为,人的偏好既有自利偏好也有利他偏好。前文已述,该人性假设的提出者之一塞缪尔·鲍尔斯多次阐明这一观点。他在2016年出版的《经济动物:自利的人类如何演化出利他道德?》中说,人们“会因补贴或其他经济激励措施而受到鼓励,为公共产品做贡献”。但是,也有很多人具有“社会偏好,这些会促使他们即使是牺牲自身利益也要使他人获益”[3]塞缪尔·鲍尔斯:《经济动物:自利的人类如何演化出利他道德?》,刘少阳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页,第38页。,其社会偏好意指“类似于利他主义、互惠、助人为乐、反感不平等,道德承担这样的动机,以及那些促使人们帮助他人,而不是一味地坚持自身财富或物质回报的最大化”[4]塞缪尔·鲍尔斯:《经济动物:自利的人类如何演化出利他道德?》,刘少阳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页,第38页。。他明确地把这些表现为慷慨和具有伦理性的人类行为动机命名为人性,而且认为人性是由基因和文化等造就的。这就意味着,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并不否认人的自利偏好,而是认为偏好中还有与自利偏好同时存在的利他偏好,这种利他偏好不能否认且不能归结为基于自利的偏好。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偏好既有以竞争行为表现出来的自利偏好,也有以合作行为表现出来的利他偏好,自利偏好与利他偏好并非“判然二分”,而是“紧密相连”[5]弗朗西斯·福山:《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唐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6页。。斯蒂芬·平克也说,我们需要放弃那种以人性天性良善或天性邪恶来认识人性及人的偏好的二分法,因为“人性中的某些成分,如捕食、支配和复仇,都是制造暴力的动机,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有另外一些成分,如慈悲、公平、自制和理性,推动我们趋向和平”[6]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安雯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558页,第5—6页。,趋向合作和利他。人性自利性的典型表现——侵犯性“不是单一的动机,更不是一种日渐迫切的冲动。它是几种受环境触变、内在逻辑、神经生物基础,以及社会分布形态影响的心理系统的共同产物”[7]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安雯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558页,第5—6页。,人性及人的利他偏好也是人类生来具备的。因此,与自利人假设相比,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对偏好内涵的看法更为适当。
第三,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突显了社会偏好范畴的伦理维度。偏好作为人的行为取向,不可能与伦理无涉。然而,在边际效用学派那里,偏好的伦理维度却被丢弃了,比如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卡尔·门格尔就认为,古典经济学有着突出的缺陷,即伦理假设与方法论工具集于一身,这是经济学不能成为科学的根本原因。他为了使经济学成为精确的科学,就把伦理假设从经济学中剥离了。他说:“只有当我们设想,人在其经济活动中,总是受同一种动机——即自利——之引导,随意而为的因素才是不需要考虑的,只有这时,人的每一个行为才能够被严格地予以确定。只有依靠自利的教条,经济的规律才是可以设想的。”[1]卡尔·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66—67页,第72页。他甚至断言:“承认人性自利的教条乃是人类活动的唯一真正的动力。”[2]卡尔·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66—67页,第72页。这仅仅留意了亚当·斯密开创的第一传统,即《国富论》指出的经济人出于自利而从事经济活动,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创造经济繁荣和奇迹;而偏离了第二传统,即《道德情操论》指出的道德人出于利他而从事社会交往,与人合作,从而创造社会和谐和兴旺。但这两个传统都是亚当·斯密人性假设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他看来,人性是二重性的统一体。作为经济人,在经济领域人会展现自利心,孜孜求利;作为道德人,人会关心他人,轻看自己,抑制自利。自利性与利他性之所以协调地集于一身,是因为社会系统由无数个人所构成,所以个人利益的总和就构成了社会利益。个人越是努力求利,社会利益就越得到增进。显然,如果排除人性的利他性和偏好的伦理维度,就不可能对人性进行准确探讨,人也就只会成为形象不完整的单面人。
而在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看来,偏好是与伦理密切相关的,即使自利偏好也无法脱离伦理,利他偏好即社会偏好就更直接是伦理行为的体现。比如,在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迪斯看来,社会偏好表现为“对他人福利的真正关心、试图维护社会规范的愿望”和“合乎伦理的行为本身”,是“道德情感”[3]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张弘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这就意味着,社会偏好主要是指人类怜悯他人、援助他人、厌恶不平等、互相惠顾、乐于合作等亲社会行为,本质上是个人超越自利的、涉他的偏好,体现的是人性的积极面,拥有丰厚的伦理内涵。社会偏好的伦理内涵表现为:它是个人从情感上对他人境况的共鸣、共情,是人际同情心的体现,也是个人基于义愤的正义感,是同情心与正义感的有机统一;同时,社会偏好还是人的亲社会行为即道德行为的重要诱因。当然,从根本上说,社会偏好的人性基础仍然是人的社会性。虽然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并不否认自然人性和基因对社会偏好的决定作用,但它特别强调社会偏好受文化、伦理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这样,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就合理地展现了社会偏好的伦理维度。叶航等在总结新兴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4]新兴经济学指诞生于20世纪中期至21世纪初的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论,主要包括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神经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传统经济学指以自利人假设为逻辑起点的新古典经济学及以其为基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时认为,就本质上看,新兴经济学“并没有排斥传统经济学的逻辑体系,而是把传统经济学作为一个‘特例’或‘子系统’包含在自己的理论框架内”,“在承认一致性公理与个人自利性的前提下”,两者“存在着互相包容的交集”,而后者“所不能涵盖的内容”,则是前者“对人类社会性的认识与洞见”[5]叶航、陈叶烽、贾拥民:《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7、28页。。如果用这一结论来看待自利人假设和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的关系,其实也是适用的。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突显了社会偏好的伦理维度,有利于人们完整认识人性及人的偏好。因此,与自利人假设相比,社会偏好理论的人性假设更值得被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