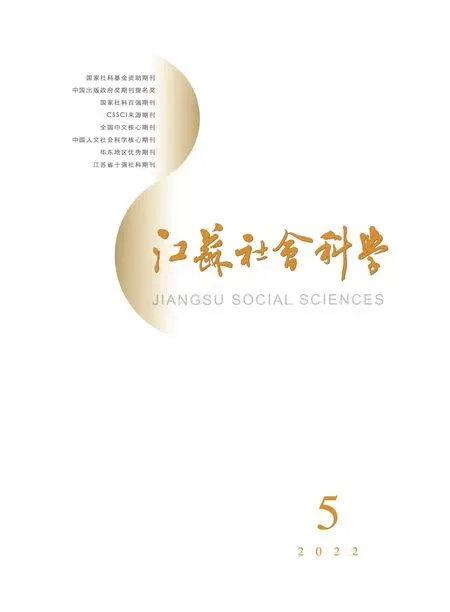现代文明的生发逻辑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建构
张永刚
内容提要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现代文明是一个辩证的矛盾体,现代文明在开启世界历史进程的同时,又呈现出内在对抗性与局限性。人类文明发展依循内在矛盾动力和世界交流动力的双重演变机制,具有特定的发展规律和历史走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道路中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思想空间与实践样态,实现了文明发展从资本的对抗性逻辑向建设性逻辑的转变。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必须坚持文明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动摇,积极借鉴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有益成果,推动现代智能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对接,方能不断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创造与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确立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承继人类文明发展成果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和共同挑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奋斗中,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伟大的实践创造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使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开出新的文明之花,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4页。该论述为从人类文明发展层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未来走向提供了重要视角。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立足新时代对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对资本主义文明批判性反思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结果,构成全面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文明之维。笔者认为,考察现代文明的生发逻辑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建构,必须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基于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演进历史长河的理论研判,着眼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情境和动态体系,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方能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构的现实情境和路径,以此探究现代文明发展规律和动力,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路径提供可资借鉴的科学遵循。
一、辩证的矛盾体: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现代文明”
“文明”(civilisation)一词在18世纪上半叶还仅仅是一个法律术语,用于指称正义的行为或正义的审判,文明作为其现代含义“开化”的运用最早出现于1752年法国政治家杜尔哥的作品之中[1]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有“文明人”“文明形式”“文明因素”“文明传播”“文明程度”“文明作用”等不同话语表述方式。就广义而言,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文明”一词是指由物质基础、制度设计、文化活动等多重要素构成的发展体系。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立足于人类文明演进大势,将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内涵凝练为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多维创造,丰富创新了“文明”一词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除此之外,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文明”还有一重狭义的概念界定,即表示与“野蛮”相对的意义,指称资本主义文明或生产力文明。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西方资产阶级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进程中,“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第632页,第36页。。无独有偶,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以野蛮与文明代指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第632页,第36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表征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文明展开猛烈批判和辩证分析,指认前者实为野蛮与文明的矛盾体,属于一个辩证的概念。
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客观肯定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步性。现代文明的诞生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现代文明”这一术语,并认为相较于以往任何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成就。在生产力层面上,资本主义为物质生产注入强大活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第632页,第36页。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段与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生产力是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关键推动力量,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差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所以,马克思晚期多次将“文明国家”与资本主义或生产力交替使用。例如他在《资本论》手稿中阐释道:“在各文明国家中,不管工资怎样,要想得到工资,就必须劳动一段平均时间。”[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第247—248页。这里的文明国家实际是指代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又阐发道:“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这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第247—248页。此处的文明亦可作资本主义解。在生产关系层面上,资本创造了世界市场,推动人的普遍交往,开创了人类社会世界历史化的进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称为“伟大的文明”:“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尤其对比以往的社会形态,更能显现出其优越性。“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7—928页。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文明唤醒人的自我意识,推动人的自我解放和发展。“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第230页。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审视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的对抗性与局限性。不管是工业文明时期还是当代智能文明时期,资本主义文明从根本上都是“物”的文明。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现代文明包含严重的异化,呈现为一种“粗陋野蛮的文明”[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第230页。。在《神圣家族》中,他还使用“文明中的野蛮”一词对资本主义文明予以无情揭露和猛烈批判。而在后期的作品中,马克思使用大量丰富而生动的词语,诸如“文明灾祸”[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2页。“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2页。“文明贩子”[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6页,第690页。等,彻底揭露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性和对抗性。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两篇关于印度的评论《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聚焦于殖民地,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野蛮面进行了揭露:“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6页,第690页。这种对抗性和野蛮性突出表现在文明进步与人的发展的悖反关系上,而马克思指出,必须由无产阶级掌握文明果实,方能保证社会“文明面”的持存。“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5页。恰恰是由于这种对抗性,“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页。。很明显,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层面克服了自然的局限性,却使人类社会发展陷入自身的悖论。而且这种局限与束缚从资本主义文明开始即已存在,所谓被解放的群体被剥夺一切生产资料沦为“自身的出卖者”,“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22页。。这种矛盾性一经生成,就导致进步过程“使人感到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退化,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8页。。也正是这种对抗性的存在,致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系列难以调和的悖论,继而导致“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页。,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197页。。
由此可见,现代文明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人类文明被深深打上了资本的烙印。然而,西方现代文明并不构成唯一的文明发展道路,西方文明也并不构成世界丰富多彩的文明形态的模板。虽然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具有自身的先进属性,但是马克思对于资本文明中消极方面的深刻揭露说明,作为世界历史初始阶段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就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化。我们必须通过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互动思考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交流互鉴,在规律与现实情境的契合点上推动文明形态的重塑和创造,而不是简单地断言文明的代替关系。全面审视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面与消极面,恰恰是把握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奥秘的关键所在。对此,有学者指出,全面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辩证把握作为“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文明本身的对抗根源,明确资本既是促进文明进步的积极力量,又“像高利贷一样”阻碍和破坏文明发展,这一观点构成理解资本主义文明悖论的理论基石,从而也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必然被新的文明形态所取代的发展趋势[2]黄广友、韩学亮:《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二、文明及其超越:人类文明跃迁的双重动力
既然资本主义文明有上述内在缺陷,那么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文明形态呢?马克思在1846年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明确指出:“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0页。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并不是将资本主义开创的现代文明类型完全排除在外的抽象范式,而是在对资本主义文明批判性扬弃的基础上创造性阐发人类文明形态演进与跃迁规律,并将资本主义文明视为人类文明辩证发展的必然环节。
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现代性话语尚未流行,但现代性问题已然凸显。按照亨廷顿的观点,历史总是上演文明终结的戏码,原因就在于一种文明在鼎盛时期的认知偏差。相应地,资本主义文明在历史上取得了伟大的文明成就,然而它并非人类文明的终极或唯一形态,其本身充满无法调节的矛盾与悖论,呈现出历史上的支配地位与现实中的衰落样态两幅迥然相异的画面[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61—62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已阐释了这一问题:“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像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的结果。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8页。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展开探索,并论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动力及其演变规律。文明形态的更替具有历史展开的必然性,而不同文明之间更替的动力规律构成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面对的最为棘手的理论难题之一,这也成为其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理论延展维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及其晚年对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阐发,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文明的发展具有两大基本动力。
一是矛盾动力。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初动力系统中,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促成的生产关系的飞跃,构成文明跃进的基本结构性力量,进言之,物质文明在文明的不同内在性面向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此意义上,历史的发源地不是浮于“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外”,而是扎根于“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页,第532—533页,第567—568页。中,《神圣家族》中的这一表述可视为马克思对物质文明在历史发展中基础性地位的初步判定。而在对东方社会的分析阐发中,马克思将“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视为洞悉东方文明的“一把钥匙”[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并据此物质生产方式将印度的开化程度定位为“半野蛮半文明”[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2页,第591页。。又如,马克思指出:“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页。很明显,马克思将物质生产状况视为人类文明更替的标志性力量,而在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动力中,作为第一性的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模式与文明样态,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释的,无论人们的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页,第532—533页,第567—568页。。毕竟,“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文明时代一开始,物质生产就建立在阶级对抗与矛盾之上。“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197页。。也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使得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中呈现出不同的文明样态,无论是经典文本中的“三形态说”还是“五形态说”,都基于时间维度从不同层次体现出人类文明演进的发展阶段。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人类文明演进的对抗性与悖论性,决定着我们必须辩证把握文明发展趋势,正确看到每一文明成果的两重性及其实质[8]侯惠勤:《论人类文明新形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指导意义,尤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断通过改革力量推进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来理解更显深刻。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的文明史研究要摆脱西方文明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影响,坚持依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阐释文明体之间交往关系的演变[9]吴英:《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
二是交流动力。罗素曾言:“以往的历史表明,不同文化的接触往往能够成为人类历史进程上的里程碑。”[10]罗素:《罗素论中西文化》,杨发庭等译,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阐释的:“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于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页,第532—533页,第567—568页。从民族文明到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亦是资本主义文明对“野蛮”区域产生颠覆性文明影响的过程,其中包括生活状况、社会结构、制度安排等。一方面,交流贸易具有传播文明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明确指出:“最初,对生产的影响较多地来自物质方面。需求的范围不断扩大;满足新的需求已经成为目的,因而生产就更有规则性并且扩大了。本地生产的组织本身已经被流通和交换价值改变了;但是流通和交换还没有影响到生产的全部广度和深度。这就是所谓对外贸易的传播文明的作用。”[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0页。所以,资本主义文明“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肯定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会促进文明的演进,即使是中国这样古老的文明,也被英国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9页。在这种无法抗拒的历史进程中,扩大的全球交往使得“文明开始生根,贸易获得增长,新的思想产生”[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不难发现,基于世界历史的眼光,交流是文明发展乃至跃迁的重要推动力量。任何一种文明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重要规律,人类文明发展是在差异中寻求交流互鉴的演进过程,文明形态的生成是在对矛盾范畴扬弃基础上更高程度的统一[5]孙代尧:《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在交流动力的推动影响下,人类文明在横向维度上呈现出从民族文明向世界文明发展、从区域文明向全球文明演进的总体趋向。习近平指出:“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6]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病症的解剖之上,基于矛盾动力与交流动力,揭示出人类文明发展的三重趋向:资本主义文明由于内在的对抗性和矛盾性,呈现出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明发展的趋向,地域文明与民族文明呈现出走向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向,被奴役被支配的个体呈现出向自由解放的文明发展趋向。我们由此可断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建构至少包括三重基础,即基于理论自信对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基于世界历史眼光对资本主义文明最新成果的积极吸收、基于道路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研判。在此基础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想空间与实践样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情境中开出了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之花。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建构
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指出,文明的历史是提炼集体性格的过程[7]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文明是具有区域性的长期的存续与流变过程的结果,也因此,国家和族群构成考察文明演变的基本单元。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在建设文明形态方面都有不同的探索和成就,表现出各自的民族特色和国家特点。基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及其动力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建构至少包括三重路径。
第一,基于人类文明演进规律与发展方向,辩证审视并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牢牢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动摇。社会形态是人类文明形态的制度空间,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新时代的开创,也就没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和创造。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致思逻辑,资本主义文明究其根本是一种物的文明而非人的文明,甚至表现为一种文明暴行,一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写:“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2页。尽管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描绘社会主义文明的图景,但已然廓清了总体思路和基本框架,所以只有将人类文明新形态置于现实道路的实践路径中,才能总体上把握其发展方向。习近平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述是立足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双重统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承继与实践推进,这也就决定了必须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开拓中深刻把握和不断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质意蕴。基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首先必然是对资本主义物的文明的扬弃与超越,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不断发展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即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建构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而不是其他什么文明,是优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新型文明样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基本前提和根本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范畴为相互联系、互为一体的整体性内容。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通过不断对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艰辛探索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必然是以人为本的社会逻辑对以物为本的资本逻辑的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创新性实践和伟大历史成就,显露着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端倪,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大旗。
第二,基于文明交流动力,坚持世界历史眼光,秉持交流互鉴的基本立场,借鉴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有益成果。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肯定和探索是对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大发展,树立了世界文明发展图式的重要遵循。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明观,文明演进呈现出基于地域发展差异的不平衡规律,故此,在世界历史的视域内,社会主义应当并且可以吸收资本主义的最新成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实际指向了一种文明的建构范式,而这恰恰为我们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文明演进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模式。对此,有学者明确指出,当人类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才真正有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文明,所以,我们要建构基于普遍共识的人类文明,就必然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的文明观[2]陈曙光:《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重建》,《哲学研究》2022年第3期。。纵观人类历史发展也可看到,历史从野蛮到文明、从低级到高级的纵向发展制约着它从部落到国家、从分散的各地区到连接为一体的世界的横向发展。而横向的发展又对纵向的发展发挥反作用力,如若一个地区缺少与其他地区的横向联系,其文明的纵向发展也必然迟滞。如美洲的玛雅文明,由于缺少与世界历史视域内纵向发展相适应的横向发展,长期停滞而并未达到高一级的社会阶段[3]吕世荣:《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216页。。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形式,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一般特点,内在地要求借鉴吸收继而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结合时代境遇走出一条新的文明道路。“作为全球共同信仰的人类文明,本质上说不应该是某种单一文明的世界化,而应该是不同国家文明的调和。”[4]陈曙光:《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重建》,《哲学研究》2022年第3期。资本主义文明即是将资本运作逻辑延展至社会生活各层面的文明形态,这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必然具有内在的对抗性与难以克服的基本矛盾,呈现为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诸多弊端。然而,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同时创造了“伟大的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了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进步和文明样态的跃迁,使得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丰富了人的发展维度与交往范式,奠定了向更先进文明发展的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孤立的、与世隔绝自在创生的,而是在与世界不同文明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密切联系中开出的文明之花,是在借鉴吸收资本主义文明先进成果的基础上,实现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重维度的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和扬弃,实现文明发展从资本对抗性逻辑向建设性逻辑的转变。
第三,基于结构性矛盾动力,积极发展现代智能文明,推动智能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对接与深度融合。发展文明形态必须牢牢扎根于本国文化传统和具体实际,任何不顾现实限制的加速或拔高行为,都只会适得其反。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作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目前,学界较多地从传统文化角度阐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根基,立足民族基因把握文明发展根基。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尊崇历史,确立历史思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当然,也要看到,传统文明只有在与现代智能文明融合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产物,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所衍生的现代智能文明的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智能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然而,资本主义文明囿于资本逻辑的主导,在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e)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e),从而成为技术进步的阻碍力量[1]Alex Williams,Nick 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in Robin Mackey,Armen Avanessian(eds.),Accelerate:Accelerationist Readers,Windsor Quarry:Urbanomic,2014,p.354.。当代左翼加速主义的这一分析应当说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论证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技术发展的限制因素进行了诸多论证,对无形磨损的忌惮、危机造成的生产力浪费等均构成资本在加速增殖之外的对进步的阻滞力量[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1—452、465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发展是在控制资本力量基础上的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这也决定了中国特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主动面向人类智能文明的发展,既来源于历史又从根本上面向未来。
四、结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于世界历史的眼光深刻洞察人类文明发展的地域不平衡规律,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是构成一种文明形态发展自身的必然选择。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形态的互动和交流说明,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必然建立在对多元文明共生共荣、相互借鉴的基础上,超越资本主义宣扬的两极对立思想,尊重各国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制度特点,追求符合自身实际和文化传统的文明形态,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交流范式的一个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世界历史的眼光,尊重不同文明的内在发展规律,并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多元共生的人类文明视角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相得益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中国的文明新形态,而且是人类的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