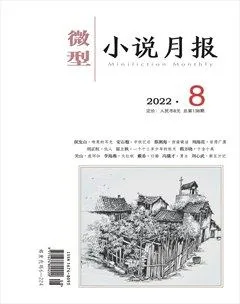离海而去
陈雪出生在海边,长大在海边,从小吃的是海里的鱼虾螃蟹,呼吸的是从渔村房子缝隙间呼啸而过的海风,睡在海风吹拂着的一栋小木屋里,每天夜里,听着浪涛淹没房屋的声音,猜测自己第二天醒来一定会从世界上消失。更小的时候,她也曾睡在海上的渔船上,吃着细嫩的鱼肉,难以从幼年的失语症当中好转。
陈雪每天早上睁开眼就能够看到海,吃饭时听着涛声(父亲说松涛的声音和海涛是一样的),上学路上,脚丫始终泡在海水里。
学校也建在海边,是一座比她家高大不了太多的二层木楼。上课的时候她就爱往窗外看,看蓝色,蓝色的水、蓝色的天空,看白色的云,看棕黑色的房子,看金黄的沙滩,看船上的帆和红旗。
“陈雪,看黑板!”
陈雪还看黑板。青春期以前的陈雪,至少有七成的时间用来看黑板。后来她脸上长出了青春痘,青春痘破了,流脓了,她就不怎么爱看黑板了,总是一副意兴阑珊的样子,读着些有群山和草原的诗歌,厌倦着肺里充斥着的腥咸的空气。
唉,人家的海边上有草原,还有雪山,怎么我这片海什么都没有,只一片光秃秃的沙滩和一群破旧的渔船?
“陈雪,看黑板!”
陈雪的中学是海岸线更远处的一座砖瓦盖成的小楼,楼下有一片沥青的操场,楼的另一面是海,海这时候已经有点远了,必须在楼顶才能看到。陈雪从来不上楼顶,她一有机会就爱去操场玩。放学之后,她从教室走下楼,穿过操场,继续前进,继续前进,穿过小镇里并不高大密集的楼房,穿过渐渐沦为星星的背景的天空,穿过无定形的深渊,穿过一些早已死去的人写在书里的句子。她想象自己是一尾鱼,穿行在深海的渔网中间,闪躲腾挪,在海面跳跃,跳得一次比一次高,她感觉到自由得几乎透明,一直到路灯亮起来,风使她忍不住打起寒战时,才会往回走。她记得最远曾走到西半球。
“又上哪儿胡闹去了?这大半夜的多不安全。”
“雪,你这高中都快要念完了,就没看上哪个好人?”
“雪,高中毕业赶紧来家帮忙啊,爸妈快累死了。”
“我不会!”
“有什么不会的?谁一开始不是不会?再说了你上学都学了些什么东西?抖网、编网,这些也没学吗?”
“女人家的也不能叫你上船,怪不吉利咧。你就在沙滩上摆个摊卖鱼也是好。”
灯泡闪了一闪,熄灭了,陈雪爹烦躁地啐了一口痰,弓下腰找起灯泡来。
正当壮年的父亲已是满头白发,哪怕洗过澡了,仍然一身浓重的鱼腥味。陈雪鼻头一酸。这种鱼腥味是他与生俱来的,是这片水域上的人所共有的。远远地,他们凭借气味就能认出彼此,鱼腥味是渔民们的信息素,是他们的胎记,孤傲、顽固地伏在每个人的脸上。
第二年,陈雪考上了大学。
陈雪一直梦想着可以离海远一点,再远一点,可以远到闻不见鱼腥味,可以远到站到楼顶也看不到海,或者看过去模模糊糊的,像是海市蜃楼一样,或者很小很小,简直像是远远的蔚蓝的星辰。
现在陈雪真的看不见海了,她上到学校最高的六楼也看不见海,无论往哪个方向都看不见了;陈雪也真的闻不见腥味了,室友们都香香的,宿舍楼走廊里有股辛辣的狐臭味。陈雪意识到她可能离海真的很远,比西半球还要远一点。
短暂的高兴过去之后,故事中最诱人的部分来了——有一天早上,半梦半醒之中,她又听到了熟悉的涛声,感觉到自己漂浮了起来。醒来之后,她意识到鱼腥味又来了,而且来自自身,她一跃而起,冲进了浴室。
就这样,在入学的第一个月里,陈雪频繁地在自己身上嗅来嗅去,同学见了都因感到莫名其妙而发笑,于是她不再嗅自己的腋窝和衣襟,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香水,但是没有用,那股味道遮掩不掉,如狗皮膏药一般缠着她。
无论多冷的天气,她都喜欢站在寒风之中,敞开衣襟,试着散散身上的味道。有一次她特地去坐摩天轮,在到达最高点时脱下外衣,撩起衣襟,张大嘴巴,希望风最大限度地灌进体内。但是没用,那一天,在狂风的帮助下,她觉得自己的味道被散播到了全城,整个城市都散发着浓郁的腥气。
一年之后,陈雪接受了现实:除了自己,这座城市没有意愿与海发生任何关系。这个世界上竟然有地方真的看不到海,从前的陈雪不能够相信,更不能够想象。无论爬多高都看不到海,别说三层楼,就是三十层楼也没用,哪怕你飞上天去。这个地方的大楼后面没有海作为背景,这个地方的山丘后面没有海作为背景,这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涛声,这里的人身上没有海风的腥气,这里的沙子一点湿意也没有,空气中一点水分也不含。
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她时刻受到这个念头的折磨:没有海,没有海,这里没有海,不论你放学之后走多远,你都走不回海边去。
夜幕降临的时候,腥味会加重,空气会变湿润,她会有种短暂地回到海边的错觉,她会看到海边的渔船、亲人、伙伴,想到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和她有娃娃亲的男孩儿或许已经成了家,或许已经死了。忧伤之中饱含愤怒,她不认为这是公平的:世界上有的地方有海而有的地方没有,有的人出生在海边而有的人出生在内陆。她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出生在海边而承受失去海的痛苦。
“我不想念大学了,我要回去帮你们卖鱼……”她打电话回家。
“雪呀,村子里多少年出了一个大学生,怎么能说不念就不念呢?你要是缺啥跟爸妈说,多出两趟海就有了……”
热心市民说,幸好他在宽阔的河水中捞起陈雪的尸体,不然她就要漂到海里去了。
陈雪留下了一封遗书,说她投水不为别的,就因为一种皮肤疾病,一种干枯,一种难以名状的焦虑,还有一分对于世界真实性的疑问。陈雪,一张沉入海底的可爱脸庞,憔悴但是红润,人家说那是典型的陷入爱情的少女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