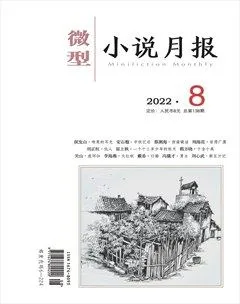远山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有哪儿不对劲儿。
“我跟你妈想回老家住一段时间……”一天吃晚饭时,退休没多久的父亲突然对我说。
老家有五间闲置的老房子,还有一个宽敞得有些空旷的大院子。父母亲进城后,那个院子,一年也回不去几天。
而我以为,父母已经老了,几个儿女都已成家,孙辈们也都上学了,他们应该在离儿女近的小区,过一过不用定闹钟、不必顶风冒雨的缓慢自在的晚年生活了,谁承想,他们要回老家。
住不惯城里的高楼,找回乡野的烟火气息也挺好。老家不远,开车一个多小时就能到。想象一下,房前屋后,花香缭绕;朗朗夏夜,星月入怀;邻里守望,乡音萦耳;举目远山叠望,回首鸡犬相闻。当真是一派田园悠然。
“那行吧,但天冷了,你们就得回市里啊……”我话没说完,父亲似早有准备,一个劲儿地点头。
很快,我就感觉哪里不对劲儿了。
父母搬回老家两个月后,一个周末,我回到老屋时,父亲竟然正一脸灰地和母亲在院子里搭鸡窝呢。旁边,一个纸箱里,十来只从集上新买的绒球般的小鸡叽叽喳喳地叫得正欢。其实,刚搬过来没几天,父亲就把院子分成一个又一个规规整整的菜池子,再分别种上不同的蔬菜。这哪里是过来体验乡村生活,分明是要在老屋重新扎根了。他们坚持不用化肥,只给院子里的蔬菜施用农家肥。也不用一滴农药,一旦蔬菜生了虫子,母亲和父亲便用手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除虫,有时蹲在院子里,一蹲就是小半天。
我仿佛已看到满院成片的绿色,仿佛看到时不时隐藏在脚下某地圆圆的小南瓜、夺人眼目红红的西红柿,还有成片成片或长或扁的豆角、成串成串或青或红的辣椒……
秋凉的时候,父亲不仅半个字不提回市区,而且还张罗着买煤过冬了。“不是说好了回市里过冬吗?再说了,这菜地冬天也不用人管啊。”我气恼地问。
父亲不慌不忙地笑着:“那哪行啊,这些鸡啊鸭啊都得有人管。再说了,房子住了人就不能空着……”
很快,我越来越感觉不对劲儿了。
“明天来,给我取五千元钱,我得买台车。”一个周五,父亲打电话给我。
我一下子警觉起来。父亲是老司机,在单位开了半辈子车,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车啊,我是开得腻腻的了。这辈子都不想再碰了”。父亲还一直以自己开了那么多年车,零事故纪录为傲。“你要去哪儿,我开车带你去啊。我不是每周都回来吗?你还买车做什么?”父亲反驳:“你那车在农村能干啥?能上山吗?能拉柴吗?”
我又疑惑了,五千元钱,能买啥车?据我所知,再一般的二手车,五千元钱也买不下来啊。我知道有汽车下乡政策,难道优惠力度这么大吗?
很快,父亲便兴高采烈地从乡里的农机销售点儿开回来一辆单缸发动机的农用三轮车。从此,用他那半辈子积累的娴熟驾驶技术,在山岭上、河沟里驰骋,父亲大脚轰着油门,身后扬一路烟尘。
等到第二年春天,父亲竟然跟村里人借来两块地,一块种上了花生,一块种满地瓜。农用三轮车的真正用途随即显现出来。父亲用它载着耕地机下田打垄,开着它去邻村买回一袋袋化肥……到了秋收时,又一趟一趟把收获的花生和地瓜,甚至是邻居们成堆的玉米秆尽数运回院子。
三年中,我们家在农村过了三个春节。那时,院子里铺满了厚厚的白雪,大红的灯笼在大门两旁的门柱顶悠闲地晃着。热气腾腾的屋子里,火炕上摆着一大桌热气腾腾的酒菜。我突然发现,在城市里有些虚胖得发白的父亲,又变成了一个粗黑的汉子。他的手上生出了老茧,他的腰虽有些弯曲,目光却更加锐利。
“接下来呢?”我问父亲。
父亲望了眼窗外市区的方向:“你们年轻人继续在城市里打拼吧。我和你妈啊,哪儿也不去了,就守着这片青山绿水。”
选自《辽宁日报》
2022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