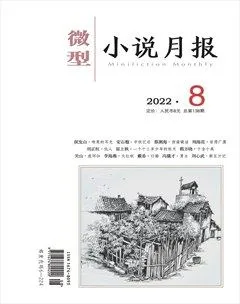将离
碧玉穿上白色旗袍,站在镜子前打量起自己。镜子金色的边缘已经有了斑斑点点脱落的痕迹,看上去像是一块发了毛的毯子。碧玉偶尔会在镜子边框上摸一下,脸上显出一种心疼的表情。镜子里的人亦没了从前的模样,碧玉头脑里闪现出那些往日时光。
旗袍是很早以前的,米白色的,暗黄色的绲边,胸口是手工的蝴蝶花扣,米白色与黄色相间盘制而成,看着如同一只蝴蝶落在上面。碧玉在镜子前站了很久,直到太阳懒洋洋地从窗外爬到镜子前,她才挪动了脚步。
那时,我只有十岁,祖母经常带着我去碧玉家。每次,祖母牵着我的手,总要再三地叮嘱我,见到了你碧玉姑奶奶,不要乱说话,记住,你说了不该说的话,她会伤心的。
她为什么会伤心呢?
祖母听到我的问题,总是长叹一声,那声悠长的叹息伴着脚步踏在青石板的小路上,被抛在小巷深处。
祖母带我去碧玉家的时候,通常是在晚饭后。那时,推开漆黑的木门,满院的花香便扑鼻而来。走进院子,就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花园里,院子里盛开的只有一种花:芍药。夕阳的余晖,在那些红色的、白色的、粉色的芍药花上,像是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那时,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居然有这么美丽的花,层层叠叠的花瓣围着黄色的花蕊,那花朵散发出高贵与优雅的气息,如同一个个打扮得雍容华贵的女子。
碧玉总是拍拍我的头,然后我们就会在院子里坐下,那里有一个小小的亭子,摆放着一张小木桌。
碧玉最爱芍药盛开的时节。那些天,她每天都是早早地起床,对镜梳妆之后,来到院子里。芍药从四月下旬开始,陆续开放。不同种类的芍药,花期与开放的时间也有所区别,这样断断续续地开到六月。那些日子,碧玉的脸上都会带着笑,她每天都会穿着旗袍,在院子的芍药花之间穿梭。
永平府的春,总是来得晚。往往到了三月,才会有小草歪歪扭扭地从地里冒出头。年幼时,我觉得碧玉是一位从芍药花丛中走来的仙子,尤其是她穿着白色旗袍的时候,脚上通常穿着一双白色的皮鞋,五寸左右的鞋跟。她看似轻描淡写地走在院中的芍药花间。我从没有见过她散开着头发,她的头发总是盘在脑后,然后会在上边插一支步摇,不管是何种材料所制的,那上边也一定会有一两朵芍药花。她走路时,脑后的步摇也会如蜻蜓点水一般地摇曳。不知何故,祖母总会在那样的时刻,不合时宜地长叹,那一声悠长的叹息中,似乎透露出她的悲凉。
碧玉偶尔会在花丛间回头,说,二嫂,你不要叹气,你一叹气会把花吓得不敢开了。
祖母苦涩地摇头,似乎找不出话来回她,只能说,你当那花是妖啊,你二哥说得没错,你是入魔了。碧玉也不恼,看着满院的芍药花说,每一次花开,都是将离来看我了。
每一次,这句话像一枚无声的炸弹,在这个小院里默默地释放着挥之不去的悲凉。这氛围与绽放的芍药花格格不入。祖母不说话,她默默地抹着眼泪。回去的路上,祖母便是漫长地沉默,她紧紧地拉着我的手,一脸悲伤的表情。那时,夕阳正在永平府的城门楼上缓缓退去。
芍药虽美,但在永平府却少有人在家中种植,偏偏碧玉在院子里种那么多,自然招来很多非议。哎哟,芍药可是喜阴的,那都是长在寺庙里的,好端端的人家谁种那个啊!打扮再漂亮有什么用呢,还不是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日子。
一开始,这些话还只在背地里传,说得多了,那些人便不再回避,即使路过碧玉家那扇紧闭的门,也会毫不避讳地发出几声闲言碎语。院内的碧玉,那时一准儿在芍药花间流连,那些话真真切切地传进了她的耳朵里,她却如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脸依然贴在一朵芍药花上,闻着那淡淡的清香,一副沉醉的样子。每当这时,碧玉的记忆便情不自禁地穿越到几十年前。
一九四〇年六月,日伪军疯狂扫荡丰滦迁地区,在迁安县二拨子战斗中,身为队长的刘将离,为保护战友转移冀东军区的重要文件牺牲了。那年,刘将离二十三岁,碧玉二十一岁。刘将离出身当地的大家族,少年时受革命思想影响,投身到抗日队伍中。碧玉依旧记得,他们新婚不久,将离从冀东革命根据地的柳河北山基地归来时,为她带回来一株山中挖来的芍药根,他说,在《诗经》中,芍药也叫将离。于是,他们一起将芍药根埋到了小院中。
沉默了一会儿,将离望着远方说,现在形势危急,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你一定要替我看着咱们的国家强大起来,替我好好地活着!
刘将离牺牲的噩耗传来后,碧玉躺了半个多月,睁眼闭眼都是他的影子。祖父祖母强行把她从床上拉起来时,透过敞开的门,她看到那株芍药居然开出两朵红红的花。
二〇〇七年五月,九十二岁的碧玉迎来了生命中最后一个芍药花开的季节,在满院的花香中,她呼唤着他的名字,手抚鲜花寻找她的将离去了。
二〇〇七年九月,在冀东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我望着墙上刘将离的照片,眼前浮现出的是碧玉和那满院的芍药花。
选自《天池小小说》
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