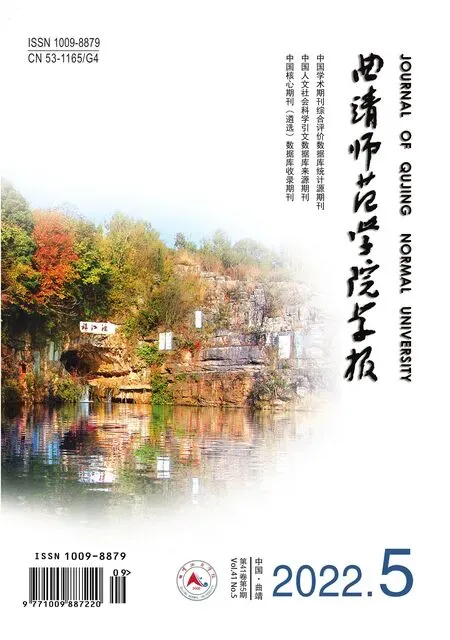论西晋亲情诗兴盛的原因
陈志刚,陈威元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
我国诗歌批评一直没有将亲情诗作为一种专门的诗歌类型看待,原因很多且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亲情大多只作为一种抒写元素存在于其他诸多类型的诗歌中,如爱情诗、思乡诗、战争诗等,文论家们可能都认为没有必要单独提出亲情诗这个概念。然而,我国悠久的古代文学史告诉我们,在古代文学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个持续的亲情抒写传统,甚至在有的历史时期还涌现出亲情抒写高潮,如西晋(265年—317年),就出现了亲情诗异常兴盛的局面。因此,中国诗歌史是很有必要提出亲情诗这个概念的。那么,什么是亲情诗?亲情诗为什么会在西晋兴盛呢?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研究讨论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这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西晋文学,而且还可以让我们更完整更深刻地认识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轨迹以及其中的一些重要节点,古人囿于时代(如长期的封建社会)、自身局限(如儒家士大夫身份)没有正视这些节点,今人却有机会、有必要揭示这些节点所包含的诗歌史意义。
本文所说的亲情诗不包括那些虽含有亲情元素却没有集中、突出亲情抒写的诗歌,而是指比较集中、突出抒写基于血缘关系之上的情感的诗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夫妇间没有血缘关系,但是相濡以沫的生活实际上培养了不是血缘胜似血缘的情感,故抒写夫妇情感的诗歌理应为亲情诗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历史,亲情抒写始于《诗经》,经“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1]的两汉,历曹魏时期家庭亲情抒写诗歌的曲折发展,至西晋,士人在个体(私人)场域爆发式地以诗歌抒写亲情,西晋亲情诗在西晋得到兴盛。西晋士人以诗歌真情抒写回归凡俗的家庭亲情[2],在“私制”中寄情、自慰、疗伤,思家念亲,以之寻求心灵的宁静,以之体味人生的艰辛,以之积蓄生活的勇气。他们以诗歌进行亲情抒写的创作实践无意间促成了中国诗歌史上亲情诗这一全新诗歌类型的形成。西晋亲情诗以汉末建安肇端的强烈个性意识和生命意识为思想基础,涵盖日常家庭的种种亲情,超越了前代那些仅仅包含亲情元素的诗歌,展现出独特的情感深度和力量。归纳起来,西晋亲情诗的亲情抒写包括如下家庭亲情:夫妻之情、父子之情、父女之情、兄弟之情、兄妹之情、叔侄之情等。西晋亲情诗的数量亦很可观,西晋文坛一流二流诗人均有亲情诗传世,较为著名的有:潘岳《悼亡诗三首》《杨氏七哀诗》《思子诗》;左思《娇女诗》《悼离赠妹诗二首》;陆机《赠弟士龙》《与弟清河云诗》;陆云《答兄平原》……对西晋亲情诗的思想情感和艺术特色,笔者将另行撰文研讨,在这里,本文拟集中探析西晋亲情诗兴盛的三个主要原因:政治环境、儒学的变异和诗歌自身的发展。希望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一、政治环境对亲情诗兴盛的影响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清代赵翼《题遗山诗》),西晋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起到了促使士人回归家庭亲情的意外的作用,西晋诗歌的亲情抒写由此大量增加,竟至成就了专门的亲情诗类型。
西晋在实现短暂统一并逐渐走向稳定繁荣后,晋武帝在晚年陷入骄矜昏昧的精神状态,糊里糊涂地选择“白痴皇帝”晋惠帝接班,终于导致“太康之治”稳定繁盛局面的恶化。“贪鄙、淫僻之风”[3]自上而下弥漫整个社会,西晋政权陷入皇室、诸王和外戚此起彼伏的权力争斗之中,因政治斗争被杀的著名文人之多在我国历史上亦属少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西晋)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4]太多西晋诗人在诗歌风格即将成熟的时候,遗憾地丧命于纷乱动荡的政治权力争斗,如张华、陆机、陆云、潘岳等。可见,西晋政治环境之凶险、恶劣是历朝历代中比较突出的,初唐史臣编撰的《晋书》记录了许多身陷政治漩涡的士人的悲剧命运。在西晋恶劣凶险的政治环境中,形成了以下三类士人:一是仍然留恋功名利禄的士人,他们在官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们虽未回归家庭亲情,但家庭亲情显然是他们仕途受挫后的精神抚慰,如张华、陆机、陆云等;二是随波逐流的士人,家庭亲情成为他们寻求个体价值平衡的避风港,如潘岳等;三是为了保身全生而毅然退出官场的士人,他们理性地选择回到故乡、回归家庭亲情,如左思、张翰、顾荣、戴若思等。可见,西晋士人面对恶劣政治环境时的选择各不相同,但家庭亲情在他们后期的生活中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我国历史上,也有因为政治黑暗而促使士人多方选择的时期,但都不像西晋表现的如此激烈。举一则《世说新语》的故事为例,《识鉴》载: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谓为见机。[5]
张翰遽然放下仕途名利,决定回南方老家过自由自在的生活,这固然是当时身处凶险恶劣政治环境中大多数士人的想法,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有张翰面对功名时的那份率性和洒脱,大概由于西晋士人多濡染玄学,很多就是“魏晋风度”的践行者,而后世许多士人面对恶劣、黑暗政治时更多的是受儒家“独善其身”的思想的影响。《世说新语˙识鉴》引《文士传》云:“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张翰劝动了顾荣,可顾荣没能劝动陆机,不能不说陆机主要受儒家思想影响,他光宗耀祖的欲望是很强烈的。《晋书˙陆机传》载:“时中国多难,顾荣、戴若思等咸劝机还吴,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从。”[6]同为东吴“南金”,顾、戴目睹“中国多难”的政治现实,以乡人之谊劝说陆机退隐,可陆机自恃才高而不听,后竟祸及其弟陆云和陆氏子侄,此真令人扼腕叹息!从陆机“羁寓京师,久无家问”而依靠“骏犬”“黄耳”传送家书的记载来看,他其实是一位挂念家庭亲情的重情之人,可家世祖德的荣耀驱使着他,让他不惜性命游走于危险的西晋官场。由此可见,在西晋恶劣凶险的政治环境中,主动回归家庭亲情确为明智之举,而那些将生命寄托诸王以谋求功名利禄的固执士人是多么愚蠢啊!“命驾便归”的张翰从处处充满凶险的政治环境中果断脱身,回归故乡、回归家庭、回归亲情,从此与那个时时需要提防、伪饰的西晋朝廷诀别。“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士人回归家庭亲情后,生活的世界发生了改变,诗文抒写的内容也随之出现了变化,过去不太可能大量而集中进入诗歌的亲情因之遽然增多。与此同时,那些混迹官场时违心创作的歌颂酬赠的诗歌在不断减少。
在西晋充满危险的恶劣政治环境中,士人普遍抛却儒家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回归卑俗而真实的生活,卸下社会责任、转向崇仰玄佛、肆意张扬个性、大胆表现个体欲望的人生选择,士人思想、人格的这些变化促使他们回归家庭亲情。有的士人较为彻底地回归家庭,有的士人在虚与委蛇的官场生活中同样展现着家庭亲情世界中才会显露的真性情。因为西晋士人多样的人生选择和多方回归家庭亲情,所以诗歌第一次具有了全面深入触及士人个体家庭亲情世界的可能。事实上,西晋士人以实际的诗歌创作记录家庭的真实生活、情感,抒写亲人之间的挚爱深情,慰藉个体的卑俗人生,彰显诗歌抒情的广度和深度。西晋士人以诗歌抒写家庭亲情的这份亲切感、真实感、卑微感令后世读者无比动容,不期然而然地开创了以诗歌集中抒写家庭亲情的先河。
在西晋恶劣、凶险的政治环境中,士人大概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退隐,如张翰、左思;另一种是继续为功名及绑架在功名之上的个人价值而挣扎,如潘岳、陆机。前者诗中的亲情抒写成为自由自在家居生活的一部分,透露随意、自然和纯真的情趣;后者诗中的亲情抒写仍在仕与隐之间挣扎,是诗人身处凶险政治环境中的寄托和抚慰,充满无可奈何的悲情和痛楚,在情感上呈现不能解脱不能释怀的紧张。二者也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两种生存情境中的亲情抒写都是真情的流露,都是士人向个体家庭世界的回归,也可以说是受伤的个体向家庭亲情的求助,只不过前者是身心合一的回归,后者的回归基于身心分裂基础之上。试以张翰、陆机的诗对比如下:“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张翰《思吴江歌》)[7]“羁旅远游宦,讬身承华侧。抚剑遵铜辇,振缨尽祗肃。岁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载离多悲心,感物情悽惻。慷慨遗安豫,永叹废寝食。思乐乐难诱,曰归归未克。忧苦欲何为,缠绵胸与臆。仰瞻凌霄鸟,羡尔归飞翼。”(陆机《东宫作诗》)[8]两首诗都写于仕宦之时,都向往回归家乡过隐居生活。不过,张翰践行了隐退的想法,而陆机却始终没有隐退,陆机诗歌就是功名利禄与人格自由矛盾煎熬的产物,其身心分裂之痛苦尤为明显。由于陆机的人生总是处在政治与亲情的博弈中,故其亲情诗充满悲情。
总之,当士人面对西晋恶劣凶险的政治环境时,他们都无一例外的要在仕与隐之间作出抉择,不论是选择继续出仕的士人,还是及时退隐的士人,都为西晋诗歌亲情抒写量和质的变化打开了一扇窗子。所以,恶劣的政治环境是西晋亲情诗兴盛第一重要的原因。
二、儒学变异对亲情诗兴盛的影响
除了政治环境,西晋亲情诗的兴盛深受西晋社会思想的影响。西晋前期统治者对思想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后期统治者深陷内忧外患而无暇顾及对思想的管控,因此,西晋儒学、玄学、佛学、道教等思想得到自由发展。佛学、道教是宗教,其在本质上排斥亲情,儒学提倡忠孝等伦理道德规范,是亲情得以维系的原始思想,玄学吸引着许多对儒学失去信任的士人,儒玄结合的思想比较能激发出士人的真性情。总的来看,西晋儒学变异是西晋诗歌亲情抒写兴盛的思想基础。这里主要讨论变化了的西晋儒学与亲情诗兴盛的关系。
首先,西晋儒学一边导致士人在官场等公共场域的虚伪性,另一边催生士人在家庭等私人场域的真实性,但主要还是促使西晋士人真诚面对家庭亲情。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倡导“以孝治天下”,然而,这只是司马氏的统治策略而已,自汉末即已式微的儒学思想不可能在西晋复兴。事实上,司马氏打着儒学旗帜干了许多违背儒家礼义的事情,实际上助推了虚伪、矫饰、纵诞等士风的形成,造就了一大批西晋式的虚伪礼法之士,比如何曾。徐公持先生指出:“要之西晋一朝儒者,笃行体道者少,而德行堕落者多,一如阮籍所深恶痛疾的‘礼法之士’那样,风气败坏,伪饰成习,影响儒学的素质及整个社会道德状貌。”[9]一些士人痛感儒学的衰颓和浇薄的世风、士风,或正面批判,或退隐家居著述自娱。左思早年攀附贾谧,应其请而讲《汉书》,预“二十四友”之列,然与其“家世儒学”“不好交游,惟以闲居为事”的本性相违。贾谧被诛后,左思“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10]。如果没有这次坚决的退隐,就不会产生著名的《娇女诗》,《娇女诗》的亲情抒写离不开隐退家居这样特殊的个体生活环境。
同样,潘岳溢满深情的《悼亡诗》离不开儒学丧制。“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改服从朝政,哀心寄私制”,这表明,潘岳在为妻子守丧期间是不能任职的,只有守丧期满,他才能赴朝任职。因此,儒学礼制不期然而然地促使西晋亲情诗的兴盛。假如没有儒学礼义的影响,潘岳就丧失了创作《悼亡诗》的环境和心境。
上面为儒学对亲情诗的正面影响,然而,西晋儒学的变异对西晋亲情诗的影响更深刻、更全面。西晋儒学日益式微,这使西晋诗歌关注社会民生疾苦的现实题材大为减少,抒发个体人生理想的意识明显淡漠,诗坛盛行赠答模拟之风,士人以诗歌炫才耀博,诗风愈来愈朝着绮靡的方向发展。儒家“兴观群怨”“观风知政”“发乎情,止乎礼义”等传统的诗歌主张被遗弃,“缘情而绮靡”的诗歌思想和审美标准取代了“诗言志”,诗歌在形式主义道路上肆意驰骋。西晋诗歌的宏大主题少了,而日常生活的主题愈来愈多。有研究者指出:“西晋诗人处理的一些题材,都是相当世俗日常的题材。”[11]西晋诗歌的这个特点正好给亲情诗的兴盛创造了条件,亲情诗意味着士人个体世界首次被自觉而充分的发掘和关注。
儒学思想熏陶养成了士人真挚的私人情感,这在他们面对家庭亲情时的态度和选择中得到更加鲜明的体现。陆机“伏膺儒术,非礼不动”[12]。左思“家世儒学”[13]。潘岳“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内史”。[14]由上可知,西晋士人自幼深受儒学思想影响,打下深厚的儒学根底,涵养了醇厚的儒家人格,虽然许多士人后来转而崇信玄学或佛学,但幼年时期建立的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还是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情趣爱好和精神追求。事实上,在西晋儒家思想衰颓及儒学被作为工具而庸俗化的大背景下,士人早期所受儒家思想熏陶而养成的真诚品格反而得到激发显现。以此品格面对家庭亲情及创作亲情诗,遂展现了个体情感世界真挚动人的面相。
西晋儒玄结合的思想特征也深刻影响了士人的人生选择和情感走向。西晋郭象玄学欲会通儒道,然而遭遇司马氏虚伪残暴的统治,再加上西晋社会中后期的动荡不安,儒道不但没有得到会通,原先的思想品质反而被减弱降低,有时不免沦为权力争斗和欲望满足的工具,儒道两家的反思批判精神不断弱化,最终变得相当世俗化。西晋世俗化的儒家思想从而推动文学向世俗、凡俗回归。西晋士人儒玄结合的思想为西晋文学撕开一条家庭亲情抒写的狭窄缝隙。其实,这种社会风气极度衰败后人们心理、情感的正常反弹根源于变异的儒家思想。在西晋,你会经常看到一种特别矛盾的现象:违背传统儒家“忠”“孝”品德的士人竟然对家庭亲情那么在意!
西晋玄学提倡“名教即自然”,摈弃王弼、何晏、嵇康、阮籍为代表的正始玄学的批判精神,朝着儒玄交融的方向发展。儒玄交融的思想促使西晋士人形成与现实妥协的作风,这为士人准备了回归家庭、亲情的思想基础。《晋书˙文苑传˙张翰传》载:“翰任心自适,不求当世。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时人贵其旷达。性至孝,遭母忧,哀毁过礼。”[15]既“纵适”“旷达”,又“至孝”“过礼”,儒玄交融,这正是西晋士人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但又在后来的人生和现实中看到、感受到儒家思想的变异,甚至有的士人打着儒家旗帜干满足私欲的勾当,他们遂进行新的思想组合和选择。余英时先生指出:“尤可证(魏晋)儒家的名教已不复为士大夫所重,无论是在父子或夫妇之间,亲密都已取代了礼法的地位。”[16]在社会思想如此复杂、变化的情况下,士人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向着世俗“穷则亲情相伴”转变,个体家庭世界中的“以情代礼”(余英时先生语)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时髦了。
总之,西晋统治者提倡的儒学充满虚伪,士人自幼学习的儒学体现真诚,儒玄结合的思想没有找到政治出路,反而引导儒学走向世俗和日常。西晋儒学这些变化为诗歌抒写亲情提供了思想上的条件。
三、亲情诗兴盛是诗歌自身发展的结果
从西晋诗歌的内容来看,政教伦理等内容急剧减少,非政教的内容在日益增加,诗歌的天秤向着个体家庭亲情抒写倾斜,这是诗歌自身发展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徐公持先生认为西晋文学是“非政教主导型文学”[17],这是符合西晋诗歌实际情形的。
先从西晋之前诗歌发展历程的角度来看。从先秦至汉末,中国古代诗歌遵循“诗言志”的政教伦理传统,写作目的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诗歌中的个体情感,尤其是潜隐且不易吐露的情感是不被认可的,诗人们大都不敢冒着舆论的危险逆“诗言志”传统而行。汉末大帝国解体,儒家学说的权威开始动摇,士人思想走向多元,情感自由了,兴起了感叹生命短暂、羁旅漂泊的个体之思,这集中反映在《古诗十九首》里。由《古诗十九首》肇端的诗歌个体抒情理想进一步在三国魏初的诗人创作中得到继承和弘扬。魏初诗歌抒情性高涨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曹氏父子思想通脱、热爱文艺;二是频繁的战争和肆虐的疾疫破坏了社会正常生产生活,人们普遍产生了异常强烈的生命意识,推动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西晋统治者提倡儒家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寻求政权统治的合理性,其意并不在复兴儒学,反倒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种虚伪、奢靡的世风、士风,诗歌的个体性、抒情性有所减弱。然而,西晋士人在公共空间的虚伪并没有完全掩盖自汉末即已兴起的个体生命意识,他们的个体生命意识改变流向突出体现于他们的私人生活和空间,而家庭亲情是私人生活和空间的主体情感,尽管它极普通、平凡。从西晋文学的创作实际来看,西晋文士多以诗文记录、描写个体化、私我化的生活和情感,如潘岳善为哀诔文、左思写娇女、“二陆”的诗歌酬赠和写作技巧探讨等等。可见,西晋亲情诗的兴盛的确是我国古代诗歌自身发展演进水到渠成的结果。
再从西晋诗歌的形式技巧角度来看。西晋诗歌越来越趋于辞藻华丽,追求“形似”,形成一股竞相模拟之风。当西晋士人厌倦了过去那些传统题材后,他们自然乐于尝试将一些新题材作为驰骋文才的试验场,一些新鲜题材就伴随文学注重形式技巧的风潮应运而生。《世说新语˙文学》曰:“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18]这是在诗歌模拟之风盛行背景下产生的家庭亲情抒写的典型例子。可见,当这种全新的极其重视文学形式美的写作风气遇到合适的诗歌题材的时候,不仅会推动诗歌新题材的产生,而且诗歌的整体品格和精神也会得到改进和意想不到的提升,西晋亲情诗正是诗歌在形式技巧上寻求发展突破时产生的一朵诗歌奇葩。后世学者几乎一致将西晋亲情诗这一重要的诗歌自身发展成果连同西晋形式主义文风一同倒掉,或者说,西晋亲情诗的独特贡献被弥漫诗坛的形式主义风气遮蔽了。然而,放眼整个文学史,这对西晋诗歌是不公平的。西晋士人普遍倾向创作赠答、模拟之作的主要目的是维护现实人际交往、学习前代文学遗产、寻求个体进身之阶,大多缺乏真挚的情感,呈现攀附、阿谀的雷同面貌。模拟诗多为学习前代作品之辞,从某种程度上说遗落了前代作品真正的意趣、精神,这是西晋文士迎合时代尚博学风而形成的炫才耀博的创作习气。然而,当他们厌倦了名利场的阿谀逢迎和尔虞我诈后,他们其实渴望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感受真诚、真情和温馨,当然也能获得精神的放松和畅快。因此,西晋形式主义诗风间接推动了亲情诗的兴盛。
最后从西晋文学总体特征的角度来看。西晋文学缺乏崇高感、使命感,其沉沦平庸恰恰可能回归凡俗。徐公持先生指出,西晋“殊难产生内容深厚、气魄宏大、精神崇高、辞采瑰丽的伟大作品,亦难涌现人格高尚、文品超卓的伟大作家”。[19]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鄙薄诗歌亲情抒写的阻力减小了,亲情终于有了进入诗歌的顺畅通道。从这个角度上看,西晋亲情诗无疑创造了也许更有温情、更有个体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诗歌历史,尽管它并不那么宏大,但可能更能彰显西晋一代士人复杂而艰辛的心路历程。
总之,从西晋之前诗歌的发展历程、西晋诗歌注重形式技巧的风气和西晋文学的总体特征来看,西晋亲情诗的兴盛正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西晋恶劣的政治环境迫使士人回归家庭、面对亲情。西晋儒学变异让一些士人养成关注日常人伦情感的真诚品格,儒玄结合的人格自觉抵制将儒学作为工具的虚伪,更加容易养成士人真挚的情感,这为西晋诗歌亲情抒写准备了思想条件。西晋之前诗歌的发展历程、西晋诗歌的形式之风和西晋文学的总体特征冥冥中催生了诗歌亲情抒写在西晋的兴盛。当然,西晋亲情诗的兴盛是在这些原因综合作用下才形成的。西晋诗歌愈来愈重视家庭亲情,承续了汉末魏朝开创的诗歌的抒情性,真挚地记录属于私人生活空间的家庭亲情,艰难地维系着、丰富着我国古代诗歌的抒情传统。经过士人们不断地写作实践,西晋亲情诗不仅充满强烈的个体抒情色彩,而且使诗歌中的亲情元素从政治、伦理道德、哲学等的附庸地位独立出来,甚至过去一些传统的诗歌主题反过来为亲情抒写助力,西晋诗坛最终形成“为情造文”的独立亲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