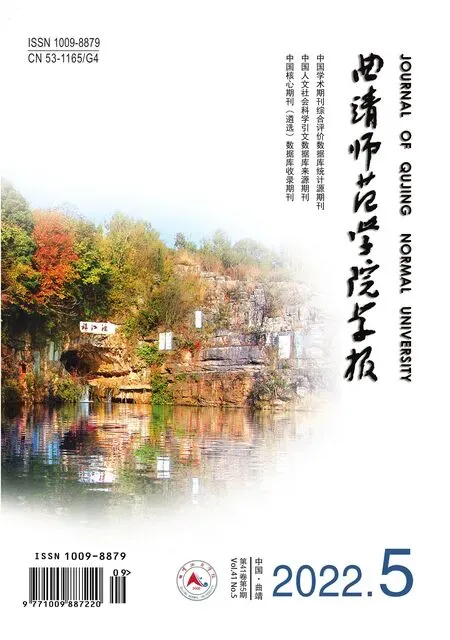论电影《青蛇》的奇幻空间及其意义建构
王淑苹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福建 福州 350202)
关键字:影视艺术;《青蛇》;徐克;奇幻空间;意义建构
“奇幻”(Fantasy)文类虽肇始于西方,但在中国,自古以来也不乏奇幻叙事。《白蛇传》是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成型于明冯梦龙的《警世恒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通俗短篇小说。
徐克电影《青蛇》改编自香港通俗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对于蛇妖恋的故事又进行了重现演绎和诠释,摆脱了故事陈旧的叙事结构和道德训诫,在文本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第二世界”,他们也成为了“次创造者”。电影《青蛇》从类型上属于奇幻仙侠片,“表现神、仙、妖、魔的情感故事和正邪较量为主要内容,主人公大多具有超自然能力,在艺术风格上充满非写实的瑰奇浪漫色彩。”[1]“魔”或者“妖”,是奇幻故事中想象出来的、有别于人的异类生命形态。妖魔想象,一方面源于“万物有灵”的原始认知,另一方面来自于人对自身潜在欲望、阴影、邪佞的心理映射。“奇幻就取决于我们认为的真实,它是真实与不可能的冲突。”[2]
“第二世界”(The Secondary world)是托尔金在《论仙境故事》中首次提出的,这一世界指的是作家创造的脱离现实经验世界的文本世界。它相较于现实存在的“第一世界”(The Primary world)而言是一座想象中的世界,但“这个想象世界绝非什么美丽的谎言,而是另一种真相”[3]。虚构是真实的一种折射。第二世界通常是一个架空世界,这个世界拥有自己的一套历史,拥有自己所在的空间地域,而奇幻首先表现为这个架空世界的空间想象。包亚明认为,空间不是自然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它是社会的产物,“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4]。电影首先是一种视觉建构,视觉的主体部分就是空间的建构。在奇幻电影中,空间的建构总是通过隐喻或者象征的手法达到意义的表征。《青蛇》就用更为瑰丽奇幻的想象来建构了这个“第二世界”,改造原有的叙事空间,对空间进行重构,从而表达了导演徐克对于欲望、人性的另类解读。
一、共生奇境的建构
(一)“江南”——神人鬼妖共生的“第二世界”
托尔金在《论仙境故事》谈到:“上帝创造‘第一世界’,童话奇境就是人类创造的‘第二世界’”“故事创作者被证明是成功的‘次创造者’。他造出了一个第二世界,你的心智能够进入其中。他在里面所讲述的东西是‘真实的’,是遵循那个世界的法则的。因此,当你仿佛身置其中的时候,你就会相信它。”[5]架空现实,展现人、神、妖、魔共生的世界,是古今奇幻故事惯常的时空设定。《白蛇传》的故事并不是架空世界背景、与现实相距遥远、甚至完全隔离的第二世界。不是托尔金《魔戒》的“中土世界”。而是裹挟在现实世界之中的“第二世界”。这个世界不需要什么入口,因为它就潜藏在现实世界的某一个隐秘的角落。白府后花园有一座铁桥,当白府被法海显现原型的时候,铁桥成为人间与妖界的最后桥梁,经由这道桥梁,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不仅相互裹挟,同时也有了出入口。
在“江南”这个世界中神、人、鬼、妖同处共存,并行不悖,当然有时也会互相干扰,人间有人间的秩序,而神界有神界的戒律。神、人、鬼、妖,各有等级次序,神最尊,人次之,鬼妖最次,为低等生物,被认为应该去除或者隔离。不同生灵之间不能交媾、更不能成婚。但是,低等生灵可以通过修炼,或者接触仙界的象征物(佛珠),来跨越种属的界限,实现阶层的晋升。这个神人鬼妖共生的“第二世界”正是等级分明、阶层严密的现代社会的表征。而对于鬼妖的歧视观念也是对于现代社会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表征。在这个世界中,法海认为“人就是人,妖就是妖,神人鬼妖四界,等级有序”(电影台词)。所以在电影开场第一幕中,面对兽脸人身、面目狰狞的人以及丑陋暴露无遗的人性,法海没有任何杀之而后快的冲动,反而将修炼百年的善良的蜘蛛精,镇压亭底,使其百年道行功亏一篑。“神人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其它次等生灵作为“他者”,被标签化、物化、规训。
在电影中,叙事的场域就是“江南”,这个“江南”既有复制现实的部分,如乞巧节放花灯、端午节喝雄黄酒等,同时也有许多想象的部分,比如古代书院一般设置在远离闹市的山林僻静之地,而电影则将书院设置于闹市妓院之旁,雅俗并置,使学子春心荡漾,情欲萌发。同时电影也架空了故事时间,何时的江南,观众无从知道。现实与虚构交织、神人鬼妖并行的“江南”上演的故事也就更能吸引观众,引发想象。
(二)“白府”——情爱本能释放的自由空间
“白府”是白娘子与小青居住宅邸,是白蛇使用法术变出来的一个虚幻空间。它模拟的是钱塘富裕人家家宅的模样,有院落,有花园。位置较偏,远离尘嚣,与道德规训较多的人间隔开距离。白娘子与许仙在此结合,无拘无束享受情爱的美好,青蛇也在此学习人的欲望与情感的功课。
白府的空间设计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开放性与通透性。电影在布景时,偏向于简约化,江南府衙被化约为大厅(与各个卧室连为一体)和花园两处,大厅只用几扇门隔开几个房间,甚至没有所谓的“门”,只用了一些网纱和屏风,房间之间彼此打通。青蛇、白蛇、许仙在这里穿梭往来,游弋自如。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宅院,通常包括好几个院落,面积大,几进几出,房间多,房间之间通常都是严格隔断的,以保留一定的私密性。此外,进出宅院也讲究礼法秩序,并不是可以随意穿行的所在,空间是有等级秩序的。而徐克的电影中,江南的家宅完全没有了空间的阻断,也没有空间的规定性,礼法秩序、道德规训全部被破除了,“白府”通透、敞亮,花园荷花绽放,绿树繁花,生机勃勃。白府显然是做了“美化”处理,居住其中的人仿佛进入幻境。对比电影中其他几处空间,比如古代书院,就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书院并不美好,反而显得单调乏味。空间的特点映衬的是居住其中的人的特点。白府的通透敞亮、如梦如幻,映衬的是这一对蛇精内心的透亮、干净、直接。
白娘子与小青在这个空间释放她们的情欲本能,在这里历经春夏秋冬,感受万物的美好,情爱的欢愉。白府的荷花池,荷花朵朵盛开,整个居室与自然完美交融,生命与生命之间互相映衬。“白府”并非秦楼楚馆那般纯粹是情欲发泄的场所。正如许仙所说,这是“家”。在这里白蛇青蛇学习如何享受并经营人类情爱。许仙亦在此读书做功课,青蛇在此玩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白府”更像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呈现的空间。“本我”按照“快乐原则”活动,呈现人格中最原始的部分,是生物性冲动和欲望的贮存库。青白蛇与许仙三人在这里释放情欲、感受性爱的美好,同时在这里吃火锅、泡澡。这里是令人欢愉的所在,是释放“本我”之地。当然包括青蛇与白蛇之间的斗争(人性的嫉妒、自私本性)也在这个空间展开。
托尔金在《论仙境故事》一文中提出,仙境故事具有四个功能,第一就是幻想(Fantasy)。“幻想是一种自然的人类活动。它当然不会破坏甚至侮辱理性,它既不会削弱人们对科学真理的渴望,也不会模糊人们对科学真理的看法。恰恰相反。原因是越强烈,越清晰,就会产生更好的幻想。”[6]幻想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是一种人权。而白府恰恰就是幻想的场域,在这里导演创造了一个空间,让人被压抑的情欲本能和爱与被爱的渴望得到实现,人的情爱可以逃离礼法秩序的规范,自在自为,可以嬉戏,可以表演,可以创造。当法海捆绑许仙去金山寺的时候,许仙说,“我就是迷恋红尘,这是我的事,你有什么权力管我”(电影台词)。这句话直接道出了真相,白府当中许仙拥有选择的权力,而在金山寺则成为被阉割的对象,丧失了人权。电影甚至采用了戏中戏的结构,白蛇与许仙都用戏曲的念白腔调进行对话,他们的恋爱仿佛就是一场戏,两个人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即使许仙已经知道白蛇是妖,他也依然愿意继续与其一唱一和,因为两人彼此相爱,不忍相离。仙境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逃离(escape)。“童话提供了一种逃避,旧的野心和欲望(触及幻想的根源),他们提供了一种满足和安慰。”[7]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白府提供了逃离礼法、道德秩序的一种满足和安慰。
(三)金山寺——人造神圣空间的腐化与坠落
金山寺,始建于东晋,原名泽心寺,亦称龙游寺。唐朝有个名叫法海的禅师在此开山得金,重建古刹,便更名为金山寺。在传说以及传奇小说的《白蛇传》版本中,金山寺本是实有其地,是江南有名的佛教圣地,位于江苏镇江金山上,像中国其他寺庙一样,位于山林僻静之地,寺庙以木质构造为主,庄严神圣。
然而在电影《青蛇》中,金山寺被架空了,寺庙不在金山上,而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仿佛固若金汤,其实可能随时倾覆(结局也正是如此)。此外,金山寺不是木质构造,而变成一座佛陀偶像石窟,高大伟岸,但同时也是既冷又硬的石头,幽暗不明,仿佛进入冷兵器时代,让人感到无限的压抑和沉重。金山寺成为绝对理性的化身,佛寺的庄严意义被置换为一种压倒式的理法世界的冷酷。它的冰冷与坚硬,同江南白府的明艳与温柔形成了对比。金山寺成为可怕的人造偶像,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与自然相对,与流动的生命(欲望)相对。正如徐克在《狄仁杰》中的通天浮屠一般,它是权势与信仰的象征。
同时,相对于白府的通透、开放,金山寺是个密闭空间,寺庙只有一个出口,四面都是石壁。“对个人而言,空间具有强大的管理和统治能力。物理性的空间,凭着自身的构造却可以构成一种隐秘的权力机制,这种权力能够持续不停地监视和规训。在一个密闭空间内部的监视和规训,可以将个体锻造成一个新的主体形式。”[8]金山寺的和尚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封闭的空间进行规训,最后连许仙也遭到“剃度”(阉割),而且被封了视听觉,从而丧失了分辨是非、看清自我的能力。
与外部空间相同,金山寺内部空间也呈现冰冷、灰暗的特点。色调都以深蓝色、灰色等暗色系处理,显示出阴森、魅惑的特点。由于寺庙只有一个出口,寺庙内部几乎没有光线,灰暗是主色调。几尊硕大佛像矗立四周,中间只剩下一小块空地,空间封闭而且窄小。硕大的佛像与矮小的僧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僧人在此地被佛像规训。在影片的后半部分,青蛇进到寺庙内部,来解救许仙,随着她的飞行,观众可以看到整个金山寺内部的格局。石壁、石柱、石像包围着一批形容枯槁、闭目塞听的僧人,空间与人一体,成为一个压抑人、规训人的可怕所在。当许仙被剃度时,摄影机位放到了佛像上面,从佛像的巨大的侧脸俯拍下去,僧人、许仙都成为了渺小、卑微的存在,许仙不是被僧人剃度,而是被佛像象征的“礼法秩序”所阉割。当摄影机的“特写”镜头将和尚敲的木鱼硕大化,超出了正常比例,象征着威权法理对人的宰制。
“重复”是对意义的强调。影片中有一处重复的镜头,当法海陷入心魔,又自欺欺人、不愿面对自己有情欲本能的时候,佛祖面颊上脱落了一块面皮,法海打坐的蒲团自燃,都在释放秩序遭到破坏的信号。当许仙被剃度之后,佛祖面颊上再次脱落了一块面皮,佛法秩序已经崩溃。巨大佛像只是人造之物,人造之物一定会朽坏。
江南、白府、金山寺作为三个多元异质的空间,空间的并置本身就会产生意义。江南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建构,遵照历史对江南人情节俗世态的描摹。江南也是一个善恶交织、是非难辨的“人间”。而白府则是一个释放内在欲望的自由空间,但它并非妓院那般纵欲无度,而是有节制地体会情爱之奥妙的场所,是人被压抑的性欲和被道德戒律捆绑之后的一个释放空间。相反,金山寺则被提炼为一个纯粹的象征符号,理性、秩序、禁欲、等级规范,是硬邦邦不可逾越的封闭空间。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从某种程度上,江南是自我,遵从现实原则;白府是本我,遵从快乐原则;金山寺是超我,遵从理性原则。在超我当中,弗洛伊德增加了自我理想的成分。自我理想指“自我渴望达到的成就目标,个体以超我所认同的对象为榜样,努力实现自己(想成为什么人)的理想”[9],实际上相当于个体为自己所设的行为价值标准。金山寺就是法海的自我理想,脱去人类情欲,达到神人一体的境界。按照拉康的观点,金山寺就是“象征界”,就是“大他者的言说”[10],是道德、秩序、规范的言说。
还要注意的是江南、白府、金山寺这三个空间中,并非都是并置的关系,实际上,白府是江南的一部分,是现实人间的一个场域建构,融入人类的陆地生活中。而金山寺则是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上矗立,像一座孤岛,远离人间。当白素贞为了解救许仙来到寺前,镜头将白素贞忧郁的脸部特写与金山寺佛像的脸部特写并构,观众感受到妖的有血有肉、佛的冷硬无情。因此金山寺是悬置在人间之上的清规戒律,其本身就高度抽象化的一个所在。而导演很明显地将其作为与有情有爱有性的白府作为对比来加以反讽和嘲弄。
二、奇幻形象的塑造——身体空间的欲望及其话语表达
(一)法海——理法与欲望的矛盾体
法海在历史上实有其人,是唐代名相裴休之子,曾住持金山寺。在历史上,有他在金山寺驱退蟒蛇的传说,后经不断演绎,变成了人妖恋故事中的一个主角。
法海是佛法、三界秩序的卫道士。用固着的阶层观念看待一切。这与其他版本相同。但是《青蛇》不同之处在于,在以往的文本中,法海都是没有任何人间情欲的老者,内心秉承佛法,没有内心矛盾与挣扎,是一个完全摆脱人性的得道高僧,是一个纯然正确的“扁平人物”。然而在《青蛇》中,法海虽然已临近“神人一体”的境界,但是仍然无法摆脱自己作为人的原始欲望,他的自我呈现出矛盾的景象,法海成为了一个“圆型人物”。
另外,法海的身体也被“年轻化”重构,肌肉发达,棕色肤色,阳光健朗,赵文卓的扮像,俊朗不凡,充满阳刚之气。这一方面满足了观众的情欲想象,另一方面也在电影中激发青蛇的情欲想象。男性成为被凝视被欲望的对象,这也是违背以往的观影惯例,本身就是一种颠覆,表达了女权主义的某种话语。
年轻身体,充满力比多,更加难以克服本能欲望。在电影中,法海在理法追求道路上,总是会受到情欲的魔障。法海看到的女妖,就是他自己被压抑的人性部分。这些长尾的狐妖,代表的就是最为赤裸的色。长尾是男性“阳具”的象征。女妖衣不蔽体,又裸露着头颅,是人性欲望最赤裸裸的表征。“光头被认为是最不自然的。因为它去除了一切自然生长出来的头发,它是彻头彻尾的反自然……头部通常被认为是秘密的发端处,是精神和隐私的策源地,是需要覆盖和掩体的矿藏……大脑,如果失去了头发,就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和理性,失去了它的内涵和定义。”[11]这些狐妖似人又似动物,显示出了强烈的兽性。“怪物(非理性的、未知的)生活在我们体内……(怪物)代表了我们所有的邪恶和杀人倾向;渴望自由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倾向。在荒诞的叙述中,怪物和受害者象征着我们存在的二分法;我们无法形容的欲望和它们在我们身上激发的恐怖。”[12]狐妖就是法海内心非理性部分的展现,成为他身体不可控的部分,常常侵犯他的理性领地而遭到他自己的扫除。色欲被认为具有动物性(兽性)的特征,因此极力被规避和扫除。然而兽性是人的本性,是无法战胜的。
人身上具有动物性,“巴塔耶将兽性看作是一股强大的回溯和逆转力量,开始,它的确被人性所否定;但是,在否定它的同时,它像某种倔强的野草一样反复地生长出来,兽性从来不会在人身上完全根除。”[13]人性及世俗世界对兽性,对这些被诅咒的东西进行否定,并不能让它们不起作用,而是赋予她们一种别样的价值,使它们成为一种“陌生的、令人困惑的东西”。这些被诅咒的东西“不再仅仅是自然,而是经过改造的自然,是神性。这不是兽性,而是形象是野兽的圣物,是神圣的兽性,这些被诅咒的东西被涂上一层辉光,它对世俗世界进行否定,犹如世俗世界对自然兽性进行否定一样。这就是神圣世界的诞生。”[14]人类是会思考的动物,动物性是人不可规避的自然本性。只要法海还是人,他就无法成神成佛。
(二)青蛇——情欲话语表达的主体
在古老的白蛇传故事中,青蛇只是作为白蛇与许仙之间的一个帮助者角色,只是一个配角。然而在李碧华与徐克创造的文本中,青蛇从边缘角色变成主角,成为边缘话语的代言人。相比于白蛇,青蛇修炼只有五百年,她的身上是人性与兽性并存的一个存在。她在一开场就在酒楼与舞女热舞,并对舞女进行性挑逗。同时在白府她也极力勾引许仙,想要尝试人间的情爱。
尤其在她与法海的对戏中,青蛇的蛇性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昆仑山盗取灵芝的过程中,青蛇为了掩护白蛇,主动留下与法海对峙。法海借她来修炼自己的神性。于是在昆仑山的水池边,法海在青蛇的色诱中败下阵来,成功勃起。理法败给了欲望。而青蛇就是欲望的主体表征。水池中央矗立着一支擎天石柱,作为“阳具”的再次表征,在神圣的昆仑山的空间表征中,出现了神界与动物界的交融。
青蛇是人头蛇尾的身体,是兽性与人性兼具的产物。青蛇的身体在同时表达动物性(兽性)与人性的话语。“人首先是一个身体和动物性存在,理性只是这个身体上的附着物,一个小小的‘语词’。身体就是权力意志。”[15]
青蛇虽然一直在学习如何做人,但是终于在结尾看清了人,人间有情,其实妖间也有情,人间之情不能有始有终,而妖间之情却可以彼此扶持、长长久久。
斯宾诺莎认为欲望是人的本质本身。人的本质就是一种情感决定的行为,这也就是欲望。欲望意味着情感驱使去做,欲望就是情感行为。affect(情动)乃是人的本质。[16]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便用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象征,来说明艺术的起源、本质和功用,乃至人生的意义。他说:酒神状态是“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状态。酒神植根于人的至深本能,是个体的人自我否定而复归世界本体的冲动。[17]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青蛇》的改编即是为了肯定日神(理性)压抑的人的酒神(本能)部分。情、欲本身就是一体。青蛇在结尾对法海说,“我来到人间,为世人所误。你们说人间有情,但情为何物。可笑,连你们人都不知道。等你们弄明白了,也许我会再回来”(电影台词)说完,纵身跳入大海而去。人间情感最为宝贵,理法秩序也无法褫夺情爱的欢愉,但人之情爱不应成为短暂的情欲满足,而应该超越情欲,达到更高的层次,白蛇所追求的“从一而终”固不免落入了儒家的伦理圈套之中,但其追求人间情感的广度与深度的执着精神则在诸人之上。
结 语
《青蛇》的故事重构所要表达就是导演对于人的本能、欲望的肯定。欲与理永远在持续的张力之中。欲望无法被取消和扼杀,但是欲望也不可被无限纵容。在电影当中,从白府与金山寺的空间并置,从法海与本能情欲的对抗,从人性与兽性兼具的青蛇从副角变为主角,可以看出,导演更赞赏人的欲望、力比多的发挥,更肯定的是欲望带来的丰富性、血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