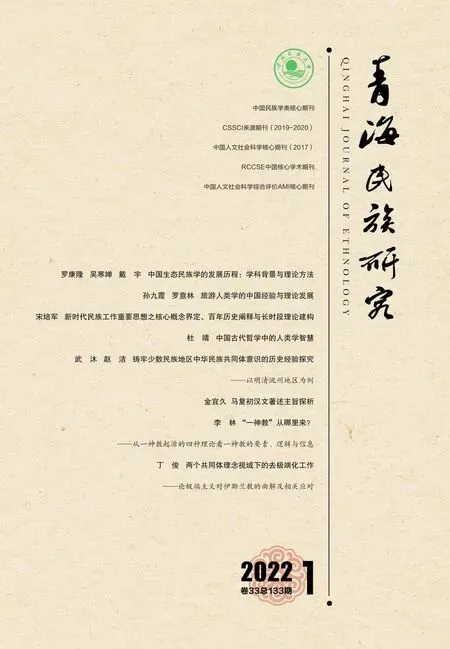困惑中前行: 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之争与反思展望
王佳果 许宪隆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桂林理工大学,广西 桂林 541004)
人类学自西方进入中国已有百余年,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发展过程。 在学界以往的研究中,对中国人类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已十分深入和详尽,对人类学发展的历史成就、经验教训也有所总结归纳,对人类学本土化问题的讨论异常热烈并延续至今。在改革开放学科恢复重建以后,中国人类学进入到了一个较快发展的阶段,但与此同时,人类学与民族学在学科发展方面出现了一定的重叠、错位和冲突,特别是在学科认定与划分过程中,人类学的学科位置呈现出一个动荡错乱的历史轨迹,最终的结果是民族学获得了官方认定的一级学科地位,而人类学至今也未能实现学科独立发展的愿景。 对于这一学科发展遭遇,国内的人类学者曾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研讨,对此进行分析、反思并奔走呼吁,不少研究者也注意到学科认定划分和学科纷争对本学科发展的影响极大,甚至决定了人类学学科在一定时期内的命运走向,但是鲜有学者对中国人类学在体制内的学科划分设置的历程,特别是对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发展之争进行总体性的梳理反思。 距上一轮的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已满十年,按照《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学位〔2009〕10 号文件)的规定,一级学科的调整为每10 年进行一次,新一轮的学科目录大调整即将来临①,人类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再次引起学界的忧思。 为此,本文通过对人类学学科划分设置和发展地位的系统梳理,呈现这一复杂的历史演变轨迹, 以此透视人类学学科的总体发展历程,反思人类学与民族学“剪不断理还乱”的学科纠缠争斗,提出中国人类学学科未来发展的若干思考和展望。
一、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早期发展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中国人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作为一门认识他者、辨种识族的知识体系,人类学由西方传入中国,并被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期以“洋为中用、强国保种”的厚望,因而受到了知识阶层的广泛关注和研习。大量的西方人类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并流传开来,人类学也很快进入了大学教育并占据重要地位。 1903 年,在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中,“人种及人类学”和“人类学”成为大学课程学习的重要科目[1]。 其中,人类学成为动植物学门科目的“主课科目”,成为中国史、万国史和地质学门的“随意科目”(类似现行之选修科目); 人种及人类学成为中外地理学门 “主课科目”和众多外国文学门科目的“随意科目”。同年,京师大学堂依据《奏定学堂章程》正式开设了人类学课程。 1912 年蔡元培执掌教育部以后,在1913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令》中,已经开始明确规定,“人类及人种学” 是大学文科众多学类(近似于现今的学科、专业)的学习科目,涉及哲学门、历史学门、地理学门等三大文科学门,“人类学”则成为文科文学门言语学类、理科动物学门、地质学门学习科目[2]②;至1923 年,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学系创立于南开大学, 但这个系存在的时间并不长[3];1928 年清华大学将社会学系改称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系;1929 年, 国民政府公布了新的 《大学规程》,社会学系成为大学文学院的“标配”[4]。 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燕京大学等为代表,有为数众多的高校开设了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讲授人类学相关课程,开展社会调查;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人类学的专门研究机构也开始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设有民族学组)、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等。上述机构成立后独立开展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后续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民族志作品,如《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等。和西方不同,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作为“内部他者”的少数民族, 加之在学科发展上同社会学存在伴生关系,这一时期中国研究者对汉人社区的研究也颇有收获,如以《江村经济》《金翼》为代表的本土研究成为蜚声世界的佳作。 20 世纪30 年代末至40 年代,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 中国的政权机关和学术机构西迁,中国西南地区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中心,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边政研究也一时兴起,众多人类学家投身于社会调查和边疆民族研究, 这也是20 世纪前半期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鼎盛时代,极大地推进了人类学中国化的进程。 在北上长征过程中,红军途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到达陕甘宁边区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的民族问题进行研究,形成了以《回回民族问题》《蒙古民族问题》等为代表的研究成果,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与政策, 并在1941 年成立了延安民族学院。 抗战结束后,由于内战造成国内局势不稳,加之大量研究人员流向政界,人类学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大发展。
纵观1949 年之前的中国人类学, 从西方引入伊始的发展起点就很高,既有当时学界领袖蔡元培的加持,又有包括李济、吴文藻、凌纯声等一大批学者孜孜不倦的研究推动,形成了具有一定世界影响力的人类学中国学派。 同丰硕的理论研究和田野调查成果相比,人类学在高等教育体系内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状况并不理想。 在院系设置和专业课程安排方面,人类学大多时候依附于社会学。 1947年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各自成立的人类学系,当年都只有一个学生[5]。 至新中国成立前,在全国205 所高等院校中,设置人类学系的仅有3 个、少数民族系1 个,远逊于社会学系(20 个)[6]。回顾彼时的学科发展势态,我们必须坦承一个事实:中国人类学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学科地位远逊于其学术成就,中国人类学在此期间也从未在高等教育体制内获得过真正独立的学科和专业地位。
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之争③
(一)学科撤销与重建
新中国成立之后, 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一系列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在内的诸多人文社会学科, 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伪研究”,遭受了严厉的批判。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和1952 年开始的院系调整,中国大陆高校的社会学系和人类学学系被迅速撤销,在1954 年新中国颁布的第一份专业分类目录——《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 (草案)》 之中,(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彻底消失。 形成对比的是,因“一边倒”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民族学和民族研究虽然也被冲击改造,但作为学科名称得以被保留,并在 《1956—1967 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和《中国科学院规划任务书》中被正式列为一门独立的学科[7],1956 年秋,中央民族学院在历史系设立民族学专业并开始招收研究生[8]。 1951 年之后陆续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 中南民族学院等成为吸纳原有人类学研究者的主要机构,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员转入到相关院校的历史学或考古学工作, 极个别从事体质人类学的次级研究机构侥幸得以剥离和保留, 例如, 复旦大学的人类学教研室。伴随机构人员的调整,苏联模式的民族学逐步取代了过去受欧美影响的人类学, 根据苏联的学科体系, 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被限定于体质人类学之内,文化人类学的名称则被民族学代替,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理论基础、研究旨趣、政策导向同旧时的人类学大相径庭, 这也成为今日学科争执的重要历史缘由。 然而,好景不长,院系调整之后的民族学刚刚有所发展,就再次遭受到20 世纪50 年代末“反右”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冲击,民族学被视为苏修和资产阶级的学说并被取消学科地位,作为独立学科的“民族学”实际上被作为综合研究领域的“民族研究”所代替。 在1963 年的《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之中,人类学作为学科名称只残留在理科部分的(070027)人类学,实际仅是指体质人类学,(文化) 人类学和民族学完全不见踪影。 1966 年“文革”开始后,就连掩盖在民族研究名下的相关工作也陷入停滞[9]。
改革开放以后,人类学和民族学率先在硕士(中山大学,1979 年;厦门大学,1982 年)、博士(中山大学,1983 年)层面恢复了招生和人才培养④。1981 年1月,教育部正式批准中山大学建立人类学系,学系下设民族学、考古学两个本科专业;同年5 月,中国人类学学会在厦门大学成立;这标志着中国人类学开始进入学科化建设阶段,南方的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逐渐成为人类学重建与研究的重镇。 此后,1984 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成立并于1986 年开始招收人类学本科生⑤;1987 年,云南大学在历史系下成立全国第二家人类学本科专业。 几乎与此同时,1980 年“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在贵阳也宣告成立(1984年改称“中国民族学学会”);1983 年,中央民族学院设立民族学系并开始招收民族学本科生。 此外,在社会科学院系统、民委系统也恢复或新建了一批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机构。
(二)学科错位与纷争
伴随着人类学、民族学两个学科同步恢复重建和时间推移,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错位、重叠发展和学科划分问题渐渐浮出水面。 导致上述问题出现的成因是多重的,其内部张力包括:学科自身发展的学术逻辑和历史演进后果、本领域研究者对学科定位和认同的争议等;其外部原因包括国家政治权力的介入、欧美人类学发展的整体势态等因素。 在人类学引入中国的初期,其学科概念翻译本身存在争论,欧美不同国家、不同的学派都对中国产生过一定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后对学科改造、合并、撤销以及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民族学的影响;学科恢复以后行政部门对学科门类的划分和学科地位的认定也造成巨大影响。 学科重建以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对人类学的学科定义、定位和认同历来有两种主要观点[10]:第一,主流观点认为人类学(主要是指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基本上是同一门学科;第二,部分人认为人类学与民族学是不同的两门学科。 不同研究者对学科定位的不同看法,导致在学科恢复时采取的策略不同,表现在系所名称及其专业组成、具体专业名称和课程设置等方面。 最早恢复学科的院校当中,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师从美国人类学的学科设置, 倾向于人类学的叫法,而中央民院和云南大学的专业设置带有更浓重的民族学色彩,在教学和研究上也保留了相当多的民族史内容。 时至今日,中东部综合性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学术研究偏向人类学,中西部地区的民族高校和地方院校总体偏向民族学。 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和诱因:改革开放之后,学界恢复了与西方中断已久的学术交流,西方人类学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被大量引介到国内,对原有的民族研究知识体系和学科意识产生巨大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有一批从海外求学归来的新一代学者(以英美人类学背景为主), 受欧美人类学学科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影响,力图撇清与以往“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关系,坚持为“人类学”正名⑥。 由此,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错位发展日趋明显,两者相行见远,学科之争愈演愈烈。
这种学科错位与纷争的状态,除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自身发展历史逻辑所造成的原因以外,还和这两个学科在西方的起源、发展过程中的交织状态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受到西方人类学和民族学之间的学科竞争传统以及当代学科发展潮流的潜在影响。
人类学与民族学在西方的起源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源头相近、共生发展但又彼此渗透、相互竞争的状态。民族学作为一门被承认的独立学科,其产生时间虽早于人类学, 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人类学的挑战。据郝时远先生的考证,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的法国, 民族学初始确定的研究对象建立在 “身体与文化” 基础之上, 而后起的人类学则从古人类化石的鉴别介入到“身体与文化”的学科领域,两者的研究议题重叠颇多, 但人类学在19 世纪下半叶异军突起,其影响力逐渐盖过民族学的风头[11]。 何星亮先生从研究学会成立、分化的角度发现,欧美早期很多人类学会都是从民族学会中分化而出, 两个学科难分难解[12]。 民族学被认为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一个早期阶段, 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后, 人类学作为一个总体性的术语变得越来越流行,成为包括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民族学在内的综合性学科[13]。 特别地,在二战结束后1946 年美国人类学协会(AAA)的重组过程中,民族学这一称谓在美国被正式转变为文化人类学⑦[14], 随后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渐变成一种主流观点并影响至今。 列维-斯特劳斯在1954 年也曾提出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志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三个连续阶段, 但民族学仅是利用民族志材料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中间阶段, 而人类学才是关键的能够进行理论构建的最后一个阶段[15],按照这个观点,传统民族学的学术作用和学科形象被进一步贬低⑧。 要之,从19 世纪末至今,人类学及其学科发展大放光彩, 而民族学一词在欧美学界(严格意义上只是在英美,或者说英美的情况尤其突出)处于不断消退的势态,至多被当做人类学的一个分支, 甚至只是被视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古老而过时的同义词, 民族学的发展不断被人类学(主要是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所消解和掩盖。 这种此消彼长的局面不仅和学科各自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势态密切关联, 更是英美社会/文化人类学学术霸权扩张的结果[16]。
除了时间推进造成的学科概念所指变迁和学科竞争势态嬗变以外,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差异显著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学科发展轨迹,这导致了人类学、民族学两种学科在空间区域之间也呈现流变和差异。 克里斯·哈恩也曾指出,人类学发展的多重轨迹深深地打上了他们“民族性”背景的烙印,受到不同社会和政治环境的烙印[17]。与美国人类学四分法的传统明显不同,在欧洲大陆,人类学学科内部的对立不是文化人类学和生物、 考古人类学之间的对立,而是文化、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也包括民俗研究)之间的对立,特别是在中东欧地区,民族学(和民俗学密切相关)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是在文化、社会人类学占主导地位的西欧、 北欧和南欧地区,民族学依然有一席之地。 欧洲人类学学科中的这种分裂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埋下了种子,那些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国家,以海外人群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蓬勃发展起来,这成为英法社会人类学传统的重要支撑;那些只有少量甚至没有殖民地的国家侧重研究本国的民族和文化, 特别是传统的农村社会,这一传统成为今天欧洲民族学(或民俗学)的重要来源[18]。人类学和民族学的重叠和差异,在当今欧洲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组织方面也有所体现⑨,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协会 (EASA,Europe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Anthropologists)成立于1989 年,面向所有有资格或在欧洲工作的社会人类学家; 成立于1964年的国际民族学和民俗学学会(ISEF,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thnology and Folklore),主要参与人员是欧洲的民族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虽然两者都号称尽可能的开放和广泛吸纳相关研究人员,但实际上两者的人员构成(包括地域和学科背景)有显著差异,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19]。
欧洲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学科矛盾和竞争在中东欧国家表现的尤为明显,并在苏东巨变之后日益突出。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中东欧的民族学研究受到西欧特别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央格鲁-撒克逊人类学体系和观念的巨大冲击和影响,相关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纷纷更名,民族学院系和研究所纷纷将其名称冠之以“人类学”,以更接近西欧和英美的传统[20][21]。 可以说,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人类学趁着当时政治势力版图的剧变, 迅速抢占新的学术地盘。 这种扩张潮流影响至今,甚至波及中东欧以外的地区和国家。 例如,2004 年4 月,日本民族学会正式改名为日本文化人类学会;中国台湾省的“中国民族学会”在2005 年6 月更名为“台湾人类学与民族学学会”; 甚至连德国这种有着悠久学术传统的国家也不能幸免,德国民族学学会(DGV)在争论多年以后,最终在2017 年10 月更名为德国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协会(DGSKA)。 当代中东欧的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尤为复杂:一方面,其传统的民族学被西欧和美国学界所轻视,被视为一门陈旧过时且无甚理论深度的研究, 往往和民族主义纠缠不清;另一方面,中东欧国家的学者和机构也急于摆脱传统研究范式的窠臼,积极引进英美文化、社会人类学的新范式和新理论。这种双向合力使其内部出现了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错位竞争发展的局面。中国人类学的正名活动和学科地位争取行动很难说没有受到这股潮流的潜在影响,至少是在世界人类学学科发展潮流和学科版图变动势态中的一种 “无意识”顺势行为。
虽然英美主流人类学不断地强化民族学古老、衰退、次要的神话观点,欧洲大陆的民族学在某些方面也不断受到央格鲁-撒克逊人类学的侵蚀,但作为民族学的发源地,民族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依然在欧洲被广泛使用, 并伴随着 “欧洲民族学”(European Ethnology) 的兴起而被重新发明和利用⑩,只不过多数成果不是以英文发表,其影响力远逊于英语世界的研究者[22]。 在欧洲民族学的影响下,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传统上以国内为研究对象的德国民俗学(Volkskunde)也开始出现了一次广泛的改名运动,即由民俗学改成欧洲民族学(Europ ische Ethnologie),并涌现一大批学术研究机构[23],即便是在英国,作为“国内人类学”的民族学在近些年也开始有所发展[24]。 民族学在当今的欧洲大陆依然彰显着蓬勃的生命力,只是国内的研究者对欧陆新近情况极少关注,在以往的学科史研究中少有论述, 以至于我们言及国外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之时,多是在引用英美的情况和较为陈旧的材料。
至此,本文作者无意也无法在简短的篇幅里对欧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纠缠关系进行全景式的描绘⑪,只是想通过以上概述和例证说明,作为两个历史悠久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人类学和民族学有着繁芜杂乱的学科关系,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错位与纷争绝不是单独的个案,类似的学科差异和纷争现象在许多历史时期和众多国家地区都曾存在,或许在未来我们能从中借鉴学习若干有益经验。
(三)学科认定与划分
学科发展之争绝不纯粹是内在的知识生产单一逻辑的后果, 西方人类学早先有着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说不清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人类学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被视为一门具有浓厚西方 “意识形态”色彩的学科,国家政治对其规训、改造从未中断。 在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力量以更加软性、间接的方式对学科发展进行规训。 这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对学科进行认定和划分。 “政治因素介入科学认识过程中, 权力原则与社会控制原则将会通过学科制度实现,并通过这些制度进入人们的意识,制度的改变会使知识分类和框架结构发展根本变化”[25],学科在国家法定文本中的表述、分类、归置,既体现了学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结果,又展示了行政机构对学科未来发展的权力意志。 这种强制性的规训,对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和学科纷争的影响是决定性的。通过改革开放以后人类学和民族学在学科和专业划分目录中的变动情况⑫,可以看出学科发展之争和外部政治权力对其影响、干预后的复杂历史轨迹和未来发展可能性。
在中国,对学科、专业划分主要有两大体系⑬,其一是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原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先后发布两版国家标准文件《学科分类与代码》⑭;其二是国家教育部(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先后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包括1987 年、1993 年、1998 年、2012 年四版,以下简称《本科专业目录》)和 《授予博士、 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目录》(包括1983 年、1990 年、1997 年和2011 年四版,以下简称《学科目录》)⑮。 教育部的学科、专业分类体系对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划分大同小异,民族学大多时候被明确定位为和社会学、 历史学等学科并列的一级学科,而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不高、分散模糊,经常同社会学、民族学重叠交叉并被归属其下, 这成为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困境的体制性根源。在两版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人类学同样被拆分于自然科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两大门类之下, 被细分的近十个分支学科分别归属一级学科(学科群)生物学、社会学、民族学之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学先是被单列,尔后又和文化学合并成“民族学与文化学”,始终稳居一级学科(学科群)地位。 《学科分类与代码》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稳定性,但作为一个非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 对学科专业的设置和发展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其使用场景多限于国家宏观管理和科技统计,真正对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有影响的仍是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和《本科专业目录》。
其中,《学科目录》是决定特定学科的地位和发展前景的最关键文件,对人类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影响尤为突出。 在最初的分类体系当中,人类学学科名称错位、学科划分重叠、分支学科分散的问题非常严重。 依照1983 年版的《学科目录》,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部分被视为等同于“狭义民族学”,被划分在法学门类的民族学一级学科之下。 这里的民族学一级学科显然是对解放后学科合并改造后形成的“民族研究”大框架的重建和延续,在此框架之下,原有的原始社会史、民族学史、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艺术、世界民族等研究议题都被视为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平行的二级学科,而按照英美标准理应被划入“广义民族学”(人类学)的考古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被分别归入文学门类的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学门类,体质人类学继续游离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地质学和生物学之内,并占有了“古人类学”和“人类学”的学科专业名称。 前一阶段在民族研究框架之下,“过继”给历史学的中国民族史保持在历史学名下,而原始社会史则同时出现在历史学“继父”和民族学“生父”名下。 根据1984 年各省统计上报情况,本科层面的人才培养和专业设置,只有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招收民族史(民族学)专业[26]。 1990 年和1997 年的《学科目录》中的民族学依然保持了“民族研究”的大框架思路,这种学科集群的设置思路延续至今,民族学、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经济、民族艺术稳定保持在内,民族史则逐渐脱离历史学重新归属民族学,但是民族语言文学、民族考古、民族医学被更强势的学科所吸纳而脱离在框架之外,民族体育等新兴分支学科若即若离。 与此同时,人类学的学科重建之路尤为坎坷,一直未能取得一级学科的地位,从民族学脱离后又辗转划归社会学之下,似乎在朝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学科设置传统回归。 几代人类学家欧美式的“大人类学”学科的梦想愈发缥缈无影,作为一个弱势的二级学科,语言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难以被吸纳归位,体质人类学在自然科学领域不但没有保持自立门户,反而被传统优势学科和新兴学科所边缘和消解, 地质学下属的古人类学在1997 年的目录中被归入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生物学下属的人类学已经销声匿迹。 人类学与民族学在学科名称、研究对象和领域边界的争执和冲突也从未停止,这恐怕是其实现学科一级地位的最大外部障碍。 在最新的《学科目录》(2011 年)中,民族学的一级学科地位再次被确认,人类学的一级学科梦想则再次破灭。 而且,根据2001 年的文件目录, 研究生专业点的设置只设定了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名称,作为二级学科的人类学在目录中彻底消失, 在大部分高校的硕、博专业、方向设置和招生简章中,人类学出现的频次也越来越低。
在本科教育的专业设置层面,主要依据文件是教育部发布的《本科专业目录》。 在前两轮的《本科专业目录》和《学科目录》编制中,民族学、人类学本科专业和学科学位不对应的现象还很突出,民族学和人类学在本科专业同属二级学科,但在学科归置和硕博人才培养层面,民族学是一级学科,人类学是二级学科。最新两轮编制的《本科专业目录》已经同《学科目录》保持一致和稳定,体制的固化进一步加剧了人类学、民族学错位发展的势态。起初,1987年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认为当时学界对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归属意见尚不统一,鉴于两个专业和历史学、考古学的密切关系,提出折中方案, 将两个专业平行地暂时归于历史学类[27]。 根据1989 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专业介绍, 民族学的人才培养主要面向民族工作和教学科研,课程设置以中国民族概论、民族史、人类学概论、考古、语言和民族调查为主,而人类学的人才培养和就业面向更广,不仅针对民族工作,还包括文博、考古等部门,涉及了行政管理、城镇发展规划、教育科研等领域,课程体系围绕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等展开[28]。很显然,人类学和民族学在本科教育层面,两者的界限依然模糊,课程重叠度高,人类学学生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就业发展前景似乎更优于民族学。 但是, 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的毕业分配制度下, 人类学的本科招生和就业始终没有任何起色,在1997 年高校扩招之前, 只有两三所高校开设了人类学本科专业。 1990 年代初期以后,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社会需求成为高校本科专业设置的主要考量因素, 专业口径窄、应用性差的专业被削减。 在1993 年 《本科专业目录》调整时,民族学和人类学同时被打入“冷门专业”,成为历史学下面仅有的两个“需要适当控制设点”的专业。 到了1998 年,民族学仍旧是历史学类下的“需一般控制设置”的专业,而人类学则从历史学类转移至社会学类, 成为社会学类下属的三个“目录外专业”之一,其专业地位进一步下降。 2008年以后,中国西部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出现的严重暴恐事件,使民族问题研究和人才培养摆在了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在2012 年的《本科专业目录》中,民族学成功摘掉了“需一般控制设置专业”的帽子, 并一跃成为一级学科, 至今开办院校已有24所,广泛地分布在15 个省份;而人类学依旧是社会学类下的“特设专业”,情况不容乐观,至今只有7所院校开办过。
三、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困惑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类学如今处于一种越来越尴尬的发展状态, 历经学界多次呼吁之后,人类学依旧作为二级学科游走、依附在历史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之下。 处于学科夹缝和阴影之中的中国人类学,其本土化发展和谋取独立学科地位的任务十分艰巨、前途不甚明朗。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学界对学科地位的呼声也从未停歇,在1995 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三科并列、交叉发展的构想后,人类学家先后在20 世纪90 年代后期、2010 年、2016 年以论文研讨、集体建言、专题会议等形式为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发声正名。⑯虽然在理论研究和知识溢出方面, 中国人类学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纵有学者奔走呼告,但现实发展情况与学界理想情怀之鸿沟愈深愈宽,学科地位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最大遗憾和困惑。
首先, 历史时期人类学的学科地位情况限制其未来提升的可能性。 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历史事实就是, 人类学申请一级学科在中国缺乏坚实的历史依据, 人类学在解放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内也从未获得过真正独立的学科地位。 今天的中国人类学家经常以中国人类学曾经辉煌的历史作为争取一级学科的理由之一, 但这只是学术研究本身的昔日荣光而非体制性学科地位的历史事实。纵然人类学自从西方传入中国以后在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起点很高, 但人类学从未在真正意义上获得过类似于今天所谓一级学科的地位,即便是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鼎盛时期相比,今天人类学在高等教育体制中的学科地位也毫不逊色, 只是和有着共同源流却已成为一级学科的民族学、社会学相比,总会令“局内人”忿忿不平。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下降的话,似乎就是,今天的中国人类学缺乏在那个时代不断涌现的杰出人物和优秀研究作品, 缺乏产生对世界人类学有影响力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缺乏对中国人文社会领域其他学科产生足够多的知识溢出。
其次, 学科之争困扰人类学的发展和学科地位。 受英美的影响, 欧美主要国家和顶尖大学大都构建了系统的人类学学科体系, 人类学是人文社会基础学科中最重要学科之一。 中国的人类学家也经常以西方作为“唯一”参照的“国际标准”,呼吁把人类学列为一级学科。 但是, 在中国的学科发展历史情景中,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等人类学分支学科早已被相关强势学科吸纳、支配。 当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类学多是在指英美语境中所说的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在研究旨趣、研究问题、研究对象等方面和中国民族学虽有着一定的差异, 但在研究理论, 特别是研究方法方面有着相似的渊源和基础。 更进一步的说,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就是:所谓“中国化的人类学”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有着太多的学科重叠,两者在学科发展资源、学术研究权力等方面保持着 “暗斗而不明争”的微妙境况。 人类学争取一级学科地位, 主要是向民族学发起挑战和竞争,不少人类学家认为,单纯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 把人类学视为民族学的平行学科列为一级学科没有太大疑问。 但现实是,学科之争往往超越了学术研究本身。 在中国这样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之中, 民族研究和民族学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构建民族认同话语体系、解决内部民族问题的关键性知识生产领域,历来被国家权力机构所重视, 民族研究和民族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培养了大量研究人员、 成立了众多的研究机构、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成为政府解决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问题的主要智力支撑,并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体系和知识话语体系, 这些都是中国人类学所必须面对的民族学发展事实。 很多人类学家还认为, 和民族学相比,中国人类学在研究对象上超越了“内部他者”的局限性,汉民社会一直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在近些年还积极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 诚然,作为目前中国民族学主要研究对象的少数民族,其人口比例只占8.49%⑰,但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土面积比例却高达64%左右[29],即便是只限于少数民族的研究, 中国民族学仍具有丰富的研究议题和纵深空间,更何况,不少民族学家也在呼吁超越“内部他者”的对象局限性[30][31],将汉族社会纳入研究对象,并积极开展海外民族调查研究。 由此可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学很难挑战民族学的学科主导地位。 事实上,抱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的心理, 不少民族学领域的研究者特别是 “关键人物” 并不乐见人类学与之平行独立, 国家权力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也很难重视人类学家争取学科的呼声。 除了民族学, 人类学与社会学也存在着一定的学科竞争, 虽然绝大部分人都认为人类学和社会学在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方面差异显著, 两者是平行关系, 作为曾经和当今的体制性依托学科,社会学界对人类学“独立”的态度也十分微妙[32]。不难理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之争早已超越了学术本身的“名实之辩”,折射出学术权力控制、 资源竞争的诡异之光,致使人类学在中国受到极大的发展限制。
最后, 人类学对当代中国的社会贡献和公众影响十分有限。 虽然有不少学者在大力呼吁加强人类学的应用研究[33],但同民族学研究明确的现实导向相比, 中国人类学研究依然未能很好地走出“象牙塔之困”,在国家和区域发展重大发展议题上, 人类学的研究很少能影响到政策制定进程。 不仅如此, 人类学在社会公众的认知中也十分有限,在功利主义和社会现实面前,普罗大众最关心的是所谓的“专业冷热”问题,考量的因素是专业开办数量、就业发展前景、毕业工作收入等,人类学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一如既往的令人沮丧。截至目前, 全国只有5 所高校招收人类学本科生⑱, 根据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最新发布的数据, 人类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只有3.0,低于社会学的3.2,稍高于民族学的2.9,大部分的就业出路是公司业务、公务员和考研深造。 当然, 就业率低不仅是人类学这样的传统人文专业的通病, 也是当代基础学科的普遍遭遇。 当前教育部对学科专业发展有一套完备的考核评估体系, 学科专业的应用性和社会需求是其重要的考量因素, 专注于纯粹的学术研究而忽视人类学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价值和应用之处,争取学科地位只会沦为纸上谈兵。 中国的人类学家必须直面这些现实问题, 否则向权力机构讨要学科地位就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四、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反思与未来展望
学科地位之争已经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最大掣肘,为此,中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都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
对于中国人类学而言,首先,必须明确地对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进行修正调适,建构人类学中国理论话语体系,真正走上“人类学中国化”的道路。中国的民族学源于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其理论方法都直接来源于文化人类学,在特定历史情境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舍弃、改变了西方人类学原有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思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思想,并融入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些传统,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 中国的人类学也要正视这样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曾受到殖民主义掠夺和帝国主义入侵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必须对西方人类学理论进行甄别和批判,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本土国情相结合,走上“人类学中国化”的独立发展道路。 对理论本土化的呼吁绝非是对西方理论话语霸权想象性压迫的恐惧和非学术、非理性抗争的反应,西方人类学本身亦非完美的理论科学,二战以后对功能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后现代主义对人类学田野书写和理论体系的解构,即是明证。 特别是在力求构建社会科学中国话语的当代,更有必要对西方人类学的理论话语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实践场景进行批判性改造和转述。 目前,中国同个别西方国家的关系较为紧张,一些在研究场域看似无妨的理论观点和话语,在现实中很容易被政府机构和普通民众视为映射甚至攻击中国社会体制或传统文化的言论,很难获得政府和公众的支持, 影响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 一个具有中国化理论和话语体系的人类学才能被政府和公众所接受,这是中国人类学实现学科独立的基本前提。
其次,中国人类学必须关切现实发展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国家战略、国计民生的宏观重大议题。 西方人类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早期的民族志研究与殖民扩张、殖民地管理千丝万缕的勾连,到二战期间国民性格研究对政府军事外交决策制定过程的介入,再到人类学家与种族歧视长期不懈的斗争, 无一不是对当时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有所关切、积极回应,这也是人类学能在欧美学界立足乃至成为社会研究主流的重要原因。 人类学历来擅长对传统、微观社区进行细致全面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阐释和理论建构,这种脚踏实地、以小见大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策略对主流的经济学、管理学来说是难以企及,可与之形成良性互补之势。 中国人类学原本就有着关切现实、关注民生的学术传统和研究情怀,费孝通先生作为老一辈人类学家的杰出代表, 从江村到云南三村,从小城镇建设到乡镇企业发展,再到整个晚年不辞劳苦的“行行重行行”,穷其一生都在扎根乡土、志在富民。 当代中国的人类学家已经在人类学应用方面开展了诸多有益的工作,例如移民研究、艾滋病研究等等。 今后在研究议题的选择上应进一步和国家、区域重大发展战略贴近,使人类学家和人类学研究机构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智库力量,这是中国人类学实现其学科价值、学术使命,更现实的讲,也是实现其学科地位的必由之路。
再次,中国人类学应不断丰富其研究对象,以区别民族学的传统研究领域。 从学科发展的现实来看,中国民族学保持着沉重的“学术惯性”,依然以国内的少数民族和民族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中国的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一直都更为宽泛,从汉民社会到少数民族,从华人群体到海外民族,有着更为柔韧和灵活的学术发展空间。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传统乡土社会面临着乡村振兴的问题,现代城市也迫切需要消解城乡二元结构走向创新发展之道,中国人类学已积累了丰厚的乡村研究成果,对乡土中国有着独特深刻的理解,今后应将研究对象进一步扩展到现代城市问题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研究。 随着中国 “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愿景的提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文化的研究成为政府和企业的重大需求,中国人类学面临着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类学应抓住机遇,积极开展海外民族志调查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同民族学、社会学实行差异化的选择,这是中国人类学彰显其特色的主要途径, 更是实现其学科地位的支撑条件。
此外,中国的人类学家也应积极走出封闭的田野世界和“象牙塔”,向社会大众传递人类学的价值功能和趣味知识,扩大普通民众对人类学的认知了解。 作为一门旨在研究他者文化以反观、理解自身社会的学科,人类学对世界各地不同人群的社会文化和地方性知识进行了系统研究,积累了丰饶有趣的理论观点和经验知识,这些理应成为本学科向公众传递普及人类学知识的绝佳素材。 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普通民众同外界交流沟通的机会越来越多,人类学理应担负起向社会大众传递“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流价值观念,这也是推广人类学的绝佳机遇。 被民众广泛认知乃至认同,这也是一个学科走向独立的重要社会基础。
就中国民族学而言, 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在人类学争取学科独立地位呼声此起彼伏的外部刺激下,学科危机在民族学内部若隐若现[34]。学科恢复以来,不少研究者对中国民族学陈旧的理论框架、狭隘的研究对象、松散的学科构成等问题一直有所反思和批评,过分强调政策导向研究和对策应用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学研究的学术严肃性和相对独立性。 在部分新一代的年轻学者眼中,和人类学相比,民族学是一门不怎么“时髦”的陈旧学科,理论性不强、政治意味太浓,研究少数民族和民族问题成为其刻板印象标签。 为此,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一方面要吸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研究传统,融合西方人类学发展的新理论,构建与时俱进的理论框架体系;另一方面,民族学的研究重点和研究议题要有所切换,首先要紧紧围绕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此为核心开展、拓展中国特色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其次,要重视学科中国化问题和知识体系创新工作,用理论讲好中国故事,以理论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通过理论和实践的有机互动、互促,使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走向良性发展。
对于人类学争取一级学科,民族学界应抱着一种静观其变、乐见其成的包容态度。 毕竟,一门学科的兴衰不以特定人群的意志为转移。 如果说中国民族学成为一级学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中国人类学家争取学科独立的努力则是一种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 一个乐观的学科发展结果可能就是,两个学科经过各自的努力,都能成为彼此守望、彼此支撑, 但又有所差异的相互独立的研究学科,平等相待、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注释:
①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在2021 年上半年已下发了《关于成立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专家论证组和工作组的通知》, 新一轮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已经启动。
②《教育部令第一号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令》(1913 年1月12 日)。
③本文所讨论的学科设置演变和学科之争问题,只限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省的情况暂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④中山大学最初是民族考古方向; 据厦门大学官网https://anthro.xmu.edu.cn/bxjs1/bxjs.htm 介绍是1983 年,胡鸿保主编的《中国民族学史》(第233 页)表述是1982 年。
⑤厦大人类学本科专业1986 开办,1994 年停办,2007年重办。
⑥也有人据此将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划分为所谓的“本土派”和“海归派”。参见:马英杰. 人类学主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第四个”组成部分的再探讨[M].虎有泽,贾东海. 民族问题研究第四辑.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6:49—59。
⑦但民族学这一概念在美国仍被继续使用,主要是指使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 成立于1842 年的美国民族学学会(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AES)在上个世纪80 年代初成为美国人类学协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AAA)的一个分会,并将自身定位于在“文化人类学中推广丰富的民族志和相关前沿理论”。
⑧列维-斯特劳斯在1954 年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人类学在高等教育中地位的报告,本文所查阅的英文译稿出版时间是1975 年。
⑨ISEF 的前身是成立于1928 年的民间艺术传统委员会(CIAP,Commission des Arts et Traditions Populaires) 有 关EASA 和ISEF 的相关信息及其组织旨趣差异,可进一步参见两 个 组 织 的 官 网:EASA:https://www.easaonline.org/;SIEF:https://www.siefhome.org/。
⑩欧洲民族学被视为旧术语民俗学(Volkskunde)和民俗研究(Folklore Studies)的替代概念,出现于20 世纪30 年代,并在20 世纪60—70 年代不断扩大影响力,是当代欧洲人类学民族学发展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⑪有关欧洲人类学和民族学复杂关系的论述可以进一步参 见:(1)SCHIPPERS T K. A history of paradoxes: Anthropologies of Europe [A]//Vermeulen H F, Roldán A A. Fieldwork and footnote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nthrop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5:234-246.(2)Vermeulen H F,Roldán A A.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and Europe[A]//Vermeulen H F, Roldán A A. Fieldwork and footnotes: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anthropology [M]. London: Routledge,1995:1-16.(3)Frykman J. A Tale of Two Disciplines: European E thnology and the Anthropology of Europe [A]//Kockel U,Craith M N, Frykman J. A Companion to the Anthropology of Europe.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2:572—589.(4)CAPO J.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 Europe Towards a Trans-National[J].Cultural Analysis,2014,13:51-76.(5)WELZ G. Ethnology[A]//WRIGHT J 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Behavioral Sciences Volume 8 [M].Amsterdam:Elsevier, 2015:198—202.(6)VERMEULEN H 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in Europe Today [J]. Anthropos, 2020,115(1):188—192.
⑫需要指出的是,学科(discipline)和专业(program or major)是两个密切相关但又不同的概念,专业是学科人才培养的依托,学科是专业持续发展的基础,鉴于两者密切的关系,在对学科认定与划分的讨论中,学科和专业被一并纳入分析。
⑬除此之外,图书馆系统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和国家社科基金也制定了相应的学科分类,因其对学科发展影响相对稍小,本文暂不纳入讨论。
⑭1992 年推出第一版,标准代码为GB/T 13745-1992;2009 年进行了修订第二版,标准代码为GB/T 13745-2009;此后,在2012 年和2016 年进行了小幅修改。
⑮四版文件目录名大同小异,2011 版的文件名为 《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去掉了以往版本文件名中的“专业”二字,2011 版颁布以后,在2018 年进行过轻微调整和更新。
⑯一是1995 年乔建先生《中国人类学的困境与前景》一文发表后引发的学术讨论; 二是2010 年以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发起的《“人类学”一级学科调整建议书》;三是2016 年在广西贺州召开的“人类学学科建设座谈会”。
⑰此处为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最新的人口七普数据比例为8.89%。
⑱结合资料查阅和作者对相关院校师生的访谈整理,改革开放以后开办过人类学本科专业的院校有:中山大学(1991年至今)、厦门大学(1986 开始招生,1994 年停办,2007 复办至今)、山东大学(2013 至今)、广西民族大学(2012 年至2019年)、北京大学(2019 年至今)、云南民族大学(2020 年开办)、云南大学(1987 年开办,1999 年停办)。 延边大学、沈阳师范大学等院校曾经在社会学专业下开办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方向的本科专业,此类情况不计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