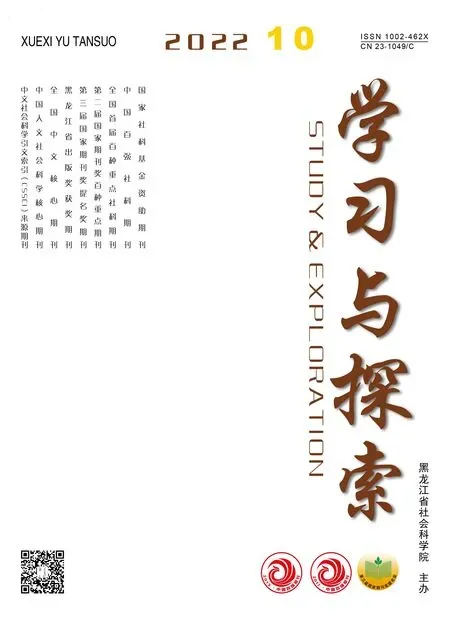文明型国家文化精神传统与当代中国文化自信
——基于马修·阿诺德的“文化至上”理论
桑 影 影
(1.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哈尔滨 150025;2.哈尔滨石油学院,哈尔滨 150028)
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在其专著《文明型国家》中,将今日之中国定位为整合了“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长处而形成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即“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1]2,是一种与西方话语系统下所形成的“民族国家”概念不同的国家形态的解读方式,为当代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极大的理论支持,并且为解构、脱离西方话语,创造“中国话语”做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
一、文化精神——国家建构的基础性要素
(一)马修·阿诺德的“文化至上”理论
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将欧洲(西方)的文化精神传统界定为希腊精神(智)与希伯来精神(力)的对立与统一。他认为,“和一切伟大的精神传统一样,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无疑有着同样的终极目标,那就是人类的完美或曰救赎”[2]111。只有将这两种精神进行合理地结合,理想中的一个完善的人、一个道德观念充沛的社会、一个强力有效的政府、一个繁荣统一的国家才能够以此为基础而逐步建立起来。当然,两者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处于平衡状态的,正如阿诺德所言:“依照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时代、依照我们与两者的不同关系来看,各自都出现过比对方显得更辉煌、更可贵、更优越的时候。”[2]111哪种精神更加值得被发扬,需要依据具体的历史语境而言。尽管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所代表的种族有所差异,然而由于终极目标的一致,两者是有机会进行有机结合并且绽放光芒的。
在阿诺德看来,海涅就是两者完美结合的典型代表:“海涅的身上既具有希腊精神也具有希伯来精神,两者都延及无限——即一切诗歌和艺术的真正目标——希腊精神通过美走向无限,希伯来精神则通过崇高走向无限。从他完美的文学形式、对清澈和美的热爱来看,海涅具有希腊魂;而他的激情、他的桀骜、他那不可名状的渴求,则是希伯来的。”[3]因此,阿诺德将“文化”崇高化,力图让人们通过对文化的学习与感悟,最终达到人类的“美好与光明”的状态。与阿诺德同时代的诸多学者、政治家,诸如托马斯·卡莱尔、约翰·罗斯金、弗雷德里克·哈里森等,都对他忽略政治与社会实践,“空谈”文化而颇有微词。然而,或许正是因为阿诺德看到法国在风云激荡的大革命结束之后,始终无法建立一个稳定、高效的国家政权——就像托克维尔所理解的那样,大革命之后建立的所谓的“新”的制度,不过是在旧制度的破旧不堪的外衣上缝合了华丽的补丁。他才会将对人在文化方面的培育看作头等大事——无视文化,盲目“实干”,会有坠入到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更奢谈一个“国家”的建立。而19世纪的英国正处于一个由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阿诺德称之为非利士人)所主导,重视实利与技术,盲目崇尚个人自由,公共秩序混乱不堪的社会状态:“我们崇拜自由本身、为自由而自由。我们迷信工具手段,无政府倾向正在显化。因为我们盲目信仰工具,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理智光照,不能越过工具看到目标,不能认清只有为目标服务的工具才是可贵的。”[2]45
因此,加强个人在文化方面的修养,提高人们对事物本身的理解能力,才是一条“认清”目标的正确途径。只有在人民重视文化,对文化精神进行传承的基础之上,人民方能树立统一的伦理价值与道德观念,分享共同的情感体验,进而摆脱孤立,为了相同的目的聚合一处,最终形成一个作为国民集合体、共同体性质的,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国家政权。
(二)文化精神是国家建构的核心要素
综观阿诺德的文化主义理论,不难发现虽然在诸多批评者的眼中,他所持的文化至上的观念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现实指向,尤其是政治实践,但实际上,阿诺德恰恰提供了一种文化与政治相结合的全新形式。他强调文化的功用在根本上是为一个强有力、具有威权的政府而提供服务的——文化精神成为政治的原动力,这正是西方传统文化精神中“智”与“力”相结合的展现。尽管阿诺德并未提及建立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系统理论及基本策略,但是他仍为18—19世纪欧洲诸多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当然,与公认的西方现代国家理论的奠基者霍布斯与卢梭不同,阿诺德并没有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对国家的出现进行思考,而是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国家在实践层面的功能与意义。霍布斯与卢梭从人本身的自然属性出发,对国家的由来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国家实际上是由于人坚持自身的发展所发生的诸如“一切人反对以其人的战争”的矛盾冲突之后,为维持稳定通过“契约”而产生的,多少带有一些无奈与权宜的意味。在此时,国家多数情况之下被视作一种工具,维持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二人眼中被预设为对立的矛盾双方——之间微妙的平衡。阿诺德也曾坦言:“我们说一个国家事实上由无数个人合起来所组成,每个个人都是他自身利益的最佳裁决者。”[2]44很多人可能会误解阿诺德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深刻含义,甚至与会将其与霍布斯的“战争”论调相提并论。阿诺德之所以强调每个人对于自身利益的裁决,其重点并非在“利益”,而是在“裁决”上。人们通过理性对自身加以裁决,判断利益的归属与限度,而这种裁决的理性更多的是凭借文化精神的培养而形成的。
因此,在阿诺德看来,国家更多是倾向于作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主体而存在的,是一种诸如文化、民族、习俗、生产方式、统治机器及地域特征复合在一起的有机构成。国家“最能代表国民健全理智的力量,也最具统治资格,在形势需要时,最能当之无愧地对我们全体行使权威”[2]51。而文化与文明精神作为维系国家稳定与人类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则是阿诺德所关注的焦点。如果忽视甚至抛弃了文化精神与传统,那么国家将面临彻底演变成一种单纯执行统治功能的工具之威胁。
在当下,我们不难发现阿诺德的理论具有很高的预见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日趋完善,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4]117,成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4]117。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在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进入了后福特主义时代。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民族国家正在被一种全新的统治形式——奈格里与哈特意义上的“帝国”所取代,并且逐步丧失了对本民族与本国文化的掌控,面临着被在消费主义潮流影响下的同质性、同一性的大众文化所取而代之的危机——不仅仅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也面临着相同的威胁。因此,加强对民族与国家自身传统文化精神的认同,保持文化的差异性与独特性,是全世界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共同任务。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立过程与西方国家虽然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同西方国家一样,具有着独特的文化与文明传统,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这一传统深刻影响着国家对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张维为在《文明型国家》中对中华文明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文化核心”。而在这个核心的周围,则围绕诸多不同形式的文化,两者之间相互交流、吸收与融合,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这种文明格局的形成同“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传统具有紧密的联系,而后者也是中国发展成为一个“文明形态国家”,进而构建为一个新型的、同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路径相异的“文明型国家”的关键所在。如今,西方话语与西方模式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在今日已显露疲态,运用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发展进行解读与预测经事实证明——尤其是2020年以来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了极大的偏差,中国没有发生诸如“阿拉伯之春”以及苏联解体等指向政治体制变革的所谓“颜色革命”事件,反而通过对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与文化精神传统的理解与发扬,走出了一条同西方模式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二、文明型国家的文化内核与实际展现
(一)天人合一
就哲学意义而言,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天(或言天道、天命)与人之间关系的探讨,重点则是天与人之间的互动。《庄子·山木》篇有言:“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与人同根而生,但显然,天道是大写的,人类则需要适应自然以存在。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天道并不会因为个人的行为而发生改变,人只能改变自身思想意识与具体行为以适应天道。而“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则进一步表明,个人在自然面前是无法与之抗衡的。西汉时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天人之际,合二为一”“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更是在本体论、伦理学及政治哲学等多重维度中详细阐述了“人”与“天”之间的密切关系。“天”作为整体,包含着人与除人之外世间万物,人与万物之间则有异有同。万物在世界中的和谐共生即是“天道”中恒定不变的真理。因此,追求整体性,追求人与天、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精神的内核,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传统。正如曾繁仁所言:“‘天人合一’是在前现代神性氛围中人类对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种追求,是一种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体现为中国人的一种观念、生存方式与艺术的呈现方式。”
《庄子·德充符》写道:“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这表明了人与世间万物一切变化的背后都有一种不可知的天命进行操纵,人只能顺其自然。显然,在高速发展当今社会,抱残守缺就意味着停滞不前。因此,当下我们对“天道”应采取不同的理解方式。“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人与自然应是和谐共生的关系,两者的命运是相互连结的,所谓“人定胜天”并非是将人与天完全置于对立的两个方面,而是强调人在面对外界的挑战时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的能动性——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但并非颠覆自然。一味对自然的攫取与破坏最终势必会使人类面对生存的危机,对自然规律的遵守与运用、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成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关键所在。因此,在当代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建构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200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发展论断,并在十九大报告中重提这一论断,确立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彰显了“文明型国家”在制度上、治理上以及观念上的优越性。可见,“天人合一”观念的出现,为人类提供了日常行为规范的伦理法则;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人类在自然之中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与文化上的指导;促进了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以及其稳定、高效地运行;保证了作为整体性的中华文化稳定、延续地发展;同时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传统,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文明型国家”的建构赋予了深厚的文化意蕴。
此外,“天人合一”的观念也在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同祭祀时的巫术息息相关,人们通常以歌舞的形式展现对天地与祖先的崇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诗经》中的“周颂”大部分都同祭祀天地与祖先相关,其中《维天之命》最为典型:“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展现了周文王呈上天之命,奉天道而行的纯净品德,将天地运行的规律与人自身的行为方式与价值判断融为一体。而我国最为古老的乐器——古琴,其身长三尺六寸五分,象征着一年的365天;十三个徽位象征着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以及一个闰月;琴身各部分的名称分别以额、颈、腰、尾进行命名,实际上是将人身体的形象投射到乐器之中,充分人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以及期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时至今日,“天人合一”的观念作为中华文化精神的瑰宝,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道路中依然占据着核心的地位。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文明型国家,坚持“天人合一”的思想,能够使人们了解自然万物运行的规律,并因之形成人们自身的价值判断与道德观念,指导人们日常的行为与生活的方式;同时也为传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建设与完善中国话语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和而不同
《论语·子路》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原意指的是作为“君子”应当一方面与周围人保持和睦、融洽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应有自己的思考与原则,不随波逐流。这是儒家思想在为人处事方面为我们提出的道德标准,要求人们在重视整体性的同时要具有包容性,尊重差异,允许不同思想、文化之间进行交流与对话。实际上,“和而不同”的观念并非儒家首创,先秦时期,诸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名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等诸多学术思想派别纷纷出现,尽管各派别学说的观念与方法论有所不同,但都有着相同的目的:即期望结束战火纷飞的分裂时代,形成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使人民能够各司其职,安居乐业。西汉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学说千余年来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核心地位,而“和而不同”的理念也由此投射到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之中,并且作为中华文化的优秀的精神传统传承至今。
就地域而言,中华文化是以长江、黄河流域为中心的,“联结周围区域文化的格局,其整合的模式是以中原华夏地区和华夏族文明为核心,核心与周边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而形成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而这种文化格局的形成同当时的“王国(中央政权)——方国(分散在王国周边,王国势力范围之内与之外的部族)”的政权分布形式有着密切的关联。王国在与方国的交流与互动之中,不仅促进了周边方国在文化上的“向心运动”,同时也保留了各方国文化的独特性,促进了“和而不同”的精神传统的形成。商代末年,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周太王)之子太伯与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实际上就是遵从了与中原文化相异的吴地蛮族的文化特性。而在周朝建立之后分封制的兴起,更是将中原文化快速向周边地区传播,而原属于“蛮荒之地”的后者也逐步对中原文化产生了认同。自秦朝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度量衡,尤其是“废分封、行郡县”等政策后,中华文化“统一”的观念基础就得到了确立。不同区域的民众由此在文化意义上确立了追求“整体”与“统一”的思想,“地方”与“中央”之间不再是先秦时期的离散状态,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愈加紧密。
纵观中国历史,虽然出现过短暂的分裂纷争的局面,但大体的政治走向依旧是寻求统一。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自然气候、资源环境、人文生态等方面各有不同,导致了各地区的发展时常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针对这一问题,我国在“九五”计划中首先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并在随后的二十余年中不断对该理念进行丰富,其中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重视不同区域的独特性,在发展中进行结构、优势与功能的互补,最终实现各区域在经济、文化、自然、社会等方面可是持续性地协调发展。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这一重要任务。而“区域协调理念”的提出与施行,正是对“和而不同”这一文化精神传统的深刻践行。
就民族政策而言,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和而不同”观念的体现。依照张维为教授的观点,中国人是“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的。所谓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实际上是历经了“百国之合”式的民族大融合后所形成的一个整体概念。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就认为,一个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指的是在中国疆域内所有民族历经千年的交流与融合的结果——“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先秦时期诸如西戎、北狄等同中原文化相对立的民族,其政权同样与中原诸侯国建立了较为紧密的联系,表现最为典型的即是晋国。所谓“戎狄之民实环之”,“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而远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晋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同戎狄部落相邻,甚至当晋公子重耳去国逃亡之时的首选也是北狄部落。秦朝建立后,大一统的局面初步形成,随后,在中国千余年的发展进程中,历经了数次民族大融合,逐渐形成了以中原汉族文化为核心,多种民族文化共存的“多元一体”的东亚文化圈。民族间虽然时有矛盾冲突,但在总体上是向积极融合的方向发展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5]于是,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施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自治政策,完善了区域自治的制度,设立了省级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等行政区划,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利,促进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维护了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在2014年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新形势下做好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正确政治方向。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更好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由此可见,民族间并非是“他者”的对立关系,而应是在一个共同的理想与目标之下求同存异、和谐发展、团结友爱、交流互助的民族共同体。
三、文明型国家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
学界普遍认为,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文化差异与文化同质并存的时代”[6]。这就提醒我们需要重视并传承自身的传统文化精神,防止西方文化霸权对民族与国家的渗透。盲目追求西方模式最终只会逐步消解自身的文化与历史的积淀,丧失自身发展的独特性。保证历史与文化精神的积淀与传承,是一个国家能否保持稳定与长久运行的核心与基础。树立中国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并非是要同与自身相异的文化进行对立,而是向世界展现出一条以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为基础的全新的、独有的发展道路。
迄今为止,中国在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问题,然而也不能因此就断定中国走错了路,进而重新投入到西方话语系统中抄西方模式的作业。2020年末,有一种观点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三十年的启蒙已经失败了,越来越多我们想给予帮助免于恐惧的人,变成了痛恨我们的人。”针对这类观点,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辨析。首先,一批掌握了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将自己置于“意见领袖”的位置之上,“代表”人民进行发声。这在新世纪最初十年的舆论场中是极为常见的现象。其次,这批学者对于“启蒙”的解读令人惊讶的简单粗暴。对于他们而言,中国所特有的历史与精神文明传统很大程度上是应当加以摒弃的所谓“封建残留”,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应该逐步转向西方模式,以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理念为典范,在“理性”的感召之下,仿照西方建立西式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这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就中西发展道路的进行不同声音的探讨,而是将两者完全对立,并且认定西方模式要优于中国自身道路的偏见。简而言之,这些人几乎默认了“西方中心主义”这一论调的合法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步走向巅峰,历史也在西方模式发展的顶峰走向了“终结”,并对当今中国的发展始终怀有所谓的“现代国家焦虑”。这种焦虑与盲从极为清晰地表征于当今的政治、学术话语之上——诸如“远东”“中东”等术语约定俗成般的使用,甚至还侵袭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如评价一个人“土气”与“洋气”的分别,实际上暗含着对前者的贬损和对后者的崇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所提出的“赶英超美”的目标虽然指涉于生产的范畴之中,但在其背后却展现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独立自主精神。然而在世纪之交,“赶英超美”逐渐蜕变为“学英仿美”,这实际上就是彼时在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熏染下中国大众日常生活以及心态上的反映。
所幸的是,时至今日,在“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传统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国人逐渐对自身的历史与文化精神产生了认同感,也逐渐破除了对诸如所谓“西方中心”“历史终结”的迷信。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大众媒介传播的蓬勃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逐步拉近,为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条件,让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们能够彼此分享与交流自身的文化精神与文化成果,这也是对以当代后福特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受民族国家的“惩戒性话语”影响,消解多元性与复杂性、建构同一性之资本主义文化——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一种反抗。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始终彰显着人道主义的人文关怀,重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和谐关系。尊重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精神传统,是历史赋予当代华夏儿女的重要任务,也是树立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的重要途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传统伴随着中华民族超越千年的生存与发展,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基础,“视国家为文明的监护者和管理者的化身”[7]的文明国家;也成为当下构建统一、多民族及多种文化和谐发展的文明型国家、形成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崛起路径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作为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中国的发展与崛起的路径势必要与西方不同。近年来一直在强调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的核心即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与传承,而“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正是这一核心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