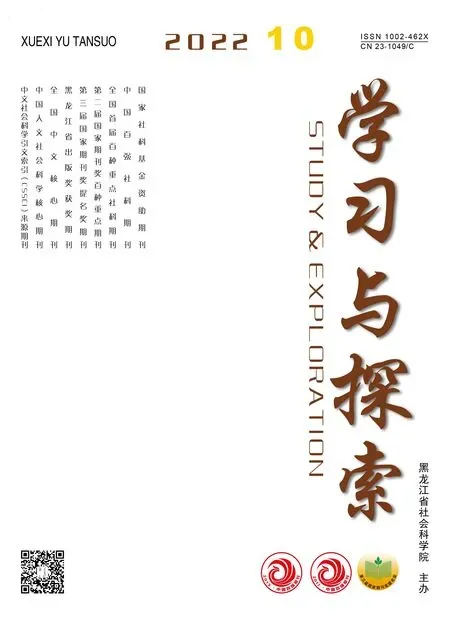风景:复杂的思维轨迹
金 钢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哈尔滨 150028)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来自哈尔滨的冯晏便登上了诗坛,在内地和香港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她早期的诗作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以及香港的《星岛晚报》《新晚报》等报刊上,《星岛晚报》还连续发表评论文章推介她的作品,认为她的诗歌是舒婷、北岛等新一代诗人之外又一个值得关注的声音。冯晏的诗歌创作以新世纪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原野的秘密》《冯晏抒情诗选》等为代表,偏重抒情,受普希金、莱蒙托夫、雪莱等诗人的影响较为明显,语言也比较浅白。在20世纪90年代,冯晏停笔了几年,2000年又重新开始写诗,陆续出版了《看不见的真》《纷繁的秩序》《镜像》《碰到物体上的光》等作品集,以及民刊“诗歌哈尔滨”系列诗集《小月亮》《边界线》《意念蝴蝶》等。冯晏2000年之后的诗歌可以看成她的后期创作,作品的抒情成分逐渐消隐,而哲思性却在不断增强。这种变化是脱胎换骨的,显示了冯晏对诗的本质的不懈追寻。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指出,“如果仅仅描写自然事物,或者仅仅叙述自然情感,那么无论这描述如何清晰有力,都不足以构成诗的最终目的和宗旨……诗的光线不仅直照,还能折射,它一边为我们照亮事物,一边还将闪耀的光芒照射在周围的一切之上”[1]。经过停笔几年的沉潜,冯晏对诗的本质与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诗不仅是写景抒情,还闪耀着人类思想的光辉。冯晏新世纪的诗歌更加睿智、深邃,能够使读者体察到新世纪汉语诗歌的多维时空建构,也给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
一、从风景空间到符号世界
《复杂风景——致维特根斯坦》是冯晏自己最喜欢的诗作之一。她在诗中写道:“你思维的轨迹,犹如/成群蚂蚁爬过的/白色细沙,惊人的密纹/足够我用破解密码的焦虑/去观察一生的。有多少/酷爱哲学的学友,蜗牛般/正在你的垄上穿越。”[2]71这里的“复杂风景”是动态的,从某种程度上看,风景在冯晏笔下从名词变成了动词,风景不仅是一个物体或文本,而且是一个过程,诗人的主体身份通过这个如蚂蚁、蜗牛般的思维爬行过程形成。米切尔认为,“风景在人身上施加了一种微妙的力量,引发出广泛的、可能难以详述的情感和意义”[3]1。看起来,冯晏发现了这种微妙的力量,并沿着复杂的、多向度的思维轨迹,用她的诗歌把“难以详述的情感和意义”表达出来。
对冯晏新世纪诗歌思维轨迹的探索应从空间开始。不管是在阿赫玛托娃的厨房、新圣女公墓,还是百慕大,风景在冯晏的诗歌中总是以空间的形式出现,诗人在空间中找到或者迷失自己。冯晏曾谈及俄罗斯文学是她无法绕开的情节,“俄罗斯文学始终贯穿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忧患”,“一个忧郁的民族对我的文化好奇心具有更加强大的魅力”[4]169-170。当诗人来到圣彼得堡,亲身拜访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的阿赫玛托娃的故居博物馆时,她从中发现了什么?或许是源于女性特有的敏感,诗人发现了厨房这一角落,“厨房,犹如一枚书签夹在暗处”[2]18。藉此书签,诗人翻开了俄罗斯文学的大书,并实现了从现实的小空间向词语的大空间的穿越。在《新圣女公墓》中也是如此,诗人徜徉在这片埋葬着俄罗斯众多历史文化名人的墓园,与果戈理、契诃夫等伟大的俄罗斯灵魂相遇,“为了果戈理,特朗斯特罗姆用诗句/打碎过圣彼得堡/犹如打碎一只水晶玻璃杯”[2]30-31。庞大的城市在冯晏的诗歌世界里被轻盈地打碎,穿透现实的城墙对灵魂来说轻而易举。
刘小枫在《诗化哲学》中谈道:“人之为人,并不只是在于他能征服自然,而在于他能在自己的个人或社会生活中,构造出一个符号化的天地,正是这个符号化的世界提供了人所要寻找的意义。”[5]对于一位诗人来说,可能符号化的词语世界比现实世界更为重要,个体生命是有限的,经历的现实空间也是有限的,而词语的世界是无限的,就如冯晏写阿赫玛托娃“在时间上死去,词语下活着”。诗人生命的价值或许在于竭尽全力把那种茫然无措的情感转变为诗词的真实可靠的力量,如此我们大概能够理解冯晏为什么会踏上百慕大的航程。在很多人看来,百慕大意味着飓风、海龙卷以及神秘的舰船失踪事件,是一个未知的、让人恐惧的地方,而正是探索未知的诱惑,让冯晏怀着内心的恐惧在百慕大的航船上度过了五夜,饱览了百慕大的奇异风景,写出了引起评论者广泛谈论的长诗《航行百慕大》。
如果说百慕大意味着未知与神秘,那么“航行百慕大”便是对未知空间的探索。《航行百慕大》呈现为五个夜晚的抒写,第一、三、五夜是从容优雅的诗行,表达了诗人智性的思考,第二、四夜却是连绵不断的长句,有的句子甚至一百多字没有间断,仿佛奔流不息的潜意识。如果说第一、三、五夜是诗人思维的阳面,那么第二、四夜就构成了暗面。在阳面是“我”的理性节制地冥思,“未来,我们是否存在,/只有词语知道”;在暗面则是“你”汹涌的情感和词语的洪流,“你在他们的文字未来中深陷沉迷,仿佛承担了被塑造过的宏大预知尽管你感觉自己突破甚微,整个旧时光似乎依然在你新发现的真理中重复。除了在百慕大海域的神秘消失人类那种无声大过有声”[4]113。在阳面与暗面的交替进行中,冯晏实现了对诗歌意绪的多向度探寻。《航行百慕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形式上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对词语紧追思维的多重表达。
冯晏对符号世界有着自觉的追求,她认为写作是“为破解词语所蕴含的最小粒子的突变与体力较劲”[4]2。于是我们看到,她在《一百年以后》中写道:“写作是蛇脱掉的皮。/如果幸运,词语可以穿过鳞。”[2]3对诗人来说,写作如蜕皮一样,艰难同时也意味着新生。冯晏新世纪的诗歌体现出了她高强度的思维能力和对潜意识的灵活运用,她所构筑的词语世界既让人困惑,又会激发读者破解谜题的好奇心。
二、作为媒介的风景
在冯晏新世纪的诗歌中,我们可以读到世界各地的风景,除了圣彼得堡、百慕大,还有卡蒙斯的塑像、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新疆浮雕以及那辆开往图们的绿皮火车。“夜晚,乘坐一列绿皮火车/去图们。黑色车窗犹如几处缺口/向旷野蔓延着。此刻/你不走动已在路上。”[4]73“你不走动已在路上”,旅客并没有走动,却已随火车奔向远方,恰如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命运,在不知不觉中被历史的车轮滚滚推动。在这个高铁、飞机四通八达,网络全面覆盖的时代,冯晏精准地找到了绿皮火车这一具有历史感的景象,透过车窗依稀看出时代的变化与记忆的裂痕。在冯晏的诗中,“风景是人与自然,自我与他者之间交换的媒介。在这方面,它就像金钱:本身毫无价值,但却表现出某种可能无限的价值储备”[3]5。通过风景这一媒介,冯晏实现了诗歌中地理图景、空间经验与精神场域的结合。
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交通工具的便捷以及旅游产业的推动,新世纪以来的旅行诗歌、见闻诗歌大行其道,冯晏的诗歌能否避免这种流行的俗套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冯晏曾说她与写作伴随的另一种兴趣就是旅行,“旅行所打开的眼界对于一位诗人具有着知识被膨化的作用,真理产生于真知灼见。是语言让万物作为万物而存在。作为诗人,我希望对事物的描述精准、细腻、视角辽阔”[2]184。诗人在与自然、与他者的联系中,直接经验是不可缺少的,对事物的判断如果仅仅建立在间接经验上,往往会浅薄、会出现偏差,而冯晏诗中的风景,是她在现实生活中深入游历的图景,也是她在不同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碰撞下的诗思迸发。新疆与黑龙江同样辽阔,却又有完全不同的地域风情,“一条皮鞭沉默着,让我了解羊群的天堂/就在白云之上!游牧的居所喜欢在内心建筑/天大的屋宇,取之不尽的光线/我正慢慢接近一份世纪遗产,像进入/一只饱满的香梨,正在接近感知的核”[4]132。同样是北方,黑龙江的风景是良田万顷,新疆却是戈壁、沙漠、牧民的羊群和甜美的水果。冯晏对生态自然有着敏锐的认识,她认为“自然,是视觉的远方,是苦闷的释放之地,是生活乏味的逃避场所,也是诗中情感被提醒以及抒发的最终指向”,“自然是诗歌永恒的依赖”[2]123-125。从生态自然方面看,新疆是与黑龙江截然不同的世界,于是走过新疆的诗人写道,“我仍在地球上生存却像我从地球归来”。
除了不同的自然生态,异域风景还包含着路德大教堂、古老的水塔、岛上的灯塔等西方宗教化的场景,以及奥林匹克广场、西贝柳斯故居、赫尔辛基书店等带有繁复文化功能的建筑和公共空间。当一位来自东方的女诗人置身于这些异质空间中时,她由此生发的陌生感和追问是意味深长的。“思维无法越过黑暗,不快的风景。/一张静止的合影照,空缺部分,/时间在流过,生命之间的冲突/将到何时?一个诗人在身体里/安睡着两个国家,或者更多。”[4]100-101冯晏表现出一种知性而又偏执的态度来面对历史与时代,诗人可以包容不同的国家与文化,而“那时代的真相”,显露在语言的“逆行部分”中,也就是说,诗歌“要离开一个又一个语言或语感的故乡”,“在一个信息嘈杂、心灵被阻隔的时代,以往语言的轻柔已经无法让你抵达深处的灵魂”[4]168。诗人是时代的审视者,在看清了时代之后,寻觅最恰当的词语与时代进行碰撞。
即便是冯晏这样一位从容的诗人,她的诗歌中仍或多或少流露出对当下时代的焦虑。当诗人身处异域时,祖国、汉语仍是她诗中不断出现的词语。“这时国内电话/一座新松浦大桥尾部垮塌/瞬间,道路成为深渊/死去的人,灵魂正迷失在途中”[4]137。诗歌从赫尔辛基奥林匹克广场突然转回家乡发生的惨剧,表现出诗人此时的痛心与震惊。冯晏的诗歌在极具哲思性的同时,是不乏现实感的,现实感“来自于一种共时性的作家对生存、命运、时间、社会以及历史的综合性观照和抒写”[6]。这种观照和抒写除了与当下时代紧密相关之外,也延伸到普适性的人的内心,冯晏说“真实是内心唯一宗教”(《北欧旅行片段·芬兰最南端,汉高小城》),她在充满了“忏悔”的异域风景中反思当代中国的命运与个体的命运,就如《一只黑色甲虫》里那只旅途中的甲虫,不厌其烦地翻越一座座“山峰”,却仍然要面对不可知的未来。
三、城市风景与城市文化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冯晏新世纪的诗歌就会发现,这些诗歌虽然具有很强的哲思性,但并不完全是玄之又玄的。比如,有关冯晏生活的城市哈尔滨的只鳞片羽时常浮现于诗中:暴风雪、露西亚、中央大街、波特曼西餐厅、呼兰河、萧红以及仍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诗友张曙光等,会让熟悉哈尔滨的读者会心一笑。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生活的城市是另一种风景呈现的形式,对城市的书写日益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部分。冯晏新世纪诗歌的思维轨迹密布在哈尔滨这座东北城市里,而城市风景的书写,在冯晏新世纪的诗歌想象中不仅是背景、环境,而且深入了城市文化、城市精神。
哈尔滨这座因中东铁路的修建而兴盛的东北边疆城市,具有浓郁的俄罗斯文化风味。以至于冯晏初访圣彼得堡的时候,竟觉得那里与哈尔滨非常相像,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过程使得哈尔滨具有了与北京、上海等国内其他城市不同的文化气质。俄日殖民统治、左翼文化思潮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重工业基地的兴衰等,都对哈尔滨的城市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笔者看来,冯晏新世纪诗歌所呈现出的哈尔滨城市文化特征主要有三点:其一,因地处东北大平原中心,水陆交通四通八达而产生的广阔、包容的气质;其二,大量俄罗斯侨民长期居留此地而形成的俄罗斯文化风味;其三,老工业基地衰落之后的锈迹斑斑的工业城市形象。
冯晏曾谈道:“哈尔滨处在北方辽阔地域的中心,辽阔本身对于诗人的创作是一种自然教育,犹如东西方文化或者思想对于诗人的教育一样重要。”[4]207这种地域的辽阔性在冯晏的诗歌中也有较为充分的表现,如她所写的《暴风雪》:“一层玻璃隔开严冬,/窗外冰河如白纸,/足迹让给平原。”[2]11暴风雪落得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如一张无边的白纸,人的足迹走在上面就像一行诗。由于太过辽阔,《暴风雪》显得空旷,甚至孤独。风雪本是纷繁密集的,诗中却说像“一只绵羊在草原追赶离散的白云”,绵羊应是成群的,诗中却只出现了一只。《暴风雪》所写极广阔,又极单调;极纷扰,又极宁静,在动静之中写出了地域的特色和诗人的心境。哈尔滨的春天因其短促而让人觉得特别珍贵,《立春》透露出春天生机勃勃的气息,“立春,转动着钥匙。/是时候放出被困在思想里的狮子、海豹了,/以及沙漠、花园和蜥蜴。/在解冻之季通往海市蜃楼的梦境里”[2]9。春回大地,诗人的思想也解冻了,释放出各种各样奇妙的词语和意象,甚至灵魂都“骑上一只野兔”,穿过枯草和荒原。
20世纪初大量俄国侨民和殖民者来到哈尔滨,他们在建设哈尔滨的时候一定程度上模仿了圣彼得堡。模仿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手段,不仅是建筑,写作也是如此,艺术创作往往是在模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冯晏在《复制或模仿》中写道,“旁边的中央大街始终像俄罗斯,/街上新增一个画街景的雕塑,/继续着伟大的模仿”[4]86。诗歌既展现了哈尔滨的俄罗斯文化风味,又进行了深入的哲理思考,“经验是创意的敌人。/复制是逃脱之绳打起的结”。诗歌写作离不开经验,杜威认为艺术即经验:“经验本身具有令人满意的情感性质,因为它拥有内在的、通过有规则和有组织的运动而实现的完整性和完满性。”[7]“诗是经验”是当代汉语诗歌的一个重要创作观念,李琦、张曙光、赵亚东等诗人都以丰富的诗作诠释了这一观念,而冯晏的创作并不满足于经验,她的写作是超验的,她试图把普通的词语带到更高的、更完美的层次。就如在《波特曼西餐厅》中,“我们背靠着印有列宁和叶卡捷琳娜头像的俄罗斯椅子”是现实的经验,“语言爆破像一场仪式”[2]64则是超验的。与北京、成都等城市的茶馆文化不同,俄式西餐厅可以说是哈尔滨的城市名片,华梅、露西亚、波特曼等俄式西餐厅常在文艺作品中出现,构成了哈尔滨城市的一个重要文化空间。在《波特曼西餐厅》中,文化空间的现实经验被词语的超现实爆破打碎,然后又重新组合成超验的、具有神秘色彩的诗句。
现代城市是钢筋水泥的森林,看起来是缺乏诗意的,特别是在哈尔滨这样一个拥有“三大动力八大军工”的老工业基地城市,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座城市的烟尘和锈迹同样存在着诗意,这需要诗人发现的眼睛。冯晏对哈尔滨的抒写不是单纯地写风景,而是把时势寓于风景之中。在《五月逆行》中,“道路拥堵犹如浮肿的腿”。在《这座城市有些偏远》里,“加入的车流,仿佛穿越一场战役。/拥堵甚至会一直深入你的梦中。/我时常梦见氧气在天边,成为商品,/梦见惊恐,身体丢失在心灵的后面。”[4]93拥堵是现代城市的顽疾,不管修多少马路、立交桥、地铁,在特定的时间段里,城市还是拥堵得让人绝望,“甚至会一直深入你的梦中”。《内部结构》有着对现代城市病的系统批判,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在诗中不断出现和累积。“都市,雾霾一次次越过母亲/新赠送给你的护身符,血管里/后来流进什么,父母一无所知/就像他们的血液,生你时/大自然还洁净”[4]145,这是诗人在烟尘滚滚的城市中的悲鸣。“杀虫剂在空中,雨里/和泥土深处,任由你血液/迎来送往”,这让我们想到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与卡逊女士一样,冯晏相信人类应该敬重自然,人类的生存与自然生态的平衡息息相关,而不像有些狂妄的人那样觉得人类能够统治自然。
在世界日益扁平化、同质化的今天,诗人如何提供个体经验,展开独特的想象与思考,成为衡量诗歌品质的重要因素。具体到城市书写中,城市不仅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它还有各自的地理特征与历史文化脉络,以及城市人灵魂的“内部结构”。有研究者认为,哈尔滨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以诗歌获得认同的城市”[8],而冯晏以其对城市文化精神的思考,以及起伏跳动的词语想象,为新世纪城市诗歌写作提供了难得的范本。
四、镜中风景
冯晏对哈尔滨城市的书写,不像李琦、张曙光、桑克等诗人那么直接、完整,而是隐晦、破碎的,需要读者去重新拼接。应该看到,城市形象、城市精神并不是冯晏书写哈尔滨的终点,她对城市文化精神的书写仍是诗歌的表象,她的思维轨迹并没有停留在伦理化的城市空间,而是强力地探入到城市人的内心。评论者多强调冯晏新世纪诗歌的哲思性与潜意识等深层次的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哲思对诗歌的影响,或诗歌对哲思的反映并不是以直接方式进行的,而是以“镜像”的形式迂回展开。冯晏认为,“对于一首好诗来说,其中一点就是怎样把思想隐藏好”[4]2。在冯晏的诗中,她的思想是隐藏的,不那么直露的,概念性的思考转化为了意象的蝴蝶,需要读者去耐心地捕捉。诗集《镜像》的封底选取的是《镜子》中的两句诗,“镜子里的我是精细的,/她听到生活发出撕纸的刺耳声。//然而,粗糙是一种诱惑,始终都是”[4]3。这两句诗大概可以看成冯晏新世纪诗歌的自况,她的诗歌虽然是精细的,却是粗糙生活与复杂内心的镜像,诗人通过镜像的折射去追求真理。
梦是冯晏新世纪诗歌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仲夏夜之梦》中,“一条花蛇从梦中向外张望”;《旅行在凯恩斯》里,“她随幻觉出海,反而从梦中惊醒”;《灰空气》里,“你梦见视线穿透屋顶,比昨夜梦见翻过乌云寻找星星还要低”。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大致能够看出,“梦”所包含的象征意义对诗人的重要性。梦是人类思维的隐秘部分,每个梦都是有意义的,诗人试图通过梦境来解析人类的潜意识,就如她在《走进梦境》中所表达的,对于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来说,梦与现实互为表里。在《清晨的局部速写》中,冯晏引入了“捕梦网”这一意象,捕梦网源自18世纪的印第安人,传说好梦能从网中的圆洞流出来,而噩梦会被困在网中,并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彻底消失。这一奇妙而又美好的意象让人印象深刻,并且恰恰指明了梦处于真与假的边界,从梦境出发,真实与想象、过去与将来、家乡与远方、生与死等不再相互对立,这或许是超现实主义提供的一种超真实。然而,若想在超现实主义的诗歌里寻找一个确定的支点,那恐怕是徒然的,就如冯晏所写,“梦境对神经系统进行解密,/研究,最终是徒劳的”[2]8,我们所能发现的只是若有若无的定位的希望而已。
冯晏新世纪诗歌中所描写的景象大多是生活的细节,是诗人的经历以及旅途印象等。这些细节是真实可感的,但细节之间的现实关系却被诗人用梦境化的手法打碎,我们大致能够感受到梦境的色彩,却理不清梦境的逻辑。诗人甚至有意制造了观察的困境,“镜子里的我刚穿过梦中瀑布”,我们需要通过瀑布、梦、镜子三重阻隔来观察诗人的内心,这种多重阻隔带来神秘的效果。冯晏曾说,“我确认每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与神秘主义的区域相接通的路径,一首理想的诗作给写作者本人带来的欣喜不可言说,只能体会。”[9]诗人有意营造的错位、颠倒、迷失等等,可能正是梦境的迷惑,它将读者引向缝隙之下的深渊,一种深层的、超验的真实。在《缝隙与日月》中,“铅字已经深陷在缝隙里,/仿佛不合时宜的幽静生活。/还有笔记,被追忆拉直的横与竖,/撇和捺的飞扬时光,她都留恋。”[4]66诗人甚至不满足于意象与词语的破碎,连汉字都要拆解为笔划,从而在汉字的缝隙中发现真理。或许诗歌的真理就在于以字词的重新拼接来抓住事物隐藏在缝隙中的核心,词语的力量是巨大的,“几个词就能划伤全部,这并不夸张”(《渐行渐远的日子》)。
在新世纪以来的汉语诗歌中,日常性、历史性、叙事性等是较为常见的诗歌审美范式。与这些范式不同,冯晏的诗歌带有强烈的超验色彩,执著于探索词语的奥秘,表现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她认为,“诗歌写作就是让诗人去体验发现奇迹的感觉。你的才华需要在每一首完成的诗歌中去被时间检验。虽然有些无情,但给出的标准一定是真理”[4]166。冯晏在她的诗中并没有给出真理的明确定义,但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她通过诗歌的镜像所进行的迂回的词语与思想的创造,就是她诗歌的真理所在。
结 语
不管怎么说,冯晏新世纪的诗歌是晦涩、难懂的,在阅读、阐释她诗歌的过程中,常会想到阿伦特所说的:“讨论诗歌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任务。诗歌可以引用,却不宜用来讨论。”[10]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诗歌的“晦涩”不能仅归咎于诗人所采取的表现手法。“诗歌的‘晦涩’有它的认识论方面的来源。人的认识本身就包含着‘晦涩’的成分。而诗歌作为一种人的认知方式,只不过比其他的认知方式更强化了其中的‘晦涩’成分。”[11]冯晏新世纪诗歌的思维轨迹构成了复杂的风景,犹如一座迷宫,不过,冯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迷宫的入口,比如新疆“大巴扎市场一块小玉的裂缝”,又如波特曼西餐厅“被缝合后又重新开启的唇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