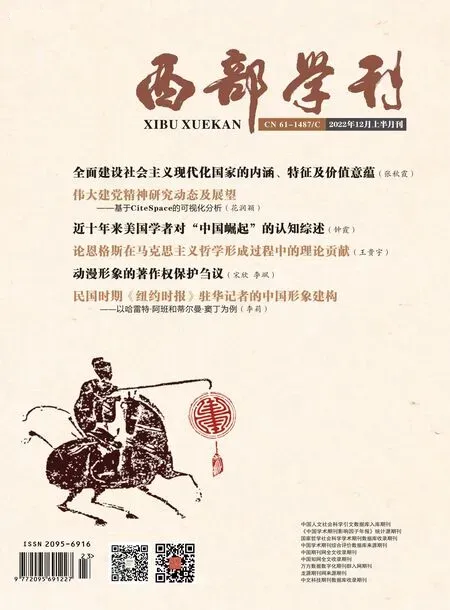金世宗朝储位之争新探
邓子聪
金世宗一朝的立储得益于世宗秉承中原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与预立太子之制,因而其与章宗之间的传位被认为是金代嫡长子继承制下皇位顺利交接的成功典范。但此间过程的曲折,尤其是太子允恭与世宗及其兄长永中之间的矛盾同样不可忽视。允恭虽不是金朝首位皇太子,但此前熙宗与海陵朝的济安、光英两位太子皆未及成人而亡。相比之下,允恭在储位二十五年,为金代皇太子制度的构建打下了基础,具有更高的研究价值。前代学者如张博泉、陶晋生、刘肃勇等在论述世宗、章宗的权力交接中都只着眼于章宗,而对允恭在大定年间的政治作用关注不足。董四礼、刘浦江虽注意到大定年间世宗诸子的斗争但并没有对此问题做深入论述。近年虽亦有学者进行相关研究,但未有新论产生,这使得世宗朝皇位传承的研究目前仍缺乏整体连贯性①。对世宗朝储位之争的研究既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金朝内部的政治矛盾以及世宗为政的方式与特点,同时可从新的角度认识金世宗与其治下朝堂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一面。
一、皇太子允恭的储位危机
女真人早期的权力传承方式比较原始,一般由前任首领的兄弟、子侄中实力强劲或才能出众者继任,这种方式虽能选出优秀的领导者,但易导致参与竞争者过多,引发统治阶级内部夺权的残酷斗争。在入主中原后,为了皇位传承的有序,减少内耗,金朝皇帝将汉文化中的嫡长子继承制引入女真宫廷,这个过程以熙宗为始,经海陵王完善,至世宗时金朝的皇太子制度最终确立。金世宗一朝共立有两位储君,分别是世宗的嫡长子完颜允恭与嫡长孙完颜璟。世宗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因而对名位的问题极其看重,加之大定初年朝局尚未稳定,因此其在正式称帝后的次年便“立楚王允迪(即允恭)为皇太子”[1]127以稳定人心。在面对立嫡还是立长这一传统政治难题时,世宗最终选择嫡长子允恭为储君,这不仅是他深受汉文化中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影响②,更多还是出自于对未来朝局的考量。允恭的生母昭德皇后出身于女真乌林荅部,对于一向倡导女真旧俗并有志于重振宗室的世宗而言,允恭纯正的女真血统更有利于他在日后继承世宗的政治事业,这是其他带有渤海、汉血统的皇子们所不具备的先天优势。
然而作为金代宫廷中第一个成年的皇太子,允恭的处境却并不乐观。尽管允恭“在东宫二十五年,不闻有过”[1]416,但世宗与他的矛盾却在日益加重。《金史》虽对此未有明言,却也为后人留下了礼仪之争与赵承元案这般蛛丝马迹。
在皇家礼仪上,世宗一改旧日女真宫廷礼仪的混乱之风,严格要求行汉制以定尊卑。大定六年(公元1166年)世宗自西京回都时,礼官依海陵朝制使皇帝与皇太子车驾共行玉路并以太子车驾在前,引起世宗不满。最终,此事以“礼部郎中李邦直、员外郎李山削一阶,太常少卿武之才、太常丞张子羽、博士张榘削两阶”[1]411的处罚而结束。同年末,世宗因授皇太子册宝的仪式问题再次表露出他坚决不允许皇太子礼仪超过自己的态度。《金史·仪卫志》载,“明年(大定七年),将册皇太子,宰臣奏当备仪仗告庙,上曰:‘前朕受尊号谒谢,但令朕用宋真宗故事,朝服乘马,于礼甚轻,今皇太子乃用备礼何耶?’丞相良弼谢,上徐曰:‘此文臣因循,不加意尔。’”[2]950此处世宗所谓的“前朕受尊号谒谢”是指大定五年(公元1165年)“三月壬申,群臣奉上尊号曰应天兴祚仁德圣孝皇帝”[1]136一事。宋真宗朝服乘马是因其继位时王继恩变乱所致,金国群臣以宋人特例,让世宗以朝服乘马的轻简之礼完成上尊号的仪式显然令世宗不满。朝臣对自己与太子所用礼仪规格截然不同的态度,则令世宗感到皇权受到了威胁。最终,世宗以“前后不称,甚无谓也”[1]411的理由否决以备礼册皇太子,既维护了自己在政治礼仪上的权威,更以礼法的形式将皇太子的影响力牢牢压制在皇帝之下。
作为通过政变登基的帝王,世宗与前任海陵王一样极重视君权的集中,而从中国故有的历史经验来看,成年皇太子身边极易出现以其为核心的政治团体,成为皇权集中的阻碍。从《金史》与其他金代史料中几乎不见允恭参政记录的情况来看,世宗显然不希望太子过多干涉朝廷事务,赵承元案的爆发则证明世宗对允恭在朝势力的不满达到了高峰。“(大定十八年十一月,公元1178年)戊寅,上责宰臣曰:‘近问赵承元何故再任,卿等言,曹王尝遣人言其才能干敏,故再任之。官爵拟注,虽由卿辈,予夺之权,当出于朕。曹王之言尚从之,假皇太子有所谕,则其从可知矣。此事因卿言始知,其不知者知复几何。且卿等公受请属,可乎?’盖承元前为曹王府文学,与王邸婢奸,杖百五十除名,而复用也。”[1]171-172赵承元得以再任,乃是曹王永功偏私包庇所致,与皇太子无涉。世宗在申斥宰臣与曹王后特别强调自己作为皇帝的“予夺之权”,但随即突转话锋,将矛盾对象预设到了太子,这种突兀的转折显然是针对太子的借题发挥。尽管未有明证显示允恭与朝臣间的关系是否如世宗所猜忌的那般紧密,但世宗这种毫不避讳的言辞充分表明他对太子缺乏信任。由此看来,至少在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时,世宗与太子间已生嫌隙,而从后续的发展看,双方的矛盾甚至可能危及允恭的储位。
关于世宗在大定十八年前后是否产生了废储之心,可从《金史·石琚传》中找到相关证据。“大定末,世宗将立元妃为后,以问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无异辞,如东宫何?’世宗愕然曰:‘何谓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东宫摇矣。’世宗悟而止。”《金史》对此事的发生时间只有模糊的“大定末”,方秋爽论证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应在大定十八年至大定二十一年间[3]。据《金史》中“(大定十九年)八月壬辰,尚书右丞相石琚致仕”[1]173后“即命驾归乡里”[4]1970的记载,笔者认为此段对话的时间当介于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八月至大定十九年(公元1179年)八月间,正好处在赵承元案发生的前后。结合此时世宗与太子的嫌隙来看,他向石琚询问立后一事的背后含义极可能是在试探石琚对储君问题的态度。从石琚的回答看,他已表明“太子不可动摇”的观点。石琚之所以如此坚决支持允恭,除了他作为太子师傅的个人情感外,朝中汉臣们对汉化成果(以嫡长子继承为代表)的维护态度应当是支撑他反对世宗立后的重要原因。从结果来看,石琚的表态应是允恭储位不失的重要助力,而允恭显然对石琚十分感激,石琚致仕后“显宗亦思之,因琚生日,寄诗以见意”[4]1963,可见两人间关系之亲密。这一系列隐藏于史料背后的细节虽不能完全还原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世宗在易储问题上的犹豫,但大定十一年(公元1171年)世宗对太子所说的“吾儿在储贰之位,朕为汝措天下,当无复有经营之事”[1]150,恐怕不仅是单纯的爱子心切,更有告诫太子不要过多插手政事的含义。而世宗此时所说的“子为众爱,愈为美事”[1]150到了大定十八(公元1178年)至十九(公元1179年)年间已经转化为对太子隔阂与防备。
世宗为何对太子的态度由大定初年的寄予厚望渐渐转向提防排斥?对这一问题除了从担心太子威望过高威胁皇权的角度看以外,还要从世宗朝的汉化问题入手。作为对金朝汉化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一位皇帝,世宗虽对汉文化特别是儒家礼教极为推崇,但也始终担心女真族被完全汉化而丧失民族性,因此其在学习汉制典章的同时大力推广女真族文化,保持女真旧俗之风。作为太子的允恭与其父不同,虽然《金史》未记录允恭对汉化的态度,但刘祁在《归潜志·辩亡》一篇中有如下论断“宣孝太子最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向使大定后宣孝得位,尽行中国法,……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5]。可见金末的儒家士大夫认为允恭有孝文帝之志。北魏的孝文帝改革尽废鲜卑旧俗,实现了北魏政权的完全汉化,允恭若真有孝文帝的政治理想,则其与主张保守女真故俗的世宗是极有可能产生冲突的。其实世宗对皇太子不熟悉女真故俗一事早有微词,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三月,世宗曾对宰臣言“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1]158-159。与此相对,世宗对章宗通习女真文字十分欣赏,“朕尝命诸王习本朝语,惟原王语甚习,朕甚嘉之。”[1]208可见通晓女真文化对世宗而言是评价继承人的重要标准之一。从可见证据中看,允恭并未在文化问题上与父亲针锋相对,随着时间推移,允恭对世宗坚持女真文化的政策表现出认同。《金史·完颜匡传》记驼满九住与完颜匡辩论经史后,“显宗叹曰:‘不以女直文字译经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直科举,教以经史,乃能得其渊奥如此哉。’”[6]2164后来允恭命完颜匡作《睿宗功德歌》,让章宗于大定二十三年(公元1183年)万春节时为世宗演唱,以彰显祖先功绩。世宗由此大喜,“顾谓诸王侍臣曰:‘朕念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孙无由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其子,嘉哉盛事,朕之乐岂有量哉。卿等亦当诵习,以不忘祖宗之功。’”[6]2165这表明此时允恭对世宗的政治追求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而投其所好,二者间在文化问题上的矛盾显露出缓和的趋向。
二、永中与允恭兄弟围绕储位的矛盾与争斗
完颜永中是金世宗的庶长子,其母张元妃出身渤海大族,他的母舅张汝弼则是世宗一朝重要的大臣。由于世宗有意扶持,加上母家的政治帮助,永中的实力不断增强,并对其弟的太子之位产生了非分之想。历来学界对允恭与永中兄弟间的政治矛盾进行分析时,常将大定十九年(公元1179年)昭德皇后改葬仪式上的礼仪之争作为重点分析的对象。然而在《金史》之外,还有其他的文献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到更早关于二人矛盾产生的时间线索。
据宋人楼钥的《北行日录》记载,宋乾道六年(金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楼钥由金返宋时,于相州安阳驿的“把车人”处得知“越王不平其弟为储,国主曾以女小底十人赐之,逊谢不受,云:‘他日生出孩儿来,亦无用处’”[7]。从车夫口中的故事来看,永中(即越王)对储位的野心和对父亲世宗的不满已跃然纸面。驿站车夫虽是底层人群,但他们常年行走于全国各地,对各种消息最是灵敏,故而此事虽不见于正史,却通过这种闲言碎语的方式被宋人所知并记录下来。由此来看,早在大定十年时,永中与允恭兄弟间就已因储位而生隙,虽然当前没有更多的文字证据证明此时他们斗争的激烈程度,但连驿站车夫都对永中不满太子的言行知晓得如此详细,恐怕此时世宗二子不和的事情早就在金国上下人尽皆知。
大定十九年,昭德皇后改葬大房山坤厚陵仪式上的冲突标志着世宗朝的夺嫡之争由隐蔽正式走向了公开。史载“永中以元妃柩先发,使执黄伞者前导。俄顷,皇后柩出磐宁宫,显宗徒跣”[6]1898。依照礼制,永中之母李元妃的灵柩应当位于皇后的灵柩之后出发,且金代诸妃嫔导从皆有定制,“伞制,皇太子三位妃皆青罗表紫里、金浮图”[2]959,永中以执黄伞者为前导是逾越的行为。面对此等挑衅与羞辱,允恭表现出惊人的隐忍与宽容,不但不追究永中的逾越行为,甚至为其开脱“是何足校哉,或伞人误耳”,并阻止少府监张仅言上奏此事。尽管永中的野心早已显露,但在如此重要的典礼上公然羞辱太子,恃宠而骄恐怕已不足以形容其狂妄。联系前文所分析的大定十八年(公元1178年)时世宗对允恭的不满与动摇,永中的行为似乎正是要向世人宣告太子的失宠以打击太子的政治势力。
然而在大房山改葬风波的两年后,永中于“(大定)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改判大宗正事”[6]1898,《金史》未言此事是世宗对永中的处罚,但由执掌军权的枢密使迁为有名无实的大宗正表明世宗对他掌握军权的忌惮。同时,大定十九年(公元1179年)后的史料再没有出现世宗打击太子的记录,可见双方的关系在波折后日趋缓和。世宗希望借永中之力打压太子却也不愿他在朝中坐大,当世宗与太子走向和解,削弱永中的权力便势在必行。
三、结语
金世宗朝围绕储位的政治矛盾从表面上看是由于世宗纵容庶长子永中的野心导致,但其背后还有着世宗与允恭在选择女真传统文化与汉文化道路间的矛盾,以及朝廷内不同势力的推波助澜。尽管《金史》称大定朝“群臣守职,上下相安”,然在立储问题上朝臣们却有明显的派系之争,虽然关键时刻世宗仍存有乾纲独断的决心与实力,但因其犹疑的性格与对太子的猜忌一度使得太子的储位岌岌可危,也催化了其他皇子的僭越之心。随着历史的发展,世宗一力促成嫡长子允恭与嫡长孙章宗登上储位以继承他强化金朝宗室与国内女真族力量政策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永中、永蹈二王相继以谋逆罪死于章宗之手,章宗及其后的金朝皇帝对宗室的不信任导致宗室的力量不但没有增强反而成为被严格防范的对象日趋衰弱。至于世宗欲借发扬女真旧俗巩来固女真人共同的民族记忆与民族情感,防止本民族过度汉化的战略虽被章宗部分继承,却无法扭转女真上层群体日益腐朽、庸懦的趋势。
注 释:
①关于金世宗向金章宗权力交接的相关研究可参见:张博泉《金史论稿》、陶晋生《金代的政治冲突》、刘肃勇《金世宗传》、董四礼《金代皇位继承制度试探》、刘浦江《渤海世家与女真皇室的联姻——兼论金代渤海人的政治地位》、茌家峰《金朝皇位继承研究》、方秋爽《金世宗及其子孙皇位争夺问题研究》、薛振威《浅析金朝皇位继承制度》等著作。
②世宗对嫡长子继承的支持亦可参见《金史》中其他案例,如《突和速传》中突和速正室与次室二子争袭猛安,世宗对此的裁决是“‘次室子岂当受封邪。’遂以嫡妻长子袭”(脱脱,等.金史: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03),由此可见世宗对嫡长子继承制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