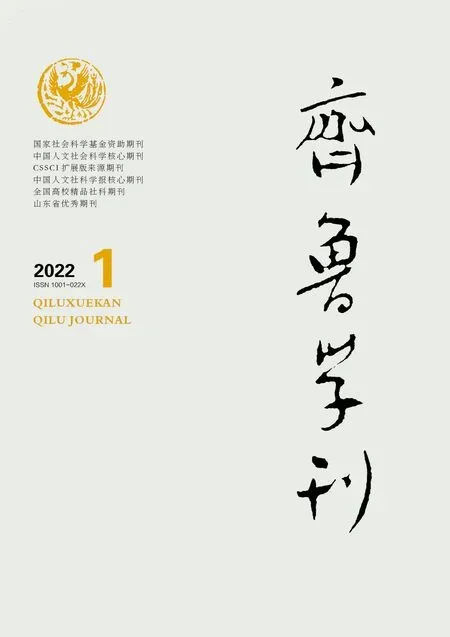中国德育研究的认识论困境及突围路向
孙彩平
(南京师范大学 道德教育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24)
知识是人类意识的一种形态,也是影响现代社会运行的重要力量。认识活动如果对自身缺乏认识论的敏感,就缺少了自我反思的自觉性。德育研究,如同教育研究、甚至更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然科学研究一样,都是人类的认识活动,它必然以某种认识论为基础,增进人类对自身及所在世界的理解。
德育研究的认识论,不同于道德认识论和教育认识论,尽管它们之间有些关联。道德认识论(Moral Epistemology)关注的是道德认识的独特性、道德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它作为认识论的一个分支,早在二十多年前在国内就已引起关注,其中以廖小平的《道德认识论引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为主要代表,但后续的专门研究非常少见,且多杂糅在对哲学家、伦理学家思想的研究中。在英文文献中,Zimmerman Aaron是一个重要贡献者,他出版了以《道德认识论》为名的专著(Taylor & France Group,2010),还在Routledge出版了道德认识论的研究手册(2018)。教育领域的认识论研究,属于比较高冷的话题,一直只是少数学者的兴趣(康永久,2005;雷云,2011;朱新卓,2015;金生鈜,2015;薛晓阳,2018),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教育知识生产的社会性、科学性以及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但德育研究的认识论既不等同于道德认识论,也不与教育认识论完全重合。德育研究的属概念既不是道德也不是教育,而是研究,是以生成由概念和命题构成的知识体系为使命、以德育经验为对象的认识活动。
迄今为止,国内德育研究中的概念体系,基本上是以教育学为摹本的,德育学的基本框架,也与教育学大同小异。这一知识体系的现实状况表明德育研究作为教育研究的一个次级学科的知识依赖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德育研究本身认识论自觉的不足。认识论作为德育研究展开的哲学基础,为德育研究合法性提供理论辩护,同时也规范德育知识立论的基础,生产的过程、方法与原则,为德育知识表述提供指导性原则与规范。认识论自觉是当下德育研究急需提升的一个方面,也是当下德育研究从方向到方法急需明确的一个问题。
从认识论的视角看,部分地由于文化性和历史性原因,当前中国德育研究深陷三重认识论困境。困境或者说危机有不同的出现形式。突发性的危机常常横空出世,致使我们的生活世界旦夕惊变。这种危机带来的混乱极具震撼性,容易吸引反思性的目光。而另一种危机却在不知不觉间,以日积月累的方式进入和改变世界。在走向这种困境的途中,人们甚至是满怀着欣喜和期待的,以为正在走向进步与美好,浑然不知路的尽头可能是深渊或断崖。德育研究的认识论困境,在今天看来是后一种情况,是一种日积月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一、中国德育研究的三重认识论困境
(一)先天不足。中国五千年文明,有丰厚的文化积淀。中国哲学,李泽厚说基本上是伦理哲学,这其实是德育研究的一笔丰厚文化遗产。纵览国学经典我们会发现,以伦理为中心的中国文化,有对人生、社会与世界的深刻洞察,形成了一整套家国天下的伦理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表现出对生活本身或者说伦理实践的强烈关注,在“思”与“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使得由“思”至“行”和由“行”至“思”有着顺畅的双向通道。然而对于“思”本身之思,却略显薄弱。
中国文化采用“道出结论”的方式,即直接讲出自己思考的结论,并不关注这个结论的获得过程。在“思”的类型上推崇类比、打比方,所谓“善喻者,以一言明数理”,以适合、仿效、类推、交感为基本思维路径,以相似性作为推论的依据,属于福柯所说的相似性知识型(1)[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3-25页。。这种由相似性获得知识的方式,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直观明察,而非逻辑证明和推理。因为直观是直接获取式,几乎没有过程,所以对知识获取本身的思考一直没有成为这个文化体系关注的问题,尽管它也触及到了“思”。耳熟能详的庄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发问,可以说非常精要,可惜只是触及,缺少更深入的对这个“知”或“安知”本身的“思”。到宋明理学,张载区分“德性所知”和“见闻之知”(2)张载:《正蒙·大心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4页。,触及伦理之知的特殊性,非常可贵,但依然没能形成对伦理之知的体系化思考。有深刻的洞察,却没有对洞察本身的洞察,没有对“思”本身的系统思考,这是中国文化的先天不足。我们至今还没有从知识论视角解释中国伦理体系绵延不绝的原因,甚至这一思路本身也尚待开启。
(二)后发劣势。作为后发现代国家的中国,可以借鉴先发国家的诸多已有成果,享受先发的溢出(spillover)效应,即“搭便车”。理论上这可以避免先行者的试误过程,少走弯路,节省时间,即常说的后发优势。实际上,后发的劣势也赫然在目:搭别人便车只能随车走,失去了自己选择的可能。且不说上车时的被迫无奈与途中遭遇的被排挤、歧视等,上车不易,下车更难,更为严重的是可能会不觉间随车一同走进深渊。中国文化领域的现代化基本上是搭西方文化的便车,在吸收西方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展开,这对中国走出封建治理模式无疑起了极大的助力作用。尴尬的是,现在看来,孕育现代西方文化的理论体系在认识论上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批判与弥补这一根本性缺陷,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题。而搭在这个车上的我们却对这个根本性的缺陷尚不明就里,甚至趋之若鹜!
其实在我们20世纪上车之前,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已经开始对二元对立的现代理性主义认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后来胡塞尔直接用“危机”来定义近代西方科学与哲学状况。在胡塞尔看来,近代哲学中的实证主义将科学的理念还原为纯粹事实的科学,走上了单纯追求客观化、精致化、逻辑化的道路,“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意事实的人”(3)[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5-30页。,其在根基处丧失了对生活的意义支撑。胡塞尔提出了一个被大家忽视的认识论问题——直观的意义。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主义的认识论无法抵达生活意义,生活意义有不同的认识论路径。前者依赖逻辑实证提供可靠性保证,后者却由先天直观形式通达本质。在胡塞尔之后,海德格尔继续以时间性为切入点,深入阐明了在世“操心”着的此在何以组建意义世界的日常生活环节,将“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存在论研究的基本任务”(4)[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3页。。舍勒则明确将“直观明察”作为伦理认识的独特方式并将先天直观从纯粹形式扩展到质料,“打破了观念对象只局限于理智理性的知识论模式,指明了观念对象可以作为价值质料在情感的感受活动和明察性体验中自行呈现和自身给予”(5)邓安庆:《现象学伦理学对于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要?》,《现代哲学》2016年第6期,第54-61页。。这是现象学派拯救近代欧洲(西方)哲学和认识论危机的努力。
而大西洋彼岸的杜威,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也深刻认识到西方哲学传统的内在局限,努力通过“经验”实现理性与实践间的超越。他将经验解释为主动与被动的独特结合:尝试(trying,这一点在实验中清晰可见)与承受(undergoing,承担尝试的结果),提出认识就是在人对物有所行动、同时承受物因人对其行动而产生的反作用这一人与物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发生的(6)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State College: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1),145.,尝试以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为切入点,实现西方哲学困境的突破,并自诩为真正的哥白尼式的革命(7)[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4卷,傅统先译,童世骏译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6页。。稍后在瑞士,皮亚杰带领“发生认识论国际研究中心”进行跨学科的探索,从发生学的视角证明建构主义认识论,强调认识结构“既不是预先形成于可能性的理念王国之中,也不是预先形成为客体之中,又不是预先形成为主体之中”,实际上“不能归结为一组初始条件的状态”(8)[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王宪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4页。,以此突破西方文化中的唯理论、机械经验论和主观先验论传统,明确“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9)[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第21页。。不同于皮亚杰将“活动”作为认识发生的起点,芭拉德(Karen Barad)以量子力学经典实验为基础,超越玻尔(Bohr),把“现象”而非具有内在边界的独立客体作为最基本的本体论单位,从物理学这一经典科学体系内部提出了弥合现代科学认识论之主客二分的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10)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Durham &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97-139.。20世纪后半叶,席卷欧美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则更是将对现代哲学的批判与重建推进到所有领域,在此基础上延伸至今的“后—主义”(post-ism,如后人本主义、后基础主义等),无一不是西方现代思想家试图突破西方文化内在困境的殚精竭虑的努力。更有一批西方的思想家,意识到在西方文化内部实现超越这一思路本身的局限,提出“迂回式”(detour)文化研究思路,将目光转向古老的东方哲学,以异域文化为方法,“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11)[法]于连:《道德奠基》(前言),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福柯说“真理史上的现代,是从唯有知识可以通达真理的时期开始的”(12)[法]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16页。,这意味着主体无法通过获得真理而回到他自身、改变其自身的精神世界。福柯一语道破现代知识论观念下知识与人的精神性之间的分裂,即知识的获得和一个人的精神性成长间的分离,真理与主体的分裂。这其实也是我们已经深刻感受到的知识与德性的分裂问题:一个人可能有广博的知识,但其德性或精神世界不一定崇高和丰富。而这种局面,在福柯看来,就是真理的现代性困境,在教育中体现为知识学习与包含德性在内的人的全面成长的分离。我们一百年前搭上了现代之车,现在正不自觉地随车走了一些弯路。要想真正在基础教育中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必须要先纠教育的现代认识论之偏。目前还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现代认识论。
(三)文化殖民之痛。国内的德育研究者在国际交流中都面临着一个困扰:如何解释或者翻译中国的德育这一概念。现在通行的做法,是把德育译为“moral education”。但这样的翻译导致了一个双面困境。一方面,“moral education”在英语的意义世界中有自身的文化和社会内涵。在西方,现代教育作为世俗化的文化生活空间,以保持宗教和政治中立为价值前提,非宗教性和非党派化是moral education的价值论前提。但德育在中国这一非宗教文化语境中,自古以来就担当着“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政治和文化使命,是建构文化团结和共识的重要力量。所以用moral education翻译德育,实际上是把中国德育放在宗教与政治中立的框架内去思考,这就非常容易得出中国德育存在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灌输问题的结论(13)参见Lee, W.O., & Ho, C.H.,“Ideopolitical Shifts and Changes in Moral Education Policy in China,”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34(2005:4): 413-431; Li, M.S.,“Changing Ideological-Political Orientations in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Some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Reflections,”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40(2011:3):387-395.。但从中国文化来看,纯粹的心理学化的道德教育,仅限于促进个体人格的发展,无法担当中国社会的文化建构和社会团结责任。这是一个削足适履式的困境。
如果说这还是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困境,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在这一思路下中国学术概念与本土文化内涵的剥离。当我们把德育=moral education,德育研究的议题就随之转化为moral education的议题,从而使德育研究转变成了文化意义上异己问题的讨论,即我们在德育概念下讨论的却是moral education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最近先由学术界发起随即成为国家教育方案的“核心素养”中看到其典型状况。“素养”是一个承载着中国文化内涵的概念,“素”原指“以麦杆为原料的草编”,在中国古文中转义为“未染色的丝绸”,再转义为“日常”,所以“素养”的本意是指“日常的修养”。由此而言,“核心素养”当是日积月累而成的重要修养。但在学界,“核心素养”这个概念从出现到意义解释,完全不是在汉语意义上展开的。“核心素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作为key competency的中译文出现的,国内学者界定“素养”的产生和内涵大都参考西方学界对于competency的界定,通过厘清OECD、欧盟或美国对于competency的理解来阐发“素养”的意义(参见张华,2016;崔允漷,2016a,2016b;柳夕浪,2014;李艺、钟柏昌,2015)。核心素养=key competency,核心=key,然后讨论key是重要的,还是基础的;素养=competency,然后讨论素养是competence, skill, ability还是literacy。在这个汉语字形下,所添加的完全是英语的意义与内涵,汉语的意义被替换了,只保留了声与形。如果说意义是语言的灵魂,那么这一概念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灵魂;如果说语言是存在的家,那么这个家中的存在已经被置换了灵魂。类似“素养”的例子在目前的教育学甚至整个中国人文学科“如此普遍和自然,这些非西方文化的使用者们对此竟熟视无睹。结果,在不知不觉中非西方文化的知识系统被蚕食了”(14)Zhao, W.,“Problematizing ‘Epistemicide’ in Transnational Curriculum Knowledge Production: China’s Suyang Curriculum Reform as an Example,” Curriculum Inquiry 50(2020:2):105-125.。这是一个鹊巢鸠占式的困境。
除词汇本身的文化意义被替换外,更为深层的问题是:当我们在进行德育思考、教育思考,甚至其他各种思考的时候,赫然发现除了现代思维方式,我们已不再有别的思维方式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因被看作是落后的、封建的、缺乏科学性的,已经被先进的现代性认识方式取代了。我们何以如此了呢?
实际上,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非西方文化国家陷入了现代的以线性时间为基础的价值谋划之中。线性时间,将所有文化排列在一条不断走向未来的时间线上,并赋予后来的时间以更高的价值:先进、文明、进步。“在这一现代时间结构的框架下,将共时态转变成历时态的价值序列的过程中,在当下时刻(为现代性瞩目的此时此刻),一些民族(我们)注定永远处于落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位置上,注定永远走在忙碌的追赶路途中,这是由现代时间数轴上进步与落后的原初设计决定的。”(15)孙彩平:《传统与意义建构——一个时间哲学的视角》,《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年第3期,第1-6页。在这一设计中,过去的传统被定义为落后的、阻碍进步的,因而被无情地遗弃。所以我们对自身的文化传统错误地产生出鄙视甚至憎恨,同时也对时间数轴上排在前面的文化错误地产生出由衷的崇尚来。
这一由西方文化主导的全球化带来的非西方文化的危机,被葡萄牙社会学家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称为认识论危机(epistemcide)。这一危机的症候,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国内已经非常明显:西方的理论、概念、方法不只被认为是不同于中国的,更是被标定为先进的、科学的,它们成为中国学界的学术评判标准,主导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和研究热点,成为学术正确的标签。
先天不足、后天劣势和长期文化殖民,是当下中国德育研究面临的三重认识论困境。但这绝不是说中国的学术研究必须切断和世界的文化联系,那将会陷入闭门造车的境地,这在现代化、后全球化进程中显然是不可能的。揭示这一处境的目的是意在提醒:在开放与引进时要有清晰的文化自觉,以防卫的文化立场和拿来主义的姿态来面对多元的、其他的文化,在现代化的裹挟中实现自身的认识论与文化重建。
二、中国德育研究认识论的突围路向
20世纪前后,面对日益技术化、工具化的科学主义认识论带给西方/欧洲世界文化和哲学的危机,胡塞尔重新发现“直观”的认识论意义,以“回到实事本身”、悬置科学主义认识为突破口,提出了对20世纪西方哲学重建影响深远的现象学理论体系;面对西方文化的现代困境,法国文化学家于连则将视线转向东方文化,希望通过“迂回”到中国这一西方文化的外部以实现自身的一种“进入”。这些智慧给我们的认识论突围带来启发:置身世界中,深入自身文化和问题的研究。
(一)接续和深化传统。面对教育研究的现状,刘铁芳感慨说“我们的研究根本上就陌生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与价值理路”(16)刘铁芳:《教育研究的中国立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1-7页。。回到中国经验,回到中国自身的问题,其实首先就是回到中国传统自身。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转身,因为回到传统的本质不是停留于了解,而是要接续和深化。这需要做中国德育的考古学、谱系学和解释学研究。
之所以说艰难,首先是因为上文所说的文化殖民,导致当下中国德育学者与自身传统的疏离。这种疏离不只是情感上的冷淡,而且是认识上的不了解,是文化上的深层断裂。古汉语对于当下的中国人俨然成为另一门语言。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都很难直接阅读中国古籍,甚至不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这导致我们不能在学术意义上理解中国文化和哲学传统。“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置身其间而缺少旁观者之眼带来的澄明,另一方面更在于从根本上对庐山本身认知的缺乏。
裂痕越深,接续越难。但如果要研究中国德育,不理解自身所在的文化传统就无法历史性地理解中国德育的很多问题,也无法文化性地解释中国德育的很多现象。中国教育日常概念中有“校风”“班风”“学风”的说法,但“风”如何成为中国描述教育和学习风格、氛围、理想的文化标签?为什么不是“雨”“雷”“电”等其他概念?它是否隐藏着一种中国式的思维?“风”的说法,不只是在教育中,此外还有“国风”“民风”等。我们对这种说法习以为常,以致于它不能引起我们的思考,不能激发我们的教育问题意识。赵伟黎先生因为在异域文化中沉浸多年,乃以他者之镜反观中国教育现象,捕捉到了中国教育的这一“风”景,进而通过对《周易》“风”卦的考古式研究,发掘出中国传统中“风”与孔子之“教”的内在关联,打开了中国特有的“风”教文化与思维方式(17)Zhao, W., China’s Education, Curriculum Knowledge and Cultural Inscriptions: Dancing with the Wind(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19), 97-121.,引起了国际教育研究领域的关注。这样的研究是不易的,它不仅需要捕捉中国问题的高度学术敏感性,还需要具有中国古汉语的阅读能力,能深入追溯中国古代典籍,更需要有教育研究的专业视野。此外,这样的研究还需要耐得住在故纸堆中搜寻的寂寞,唯其如此,才能够充分开掘出中国教育的宝藏。
可喜的是,这一努力已经开启。2019年的全国教育基本理论学术年会,以“发现‘中国教育学’的文化逻辑”为题,深入讨论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教育的使命,在本土化与国际化两个路向的讨论中,文化视域被凸显,与会学者基本认同“中国文化基础上的中国话语是构建与展示中国教育学文化特征的历史之根,也是分析和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智慧之魂,更是生成与培育中国教育学学科的知识奠基”(18)刘铁芳、李明达:《发现“中国教育学”的“文化逻辑”——全国教育基本理论第十七届学术年会综述》,《中国教育科学》2021年第2期,第142-143页。。2019年,受中国文化领域浓厚的“回顾与前瞻”氛围的影响,笔者尝试了“回顾与前瞻”的时间现象学考察,以期对中国德育传统对“反省”的衷情问题进行理论探索(19)孙彩平:《回顾与前瞻:意义世界的时间现象及其德育意涵》,《高等教育研究》2019年第8期,第18-26页。;2021年,基于两次全国大样本调查中中国儿童“缺格局”的现实问题,笔者追溯了“格局”作为中国文化伦理图示的理论意义,并从中揭示了空间直观思维在中国伦理传统中的独特意义(20)孙彩平、周亚文:《追寻格局:中国文化伦理图示敞开与德育路向》,《教育研究》2021年第8期,第69-77页。。点滴努力,愿与同仁一起汇小流以成中国德育话语研究之江海。
(二)回到中国德育经验。回归自身问题的第二步,就德育研究而言,是回到中国德育经验:通过经验研究走近中国儿童和中国的德育实践,准确把握中国儿童道德发展的整体现实状况,清楚地认识他们道德成长的困难与障碍;深入走进中国德育的田野,实事求是地面对中国德育当下的困境,分析这些困境产生的原因,讨论问题解决的可能路径。在回到中国自身德育问题的基础上,从对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切出发,走向问题和现象的深处。研究者以扎根现实的方式,界定中国德育问题,提炼中国德育概念,推出有本土生命力的命题,包括具有本土实践可能的问题解决路径。这是走出当前德育认识论困境必须迈出的一步。
实际上,关注中国问题、服务中国社会一直是德育研究的一个努力方向。随着开放的深化,针对当时整个教育研究中出现的新的全盘西化、简单移植的研究倾向,鲁洁教授提出了教育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把它当作是“关系到我国学术发展前途的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21)鲁洁:《试论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高等教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3-35页。。德育研究者以高度的学术敏感性和深刻的社会洞察来反思中国社会的商品/市场经济、产业化、全球化等带给德育的可能与挑战,构成了不同时期中国德育研究的热点问题,使得德育研究能够与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同步。
当然,德育研究回归自身并非只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德育问题与挑战就可以了,其更深层的、前提式的回到自身是回到德育研究自身。改革开放伊始,针对“文革”前德育研究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以胡守棻、鲁洁、王逢贤、班华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德育研究学人开启了德育研究的科学性探讨,通过对德育目标、内容、功能、方法的重新界定,将德育研究从话语到思维、从价值论到方法论转回到学术研究本身(22)班华:《德育理论在科学化轨道上前进》,《教育研究》1988年第12期,第31-37页。。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也是德育研究要不断追求和捍卫的认识论立场。只有回到德育研究本身,依靠学术逻辑建构起德育的科学范畴和规则方法,才能保障德育研究生产的是可靠和可信的知识。学术逻辑要求德育研究需保持研究的独立性,拒绝为学术之外的种种“立场”背书,但也并不排斥研究的社会和实践关怀,恰恰相反,推动社会和实践发展构成高品质德育研究的人文底色。
上述研究多是思辨研究,基于基本逻辑对教育现象发表看法、提出主张、呼吁或捍卫一种德育立场,常常为中国德育发出方向性指引或警示性告诫,成为一段时期内德育研究的核心命题。宽泛而言,这些研究基本属于规范性研究。“规范性研究与知识的指导性涉及教育世界应然的理想、价值取向、行动方式与目的,涉及教育实践的‘好’、正当性,等等,它们是在正价值方向上提出‘应然’的,因而具有唤醒积极行动态度的意义。”(23)金生鋐:《教育研究的逻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2-23页。也正是这些规范性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担当起德育学科重建的任务,并在社会伦理的迅速转型中保持了理智的声音。
规范性德育研究作为一种价值主张和洞察,多数情况下由研究者个体独立完成,但好的规范性研究并不表达个人化的意见,而是基于理性审视提出具有普遍性的教育原则和立场。这是规范性研究者的超越个体化的问题。康德对普遍性知识何以可能的回答是知识源于纯粹理性的“先天逻辑”能力,但他同样重视经验在知识构成中的重要性,其《纯粹理性批判》导言的开篇即讲“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24)[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页。。他提出,知识是由形式加内容两部分构成的,先天逻辑是知识的形式,这一形式通过经验得以充实,经验为知识提供了内容。好的规范性研究需要以广泛、深入的经验材料为支撑。个人经验显而易见的有限性与知识的普遍性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尽量以广泛的经验材料(数据)为依据成为好的规范性研究的另一必要条件。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研究者的中国德育经验有限,使得多数思辨研究失去其普遍性视野,成为个人意见的表达。同时,由于缺少对现实德育问题形成原因、机制的深入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使德育研究的知识生产流于空洞的观念传播,所提出的建议缺少现实的针对性和实践的可能性,仅止于学术圈的自说自话,陷入知识的社会信任困境(25)雷云:《教育知识的社会镜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21-23页。。所以,一方面,要坚守规范研究的逻辑性,使德育研究遵循知识生产的基本规则,保障其学术合理性,这是德育研究的底线;另一方向,规范研究要建立在广泛经验研究的支持上,以对中国德育经验的深入分析为依托,使逻辑思维扎根在中国德育的田野上,研究中国问题,提炼中国经验。在这方面,叶澜老师带领的“新基础教育”研究可谓典范。
(三)做有思想、有价值的经验研究。相较于思辨的研究形式,德育领域高品质的经验研究并不多,特别是在21世纪质性研究热潮来临之前。在德育甚至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经验研究或者事实研究描述事物,给出的知识都是信息性的”(26)金生鋐:《教育研究的逻辑》,第20页。。这与其说是对经验研究本身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现有经验研究的批评。当下的经验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多限于关注数据的来源和分析方法,也存在为了体现科学性而过度追求更为复杂的数学呈现方式的倾向,的确存在着碎片化、技术化的问题。相关研究停留在对教育问题事实的浅层关注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实证和数据的偏执与盲信。但这并非经验研究本身的局限性,这是具体研究的局限性。审视迄今影响着人类知识生产乃至日常生活的重要知识体系,如19世纪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20世纪的系统科学理论,以及方兴未艾的量子哲学,无一不是以经验研究为基础提出的。所以,并不是经验研究只能提供信息,好的经验研究同样能提供深刻的思想和有解释力的理论。为强调当下实证研究对推进教育研究科学化的意义,袁振国说,“思想是实证研究的灵魂,没有思想的实证研究如同稻草人徒有其形”(27)袁振国:《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4-17页。。任何有深度的研究,都是以思想为指导的,也是为了生产思想而进行的,经验研究同样如此。超越碎片化、技术化,走向基于思想、表达思想和追求思想的经验研究,正是立足中国经验的德育研究要努力突破的方法论瓶颈。也只有在这一思路上,才能将实证研究理解为“首先是一种思想,一种精神”的原因。
认为经验研究只能局限于事实与信息,可以称之为对经验研究的思想性偏见。在德育领域,经验研究遇冷的另一观念障碍是认为道德及价值问题排斥精确计量,这可以称之为对经验研究的价值性偏见。教育是培养人的实践活动,道德是一种实践智慧。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亚里士多德曾明确讲,“实践的逻各斯不可能是精确的,只能是粗略的”。他认为“实践和便利的问题就像健康问题一样,并不包含什么确定不变的东西”(2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8页。。德育具有实践性,是一种与价值密切相关的活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以此为依据,认为德育研究排斥精确性,不适于采用实证和经验研究的方法,则是以研究对象的特性来限制研究方法的一种误会。事实上,所有的科学在本质上都是人类文化,都是观念的生产,即使自然科学知识,也并非完全与人无涉,而是具有个人性(迈克尔·波兰尼)、价值性(进化论和日心说与宗教的冲突既是观念的冲突,更是价值的对抗)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人类学、社会学,就研究对象而言,都是人类的生活实践,都具有价值性和实践性,但它们并没有因为研究对象本身的这一特点而拒绝经验研究的方法。相反,以不同民族文化经验收集为基本研究资料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成为文化人类学最主流的研究方法,实证主义研究构成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传统,当下社会学中流行的以扎根理论为基础的定性研究,也是以进入某一社会现场收集相关材料(数据)为基础展开研究的,也属于经验研究。日本社会学家作田启一以自己的《价值社会学》研究,向世人说明价值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范畴,是需要并完全可以通过实证研究展开的。由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可见,德育研究不能因为研究对象的价值性与实践性而将经验研究拒之门外,作为一种知识生产领域,德育研究要遵循的是科学研究的规范。理解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舒茨说,“科学永远是一种客观的意义脉络,所有关于社会世界的科学论题都是针对一般的或特定的主观意义脉络去构作客观的意义脉络。所以每一门社会科学的问题都可简述如下:关于主观意义脉络的科学是如何可能的”(29)[奥]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宗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15-317页。。沿着舒茨的说法,德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是采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包括历史的逻辑的方法、经验的实证的方法,探寻儿童/人的德性发生和引导的方向、路径、过程与结果,发现以上诸环节的问题,并研究这些问题解决的可能。如果说德育本身是实践的,是价值性的,德育研究就是要探索这一价值性实践本身的普遍性问题,形成人类关于德育的客观意义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