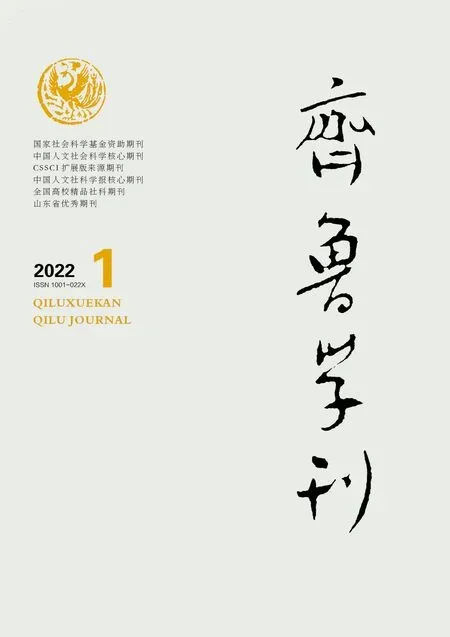夏朝的建立与其早期国家形态
沈长云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24)
经过学者长期反复的探讨,尤其是近年来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人们对于我国进入文明之初,也就是夏商周三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对于我国古代第一个早期国家夏朝在历史上的存在及其时间框架,也有了一个基本明确的认识。但不容否认且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外仍有少数质疑夏在历史上存在的声音。其中一种论调是质疑夏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称夏只能是一个酋邦性质的社会,甚至连早期国家也算不上。我想,要澄清这些问题,特别是要回答夏是否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似乎还要从夏朝的建立说起,从分析夏朝作为早期国家产生的途径入手,解决有关夏代国家的结构特征,包括它的权力结构、这个权力统治下的人群组成等具体问题,以便弄清它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及现代西方人类学定义下的“国家”标准,符合哪一类国家的标准,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释疑解惑。下面直陈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将使用尽可能早期的文献及相关资料,庶几使夏史、夏文化研究走向更深入的领域。
一、夏朝的建立:其地域与其产生的途径
个人以为,要解决夏王朝是如何产生的这样一个问题,还应当首先弄清楚夏朝统治到底建立在什么地方,即夏朝的地域问题。
其实过去文献对这个问题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夏朝建立在东方古河济之间,也就是今天河南东部与山东西部一带。此论点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一是文献称夏的多个都邑及夏的各路“诸侯”均分布在古河济一带地区;二是夏朝的创始人大禹据载亦是在此一带居住并治理过这里的洪水。关于前者,前辈考据大师们早就给出了明确的说法。如当年王国维就曾指出:“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452页。稍后顾颉刚、杨向奎亦有过大致相同的说法。我个人曾对这些夏的都邑及“他地名”进行过考察,确认王国维所言不误。现在一些学者,尤其是部分考古学者试图把一些夏的都邑,如帝太康所都之斟鄩、帝廑即帝胤甲所居之西河,以及作为夏同姓部族(所谓“诸侯”)的有莘氏、有扈氏的地理位置,都纷纷搬到豫西甚至豫陕交界以西的地方,但这些说法实际是很勉强的,并不足以为训。一些先生坚持主张夏在豫西伊洛一带者,大约是误读了《逸周书·度邑》。《度邑》称:“自洛汭延于伊汭,其有夏之居。”不少人将这里的“有夏”读作夏后氏之夏,殊不知此“有夏”实际是指有周,因为这篇文章实在是讲周都洛邑的建设。另外,他们也可能对二里头遗址所处时间段没能很好地把握,不知此二里头只是夏朝晚期的都邑(最新测年,二里头文化早不过公元前1750年),是夏朝后期向西发展在这里建立的一处别都。至于禹的居处及禹治洪水之所在,我想更是应当放在豫东黄河下游一带去考虑,因为禹与夏后氏族所遇到的,乃是一种洪涝性质的灾害,这样一种性质的洪水只能发生在平原低地,而不会出现在多山且地形复杂的豫西地区。日前,已有学者发表过类似看法,可以参阅(2)郭立新、郭静云:《古史复原应遵从的史料学原则——以大禹治水在豫西晋南说为例》,《齐鲁学刊》2020年第3期,第44-53页。。此外,禹的居处即所谓“禹都”阳城,也不在嵩山之下,因为那里也不会发生汗漫无际的洪水。据《世本·居篇》,所谓“禹都”阳城乃在战国魏都大梁之南,当今河南开封一带,正好处在河济之间的中心。这样,禹治洪水地域与夏朝都邑所在地域两相吻合,说明有关夏朝的史事并非出于后人的编造。
当然我们还需解决一个禹治洪水之事是否可信的问题。过去顾颉刚说大禹只是一位传说中的天神,只是后来战国时期的人们才把他变作了现实社会的人王。这个说法无疑否定了禹治洪水之事的可信性,这是我们不赞成的。顾先生肯定夏在历史上的存在值得赞赏,但对大禹人王身份的否定则不足为训。为此,我已在日前发表的《禹是天神还是人王——对顾颉刚一个疑古主张的质疑》一文中对之做过辨析(3)沈长云:《禹是天神还是人王——对顾颉刚一个疑古主张的质疑》,《齐鲁学刊》2020年第3期,第39-43页。,不赘。事实上,禹治洪水故事早在西周时期即已流传,出土青铜器铭文《豳公盨》可为之证,我们再无理由说它是战国之人的杜撰了。如果相信禹治洪水的真实性,有关夏代国家建立之事就更好理解了。对此,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历史文献《国语》早就有了明白无误的记载,它说,由于禹治水的成功,“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是古人一致认为,夏后氏国家的产生,乃基于禹对洪水的成功治理。
对于禹治洪水促成夏代国家产生这样一条早期国家产生的路径,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支持。它牵涉到两位导师对于古代东方国家文明产生问题的讨论。尤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古代东方社会“统治与奴役”关系产生的论述,我们感到更是切合夏代国家产生的实际。恩格斯在这部代表他晚年理论建树的著名著作中提出,在古代东方原始共同体内,有一些维护或管理共同体整体利益的职务,这些职务不得不由个人来承担。这些负有管理职责的人员(他们应是氏族部落中的领袖人物)一开始充当的角色,显然具有“社会公仆”的性质。但由于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因而也可以视作国家权力的萌芽。后来,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促使这些单个的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并导致建立新的机构来保护共同利益和反对相抵触的利益。而这些机构中“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由于他们权力范围的扩大和“独立化”倾向的日渐增强,难免使他们最终走向其所服务的人群的对立面,变作“社会的主人”,也就是统治与奴役人民的专制国家的君主。
禹的治水,对于居住在河济之间的广大部族来说,无疑也是一项公共事业,禹在最初应当也是一位勤于职事的“社会公仆”。但是,由于治水需要长时间大规模地集中人力物力,要对各族邦的人力物力进行调配、指挥和统一管理,要组织各氏族部落的参与,在此过程中,禹难免要利用联合体赋予自己的职权对各邦施加更多的影响,甚或强制干预。这样一来,就势必使原来较为松散而缺乏约束力的联合体发生质的变化,促使联合体领导机构发生权力集中的倾向,并逐渐凌驾于各个族邦之上,以至最终过渡到使各族邦沦为自己臣属的具有专制主义性质的权力机构。而禹则因长期担任领导治水的职务在众族邦中树立了自己及自己家族的权威,由原来的夏后氏部族的首领继任为部落联合体的首领,再发展成为君临众族邦之上的拥有世袭权力的夏代国家的君主。
以上,便是我们总结的夏代国家产生的道路。
二、夏朝的社会结构与相关国家制度
了解了夏后氏王朝的建立,我们便可进一步去探讨夏代国家的组成,包括它的社会结构及相关国家制度了。
先谈夏代国家的社会结构。个人以为,所谓夏朝,实际上就是一个大邦统治下的众邦结成的部族联合体。这个大邦便是夏后氏。夏后氏统治下的众多邦国,构成了夏代国家的领土范围。这众多邦国中的多数成员,想必从禹治洪水时期就已跟随在禹的左右,和夏后氏一样居住在豫东鲁西一带。治水符合于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应当也都参与了治水的工作。大概禹一开始就是通过他们的拥戴而登上王位的。文献记载这些族邦有有扈氏、有莘氏、斟鄩氏、斟灌氏、有虞氏、有仍氏、昆吾氏、豢龙氏、有缗氏、有穷氏,等等。他们大概也就是现时一些人所说的“夏人”,或“夏族”。现在许多人动辄称夏人(或夏族)如何如何,却不知这些“夏人”或“夏族”都生活在古河济地区。地图上找不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居住在现时一些人所主张的“夏文化”分布的区域,包括豫西二里头或嵩山南北地区。这一点只需看看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明白了(该书第一册第9-10页)。只有一个斟鄩被标在这张地图上靠近偃师的地方,但我们上面已经指出,斟鄩原本也在鲁西,根据《左传》的叙述,它应在斟灌附近。如此看来,所谓夏族和他们的祖先夏禹,原本都是河济地区的居民。
那么,这众多的氏族或者邦方是以怎样一种方式围绕在夏后氏周围,夏后氏又是怎样将他们纳入自己的权力结构之中的呢?和这种权力结构的有关制度又是如何呢?
与夏朝权力结构相配合的首要的一项制度,是夏后氏创设的“家天下”国家制度。这项制度的确立,实际也标志着各族邦对夏后氏统治权力的认同。传世文献记载了这一制度形成的过程,称这是由于夏后氏对过去实行的“禅让制”的破坏,尤其是禹的儿子启对“禅让制”破坏的结果。也有少数战国法家著作(如《韩非子》)称夏后氏王权是通过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即通过“人臣弑君”的手段建立起来的。这两种记载说的实际是一个意思。不过我想,尽管禹、启建立“家天下”之史事不能否定,但说此事出自暴力攘夺,其大概率应是法家为宣传自己的“阴谋论”而制造出来的臆说。我更相信夏后氏的“家天下”出自一场“和平演变”,是由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不知不觉地造成的。恩格斯在谈到上述“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的角色转换时,指出这种转换是“在顺利的条件下逐步”演变而实现的,似乎也是这个意思。就禹本人来说,他通过治水建立起自己的崇高威望,在他去世之后,各部族继续拥戴他的家族担任部落联合体的首长,在当时条件下,也是说得过去的。我们看直到禹以后的重孙子辈,即少康时代,多数邦国对于夏后氏王者的身份仍是表示认可的。其时,由于后羿与寒浞发起的动乱,造成少康一时流落在外,可是,当他流落到有虞氏地界时,有虞国君虞思立即将他保护起来,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使“邑诸沦,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以收夏众”,直到他“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才算了结(《左传·哀公元年》)。是可知这“家天下”的国家制度确实已得到了确立。
夏后氏国家实行的另一项重要制度,是它对臣属于自己的各个族邦进行管理的制度,即过去文献中屡屡提到的内外服制度。“服”的意思是服从,该制度就是讲朝廷根据各族邦对自己的亲疏远近关系,将他们分作“内服”与“外服”两个部分,从而规定他们对朝廷的不同义务与贡纳。文献显示,当时与夏同姓的几支氏族,如有扈氏、有辛氏、斟寻氏和斟灌氏,以及与夏联姻的几支氏族,如有虞氏、有仍氏、涂山氏等,都处在距夏后氏不远的地方,如有扈氏,在今河南郑州黄河以北的原武一带;有莘氏,在今山东西部接近河南的莘县北;斟灌氏,在今河南与山东交界的范县境内;斟寻氏,在斟灌氏附近;有虞氏,在今河南东部与山东交界的虞城县;有仍氏,在今山东曹县;涂山氏,在今山东曹县。还有任为“夏伯”的昆吾氏和任为夏“车正”的薛氏族,文献虽未明确显示他们与夏的亲属关系,但从他们与夏的亲密程度看,把他们算作夏的姻亲,也在情理之中,他们分别居住在今河南濮阳和山东滕县。上述夏后氏同姓与姻亲的这样一种地理分布,正合乎我们上面提到的三代内外服制度的原则:内服族邦集中分布在王都及其附近,其他异姓居住在外。文献没有怎么提到夏的外服族邦,只是较多地记载了夏东方诸夷的活动,包括他们对夏朝廷不断地“来宾”“来御”和“入舞”。从这些情况看来,亦正合于外服诸侯与其统治氏族相互间的关系。其时夏与东夷族的相互往来,也再次显示夏处在我国近东的地域。
至于文献还提到禹的划定九州、任土作贡诸事,我们认为可能是后代人的假托,不拟在此叙述了。
三、夏代国家性质:有关早期国家的定义问题
现在归结到我们最终要回答的问题:夏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
这个结论似乎已不需要我再重复了,但是归纳一下夏之所以应当认为是一个国家的理由,还是有必要的。夏之所以是一个国家,我想主要还是它已经具备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国家所应有的两个标志,即:第一,它已经实现了“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它已经有了“公共权力的设立”。关于后者,上面已经提到,夏朝通过自己所设立的“家天下”国家制度,实现了各个族邦对自己的权力认同。他可以将自己的权力凌驾在所有族邦之上。还在禹刚完成自己的角色转换不久,他就在行使自己的这种权威了。这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禹会涂山的故事。在这次会盟上,他借口一件很小的事情,便杀掉了前来与会的防风氏,显然就是为了树立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威。至于夏朝的“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我以为就是指它下面各个地方由各族邦构成的一套行政系统。这些族邦是血缘组织,但它们彼此之间却没有共同的血缘联系。他们既然被夏代国家编织进一个共同体,并各自长期占有某一固定地域,那就只能是国家的下属行政单位。今学者皆以为古代氏族的姓氏反映了他们不同的血缘谱系,我们看夏代居住在古河济地区的这些氏族邦方,除与夏王保持同一个族姓的诸姒姓氏族外,就还有属于姚姓(或言妫姓)的有虞氏、属于己姓的昆吾氏、属于彭姓的豕韦氏、属于妊姓的有仍氏和薛氏、属于董姓的豢龙氏……等等,文献记载他们都与夏后氏保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或与夏互通婚姻,或担任夏的官职,或充任夏的侯伯,这些,都可以说明他们作为夏的下属行政单位的存在,表明夏不是一个单纯的酋邦组织,而是由许多不同血缘关系的酋邦组合成的国家,或者可以进一步被称作是早期国家。
讲到这里,我们应该对“早期国家”做一个大致定义了。这个定义首先来自当代西方人类学者,是他们首先提出早期国家的概念。不过大家对于早期国家的认识却不大统一。最早提出“早期国家”概念的荷兰人类学者H.J.M.克烈逊给于早期国家的定义是:“一个刚分化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社会中调整社会关系的组织。”(4)[荷兰]H.J.M.克烈逊:《关于早期国家的各种学说和假说》,《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北京:时事出版社,1985年,第316页。稍后的前苏联学者A.M.哈赞诺夫则强调“早期国家具有由前国家阶段继承的许多特征”,除刚刚产生的“从属和剥削的各种形式”外,还有“在社会生活中继续有着重要意义的亲属关系”(5)[苏联]A.M.哈赞诺夫:《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277页。。比较起来,中国学者更愿意接受哈赞诺夫的主张。不少学者指出,中国的早期国家,即旧史所谓“三代”。它们之所以被称作早期国家,就是因为它们还包含有不少“原始性”的内容,即它们“不是在氏族制度被彻底‘炸毁’之后产生的,国家出现的时候,氏族组织的大量残余依然保留着,居民的血缘关系依然存在,而且此后保留了很长一段时期”(6)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8-9页。。综合大家的看法,我们认为,中国早期国家就是指夏商周三代已具备公共权力,但社会仍滞留在居民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的政治组织。
夏作为“三代”之首和我国第一个进入文明的国家,无疑也具有早期国家的这样一些特性。它的由多邦组成的结构特征,表明了夏代国家仍旧是一个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的政治组织。“邦”就是一个个具体的血缘组织。只是经过三代包括春秋时期长时间的民族融合,各个“邦”内部的血缘壁垒被打破,整个社会才发展成为真正按行政区划组织的成熟国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