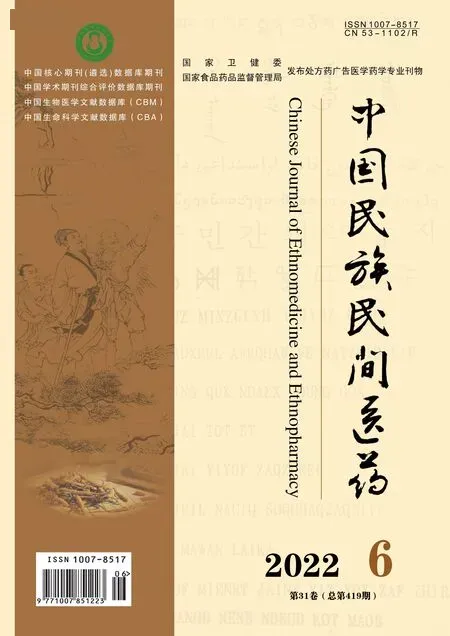德宏州傣医药的发展现状探析
赵晨勋 徐文立 李 翔 段忠玉
云南中医药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傣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因素,被冠予不同的名称,汉晋时期为“滇越”“僚”“掸”“鸠僚”等,唐宋时称之“白衣”“茫蛮”“银齿”“金齿”,在唐樊绰《蛮书》卷四《名类》中有迹可循。元明清时期则为“摆夷”“百夷”等[1],皆反应出傣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特点。傣族作为跨境民族,在泰国、越南等被称为“泰族”,老挝为“佬族”,缅甸为“掸族”。发展至今,傣族已逐步弱化了种族、血缘、民族源流迁徙的相关因素,各国各支系之间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一类民族群体。
我国傣族人口达120多万人,分布较广,在云南主要分布于四大流域(澜沧江流域、怒江流域、金沙江流域、元江流域),其中怒江流域的傣族主要居住在德宏州[2]。德宏二字源于傣语的音译,“德”为下面,“宏”为怒江,“德宏”便是“怒江下游的地方”,德宏地处横断山脉以南,高黎贡山以西,与缅甸山水相连,德宏州傣族属傣呐支系。虽然德宏傣族与其他地区的傣族支系不同,却同根同源,傣族群体的共性因而寓于相对独立的个体个性中。在漫长的文化适应过程中,德宏州傣族人民逐步总结和形成了适应其生存需要的治病方法和手段,但发展至今,德宏州傣医药的民族特色正在逐步弱化,笔者通过走访、问卷等方式挖掘和总结德宏州傣医药的发展现状,并就如何更好的发展德宏州傣医药进行考量,以期为改善德宏州傣医药的现状和促进云南民族医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德宏州傣医药的发展现状
一个民族医药的发展离不开其历史文化的传承。据考古学证实,德宏州人类的活动痕迹可以追溯到万年以前,傣族在文献《史记·大宛列传》中有最早的记载:“昆明之属无君长,善盗寇,辄杀略汉使。然闻其西千余里,有乘象国,曰滇越。”[3]在历史上,德宏州是达光王国(被誉为傣族历史上明亮的佛灯)的重要组成部分[4],之后在果占壁王国(公元567年,也被称为“勐卯王国”,以德宏瑞丽及附近为中心)也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在漫长的生产实践和迁徙中,傣族先民为了克服自然环境以及自身疾病带来的危害,逐渐融合了多种民族元素,也逐渐形成了多元的、复合的、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本民族医疗经验[5],并记录在贝叶经上,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在记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四塔”理论、“雅解学说”等,治疗上强调通过调节四塔来治病和养生[6-7],与此同时,傣医十分重视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强调顺应自然、未病先解、先解后治,并以实践为基础总结了民俗预防养生法、妇女保健法、饮食预防法等兼具民族特色和治疗效果的保健方法,这些记载大多是以口传心授、亲教秘传等方式流传开来[8],经过历史的积淀,成为了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德宏州民间傣医、拥有“一技之长”的傣医的走访和调查,笔者深刻感受到目前德宏州傣医药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并将现状总结如下。
1.1 文献古籍缺失严重 德宏州傣医药文献古籍流失严重,结合历史因素和发展实际,有三部分原因:其一为地理因素,德宏傣族的分布特点是以村寨为聚居点,分布较散,加之这些聚居点有一些为山高林密的山区,交通相对闭塞,各村寨内流传的医疗经验交流甚少,因此在传承过程中很难融合起来;其二为保存不当,大多数傣族医药文化是用老傣文记录在贝叶经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加之传统保存手段的不完善,因此,流传下来的古籍文献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存在酸化、脆化和腐化的现象,难以存继,且受战争、贸易往来等多种因素影响,部分文献资料可能已流失海外,不易寻回;其三为收集整理困难,傣族是拥有自己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民族,随着老傣医的病逝,能够完全认识和读懂古籍文献的人越来越少,语言不通,文字难识,加剧了调研者的工作难度。综上,德宏傣医药古籍文献的流失严重。目前关于德宏州傣族已经整理出版的有:《德宏民族药志》、《德宏傣药验方集》、《德宏民族药名录》等,研究者已收集58册傣医药古籍,傣药500多种,单方、验方1400余方[9],较之璀璨的傣医药文化,挖掘整理出来的资料只是冰山一角,因此,对于德宏傣医药文献古籍进行及时有效地挖掘整理仍是广大研究者的首要工作。
1.2 理论基础薄弱,缺乏有效理论支撑 在傣族医药形成和发展史中,傣族人民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对于防病治病得到了一定的理性认识,为适应德宏恶劣的气候环境,远古的傣族先民根据不同的季节、气候,常把一些可以用来御寒、解暑的动植物的叶、皮等用来做衣御寒,并煎煮当茶饮来治疗和预防疾病[10-11],在这个过程中,也吸收了古印度医学和中医药学的部分理论,并跟随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傣族社会,逐步形成了别具风格和民族特色的傣医药[12]。尽管在医药内容上呈现多元化和民族化的特征,但未形成能够代表德宏州傣医药的理论体系仍是无法规避的困难之一,无法给当地的傣医药教育工作和其他医疗行为提供指导意义。笔者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到德宏州傣医的疾病认知属于散在的认识行为,缺乏系统性。在走访芒市和瑞丽民间傣医的过程中发现,能够了解“四塔”和“五蕴”理论,并且能够准确且完整叙述出治病理论的傣医少之又少,许多都是经验之谈,芒市的民间傣医龚医生告诉笔者,在德宏地区,人们普遍认为“兵痧”是小病,其余都是大病,“兵痧”是指通过刮痧就能治好的疾病,属轻症,如咳嗽、流涕等。另一方面,民间傣医的疾病认知和治疗行为保留了一定的原始信仰色彩,难以形成确切的科学理论材料。如芒市风平镇芒别村的傣医线波岩团保认为非自然因素可致病,如鬼邪致病,治疗上会配合口功治疗,医者念完咒语之后,按在疼痛部位,就可以将引起疼痛的邪祟驱走,之后患者的病就会好。芒市风平镇等稿村的傣医周五坐也认为鬼邪是致病的一个因素,除此之外,傣族村寨居民在进行某一盛大活动时也会祭拜寨神或家神,如丢失了这一环节,则认为会家宅不宁,身体抱恙。我们在尊重民族信仰的同时,也面临难以将这一部分经验整理成文字的现状,因此对于德宏州傣医药的理论体系也会相应的缺乏支撑材料。
1.3 傣医认定范围有限 2019年德宏州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试资格审核合格人员共计40人,在梁河、陇川、瑞丽、芒市和盈江均有分布,但拥有“一技之长”资质的傣医主要集中在芒市,如芒市风平芒别村的腾波岩伦和景波岩相喊,其中滕波岩伦属小学学历,会傣文和新傣文,不难发现,相较于确有专长的中医,“一技之长”的傣医存在数量少、受教育程度有限的问题,除此之外,大部分民间傣医没有相关的行医证书,也未得到政府的认同,只局限于小范围的影响力。笔者在对德宏州13位民间傣医进行访谈时了解到,主治内科疾病的有4人,其余内外科均有涉及,内科治疗用药剂量多不精确,多为经验配药,外科治疗中以骨伤科疾病占比较大,由此可见傣医内外科发展的不均衡。
1.4 传承方式和群体的局限性
1.4.1 传承方式的局限性 笔者在对德宏州民间傣医进行走访时发现,他们大多是家传或者师带徒的方式来传承医术,瑞丽市姐相乡芒约村的民间傣医景波月团过告诉笔者,他的医术主要是传给他的儿子,但在他行医的期间,他的儿子不能行医。除此之外,部分民间傣医也有传男不传女的习惯,瑞丽市姐相乡勐板崃的民间傣医约相尚依只有两个女儿,因此其医术只能传授给女婿,但女婿并无跟师学习的意向,因此,约相尚依医生的医术也面临失传的风险。
1.4.2 传承人才匮乏 ①专业高端人才紧缺:一方面是傣医持证人员数量有限,2008年,德宏州开设傣医医师资格考试,自2009年开始实行两年一考,截至 2019 年,德宏州共组织傣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7批,仅有43人通过考试,其中傣医执业医师 6人,助理医师37人[13];另一方面,是缺少既能了解新、老傣文和中文,又具备一定医学素养的专业人员, 目前传承下来的古籍文献大多是老傣文记载,且部分藏匿于经书之中,尽管这些年的研究把有一些经书翻译成了新傣文,但翻译也存在一定的误差。②民间传承人出现断层:文化的来源需要以人民群众作为基础,民间草医是本民族医药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保护者和传承者,德宏民间傣医仅停留在治病技术的传承,缺乏对治病理念的传承。随着医疗资源的普及,村寨内许多人生病之后大多选择到正规医院就诊,民间草医的数量急剧减少,且年轻一代的大部分传承人接受新潮观念,不愿意留在边远的家乡跟随父辈们学习传统傣医药技能。笔者在对瑞丽市畹町镇芒棒村的民间傣医四团进行走访时了解到,他的医疗经验以家传为主,他的孩子不愿意跟随其学习,他也没有徒弟。在对方克辉傣医工作室的李老师的进行访谈时了解到,自方老师逝世后,其留下的手稿难以完成校对工作,因此,目前以方克辉老师为首的傣医工作室难以完成前期工作。综上,德宏州傣医药的发展正面临“后继乏人”的危机。
1.5 道地药材资源的稀缺 宋代《本草衍义》云:“凡用药必择土地所宜者,则药力具,用之有据。”由此可见,道地药材在促进地方医疗发展中的重要性。1988年,民族医药研究室成立后,相关研究人员共发觉傣药近100种,并编写出版了《德宏民族药志》、《德宏民族药名录》(收集傣药350多种)、《傣族医药验方集》(收集傣药方400余种),刘世龙等调查发现德宏州高等植物有6033种1908属339科[14-15],原生植物5414种,引种栽培植物618种,经济植物3906种,国家级保护植物94种,省级保护植物65种[16];在对德宏州种子植物科和属的地理成分分析中也提及德宏地区野生种子植物共有227科,1432属,4937种,且热带成分、温带成分均有涉及[17];杨新周等[18]通过调查发现德宏州园林景观药用植物主要有122 种,共有67科,但尽管如此,德宏州傣药仍在急剧减少。笔者通过对德宏职业学院临床学院的李老师进行访谈时了解到,目前德宏州傣医药发展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道地药材资源的稀缺,究其缘由,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①自然资源被破坏: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以及全球气候的恶化,部分草木植物、动物的生存环境被破坏,药材来源稀缺,药物产量也急剧下降,除此之外,因没有形成规范化的挖掘和采药机制,部分傣药被当地居民肆意挖掘,且多为全株采挖,药材资源正面临着枯竭的风险,并且傣族村寨分布较为集中,缺乏大规模种植的条件;②被经济作物代替:傣族聚居的村寨离城镇中心尚有一段距离,要想改变落后的生活环境,除了政策帮扶之外,还需要发展地方经济,因此,当地许多居民开采山地,种植经济作物,发展经济的同时也破坏了部分药材的生存环境。
1.6 傣药缺乏有效产业支撑 德宏州经济总体水平偏低,与全国相比差距较大[19],发展动力不足,对企业的吸引力较低。目前,德宏州傣药尚无专门的开发厂家、实验基地和科研人员。现有的德宏州傣成药制剂有治疗急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胃肠系统的“德傣胃药”,德宏州医院开发的“保汉大力膏”“伤湿止痛药”“水火烫伤散”“拔毒散”“戒断散”等傣成药,但临床使用面不广,患者的认知度、信任度较低。
2 德宏州傣医药发展路径思考
2.1 加强文献挖掘整理和保护工作 首先,要依靠相关政府部门,从法律层面制定相关文献保护法,并在基层建立文化服务站,扩大宣传力度,提供专项研究经费。其次,要依靠民间傣族医生,民间医生手中掌握着许多文献资料,也掌握着不外传的秘方秘药,他们是傣医药文化传承的主力军之一,鼓励与支持民间傣医加入到文献的保护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很多民间傣医的诊治方法至今保留着不外传的习俗,加剧了收集、挖掘工作的难度。考虑到民间傣医的实际情况,应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得到民间傣医的信任,消除他们的顾虑。此外,还要依靠专业人员和当地群众,凭借他们对傣族地区的了解,能够快速地展开调研工作,通过对实地走访、人物访谈、史料查找等方式及时地对医药文献进行抢救性的整理、保护[20]。
2.2 增强对民间傣医的监管力度 其一,要加强对德宏州现存民间傣医的调查摸底,通过彻底的调查寻访工作,逐村走访,了解掌握每一位民间傣医的基层医疗服务工作,深入了解其掌握的传统傣医药文化知识、医术水平、专长领域、诊治方法,将每一位民间傣医进行相关信息的录入,必要时,针对性地挑选部分民间傣医,进行更深层次的访谈;其二要尊重民族医药的特殊性,简化行医资格审核制度,适当降低职业傣医的考核标准的同时,严格管控民间傣医,规范民间傣族医生的医疗行为,减少假傣医的数量。
2.3 加强对傣医傣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2.3.1 重视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基础,是保护和传承傣医药的有效途径之一。目前云南省培养傣医学专业的学校主要有:云南中医药大学、滇西应用科技大学、西双版纳州职业技术学院和德宏职业学院,为进一步发展傣医药,应该加大宣传力度,扩招生源,借鉴现代教育体制的模式,在充分保留傣医药特色的同时,促进傣医学教育体制的改革,培养具备医学常识以及掌握傣语的复合型人才。
2.3.2 完善跟师制度 民间傣医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临床经验,以师带徒的形式来传承傣医药事业是德宏州打破传承困境的关键之一,但大多民间傣医文化水平较低,对于汉字和语言的掌握不够熟练,因此如何强化师带徒制度,加大师带徒的规模就有了弥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协调医院、学校和民间傣医之间的关系,充分尊重民间傣医的意愿,在医院、学校和民间傣医三者之间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给予民间傣医充分的社会保障,提供固定的坐诊地点。另一方面,就学校而言,可以将傣医学专业的学生分批送到民间医生的就诊地点进行跟师学习,以便获得更多的临床经验[21]。
2.4 健全地方傣医药保护的法律制度 明确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与职权,在遵循国家主权原则、利益分享原则、知情原则的基础上行使地方立法权和民族区域自治权,建立法律制度,健全法律中对保护民族医药知识产权、医药文化传承、良好环境资源、专业技术人才储备等方面的制度,在强化国内政策和法律保护的同时,也要借鉴国外保护民族医药的成功做法,如泰国的《泰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法》,印度的数字图书馆等。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申遗来促进傣医药的活态传承,加大对德宏州中傣医院建设的投入,拓宽傣医药的普惠范围,积极发展傣族医药传统产业,推动傣族传统医药市场化,实行全面的保护、开发与发展措施[22],坚持走傣医药可持续发展道路。
3 小结
综上,德宏州傣医药的发展正面临文献古籍缺失严重、理论基础薄弱、缺乏有效理论支撑、傣医认定范围有限、传承方式和群体的局限性、道地药材资源的稀缺等问题,因此,解决德宏州傣医药的困境,应立足于当地的发展实际,总结前人经验,在发展的过程中凸显自己的民族特色,彰显傣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应从加强文献挖掘整理和保护工作、增强对民间傣医的监管力度、加强对傣医傣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健全地方傣医药保护的法律制度等方面来改善现状,不断为云南民族医药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