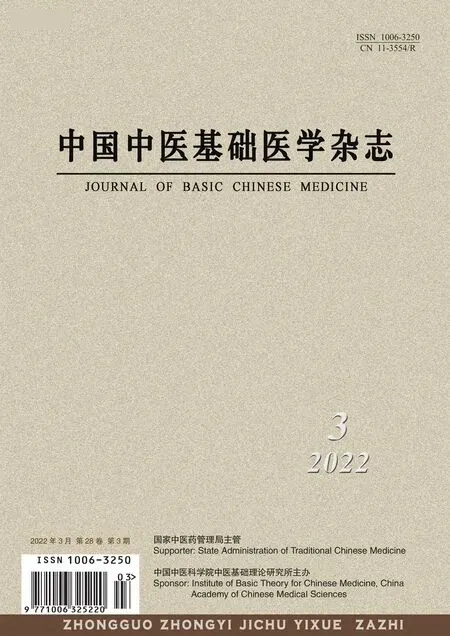敦煌脉书《玄感脉经》研究
刘 冉, 李铁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201203)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脉书《玄感脉经》(P.3477)残卷,是敦煌医学文献中的诊法类文献。该残卷自20世纪30年代由日本学者黑田源次首次自欧洲抄录见世,后经冈西为人、罗福颐和马继兴等学者题跋、校录、整理与研究,形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有益成果。本文将从“抄录、题跋与校注”“撰者与撰写、抄写年代考证”“文本结构、内容与重要学术问题研究”“文献、学术与临床实践价值揭示”等方面,对《玄感脉经》的既往研究进行简要评述,并就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1 抄录、题跋与校注
1.1 早期的录跋、考证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前,随着《玄感脉经》文本的发现,相关研究得以开展,但研究内容集中于文本抄录、题跋和作者考证等方面,主要以黑田源次、冈西为人、罗福颐等为代表。
日本学者黑田源次是较早关注并研究敦煌医学文献的学者之一。1931至1934年黑田源次到欧洲考察时,抄录了不少敦煌和西域医学文献,后来汇编为《法国巴黎图书馆藏敦煌石室医方书类纂稿》,其中即包括《玄感脉经》残卷。1939年4月,冈西为人编纂出版的《宋以前医籍考》第二辑中将该残卷归入脉经类并作了题录,简述了该残卷的尺寸、形态、纸张和书法特征[1]。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罗福颐在黑田源次类纂稿基础上,又增入不少国内所藏敦煌西域医学文献,并在前人考订基础上对相关残卷进行了考订补充,最终形成《西陲古方技书残卷汇编》,其中也包括《玄感脉经》残卷录文及相关考证[2]。可惜罗福颐原书未出版,目前难以得见,但从马继兴[3]、王淑民[4]等学者的引述中可知,罗福颐曾对该残卷的作者等进行过考订。
1.2 文本校录和考释研究的深入
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国内敦煌医学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敦煌医学文献的辑佚、校勘和整理工作也逐步展开。作为敦煌医学文献中的脉学诊法类文献,《玄感脉经》也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对其文本进行了校录和考释,部分学术问题也有相应探讨,相关校录和考释方面的研究成果多收录在马继兴、赵健雄、丛春雨、沈澍农等相关著作中。《玄感脉经》的文献研究在此时期日渐成熟。
1988年,马继兴和赵健雄分别编撰出版了敦煌古医籍校注著作《敦煌古医籍考释》[3]76-88和《敦煌医粹-敦煌遗书医药文选校释》[5],两者都校录了《玄感脉经》残卷。马继兴著作包括提要、原文、校注、按语和备考等内容,赵健雄著作则包括注释、原文、校勘和按语等内容。马继兴著作主要依据前后文义和其他敦煌脉学残卷出校记,赵健雄著作则主要根据前后文义和传世医学经典《素问》《灵枢》《难经》《脉经》《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出校记。因当时所据摄影胶片的清晰度有限,两著在录文和校注中都有误认、漏录、误补等情况。1994年,丛春雨主编的《敦煌中医药全书》[6]也收录了《玄感脉经》残卷。丛著在考校体例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包括述要、原文、厘定、按语、校注等内容。丛春雨基本承袭了马继兴和赵健雄的校勘成果,对二者部分漏校、讹误和缺文等作了校正和补录,并将原文和校补厘定后的录文共同列出,既保留了卷子文本原貌,也清晰地展示了编撰者的校补成果。1998年马继兴编撰的《敦煌医药文献辑校》[7]除了将体例变更为题解、原文和校注三部分外,其他则基本与1988年的保持一致。
1.3 对既往校勘研究的补充完善
新世纪以来,随着研究方法的改进、高清文献图片的公布,可利用学术资料增多,陈增岳、袁仁智和潘文、沈澍农等在相关敦煌医籍校录论著中又对《玄感脉经》进行了校补和考证。2008年陈增岳编著的《敦煌古医籍校证》[8]侧重语言文字上的整理与解释,除对《玄感脉经》校录中的个别地方有所修改外,基本上承继了前述各著的校释成果。2015年袁仁智与潘文编著的《敦煌医药文献真迹释录》[9]附《玄感脉经》的完整黑白图版,录文基本保留了图版的原貌,但图版清晰度有限。2017年沈澍农编著的《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10]汇集了前人的校勘成果,首次展示该残卷的高清彩色图版,其校录极大程度地保留了卷子原貌,释读更为详实、准确,是目前《玄感脉经》文献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
1.4 对缺文的校补
另外,原残卷第4~16行文字残缺较多,影响前后文意的理解,但在是否校补、如何校补上存在不同意见。马继兴[3]78-79、丛春雨[6]298-299等依据上下文义及文例,并参照《素问·三部九候论篇》及敦煌出土的其他脉学文献对之进行了校补。赵健雄则以内容残缺较多、存疑待考为由未予校补[5]64。陈增岳在原文校录部分保留了文字残缺原貌,未对阙文进行补录,而是以汇校形式展示了前人的校补成果[8]104-105。袁仁智、潘文[9]70-71、沈澍农[10]110-111都采用了分行校补,并用“【】”符号对补录内容进行标注,但沈著校补内容更为详细。沈著充分考虑到早期摄影照片与现今高清图影之间可能存在部分出入,故其校补将两者一同利用起来,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校补内容的完整性。
2 撰者与撰写、抄写年代的考证
《玄感脉经》未载撰者、撰写与抄写年代等信息。罗福颐据《旧唐书·经籍志》所载苏游撰著的《玄感传尸方》,推断认为“玄感”是苏游的字,并认为苏游应为《玄感脉经》的作者。此后,马继兴[3]76-77、王淑民[4]、赵健雄[5]65、苏彦玲[11]、陈增岳[8]103等在认同罗福颐观点的同时,又结合相关传世文献对苏游可能的生活时代等做了一些补充考证。如王淑民依据《旧唐书》中的相关记载,推断认为苏游为唐或唐以前的医家。又根据《旧唐书》《新唐书》《宋史》等史书所载苏游相关著作年代,推断《玄感脉经》也为唐代写本。马继兴则依据原文中未避讳“治”字,进一步推断其撰写年代在唐初或以前。
关于该残卷抄写年代,学界主要依据残卷中的避讳字对抄写的可能年代及上下限问题进行讨论。因文中出现三处“旦”字的缺笔避讳,且前后写法不一,这成为学者们考证《玄感脉经》抄写年代的重要依据。关于抄写年代上限学者们的观点一致,认为不早于唐睿宗李旦执政时期。但对于下限则有分歧,王淑民认为“似在晚唐”[4],马继兴则推断在五代时期[3]76-77。其后,赵健雄、苏彦玲又从相关文字的写法角度对马继兴的观点予以佐证[11]。
3 文本结构、内容与重要学术问题研究
3.1 文本结构与内容
就文本结构来看,虽然该残卷首全尾残,前半部分还有部分缺文,但现存文本内容依据其原有标题划分为三部分的整体结构比较清晰,因此学界对该卷文本结构的认识没有异议。
就文本内容来看,目前学界关于各部分具体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二两部分。张绍重、刘晖桢首次对《玄感脉经》的内容结构做了简要介绍,指出了残卷内容与《黄帝内经》《脉经》类似,但在字句、次序上有不同[12]。马继兴[3]76-88、赵健雄[5]64-83、苏彦玲[11]对第一二两部分内容进行分类研究,简要考察了第一二两部分内容与《平脉略例》等其他敦煌脉学文献及《素问》《难经》《脉经》《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传世医学文献的相似性。与马继兴相比,赵健雄除指出残卷文本内容与传世文献相关篇目可互参外,还从文法、语义等方面对两者的流畅性、合理性、准确性和全面性进行了评析。丛春雨[6]296-312则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医理论与临床实际对该残卷各部分内容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解读,对具体内容的医学价值进行了多方面分析。
3.2 重要学术问题探讨
除上述整体上的探究外,学界还围绕三部九候、呼吸定息、诊脉时间、诊脉手法、脉象与形性关系、脉名脉象和精识之主等几个重要学术问题进行了具体讨论。
该残卷“三部九候”理论引起了学界关注。丛春雨认为,该残卷所论三部九候是指寸关尺三部,与《素问·三部九候论篇》的“意义”有区别,但并未详细揭示其不同点[6]297。其他学者虽亦有所论及,但都未对其与《素问》《难经》中相关理论之间的关系做深入讨论。
关于该残卷中的“呼吸定息”研究,赵健雄依据《灵枢》《难经》记载及人之实际呼吸息数对“人一日一夜三千五百息”的论述予以质疑[5]67。田永衍则依据敦煌脉学文献《平脉略例》对其予以旁校,指出此处有脱文,并结合“天人相应”的思想分析了其与人之实际生理参数存在出入的原因[13]。丛春雨则从医生诊脉基本功的角度对以呼吸定息测脉动的理论予以了肯定[14]。
关于“诊脉时间”的研究,马继兴和赵健雄在原文文意的认识上存在分歧。马继兴结合《脉经》和敦煌脉学文献《平脉略例》认为,其分属2种不同的平旦诊脉理论[3]80。赵健雄则从文本本身出发,认为两者文意重复,后者或为前者的注语[5]68。田永衍则主要结合《平脉略例》《素问》对此进行考证,从本义、平旦诊脉与独取寸口的原因等方面对此予以解读[13]。
关于“诊脉手法”的研究,因对原文断句的不同,学者们对其认识也存在一定差异。马继兴认为其为一种诊脉方法,即依据指下轻重诊断五脏[3]82。而王淑民[4]则认为其为2种诊脉基本手法。赵健雄[5]72与王淑民观点相同,并比对《难经》《脉经》中所载五脏诊法,认为《玄感脉经》论述更为全面。丛春雨在王淑民与赵健雄观点的基础上,认为这2种诊脉法既是对医生诊脉基本功的强调[14]53,也是对脉象胃、神、根理论的具体应用,可据此判断疾病邪正盛衰及预后吉凶[14]62、64。田永衍则重点结合《平脉略例》与传世医籍对诊脉指力轻重与五脏、人体层次对应关系进行考证,指出彼此间的差异,并从文字写法、抄写年代、文献关系等角度指出,《玄感脉经》部分文字存在误抄可能,还就其临床意义进行评述[13]。
关于“脉象与形性关系”的研究,丛春雨认为这是对个体差异的重视[14]54,实质是要求医生诊脉知常达变,注重辨证,这正是中医学的精髓之处[6]303。
关于“脉名脉象”的研究,马继兴首先将其整理分为23种病脉和6种死脉,并将其与《脉经》《伤寒论》《千金翼方》《察病指南》所载脉象比较异同[3]83-87。赵健雄数目上与马继兴有出入,整理出24种病脉6种死脉[5]76-82。丛春雨则比对《脉经》《千金翼方》中脉象描述后,推断其所抄内容或源自《千金翼方》[6]305-312。丛春雨亦就该残卷所载23种病脉依照脉位、脉至、脉势、节律、形体进行分类,对其病理和主病予以阐释,并结合临床对6种死脉进行解读,指出其对于预报疾病的危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4]68-83。
“精识之主”也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问题。“精识之主”前面有缺文,王淑民首先通过理校和旁校的方法,在其前补足了“头角者”三字,从而实现了前后文意的贯通[4],其后学者在对此处进行校补时皆与其相同。“头角者,精识之主”的论断,王淑民[4]、马继兴[3]79、丛春雨[6]299皆指出其不见于其他典籍,为《玄感脉经》所首见,学界认为这一论断的发现意义较为重大。朱定华、王淑民率先对其内涵进行阐释,指出其为最早的关于头脑具有精神意识功能的记载,但未能对其进行详细考证[15]。后王凤兰也指出,该论断是与传世古医籍不同的理论[16]。近年来,田永衍在吸收王淑民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汉唐文献和佛教思想,对该论断形成的背景、原因和内涵等做了进一步的考证和分析[17]。
综观上述研究,虽然学者们围绕文本结构、内容、几个重要学术问题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但还有如“形藏、神藏”等内容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与解读。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多借助传世医学文献进行比较研究,但对同类型、时期相近的敦煌脉学文献的利用不足。
4 文献、学术与临床实践价值的揭示
自20世纪80年代敦煌医学文献研究兴起之后,随着对《玄感脉经》残卷研究的日渐深入,学界对其学术、文献及临床价值也进行了讨论,张绍重、刘晖桢率先评价此卷为佚书可珍[12]。就文献价值看,学者们普遍认为,《玄感脉经》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可以为古医籍整理提供重要帮助。如王淑民[4]、丛春雨[6]297、王凤兰[16]等认为,《玄感脉经》是继《脉经》之后的一部重要脉书,是未见传世的古医籍,是对隋唐前后医籍的补充。其中不少文字表述与传世和敦煌出土的其他脉学文献相同或相似,可以为校勘、辑佚传世经典文献提供早期校本。
学界对该残卷的学术价值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朱定华和王淑民认为,《玄感脉经》保存了唐以前的脉诊理论和经验,为研究唐以前脉诊发展史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15];丛春雨认为,“寸口诊脉”理论是对《黄帝内经》《脉经》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和发展[14]55、57,23种病脉的论述是继《脉经》之后的又一个脉诊专论,对发掘脉诊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4]68-81。另外,王淑民[4]、田永衍[13]等对“头角者,精识之主”这一首见于该残卷论述的学术价值进行了探讨,认为其可以为唐以前医学思想史研究提供重要帮助。
学界对该残卷的临床实践价值也进行了探讨。丛春雨将《玄感脉经》的脉诊理论与临床诊断相结合进行了探讨。认为该残卷的脉诊理论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对医家临证诊脉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较好地呈现出脉诊的方法和原则。如“呼吸定息”“诊脉手法”是对医生诊脉基本功的强调;对诊脉手法的要求则是对中医学脉象“胃、根、神”理论的具体应用,可据此判断疾病邪正盛衰及预后吉凶;23种病脉及6种死脉则对于预报疾病的危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4]53、62、64、68-83。
5 结语
综上所述,学界在《玄感脉经》文本的考校、抄写年代的考证、文本内容的分析、学术价值的揭示等方面已取得了不少积极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启示。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相关研究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一些重要问题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如既有研究中对残卷作者的考证还不够严谨;对《玄感脉经》编撰体例、引书情况和文本特征等还缺乏全面具体的讨论;没有将该残卷放在隋唐时期脉学演变脉络中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学术渊源、脉学理论特征研究还未深入。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的深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