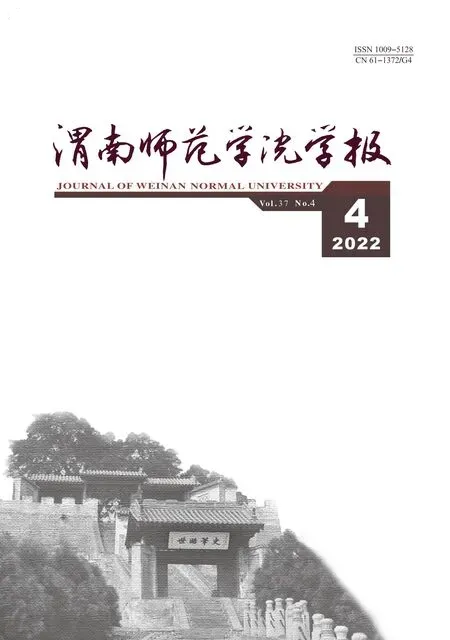戏剧化艺术手法与《史记》战争描写
马 宝 记
(许昌学院 文史与传媒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史记》是一部严肃的“正史”,其中有大量的战争描写,所记载的大大小小的军事行动多达五百次,其中较大规模的战役就有七八十次之多。在这些高超的战争艺术描写中,常常显现出独特的戏剧化手法,这种明显“失真”的战争叙事,不但不会给人“虚假”的认识,反而还会极大地增强战争的真实性和感染力,突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战争效果,提高作品的艺术力量。
一、戏剧化的战争场景
戏剧场景指为了达到戏剧效果而精心设计的艺术化环境,通过这种艺术化环境,可以极大地突出人物的地位,增强事件的重要意义,进而实现作者表达的主要意图。个性鲜明、特色突出的典型场景,往往让读者过目不忘。这些戏剧场景,既有战争发生时的自然环境,也有尖锐激烈的战争场面。
首先,《史记》战争中的自然环境具有鲜明的倾向性。
对自然环境的关注,不是《史记》描写战争的主要手段,但是,大凡出现自然环境的时候,作者都是用来表达极其明显的写作目的,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如楚汉战争中,刘邦带领五十六万大军占领彭城之后,项羽带领三万精兵反击,汉军大败,楚军将刘邦包围在核心,“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1]322。刘邦性命危在旦夕,突然狂风四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有意思的是,这种极其恶劣的天气,针对的是楚军,而不是双方的军队。很明显,作者通过这样特殊的环境描写,是为了显示刘邦的帝王身份,由于刘邦后来成了大汉皇帝,所以刘邦不能有危险,即便遇到了危险,神灵也会通过各种办法保护他。因此,这种自然环境实际上是对封建帝王的神化手法,带有作者明显的思想倾向,也表现了作者的时代局限性。
与这种手法相近的,还有《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描写的汉匈漠北之战。元狩四年(前119)春,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带领大军出塞千余里,深入漠北,与单于带领的匈奴大军正面相逢,“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骡,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挐,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余级,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1]2935。这次漠北之战是汉匈之间的一次大规模战役,司马迁在叙写战场气氛时,使用了环境衬托手法,“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虽然只有短短数语,却写出了战场的残酷,傍晚时分,两军相对,突然风沙四起,飞沙走石,两军对阵却看不到对方。这种环境的恶劣与面对敌军所遭遇的凶险合二为一,充分渲染了汉军深入敌人腹地的艰难以及最终取得胜利的壮举。
很明显,环境描写在《史记》中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司马迁在环境描写中寄寓了自己独有的思想情感,这种情感对于我们了解环境之中的人物和事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史记》极具震撼力的战争场面具有强烈的主观性。
作为史书,《史记》记录了大量的战争,其中有许多规模宏大、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战争。作者在叙述这些战争时,主要采用了客观、真实的描写手法,但是,透过这些战争场面,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寄寓在战争叙事中的主观情感,通过不同的叙事手法,表达出作者对战争和战争参与者的主观认识与评价。《田单列传》为了表现“复仇者”的正义性,充分体现田单反击燕军收复家园的目的,司马迁设计了一个想象奇特、场面宏大的“火牛阵”:田单收得千余牛,给牛披上绛色缯衣,画上五彩龙纹,将牛角上捆绑兵刃,在牛尾上绑上芦苇,再在芦苇中灌满油脂,然后点燃芦苇,将城池凿开数十个洞口,趁着夜色,将牛驱赶进城中。燃烧的牛尾将牛逼向燕军,燕军大惊。牛尾的火光将牛身上的龙纹清晰地映现出来,火牛所到之处,燕军非死即伤。跟随在火牛阵之后的五千齐兵,趁机衔枚攻袭,城内事先埋伏的战士鼓噪呐喊,老弱者奋力敲击铜器制造声势,一时间,喊杀声震天动地,燕军大败。被燕国占领的七十余城即日收归齐国。
这种战争场面,气势宏大,生动形象,充分表现了正义者的智慧,谱写了一曲为正义而战的动人颂歌。司马迁通过这种描写手法,将自己对战争的态度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著名的破釜沉舟战例,面对强大的秦军,《项羽本纪》记载:“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1]307项羽凿沉船只,摔破釜甑,烧毁庐舍,孤注一掷,表现出了无比顽强的毅力与决心。此战是奠定项羽军事成就的重要战役,司马迁为了将项羽塑造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给他设想了这么一次极端战术,战术的成功,让项羽成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历史巨人,“破釜沉舟”也成为浓缩着重要文化内涵的故事而永垂青史。
如果说破釜沉舟再现了项羽传奇人生的话,那么,身死乌江的悲惨场面则再现了一个英雄的毁灭之路。项羽明知汉军众多,难以抵敌,但依然选择了应战,经过酣畅淋漓的“东城快战”,最终自刎乌江。司马迁并未就此给项羽一生画上句号,而是进一步描写了项羽的尸体被撕成了碎片,五个人人手一块,他们甚至还“共会其体”,项羽的悲惨结局才算结束。这种带有巨大渲染、夸张成分的描写,正是司马迁刻意营造出来的振聋发聩的悲剧效果,目的是突出项羽之死的悲惨。《史记》中大量的战争场面,都带有极大的目的性,主观色彩非常浓重。
最后,《史记》战争场景中的细节描写具有明显的虚构特点。
司马迁为了强调战争的真实性,在各种战争环境中进行了大量的细节描写,这些细节描写从不同角度刻画了主要人物的内心情感与性格特征。从艺术手法上看,则具有明显的虚构特点。
垓下之围是项羽走向灭亡的开始,为了表现项羽处于极度困窘中的内心感受,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设置了“四面楚歌”和告别虞姬等场景,四面楚歌将项羽内心的惊奇、失望乃至绝望、痛苦、无奈等情感熔于一炉,“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充分表现了项羽英雄末路的巨大悲伤。接着,项羽夜起悲歌,“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为了渲染这种极度悲伤的氛围,项羽连歌“数阙”,然后,虞姬也悲情唱和,“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1]333。至此,作者将悲剧气氛烘托到高潮,之后,悲剧大幕才缓缓落下。关于这段极具悲剧气氛的描写,明末清初人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2]634所谓“笔补造化,代为传神”正是司马迁用情极深、用意极明处,是作者采用的文学虚构手法。
前述田单火牛阵,在今本《战国策》中只简单地记载道:“燕攻齐,齐破。闵王奔莒,淖齿杀闵王。田单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复齐墟。”[3]460没有火牛阵之说。《太平御览·兵部》所引《战国策》文字几乎与《史记》完全一样[4]589,很可能是《太平御览》将《史记》误为《战国策》。另外,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看,田单组织这样大规模的火牛阵也不大可能。“蕞尔小邑,被围已三年,其不至‘析骸易子’者盖已几希,何得城中之牛尚有千余耶?火牛之事,当日谅或有之,史家过为文饰,反启后人之疑窦矣。”[5]4469如此看来,火牛阵很可能是司马迁的“传神”之笔,体现了司马迁卓越的艺术创造力。
此外,淮阴侯韩信勇擒魏王豹木罂缻渡河的巧妙、李广精准的射箭技艺等,无不彰显着司马迁对战争场景的绝佳设计。
二、戏剧化的战争情节
战争情节是战争进行的重要过程,史学著作十分重视战争过程,甚至重过程而轻结果。《史记》中的大量战争情节极具戏剧性,从情节设置、细节处理、过程进展到结局安排等各环节无不如此。
田单复国之战中,为了达到削弱燕国的目的,田单使用了一环套一环的“反间计”,先是利用燕王与乐毅的矛盾,公开宣称乐毅要背叛燕国,齐国最害怕的不是乐毅,而是其他将领。《田单列传》这样记述:“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乐毅。”[1]2454田单的第一步成功了。第二步,又公开宣称说:“吾唯惧燕军之劓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败矣。”[1]2454燕人又上当了,但却引燃了齐人对燕人的愤怒之情。第三步,又实施反间计说:“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为寒心。”[1]2454燕军再次上当,也再次让齐人更加愤怒,“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1]2454。田单成功引发了齐人对燕军的憎恶情感之后,开始部署第四步:犒赏将士,埋伏士兵,让老弱妇女登上城墙诈降燕军;又让富豪带着自己募集来的千金送给燕将,瓦解燕军斗志,防务松懈。这一切做完之后,才开始实施火牛阵战术,并一举收回失地。田单的战争计划安排得天衣无缝,步骤合理巧妙,但很难经得起推敲,仿佛燕王、燕军总被他牵着鼻子走,丝毫没有辨析能力。其实,这正是作者高度艺术化处理的结果。
与此相似的,是楚汉战争中,陈平实施反间计,成功离间了项羽和范增之间的关系。《项羽本纪》这样记述:“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详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1]325盛怒之下,范增离开项羽,“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1]325。此计虽然非常成功,但似有刻意之嫌,引起不少后人议论,史珥亦云:“曲逆间范增,号称奇计,然其术甚浅。岂羽本无机智,以浅中之,乃所以为奇欤!”[6]621
马陵道之战中,为了表现孙膑的战争才能,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中也采用了这种“预设机关”的手法。孙膑估计庞涓在傍晚时分到达狭窄的马陵道,于是,提前在路两边设下“善射者万弩”的埋伏,约定信号说“暮见火举而俱发”,又在树上砍下一块树皮,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1]2164。最终,情节的发展完全按照孙膑的设想,庞涓失败后自杀。马陵道之战也大大改变了《战国策》的简单叙述,增加了大量生动、逼真的故事情节。
田单、孙子、陈平等人在战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神机妙算”,虽为巧合却不失艺术真实,既给战争情节增添了无穷的吸引力,让战争变得波澜起伏、曲折有致,又符合战争发展规律的逻辑性,是作者戏剧化艺术手法的成功体现。
三、戏剧化的战争智慧
战争智慧对于战争的胜负至关重要,一场精彩的战争,靠的是双方智慧的较量。而智慧体现在战争的部署、计策的制定、过程的完善,以及结果的完成等各方面。《史记》描写的战争智慧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韩信是楚汉战争中的重要军事将领,他先后指挥的擒获魏王豹的安邑之战、击败赵王的井陉之战、消灭龙且的潍水之战等,每一场战役都惊心动魄,都充满了战争智慧。尤其是井陉之战,整个战争过程波澜起伏,在《淮阴侯列传》中把韩信的战争智慧体现得淋漓尽致。
韩信与张耳带着“数万”兵力要进攻赵国,赵国君臣召集二十万兵力应对。按理说,韩信以少战多,而且是长途行军,没有优势可言,取胜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事情往往有“戏剧化”的发展,广武君李左车看到了韩信军的不足,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但是,“儒者”成安君陈余固守兵法理论,听不进李左车的建议,这样,就给了韩信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韩信“大喜”。之后韩信从容地进行战术部署,部署之严密、巧妙,甚至连部将都不相信。战争的过程完全按照韩信的设想进行,结果也与韩信预计的完全一样,最终,陈余被杀,赵王被俘。此战显示了韩信极其高明的战术,当然,这种战术带有极大的冒险成分,有很明显的“戏剧化”特征。明代茅坤说:“使成安君能用李左车之计,以奇兵绝井陉之口,而亲为深沟高垒以困之,信特投虎于匣矣。信之间知成安君之不用,故敢入焉。信之虑盖亦岌岌矣。兵入之后,又安知成安君不以战少利而悔悟乎!”[6]4836姚苎田对韩信得到赵国情报的原因予以推测说:“左车之策果用,必不使敌人得知。所以为信知者,余方以大言恫吓、创虚声以折之之故耳。”[7]174这说明姚苎田注意到了司马迁描述的细节存在的问题,但他的推测似无道理。应该说,不是韩信不知危险,也不是成安君没有悔悟的可能,韩信得知情报的途径也不可能如姚苎田所说,这一切都是由司马迁出于一种“戏剧化”效果需求而“设定”的,当然,这种“设定”是由高明的艺术手法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司马迁的艺术创造既合乎历史事实,又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李将军列传》中,李广与匈奴的交锋,也体现了极其传奇的一面。李广带领百十个骑兵去追“射雕者”,误与敌军数千骑兵相遇,对方却把他们当作诱骑,这时,双方斗智斗勇,匈奴骑兵立刻占据了山上的有利位置,并布列好阵地,严阵以待。而汉军这边,面对数十倍的敌军,都极度恐慌,想要迅速撤退。李广从容不迫,告诉部下,如果逃走,只有死路一条,这时要做的,就是要让敌人把我们当成真的诱骑,他们才不敢轻易动手。确定了这种做法之后,李广采取了更加冒险的几个行动:第一个是继续前进,到离敌军阵地不足二里的时候停下来。第二个是停下来后不但不做防备,反而还下马解鞍,这可是极其危险的命令。第三个是看到敌军有白马将走出阵列护卫自己的骑兵,李广竟然带领十余名骑兵主动出击,杀死白马将之后又回到自己队伍之中。经过这一系列大胆又极度冒险的举动,敌军竟然越发不敢有所动作,夜半时分偷偷将军队撤走了。这次“战役”虽然没有直接作战,但反映了李广沉着、冷静、机智、大胆的超人战争智慧。这种“超人智慧”,司马迁通过几个节点表现出来:其一,在敌军犹豫的片刻,李广迅速判断出敌军把自己当作诱骑了,这个判断极其重要,是后来一系列决定的基础。其二,就是上述三个行动,这三个行动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李广这百十个骑兵都将是悲惨的结局。这几个节点是李广大智大勇的具体体现,更是司马迁的“神化”之笔。
四、戏剧化的战争效果
司马迁在叙述战争过程时,为了突出战争某一方面的特点,达到战争叙事的目的,采用了大量的戏剧化的夸张手法,极力渲染战争效果。
“申包胥哭秦廷”是著名的爱国故事。楚昭王时,吴军占领楚国,楚昭王逃亡到随国,申包胥到秦国请求救援,为了求得秦国的帮助,立于秦廷连续七昼夜哭泣,终于感动了秦君。
这段历史记载,是司马迁根据先秦史料改编而成的。《左传·定公四年》记载:申包胥被秦哀公拒绝后,申包胥“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8]1548。司马迁对原文的改编主要有三点:其一,申包胥站立哭泣的地点由庭墙而变为“秦廷”,亦即秦王的王廷,站在墙壁边与站立在廷堂之上效果显然不同。其二,原文是“日夜不绝声”,这里的日夜可以理解为一昼夜,也就是哭了一整天。司马迁在“昼夜哭”之后,写道“七日七夜不绝其声”,可见是连续七昼夜哭声不断。其三,原文是“勺饮不入口七日”,也就是连续七天不喝一口水,而司马迁改编为连续七昼夜哭泣,将事件由喝水改为哭泣。经过这样的精心改编,申包胥哭秦廷的效果大大增强了。当然,原文的“勺饮不入口七日”已经具有了明显的夸张因素,正如杨伯峻注云:“此言或太过,以生理言之,七日不饮水,不能生存。”[8]1548司马迁将之改为“七日七夜不绝其声”,恐怕更难符合人的生理条件。因此,这里只能作为一种文学化手法来理解,是司马迁为了突出申包胥的哭声而进行的对艺术效果的强化。
秦晋崤之战是秦晋两国进行的争霸战,秦国趁晋文公去世,偷袭郑国,灭掉晋国的同姓国滑国,被晋国认为是对晋的巨大侮辱。司马迁为了表现这次出兵的非正义性,设置了蹇叔哭师、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和晋灭秦师等情节,这些环节以极其典型的艺术手法,体现了司马迁对这次战争的态度。
蹇叔哭师重点表现秦国内部对非正义战争的反对力量,秦穆公因为有人做内应而悍然对郑国发动袭击,征求蹇叔意见时,蹇叔态度鲜明,反对出兵,而秦穆公却我行我素。秦穆公不听谏阻,蹇叔悲愤而哭。蹇叔是秦穆公的辅佐大臣,司马迁通过蹇叔的态度,对秦穆公劳师袭远、试图投机取胜的做法进行批评。有意思的是,司马迁在记述这段史实时,对《左传》和《谷梁传》的记载进行了改写,重要的改写有两处:其一,将蹇叔对参与战争的儿子的两次哭泣改为一次;其二,将“蹇叔之子与师”改为“使……蹇叔子西乞术及白乙丙将兵”,将蹇叔之子改为将领。这种改写虽然“降低”了蹇叔“忧国忧民”的“思想觉悟”,却使情感更加真实,试想,一个堂堂的秦王廷上大夫,面对必然失败的出征军队,可以悲伤,可以愤怒,可以痛心疾首,但是号啕大哭可能性不大,所以,也只有自己的儿子是征战的将帅,手中掌握着众多一去不返的士兵的生命的时候,他的内心才能够因震颤而哭泣。司马迁因如此似无证据的改写,遭到后人诸多苛责,清代梁玉绳说:“史公叙袭郑之事依《公》《谷》,故与《左传》异,然《公》《谷》但云二老哭送其子而已,未尝谓三帅即其子也,乃《史》取而实之。……真《史通》所谓李代桃僵也。”[9]129王若虚亦云:“司马迁记此,以为二老同辞,不知其何据也。”[6]333马非百甚至说:“伐郑之役,谏而哭送其子者,只蹇叔一人。《史记》以孟明视为百里奚子,西乞术为蹇叔子,尤属荒谬至极。”[6]333
王孙满观师,是作者用来表现秦军“无礼”而败的证据,从战争规律来看,“无礼”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部队的作战效果,但并非军队失败的必然原因,司马迁这样写,主要是从艺术的角度将秦军失败的各种因素串联在一起,说明这次战役的非正义性。至于郑商人弦高犒师的故事,作者也本着从现实生活出发,把犒师的原因说成是“恐死虏”。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渲染,秦军在返回途中,晋军“发兵遮秦兵于殽,击之,大破秦军,无一人得脱者。虏秦三将以归”[1]192。
司马迁将这次秦晋崤之战作为典型战役,表现了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实力的强弱,而在于人心的向背,通过极具文学特点的故事情节,强调了战争的正义性与否与战争胜负的密切关系。
对于项羽失败的悲惨结局,司马迁使用了渲染手法。从阴陵失道时的无奈、四面楚歌的凄楚,到东城快战的酣畅、五人分尸的惨烈,环环扣人心弦、步步痛心疾首,英雄失路之悲、穷途末路之哀跃然笔端。姚苎田说:“皆子长极意摹神之笔,非他传可比。”[7]19
除了完整的战争故事之外,还有许多“戏剧化”语言和戏剧化行为动作,如郦食其面见刘邦时高呼自己是“高阳酒徒”,刘邦才待之以礼(《郦生陆贾列传》);项羽被围呵斥赤泉侯,让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表现了项羽的高大威猛(《项羽本纪》);楚汉战争项羽反击刘邦,汉军死伤无数,“睢水为之不流”,说明了项羽反击力量巨大,成效显著(《高祖本纪》)。
《史记》描写了许多战争,这些战争的基本创作手法是纪实的。但是,为了突出战争效果、表现作者的军事战争思想,司马迁也采取了戏剧化的描写手法,用各种文学手段将战争描写得极其生动、形象,表现了作者通过战争所寄寓的丰厚意蕴。这种戏剧化手法对后世散文作品和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