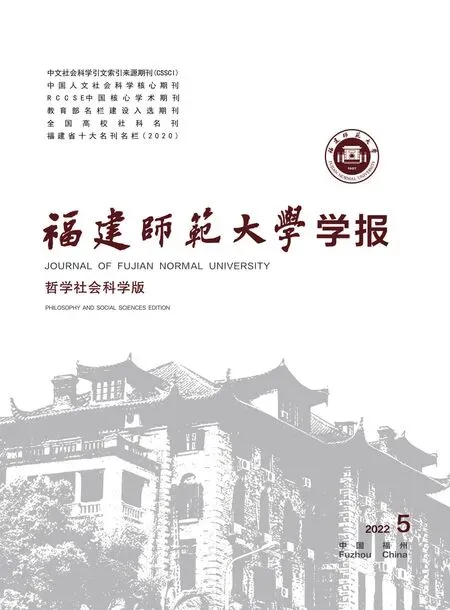物质阐释学:一个概念史
张 进,王红丽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概念史研究“关注的是一个(重要)概念的生成、常态或者非连续性、断裂和变化,关注变化的转折点、衔接点、关节点”(1)方维规:《关于概念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第151-160页。。“物质阐释学”(Material Hermeneutics)思想在“局部阐释学”“一般阐释学”和“哲学阐释学”中,(2)[美]R.E.帕尔默:《解释学》,孟庆时摘译,《哲学译丛》1985年第3期,第21-29页。都可以窥见其痕迹,尤其是在阐释学范畴转变的关键节点上。以语文学阐释学为主的“局部阐释学”作为原文注释或翻译的规则和方法,强调了一种解释的物质理论,关注了语言文本、语料库以及相关的物质性阐释技巧。自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把阐释学发展为“一般阐释学”之后,语文学阐释学逐渐向以主体性为中心的阐释学转变。经由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人的进一步发展,阐释学不仅把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排斥在外,而且更偏向于精神科学的一般“理解”,解释规则体系内外的物质性因素受到一定程度的漠视。在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哲学阐释学”中,物质性因素逐渐退到了阐释学的后台。
随着21世纪以来对“一般阐释学”“哲学阐释学”的反思和批判,文学阐释学视域内出现了语文学阐释学的复归。正如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Raman Selden)观察到的那样,21世纪“理论的终结”之后,“批评家、教师和学生们首要把握的是文学的‘基础和基本功’,不是那些理论的种种‘主义’,而是文学传记和版本目录学”(3)[英]拉曼·塞尔登、[英]彼得·威德森、[英]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2页。。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德国文学史家彼得·斯丛狄(Peter Szondi)立足文学阐释学,呼唤语文学传统的回归,提议并使用了“物质阐释学”(4)据现有材料看,斯丛狄于1975年提议并使用了“Material Hermeneutik”一词,在其著作Einführung in die Literarische Hermeneutik中探讨了语言文本的物质性在文学阐释学中的作用。英语把该词译为“Material Hermeneutics”,法语译为“Herméneutique Matérielle”,另有译为“Hermenéutica Material”。术语,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了阐释学的历史;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后现象学家、“技科学”研究者唐·伊德(Don Ihde)立足实证主义和具体的科学文本,把自然科学重新拉回阐释学视野,提出并论述了“事物阐释学”(Hermeneutics of Things),从物质性角度考察了物质技术在科学研究和科学文章中发挥作用的方式(5)Don Ihde,Expanding Hermeneutics:Visualism in Science,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8,p.139.。经过彼得-保罗·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莱安德罗·罗德里格斯·梅迪纳(Leandro Rodriguez Medina)等人在“物质阐释学”概念下对伊德思想的引申论述,以及伊德本人对“物质阐释学”的系统阐发和分析运用,“物质阐释学”逐渐突破了特定类型“文本”的物质维度范围,反转了“语言论转向”,跨越了“狄尔泰鸿沟”(Diltheyan Divide),渐次发展为一种基于物质性研究的新型“一般阐释学”,一种“非单一学科的”通用方法。
一、物质阐释学“前史”:关注语言文本的物质性
(一)语文学阐释学
据现有材料看,“物质阐释学”这一术语在20世纪中叶以后才出现,但阐释学早期的语文学文本注释和辨别原文的活动,以及宗教、文学、法律等不同学科的阐释实践已经突出了语言文本的物质性在阐释学中的重要作用,可视为物质阐释学的早期形态或“前史”。从《圣经》解释而来的“局部阐释学”方法发展为一种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即语文学注释的一般法则,一种语文学阐释学。19世纪初,“圣经诠释将语法分析的技术发展到精微极致,而诠释者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全然专注于圣经解释的整个历史背景知识……诠释者的真正任务变成了一项历史的任务。随着这些发展,圣经诠释学的方法从本质上就变成诠释的世俗理论——即古典语文学——的同义词了。至迟自启蒙运动起,乃至今天,研究《圣经》的方法就与语文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6)[美]理查德·E.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8-59页。。施莱尔马赫建立起“一般阐释学”之后,阐释的重心从语言转向了主体性,因为“惟在诠释学(阐释学)基本上不再专心于澄清诠释不同种类文本多变的实际问题时,才可能将理解的行为作为它真正的出发点。在施莱尔马赫那里,诠释学真正成为了‘理解的艺术’”(7)[美]理查德·E.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14页。施莱尔马赫的论断是:“作为理解艺术的诠释学,并非作为一种普遍的领域而存在,而仅仅是作为专门化诠释学的复数而存在。”基本目标是建构一种作为理解艺术的一般诠释学。。这把重视语言文本及其物质性的语文学阐释学转变为一种对理解本身的研究,暗含了对语文学立场的批判。
语文学与阐释学关系紧密,语文学源自古希腊语“philologia”,常译为“文献学”,主要指一种“古典学术”,其任务是利用科学的方法来复活已逝的世界,其出发点是对不理解的现存事物的敬畏之感。(8)[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陈恒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页。古典学术是一种包括语文学、文学、考古学等学科在内的整体性存在,早在公元前的古罗马时代,就有大批学者致力于古代文献的保存工作。在19世纪的欧洲,语文学曾被认为是一门与数学、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相媲美的准科学,是一切精神学科或者人文学术的基础,也是现代人文学科形成的基础。(9)Sean Gurd,Philology and Its Histories,Columbus:The Ohio University Press,2010; James Turner,Philology: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xiii.语文学问题与阐释问题密不可分,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
在形式主义盛行的整个20世纪,学科划分越来越细,语文学作为一门与文学研究相关的学科并不在文学研究的“内部”。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发生了广泛的重组,其结果之一就是文学概念扩大并包括了许多被视为边缘的东西。一方面,文学自身发生了转向(10)王冠雷:《“后理论”的三种文学转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45-51页。;另一方面,产生了一种文学物性的彰显与文献笺注批评的复归。(11)张进:《通向一种物性诗学(笔谈)》,《兰州学刊》2016年第5期,第48-69页。在“后理论”的种种探讨中,塞尔登指出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认为即便在转向意识形态的整个时期,传记的、历史的、目录学的、版本学的文学研究依然在理论闹嚷的轰动中静静地继续进行着,而“版本目录学考察一个文本从手稿到成书的演化过程,从而探寻种种事实证据,了解作者创作意图、审核形式、创作中的合作与修订等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这种考索程序一般被称作:‘发生学研究’”(12)[英]拉曼·塞尔登、[英]彼得·威德森、[英]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2页。。文本发生学主要是对作家手稿进行分析、整理和辨读,需要时予以出版,发生校勘学主要是对这一分析的结果作出解释。(13)[法]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文本发生学》,汪秀华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页。一方面,文学概念本身发生了变化,所恢复的语文学或版本目录学与传统的语文学阐释学不尽相同;另一方面,它也强调了原文(手稿)及其物质性的特殊性和可理解性。
传统语文学阐释学规则和标准需要根据目前对文本的理解加以批评或修正,发展出一种批评的语文学阐释学。斯丛狄作为“文学阐释学”的重要人物,在1966—1967年的讲演和著作中,研究了施莱尔马赫以前的阐释学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学者,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孕育的阐释学者约翰·马丁·克拉德尼乌斯(Johann Martin Chladenius)、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迈尔(Georg Friedrich Meier)和格奥尔格·安东·弗里德里希·阿斯特(Georg Anton Friedrich Ast),对文学阐释中哲学的客观性进行了批评。(14)[美]R.E.帕尔默:《解释学》,孟庆时摘译,《哲学译丛》1985年第3期,第21-29页。在斯丛狄看来:“文学阐释学是对文学作品的注释(exegesis)、诠释(interpretatio(15)从历史发生学来追溯,interpretation一词来自拉丁文interpretatio,它同时意指“阐发、解释的行为”以及“翻译作品”。在拉丁修辞学中,interpretatio指的是“用一个词来解释另一个词”,也就是同义词的使用。同时它也是根据“interpres”引申而来,后者指的是“中介者、媒介物、使者”以及“外语的翻译者、译员”。(见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501-502页))或解释(interpretation)的理论。”(16)Peter Szondi,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Hermeneutics,Martha Woodmansee 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3.这突出了语文学在其中的作用,但阐释学现在“已经开始认为自己优于它曾经的任务——成为一个关注解释规则和标准的物质理论”(17)Peter Szondi,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Hermeneutics,Martha Woodmansee 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3.,成为一种“规则背后的方法,指向对理解的分析。虽然这种阐释学的哲学基础是与施莱尔马赫和物质阐释学的延续结合在一起的,但在神学领域之外,只有哲学冲动继续活跃。此外,近百年来的文学研究几乎没有展现物质阐释学的必要性”(18)Peter Szondi,“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Hermeneutics,”New Literary History,Vol.10,No.1,1978,pp.17-29.。这印证了始于物质理论的阐释学发生转变的事实以及物质阐释学的缺失状况。
解释的“物质理论”(the ‘material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是一种关于理解的认识论,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实用的解释方式。(19)Peter Szondi,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Hermeneutics,Martha Woodmansee 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Cover introduction.与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一样,斯丛狄拒绝最小化对理解的认识论的需要,认为理解的认识论是建立一种实用的解释方法论的基础。(20)Paul Ricoeur,“Existence and Hermeneutics,” in Josef Bleicher (ed.),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Hermeneutics as Method,Philosophy,and Critiqu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0,pp.236-256.他关注阐释规则制定的实用或实践意义。“如果我们想把文学阐释学建构为一种物质理论以融合历史意识和后启蒙诗学的密切相关洞见,那么它就不能是一种必然从理解对象的特定性质中抽象出来的规则阐释学。相反,阐释学将通过澄清标准来表达其物质性,从而使文本在其特定性方面可供理解。也许这些标准中最重要的是最广义的历史性(historicity)和体裁(genre)。”(21)Peter Szondi,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Hermeneutics,Martha Woodmansee Tra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30.历史性和体裁是系列标准的基础,需要沉降到物质性层面才能被理解。
(二)语言文本的物质性
在1957年使用“物质阐释学”一词时,斯丛狄就比较谨慎。对他来说,物质阐释学一词无疑指阐释学必须依赖“物质”(matériaux),即一个特定的语料库(corpus déterminé)。(22)Denis Thouard,“Qu’est-ce Qu’une Herméneutique Critique ? ”Methodos:Savoirs et Textes,Vol.2,2002,pp.289-312.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methodos/100,February 3,2021.语料库是根据构成它的文本的类型、关系和用途建构的,对文本的阐释取决于文本所属的语料库,突出了历史背景的整体性。在文学阐释学视域中,斯丛狄反对文本和接受之间的时间连续性,而强调历史意识,即一种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物质和知识关系。“物质阐释学(hermenéutica material)是一种时间性的阐释学,其核心是对文学作品形成过程中内在的不连续性和矛盾性的文本解释。”(23)José Manuel Cuesta Abad,“Lectio Stricta:La Hermenéutica Material de Peter Szondi,” in Peter Szondi (ed.),Introducción a La Hermenéutica Literaria,Madrid:ABADA Editores,2006,p.23.这种不连续性和矛盾性体现在斯丛狄所谓的文本变体和平行段落中。前者如一些文本提纲或不同片段的版本,通过这种物质过程可以重建作品,同时也可以基于此种文本物质性,在接受过程中出现断裂,如删改、更正和矛盾等。变体文本化在笔记、信件、文件或散文等不同体裁形式上。后者意味着同样的词出现在同一作者的不同文本中,具有不同含义;或具有相同含义的词出现在不同文本中。这种语言上的平行和实际语言的不同可以证明文学作品的某种历史性。
批判阐释学家让·博拉克(Jean Bollack)发展了物质阐释学,认为“斯丛狄对语文学的辩护和呼吁,与把‘阐释学’作为一门‘科学’联系在一起,是基于对局部(文学、历史或司法)的重新定义,并由其对象的性质决定”(24)Jean Bollack,“A Future in the Past:Peter Szondi’s Material Hermeneutics,” in Peter Szondi (ed.),Martha Woodmansee Trans.,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Hermeneu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35.。这种研究是一种批判的语文学(a critical philology),很大程度上符合解经学、语文学研究方法并内含了一种批评维度,成为批判阐释学的理论来源之一。
斯丛狄的物质阐释学整合了阐释学和语文学,是一种可以在实践中应用的文学文本的解释学说。安东尼·约翰·哈丁(Anthony John Harding)认为斯丛狄的物质解释学一方面尊重“待解释文本的真正多样性”,另一方面也是经验性的,因为它需要“足够具体,不必为了专注于理解行为而忽视个别问题”。(25)Anthony John Harding,“Coleridge’s Notebooks and the Case for a Material Hermeneutics of Literature,” Romanticism,Vol.6,No.1,2000,pp.1-19.在对1957年出版的《柯尔律治的笔记》(Coleridge’sNotebooks)的研究中,哈丁考虑的问题是,若“思想”概念本身是由记录的物质对象塑造的,那么笔记(notebooks)作为一种铭写模式如何为作家记录提供形式?铭写模式或记录方式的物质性变化对“思想”概念是否产生影响?当试图在物质材料记录的随意性上强加某种秩序,即把笔记变成一本印刷书籍时会发生什么?因为强加的秩序可能创建出新的文本和新的主题。另外,当印刷和注释文本代替手稿的“混乱”后将如何影响文本的接收和解释?哈丁把斯丛狄对传统文类的思考扩展至非传统文类(如信件、日记和笔记)上,突出了“文本的特异性”可供理解的原因,且定义了对此类文本的解释选项,关注了笔记的物质性质,以及与手稿、印刷文本的物质关系,强调了阐释过程中原文的物质载体、物质媒介和物质环境的重要性。这是意义依赖于文本物质性的例子,同时也彰显了“待解释文本的多样性”,有助于理解作者的话语,以及该作品与当代话语的互动。
至少,在接触文本时,首先会“读到”文本的物质性,一种“物理现实”(physical reality),在对文本及其阅读活动展开研究时,需要将这些物质性纳入考量。(26)Graham Allen,Carrie Griffin,Mary O’Connell,Readings on Audience and Textual Materiality,London:Pickering & Chatto Publishers Ltd,2011,p.1.斯丛狄的物质阐释学有助于语文学与精神科学的结合。他提醒我们,在启蒙运动时期,一种既哲学化又逻辑化的阐释学已经存在,他发现了回归阐释学的另一种理解的合法性,具体来说是以一种语文学阐释学,来回应哲学阐释学的反实证主义倾向。也就是说,阐释学依赖于“物质”,而不是直接建立在更高层次上的一般理论(比如本体论)上。这种文学研究中的物质阐释学视角,其研究对象是语言文本及其物质性。随着阐释学和文本概念的扩展,物质阐释学试图突破语言文本模态的阐释,走向深化和“普遍化”。
二、“局部”物质阐释学:聚焦“技科学”的物质性
(一)技科学阐释学
在阐释学理论发展史上,随着“一般阐释学”的发展,生命体验活动代替语文学阐释,逐渐成为关注的重点,阐释学成为精神科学的基础,并将自然科学或实证主义的传统“挤出”阐释学视野,进而在理论层面建起阐释学与实证主义之间的“狄尔泰鸿沟”。从现实层面来看,当代科学和大部分当代技术都是技术化的科学(techno-science)。当代科学是物质化的、技术化的和具身的(27)[美]唐·伊德:《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页。,这是“技科学”的一种含义(28)“技科学”(technoscience)这一术语是比利时哲学家霍托伊斯(G.Hottois)在1979年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现代科学实验使科学研究与实验仪器及相关技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主张用“技科学”来代替“纯科学”,以表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不可分离性。1987年拉图尔(Bruno Latour)扩展了技科学内涵,目的是超越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两极对立。而唐·伊德认为技术在历史上先于“科学”,至少在任何现代意义上是这样的。技术总是我们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科学不是技术的起源而是技术的工具。所以技术“在存在论上”先于科学,而技科学是科学和技术杂交后的产物,在同一个杂交体中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技术在历史上甚至比人类(现代早期智人)还要古老;另一方面,当代技术又是技术科学化的技术。那么对技术的批评的、哲学的研究是一种后现象学、技术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technics)的方法。技术现象学研究人类经验技术的范围和各种形式。(Don Ihde,Instrumental Realism,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p.140; [美]唐·伊德:《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55页)。阐释学与实证主义交往互动,使阐释学不仅成为科学的,而且成为“技科学”的,从而形成一种技科学阐释学。
狄尔泰于19世纪90年代转向阐释学,已明显超越了他对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研究中所采用的心理化倾向。(29)[美]理查德·E.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9页。他对“说明”(explanation)、“理解”(understanding)和“解释”(interpretation)的区分导致了一种偏见,即科学“说明”自然,而人文研究则是“理解”生命之表现。(30)张进、蒲睿:《论“狄尔泰鸿沟”》,《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40-48页。阐释学成为一种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并经由伽达默尔等人发展出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阐释学。唐·伊德认为“狄尔泰鸿沟”从理论上放大了自然科学(一种说明的方法)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一种理解的方法——主要是阐释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31)Don Ihde,Material Hermeneutics:Reversing the Linguistic Tur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22,p.126.这导致阐释学缺乏自然科学倡导的实证主义分析模式,而且“物”本身的“物性”被科学化、单维化(32)张进:《通向一种物性诗学(笔谈)》,《兰州学刊》2016年第5期,第48-69页。,弱化了事物研究中的阐释学维度。
伊德批评实证主义和阐释学之间的二元对立,指出前者基于一种信念,认为科学可以通过严谨的方法准确地描述世界;后者是一种试图理解文本所说内容的活动,没有严格的科学基础。这种区分既无法使我们加深对事物深层要素的理解,也不能反映科学家或阐释者的现实工作。事实上,每一项科学活动中都有阐释学因素,而阐释活动中都包含科学或实证的(positivistic)元素。一方面,“许多科学实践在功能上都是阐释学的”,科学哲学无法回避阐释学,且阐释学可以通过关注技术来扩展自身。(33)Don Ihde,Expanding Hermeneutics:Visualism in Science,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8,pp.3-4、46、137.伊德结合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的具身化(背景)实践现象学和帕特里克·A.希兰(Patrick A.Heelan)的科学仪器阐释学,立足人与技术关系的现象学开展研究,认为技术需要以一种独特的现象学-阐释学方式,间接或反思性地揭示自身。(34)Don Ihde,Expanding Hermeneutics:Visualism in Science,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8,pp.3-4、46、137.科学是技术的工具,“科学已经能够创造出一种视觉阐释学,虽然它的功能类似于更早期的写作发明,但它通过事物的视觉化的各个维度发挥作用”(35)Don Ihde,Expanding Hermeneutics:Visualism in Science,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8,pp.3-4、46、137.。这就像人文学科中的阐释学实践一样。另一方面,“狄尔泰鸿沟”的后果之一是处于人文学科活动中心的阐释学被边缘化,与所谓的科学和数学等学科隔绝,设定人文学科无法获得“真理”。但正如众多人文学者所揭示的,人文学科内确实存在客观和真理因素。伊德认为哲学对技术的忽视,部分来自哲学本身,从柏拉图(Plato)开始,哲学家把哲学视为一种概念体系而非物质体系,理论作为关系体系中的概念通常与心灵相关,而实践总是与身体相关。(36)Don Ihde,Technics and Praxis,Dordrecht: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79,p.xix.
两种情况都涉及对物质的解释,而解释往往通过技术手段调节或中介,并使现实以新的方式呈现。伊德认识到以前的“文本主义者”(textists)赞成的阐释学是一种“文本阐释学”(textual hermeneutics),(37)Don Ihde,“Postphenomenology-Again? ” Working Papers from Centre for STS Studies,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 Media Studies,University of Aarhus,2003,pp.4-25.遵循了“狄尔泰鸿沟”的理论设定,忽略了与科学(实证主义)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研究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的阐释学方法以及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建构主义”,他转向了对“科学阐释学”的恢复。通过研究感知、身体、物质和阐释学在我们通过技术感知世界时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伊德扩展了阐释学和现象学之间的联系,发展出一种“科学的技术扩展阐释学”(the technologically extended hermeneutics of science),其中隐含了一种物质阐释学。
1998年以前,伊德较多地使用了“事物”(things)以及“事物阐释学”(hermeneutics of things)和“事物的阐释学”(thingly hermeneutics)等相关概念,这在阐释学中有其传统。20世纪以来,阐释学融入了现象学研究,从而扩展了自身。海德格尔从现象学转向对事物(things)的研究,阐发了一种可称之为“物性存在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事物观(38)Graham Harman,Heidegger Explained:From Phenomenon to Thing,Chicago and La Salle,Illinois:Carus Publishing Company,2007,pp.1-2.,此时阐释学既不是文本阐释学的科学或规则,也不是精神科学的方法论,而是对人类存在本身的现象学说明。(39)[美]理查德·E.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1、62-63页。伽达默尔遵循海德格尔开创的此在阐释学,发展出一种“哲学阐释学”,但他主张“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将阐释学带向了“语言学”,这一点被利科所继承。利科对阐释学的定义“重又聚焦于文本注释,以此作为诠释学中独特的和核心的规定性要素”,(40)[美]理查德·E.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61、62-63页。他公开反对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传统的心理和历史的阐释学,赞成研究话语与符号学相关的原文的阐释学。
伊德在其博士论文《阐释学现象学:保罗·利科的哲学》以及之后的数篇文章中(41)Don Ihde,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1.(该书基于其博士论文);Don Ihde,Material Hermeneutics:Reversing the Linguistic Tur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22,pp.123-129.,系统阐述了利科的理论,认为利科以语言文本(textual-linguistic)的形式对历史进行了阐释,重新聚焦文本注释,在将阐释客体从语言文本向非常宽泛意义上的文本的转变过程中,产生了阐释学现象学,弱化了现象学中的先验倾向。虽然这一研究并未涉及技术问题,但对利科现象学的阐释思想内在衍变历程的研究,奠定了伊德物质阐释学的基础。利科对语言、文本等问题的关注是伊德阐释学思想的主要源泉,他后来提出的物质阐释学思想是从反对利科关注的“语言”开始的,而且他把利科视为沟通欧洲哲学与美国哲学的桥梁。(42)杨庆峰:《翱翔的信天翁:唐·伊德技术现象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二)让事物“说话”的阐释学
20世纪70年代,伊德转向技术哲学研究,其研究兴趣在于成像技术,而成像技术的产品和图像需要解释,预示了“局部”物质阐释学的出现。“事物阐释学”狭义上指的是一种“科学对象的阐释学”(43)Don Ihde,“Thingly Hermeneutics/Technoconstructions,”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Vol.30,No.3,1997,pp.369-381.。伊德强调,科学通过把事物转化为科学对象来解释事物。(44)Don Ihde,Expanding Hermeneutics:Visualism in Science,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8,p.139.阐释学从语言情境扩展到了技术情境,研究对象也从文本扩展为科学对象或物质现实。21世纪以来,伊德通过修改现象学维度的事物概念以及把具体事物引入阐释学分析,基于与成像技术相关的物质实践的解释风格,分析科学如何进行了“事物阐释”,发展出“让事物说话”的阐释学——让曾经沉默的事物发出声音,并把看不见的东西带入视野之中。(45)[美]唐·伊德:《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3-105页。
起初,伊德并未明确“事物”的具体含义,他担心“范畴失误”,(46)计海庆:《“所有的科学都是具体化于各种技术中的”——访当代美国著名现象学家和技术哲学家唐·伊德》,《社会科学报》,2007年9月13日第5版。他的事物观是逐渐形成的。后来在与他人的合著中,伊德认为所谓的“事物”(things),是在物质形式和技术的广义层面上使用的,它涉及日常对象(mundane objects)、器具(tools)和手工制品(artefacts)的物质性,也指现代技术和数字文化的新形式。(47)Don Ihde,Lambros Malafouris,“Homo Faber Revisited:Postphenomenology and Material Engagement Theory,” Philosophy & Technology,Vol.32,No.2,2019,pp.195-214.伊德使用了一种修辞学方式,将文学文本或语言文本扩展为一种“技科学”文本。因为技术不能脱离物的状态而存在,就像文学不能脱离文字文本一样,技术应该是一种“交互关系存在论”(inter-relational ontology),其能动性是人与事物交互建构的能动性。
维贝克以“物质阐释学”(material hermeneutics)为题,对伊德1998年出版的《扩展阐释学:科学中的视觉主义》一书作了书评,认为该书是物质阐释学的“大纲”。伊德考察了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利科的著作,发现阐释学不应仅仅指向语言学(the linguistic),也应该指向解释的感知方面。从伊德的现象学方法来看,感知具有阐释维度,因为它构成了人与现实的关系。比如仪器使科学家能够感知没有仪器就无法感知的现实的各个方面,待研究的现实必须被技术“翻译”为可感知的现象,“现实”是由感知它的仪器共同塑造的。(48)Peter-Paul Verbeek,“Material Hermeneutics,” Techné: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Vol.6,No.3,2003,pp.91-96.如对于奥兹冰人的研究及其考古学的分析即接近于维贝克对物质阐释学中技术的强调。技术让事物说话,碳-14年代测定、DNA分析和质谱技术创造了新的解释可能性,揭示出奥兹冰人的更多信息。
物质阐释学分析的对象不再只是文本,还有自然本身,使用的“工具”(instrument)也不仅是眼睛,还包括各种技术设备。一方面,它探讨“通过‘让事物说话’可能产生的知识类型”,即“用科学工具制造知识”(49)[美]唐·伊德:《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这种论点表明后现代科学需要通过图像或视觉的解释产生知识),可能是基于考古学的定义,因为考古学主要是一种视觉物质阐释学;另一方面,物质阐释学与后现象学相联系,通过利用自然科学中的工具和仪器,使人文社会科学获得更多新的信息。伊德讨论的阐释学是物质的和后现象学的,利用技术开启新的阐释类型,几乎颠覆了文本注释的传统阐释实践。阐释的视角聚焦于技术文本的物质性维度,强调了技术在事物转变过程中的阐释学效用,认为物质阐释学隐喻地来看是一种通过新的科学成像技术“让事物说话”的解释方式,并指出这样一种物质阐释学也许会取代由利科改良的常用语言——文本阐释学(linguistic-textual hermeneutics)。(50)Don Ihde,“A Prelude to Material Hermeneutics,”Acta Baltica Historiae et Philosophiae Scientiarum,Vol.8,No.2,2020,pp.5-20.(该文是对2013年讲稿的整理)
曾参加伊德研究小组的梅迪纳,将物质阐释学方法引入社会科学,吸收“行动者网络”和物质符号学等相关理论,关注了对象及其背景的物质性维度对意义生产的作用,表明政治学家需要考虑政治实践过程的物质背景,并相应地调整他们的阐释学,通过检查人工物(artifacts)、设备(devices)和技术来理解政治过程。将注意力转向行动者的物质方面,研究的关系或现象至少可以引导我们进行更精确的解释。(51)Leandro Rodriguez Medina,Material Hermeneutics in Political Science——A New Methodology,Lewiston,Queenston und Lampeter:The Edwin Mellen Press,2013,p.9.物质阐释学不是要取代文本阐释学,而是要增强社会科学家解释社会事件的能力并补充阐释学的内涵。迈克尔·芬克(Michael Funk)把物质阐释学方法引入古人类学研究,将焦点集中于古人类学和当前人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上,以此探讨“变更关系”何以可能以及机器人如何调节社会关系等问题。对于无语言文字、文本时代的解释和理解,物质阐释学是一种积极的方式,它通过与进化论、地质结构或医学、动物学等知识进行关联,对人类行为和文化发展做出解释。(52)Michael Funk,“Paleoanthropology and Social Robotics:Old and New Ways in Mediating Alterity Relations,” in Robert Rosenberger,Peter-Paul Verbeek,Don Ihde (eds.),Postphenomenological Methodologies:New Ways in Mediating Techno-Human Relationships,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18,pp.125-149.此时,物质阐释学延续了考古学和后现象学的传统,并试图扩展至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视域中。
随着研究的丰富和扩展,物质阐释学也在尝试新的实践语境。对凯瑟琳·哈斯(Cathrine Hasse)来说,从文化学习过程的角度来看,人文和自然科学中的物质阐释学不仅仅依赖于中介工具,还涉及科学仪器的物质文化环境和科学家在文化实践中的学习过程,这把后现象学的焦点从关系转向了关系的过程。(53)Cathrine Hasse,“Material Hermeneutics as Cultural Learning:From Relations to Processes of Relations ,”AI & SOCIETY,March 18,2021,https:∥doi.org/10.1007/s00146-021-01171-7,July 27,2022.而物质接触理论(Material Engagement Theory)(54)Material Engagement Theory,简称MET,是马拉福利斯(Lambros Malafouris)在2004年提出的理论,并持续发展。“MET”包括“扩展思维(The Extended Mind)”“生成符号(The Enactive Sign)”“物质代理(The Material Agency)”三个维度。 在马拉福利斯与伊德共同撰写的Homo Faber Revisited:Postphenomenology and Material Engagement Theory中结合物质阐释学发展了这种观点。他们基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科学经验,采取了长期和比较的观点,关注的是我们遇到和使用的物质事物(material things),如何塑造生活世界实践中的物质文化,认为物质接触产生于社会和文化的主体间互动,并在互动中持续存在。认为,物质阐释学分析技术如何揭示世界并让人采取行动的同时,也应该强调一种关系存在论的思考,不仅强调思维和行动的关系,而且假定“物质接触”本身是一种基本的认知资源。(55)Kåre Stokholm Poulsgaard,Lambros Malafouris,“Understanding the Hermeneutics of Digital Materiality in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Modelling:A Material Engagement Perspective,” AI & SOCIETY,August 29,2020,https:∥doi.org/10.1007/s00146-020-01044-5,July 27,2022.
维贝克、拉斐尔·卡普洛(Rafael Capurro)、简·凯尔·伯格·奥尔森·弗利斯(Jan Kyrre Berg Olsen Friis)认为物质阐释学是“一种让事物的物质性(materialities)发出声音的技术”(56)Peter-Paul Verbeek,What Things Do: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Agency and Design,University Park,P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5; Rafael Capurro,“Digital Hermeneutics:An Outline,” AI & SOCIETY,Vol.25,No.1,2010,pp.35-42; Jan Kyrre Berg Olsen Friis et al,“Book Symposium on Don Ihde’s Expanding Hermeneutics:Visualism in Science,” Philosophy Technology,Vol.25,No.2,2012,pp.249-270.;正如阿伦·库马尔·特里帕蒂(Arun Kumar Tripathi)所言,物质阐释学研究的是对物质文化和技术进行具体解释的艺术。(57)Arun Kumar Tripathi,“The Significance of Digital Hermeneutics for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Matthew Kelly,Jared Bielby (eds.),Information Cultures in the Digital Age:A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Rafael Capurro,Wiesbaden:Springer VS,2016,pp.143-157.也就是说,“物质阐释学是运用新变化来解释和理解技术的艺术。传统上,阐释学是用来处理圣经文本的,但是,当我们想要解释和理解我们以技术为中介的生活世界时,它显示了传统阐释学的局限性”(58)Arun Kumar Tripathi,“Technological Mediation and Sociocultural Variability,” in Jesper Aagaard,Jan Kyrre Berg Friis,Jessica Sorenson,Oliver Tafdrup,Cathrine Hasse (eds.),Postphenomenological Methodologies:New Ways in Mediating Techno-Human Relationships,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18,p.230.。同时,物质阐释学也发展出另外一些维度,当被应用于解释数字现象时,形成了更具体的“数字阐释学”“机器阐释学”及“软件阐释学”(59)Luca M.Possati,Software as Hermeneutics:A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Study,Cham:Palgrave Macmillan,2022.p.3.。
但是,技科学阐释学并不是一般的“理解的艺术”,它关注的是技术如何通过物质阐释学让事物说话。物质阐释学是在对物质技术和科学文本的关注中逐渐形成的,赋予了事物的物质性一种声音。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伊德认为阐释学意味着解释(interpretation),但在更特殊的意义上,它是指文本解释,从而涉及阅读。他采用了这两种含义,把阐释学作为一种技术情境中的特殊的解释活动,这种活动需要一种特殊的行为和知觉模式,这种模式类似于阅读的过程。(60)[美]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从伊甸园到尘世》,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6页。阐释学从对语言文本的“阅读”转向了对感知模式的“阅读”,即使它现在仍旧属于技术情境,但蕴含了巨大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而且伊德本人也强调“物质阐释学应该同时属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61)Don Ihde,Postphenomenology and Technoscience:The Peking University Lecture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9,p.64.。
三、“一般”物质阐释学:彰显阐释实践的物质性
21世纪以来,物质阐释学在不同学科之间开展对话,它不再囿限于文学阐释学或技科学阐释学,而是逐渐突破特定的、局部类型“文本”的物质维度,向更广泛的物质事物(material things)扩展,渐次发展为一种基于物质性研究的“一般阐释学”。帕尔默所指的“一般阐释学”,试图建立以考察众多学科中解释的模式为基础的普遍“理解”方法,规定一套解释标准,构想出以连贯一致的理解的哲学为基础的一般而普遍的方法论。(62)[美]R.E.帕尔默:《解释学》,孟庆时摘译,《哲学译丛》1985年第3期,第21-29页。其前提预设是阐释学在不同学科中表现为不同的模式,却有一种共同的规则和方法基础。作为一般阐释学的物质阐释学,它将物质性研究视为阐释学的基础,以考察物质阐释学在多学科解释模式上的适用性和普遍性。
(一)从文本到非文本
伊德在“扩展阐释学”的思考阶段虽然较少使用“物质”(material)一词,但随着研究深入,他发现物质可以作为阐释学的基础维度,从而形成物质阐释学并发展为一种“一般阐释学”。物质阐释学不仅解释技术事项,而且切近不同文化及学科背景下的更广泛的阐释学实践。物质阐释学中的“物质”意味着阐释学摆脱了纯文本而进入了非文本的世界。(63)杨庆峰:《翱翔的信天翁:唐·伊德技术现象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1页。伊德2022年出版的新著《物质阐释学:反转语言论转向》(MaterialHermeneutics:ReversingtheLinguisticTurn),就以更多的案例论证了物质阐释学具有的普遍阐释学方法论效应。如被埋藏的金字塔、丝绸之路、城市的海底遗址、“巨石阵”以及其他与考古学相关的事物,经由新技术产生了新的“物质阐释学图像”,对这些图像的“阅读”和“解码”同样是一种物质阐释学的过程,由此获得的知识将丰富甚至可能改变我们对古代史的看法。(64)Don Ihde,Material Hermeneutics:Reversing the Linguistic Tur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22,pp.17-36.我们似乎能通过物质阐释学将自己置身于任何可能的情境中来理解和解释事物。
根据伊德的新著,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伊德把物质阐释学从“局部”转向“一般”阐释学的努力。有关奥兹冰人的研究延续了维贝克意义上的物质阐释学方法论,并粗略划分为业余期、科学对象期和物质阐释学三个研究节点。业余期是一些非科学人员对奥兹冰人进行的研究,时间短且充满了猜测;科学对象期开始将奥兹冰人视为一种科学研究对象,有专业的实验室对其进行研究和保护,这种“封闭”的背景预示着一套比以前更具“解释性”的实践的开始;至物质阐释学阶段,研究者运用更加专业和先进的仪器设备,通过对物质事物及其情境的分析,以及与现代知识的对比,得出了诸多与前两个阶段不同的“事实”。比如根据DNA溯源和同位素等的分析,发现奥兹冰人的出生地(意大利的埃萨克山谷)和发现地(奥地利的奥兹山谷)不是一个地方。(65)Don Ihde,Material Hermeneutics:Reversing the Linguistic Tur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22,pp.17-36.奥兹冰人及其周边的事物被技术转化为可读的“文本”,表明即使没有语言文字,物质阐释学仍旧可以揭示或提供一种叙事情境,“还原”事物的生命轨迹。
物质阐释学关注物质的缺失对意义产生的影响和限制。我们已经发现《圣经》中的创世纪故事与《吉尔伽美什史诗》十分接近,但是这些起源故事无论在形式、意图还是证据上都不是“科学的”。随着技术工具和考古学的发展,物质阐释学成为考察对象是否“科学”的重要方法。《掀开圣经的面纱》一书,将事实(fact)和传说(legend)分开,利用当时考古学最新成果,通过在以色列、埃及、约旦和黎巴嫩发掘的实物证据,证明《圣经》中的故事不全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挑战了原教旨主义者对圣经文本的解读,(66)Israel Finkelstein,Neil Asher Silberman,The Bible Unearthed:Archaeology’s New Vision of Ancient Israel and the Origin of Its Sacred Texts,New York:Touchstone,2002,pp.4-5.也创造了一种与“局部阐释学”研究不同的阐释方式。
伊德的物质阐释学也关注到了历史事件,尤其是与文明衰败相关的重大事件。在维京人入侵英国的系列叙事中,维京人是文盲、海盗,但物质阐释学提供了不同的叙事方式。通过对事物的分析和解释,伊德发现维京人有悠久的航海和造船技术,捕杀特定鱼群自用和交易(鱼的流通暗示了人的流通),维京人间接影响了英国的语言和文化。英国对早期维京人的语言文本表达(linguistic-textual telling)显示了语言优势如何控制早期叙事,而物质阐释学发现了不同的叙事证据,可以“检验”语言叙事并观察它们是如何被修改的。古巴比伦文明的衰落通常被认为是由战争引起的,而对楔形板(Cuneiform Tablet)内部微生物和海藻含量的物质阐释学解读,为古巴比伦文明的衰落提供了新的证据(67)Don Ihde,Material Hermeneutics:Reversing the Linguistic Tur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22,pp.58-59、67-76.——战争只是导致文明衰落的其中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当时古巴比伦的土地正在经历盐碱化,传统的灌溉技术将大量河水引入土地,导致土地无法生产出供养人类的农作物。传统的人文研究更关注楔形板上文字所传达的意义,但物质阐释学聚焦于泥板本身。这补充了一种文化传统或文明衰落的历史知识,也展现出文字和物质阐释之间的矛盾关系。
(二)技艺术阐释实践
物质阐释学可以“重建”阅读,有利于理解受损文本,同时也产生了理解“技艺术”(technoart)的新途径。它可以使那些因为火山喷发等灾害而受到破坏的文本变得“可读”或可理解,也可以通过对绘画艺术品的分析,增强对图像的阐释或解释能力,把对静态作品的关注转向与作品相关的系列动态过程。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和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正处于“现代艺术”的爆炸式发展阶段,当时传统艺术转变为现代艺术,商业运作、画廊体系、拍卖等艺术活动兴起。两位画家都进行了诸多艺术实验,对绘画的颜色和形状做了大量的“现象学变更”。(68)Don Ihde,Material Hermeneutics:Reversing the Linguistic Tur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22,pp.58-59、67-76.物质阐释学通过解释经由高成像技术(high image technologies)“可视化”后的变更(物质形态的变迁),有利于更全面地理解艺术品的风格变化和实践过程。物质阐释学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艺术品的伟大之处,提供对文物、实物、文字或绘画的更多层次的理解,产生了一种更精确、更深入的知识。
物质阐释学由科学实践领域出发,逐渐包容了艺术实践领域。艺术和“技艺术”之间关系紧密,很多艺术都是技术化的艺术。现代考古学或自然科学家使用现代技术把实物变成了“阐释学的”,结合现代知识可以理解久远的物质工具是如何工作的,物质材料(比如颜料、画材、物质载体甚至是否搭建脚手架等)、技法和历史何以影响了艺术实践。此外,那些拍摄的图像或图片为艺术史的叙事提供了一种场景。伊德通过技术和艺术在旧石器、文艺复兴以及当代艺术实践的关系变化考察了艺术实践,发现每一个阶段都涉及了与视觉或听觉相关的物质阐释学的诸多方面。早期艺术具有逻辑传统和图像传统,实证主义和阐释学在法国的诺克斯洞穴壁画上实现了一种“古老”的结合。另外,大型机器技术已经改变了文艺复兴前的世界,丝绸之路、哥伦布航行等使世界变得更加开放,生活世界发生了变化,物质交易丰富了艺术的物质材料和物质工具,产生了大量的视觉艺术和音乐。现代技术传播速度的加快和“保质期”的缩短,引发了对当代数字技艺术的物质形式和对其感知的较大变化,产生了新的艺术实践,激发了相应的流行品味。
伊德不仅将阐释学关注的文本扩展到了技术文本,而且把技科学的讨论方式以一种修辞学的类比扩展至艺术,认为艺术是一种“技艺术”。正如物质阐释学在技科学中的作用一样,在“技艺术”中同样发挥功能。具体来说,若文艺复兴相关的视觉风格是一种“现实主义”,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暗箱等技术。暗箱将自然对象(natural object)转化为图像(image),让人们可以对之进行“阅读”和“解释”,又把图像从物(object)中分离出来,从而建立了一个新的知识与观看的组织方式或强制性的认知场域。(69)Jonathan Crary,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ondon & England:The MIT Press,1992,pp.36-37.对外界的认识和感知不是透过直接的感官体验,而是通过工具重新审视外界。技术工具改变了现象呈现的方式,现代科学中的自然不是原始的或赤裸裸的,而是经过技术改造的(technologically transformed)。(70)Don Ihde,“Art Precedes Science:or Did the Camera Obscura Invent Modern Science? ” in Helmar Schramm,Ludger Schwarte,Jan Lazardzig (eds.),Instruments in Art and Science:On the Architectonics of Cultural Boundaries in the 17th Century,Berlin:Walter de Gruyter,2008,pp.383-393.暗箱绘画实践是一种图像-解释实践(image-interpretive practice),那些经过暗箱投射出来的图像,成为艺术家创作的对象,并决定了相应的绘画风格和体制建构。
不仅如此,物质阐释学也倒置了音乐、科学乐器、合成器和数字乐器的传统阐释方式。艺术依靠科学技术,技术也可能依赖艺术。伽利略的技术和许多早期光学绘画设备被用于艺术,现代的合成器和数字乐器之类的物质材料也被用于艺术,这是一种从科学向艺术的巨大转变。伽利略时代的艺术促进了早期现代科学的发生和发展,而现代艺术促成了合成器和数字乐器自身的更迭,乐器从最先的模拟乐器发展为数字合成器。这又是一种艺术向科学的转变。艺术实践本质上需要物质阐释学进行更加全面的解释。
(三)阐释实践的物质性
经由这些不同学科的案例分析,伊德重申了科学转向阐释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转向阐释学的现实情况,突出了物质阐释学融合二元论的努力;另外,他也没有放弃技科学或后现象学视域,而是表明有“一般阐释学”倾向的物质阐释学对“生活世界”概念的反转,并在阐释冰河世纪科学与农历(科学和技术、科学和知识)形成关系时重新逻辑化了知识起源问题。最后回到了阐释学发展历程,考察利科从语言向物质阐释学的转变。似乎所有的实践形式中都有物质阐释学的影子。物质阐释学认为自然科学有进行解释和阐释的必要,同时扩展了人文科学(尤其是考古学和人类学)的阐释视野。大量的案例表明,艺术实践、古代历史、音乐甚至后殖民冲突等都可以采用物质阐释学得到更“科学”的理解,那些被广泛运用于人类迁移、地球变化和遗传学等现象研究的成像技术也可能改变人们对人类历史的认识。
虽然伊德在从语言转向技术的过程中,缺少连贯性的分析,有将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混淆的嫌疑,但这并不影响阐释学对物质性研究的关注和强调。20世纪60年代以来“应运而生的‘过程论’‘事件论’‘混沌论’‘物质文化论’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等新型物质观念,凸显出物作为文化、过程、事件和关系网络的属性特征,展现出物的生动性、延展性、生产性和能动性,促生出一种生态范式的物性观念,重构了人与物、物与物、物与非物、人性与物性之间的关系图景”(71)张进:《物性诗学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5页。,物质本身的能动性进一步促进了物质阐释学研究对象的扩展,经由对各种事物的阐发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阐释学概念。
施莱尔马赫的“一般阐释学”较之语文学阐释学更系统和理论化,但是他将原文意义看作是一种客观存在。相比而言,作为“一般阐释学”的物质阐释学不只是基于语言和文字,而且基于物质和物质性,主张阐释学与实证主义的结合研究,并将其运用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相比于其他的阐释方式,从事物质阐释学研究需要更大的“成本”,而且物质性连接(技术中介)或技术只是阐释学关系中基础形式的一种,所以物质阐释学也并不是唯一的阐释方案。比如依据考古学照片,可以从形状上辨别出某个实物,但是其原始环境及地理位置等信息被隐藏了;望远镜“看”到的月亮,也可能隐藏了月亮的颜色和其所处的宇宙环境;红外线照片增强了植被和非植被的差异,超出了同构彩色照片的限度,但同时也隐藏了一些外部表象。也就是说感知是可以被中介调节的,而物质“原文”和中介的形态、属性、可供性,以及对物质的占有等都可能预设或修改“文本”和所指关系,所以物质阐释学不仅需要知道“阅读”何以可能,还需嵌入一种批判的视角。
四、阐释学的多模态协同
物质阐释学给了(gives)事物一种“声音”,让事物说话。(72)Don Ihde,Material Hermeneutics:Reversing the Linguistic Tur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22,p.34.如果说传统的“一般阐释学”标志着非单一学科性(non-disciplinary)阐释学的萌芽,那么物质阐释学则标志着非单一学科性阐释学的“重置”,也就是将阐释学重新奠基于物质性之上。物质阐释学为唯物论阐释学创造了条件。它在某种程度上反转了语言转向,使阐释学的参照范式从“语言文本模态”转向“具身感知模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但是,物质阐释学并不能代替“文本阐释学”“哲学阐释学”等;而且,在物质阐释学中,诸多物质性维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协同运作问题,以及“具身感知模态”与“语言文本模态”之间的多模态性协同问题依然悬而未决。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多模态现象纷纷涌现并深度融合,(73)Gunther Kress,Multimodality: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p.1.我们需要超越语言文本或物质事物的单一模态,追求一种多模态性协同的阐释模式,以增强阐释学对当下文艺文化现实的阐释效力。
——意象阐释学的观念与方法》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