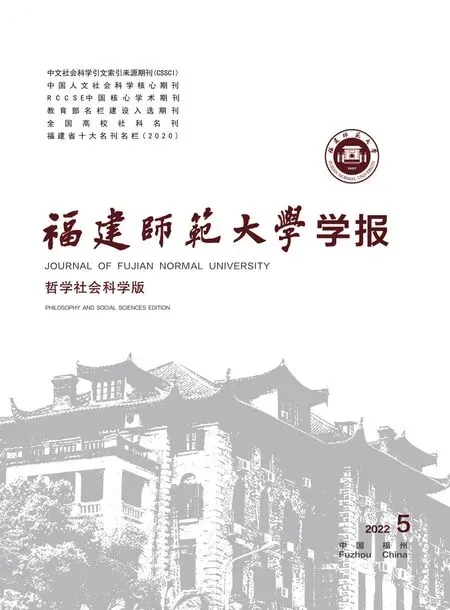电子包浆:时间性痕迹或尺度式差异
章戈浩,章倩砺
(1.澳门科技大学 人文艺术学院,澳门 999078;2.湖北大学 艺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一、电子包浆、油炸迷因与数字包浆
多年以后,当学者们试图对“电子包浆”进行媒介考古或是观念史考察时,或许会发现,它的源头竟也是一个充满“包浆”的递归。
按照中文互联网上最流行的说法,电子包浆一词诞生于2018年7月10日。在中文互联网上最大的ACG论坛之一Stage1上有人提问:“为什么网上流行质量很差的表情图?就是黑白熊猫之类,中间P个表情,故意把图像质量做得很差。有什么意义吗?特别流行。”对此有人回复:“压缩带来的自然绿斑就跟古董包浆一样,是这表情包经典的证明。相比之下洁白无瑕的熊猫人就像昨天才从PS里出来的一样,毫无底蕴,不值一提。”(1)说明:这是一段都市传说,佐证这一说法的图片,原始来源可疑,也难以考证真实的网址。在理论家眼中,这组看似无厘头的对话无疑是一次亚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拼贴操演,将当下中国的大众审美现象作为一种隐喻杂糅进抖机灵的网络段子,反倒具备了一丝赛博朋克的味道。
更反讽是,这段叙事的唯一证据是一张明显经过压缩且图像质量并不高的截图,早已无法找到原始出处,甚至根本无从知晓是否真有这么一段原始文本。或者说,对于电子包浆初始文本的追踪最终所收获的只有一张流布于网络的充满电子包浆的图片,而这张图片在诸多讨论电子包浆的网络文本、新闻报道中一次次地被引用、印刷,又从印刷品再次被数字化传到网络进行转发,从而又一次次加上电子包浆,成为一则都市传说,伴随着其他饱含电子包浆的低画质表情包一道流传。
正式出版物对于电子包浆的标准定义,通常都会不厌其烦地从文玩收藏行业的专业术语“包浆”开篇:“文物表面由于长时间氧化形成氧化层,这个氧化层会发出自然的光泽,年代越久,包浆越厚。”(2)宋宇涵:《网络新词语:电子包浆》,《今晚报》,2021年2月11日第7版。电子包浆借用“包浆”一语,“指图片时间久远、网络图片的扩散往往经过网友们的多次转存发送。有些手机系统或网站的压缩算法会导致图片变模糊,转存次数越多,图片越模糊,还有可能出现水印叠水印的现象,图片就更加模糊不清了。于是越是传播广、时间久的图片,画质往往就越差,所谓的‘电子包浆’就越厚”(3)宋宇涵:《网络新词语:电子包浆》,《今晚报》,2021年2月11日第7版。。百度百科则将电子包浆的解释导向另一条网络流行语的词条:“图都绿了”,有意无意地暗示其源自百度贴吧,尽管这其实只是一场技术误会。
电子包浆并非中国独有的亚文化现象,英语世界也存在着所谓“油炸迷因”(deep fried meme)的类似情况。“油炸迷因”一词由网名memegod420 的用户于2016年11月21日在网络辞典《都市辞典》(UrbanDictionary)上创建(4)2016年11月21日,https:∥www.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deep%20fried%20meme,2022年9月3日。,最初是指一张高质量的网络迷因被截图、转发和重新过滤了很多次,致使它分辨率下降、图片发黄、质量不高,看起来像被油炸过一样。最早的一张油炸迷因出现于2015年3月24日。(5)2016年11月21日,https:∥www.urbandictionary.com/define.php?term=deep%20fried%20meme,2022年9月3日。
迷因(也译作模因)由英国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Clinton Richard Dawkins)于1976年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首次提出,借用生物学中的基因及其进化规则来比拟文化信息传播的方式。互联网时代,又出现了所谓的网络迷因,指那些一夕间在网络上不胫而走的事物。(6)Patrick Davison,“The Language of Internet Memes,”The Social Media Reader,Ed.M.Mandiberg,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2,pp.120-34.有学者认为,在线上/线下被分享、转贴、评论的网络迷因代表了一种新的在线传播类型,理解它们的生产、传播和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有助于提高数字文化的驾驭能力。图像、GIF动图或视频在重新融合后,进入大众文化互文之中。网络迷因代表了一种新的意义创造形式,它们的迅捷产生与传播正凸显出它们的重要性。(7)Bradley E.Wiggin,The Discursive Power of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Ideology,Semiotics,and Intertextuality,New York:Routledge,2019.值得说明的是,油炸迷因与电子包浆两个概念虽然相去不远,但在不同时空背景下,两种命名侧重点不尽相同。对于电子包浆的讨论很难像油炸迷因那样简单地放在网络迷因的框架之中,因此笔者将集中分析电子包浆,而不过多涉及油炸迷因。
无论是中国的电子包浆,还是英语世界的油炸迷因,其实都是基于计算机图形的图形物(Image object)。值得注意的是,“计算机图形所再现的不是世界,而是另一种模拟的媒介……作为屏幕上的图像……计算机图形远不止是我们看到的图像。它们是我们历史上的主要技术之一,并且重塑了我们今天理解、联系和参与物质世界的方式”(8)Jacob Gaboury,Image Objects:An Archaeology of Computer Graphics,MIT Press,2021,p.6.。本质上,图形物属于技术哲学家许煜所定义的数码物,即“成形于屏幕上或隐藏于电脑程序后端的物体,它们由受结构或方案管理的数据与元数据组成”(9)Yuk Hui,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6,p.41.。
英语学术界在研究数码物时还曾使用过一个与电子包浆颇为类似的词:数字包浆(digital patina)。早在20世纪90年代,曾有技术史学者使用这一术语,讨论不同历史模式再现的早期计算机项目(10)Jon Agar,“Digital Patina:Texts,Spirit and the First Computer,”History and Technology,Vol.15,No.1-2,1998,pp.121-35.。1998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篇硕士论文中也使用了这一概念,来探讨以实验方法追踪数码物的可能性及其影响(11)Ansel Arjan Schatte,“Patina:Layering a History-of-Use on Digital Objects,”Master Degree Dissertation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98.。此后数十年间,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把自己当作这一术语的首创者来讨论数字时代诸多截然不同的现象。有人从物质文化视角出发来比较实体物(solid object)包浆与数码物的数字包浆在时间、记忆关联上的异同(12)Johanne Pelletier,“Matter of Time:Digital Patina and Timeboundedness in New Media,”Master Degree Dissertation at the McGill University,2005.;有人探究胶片电影的数码修复过程中胶片包浆的数字再现对于电影研究的意义(13)Ivan Capeller,“The Patina of the Film:From Time’s Cinematic Reproduction to History’s Cinematographic Representation,”Revista MATRIZes,Vol.3,No.1,2009,pp.1-15.;有学者讨论作为遗产的数字物件(digital artifacts)的生命周期及其价值(14)Rebecca Gulotta,William Odom,Jodi Forlizzi,Haakon Faste,“Digital Artifacts as Legacy:Exploring the Lifespan and Value of Digital Data,”CHI 2013:Changing Perspectives,Paris,France,2013.;有学者研究数字收藏中数字包浆的物质化如何拓展了数字物质性的概念(15)Rebecca Mardon,Belk Russell,“Materializing Digital Collecting:An Extended View of Digital Materiality,”Marketing Theory,Vol.18,No.4,2018,pp.543-70.。数字包浆与电子包浆名称相似,所讨论的对象及使用的理论却不尽相同,为避免混淆,笔者此处只讨论中国本土定义的电子包浆,而不再详究数字包浆。
无论是电子包浆还是数字包浆,这种命名本身就戳穿了一个关于数码物的自相矛盾的神话:技术是会过时的,而数码物是永恒不灭的比特。其实,电子包浆并非时间留下的痕迹,而是所谓尺度理论(scale theory)意义上数码物差异的物质性体现。
二、算法磨损、算法污渍与数字绿锈
(一)线性想象的时间留痕
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数码物,无论是一张图片、一个网页、一段代码,还是一个软件程序、一个手机应用app,它们不像渲染在宣纸上的水墨或是涂抹在画布上的油彩,会因岁月的磨洗而泛黄或褪色。要么永恒存在,即使周遭世界天翻地覆,它们始终锁定在一个恒定状态;或者,它们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形态,反倒不断更新迭代,根本谈不上老化。对此,来自计算机科学的常识提供了解释,即它们是基于比特的信息,而非基于原子的物质。早期互联网文化讨论中曾经流行过的“比特不灭”的技术神话不断强化了这种刻板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在那本风靡一时的数字时代预言《数字化生存》中,刻意进行的“原子”与“比特”二元对比。基于原子的实体物可能会实时损耗直至湮灭,而以比特为单位进行信息存储的数码物似乎是永恒存在的。换句话说,自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广泛渗透进人类生活后,人类仿佛进入了一个非物质文化时代,在比特与原子的二元对立想象之中,非物质信息替代物质实体的倾向似乎也日趋明显。然而,近年来包括媒体与传播研究在内的诸多学术领域中,对数字技术非物质性的过度凸显频遭质疑。尽管信息看起来是非物质的,但是它不可能脱离物质形式而存在,比特也难以逃离物理设备的物质限制。不少学者呼吁互联网乃至数字媒介研究的“物质性转向”(16)John Hondros,“The Internet and the Material Turn,”Westminster Papers i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Vol.10,No.1,2015,p.3.Ramón Reichert,Annika Richterich,“Digital Materialism,”Digital Culture and Society,Vol.1,No.1,2015,pp.5-17.章戈浩、张磊:《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第103-115页。。平台、程序、算法是可编程的物(programmed object),电子文本也是实体物件(material artifact)(17)Tanja Carstensen,“The Internet as Material Object in Social Practices:Recording and Analysis of Human-Internet Interactions,”Nature and Culture,Vol.10,No.3,2015,pp.284-302.。在这个意义上,计算机图形其实是数码物的某种子属,电子包浆也正是某种物质性的彰显。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讨论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时指出:“艺术品的存在过程就受制于历史。这里面不仅包含了由于时间演替使艺术品在其物理构造方面发生的变化……变化的痕迹只能由化学或物理方式的分析去发掘……”(18)Walter Benjamin,“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Second Version),”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and Other Writings on Media,Ed.M.W.Jennings,B.Doherty and T.Y.Levin,Cambridge,MA,London: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9-55.无论是否艺术品,实体物都可借由化学或物理方式分析来发现时间演替所带来的变化痕迹。这种痕迹就是所谓的“包浆”,它既有可能源自物理上的磕碰磨损,也有可能表现为化学反应生成的氧化层。所谓的“电子包浆”,即借用这一物质隐喻、挪移了这套符号指称背后的意义,把低下的像素与分辨率、层层叠叠的水印等视为时间性痕迹,电子包浆的流行也就被解读为审美品位上的怀旧。这种判断的背后,隐含了对计算机技术线性发展的想象,将电子包浆视作经年历久的时间性印记正是从这种想象中衍生出来的。其实,电子包浆的时间性留痕与技术的线性发展一样都要打上问号。
从线性技术发展观出发,数字时代往往被描述为一个不断加速、更新的时代。昨日风头正劲的时尚潮物一夜之间就成了今天的破烂和明天的垃圾。譬如雄踞人类文明史长达千年的最主要的物质媒介书籍,就被认为早已站在悬崖边缘,只剩被它的数字继承者最后轻轻一推。计算机磁盘诞生仅仅数年之后便被可擦写光盘所取代,现在装有光盘驱动器则是一台计算机成为古董的证据。相较于硬件,软件的更新与过时更为频繁。对于用户来说,甚至无须费心查验软件的版本编号,电脑上不时弹出的各种更新提醒弹窗仿佛预先埋下的定时炸弹,到点依次爆炸。数字媒介的各个方面都在加速更新:像素越来越大,分辨率越来越高,动态范围越来越丰富,带宽越来越宽,网速越来越快……这时,对于小像素、低分辨率这类“过时”特征的欣赏与保存成了数字时代独有的复古与怀旧。当然,这种怀旧本身也具有独特的媒介性。(19)Dominik Schrey,“Analogue Nostalgia and the Aesthetics of Digital Remediation,”Media and Nostalgia,Ed.Niemeyer,K.,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4.古老版本的软件只能运行在比它更为古老的操作系统之上,并由至少与它们同样古老的硬件所支撑。
这种让我们习以为常的线性技术发展观早已受到反思与批评。从媒介考古学视角来看,曾经失败的媒介技术或许恰恰昭示了新的可能性,一度过时的媒介技术或许会在变形后重新出现。小像素、低分辨率并不一定意味着时间上的久远与技术上的落后。或者说,这种怀旧审美、对貌似过时技术的欣赏,本身就是对技术线性发展的无情嘲讽。
(二)算法磨损、算法污渍及其物质性
电子包浆的出现与盛行,不是一个简单的怀旧审美问题,正如电子包浆本身并非时间的留痕,其最初来源很可能是所谓的算法磨损,当然磨损同样是一个并不准确的物质隐喻。为了减少图片体积、加快处理速度,有些技术平台会压缩上传的图片,且通常会进行有损压缩,而不同的平台又采用了互不通约的压缩算法。图形物在不同平台的上传、下载、传输过程中不断地被压缩和改变,一开始可能是肉眼不可见的变化,但在多次处理后某些变化会呈几何级数增长,图片的像素变得更小、分辨率变得更低,最终出现明显的视觉性变化。比如在图片分享网站Instgram上传图片时,后台便会锐化图片,这是西方世界油炸迷因产生的原因之一。如果说,实体物的物理包浆部分源于物体表面的磨损磕碰,那么,通过所谓离散余弦变换的有损压缩算法磨损,则是电子包浆的主要成因。
图片不仅会磨损,还会“增殖”。实体物的化学包浆大多来源于附着的污斑、尘埃、油渍,氧化后成为物体表面的薄膜,电子包浆同样不仅意味着消减,也可能意味着数码物被添加了原来不曾包含的内容。有些网站会对上传的图片增加新的信息,最典型的是强制性地在图片上加上肉眼可见的水印,如网站名称标识或者使用者的名称。当一张图片在不同网站间流传时,水印不断叠加,有时来自人为的添加,更多时候则是不同平台的自动算法行为。
无论是算法磨损还是算法污渍,都无须在时间的容器中打熬,而是可以使用软件在几秒钟内模仿出来,并不像实体物的物理或是化学包浆必须经久历时。这恰恰体现出电子包浆作为数码物的物质性特征。在讨论数字物质性时,有学者提出了构成数字物质性的一组对应概念:鉴识物质性(forensic materiality)与形式物质性(form materiality)。鉴识物质性是指“生产、流通、接受与保存过程中的物理证据。无论是通过肉眼还是通过仪器设备,均可对痕迹、印记、遗存、刻印以不同方式辨识与分析”(20)Matthew G.Kirschenbaum,Erika L. Farr,Kari M. Kraus,etc.“Digital Materiality:Preserving Access to Computers as Complete Environments,”Proceedings of the iPRES 2009:the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eservation of Digital Objects,2009,pp.105-112.。形式物质性是指“数字媒介及其象征形式的架构,无论是单个软件程序的结构,嵌入的数据标准或是操作系统的架构”(21)Matthew G.Kirschenbaum,Erika L. Farr,Kari M. Kraus,etc.“Digital Materiality:Preserving Access to Computers as Complete Environments,”Proceedings of the iPRES 2009:the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eservation of Digital Objects,2009,pp.105-112.。电子包浆在特定图片中同时体现出了这两种物质性特征。一方面,无论是算法磨损还是算法污渍,它的确产生于数码物的流通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对数码物加以辨识与分析的类似“物理”特征的证据。另一方面,它又具备了形式物质性的特点,磨损与污渍都来自于算法,来自于软件程序中的计算过程,也正是由于不同平台、不同软件的不同算法,才会在不同的图形物上分别或同时出现不同类型、不同方式的算法磨损与污渍。
(三)“数字绿锈”的分布物质性
本雅明提到,在一个前机械复制的时代,对一件铜器上的绿锈做化学分析,可能有助于确定其本真性。非常有趣的巧合是,在中文世界流传的电子包浆的特点之一便是图片往往会呈现出绿色,绿色的深浅甚至会让人联想到包浆的成色。这并非来自于特定的美学口味,比如对于绿色铜锈的刻意模仿。它也无法简单地用算法磨损或算法污渍加以解释。
如同算法磨损,数字绿锈同样源于图形处理速度的优化。通常来说,标准的 JPEG 图片格式在做色彩空间转换的时候,会使用至少16比特的精度。然而,安卓操作系统提供的压缩图片接口为了执行速度,有意降低到8比特的精度,并使用名为Skia的图像库来处理图像。JPEG 算法本身为了达到更好的压缩效果,会将屏幕上表示颜色的RGB(红、绿、蓝)数值,转换为YUV(亮度、蓝色分量、红色分量)数值。这种转换本来就轻微有损,Skia库在进行变换运算时,又在代码中采用了小数部分向下取整的右移操作来代替除法以提高执行速度。这样一来,Y值的变化会使得图片随之变暗,而U值与V值的变化又会使图片变绿。图片随着 Skia 的色彩空间变换算法反复压缩,自然越变越“绿”。这一问题在2016年8月推出的安卓系统7.0版本中得以修复。然而,出于技术成本等诸多原因的考虑,仅仅部分面向高端市场的安卓手机及时升级了系统,相当数量的面对中低端市场的国产手机在数年之后仍然继续使用较早版本的安卓系统,使得这一问题一直延续下来,直到电子包浆的大流行。换言之,“图都绿了”这类电子包浆亚文化的称谓或许源自百度贴吧,但电子包浆中的绿锈效果并非百度网站的算法压缩等技术因素所导致,而是源自安卓系统本身的未能修复。使用非安卓系统的手机进行上传、下载的图片则不会产生这种数字绿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可以视为一种算法磨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仅出现在特定时期、特定平台的设备上,从而使得技术问题成了一个符号政治经济学问题。甚至可以不无刻薄地认为,电子包浆中的数字绿锈是一种所谓“穷人”手机的特有效果。小像素、低分辨率的能指共同指向技术过时的所指,而这些能指却产生于价格相对低廉的硬件设备。象性意义与物质条件在这一刻居然严丝合缝地弥合在一起。
曾有学者提出了分布式物质性(distributed materiality)的概念,即有些数字信息表面看起来是非物质性的,但是它无法独立于存储设备、电源等物质性限制而存在。数字信息系统由应用程序、软件架构、基础设施硬件层叠而成,其中应用程序又往往以桌面、文字处理等隐喻性的任务模型而存在。因此,分布物质性可以描述驱动、存储、软件、硬件、系统等共同依存与相互叠加的可能性。单独来看,它们可被视作物质,更重要的是,它们被锁定在相互间的关系之中,由这种物质设计与限制所主导,并对整个系统的成本与效率产生影响。(22)Jean-François Blanchette,“A Material History of Bit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62,No.6,2011,pp.1042-1057.从这种视角出发,电子包浆中的数字绿锈格外典型地体现出了图形物的分布物质性。它并非由单一因素所决定,而与特定的压缩算法相关,这种算法又与特定版本的安卓操作系统相关,安卓系统又与特定的手机硬件架构有关。以上所有技术性因素又被嵌套进更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框架之中。无论是数字绿锈的外在表征,还是其技术性因素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均为其叠加了特定的象征意义。
(四)屏幕本质主义的错觉
然而,对于电子包浆的理解并不能止步于此。当人们理解数码物,往往会犯下所谓屏幕本质主义(screen essentialism)的错误。这个概念由尼克·芒福德(Nick Montfort)所创造,并由马修·克斯契鲍姆(Matthew Kirschenbaum)进一步拓展,用以指称对数码物进行研究时的一个常见偏见:人们往往误把数码物在屏幕上的呈现当作数码物本身,而忘记了数码物是存储在不同载体之上、可以用不同程序读取、读取后会产生不同效果的代码。换句话说,数码物并不只是它们以特定的软件、特定的配置呈现出来时的样子。它们的核心是代码,虽然这些代码信息需要用特定的软件来读取或呈现,但有时忽略其缺省的开启方式反而可以从不同视角来了解对象中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文件的扩展名,用不同的软件来打开某个文件。(23)Matthew G.Kirschenbaum,Mechanisms,New Media and the Forensic Imagination,The MIT Press,2008,pp.31-35、31.比如,一段MP3音乐用音乐播放器打开听起来是一段音乐,一张计算机图形用图形浏览器开启看起来是一张图片,但如果更改了缺省的文件扩展名,使用文档编辑器来打开这个文件,看到的会是成行成列无法读解的代码。“理解数码物的完整性的价值,而不仅仅是在一个特定的读出的屏幕上‘看起来是正确的’。在许多情况下,对象的完整性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软件来表达的。”(24)Matthew G.Kirschenbaum,Mechanisms,New Media and the Forensic Imagination,The MIT Press,2008,pp.31-35、31.
正是基于屏幕本质主义,人们往往会忽略掉屏幕上无法显示出来的差异,同时又会过分夸大那些或许只是由于屏幕显示所导致的不同。两张在屏幕上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图片,可能是以不同格式存储的截然不同的二进制信息,也可能是其中一张图片经由格式转换软件生成了另一张图片,两者虽有关联,却非同样的数码物。同一个网页,采用完全相同的超文本语言编写,在不同的网页浏览器上却可能显示为完全不同的布局。当我们明晰了屏幕本质主义的原理,方能明了为什么从早期的网络文化研究者以降,人们就误以为基于比特的数码物如同吃下了唐僧肉的妖怪般长生不老。那些在屏幕上看起来经久不变的数码物,很可能早已通过不同的方式脱胎换骨,比如被置入肉眼不可见或者至少在屏幕上无法显现的数字指纹、数字签名、数字水印。下载网络图片却使电脑受到病毒荼毒的用户往往忽略的一个技术操作便是用MD5校验文件完整性。如果我们能打破屏幕本质主义的迷雾来看待数码物,任何数码物在流传过程中都有可能产生可见或不可见的痕迹,无论是在网络上被上传、下载,还是在存储器中被复制粘贴,有时视频中会内嵌进广告,有时文本中会产生乱码,有时页面里隐藏着链接,当然也有可能代码本身并无变化,但人们仍能追踪到鉴识物质性的差异,发现形式物质性的不同,以及明显受到分布物质性的牵制。那些可被肉眼识别的差别,或许就是电子包浆。当电子包浆被戏谑使用时,人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这背后涉及一个事关数码物存在论的哲学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一个数码物在经历上传、下载、复制、粘贴等操作之后,就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其本身了。
三、包浆:尺度意义上的差异
(一)机械复制、数字克隆与尺度差异
在面对数码物之前,物与物之间是否存在相同性这一难题就早已存在。尽管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认为在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认定世界上本来没有相同的东西,本雅明却认为这个复杂的哲学问题被技术复制所解决。“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人们可以用一张照相底片复制大量的相片,而要鉴别其中哪张是‘真品’则是毫无意义的。”(25)Walter Benjamin,“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Second Version),”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and Other Writings on Media,Ed.M.W.Jennings,B.Doherty and T.Y.Levin,Cambridge,MA,London: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9-55.本雅明高估了他那个时代的技术复制。实际上同一张底片复制的相片,虽然无法鉴别出真品或母本,但每个个体之间却并非百分之百的相同。在冲洗之时,药水浓度、房间温度、底片品牌、胶卷存放的时间,都可能使得照片间存在着或细微或显著的差异。在数字时代,机械复制升级成了数字克隆,数字克隆的精准度远胜于机械复制。当数学家发现人们可能永远无法精准测量海岸线从而发明分形数学后,“相同性”的问题可以部分得到解释:无论是机械复制还是数字克隆,复制品与母本,或者复制品与复制品之间,其差异与相同,其实只是一个尺度问题。
美国学者约书亚·迪卡里奥(Joshua DiCaglio)受到后人类主义思潮的影响,试图建立一个跨学科的尺度理论(scale theory)。在他看来,对物体的划分本质上是一个尺度问题,一旦改变了感知的尺度,任何物体都会显得不同。在一个尺度框架中,物体不再是明显的、独立的、自成一体的实体“本身”,尺度的变化可以揭示出同一事物的不同存在方式。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光学媒介带来的尺度变化。由于显微镜的发明,人类得以认知到以前从未知晓的微生物、细菌、病毒等等;由于望远镜的使用,人们得以发现以前由于肉眼无法识别而湮没在无尽苍穹中的星体。所有物体都必须通过可以感知并与之互动的尺度来定义。尺度改变了一切,因为它可以改变事物的意义。尺度也重塑了我们对过程、关系和组织的概念。“尺度不仅呈现了新的对象,而且在两种意义上呈现了新的关系的纠结:首先,尺度揭示了以前不明显的关系,仅仅是因为它们曾无法辨别;反过来,尺度为理解这些聚合体和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26)Joshua DiCaglio,Scale Theory:A Nondisciplinary Inquir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21,p.5、26.无论是机械复制还是数字克隆,无论是两个实体物之间还是两个数码物之间,差异存在与否取决于观察的尺度,尤其是当人们具备了超越人体自身感知能力的各种观测手段之后就更是如此。
在尺度理论中,物被定义为“那些在特定的观察范围内能够产生差异的差异”(27)Joshua DiCaglio,Scale Theory:A Nondisciplinary Inquir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21,p.5、26.。某种程度上,差异取决于观察的水平,即尺度。“尺度产生了观察同一‘物’的多种方式,这样它就会根据观察的尺度而显示为不同的对象。”“在一个尺度上出现的差异,与在另一个尺度上的差异也是不同的。差异和物体都取决于观察的尺度。”(28)Joshua DiCaglio,Scale Theory:A Nondisciplinary Inquir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21,p.26.从这个视角从发,两个物之间的差异是永恒存在的,只在于人们能否使用特定的尺度去观测并发现这种差异。对于数字克隆出来的数码物来说,它们之间永远存在的某种体现着它们差异的“电子包浆”,只在于它能否在特有的尺度上显示出来。反过来说,所谓的电子包浆,只不过作为数码物的图形物在特有尺度下可以被识别出的差异而存在。
(二)再生数码物的灵韵迁移
在讨论数码物时还有一个更常见的误区:人们往往忽略了数码物的多元来源。实际上,数码物既可能是直接产生于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代码,即原生数码物;也可能是由物质世界的实体物被数字化而成的再生数码物。大多数对数码物的讨论只关注了前者,或者把前者的特点不恰当地扩大到所有数码物上。在尺度理论的视野下来看,对于数码物的讨论所采用的尺度是局限于赛博空间,还是拉大到更广阔的视野,从而同时涵盖具体物质世界与赛博空间,所得到的答案自然会不一样。在有的学者看来,相当一部分数码物其实是对所谓具体物质世界的数字抽象(29)Brian Chantwell Smith,Digital Abstraction and Concrete Reality,Impression.Madrid,2003.。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发现,将一个物质世界的实体物进行数字化的同时,其实也存在着本雅明意义上的灵韵迁移。将一个实体物数字化成为数码物,是一个类似于本雅明所说的技术复制的过程。“一个糟糕的复制会使原件有消失的风险,而一个良好的复制的原件可能会增强其本真性并继续引发新的复制。”(30)Bruno Latour,Adam Lowe,“The Migration of the Aura,or How to Explore the Original through Its Facisimiles,”Switching Codes:Thinking Through Digital Tehcnology in the Humanities and the Arts,Eds.Bartscherer,Thomas and Roderick Coov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pp.275-298.“在原件和复制品之间的常识性区别背后,隐藏着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它与技术设备、谨慎程度以及从一个版本到另一个版本对本真性的探索力度有关。”(31)Bruno Latour,Adam Lowe,“The Migration of the Aura,or How to Explore the Original through Its Facisimiles,”Switching Codes:Thinking Through Digital Tehcnology in the Humanities and the Arts,Eds.Bartscherer,Thomas and Roderick Coov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pp.275-298.拉图尔在意的是,当数字世界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图景之时,物质世界的实体物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面临着数字化的命运:“如果接受复制的必要性,那么我们也许能够说服读者,有趣的问题不是如何区分原作和复制品,而是如何区分好的复制品和坏的复制品。”(32)Bruno Latour,Adam Lowe,“The Migration of the Aura,or How to Explore the Original through Its Facisimiles,”Switching Codes:Thinking Through Digital Tehcnology in the Humanities and the Arts,Eds.Bartscherer,Thomas and Roderick Coov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pp.275-298.
当下,实体物在数字化过程中已经产生了种种问题。当大量的文字典籍被扫描之时,实际上就必须进行所谓的存真性校勘。文本上的污渍、破损,甚至是操作员的身体阴影与动作轨迹,都有可能被数字设备采撷下来,并被当作文本本身的内容纳入数码物。实体物自带的物理与化学包浆在数字化过程中成为再生数码物的内容。数字化设备的技术精度带来尺度的转换,肉眼无法发现和记录的尘埃,在数字化后成为再生数码物内容的一部分。红外清理技术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由于引入了红外线技术,又带来了新的可测量与可记录的尺度。目前人们主要使用扫描、传感器化、数据化等方式来对实体物进行数字化,它们颇像科幻小说《三体》里的二相箔,将一个三维物质世界通过降维的方式收纳到数字世界之中。正如在尺度理论看来,两个数码物之间不可能完全相同,只是存在着尺度意义上的差异,当实体物被渐次数字化,人们只能使用数码物来认知既往的实体物,甚至于实体物最终消逝于时间长河之中,仅剩下一个个数码复制品。到那时,实体物被数字化时所采用的尺度,或许将永久地影响乃至改变人类对既往事物的认知与记忆。甚或,何种实体包浆与电子包浆都将产生灵韵迁移,都会影响与改变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与认知。
四、结语
作为网络亚文化的一部分,电子包浆风行一时,表面看似是怀旧审美的一时风潮,实则电子包浆本身并无时间性的痕迹,算法磨损与算法污渍彰显出了作为数码物的图形物的鉴证物质性与形式物质性,数字绿锈则体现出图形物的分布物质性特征。电子包浆所体现出的数码物之间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只是屏幕本质主义带来的错觉。复制、粘贴之后,数码物之间的同异本质上只是一个尺度问题,而实体物与其数字化之后的再生数码物之间同样存在一个尺度意义上的差异。
近年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数字孪生乃至元宇宙等概念风靡一时,人类似乎来到一个物质世界与虚拟世界高度融合与联通的临界点,仿佛推开一扇门就能通向充满无限想象的未来,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实体物的数字化。如果我们拉大时间的尺度,这个场景似乎并不陌生。当万维网诞生之初,互联网兴盛之始,信息高速公路等概念就曾将人类带到这扇门口。当然尺度还可以拉得更远,当无线电波将全世界相连之时,当卢米埃尔兄弟(Auguste Marie Louis Nicholas Lumière,Louis Jean Lumière)在屏幕上用光影再造出一个想象界之时,当达盖尔(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用银盐记录下世界的形象之日,甚至当人类第一次学会文字书写之初,当智人第一次画下岩画之际……类似场景早已上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下最时尚的元宇宙,恐怕也早就布满了人类想象力的包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