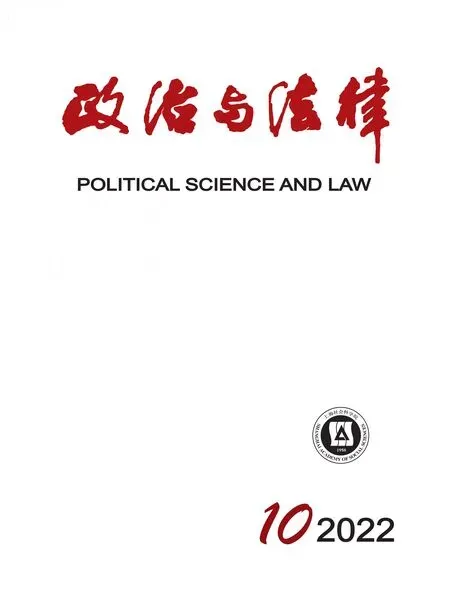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与因应:以社区团购的规制为视角*
侯利阳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030)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中央在2020 年底对数字经济提出的新要求。但何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尚无定论。〔1〕参见曾宪奎:《防止无序扩张:促进“互联网+”相关新型业态健康发展》,载《湖北社会科学》2021 年第2 期。在我国,既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主要在加强《反垄断法》执法〔2〕参见王先林:《论反垄断法对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保障》,载《江淮论坛》2021 年第2 期。与颁布新型的行业规制文件〔3〕参见高薇:《平台监管的新公用事业理论》,载《法学研究》2021 年第3 期。这两个层面展开。前者关注的垄断行为包括二选一(排他性交易)、〔4〕参见王晓晔:《论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的法律规制》,载《现代法学》2020 年第3 期。平台封禁、〔5〕参见侯利阳、贺斯迈:《平台封禁行为的法律定性与解决路径》,载《财经法学》2022 年第3 期。自我优待、〔6〕参见孟雁北、赵泽宇:《反垄断法下超级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合理规制》,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1 期。扼杀型并购〔7〕参见王伟:《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载《中外法学》2022 年第1 期。等。这些行为侧重于平台与竞争性平台、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后者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总局)2021 年10 月发布的两个指南草案即《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与《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为代表。〔8〕参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对〈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 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https://www.samr.gov.cn/hd/zjdc/202110/t20211027_336137.html,2022 年6 月30 日访问。虽然这两个指南草案也关注平台与终端用户之间的消费关系与个人信息保护关系,但其重点依然是平台与竞争性平台、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9〕参见张新宝:《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个人信息保护独立监督机构研究》,载《东方法学》2022 年第4 期。换言之,我国当前对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研究与实践主要是针对数字经济领域中的内部竞争关系。
然而,互联网平台除了与数字经济领域的市场主体之间存在内部竞争关系之外,还与实体经济中的传统市场主体之间存在着外部竞争关系。这种外部竞争关系在数字经济中早期主要表现为弱小互联网平台与强势传统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比如社交网络平台之于传统媒体、〔10〕See Peggy Valcke &David Stevens,Graduated Regulation of‘ Regulatable’ Content and the European 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 One Small Step for the Industry and One Giant Leap for the Legislator?,24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285(2007).即时通信软件之于传统电信运营商。〔11〕See James B.Speta,Deregulating Telecommunications in Internet Time,61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 1063(2004).此类竞争曾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广泛争议,争议焦点在于互联网平台是否要接受等同于传统市场主体的平等规制。为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各国往往对互联网平台持宽松规制的态度。〔12〕See Liyang Hou,Destructive Sharing Economy: A Passage from Status to Contract,34 Computer Law and Security Review 965(2018).但随着“互联网+”经济形态的发展,数字经济经营者不但持续进军由强势主体运行的传统行业,而且开始进军由弱势主体运行的传统行业。对于前者,人们尚可假定互联网平台需要特殊的关照;对于后者,互联网平台再也不是所谓的弱势主体,而是传统市场主体无法撼动的强势主体。已有学者观察到数字经济对于传统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13〕参见姜松、孙玉鑫:《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载《科研管理》2020 年第5 期。但如何因应此种冲击,学界却缺乏进一步的研究。
上述问题并非无实践之源的学理假设。我国近年来,新冠疫情背景下社区团购的兴起引发了从事社区团购活动的互联网平台与传统菜贩之间的外部竞争。在承受强势社区团购中的互联网平台低价销售的冲击之际,传统菜贩可能很快就会面临经营困境,此类主体业务收入微薄、教育背景较低、人口体量巨大,对此情形处理不慎将会引发较大规模的失业,不利于和谐社会之构建。有鉴于此,笔者于本文中拟对此类资本无序扩张的特殊形态进行研究,分析强势数字经济经营者与弱势实体经济经营者之间的竞争与冲突,提出数字经济时代保护传统弱势市场主体的妥善方案。
一、社区团购对传统菜贩的冲击
互联网平台在规制层面被施以特殊照顾的主要原因,恰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8 号)所言,是其具备“新的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新动能,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跨界融通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拓展消费市场尤其是增加就业,都有重要作用”。若某种互联网平台业务只是传统经济形态在数字经济层面的简单移植,未真正改变传统行业的运行模式,那么只需要对之按照传统行业进行规制即可,不涉及其与实体经济的协调问题。本文中,笔者以社区团购为例,分析强势数字经济经营者进入原先由弱势市场主体运作的实体经济形态时所带来的新问题,因此需要首先分析社区团购与其所对应的传统实体经济形态间的差异与竞争。
(一)社区团购的创新性
社区团购是以“线上团购+门店自提”作为主要经营模式的数字经济形态。〔14〕参见段蔚:《互联网背景下社区团购的经济法规制》,载《法商研究》2022 年第2 期。线上团购是一种消费者在购物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过程中组成购买团体,集体购买、享受集体折扣的消费形式。线上团购以消费者集体购买的意愿作为组团的主要动力。虽然集体购买降低了采购价格,但无法降低运输价格。因此,线上团购对于运输成本占价格主要部分的商品(比如生鲜蔬菜)的销售等难以适用。与之相比,社区团购以消费者物理距离的亲近度作为团购组织的必要条件。这种物理上亲近度常常以居民社区为中心,社区团购由此得名。社区团购中的互联网平台通过将网络预售商品打包运输到消费者社区周边自提点的方式降低运输成本,从而可以进军至运输成本高、总体价值低的商品类别。社区团购作为新型的数字经济形态早在2015 年就在我国兴起,但因其需要改变消费者长期以来形成的线下购买模式,一直未对市场产生较大影响。〔15〕参见刘晓春、汤佳:《社区团购的行业特点与法律关系梳理》,载《中国市场监督研究》2021 年第11 期。2020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居家消费”开始流行,社区团购也籍此迅速发展。〔16〕参见陈佳:《“后疫情时代”社区团购发展现状分析》,载《商场现代化》2020 年第8 期。
目前社区团购的主要销售标的为生鲜蔬菜。生鲜蔬菜代表着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生鲜蔬菜销售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基础型行业。生鲜蔬菜在线下销售场景中较难形成提供信息配对的中介方,因此传统上主要采用面对面的销售模式(以下简称:面售)。传统的面售可以分为三种方式,即沿街叫卖(流动摊)方式、沿街摆摊(地摊)方式、固定摊位(菜市场和超市)方式。前两种方式是通过将商品带到消费者聚集区域的方式来解决信息配对问题,第三种方式则是通过区域性集中销售来消除信息的不对称。前两种方式属于主动推销,第三种方式则属于被动推销。沿街叫卖方式与沿街摆摊方式因为影响市容市貌、阻碍交通、噪音污染等问题,于20 世纪90 年代之后,就在我国逐渐消失。〔17〕参见钟骅:《上海菜场布局规划思考与探索》,载《上海城市规划》2012 年第3 期。现有的主要面售方式即为固定摊位方式,其又可分为菜市场方式和超市方式。笔者于本文中基于如下两个方面的考虑,将超市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一方面,菜市场方式是生鲜的主要销售模式,市场份额远超超市方式。据统计,在社区团购出现之前,我国菜市场零售的市场份额大致为73%,超市零售的市场份额大约为22%。〔18〕参见易观分析:《中国生鲜电商物流行业专题报告2016》,https://www.analysys.cn/article/detail/1000341,2022 年6 月30 日访问。另一方面,目前社区团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因低价倾销引起的挤压就业问题”。〔19〕参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召开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指导会》,http://www.samr.gov.cn/xw/zj/202012/t20201222_324567.html,2022 年6 月30 日访问。因此社区团购的主要竞争对象是菜市场方式中的传统菜贩,而非超市。
与传统菜贩的销售模式相比,社区团购代表着生鲜零售领域的创新经济形态,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社区团购较好地解决了信息配对的问题,降低了用户的搜索成本。在传统菜市场的面售中,消费者只有亲身进入菜市场才可以搜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据统计,大约有75%的消费者平均每周去菜市场五次以上。〔20〕See Zhengzhong Si and Taiyang Zhong,“The State of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in Nanjing,China”(2018),http://hungrycities.net/wpcontent/uploads/2018/04/HCP9.pdf,2022 年6 月30 日访问。因此,传统的菜市场方式对于消费者来说存在巨大的搜索成本。相比之下,社区团购采用的是预售模式。社区团购的商业运行模式并不复杂,用户通过互联网浏览、预订所需要的商品,商家将之直接送往用户指定的地址。预售模式改变了消费者必须亲自去菜市场选菜的购买方式,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搜寻成本。此外,在菜市场方式中,菜贩无法充分获悉消费者的需求,只能根据自己的预估进货,若最终和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存在偏差,则需承担商品变质灭失的风险。因此,与面售相比,预售模式中的销售商可根据用户的预订备货,从而较好地避免损耗。
其二,社区团购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在社区团购出现之前,我国曾经出现过蔬菜直营店销售方式。不过,蔬菜直营店销售方式对于单次订单额度不高的生鲜销售来说存在运输成本高的问题,因此多用于有机蔬菜等高档菜品的销售,〔21〕参见曹治玮、张瑞、王波、王儒萌、吴桐:《关于有机蔬菜直营模式的探索》,载《新西部(理论版)》2014 年第23 期。也未对传统的菜市场方式产生很大的冲击。社区团购则在蔬菜直营店销售方式的基础之上增加了集中运输的环节。社区团购在蔬菜直营店销售方式中增加了“团长”这个特殊的角色,并以团长所在的物理位置为核心开发了集中销售和供给的新模式。具体而言,用户先通过团长进行预订,互联网平台将预订产品运送至团长所在地址,用户稍后再去团长所在地址取货。〔22〕参见吴星:《新零售竞争下社区团购模式市场竞争力分析》,载《中国经贸导刊》2019 年第7 期。社区团购中的集中运输解决了蔬菜直营店销售方式中点对点运输的高成本问题。
(二)传统菜贩的处境
生鲜销售行业是我国非常重要的零售行业,其产业规模约为每年五万亿元左右。在社区团购出现之前,菜市场每年的营收规模大致在3.65 万亿元。〔23〕See Macquarie,Digitalising the Distribution of Fresh Produce in China(2021),https://www.macquarie.com/au/en/perspectives/digitalising-the-distribution-of-fresh-produce-in-china.html,2022 年6 月30 日访问。虽然菜市场在生鲜销售中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但传统菜贩却具备三个弱势特征:(1)经营规模较小,涉及人员众多;(2)就业人员收入微薄;(3)属于具有相对垄断地位的强规制行业。
首先,传统菜贩的数量巨大。传统菜贩的巨大规模与生鲜的储藏时间过短密切相关。即便基于现代化的冷处理技术,生鲜的储藏时间总体上也不长,尤其是蔬菜的储藏时间大体在一周之内。储藏问题使得传统菜贩一直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紧迫压力之中。若其商品无法在短期内售出,则存在完全灭失的风险。传统菜贩时刻面临降价清仓的危机,不得不限制经营规模。因此,菜市场方式本质上是通过聚集大量菜贩的方式以高数量对抗低质量。生鲜的储藏问题不仅深刻影响传统的菜贩的经营模式,而且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模式。为了应对生鲜的储藏问题,消费者不得不形成了定期购买的消费模式。在这种消费模式的影响下,消费者也较少进行跨区域购买。由此,每个菜市场及每个菜贩所服务的消费者数量大体固定,这进一步限制了传统菜贩扩大规模的可能。因此,传统菜市场客观上需要维持数量巨大的从业人员。据商务部统计,2020 年我国各种农贸市场、菜市场、集贸市场共有各类经销商户近240 万个,吸纳就业人员近700 万人。〔24〕参见胡剑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020 年7 月3 日新闻发布会》,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200703.shtml,2022 年9 月18 日访问。
其次,传统菜贩的平均收入微薄。从业人员的数量巨大使得传统菜贩的经营客观上存在收入不高的状况。此外,生鲜销售的价格波动对于国计民生的影响极大。在我国,虽然生鲜并不属于政府定价的商品,但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对生鲜的价格进行较为严格的管制,以防止其价格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度的波动。〔25〕参见《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关于稳定蔬菜价格的提醒告诫函》,https://www.samr.gov.cn/xw/df/202102/t20210202_325772.html,2021 年2 月2 日访问。因此,虽然传统菜市场方式中的人员运营成本非常高,但这些成本无法真正反映在生鲜的销售价格之中。换言之,传统菜贩收入微薄除了传统零售模式自身问题所致之外,还存在政府规制介入的原因。根据一项针对南京菜贩收入的统计,南京菜贩2019 年的平均收入约为49000 元,〔26〕See Xinxian Qia,Zhenzhong Si,Taiyang Zhong,Xianjin Huang &Jonathan Crush,Spatial Determinants of Urban Wet Market Vendor Profit in Nanjing,China,94 Habitat International 1(2019)102064.而同年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4372 元。〔27〕参见南京市统计局:《2019 年南京市工资与收入》,http://tjj.nanjing.gov.cn/bmfw/njsj/202007/t20200727_2310805.html,2022 年6 月30 日访问。二者相比,菜贩的平均收入比居民平均收入低了23.4%。
最后,传统菜贩属于具有相对垄断地位的强规制行业。菜市场中的生鲜销售一直是我国进行强规制的行业。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虽然我国的菜市场主要为民营企业所建设,但菜市场的建设一直被认为是政府公共设施建设,一般是在土地开发的时候作为开发商的打包义务进行投资建设。〔28〕See Qian Forrest Zhang &Zi Pan,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Vegetable Retail in China: Wet Markets,Supermarkets and Informal Markets in Shanghai,4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97(2013).其二,除了普遍规制举措(比如价格、产品质量、消费者保护等),我国还对传统菜市场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我国大致从2000 年开始对菜市场进行政府规制。该项工作主要由中央进行指导,〔29〕参见《标准化菜市场的设置与管理规范》(商贸发〔2009〕290 号),商务部、财政部2009 年6 月16 日印发。由地方政府具体实施。〔30〕参见《上海市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DB31-T344-2005),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2005 年4 月25 日发布。有关文件对于菜市场的覆盖半径、公共安全、食品安全、卫生安全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虽然这些监管义务的直接对象是菜市场,但菜贩却是这些义务的最终承担主体。换言之,菜贩通过获得摊位的方式最终履行了政府为规制菜市场所设定的义务,也完成了对于生鲜零售行业的市场准入手续。在这种规制之下,摊位成为传统菜贩进入生鲜零售行业的主要障碍,但同时也成为菜贩面对其他非法经营主体(比如沿街叫卖与沿街摆摊者)的竞争时的保障措施。
综上,菜市场方式呈现出一种较为奇怪的市场现象。由于商品储藏时长所限,传统菜贩经营规模过小,营业收入不高。针对菜市场方式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通过对菜市场进行规制的方式予以解决。虽然这种规制营造了传统菜贩的相对垄断地位,保障了此类主体的稳定收入,形成了菜贩的既得利益,但也强化了此类主体经营规模过小及营业收入不高的境遇。因此,菜贩虽然是规制菜市场过程中的既得利益者,但又是非常弱势的既得利益者。
(三)社区团购的资本无序扩张表象
相对于传统菜市场而言,社区团购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这种创新具有较强的破坏性,会替代传统菜市场较大的市场份额。面对社区团购的冲击,传统菜市场市场份额的降低属于创新的自然结果,人们无需对这个替代过程本身给予关注。然而,社区团购中的互联网平台在开展此项业务之初主要采用低价销售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31〕参见樊文静、潘娴:《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逻辑与资本无序扩张——以社区团购为例》,载《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21 年第4 期。虽然这种低价销售模式对于促进社区团购这种新型业态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作用,但会对收入微薄的传统菜贩造成短时间的毁灭性打击。菜贩群体经营规模较小,收入不高,若其进货在短期内无法售出即面临着本钱完全损耗乃至退出市场的风险,在面临社区团购中互联网平台的低价竞争时,他们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并且,这部分群体数量巨大、普遍教育水平不高,在遭受毁灭性打击后进行转产的可能性较小。大量菜贩若在短期内退出市场,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处于失业的状态。在我国当前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这可能会造成一定规模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正因为如此,社区团购自兴起之后就引发了广泛关注。〔32〕参见段蔚:《互联网背景下社区团购的经济法规制》,载《法商研究》2022 年第2 期。
二、对既有规制方式的质疑
(一)社区团购的规制现状
鉴于社区团购中互联网平台资本无序扩张的现象,总局于2020 年12 月22 日联合商务部召开了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指导会,提出社区团购的“九不得”要求。这些要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重申《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比如不得违法达成实施垄断协议、不得实施没有正当理由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不得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不得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利用技术手段损害竞争秩序。第二类是明确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比如不得利用数据优势“杀熟”、不得非法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不得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从行为表现形式来看,这两类要求并不是专门针对社区团购这种新经济形态提出的特殊要求,而是对于所有的互联网企业甚至是对所有从事生鲜销售业务的企业的普遍要求。第三类则是专门针对社区团购中的互联网平台提出的要求,此即“在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积压商品等商品外,严禁以排挤竞争对手或独占市场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33〕参见《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召开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指导会》,http://www.samr.gov.cn/xw/zj/202012/t20201222_324567.html,2022 年6 月30 日访问。这项要求也明确了目前社区团购最为严重的问题正是低价销售行为。
此次行政指导会后,总局在2021 年先后两次对社区团购中互联网平台低价销售的行为进行了处罚。第一次发生在2021 年3 月3 日,总局对橙心优选、多多买菜、美团优选、十荟团、食享会等五家互联网平台进行行政处罚。〔34〕参见《市场监管总局对橙心优选、多多买菜、美团优选、十荟团、食享会等五家社区团购企业不正当价格行为作出行政处罚》,http://www.samr.gov.cn/xw/zj/202103/t20210303_326448.html,2022 年6 月30 日访问。第二次发生在2022 年5 月27 日,总局针对十荟团首次受处罚后依然存在低价倾销行为进行二次处罚。〔35〕参见《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社区团购平台“十荟团”不正当价格行为再次作出顶格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http://www.samr.gov.cn/xw/zj/202105/t20210527_329902.html,2022 年6 月30 日访问。在这些处罚中,总局适用的法律条文均为《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二项,即禁止经营者“为了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至于为何适用该条文,按总局相关负责人答记者问时的解释,在调查中,总局发现这些互联网平台实施低价销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抢占市场,“这些利用资金优势采取直降、发放优惠券等形式的补贴,致使大量商品销售价格低于进货成本,扰乱了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36〕参见《市场监管总局对五家社区团购企业不正当价格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答记者问》,http://www.samr.gov.cn/xw/zj/202103/t20210303_326445.html,2022 年6 月30 日访问。
(二)利用《价格法》进行规制的体系性漏洞
虽然总局已经运用《价格法》对社区团购中的互联网平台的相关行为进行了处罚,但遗留问题依然很多。其中的首要问题是《价格法》第十四条能否适用于社区团购中的互联网平台的低价行为。这背后的理论争议主要是《价格法》第十四条与《反垄断法》(2022 年修改)第二十二条(修改前为第十七条)存在较为严重的适用范围交叉。《价格法》第十四条规定:“经营者除了在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积压商品等商品外,不得为了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该条与《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所禁止的“低于成本销售行为”存在严重的重叠。二者的执法协调问题曾引发争议。
对此,我国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二者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即《反垄断法》是《价格法》的特别法,因此当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优先适用《反垄断法》。〔37〕参见李常青、万江:《〈价格法〉与〈反垄断法〉的竞合与选择适用问题研究》,载《中国价格监督检查》2012 年第12 期。另一种观点认为二者既不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也不是新法与旧法的关系,而是一种指引关系。换言之,《价格法》“只有原则性的禁止性条款,缺乏具体的分析和界定标准”,而《反垄断法》“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工具和思维方法”。〔38〕黄勇、刘燕南:《〈价格法〉与〈反垄断法〉关系的再认识以及执法协调》,载《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 年第4 期。虽然这两种观点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实际执法层面却具有一致性,即适用《反垄断法》的分析方法来执行《价格法》第十四条。如此,《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二项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其只能与《反垄断法》的相关条文相结合,才能被用于执法。
如果将《价格法》第十四条作为《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的指引性条款,那么违法的低价销售就应当满足四个要件:(1)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2)实施了低价销售的行为;(3)对市场竞争具有排除、限制影响;(4)不具有正当理由。〔39〕参见《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2019 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1 号)第二十一条。此外,2021 年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国反垄发〔2021〕1 号)第十三条指出,正当理由包括“在合理期限内为发展平台内其他业务”“在合理期限内为促进新商品进入市场”“在合理期限内为吸引新用户”“在合理期限内开展促销活动”等。
从目前社区团购中互联网平台的发展状况来看,其低价销售行为较难满足第一个要件和第四个要件。首先,对于市场支配地位这个要件来说,2020 年所有生鲜电商行业市场规模约为2638.4 亿元。〔40〕参见艾媒咨询:《2020Q1 中国生鲜电商平台数据监测报告》,https://www.iimedia.cn/c400/71234.html,2022 年6 月30 日访问。相对于生鲜销售这个具有五万亿规模的行业而言,所有社区团购中互联网平台的总体市场份额并不高,那么也不可能会有任何一个互联网平台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其次,低价销售若是“在合理期限内为吸引新用户”,可以被豁免。社区团购的迅猛发展仅是2020 年新冠疫情突发后的事情,消费者对于这种模式还不特别熟悉。社区团购中互联网平台采用补贴的形式改变、培养消费者习惯,也属于正常的商业策略。
因此,严格从法理来说,社区团购的低价销售模式既不违反《价格法》,也不违反《反垄断法》。并且,总局的处罚决定书并未分析涉案行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 “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 的目的。经营者的任何行为均以抢夺竞争者的市场份额为目标,也均会造成限制竞争的客观效果。若单以行为的实施为依据进行处罚,则会造成变相规避《价格法》中具体规定的现象。因此,目前基于《价格法》的规制可能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
(三)平台低价销售的深层次原因
关于低价销售的反垄断执法一直存在“本身违法”与“合理原则”之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11 年的标准石油案中确立了“低于成本销售”属于“本身违法”的执法原则。〔41〕Standard Oil Co.v.United States,221 U.S.1,43(1911).但在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之下,〔42〕参见Adrian Emch &Gregory K.Leonard:《掠夺性定价的经济学及法律分析——美国和欧盟的经验与趋势》,载《法学家》2009年第5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93 年的布鲁克案中为该行为的分析增加了“垄断者事后能否收回成本”的要件,最终将之纳入“合理原则”的分析范畴。〔43〕Brooke Group v.Brown &Williams Tobacco,509 U.S.(1993).不过,美国模式并不是处理低价销售行为的唯一模式。比如,欧盟法院就将“低于平均可变成本”的销售价格直接推定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从而将之视为“本身违法”的行为。〔44〕Case C-62/86,AKZO Chemie v.Commission,1991,ECR I-3359.当平台规制进入强监管时代之后,也有美国学者对于亚马逊的低价销售行为进行分析,认为该行为对于市场竞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继续对之适用“合理原则”不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主张在数字经济领域恢复“本身违法”的处理方式。〔45〕See Lina Khan,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126 Yale Law Journal 746(2017).甚至,我国也有学者主张对社区团购的低价销售行为进行严格规制。〔46〕参见段蔚:《互联网背景下社区团购的经济法规制》,载《法商研究》2022 年第2 期。因此,总局对于社区团购中互联网平台的处罚也存在将低价销售认定为“本身违法”的可能,那么,就有必要分析这种处理方式是否符合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
低价销售并不是社区团购的特殊问题,而是数字经济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若单纯从价格低于成本的角度进行分析,则几乎所有的平台企业都涉及低价销售的问题。低价销售或者说“免费经济”甚至被认为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47〕See Friso Bostoen,Online Platforms and Pricing: Adapting Abuse of Dominance Assessments to the Economic Reality of Free Products,35 Computer Law and Security Review 265(2019).但令人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世界各国均未有过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处罚低价销售的案件。欧盟的《数字市场法》被称为最为严格的平台规制立法,但其也未对平台实施低价销售的行为作出任何限制。〔48〕See Council of the EU,“DMA: Council gives final approval to new rules for fair competition online”,Press Release 678/22,July 18 2022.
究其原因,可能是数字经济已经逐步演变为注意力经济,即通过吸引用户注意力获得商业利益的经济模式。〔49〕See Tim Wu,Blind Spot: The Attention Economy and the Law,82 Antitrust Law Journal 771(2019).注意力经济并非数字经济所专有。在传统的实体经济中,注意力也被视为一种重要的商业资源,只是彼时的注意力往往被视为商誉、名誉、知名度等无形资产。但传统的线下经营者较难通过注意力直接赢利。正是数字经济的出现为基于注意力赢利提供了契机。互联网时代的注意力可以通过点击量、浏览量等方式进行精准的量化计算,因此逐步成为广告投放的重要载体。基于注意力的汇集,互联网广告还可以针对不同消费者的特定需求进行个体化的营销。因此,在互联网时代注意力成为广告商趋之若鹜的新领域,也演变为互联网世界的“通货”。〔50〕参见侯利阳:《论互联网平台的法律主体地位》,载《中外法学》2022 年第2 期。
当广告商愿意为注意力支付对价之后,平台的主要经营目标就不再是主营业务的盈利水平,而是注意力的汇集。在这种经营目标的转换过程中,平台企业为了吸引注意力,可以通过免费或者补贴的模式作为营销主营业务的主要手段。以此为基础,平台被改造为“双边市场”:一方面通过提供免费的互联网服务来获取用户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将注意力销售给广告商而获利。〔51〕See Giacomo Luchetta,Is the Google Platform a Two-Sided Market?,10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Economics 185(2014).因此,“免费经济”并非真正的免费,而是“双边市场”形态中针对不同边用户的价格协调。〔52〕See David Evans,The Antitrust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 Markets,20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343(2003);Jean Charles Rochet &Jean Tirole,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37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658(2006).作为数字经济的一种具体形态,社区团购在发展过程中也自然而然地运用了注意力经济发展的商业模式。
虽然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尚未对低价销售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具体实施提供合适的分析框架,但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对此类行为加以严格禁止并不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此外,从笔者于本文中的分析来看,社区团购中互联网平台与传统菜贩相比具有天然的成本优势。即便让其在经营成本之上与传统菜贩进行竞争,也依然会存在大量菜贩被排挤出市场的问题。因此,严格禁止社区团购不得低价销售只能是权宜之计,不能成为规制此类经济形态的长远方针,且不能真正解决传统菜贩的后续发展问题。
三、社区团购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社区团购引发的主要争议表面上是低价销售对传统菜贩形成的排挤问题,实质上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竞争冲突问题。该问题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之后呈现的新问题,一方面涉及创新的促进,另一方面涉及弱势市场主体的保护。如何实现二者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的有效平衡尚无直接对应的解决手段。有鉴于此,以下笔者将对创新规制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审视,明晰社区团购问题的症结,并从网约车的规制经验中探寻可行的出路。
(一)创新经济学理论的盲区
经济学对于竞争与创新关系的奠基性理论是熊彼特在20 世纪50 年代提出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理论。熊彼特在历史上首次正式明确创新在经济体系的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这四个周期性循环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垄断者是创新发展的主要动力的假说。〔53〕See Hugo Reinert &Erik S.Reinert,Creative Destruction in Economics: Nietzsche,Sombart,Schumpeter,in Jürgen G.Backhaus &Wolfgang Drechsler eds,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 Economy and Society,Springer,2006,p.55-85.虽然熊彼特在理论阐述中指出创新是对既有制度的毁灭,〔54〕Joseph 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Routledge,2003,p.83.但并未真正分析政府规制在创新发展进程中的角色与作用。在后续的研究中,美国学者克利斯坦森于1995 年提出破坏性创新理论。〔55〕See Joseph L.Bower &Clayton M.Christensen,Disruptive Technologies: Catching the Wave,73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43(1995).该理论认为真正的创新来自新兴企业而非在位企业,虽然在位企业的兴起也是因为创新,但这些企业在其创新进入成熟阶段之后就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价值体系,这些价值体系随着市场的成熟与法律的稳定被逐渐固化。虽然在位企业也重视创新,但真正的创新需要打破既有的价值体系。因此,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于价值体系之外的新兴企业,而非在位企业。
克利斯坦森认为破坏性创新应当具备三个主要特征:“(1)创新所针对的目标顾客在过去因缺乏金钱或技术而无法单独完成相应的工作;(2)创新所针对的目标客户需要简单的产品;(3)创新能帮顾客更简单、更有效地完成他们正努力试图完成的工作。”〔56〕Clayton M.Christensen,Mark W Johnson &Darrell K Rigby,Foundations for Growth: How to Identify and Build Disruptive New Businesses,43 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2(2002).既然真正的创新意味着对既有价值体系的破坏,其就被称为破坏性创新。但破坏性创新在产生之初往往是脆弱的。这种脆弱性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新兴企业缺乏足够的资源发展创新性产品;另一方面,在位企业会全力阻碍新兴企业占领市场。因此,破坏性创新理论的基本逻辑假设为:虽然创新型企业代表未来,但在开始与传统经济经营者竞争时属于弱势市场主体,因此需要政府规制的额外保护。有鉴于此,破坏性创新理论本质上是呼吁政府支持和保护从事创新的企业,并约束在位企业所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应用至本文之场景,则是呼吁政府通过限制实体经济来促进数字经济。
既有的法律规则多为针对传统经济的运行特征而量身打造,与传统经济经过多年的交互融合后,成为服务传统经济主体既得利益的工具。因此,数字经济的出现会造成既有法律体系与新经济发展需求的不匹配。这种不匹配成为平台企业与实体经济竞争冲突的焦点。〔57〕See OECD,Hearing on Disruptive Innovation,https://www.justice.gov/atr/file/823886/download,last visited on June 30,2022.应当说,我国在2020 年之前对数字经济的“包容审慎”态度正是考虑到了数字经济破坏性创新的正面效果。李克强总理对此曾有过精准的解释:“所谓‘包容’,就是对那些未知大于已知的新业态采取包容态度,只要它不触碰安全底线。所谓‘审慎’有两层含义:一是当新业态刚出现还看不准的时候,不要一上来就‘管死’,而要给它一个‘观察期’;二是严守安全底线,对谋财害命、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不管是传统业态还是新业态都要采取严厉监管措施,坚决依法打击。”〔58〕参见《李克强详解为何对新业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09/12/content_5321209.htm,2022 年6 月30 日访问。有鉴于此,包容审慎的规制态度是对破坏性创新理论的认可,代表着政府对于创新的支持与保护态度。在面对数字经济经营者与传统经济经营者的竞争时,由于各国政府均对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抱较大的期望,也都选择了对于作为弱势市场主体的数字经济经营者的保护。
不过,破坏性创新理论的缺陷在于只关注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而甚少关心在位企业的事后发展。实际上,克利斯坦森在提出破坏性创新理论的时候,也预见到了在位企业的既有经营在破坏性创新成功之后一定会走向衰亡,并为在位企业的后续发展提供了两条思路。其一,在位企业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在破坏性创新产生之后进行跟随性经营;其二,在位企业可以预先在内部建立完全独立的部门,引领破坏性创新的市场研发。〔59〕See Joseph L.Bower &Clayton M.Christensen,Disruptive Technologies: Catching the Wave,73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50(1995).无论是哪种思路,克利斯坦森其实都是假设在位企业在面对创新型企业的时候并非弱势市场主体,而是可以自行进化的强势主体。这些在位企业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并结合自身持有的资源,即便在破坏性创新出现之后也能够较为平稳地过渡到创新经济。
这种假设确实能够应用于多数数字经济经营者与传统实体经济经营者的竞争场景。时至今日,多数数字经济经营者都较好地发挥了“鲶鱼效应”,或带来传统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或再次激发传统经济经营者的活力。前者的案例,例如互联网媒体之于传统媒体,面对互联网媒体的竞争,传统媒体的衰落不可避免,但多数传统媒体都能够顺利转型以应对互联网化的冲击;〔60〕参见刘鹏:《传统媒体融合转型的若干趋势》,载《新闻记者》2015 年第4 期。又如互联网第三方支付迫使传统商业银行推出移动支付与之抗衡。〔61〕参见侯利阳:《数字人民币的竞争减损与规制补充》,载《南大法学》2021 年第1 期。后者的典型案例,如即时通信软件之于电信行业,虽然电信运营商在即时通讯软件的冲击下通话业务量迅速下降,但后者却为前者带来了宽带和移动流量业务的大幅度上升。〔62〕参见工业和信息化部:《2021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解读》,https://www.miit.gov.cn/gxsj/tjfx/txy/art/2022/art_e2c784268cc74ba0bb19d9d7 eeb398bc.html,2022 年6 月30 日访问。因此,数字经济经营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带来了传统实体经济与新经济的良性互动。
然而,克利斯坦森对于在位企业的假设可能存在三个局限。其一,并非所有传统实体经济中的既得利益者都是强势主体。其二,启动破坏性创新的新兴企业也并不总是弱势市场主体。其三,并非所有的破坏性创新都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成功占领市场。数字经济三十多年的发展造就了一批拥有巨大资本的企业。只要能够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即便是新创的平台企业也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无论是开拓新业务的既有平台企业还是刚刚进入某个领域的初创平台企业都不能被简单推定为弱势市场主体。进而,数字经济的优势之一是交易成本的大大降低。该优势可以让平台企业在短期内迅速占领市场。因此,也有学者称数字经济中的竞争模式是“抢占市场的竞争”(Competition for the Market),而不是传统经济中的“抢占市场份额的竞争”(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63〕See Michael L.Katz,Big Tech Mergers: Innovation,Competition for the Market,and the Acquisition of Emerging Competitors,54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1(2021)100883.面对数字经济的冲击,那些强势的实体经济经营者可以利用其所掌握的资本逐步转型;但在由弱势市场主体把控的传统实体经济形态中,这些主体可能在短时间内遭受数字经济经营者的毁灭性打击,完全失去顺利过渡到数字经济的可能性。笔者称这种现象为“毁灭性创新”。
经济学将效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64〕See Cento Veljanovski,Economics Approaches to Regulation,in Robert Baldwin,Martin Cave and Martin Lodge(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Regul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19-22.若以此为标尺,创新代表着市场发展的未来,因此应当对之进行无条件保护。数字经济对传统实体经济带来的破坏性创新属于正常的市场现象。原则上大可不必对数字经济的破坏性效应持敌对态度。但若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对于遭受“毁灭性创新”打击的传统弱势市场主体进行保护也不容忽视。若某个传统实体经济形态中的既得利益者为弱势市场主体,那么此类市场主体的数量一定非常庞大。当数量如此庞大的此类市场主体在短时间内蒙受毁灭性打击,并且丧失向新型经济形态转型的可能性时,这部分群体很有可能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有鉴于此,创新除了包含促进破坏性创新的因素之外,也应当包含规制“毁灭性创新”的内容。换言之,应当同时关注技术创新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
(二)网约车规制的经验借鉴
“毁灭性创新”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之后所出现的新问题。无论是国内学界还是国际学界都对该问题缺乏充分的关注。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不过,这同时意味着如何对之进行妥善的规制既缺乏相应的学术研究,也缺少直接的实践经验可供参考。有鉴于此,笔者拟从网约车这个具有相似竞争场景的行业的相应规制经验中寻找答案。
我国的网约车行业大体上从2015 年起才真正进入公众视野。〔65〕参见王静:《中国网约车的监管困境及解决》,载《行政法学研究》2016 年第2 期。网约车在传统实体经济形态中的竞争对象为巡游出租车(以下简称:出租车)。网约车与社区团购具有极强的可比性。二者所对应的传统实体经济形态中均存在数量巨大的弱势既得利益者。首先,据我国交通运输部的统计,我国在2021 年共有出租车139 万辆。〔66〕参见交通运输部:《2021 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s://xxgk.mot.gov.cn/2020/jigou/zhghs/202205/t20220524_3656659.html,2022 年6 月30 日访问。按每车配备两名司机估算,我国约有278 万出租车司机。换言之,我国出租车行业的就业人员数量虽然少于传统菜贩,但也蔚为可观。其次,我国对于出租车司机的资质有着非常严格的经营许可要求,〔67〕参见《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4 年第16 号)。对于出租车的资费实行严格的价格管控。〔68〕比如,可参见《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11 年第43 号)第六条。非经政府批准的出租车经营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从规制角度而言,出租车司机与传统菜贩类似,均属于所处行业的既得利益者。再次,与传统菜贩类似,价格管控再加上经营主体众多,使得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也处于较低的水平。根据一项针对北京市出租车司机的调查,北京市出租车司机的人均年收入远低于城镇在岗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69〕参见宗刚、王健:《出租车低速行驶费对司机福利的影响研究——基于北京市出租车市场》,载《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 年第10 期。因此,出租车司机同样属于运营传统实体经济形态的弱势既得利益群体。
此外,与社区团购类似,网约车同样是对于出租车行业的创新。出租车只能通过巡游来解决司机与乘客的信息配对问题。但这种解决方式效率较低,且会造成大量交通资源的浪费。〔70〕参见熊丙万:《专车拼车管制新探》,载《清华法学》2016 年第2 期。也正因为如此,在传统模式之下政府只能通过提高出租车与出租车司机供给的方式来满足乘客的需求。与之相比,网约车利用智能移动设备的全球定位功能为消费者和司机提供信息配对服务。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约车平台发布租车需求以及位置信息,网约车司机则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确认是否接受消费者的预约。由此,网约车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出租车巡游的低效问题,为传统出租车行业的重组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然而,网约车自出现之后就与出租车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在网约车发展初期,其破坏性创新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原来受规制保护的出租车行业运单量不断下降。其二,多数网约车司机缺乏出租车营运资格,从而产生非法经营的问题。这些破坏性创新效应引发了出租车和网约车的直接冲突,在有些地方还造成了群体性事件。〔71〕参见陈越峰:《“互联网+”的规制结构——以“网约车”规制为例》,载《法学家》2017 年第1 期。总之,网约车的出现改变了出租车行业的垄断格局,触动了出租车的既得利益。然而,面对数字经济形态的冲击,出租车行业受到的打击是否属于“毁灭性创新”,是存在疑问的。网约车平台并不禁止出租车司机进入网约车行业。因此,虽然网约车的出现抢占了出租车的大量市场份额,但出租车司机并没有承受短期内无法向数字经济经营者转型的压力。可能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国多数学者支持对网约车和出租车进行无差别的平等规制。〔72〕无差别的平等规制主要针对网约车和出租车的市场准入以及经营范围,不包含二者因技术差异而形成的差别规制。参见刘乃梁:《包容审慎原则的竞争要义——以网约车监管为例》,载《法学评论》2019 年第5 期;陈越峰:《“互联网+”的规制结构——以“网约车”规制为例》,载《法学家》2017 年第1 期。
不过,2016 年出台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16 年7 月27 日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发布)〔73〕该办法后根据2019 年12 月28 日《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关于修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修正,但这一决定未修改该办法第二条。在对网约车进行合法化认定的同时,未贸然采用平等规制的路径,而是创设了网约车与出租车错位竞争的规制格局。这种错位竞争的规制主要体现于该办法第二条规定的网约车不得提供巡游服务(该办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网约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网约车与出租车的错位竞争规制较好地解决了网约车对出租车的竞争挤压问题。虽然出租车司机不存在无法向新经济转型的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约车对于出租车不存在负面影响。我国对出租车车牌实行限额发放政策,这导致出租车车牌的价格远高于民用车牌的价格,〔74〕参见鄂智超、王溪:《上海出租车牌照转让价被炒到超50 万仍供不应求》,http://auto.people.com.cn/n/2015/0112/c1005-26366070.html,2022 年6 月30 日访问。也提高了出租车的市场进入成本。网约车除了满足地方性准入要求之外,不需要支付高额的出租车牌照费用。因此,我国也有学者指出网约车合法化构成对出租车牌照的“管制性征收”,并呼吁政府对后者的损失进行经济补偿。〔75〕参见刘连泰:《网约车合法化构成对出租车牌照的管制性征收》,载《法商研究》2017 年第6 期。
相对于出租车而言,网约车的进入成本要低得多。如果允许网约车与出租车进行完全的平等竞争,就会严重侵害出租车行业的利益。错位竞争则较好地平衡了网约车的创新性和破坏性。一方面,网约车的合法化可以逐步改变传统规制所造就的出租车垄断格局。另一方面,错位竞争可以短期内保护遭受严重打击的出租车司机。虽然出租车的巡游时间大多都处于低效状态,但也存在一些因人口密集而形成的优质巡游地段,比如飞机场、火车站、商务中心、商场等。〔76〕See Yunzhe Liu,Alex Singleton,Daniel Arribas-bel &Meixu Chen,Ident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Road-constrained Areas of Interest(AOIs)through Spatiotemporal Taxi GPS Data: A Case Study in New York City,86 Computers,Environment and Urban Systems 1(2021)101592.禁止网约车进行巡游经营是对出租车在这些地区的垄断保护。不过,此种保护并不是绝对的。处于这些区域的消费者依然可以呼叫网约车。此外,虽然网约车不得提供巡游服务,但出租车可以随时进入网约车市场。这进一步保障了出租车在遭受数字经济冲击时能够尽快过渡并适应新的经济形态。因此,出租车和网约车的错位竞争机制在短期内缓和了出租车与网约车经营者之间的矛盾,为应对“毁灭性创新”提供了较好的思路。
四、规制路径的变革
(一)规制社区团购的总体框架
信息技术的数字化应用极大地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降低了传统企业的交易成本,也扩张了规模经济效应对实体经济的传统限制。〔77〕See Carl Dahlman,Sam Mealy &Martin Wermelinger,Harnessing the Digital Econom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2016),https://www.oecd-ilibrary.org/development/harnessing-the-digital-economy-for-developing-countries_4adffb24-en,last visited on June 30,2022.数字经济的出现一方面提供了传统企业无法实现的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开始重新组织传统实体经济的生产流程。比如,社区团购就解决了传统的面售所导致的菜贩经营规模过小的问题。虽然具有破坏性创新效应的数字经济形态会逐步侵蚀传统经济形态的市场份额,部分甚至全部取代传统实体经济形态,但这是新经济形态破坏性创新所带来的正常竞争效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规制应当更多地扮演激励性的角色。然而,数字经济不是法外之地,更不能以创新的名义损害消费者、竞争者利益以及其他社会利益。对于破坏性创新,应当坚持包容审慎的规制原则,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以基本规制来保障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以及社会安全,以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保障市场竞争的良性运行。不过,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除了涉及消费者、竞争者等群体的保护之外,也应当涉及“毁灭性创新”中的弱势市场主体保护问题。
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互联网平台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将传统上必须由大型企业完成的生产流程进行改组,使之可以由众多中小企业联合完成。这个时期比较常见的商业模式是互联网平台联合弱势市场主体对抗传统强势主体的新经济、新业态。在这些领域中,数字经济展现的更多的是破坏性创新效应,因此应当遵循包容审慎的原则进行规制。但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开始进军至某些由弱势市场主体运行的传统实体经济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数字经济带来的还是破坏性创新,前述的规制原则依然有效。不过,此时开始呈现出强势互联网平台进入弱势市场主体运行的传统实体经济领域的问题。依照破坏性创新性理论,这些弱势市场主体代表着效率较低的传统经济,原则上不应当受到法律的特殊保护。但是,这部分市场主体普遍存在收入不高、数量众多、教育水平较低等问题,面对数字经济的冲击很容易出现短期内失业且无法顺利过渡到数字经济的情形,如不加以关注,很容易影响社会稳定。
笔者于本文中提出“毁灭性创新”现象,旨在分析此种创新过程中传统弱势市场主体的保护问题。“毁灭性创新”现象有三大特征:(1)数字经济对要进入的传统实体经济领域产生破坏性创新效应;(2)与数字经济经营者竞争的传统实体经济经营者是数量众多的弱势市场主体;(3)面对数字经济的冲击,传统弱势市场主体存在迅速退出市场或者失业的社会性风险。根据我国对于网约车规制的经验,笔者认为,对于“毁灭性创新”现象的规制应当遵循如下两个原则:(1)提供保障传统弱势市场主体向数字经济转型的过渡通道;(2)在过渡期内为传统弱势市场主体确立“垄断性”的经营领域,使之获得一定的过渡保护期。对处于“毁灭性创新”中的弱势市场主体进行特殊保护能够较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进而,虽然这些过渡性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传统弱势市场主体,但其实施必须建立在促进破坏性创新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毁灭性创新”语境下对于弱势市场主体的保护只是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保障传统弱势市场主体不会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被无情抛弃,并能够顺利过渡至数字经济。随着传统弱势市场主体逐步转型为数字经济经营者,这些特殊的保护措施也应当被及时撤回,最终进入平等规制的时代。
(二)规制社区团购的具体举措
社区团购的低价销售问题并非该种业态所呈现出的特殊问题,而是数字经济中的普遍现象。波斯纳认为低价销售应当被理解为维持垄断状态的行为,而不是获得垄断状态的行为。〔78〕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反托拉斯法》(第二版),孙秋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244 页。因此,企业在成长阶段所实施的低价销售行为原则上不会对竞争产生严重的影响。即便需要对之进行强化型的反垄断执法,也可待行为人获得垄断地位之后再予实施。因此,社区团购低价销售行为的负面效果主要不在于该行为自身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而在于其对弱势菜贩的毁灭性打击。社区团购通过低价销售对于传统菜贩的竞争排挤问题,应当基于上述关于“毁灭性创新”现象的规制框架,结合社区团购的具体经营特征加以解决。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具体规制举措。
首先,是对社区团购中团长资格的规制。社区团购模式的重要主体有两个,即互联网平台与团长。从目前社区团购的运行情况来看,平台与团长之间的关系更类似于委托关系。〔79〕参见刘晓春、汤佳:《社区团购的行业特点与法律关系梳理》,载《中国市场监督研究》2021 年第11 期。平台负责商品的进货、定价、运输,团长负责宣传以及向消费者交付商品。在这种模式中,平台是独立的销售主体,团长承担辅助角色。从这个角度看,传统菜贩的竞争者是平台,而不是团长。但若从角色转型的角度而言,传统菜贩未来的出路应该是团长,而不是平台。因此,政府规制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当是如何让传统菜贩顺利过渡为团长。我国目前对于团长的资质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当前,团长的人员构成主要为全职太太、快递站站长、便利店店主等。〔80〕参见李梦梦、房路生:《社区团购平台商业模式解析及发展展望》,载《经济研究导论》2022 年第3 期。传统菜贩的资质要求则通过租用菜市场摊位这种形式予以一体化体现。当缺乏类似资质要求的团长加入竞争时,一方面使得传统菜贩在竞争中处于成本较高的不利地位,另一方面会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等隐患。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在法律上对团长的运营资格进行规定。根据网约车规制中对于网约车和出租车平等规制的成功经验,〔81〕比如,上海市对网约车要求2600 毫米的轴距及本地车牌,对于网约车司机要求本地户籍。这些对于网约车资质方面的要求与对于出租车的管理规定完全一致。参见《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若干规定》(沪府令2016 年第48 号)第八条、第九条;《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11 年第43 号)第十一条;《上海市出租汽车小客车车辆规定》(上海市城市交通管理局2006 年2 月8 日发布)第四条。笔者认为应当对团长向消费者交付商品的地点进行类似于菜市场管理的规定。如此,一方面可以保障社区团购在销售过程中的食品安全,另一方面可以保障传统菜贩在向团长转型的过程中拥有超过其他市场主体的经验优势。这样,社群团购中的互联网平台在选择团长时也会比较倾向于选择传统菜贩,从而促进后者的顺利转型。
其次,是对社区团购中互联网平台的规制。社区团购与传统菜市场之间是互联网预售模式与传统面售模式之间的换代竞争。鉴于互联网预售模式的种种优势,传统的菜市场方式必将被抢走大量的市场份额。不过,面售有着消费者体验度方面的特殊优势。〔82〕See Shuru Zhong,Mike Crang &Guojun Zeng,Constructing Freshness: The Vitality of Wet Markets in Urban China,37 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 181(2020).因此传统菜市场并不会因为社区团购的到来而完全消失,只是其市场份额会迅速缩小,并随着社区团购的发展而被迫转型。在社区团购与传统菜贩形成稳定的竞争平衡之前,可以考虑暂时限制社区团购中互联网平台的业务拓展,给予传统菜贩一定的过渡空间。参考网约车规制的经验,应当确立社区团购与菜市场之间的错位竞争机制。社区团购与传统菜市场秉持不同的销售模式,二者各有自己适合的经营领域。为了给传统菜贩保留一定的生存空间,应当在短期内禁止互联网平台通过社区团购进军菜市场。进而,为了促进传统菜贩向数字经济经营者的过渡,也可以考虑通过各种规制手段激励社区团购中的互联网平台与菜市场合作,逐步把菜市场打造成为社区团购的物流周转地,从而使得传统菜市场也能够参与社区团购的发展,实现数字化转型。
最后,是发挥社区团购的积极作用,弥补菜市场规划中的缺陷。不能过于强调社区团购中的互联网平台资本无序扩张的问题,而是也要看到社区团购对于生鲜零售所带来的创新转变。菜市场在我国属于政府城市规划的范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菜市场的规划建设开始面临两个挑战。其一,随着市区人口逐步向新城区迁移,老城区的菜市场开始出现消费者数量过少的问题。但老城区的菜市场往往占据黄金地段,对于菜市场这种经济产出较小的行业来说,会逐步显现出土地资源浪费的问题。其二,新城区的菜市场建设存在建设滞后或者服务半径过大的问题,无法真正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83〕参见余倩:《上海市菜市场转型升级的对策研究》,载《上海商学院学报》2018 年第2 期。随着社区团购的引入,传统菜市场肩负的生鲜销售责任将会大大减轻。因此,在今后的城市规划中,政府很大程度上可以利用社区团购来承担传统菜市场的功能,或者将黄金地段中利用率不高的菜市场转作他用,或者在尚未建设菜市场的新城区鼓励社区团购进入,使其作为菜市场的替代方式,从而弥补菜市场规划中的不匹配和滞后性等缺陷。
五、结语
互联网平台的无序扩张,除了涉及数字经济经营者之间的内部竞争关系,须对此加以规制之外,也应当将数字经济经营者与传统实体经济经营者的外部竞争关系纳入规制范畴。目前学界的研究多侧重前者,而假定传统实体经济经营者可以自然地过渡到数字经济经营者。然而,社区团购中互联网平台与传统菜贩的竞争凸显了传统弱势市场主体在面临数字经济时的“毁灭性创新”现象。与网约车与出租车之间的竞争涉及“毁灭性创新”的问题相类似,电子商务平台与线下商店的竞争等也或多或少地会涉及该问题。这其实是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的具体表现。为了对这种冲击予以因应,笔者于本文中以社区团购为切入点,提出应对“毁灭性创新”现象的规制方案,希望能够为其他类似行业中规制方案的设计提供参考。数字经济的有序发展既需要激发平台企业的创新优势,也需要回应传统弱势市场主体的迫切需求,使其能够分享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并最终能够顺利地过渡为数字经济经营者。如此,方能真正实现数字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