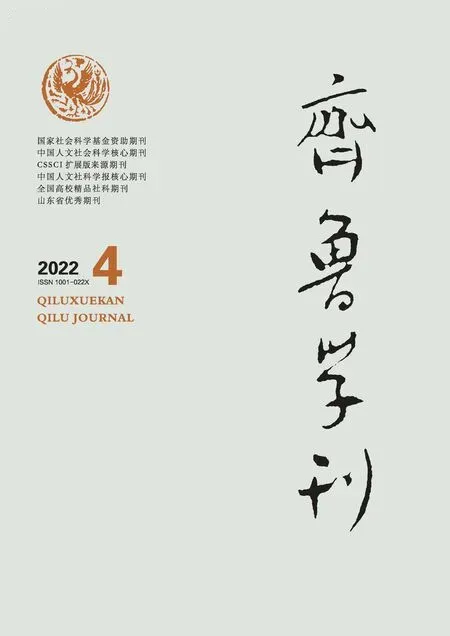性命攸关:孟子生命伦理的义理逻辑和精神
张舜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刘述先曾经说:“孟子在儒家思想上的最大贡献,无疑在他提出了一整套心性论的看法。”(1)安乐哲等:《孟子心性之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74页。孟子对生命问题的伦理思考,就其主要内容而言,也主要体现在他的心性哲学上。从孟子言说生命问题的整体特点来看,孟子对“性”与“命”(本文所曰“命”,主要就“天命”而言)及其关系的思考,构成了其生命伦理思想的核心问题,也充分体现出孟子生命伦理思想的精神特色。《孟子》文本中并没有“生命”一词,对“生命”及其相关的伦理问题的思考,在孟子那里也主要表现为对性、命及其关系的认识。故笔者以“性命攸关”概括孟子的生命伦理思想。在孟子那里,“命”由“天”来,“天”是孟子言说生命问题的根本前提。其所谓“天”,并非如牟宗三所曰只是“形上的天、德化的天”(2)牟宗三:《历史哲学》,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第113页。,它同时也是具有宗教意味的天。天和人不仅是一种伦理性的关系,也是具有宗教意味的关系,但天与人又非完全类同于宗教讲神与人的关系那样是一种从属关系。天是人之本,而人则是天之在世的“代表”、天之德的现实化身。天命从根本上规制生命存在的性质、价值和意义实现的根本方式,但它对人而言并非只是一种限制力量,它同时也是一种支持力量,为人类主体自由在天命的伦理要求下的发挥提供了动力。孟子如此理解天人关系,不仅决定了他对“人之性”的特殊理解,也决定了其生命精神即在于“事天”。
一
如果我们把生命伦理学问题理解为以人的生命问题为中心的哲学问题的话,那么孟子的心性哲学显然具有一种生命伦理学的特征。这是因为孟子的心性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天人性命之学,它的基础或核心内容即是在一种天人关系的视角下对人的生命本质及其存在意义的揭示。从生命伦理学的角度说,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之所以是人的根据来自哪里,现实中的人又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人应然的存在如何,人应该怎样做才能达到人的应然存在状态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并实现生命的价值,这些问题构成了生命伦理学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亦恰好主要涵纳在孟子对性与命及其关系的认识上。孟子所曰之“性”虽然具有多义性,但主要是就“人之生命特性”而言之性,而“天命”则是“人之为人之性”的根据和来源。在天命与性的关系中,孟子较为清楚地呈现出对生命之伦理思考的主要内容。人的生命,具有特殊的天命之规定,而其本质亦在于践行天命特殊的伦理要求。天命是人类生命的“主心骨”,人类也只有按照天命要求才能证成其自身。我们先来看孟子之“性”之于生命的意义。
孟子所曰之“性”无疑是孟子哲学的核心范畴,其对理解整体孟子哲学亦极为重要,对此学界并没有异议。但问题在于,孟子讲的“性”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性,其所曰“性善”又具体何指,学界却一直争议不断。譬如,孟子之“性”到底是一种有待生成的概念,还是指人或物所确定的生物属性?性善是指人性即善,还是说人性向善?对此学界向来意见纷纭。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尽述相关观点,而仅就孟子言性基本方式和内涵略陈己见和分析。从孟子言性的基本方式和定位来看,笔者认为性在孟子那里的基本内涵还是清晰的,即性主要是指一种天赋规定性,或曰孟子主要是在一种天赋规定性的角度来言性的。他依据人与禽兽天赋规定性的内容不同,而将人的生命与禽兽相区分,并指明了人之为人之根本的生命标志。依此,孟子又进一步区分了“君子之性”和“小人之性”。在孟子那里,食色等生物本能、事物的形体构造、脾气秉赋等皆属于天所赋予人与物的,故其均可谓之性。但孟子文本中的“性”字并不总是在普遍的天赋规定性角度来讲的性,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孟子所言之“性”字,亦特指人之所以为人之性,是就人的特殊生命天赋而言之性。大致说来,孟子讲的“性”可以区分为广义的性和狭义的性。广义的性是就天赋于人与物的规定性而言之性,在这个意义上,凡是天赋予人与物的,即都是性;而狭义之性则专指人类特有的生命之性,也即人之所以是人之性。但不管是广义之性还是狭义之性,性都是就天赋于人与物的禀性而言,其基本内涵是指天赋规定性。性并不是后天应然的东西,而是先天确定的为人与物所属之生命之性。也即孟子所曰之性乃一确定性的内容,而非生成的概念。在这里,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其一,孟子论性,就其思维模式或言性的基本方式来说,它其实和告子等人一样,遵循的也是传统上的“以生言性”或“即生言性”的思维方式。而所谓“以生言性”或“即生言性”,即是从人与物与生俱来所拥有的生命性征角度来言说“性”的内涵和意义。在这种“以生言性”的语境中,“生”的基本含义是“天生”“生而即有”,也就是认为性来自于天赋。古人意识到万物之生皆有其自然之所向和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内容,对于这些与生俱来的生命性征,古人皆归之于“性”的范畴。如唐君毅说“一物生,则生自有所向,即有性”(3)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故从以生言性或即生言性的角度来看性,性实质上即是指物之所是的天赋规定性。从天赋的规定性角度来看性,生物天生具有的生命特征,比如“口目耳鼻之欲”和身体“形色”等均可以说是性的内容。在孟子所处的时代,以生言性或即生言性可谓当时思想界的大传统,在当时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告子的“生之谓性”、荀子的“性者,天之就也”以及公孙尼子等人有关性的观点,实际上都可以说是这种思维传统的表现,他们所说的性本质上都是指物生而即有之性。这样一种对性的看法,按照陈来先生的看法,在当时其实也是儒家论性的主流观点(4)陈来先生认为告子、宓子、漆雕子、世子、公孙尼子等人关于性的看法,代表了当时儒家人性论的主流看法,孟子与告子等人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儒家内部有关性的争论。具体请参阅陈来先生的《郭店楚简与儒学的人性论》一文,载于《第二届中国南北哲学论坛暨“哲学的当代意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发表时间2005年10月22日。。孟子所说的性,其具体内涵虽然有别于他人,但这种言性的方式仍然清晰可见。
比如孟子明确肯定“口目耳鼻之欲”是性。他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下》)又说:“形色,天性也。”(《孟子·尽心上》)孟子并不否认人的生理本能是性,这一点从他对告子之“食色性也”的观点不置可否的态度中也可管窥一斑。孟子对告子的反对,并不在于告子将“食、色”等生理本能归入“性”的范畴,而在于孟子认为仅仅将这些归入性,并不能真正说明“人之性”。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人类之所以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乃在于人还有另外一种动物不具备而只为人所拥有的特殊天赋,这就是孟子所曰之“良知”“良能”或“四心”。换言之,孟子讲的“人性”,在广义上包括两种意义上的“性”,一种是人与动物共同具备的生理本能之性,一种是只为人所独有而动物不具备之性,而正是后一点,决定了人之所以是人。但无论哪一意义上的性,在孟子那里,性都是天赋的。食色本能是天赋,人独有的“良知”“良能”或“四心”同样是天赋,都是“天所与我者”“我固有之”的特殊禀赋。只是在孟子文本中,人类生命的特殊之性孟子也经常简约说成一个“性”字,从而容易给今人造成理解上的混乱。
其二,这也是尤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即孟子把人独有的特殊天赋,视为具有“善”的属性的东西,故其“道性善”(《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人的身体生来就具有带有伦理属性或倾向的天赋,这就是他称为“大体”的决定人之生命本质属性的“仁义礼智之心”。“大体”是相对于他所称为“小体”的生理本能而言的。“小体”使人“不善”,而“大体”则是人类的生命之本,此即生命之“善”。生理本能欲望是“贱”、是“不善”、是“小体”,“仁义礼智之心”是“贵”、是“善”、是“大体”,故生命之道即在于“考其善与不善”、取贵弃贱,立其大者、去其小者。故孟子曰:“考其善者不善者,岂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弗能夺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所说的“性善”是就人之特有的生命之性而言的,即其所谓“性善”是强调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善本身,而不是说人之所以是人乃在于人是向善的。但孟子道性善不是说人生来就是现实的、具有善的德行之人,不是说人生来就是好人,而是说人之所以是人乃在于其善,唯善决定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的生命中,不仅有天赋之“善”,亦有动物本能,人以动物本能行事,则人禽难分,人流于禽兽;而人如以天赋之善而行,则人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之所以是人,离不开“善”这个东西,一旦离开善,人也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的行为就流于动物本能式的存在。根据有没有这一天赋之善,孟子区分了人与禽兽;而根据对这一天赋善性的自觉和主动操存与否,孟子又区分了“君子之性”和“小人之性”。所谓“君子”,也即自觉把仁义礼智之善视为人的本质规定而主动践行、而将动物本性排斥在外的人。也即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他对于身体中存在的两种意义上的性(“本能之性”和“善性”)自主作了抉择。故君子虽然承认“口目耳鼻之欲”是性,但“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尽心下》)。君子和小人的根本区别,即在于是否自觉其善性并按照善的指引而行为。自觉其善并以善为导向则为君子,服从于自然本能之性则为小人或“庶民”。故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
从天赋规定性角度来看性,这说明在孟子那里,不管是动物之性还是人类特有之性,性都是客观的、固定的,而非说性是一种变化的、有待生成的东西,这和王夫之等人后来将性理解为一种动态的生成的东西有本质的不同。依据对“性”的这一内涵的认识不同,学界由此也形成诸多不同的有关对“性善”的理解。如果把性理解为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自然就会倾向于所谓“向善说”。此外还有所谓“善端说”“善种说”“善的本能说”,等等。这些说法较为相近,即认为人性中有一种促使人“成人”“成善”的先天基因、道德潜质或“道德本能”。这些说法的共同特点是均否认孟子的“性善”是讲“性”即是“善”,但同时均不否定“善”是人之所以是人的本质规定性。按照这些说法,“四心”还不是“现实的善”或曰“成熟的善”,而只是类似于成善的基因、种子。但这些说法在笔者看来,或许均未能抓住孟子性善论之要义。孟子讲人性善,不是指人性是由某种“善端”或“善的种子”不断发展、培育而向善的一个过程,也不是认为人之所以是人乃在于人天生有一种所谓“善的本能”(5)把孟子的“性”理解为如同食色一样的“生物本能”,华霭仁的观点较有代表性。华霭仁认为“孟子的意图是用一种更宽泛的生物学主义取代告子的狭隘的生物学主义,这种更宽泛的生物学主义在人的遗传学特征或者‘性’之中包含了道德心的本能”(安乐哲等:《孟子心性之学》,第5页)。,而是说人的生命“本体”即是善,只有善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生命标志,真正的人之为人之性即是善。
“善端”这个说法是把孟子之“四心”看成人成善的先天基质或端绪,但孟子并没有“善端”的说法。孟子的确把“四心”说成“仁义礼智”之“端”,但孟子的意思也可能是说人性是善的,而“四心”即此善在人身上的经验性的心理体现,并以此来论证人性乃善。其逻辑不是以“四心”为根基或基质然后来说明人性善、来说明人会有趋向善的自然基础,而是以人性善为前提来说“四心”。人之所以是人即是因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之性”,故人性即是善。这个“先天善性”内具于身,人之所以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亦正是因为人先天赋有“善性”,故其于身表现出这些心理。我们可以把“四心”看成仁义礼智在人身上的“初级表现”,但不能说“四心”就是善。因为善显然并不只是表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几种心理。展现人类生命丰富性特质的“善”,也并非绝对是从这几种心理发展而来的。“善的种子”和“善的本能”说观点近似,但亦均成问题。要说人性之善是由其“善种”或“善的本能”发育、成长而来,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何动物没有发展出这种人类特有的人性之善。因为动物其实也具备一些所谓“善的本能”,譬如动物之间的互助、协作、哺育后代时的“无私奉献”、某些鸟类对配偶的“忠贞”等。显然,单纯具备这些所谓“善的基因或本能”未必就意味着拥有这种属性的生命一定会发展成为道德意义上的存在(6)认为道德之“善”来自于动物某种相应的本能的看法,俄国人克鲁泡特金发表的《互助论》在20世纪初期即提出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互助”这种“美德”本身是生物进化的一个要素,是生命进化内在的东西,此看法颇接近把“互助”看成生命进化过程中普遍的基因。而这种东西是一切生命均具有的,并非只有人才具备。因此把“善的本能”看成人之所以是人的“先天基因”来说明孟子性善论的要旨,是没有抓住孟子性善论的要义。。
如此看来,孟子讲的“性善”,其本意当是指人性即善,或曰只有善才使人成为人,而不是说人性是向善的。因为“人之为人之性”这种人类独特的生命本性在人身上的充沛展现,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从广义之性来说,人性天赋,里面有“善的天赋”,也有动物本能,所以对人自然起作用的并不只是天赋善性,还有动物本性。人并不一定就会自然而然地像物种遵循生物规律而生长那样成长为“善人”。“自然而然”地长成“善人”,这有可能在极少数人身上发生,但并不是人类的普遍现象。故“人性向善”之说并不符合人类存在的自然事实。人类的善之生成,离不开自我的德性修养和后天礼法规约与道德教化。荀子之所以猛烈批判孟子,也正是基于此。依荀子,人类自然天性的发展不是自然向善,而是更易流于“恶”。“性”既非“本善”,亦非“向善”。孟子以“善”为人性之本,故真正人性的充分象征即所谓“君子之性”而非“小人之性”。能够真正证成人类自身而有别于动物的,在孟子看来只能是人类实际的善德和善行。人类正是靠这一点,才成为特殊的存在。但这种实际的善德善行不会自然而然地生成,它需要人类的自觉和主动修为。人之善“操则存,舍则亡”(《孟子·告子上》),也就是说,这种天赋之善离不开人的自觉操守,也即切实的实践,如此人才可以说是人。人性是先天的、确定的、固有的,而非后天生成的,所以它也不是变化的。孟子以“确定之善”为“人之为人”之性,如此规定“性”的确超乎人们对于性的一般理解,因而在历史上亦造成颇多误解。苏轼指责孟子是把“性之效”当作了“性本身”,大概也是出于这种误解。“昔者孟子以善为性,以为至矣。读《易》而后知其非也。孟子之于性,盖见其继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见性,而见夫性之效也,因以所见者为性。性之于善,犹火之能熟物也。吾未尝见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为火,可乎?”(7)参见《苏氏易传》卷七,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1册),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352页。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孟子讲性善是尤其彰显了人类的主体自由,这种看法虽说有一定道理,但这也未必是孟子性善论的主要意义。因为这种说法,也是把决定人之所是的“善性”看成是有待生成、有待创造的东西(8)比如梁涛说:“人与禽兽虽然都有‘生’,但禽兽之‘生’只是一种自然本能,而人之‘生’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和创造,故人之特殊性在于其能自觉地塑造、完成、实现其性,能‘动性’‘逆性’‘实性’‘厉性’‘出性’‘养性’‘长性’;正因为如此,人有自由,而禽兽没有自由。”参见梁涛:《“以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的性善论》,《哲学研究》2007年第7期,第36 -42页。。孟子性善论的意图不在于说明人的主体自由,而是在本体上说明人是与天同质的存在,从而论证出人之为人的根本依据和成人的根本途径,以及说明人类生命的特殊价值和存在意义。人类的主体自由,从根本上说,只是天命规制下的自由,这也是为什么孟子道性善,最终以“事天”为指向。
二
孟子的性论,从生命伦理学的角度说,回答了人的生命本质和存在特性的问题,人的生命不是机械的自然存在,而是对人自身的生存目的和意义建构具有充分道德理性自觉的存在,这种在道德意义上理性自觉建构自身的能力,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类拥有的某种天赋的“自由”能力,但孟子并不主张人的“任性”,认为这种“自由”本身也是在“天命”规定性下的自由。在孟子那里,“天命”是人之存在根本的决定因素,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怎么去挑战天命的权威,而是在终极意义上寻求与它的一致。孟子讲的“天”及“天命”远非孔子和荀子等人眼中的“天”与“命”,而是具有浓郁的宗教性特征和神秘主义特征。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孟子之天主要理解为“义理之天”“德化之天”,实际上并不只如此,孟子还有吸收墨家天道观的思想倾向,他眼中的“天”亦表现出浓郁的宗教化倾向,很多学者都指出了这一点(9)孟子讲的“天”具有宗教性和神秘主义特征,冯友兰、李泽厚、宗白华、陈来等诸多著名学者均明确指出了孟子思想的这一特征。相关材料可参见宗白华:《中国哲学史提纲》,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四章;陈来:《儒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天兼有伦理性,亦具有宗教性,也正是这一兼具伦理规定和宗教性质的天赋予人之为人独有的“道德理性”,从而使人类贵于群生、异于群生。在这个意义上,人不但是天创造的,也是天在地面上的“代表”。汉儒的“天人相副”说、宋儒“心即理”说等多种思想都和孟子这一天人关系思想相关。
孟子把“人性”归之天赋,并将人类生命的终极存在价值系于天命所与,天在根本上决定着人类的生命特性和可为,这自然就给所谓“人类自由”规定了根本前提和限度。人类的行为归根结底是受天命规定和制约的,“人性是天之所命”,“天是人之本根”(10)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7页。,人并没有突破这一宗教性和伦理性之天的规定之可能,故孟子讲“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莫非命也”(《孟子·尽心上》)。正因为人类生命的根本依据和可能、以及存在的根本法则都是由天命决定的,天是道德的、亦是神圣的,它赋予人类生命之“本体”、决定人类生命的发展方向,故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即在于“事天”。故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
“事天”二字,尤能体现孟子之天的宗教意味。“事天”自然就要求“顺天”,唯其顺应天命的要求,人方能挺立自己的生命,才能获得所谓“正命”。故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孟子·尽心上》)“顺天”逻辑上必然要求以天为法。不取法天道,不以天命为法,也就谈不上“事天”。所以,要“事天”,也必须“法天”。故焦循曰:“法天即所以事天也。”(11)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517页。而“法天”,也即按照天示之于人的行与事的方式而行动,所谓“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天意至仁,故法天即要求人以仁义为法。如焦循曰:“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无亲,唯仁是与,行与天合,故曰所以事天。”(12)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第1卷),第517页。在孟子那里,法天的要求与人性的弘扬是完全一致的。法天在现实性上就表现为人自觉修持其天赋的道德善性以完善自我生命的过程,而如此也即人道之当为。人按照仁义而行以至生命之终,这也就是尽了人道,实现了天赋于人的“正命”。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孟子虽然强调“事天”,但它仍然保留着人类在天命面前的某种“理性自由”,因而与那种“宿命论”的观点不同。天对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限制性力量,它同时是人性的支持力量。天确实对人来说具有根本的规定性,但是人存在的生命性质又是和这个作为天地万物之“创生本体”的本性是一致的,故其“人为”可达与天同性、与天如一的地步,这就给人之生命存在提供了超越动物本能限制的无限可能。人之生命存在的根据“受命于天”,人之生命存在的意义也是“上达于天”。天赋予了人类以“成人”的特殊天赋,也赋予了人类生命存在的特殊意义。人类生命的价值和终极意义即在于贯彻天的伦理要求,而人类的本性正是天将其性灌注于人而形成的,而这种来自于天、与天同一之性是动物不具备的,这不仅使人类生命根本不同于动物生命,也由于此性内在于人,故其为人之成人和充分实现其生命价值与意义提供了先天的、源源不绝的动力。在孟子那里,“性”与“命”具有高度同一性,而且这种同一性不是静态的同一,而是动态的“天人相与”。“天命”的内在要求是和“人性”的培育与弘扬相一致的,如此也即肯定了人之生命存在的本质和意义显证的方式。此诚如徐复观所说,孟子这种性命观的重大理论意义在于,它能“使人感觉到,自己的性,是由天所命,与天有内在的关连;因而人与天,乃至万物与天,是同质的,因而也是平等的。天的无限价值,即具备于自己的性之中,而成为自己生命的根源,所以在生命之自身,在生命活动所关涉到的现世,即可以实现人生崇高的价值”(13)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02 -103页。。由此观之,孟子虽然强调天赋予人性之善,但他同时也强调了人对其自身的各种天赋(自然本能和善)的一种自觉与选择的道德理性。换言之,人虽有成人的根本之善性,但此善性如果人类不去自觉它、刻意选择彰显它,那么人还是流于本能生活,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总之,在孟子那里,天和人的关系,并非是说人在天的面前只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存在者,相反,而是一个对自身存在使命和义务有充分自觉的存在者。正因为人性这种觉醒力量本质上与天命的要求是同一的,因而决定了人对自身在宇宙中的存在的一种绝对的自信:人是真正的天命的拥有者、体悟者、实践者。它不是一种神道设教式的对天的迷信,而是一种以体悟天道的姿态生活在天地间的从容心态和实践天命的主体自由。尽管这种“自由”在根本上受制于天命,但它仍然弥足珍贵,需要人类刻意维护和珍惜。人性天授,且质同于天命要求,因此养性即践履天命,这就是人之生命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人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成就人之生命自身。一句话,恪尽天德,人道毕现,而这也正是孟子“事天”之论非“宿命论”而呈现出来的积极内容。于孟子,人性对自我命运觉醒的力量并非是对天命的“反动”,而是这种力量本身即是“天命”的体现,故其“造命”或“立命”实际上即是对天命的主动接受和实践。而这个对天命的主动接受和实践的过程,也正是其强调的“顺天”或“事天”的实质内容。天命不可违,这是孟子论人事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天命具有绝对至上性和对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的根本规定性。人的一切行为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制于天命的。所以不管是天赋于人、物的“食色”等生理欲求,还是人追求“仁义礼智”之善,其满足、实现或发明都受制于“命”,故曰“得之不得曰有命”(《孟子·万章上》)。区别在于,二者满足和实现的方式不同。生理欲求之满足在于向外界资源的索取,故孟子曰“求在外”;而“仁义礼智”之德行的修养根据则内在于人心,故孟子曰“求在我”。“求在我者”,如同孔子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一样,只要肯求,即可有所得,因为按照仁义礼智之要求而行,这本身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意愿问题(如我想做个好人,只要诚信为人、敬人爱众,即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好人)。而“求在外”者,却不是肯求即可得到的,比如我想有一个大房子,不是想有就有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界条件。故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
三
由上,孟子思考生命问题的基本理路,是他头脑中的天乃伦理性且具有本体性、宗教性的天,这个“天”将其“性德”化入“人”这种直接代表天之存在的现实存在,人实际上就是天在现世的体现。所以人的生命存在价值和意义亦完全在于发明或展现这种天之性德。孟子的此种思想,张岱年先生认为:“天之根本性德,即含于人之心性之中;天道与人道,实一以贯之。”(14)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这种看法看到了天人的同一性,但还不够完善。孟子的天也是带有宗教性特征的,在这个意义上,天与人的关系可能并非只是性与德同一的问题,也包含人是天意在现世存在的“载体”或形式之意。简言之,“人”其实就是现世的“天”。如此看来,孟子似乎存在一种类似宗教的情怀,他试图以一种宗教性的东西来安顿人类生命、彰显人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但多年来,人们多言其天的伦理性、价值性,而很少顾及其天的宗教意味,这恐怕也有失孟子生命哲学之旨。但是,中华思想史如果真的按照孟子这一神秘主义和宗教趣味的路线走下去,这无疑也会对培育中国人的人文理性造成某种障碍。当然,按照孟子的心性哲学处理人类生活,是不是真的会像李泽厚所说的那样——“完全遵循孟子的路线发展下去,儒家很可能早已走进神秘主义和宗教里去了”(15)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册),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24页。,这本身也值得商榷。因为我们也不能忽视孟子哲学中重视道德理性的因素,而这似乎更为孟子所强调。但是孟子对生命问题的思考,在以伦理为重心的同时,也掺杂着宗教因素、神秘主义因素,这是符合孟子思想实际的。孟子将“‘天’‘性’注入宗教体验式伦理内涵并加以本体式先验化及意念式天人贯通,由此构建起‘性善’与‘尽心知命’‘反诚知天’的伦理化天人论体系”(16)林桂榛:《论孟荀天人论的差异》,《邯郸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第13 -19页。,按照这种思维逻辑,孟子讲性善、也即人之生命特质乃在于善,这确实就如熊十力所说,性善并非一种理论预设,而正是“存在之呈现”(17)牟宗三曾记载冯友兰与熊十力关于“良知”是理论预设还是“存在之呈现”的争议。依熊十力,良知是呈现,非理论预设。具体可参见牟宗三:《心体和性体》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孟子以伦理性和宗教性的天人关系或曰性天关系来处理生命问题的思路和相应观点,也构成了孟子生命哲学的思想特色。此恰如林桂榛所言:“将‘性’与‘天’伦理化、精神化打通或贯通起来,这是他与孔子的区别,也是他与荀子的区别。”(18)林桂榛:《论孟荀天人论的差异》,第13 -19页。
客观地讲,孟子的这种主张正如它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一样,它对于人的生命之成长、人类从容的生活确实具有重要的精神支持意义。人是天性之载体,是天之为天在现世的体现,人的生命与天同质,“天之性”皆具于人心之中,故此人只要“发明”此心,人的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就能得以体现。孟子的这种思想到了陆九渊那里,始以“发明本心”的形式得以彰显,所谓“仁义者,人之本心也”(19)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页。,“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20)陆九渊:《陆九渊集》,第444页。。孟子性天同质的思想,在陆九渊那里也转化为“心即理”的命题,但二者都以不同形式肯定了天人在存在性质和价值上的同一。陆九渊曰:“天地人之才等耳。”(21)陆九渊:《陆九渊集》,第463页。也正因为如此,故人异于群生且贵于群生、最为天下贵。陆九渊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人所以贵与灵者,只是这心。”(22)黎德靖编:《朱子语类》(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70页。既然人的生命就其本质而言,就在于其与天同一的道德性,故其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实现也都在于道德的成就上。天赋予人以“仁义礼智之性”,人积极开显“善性”以成就实际的仁义礼智之德行,这就是人性的完美表现,那么人也就实现了天赋予人的当有之生命。由于人的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本质上维系于确证人之生命存在特性的道德之“善”上,因此相对而言,人的自然肉体生命的寿夭长短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肉体生命的长短并不会影响到人在价值和道德上的完整性,不会影响人带有宗教意味的“事天”使命,故不会影响到人的生命可以“尽道”而终。人以“道”面对生死问题,将人的本真生命归结为一种精神性的生命,那么肉体生命的长短自然就退居次要地位,有这种认识或修为的人自然也会在对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价值衡量中权重于后者,故孟子主张“舍生取义”也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应当说,这样一种主张,也较为容易培养人们面对生死问题时的一种超然态度。人终有一死,但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肉体生命存在的时间长短,而在于我们对天命、天性的领悟、欣赏和实践。故认识到这一点,人也就容易培养出面对生命的自然限制时一种从容气度。人不受生命的自然限制所累,也就容易滋生出稳固浩然的生命信念,有此生命之“浩然之气”,人反而愈能乐观从容地生活于世间。在笔者看来,这无疑是孟子“性命攸关”生命伦理思想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孟子的生命伦理思想最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地方可能还不在于此,而是他对于“人”这一存在的神圣性的启发。人是上天性德的化身,是天命的直接代表,唯其如此,人类才是神圣的存在。“人既是神圣的存在者,则人性必然是善的,这是作为神圣存在者的必然底据。”(23)张晚林:《孟子对道德的辩正及其性善论的出场》,《齐鲁学刊》2021年第4期,第5 -13页。但也唯其性善,也才能显示其神圣性。
综上所述,孟子对生命的伦理思考,可视之为一种“性命攸关”的生命伦理思想。孟子基于性与命同一性的理解展开诠释,提出人之生命的本质及其存在价值,以及意义实现的根本方式和终极可能。孟子之天具有浓郁的宗教性和伦理性特征,而人则是天在现世的代表。天的伦理性决定了人之作为天之“在世形式”的本质特性亦在于善。性是先天的、固定的,故孟子性善即指性即善,只有善才能证明和成就人自身,而非说人性向善。人性善即“天之性”在人身上的呈现。天命与人的这种关系决定了人类生命存在的根本意义即在于“事天”,这也是生命价值和意义实现的根本途径。但这并非宿命论,孟子同样维护了人的某种“主体自由”,从而强调在顺应天命的过程中人如何“造命”而“立命”。在中华思想史上,如此论证人类自身存在的“高贵”与“光荣”的,孟子大概是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