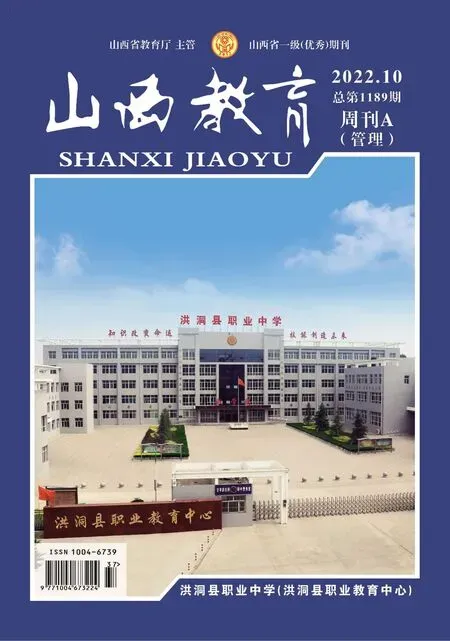劳动最光荣
文 张建军
参加劳动,对我来说是极其平常的事。虽然我们这些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人并不像父辈那样,要和父母一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但也要帮着家里割猪草、拾柴火、摘棉花、和煤泥、扫地扫院、到地头送水送饭……现在回想,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一辈子无法忘怀。那些劳动带给我的兴奋和快乐,是我童年中最光荣、最幸福的记忆。
“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这首《劳动最光荣》的儿歌为我的童年种下了一颗种子,最终形成我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当年在生产队的时候,收麦子靠人工用镰刀收割,收过的麦地里就会留下许多麦穗。这些麦穗是需要拾回来的,这时生产队长就会找到村里的小学校,由学校派遣小学老师带领小学生去拾麦穗。在劳动开始前,老师总要讲话,教育学生要热爱劳动、爱惜粮食、捡拾干净。学生在前面拾麦穗,老师在后面检查是否拾干净了。拾到的麦穗送回到麦场上是要过称的,拾得多的人有奖励。我记得生产队一斤给二分钱,就这二分钱对小学生来说也是相当有吸引力。我们都争先恐后地干,一干就是一上午,到收工时,我们的胜利果实满满当当。
在我小时候,上学还有一种劳动,就是拾粪。那时候种地的肥料是纯天然的农家肥,总是不够用,所以也把积肥这种活儿交给学校。学校在放暑假时作为劳动任务布置给我们:男生十筐,女生五筐。在假期里,我也不睡懒觉,在晨曦中挎着粪筐,一杆粪叉操在手上,一路行走在有牲口经过的马路和村里的各条小路上。当看到一坨牛粪、马粪或者洋洋洒洒散落的驴粪球子,我都会视为黄金,觉得十分亲切,不由自主地冲上去“据为己有”。每天要打理拾到的一堆粪土,到了开学还要一筐一筐地交到生产队,这才算圆满完成任务。
上初中时,同学们都要学会“打煤糕”。因为每到冬天,各个教室、办公室都要烧炉子取暖。铁炉子烧炭火,火力旺,比较费炭。为了节省炭,就要“打煤糕”,把煤糕砸成块儿烧炉子。当年学校教室是平房,前面规划出一片空地,村里派车给学校拉若干的煤和黄土堆在这片空地上。班主任以小组为单位分配任务,各小组分头行动——男生作为主力,像和面一样,按照比例把煤和黄土和成不软不硬的煤泥,然后用铁锹把煤泥填到长方形的模具里;女生用铲子将煤泥抹平,像是做蛋糕一样,打成一块一块的煤糕。做完任务,还要让老师检查数量和质量,获得老师的好评后也是兴奋不已。接下来就是摆在太阳下暴晒几天,然后摞在教室后面备用,我们冬天的“温暖”就全靠这些煤糕了。
学生时代的劳动记忆犹新,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生命里,回想起来,都是满满的收获和美好,成为我宝贵的人生财富。
前不久,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将劳动课正式列入课程体系,劳动教育得以“升级”。希望劳动课真正在中小学落地开花,让我们的下一代牢固树立起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形成良好的劳动情感和劳动习惯,让劳动精神成为每个人的人生底色、奋斗源泉。